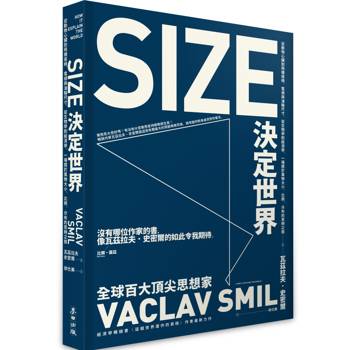IV 尺寸設計:好的、壞的、驚人的
(前略)
在大多數情形下,工程的歷史可視為不停尋求繞過物理限制的過程,透過引入新材料並且以新方法運用,但是到頭來,這些了不起的措施最後會面臨自己固有的限制。當然,人類的發明能力只是追隨演化的偉大例子,這些例子引入新的物質與結構,以應對原先棘手的需求。最值得注意的材料創新,包括:碳酸鈣構成的珊瑚骨骼,可以形成大片珊瑚礁;木質素是一種複雜的有機聚合物,大約占了所有樹幹組成分的四分之一;讓鳥類能夠飛翔的羽毛,就是由扭曲且交叉連結的蛋白質鏈組成的;人類的皮膚由於其中的膠原纖維能夠互相滑開,抗撕裂性(根據應力)可達15-21百萬帕斯卡(megapascal),相形之下,混凝土只有2-5百萬帕斯卡。
演化上的創新與調整例子可以寫成一大本書,顯然它們只能走到目前的地步,然後會有其他極限插手。例如最近的一項發現顯示,白堊紀的一種翼龍(大約生活於九千五百萬年前的Alanqua屬翼龍,有人稱為長生鳥翼龍)有非常輕的脊椎骨,建構的方式可以讓全身的骨骼質量變輕不少,甚至在挫曲負荷明顯增加時,仍然能以巨大飛獸(翼展有四到六公尺)之姿,抓起並帶走相當重的獵物,而不用擔心頸椎會受傷。 不具牙齒的翼龍當中,最大型的是諾氏風神翼龍(Quetzalcoatlus northropi),有堅硬的長頸,翼展最大可到長生鳥翼龍的兩倍,但是,歷經數百萬年的白堊紀演化過程,並未再出現任何在機械與結構上能夠產生更大飛獸的進展。
有別於那些滅絕已久的翼龍,樹的大小提供了一種容易驗證的例子。樹幹的木材是由纖維素(葡萄糖的天然聚合物)、半纖維素(也是天然聚合物,但是由低分子量的碳水化合物構成)、木質素(約占樹幹總質量的四分之一)組成。巨杉、花旗松、大王桉等最高的大樹可以長到110至125公尺高,但是樹不可能長得像曼哈頓的中等摩天大樓(200多公尺高)一樣高。 我們不能指向單一個限制因素:不論是力學(木質自立莖的負荷)與水力學(樹木裡水分的分布)的因素都限制了最終的高度,但是演化可能讓樹在生存與生殖方面最佳化,而非壽命與質量上的大小。
早在現代植物形態學家研究樹木的生長極限之前,伽利略(下一章討論縮放時,我會再來談他的觀察)在一六三八年的書《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裡面認識到,最高的樹木的高度不會超過140公尺,「我確定你們兩人都知道,一棵高達200庫比特(編注:cubit,古時量度單位,自肘至中指端,長約18-22英寸。)的橡樹無法支撐自己的枝條,如果這些枝條的分布就像在正常大小的樹上一樣。」
不可避免,這些演化極限會有似曾相識的熟悉情形發生在工程成果上。抗拉強度(每單位面積材料被拉斷所需的力)的比較結果,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摩天大樓可以蓋到遠遠高於五百公尺:以百萬帕斯卡來表示,鋼的抗拉強度是400-800,但是木材只有70-140。 目前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是哈里發塔,高度已經超過八百公尺。建造中的吉達塔預計會高達一公里(興建過程曾在二〇一八年中斷,但不是因為遇到技術問題);若採用有鏤空底座(類似艾菲爾鐵塔的設計)的扶壁核心地基,那麼還可能蓋出高出許多的建築。
這類建築的高度能夠超過兩公里,但是需要相當大的地基。以日本在一九九〇年代設計的一座4,000公尺高的建築(X-Seed 400,高度超越富士山)來說,鏤空地基會涵蓋大約1,000平方公里的面積(相當於邊長將近40公里〔譯注:細算應為31.6公里。〕的正方形,相較之下,東京有九百多萬民眾居住的二十三個人口稠密區,面積加起來還不到630平方公里)!顯而易見,除了建築材料的結構性質,還有其他因素會妨礙高度的發展。
如此廣闊的地基區如何讓自然光照射進去?這座結構裡需要多少空間安裝尚未發明的超級電梯(不只為了載人,還要運送食物與物資)?現有的電梯系統能抵達的高度不超過六百公尺,所以一英里高的建築需要搭兩次電梯才能到達頂層。或許最重要的是,施工時間必定漫長,誰會出資購買這項計畫需要的土地?對於私人投資者來說,前期資本的回報率會很糟糕,但是政府會參與興建這些規模不小的垂直市鎮嗎?而且,這種巨大結構的保險費會是多少?萬一發生火災或地震,該採取什麼措施,才能迅速撤離民眾?
這些財物、社會與組織上的挑戰,並非在追求超高建築物的過程獨有的;只要規模擴大受到限制時就會一再遇到挑戰,但這些限制不是指材料的性質,或者缺乏技術解決方案,而是投資回報減少、資金成本增加,以及彈性不足。妨礙成長的這類限制很常見,但是有三個例子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它們很重要。首先是原油的海運貿易,這種化石燃料使愈來愈多人的生活標準能夠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數十年內仍將是主要的能源(與最近想要消除化石碳的過度期望相反)。
石油的地位變得相當重要,是因為容易運輸且用途廣泛。中東地區(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儲油量特別豐富,因此輸出原油必須依賴大型油輪:最近的原油出口有三分之二是靠油輪載運的,其餘則透過油管輸出。 油輪大小的最佳表示方式是載重噸位(dwt),亦即船隻可以載運的總重量。最大型原油輪的尺寸增加情形,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約2萬載重噸,到一九五九年的10萬,到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30多萬。人們期望最終會出現100萬的船隻,但是目前為止的最大油輪,是一九七五年下水並在後來載重噸加大到56萬又4,650載重噸的海上巨人號。
那麼,為什麼我們從未建造出75萬或100萬載重噸的油輪?規模經濟推動油輪在二戰後的噸位增長趨勢,並沒有阻礙50萬載重噸油輪的問世(船隻愈大,每噸原油運送每單位距離的成本愈低),而且也沒有技術障礙:用來打造50萬載重噸船隻的施工方法,同樣能夠可靠打造等級更大的巨大油輪,我們可以裝上功率強大的柴油機,推動船隻航行成千上萬公里而不需靠岸。但正如我們一再看到,大小持續增加,伴隨而來的必然是投資回報率變小。當日本主導這個產業時,油輪載重從6萬公噸變成12萬公噸時,建造成本減少了30%,但是後來加倍成24萬公噸時,成本只省了15%,超過30萬載重噸的大小可能適得其反,由於這麼大的船隻運用彈性會受限。讓我解釋理由。
船愈大,吃水愈深(吃水是指水線到船底的距離),而這會限制船隻的航線與停靠港。只有為數不多的深水港,深度足夠容納吃水超過50萬載重噸船的超級大船,這些大船無法通過巴拿馬運河或蘇伊士運河,因為蘇伊士運河即使在拓寬之後,也只允許最大吃水20.1公尺與載重噸位20萬以下的船隻通過,而所謂的巴拿馬極限型船(Panamax ship,能夠通過巴拿馬運河的最大船隻)只能吃水12公尺,最大載重是6.5萬公噸。麻六甲海峽航線(從中東到遠東的最短海路)的最小水深是27公尺,只能讓載重噸位30萬以下的油輪經過。
顯然,巨大船舶在安排港口與航線的彈性很有限,營運風險也更大。在緊急情況下,這些船需要很長的距離才能停下來或轉頭(海上巨人號從最高速度到停止需要九公里,迴轉半徑大約是三公里)。大船的保險費也比較高,這件事在全世界兩大漏油災難發生後特別凸顯出來,一次是貝利韋爾城堡號一九八三年在南非漏油,另一次是埃克森瓦爾迪茲號一九八九年在阿拉斯加的事故。後面這場意外讓埃克森公司在清理費用、罰款、賠償方面花了七十億美元。
第一艘油輪在一八八六年下水,這種非凡機器在九十多年後停止成長,最新版本的船隻載重噸位已經是最初的一百多倍。那艘全世界最大的油輪後來怎麼了?一九八八年,海上巨人號在兩伊戰爭中遭到攻擊而損毀,然後重新命名為亞勒維京號,一九九一年再度下水,除役後又改名為諾克耐維斯號,改裝為卡達外海的儲存與卸載油駁船。二〇〇九年,這艘船賣給印度拆船業者,最後一次改名為蒙特號,駛向印度古加拉特邦阿朗的海灘,那裡是舊船的終點(也就是進行清艙,再拆解成廢鋼)。 法國也打造了四艘載重55.5萬公噸的巴替累斯級船舶(Batillus-class vessel),陸續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下水。這四艘船甚至更短命,有三艘在一九八六年以前成為廢料,最後一艘撐到二〇〇三年。 如同巨大的蜥腳類恐龍,巨大的油輪也從此消失了……
(前略)
在大多數情形下,工程的歷史可視為不停尋求繞過物理限制的過程,透過引入新材料並且以新方法運用,但是到頭來,這些了不起的措施最後會面臨自己固有的限制。當然,人類的發明能力只是追隨演化的偉大例子,這些例子引入新的物質與結構,以應對原先棘手的需求。最值得注意的材料創新,包括:碳酸鈣構成的珊瑚骨骼,可以形成大片珊瑚礁;木質素是一種複雜的有機聚合物,大約占了所有樹幹組成分的四分之一;讓鳥類能夠飛翔的羽毛,就是由扭曲且交叉連結的蛋白質鏈組成的;人類的皮膚由於其中的膠原纖維能夠互相滑開,抗撕裂性(根據應力)可達15-21百萬帕斯卡(megapascal),相形之下,混凝土只有2-5百萬帕斯卡。
演化上的創新與調整例子可以寫成一大本書,顯然它們只能走到目前的地步,然後會有其他極限插手。例如最近的一項發現顯示,白堊紀的一種翼龍(大約生活於九千五百萬年前的Alanqua屬翼龍,有人稱為長生鳥翼龍)有非常輕的脊椎骨,建構的方式可以讓全身的骨骼質量變輕不少,甚至在挫曲負荷明顯增加時,仍然能以巨大飛獸(翼展有四到六公尺)之姿,抓起並帶走相當重的獵物,而不用擔心頸椎會受傷。 不具牙齒的翼龍當中,最大型的是諾氏風神翼龍(Quetzalcoatlus northropi),有堅硬的長頸,翼展最大可到長生鳥翼龍的兩倍,但是,歷經數百萬年的白堊紀演化過程,並未再出現任何在機械與結構上能夠產生更大飛獸的進展。
有別於那些滅絕已久的翼龍,樹的大小提供了一種容易驗證的例子。樹幹的木材是由纖維素(葡萄糖的天然聚合物)、半纖維素(也是天然聚合物,但是由低分子量的碳水化合物構成)、木質素(約占樹幹總質量的四分之一)組成。巨杉、花旗松、大王桉等最高的大樹可以長到110至125公尺高,但是樹不可能長得像曼哈頓的中等摩天大樓(200多公尺高)一樣高。 我們不能指向單一個限制因素:不論是力學(木質自立莖的負荷)與水力學(樹木裡水分的分布)的因素都限制了最終的高度,但是演化可能讓樹在生存與生殖方面最佳化,而非壽命與質量上的大小。
早在現代植物形態學家研究樹木的生長極限之前,伽利略(下一章討論縮放時,我會再來談他的觀察)在一六三八年的書《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裡面認識到,最高的樹木的高度不會超過140公尺,「我確定你們兩人都知道,一棵高達200庫比特(編注:cubit,古時量度單位,自肘至中指端,長約18-22英寸。)的橡樹無法支撐自己的枝條,如果這些枝條的分布就像在正常大小的樹上一樣。」
不可避免,這些演化極限會有似曾相識的熟悉情形發生在工程成果上。抗拉強度(每單位面積材料被拉斷所需的力)的比較結果,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摩天大樓可以蓋到遠遠高於五百公尺:以百萬帕斯卡來表示,鋼的抗拉強度是400-800,但是木材只有70-140。 目前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是哈里發塔,高度已經超過八百公尺。建造中的吉達塔預計會高達一公里(興建過程曾在二〇一八年中斷,但不是因為遇到技術問題);若採用有鏤空底座(類似艾菲爾鐵塔的設計)的扶壁核心地基,那麼還可能蓋出高出許多的建築。
這類建築的高度能夠超過兩公里,但是需要相當大的地基。以日本在一九九〇年代設計的一座4,000公尺高的建築(X-Seed 400,高度超越富士山)來說,鏤空地基會涵蓋大約1,000平方公里的面積(相當於邊長將近40公里〔譯注:細算應為31.6公里。〕的正方形,相較之下,東京有九百多萬民眾居住的二十三個人口稠密區,面積加起來還不到630平方公里)!顯而易見,除了建築材料的結構性質,還有其他因素會妨礙高度的發展。
如此廣闊的地基區如何讓自然光照射進去?這座結構裡需要多少空間安裝尚未發明的超級電梯(不只為了載人,還要運送食物與物資)?現有的電梯系統能抵達的高度不超過六百公尺,所以一英里高的建築需要搭兩次電梯才能到達頂層。或許最重要的是,施工時間必定漫長,誰會出資購買這項計畫需要的土地?對於私人投資者來說,前期資本的回報率會很糟糕,但是政府會參與興建這些規模不小的垂直市鎮嗎?而且,這種巨大結構的保險費會是多少?萬一發生火災或地震,該採取什麼措施,才能迅速撤離民眾?
這些財物、社會與組織上的挑戰,並非在追求超高建築物的過程獨有的;只要規模擴大受到限制時就會一再遇到挑戰,但這些限制不是指材料的性質,或者缺乏技術解決方案,而是投資回報減少、資金成本增加,以及彈性不足。妨礙成長的這類限制很常見,但是有三個例子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它們很重要。首先是原油的海運貿易,這種化石燃料使愈來愈多人的生活標準能夠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數十年內仍將是主要的能源(與最近想要消除化石碳的過度期望相反)。
石油的地位變得相當重要,是因為容易運輸且用途廣泛。中東地區(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儲油量特別豐富,因此輸出原油必須依賴大型油輪:最近的原油出口有三分之二是靠油輪載運的,其餘則透過油管輸出。 油輪大小的最佳表示方式是載重噸位(dwt),亦即船隻可以載運的總重量。最大型原油輪的尺寸增加情形,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約2萬載重噸,到一九五九年的10萬,到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30多萬。人們期望最終會出現100萬的船隻,但是目前為止的最大油輪,是一九七五年下水並在後來載重噸加大到56萬又4,650載重噸的海上巨人號。
那麼,為什麼我們從未建造出75萬或100萬載重噸的油輪?規模經濟推動油輪在二戰後的噸位增長趨勢,並沒有阻礙50萬載重噸油輪的問世(船隻愈大,每噸原油運送每單位距離的成本愈低),而且也沒有技術障礙:用來打造50萬載重噸船隻的施工方法,同樣能夠可靠打造等級更大的巨大油輪,我們可以裝上功率強大的柴油機,推動船隻航行成千上萬公里而不需靠岸。但正如我們一再看到,大小持續增加,伴隨而來的必然是投資回報率變小。當日本主導這個產業時,油輪載重從6萬公噸變成12萬公噸時,建造成本減少了30%,但是後來加倍成24萬公噸時,成本只省了15%,超過30萬載重噸的大小可能適得其反,由於這麼大的船隻運用彈性會受限。讓我解釋理由。
船愈大,吃水愈深(吃水是指水線到船底的距離),而這會限制船隻的航線與停靠港。只有為數不多的深水港,深度足夠容納吃水超過50萬載重噸船的超級大船,這些大船無法通過巴拿馬運河或蘇伊士運河,因為蘇伊士運河即使在拓寬之後,也只允許最大吃水20.1公尺與載重噸位20萬以下的船隻通過,而所謂的巴拿馬極限型船(Panamax ship,能夠通過巴拿馬運河的最大船隻)只能吃水12公尺,最大載重是6.5萬公噸。麻六甲海峽航線(從中東到遠東的最短海路)的最小水深是27公尺,只能讓載重噸位30萬以下的油輪經過。
顯然,巨大船舶在安排港口與航線的彈性很有限,營運風險也更大。在緊急情況下,這些船需要很長的距離才能停下來或轉頭(海上巨人號從最高速度到停止需要九公里,迴轉半徑大約是三公里)。大船的保險費也比較高,這件事在全世界兩大漏油災難發生後特別凸顯出來,一次是貝利韋爾城堡號一九八三年在南非漏油,另一次是埃克森瓦爾迪茲號一九八九年在阿拉斯加的事故。後面這場意外讓埃克森公司在清理費用、罰款、賠償方面花了七十億美元。
第一艘油輪在一八八六年下水,這種非凡機器在九十多年後停止成長,最新版本的船隻載重噸位已經是最初的一百多倍。那艘全世界最大的油輪後來怎麼了?一九八八年,海上巨人號在兩伊戰爭中遭到攻擊而損毀,然後重新命名為亞勒維京號,一九九一年再度下水,除役後又改名為諾克耐維斯號,改裝為卡達外海的儲存與卸載油駁船。二〇〇九年,這艘船賣給印度拆船業者,最後一次改名為蒙特號,駛向印度古加拉特邦阿朗的海灘,那裡是舊船的終點(也就是進行清艙,再拆解成廢鋼)。 法國也打造了四艘載重55.5萬公噸的巴替累斯級船舶(Batillus-class vessel),陸續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下水。這四艘船甚至更短命,有三艘在一九八六年以前成為廢料,最後一艘撐到二〇〇三年。 如同巨大的蜥腳類恐龍,巨大的油輪也從此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