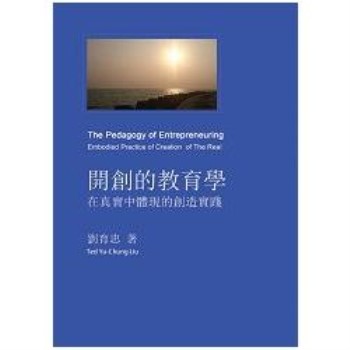第一章
導論:開創教育學的轉化
「真正的戰士不為爭取優勢或控制他人而戰。他們不為榮耀而戰,也不為財富或報酬,而是為了獲得唯一的真實,那就是自身的內在自由」
(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23)。
教育應該是朝向未來的,但不幸地,我們在教育過程中傳授給孩子的知識,卻常常傾向是過去的、封閉的歷史事實與已知的社會現實。不是已經被某種典範確證過的合法性知識,以為可以隨插隨用、具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性,就是某種經過抽象化過程,去除具體脈絡的概念性套裝知識。
固然,我們都明白,在規劃與選擇傳遞給下一世代的孩子(或者用大江健三郎的說法,「未來的孩子」)教育的內容時(而這恰恰就是我們對課程的一般性認識),我們必須仔細思考「什麼樣的知識是有價值的」,但回應這個問題的答案根源,卻常常不脫以下這幾個可能來源:主要的來源之一,是「權力」(power),或者用傅柯(Foucault)的說法叫做「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是由某種權力與其生產出的知識型構組而成的關係複合體。決定知識價值的主導評價系統,其實是來自握有權力的特定社會階層與文化立場的少數權威,並非是我們誤以為的、某種民主的共識與社會的普遍多數。知識社會學與課程社會學,一直努力地在這個面向著墨,企圖揭露課程裡頭主導的官方知識與某種通過建制與社會系統運作的「教育鍊金術」。
包裹著權力而呈現出不同表象的判斷來源,還可能是「歷史傳統」、「文化」與「現實」,分別以能否維繫特定族群的歷史傳統、人類整體文明成就與文化資產,以及提供現存社會與現實所需的專業培育與職場知能訓練連結,作為有價值的知識之判斷標準。在這樣的判斷標準之下教育過程所追求的「有價值的知識」,更往往忽略了認識主體的存在與變化,這就是傅柯(Foucault)與德勒茲(Deleuze)所強調的「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subjectivation)歷程:個體在這樣的歷程中成為什麼樣的人,成為什麼樣的主體。這使得,教育學在一味傳遞有價值知識的同時,容易忽視了教育裡頭的人的存在,只留下知識傳遞歷程的工具性思考與有效性的績效追求,使得教的人與學的人都異化為知識的客體而不是知識的主體,也讓教育學失去了活力與生命力。
教育學應該是屬於未來的一門學問,其活力與生命力就在於教育過程中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相遇與互動,在存在與真實之間的動態辯證與交引纏繞,發生於活生生的經驗與世界之上。
這樣的經驗,應該是奠基在「世界性真實」(worldly realities)之上。這意味的是,教育必須從人所居處棲居的世界出發,自人的置身所在(situatedness)所遭逢的那個主觀也是唯一能夠感覺的真實,作為主體認識經驗的起點,進行經驗的擴大與思想的顛覆,有的或許通過的是想像的同理與共感,但其著力與著眼之處,都是自身所必須直面應對、不容迴避的世界性真實。
延續過去與複製現在的教育學思考,強調的是如何延續既有的成功經驗與行為法則,以現存成功的主流思考模式與行為慣性,企圖讓進入教育過程的學習者能夠被生產為有用的、有價值的產品,在目前的社會職場上得以流通、暢銷。但現今我們面對的未來整體變化,已然是如此的巨大,且無跡可尋,我們唯一可以確認的事實是,未來的世界會與現在的世界迥異、截然不同,那麼一味還在教導過去世界與現有世界的成功經驗,就顯得有些不切實際,甚至有點緣木求魚。
也因此,我們似乎需要另一種的教育學,關注於未來的想像與創造,而且不能一直停留在想像層面的創意發想與遊戲自嗨,而必須是與真實具體接壤、對真實有所對應的具體作為,是在真實中體現的創造實踐,關於這樣的教育學想像,在本書中,即以「開創的教育學」來加以命名。
我想從底下的幾段引述來說明我所感受到的「開創教育學的轉化」的無可迴避。在一個意義上,本書即是在教育學的思考脈絡下,對此一轉化的回應,企圖有所行動並嘗試與之對話所裝配出來的,是以一本書的形式存在的暫時性構組。
第一段引述,來自<眾神的學校>(The Schools for Gods)這本書。書裡有這樣一段話:
「夢想才是那世界裡最真切的事物。你要學著在真實的世界裡生活,揮別以往的習慣、信念、準則,因為那些都不在適用。你所謂的真實只是個意象,現在該被顛覆了。別再被舊世界裡的事物所引導,因為你得學著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呼吸,去行動與愛...」(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23)。
宛如是對存在主義者Satre的著名命題「存在先於本質」的新版本詮釋,在該書裡,D’Anna大膽地給出了一個新的定義公式,來重新概念化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現實」:「現實=夢想+時間」(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134)。在D’Anna的說法裡,現實並非對立於夢想,而只是有了時間得以被實現出的夢想。也因此,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必須被顛覆,我們必須「學著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呼吸,去行動與愛」,才能夠真正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在一個意義上,對理解的嘗試顛覆,對「新的思考、呼吸、行動與愛」的方式的嘗試學習,或許就是開創最直白的意涵。大多數的學校,目的是在傳遞與建構關於真實的某些觀點與看法,但D’Anna所謂的「眾神的學校」,卻是為了顛覆、翻轉與轉變我們對世界與真實的既有觀點與看法,因而「是個使人轉變的學校........一所為眾神而設的學校........在那裏,人先學會管理自己,之後才懂得管理他人」(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60)。也因此,整個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成為自己的主人,撰寫自己的命運」(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65)。
這樣的學習觀與真實觀,自然也挑戰了我們傳統的「向外」的學習方向與知識進路,人不再是被理解為一個等待外在銘刻烙印的白板、某個資訊輸入儲存的罐頭容器,而是擁有豐富的內在宇宙,等候自我探尋的內世界,這讓學習的關注視線開始翻轉「往內」,從人的內在與存在作為開創的起點,產生新的學習路線與知識觀:「終有一天你會明白,從外在沒有任一物得以充實內在,對你已了知的事物,也無法再添加一絲一毫;教導與經驗,不能增加你的任何領悟,因為真正的知識只能被人『記住』。人的知識不可能比他的本質更大或更小,一定是恰好等量的。去瞭解,就等於去獲取.......你的本質越豐富,你的所知才會越豐富」(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62)。從這個角度來說,學習就如柏拉圖所說,基本上是一種「重新收集/回憶」(recollection),回憶起存在的本質、自我與他者、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弔詭的是, 關於這些,目前我們所認識的,卻恰恰可能是遺忘的結果。 對於人與世界、自我與存在的關係,向來是教育學最為核心也最為關注的議題。只是,這樣的關注在專業化與世俗化的工具性思維中,往往被化約成「勞動」與「工作」的準備,人往往淪為成遂某種目的的「手段」,忽略了人在這些活動中內在生命的狀態與變化,也忽略了存在的內在目的與價值。
漢納鄂蘭(H. Arendt)在她的名著<人之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曾經這樣說道:
「藉由言說和行動,我們讓自己切入人類世界,這種切入就像是某種第二次誕生,其中我們肯認並承擔起我們原初物理性外觀的這個赤裸事實。這種切入,不像是勞動,是以必要性強加在我們身上;也不是像是工作,用效益性來加以鼓吹;可能由我們希望參與陪伴的他者的現前所觸發,卻從不受到這些人左右;其動力來自於這樣的開端,在我們誕生時進入這個世界之時,以及我們通過自身開創開始的某件新事物做出的回應。行動,在其最普遍性的意義來說,意味的是,承擔某個開端、開始(如希臘詞archein所指的,『開始』、『引領』以及最終地『主宰』)、讓某種事物開始動作(這是拉丁文agere最原初的意義)......這種的開端與世界的肇始並不相同;這種開始不是關於事物的,而是關於人的,人是自身的開始者」(Arendt,1958/1998:176-179)。
漢納鄂蘭企圖以「勞動」、「工作」、「行動」三種基礎性的人類活動來掌握「生命活動」(vita activa)的根本,在漢納鄂蘭看來,這三種人類活動恰恰各自對應著人類在地球上直面著的不同基本處境。其中,「勞動」對應的人類處境就是「生命」本身,是人類肉體的生物歷程,由勞動餵養與生產生命歷程的根本必需。「工作」對應的是人類存在的非自然性面向,提供了一個由事物構成的人為世界,對應的人類處境就是「世界性」(worldliness)。而無需事物或物質的中介,直接對應著:棲居於世、處在人群之間這樣複數形的人類處境的生命活動就是「行動」。行動,直接回應的是處在眾生(multitude)之間的人類生命獨特處境;而人類的這種複數性,正是人類行動的基本條件:做為人,我們是相同的,但卻也沒有人能夠與任何一個人相同,無論是活過的人、還在世間的人、或是未來的人,這讓人類的生命處境基本上就是在「人間」,而是不是處在「人間」,更遠自古羅馬時期就被視為是「生」或「死」的同義詞(Arendt,1958/1998:7-8)。
也就是說,在人間的行動,已被理解為人存在與否的條件。通過行動,人創造了某種「開始」,也讓自身開始在人間存在,也因此行動,就本質上已然涵蓋有某種開創與創造的特性:行動必然給了某種「開始」,在行動中必然展現的創造性,也對「人間」給了新的可能。人是自身的開始者與人類世界的開創者,通過行動,我們因而可能有了不同的自己、世界與真實。
自我如何可能在自身存在、世界與真實之間發生開創的流變與斷裂,在鈴木俊隆(Shunryu Suzuki) <禪者的初心> (Zen Mind, Beginner’s Mind)這本書裡,有這樣的段落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中的可能性所在:
「在這個剎那,短暫的存在不會改變、不會移動,且總是獨立於其他的存在之外。在下一剎那,其他的存在就會生起,而你也可能會轉變成其他形相。嚴格來說,昨天的你和當下這個你是沒有關聯性的,一切與一切都是沒有關聯性的.......你是獨立的,我也是獨立的,各自存在于一個不同的剎那,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相當不同的存在,我們事實上是同樣的一回事。我們既相同,又相憶,這非常弔詭,但是事實就是如此。因為我們是獨立的存在,所以各自都是是浩瀚表象世界的一下雷閃」(Suzuki著,梁永安譯,2012:156-157)。
換言之,我們的存在其實是一個又一個短暫的剎那,在剎那與剎那之間存在的是斷裂,並不存在之間的連續性與關聯性。也因此,每一個剎那都是開始,都是獨立的存在,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都開創出新的開始,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若真如此,為何我們卻常感覺我們的生命與生活是不斷重複、僵化,了無新意呢?
或許,可能的原因就在於我們不再「不知道」,我們停留在某種「知道」中,停止了我們的「學習」。不再「學習」,所以只能一再重複我們的「知道」,而不再探索我們的不知道,開啟我們知識的疆域。所以,奧修(Osho)這樣說:
「愚蠢就是重複,重複別人的東西。愚蠢是廉價的,因為你不需要學習,所以它是廉價的。學習是費力的,一個人需要勇氣去學習,學習表示一個人必須是謙遜的,必須持續地準備好接受新的。學習指的是一個沒有自我的狀態。一個人從來不知道學習會帶領你去什麼地方,也無法對那個學習者有任何的預測;生命將一直是不可預測的,連他自己都不能預測明天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他明天會在什麼地方;他移入了一種不知道的狀態。一旦你活在不知道當中,一種持續不知道的狀態裡,你就是在學習」(Osho著,沈文玉譯,2002:223)。
也因此,真正的學習,其實是一種持續不斷地「不知道」,讓自己勇敢地一再進入「不知道」的狀態,探索自己既有知識版圖以外的寬廣天地,甚至顛覆自己原有的知識版圖。通過「開創」的轉化,召喚我們教育與學習的不同思考與想像:或許正如同D’Anna所說,學校必須重新「回到」顛覆我們既有想法與觀念那種的「眾神的學校」。真正的學習與知識始終必須回到存有的內在、人內在的開創性:
「為了改變,你必須奮鬥一生,接受引導,推翻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唯有如此,加上努力,才有辦法改變命運。不過,人類無法單獨做到這一點......你需要一所學校.......學校,意味著從群體性邁向完整性,從衝突到和諧,從奴役到自由的巨大飛躍.......尋找學校,表示要將你自己和『夢想』用鋼索結合起來......」(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57)。
上述這些信息,似乎正召喚著某種「開創教育學的轉化」,召喚我們嘗試用另外一個起點與預設,來重新思考我們的教育、我們的一切,因為「談論教育,就是談論一切」(Jean Paul,引自馮朝霖,2003)。
而這就是「開創的教育學」這本書的裝配起點。
在這本書中,我試圖從人間(inter-being)重新接引教育學開創動力,以「人間教育學」作為教育學知識重構的命題,重新回到教育學問題的發生處,以人間的教育學現場作為開創的倫理學關懷。尤其為了避免落入「為開創而開創」的工具理性的迴圈中,必須特別強調,所有的開創與創造仍然必須回到對人與人間的關懷與回應,站在某種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精神上,必須觀照到人類生命的根本生存處境,某種共存互依的共同體、棲居在某種眾生之間的世界性真實。
在關於人類生命的本體論理解上,本書主張採取流變的本體論立場,作為開創的存有論思考,來理解生命存有之流的不斷流變,並企圖通過當代歐陸哲學所關注的內在性、事件與流變等概念,作為我們思想開創的概念入口,以重構我們既有的本體論預設,增添新的語彙來掌握我們原有世界以外的真實多元性。
同時,為了開啟我們既有的知識疆界,回到鑲嵌在脈絡與內在經驗的知識與,在開創的認識論進路上,本書強調採用敘說來照見內在性的開創經驗,以捕捉人內在的難以言明的內部話語。由於開創必然是在真實之中,與既有世界的辯證對話,本書認為必須採取一種開創的實踐哲學想像,方能真正掌握重造世界性真實的開創實踐本質。
這就是為什麼本書以「在真實中體現的創造實踐」作為「開創的教育學」的註腳,因為唯有在世界之中,在人際之間,在真實裡的開創,才是真正從存有的內部進行顛覆與重構的學習的開始。
導論:開創教育學的轉化
「真正的戰士不為爭取優勢或控制他人而戰。他們不為榮耀而戰,也不為財富或報酬,而是為了獲得唯一的真實,那就是自身的內在自由」
(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23)。
教育應該是朝向未來的,但不幸地,我們在教育過程中傳授給孩子的知識,卻常常傾向是過去的、封閉的歷史事實與已知的社會現實。不是已經被某種典範確證過的合法性知識,以為可以隨插隨用、具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性,就是某種經過抽象化過程,去除具體脈絡的概念性套裝知識。
固然,我們都明白,在規劃與選擇傳遞給下一世代的孩子(或者用大江健三郎的說法,「未來的孩子」)教育的內容時(而這恰恰就是我們對課程的一般性認識),我們必須仔細思考「什麼樣的知識是有價值的」,但回應這個問題的答案根源,卻常常不脫以下這幾個可能來源:主要的來源之一,是「權力」(power),或者用傅柯(Foucault)的說法叫做「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是由某種權力與其生產出的知識型構組而成的關係複合體。決定知識價值的主導評價系統,其實是來自握有權力的特定社會階層與文化立場的少數權威,並非是我們誤以為的、某種民主的共識與社會的普遍多數。知識社會學與課程社會學,一直努力地在這個面向著墨,企圖揭露課程裡頭主導的官方知識與某種通過建制與社會系統運作的「教育鍊金術」。
包裹著權力而呈現出不同表象的判斷來源,還可能是「歷史傳統」、「文化」與「現實」,分別以能否維繫特定族群的歷史傳統、人類整體文明成就與文化資產,以及提供現存社會與現實所需的專業培育與職場知能訓練連結,作為有價值的知識之判斷標準。在這樣的判斷標準之下教育過程所追求的「有價值的知識」,更往往忽略了認識主體的存在與變化,這就是傅柯(Foucault)與德勒茲(Deleuze)所強調的「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subjectivation)歷程:個體在這樣的歷程中成為什麼樣的人,成為什麼樣的主體。這使得,教育學在一味傳遞有價值知識的同時,容易忽視了教育裡頭的人的存在,只留下知識傳遞歷程的工具性思考與有效性的績效追求,使得教的人與學的人都異化為知識的客體而不是知識的主體,也讓教育學失去了活力與生命力。
教育學應該是屬於未來的一門學問,其活力與生命力就在於教育過程中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相遇與互動,在存在與真實之間的動態辯證與交引纏繞,發生於活生生的經驗與世界之上。
這樣的經驗,應該是奠基在「世界性真實」(worldly realities)之上。這意味的是,教育必須從人所居處棲居的世界出發,自人的置身所在(situatedness)所遭逢的那個主觀也是唯一能夠感覺的真實,作為主體認識經驗的起點,進行經驗的擴大與思想的顛覆,有的或許通過的是想像的同理與共感,但其著力與著眼之處,都是自身所必須直面應對、不容迴避的世界性真實。
延續過去與複製現在的教育學思考,強調的是如何延續既有的成功經驗與行為法則,以現存成功的主流思考模式與行為慣性,企圖讓進入教育過程的學習者能夠被生產為有用的、有價值的產品,在目前的社會職場上得以流通、暢銷。但現今我們面對的未來整體變化,已然是如此的巨大,且無跡可尋,我們唯一可以確認的事實是,未來的世界會與現在的世界迥異、截然不同,那麼一味還在教導過去世界與現有世界的成功經驗,就顯得有些不切實際,甚至有點緣木求魚。
也因此,我們似乎需要另一種的教育學,關注於未來的想像與創造,而且不能一直停留在想像層面的創意發想與遊戲自嗨,而必須是與真實具體接壤、對真實有所對應的具體作為,是在真實中體現的創造實踐,關於這樣的教育學想像,在本書中,即以「開創的教育學」來加以命名。
我想從底下的幾段引述來說明我所感受到的「開創教育學的轉化」的無可迴避。在一個意義上,本書即是在教育學的思考脈絡下,對此一轉化的回應,企圖有所行動並嘗試與之對話所裝配出來的,是以一本書的形式存在的暫時性構組。
第一段引述,來自<眾神的學校>(The Schools for Gods)這本書。書裡有這樣一段話:
「夢想才是那世界裡最真切的事物。你要學著在真實的世界裡生活,揮別以往的習慣、信念、準則,因為那些都不在適用。你所謂的真實只是個意象,現在該被顛覆了。別再被舊世界裡的事物所引導,因為你得學著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呼吸,去行動與愛...」(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23)。
宛如是對存在主義者Satre的著名命題「存在先於本質」的新版本詮釋,在該書裡,D’Anna大膽地給出了一個新的定義公式,來重新概念化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現實」:「現實=夢想+時間」(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134)。在D’Anna的說法裡,現實並非對立於夢想,而只是有了時間得以被實現出的夢想。也因此,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必須被顛覆,我們必須「學著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呼吸,去行動與愛」,才能夠真正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在一個意義上,對理解的嘗試顛覆,對「新的思考、呼吸、行動與愛」的方式的嘗試學習,或許就是開創最直白的意涵。大多數的學校,目的是在傳遞與建構關於真實的某些觀點與看法,但D’Anna所謂的「眾神的學校」,卻是為了顛覆、翻轉與轉變我們對世界與真實的既有觀點與看法,因而「是個使人轉變的學校........一所為眾神而設的學校........在那裏,人先學會管理自己,之後才懂得管理他人」(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60)。也因此,整個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成為自己的主人,撰寫自己的命運」(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65)。
這樣的學習觀與真實觀,自然也挑戰了我們傳統的「向外」的學習方向與知識進路,人不再是被理解為一個等待外在銘刻烙印的白板、某個資訊輸入儲存的罐頭容器,而是擁有豐富的內在宇宙,等候自我探尋的內世界,這讓學習的關注視線開始翻轉「往內」,從人的內在與存在作為開創的起點,產生新的學習路線與知識觀:「終有一天你會明白,從外在沒有任一物得以充實內在,對你已了知的事物,也無法再添加一絲一毫;教導與經驗,不能增加你的任何領悟,因為真正的知識只能被人『記住』。人的知識不可能比他的本質更大或更小,一定是恰好等量的。去瞭解,就等於去獲取.......你的本質越豐富,你的所知才會越豐富」(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62)。從這個角度來說,學習就如柏拉圖所說,基本上是一種「重新收集/回憶」(recollection),回憶起存在的本質、自我與他者、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弔詭的是, 關於這些,目前我們所認識的,卻恰恰可能是遺忘的結果。 對於人與世界、自我與存在的關係,向來是教育學最為核心也最為關注的議題。只是,這樣的關注在專業化與世俗化的工具性思維中,往往被化約成「勞動」與「工作」的準備,人往往淪為成遂某種目的的「手段」,忽略了人在這些活動中內在生命的狀態與變化,也忽略了存在的內在目的與價值。
漢納鄂蘭(H. Arendt)在她的名著<人之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曾經這樣說道:
「藉由言說和行動,我們讓自己切入人類世界,這種切入就像是某種第二次誕生,其中我們肯認並承擔起我們原初物理性外觀的這個赤裸事實。這種切入,不像是勞動,是以必要性強加在我們身上;也不是像是工作,用效益性來加以鼓吹;可能由我們希望參與陪伴的他者的現前所觸發,卻從不受到這些人左右;其動力來自於這樣的開端,在我們誕生時進入這個世界之時,以及我們通過自身開創開始的某件新事物做出的回應。行動,在其最普遍性的意義來說,意味的是,承擔某個開端、開始(如希臘詞archein所指的,『開始』、『引領』以及最終地『主宰』)、讓某種事物開始動作(這是拉丁文agere最原初的意義)......這種的開端與世界的肇始並不相同;這種開始不是關於事物的,而是關於人的,人是自身的開始者」(Arendt,1958/1998:176-179)。
漢納鄂蘭企圖以「勞動」、「工作」、「行動」三種基礎性的人類活動來掌握「生命活動」(vita activa)的根本,在漢納鄂蘭看來,這三種人類活動恰恰各自對應著人類在地球上直面著的不同基本處境。其中,「勞動」對應的人類處境就是「生命」本身,是人類肉體的生物歷程,由勞動餵養與生產生命歷程的根本必需。「工作」對應的是人類存在的非自然性面向,提供了一個由事物構成的人為世界,對應的人類處境就是「世界性」(worldliness)。而無需事物或物質的中介,直接對應著:棲居於世、處在人群之間這樣複數形的人類處境的生命活動就是「行動」。行動,直接回應的是處在眾生(multitude)之間的人類生命獨特處境;而人類的這種複數性,正是人類行動的基本條件:做為人,我們是相同的,但卻也沒有人能夠與任何一個人相同,無論是活過的人、還在世間的人、或是未來的人,這讓人類的生命處境基本上就是在「人間」,而是不是處在「人間」,更遠自古羅馬時期就被視為是「生」或「死」的同義詞(Arendt,1958/1998:7-8)。
也就是說,在人間的行動,已被理解為人存在與否的條件。通過行動,人創造了某種「開始」,也讓自身開始在人間存在,也因此行動,就本質上已然涵蓋有某種開創與創造的特性:行動必然給了某種「開始」,在行動中必然展現的創造性,也對「人間」給了新的可能。人是自身的開始者與人類世界的開創者,通過行動,我們因而可能有了不同的自己、世界與真實。
自我如何可能在自身存在、世界與真實之間發生開創的流變與斷裂,在鈴木俊隆(Shunryu Suzuki) <禪者的初心> (Zen Mind, Beginner’s Mind)這本書裡,有這樣的段落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中的可能性所在:
「在這個剎那,短暫的存在不會改變、不會移動,且總是獨立於其他的存在之外。在下一剎那,其他的存在就會生起,而你也可能會轉變成其他形相。嚴格來說,昨天的你和當下這個你是沒有關聯性的,一切與一切都是沒有關聯性的.......你是獨立的,我也是獨立的,各自存在于一個不同的剎那,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相當不同的存在,我們事實上是同樣的一回事。我們既相同,又相憶,這非常弔詭,但是事實就是如此。因為我們是獨立的存在,所以各自都是是浩瀚表象世界的一下雷閃」(Suzuki著,梁永安譯,2012:156-157)。
換言之,我們的存在其實是一個又一個短暫的剎那,在剎那與剎那之間存在的是斷裂,並不存在之間的連續性與關聯性。也因此,每一個剎那都是開始,都是獨立的存在,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都開創出新的開始,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若真如此,為何我們卻常感覺我們的生命與生活是不斷重複、僵化,了無新意呢?
或許,可能的原因就在於我們不再「不知道」,我們停留在某種「知道」中,停止了我們的「學習」。不再「學習」,所以只能一再重複我們的「知道」,而不再探索我們的不知道,開啟我們知識的疆域。所以,奧修(Osho)這樣說:
「愚蠢就是重複,重複別人的東西。愚蠢是廉價的,因為你不需要學習,所以它是廉價的。學習是費力的,一個人需要勇氣去學習,學習表示一個人必須是謙遜的,必須持續地準備好接受新的。學習指的是一個沒有自我的狀態。一個人從來不知道學習會帶領你去什麼地方,也無法對那個學習者有任何的預測;生命將一直是不可預測的,連他自己都不能預測明天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他明天會在什麼地方;他移入了一種不知道的狀態。一旦你活在不知道當中,一種持續不知道的狀態裡,你就是在學習」(Osho著,沈文玉譯,2002:223)。
也因此,真正的學習,其實是一種持續不斷地「不知道」,讓自己勇敢地一再進入「不知道」的狀態,探索自己既有知識版圖以外的寬廣天地,甚至顛覆自己原有的知識版圖。通過「開創」的轉化,召喚我們教育與學習的不同思考與想像:或許正如同D’Anna所說,學校必須重新「回到」顛覆我們既有想法與觀念那種的「眾神的學校」。真正的學習與知識始終必須回到存有的內在、人內在的開創性:
「為了改變,你必須奮鬥一生,接受引導,推翻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唯有如此,加上努力,才有辦法改變命運。不過,人類無法單獨做到這一點......你需要一所學校.......學校,意味著從群體性邁向完整性,從衝突到和諧,從奴役到自由的巨大飛躍.......尋找學校,表示要將你自己和『夢想』用鋼索結合起來......」(D’Anna著,章澤儀譯,2009/2011:57)。
上述這些信息,似乎正召喚著某種「開創教育學的轉化」,召喚我們嘗試用另外一個起點與預設,來重新思考我們的教育、我們的一切,因為「談論教育,就是談論一切」(Jean Paul,引自馮朝霖,2003)。
而這就是「開創的教育學」這本書的裝配起點。
在這本書中,我試圖從人間(inter-being)重新接引教育學開創動力,以「人間教育學」作為教育學知識重構的命題,重新回到教育學問題的發生處,以人間的教育學現場作為開創的倫理學關懷。尤其為了避免落入「為開創而開創」的工具理性的迴圈中,必須特別強調,所有的開創與創造仍然必須回到對人與人間的關懷與回應,站在某種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精神上,必須觀照到人類生命的根本生存處境,某種共存互依的共同體、棲居在某種眾生之間的世界性真實。
在關於人類生命的本體論理解上,本書主張採取流變的本體論立場,作為開創的存有論思考,來理解生命存有之流的不斷流變,並企圖通過當代歐陸哲學所關注的內在性、事件與流變等概念,作為我們思想開創的概念入口,以重構我們既有的本體論預設,增添新的語彙來掌握我們原有世界以外的真實多元性。
同時,為了開啟我們既有的知識疆界,回到鑲嵌在脈絡與內在經驗的知識與,在開創的認識論進路上,本書強調採用敘說來照見內在性的開創經驗,以捕捉人內在的難以言明的內部話語。由於開創必然是在真實之中,與既有世界的辯證對話,本書認為必須採取一種開創的實踐哲學想像,方能真正掌握重造世界性真實的開創實踐本質。
這就是為什麼本書以「在真實中體現的創造實踐」作為「開創的教育學」的註腳,因為唯有在世界之中,在人際之間,在真實裡的開創,才是真正從存有的內部進行顛覆與重構的學習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