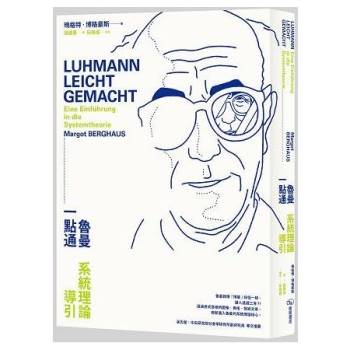第十四章 大眾媒體
一、具有特殊社會功能的傳播媒介
在我們討論過語言,書寫文字、印刷術與電子媒體等「傳播媒介」──所有這些都算是「溝通媒介」(試比較第八章第五節的媒介系統性整理)──之後,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大眾媒體」。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已經按照時代順序介紹過溝通媒介的演化。如今,這樣一個原則將被捨棄。因為大眾媒體絕對不是接續在上述這些媒介之後的下一個發展階段;這裡所要關注的,反而是另一個不同的角度與觀點:大眾媒體的特殊社會功能。
社會在它從早期的形式一直到現代的演化過程中,始終不斷持續分化,而且與此同時,還有許多諸如政治、經濟、法律、科學與藝術等次系統或者子系統或者「功能系統」逐漸形成,它們都是以自我生產的方式進行運作,並且執行特殊的功能。大眾媒體也屬於這些功能系統之一。大眾媒體建構出一個它自己的社會系統,一個現代社會的功能系統。
魯曼的研究興趣在於整體的社會理論。但是,為了檢測他的分析工具,他一個接著一個地在各個不同的次領域中進行操演。因此,諸如《社會的政治》、《社會的經濟》、《社會的法律》、《社會的科學》、《社會的藝術》等專書(試比較之前的第二章第二節)陸陸續續出現。大眾媒體對魯曼而言也是一個可供檢測的領域。他其實也可以將探討大眾媒體的專書命名為:《社會的大眾媒體》;但是,他卻將它命名為《大眾媒體的實在》(1996)。
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討論過的溝通媒介,包括語言、書寫文字、印刷術和電子媒體等等,都是一種媒介,但它們並不是系統;它們服務於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試比較之前的第十章第一節)。而且,它們是屬於大眾媒體的先決條件。唯有當魯曼提到分化出來的功能系統之時,他才會使用「大眾媒體」的概念(試比較1997,1098)。
那麼,現在大眾媒體所執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功能?《大眾媒體的實在》這本書的標題指出了一個核心的命題:大眾媒體的功能在於為全社會觀察與描述「實在」(Realität)。這本書中的第一句話如此表述:
「我們所知道的關於我們的社會、關於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一切,都是透過大眾媒體得知的。」(1996,9)
這樣一個句子相當聳動。魯曼的大眾媒體理論的核心,就像被包裹在一個核桃殼裡一般,包含在這個句子裡面。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準確地解讀這一個句子:我們關於社會與世界的知識來自於大眾媒體──這並非意味著,並沒有其他的知識存在。我們絕對知道某些出自一個除了媒體報導之外的「鄰近世界」(Nahwelt)──好比說,出自與其他人的直接對話,以及出自直接的經驗,例如說,「我給花澆過水了嗎?」──的東西。但是,這類的知識已經不再足夠;它們「僅只揭露出最小限度的(以書寫文字的形式,以及今日可以透過電視來獲得的)知識」(Luhmann in Hagen 2005,81及1997,826)。要由此衍生出必要的、關於社會與世界的認識,是不可能的。就後者這類的知識而言,我們必須仰賴大眾媒體──儘管有著各式各樣隱藏在其中的問題。根據魯曼的第一個句子,大眾媒體傳遞的正是這樣一種「見聞」(Wissen);這裡所要討論的,並不是「意見」(Meinen)的問題:媒體的目標並非在於「製造出一種具有共識的實在建構〔,而是在於生產出〕豐富大量的不同意見」(1996,126)。換句話說,這個句子裡頭同時也包含了這樣一個說法:媒體提供預先規定的見聞,是的,但並不是提供預先規定的意見。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對此做出詳盡的闡述。我們到目前為止根據一般性系統理論的概念──系統/環境、運作、溝通等等──所闡述過的,現在可以用大眾媒體的例子來做更具體的說明。好比說,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大眾媒體究竟是如何進行運作,它們根據什麼東西在它們的社會環境中做出選擇,它們在報導中置入了哪些區分?它們的運作方式對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第十四章至第十九章中,我們所要討論的核心在於「大眾媒體的實在」;其中,我們同樣也會援引《社會的社會》一書中的說明,並且根據不同的需要,援引魯曼其他的出版作品。
二、典型特徵:與大多數的溝通沒有互動
魯曼對於「大眾媒體」的定義如下:
「所有使用複製的技術手法來傳播溝通的社會設置,都應該被包含在大眾媒體的概念之中。我們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藉由印刷術所製成的書籍、雜誌、報紙;但是,我們也可以想到各式各樣攝影的或者電子的複製程序,只要它們是針對尚還無可確定的接收者來製造出大量的產物。即使是透過廣播來予以傳播的溝通,只要它是普遍可及的,也可以包含在這個概念之中。〔…〕
無論如何,這裡的重點在於:在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並沒有出現在場者之間的互動。」(1996,10 f)
科技(Technik)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技術設備創造出被包含在『大眾媒體』這個概念中的大眾的特徵:唯有透過機器,才有可能出現「複製程序」以及「大量的產物」、「複製」以及大量的「傳播」。這些大眾媒體的產物被傳送給「無可確定的接收者」,也就是說,它們並不允許以個別的方式被傳送,而是必須所有人都可以「普遍」、公開達及的。
大眾的特徵很重要,但並不是最主要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在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進行銜接的科技,阻礙了他們之間的互動。在魯曼的理論中,「互動」(Interaktion)一般意味著「在場者之間的接觸」(1997,814)。科技阻礙了互動;傳送者保持為傳送者,接收者保持為接收者。我們也可以將此稱為「單方面的」溝通。兩個主管單位──一方面是出版社、廣播電台與電視台,另一方面是讀者、聽眾、觀眾、公眾──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直接的進入管道。雖然讀者可以投書給報紙,聽眾和觀眾可以打電話和寫電子郵件給廣播電台與電視台,但這些都是例外,而且,即使他們找到了進入節目的入口,他們很明顯也是作為節目的一個組成部分,被整合進入節目之中。
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因為科技造成的接觸中斷,最早是從印刷的書寫文字開始,並且伴隨其持續發生。魯曼將此設定為他所定義的大眾媒體伴隨著印刷術的發明而開始出現的時間。口語溝通與手寫文字的溝通曾經是而且直到今日依然是直接的接觸,它們唯有透過直接的接觸才會成功。相對地,大眾溝通唯有透過接觸的中斷才會成功。
「正是印刷術如此大量地複製書寫文字產品,以致於所有溝通參與者之間的口語互動都被有效地且可見地排除出去。使用者充其量只有透過量化的方式:透過銷售數字,透過收視率,但並不是以抵制的方式,才能讓人察覺到自身的存在。這些讓使用者得以現身的量化數字,可以被標示出來並且被詮釋,但卻無法透過溝通被回送到使用者身上。」(1996,33 f)
換句話說,在大眾媒體的情況下,互動是絕對被排除出去的,但是,溝通卻絕對不會被排除出去。大眾媒體的過程就是溝通的過程。媒介系統的目的在於「傳播溝通」,它服務於「大眾溝通」(1996,10與13;試比較之前的第六章第五節)。在新聞學與溝通科學中,偶爾會出現一種觀點,認為「大眾溝通」的概念是一個畸形的概念,因為傳送者與公眾之間所進行的過程,因其片面性而不被允許標示為「溝通」。對此,魯曼有著另一種不同的看法。在這裡所發生的事情,與魯曼對於溝通的理解以及他對於溝通的定義完全吻合。如同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已經闡述過的一般,參與在溝通的三位元選擇過程中的主管單位,既可以是社會系統,也可以是個體。換句話說,他者/傳送者的角色可以好比說假定為一家出版社、一家電視台、整個媒體系統,或者也可以假定為一個單一的新聞記者;自我/接收者的角色則可以假定為一個公眾族群,或者一個單一的接收者。尤其是在大眾溝通的例子中,我們甚至可以更清楚且更完整地想像這三種選擇的過程(試比較之前的第六章與第七章,尤其是插圖6.1與插圖7.4)。
溝通,有的,互動,沒有──這界定出了什麼稱得上是大眾媒體,以及什麼稱不上是大眾媒體的界限:
◆書籍、報章雜誌、廣播電台以及電視台,都屬於大眾媒體,這非常顯而易見。
◆「互動電視」也屬於大眾媒體,雖然它的名字裡有著互動兩個字。因為「互動」在這裡所標示的,僅僅只是透過科技所擴展出來的使用功能,並不是傳送者與諸接收者們之間直接的互動。
◆相對地,網路並不屬於大眾媒體。魯曼在一次的訪談中提到:「網路並不是大眾媒體」。網路雖然廣為大眾使用,但是許許多多的直接互動發生在電子郵件、聊天室、論壇以及部落格中,這使得網路被排除在大眾媒體之外:
「即使網路被廣泛大量地使用為媒介,但是網路連同其溝通的可能性卻不是大眾媒體,因為它恰恰不是單方面的技術溝通,而是可以被個別使用的。」(Laurin 1997)
三、科技造成了接觸的中斷:接觸的中斷造就了系統
媒體提供者與公眾之間的直接互動,已經被居中介入的科技──印刷機器、錄音錄影裝置、複印和傳播裝置、傳送與接收設備等──所中斷。此所造成的後果影響深遠:首先,由於這樣的中斷,一個自己的、分化出來的大眾媒體功能系統得以產生;一個在魯曼的系統論意義上的系統,以自我生產的方式並且根據系統/環境的差異來進行運作。
「對於大眾媒體系統的分化而言,其決定性的成就可以說在於傳播技術的發明,這些技術不僅省下了在場者之間的互動,並且為了大眾媒體自己的溝通而將互動有效地排除出去。」(1996,33;文中粗體字的部分為瑪格特.博格豪斯所強調。)
那麼,假使傳送者/他者與接收者/自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直接接觸的話,將會發生什麼事?雙方都是自由的,不需要考慮到對直接的面對面做出反應。傳送者可以選擇、告知、印刷、書寫、言說訊息,指出他們想要什麼以及希望怎麼做。接收者同樣可以不受拘束地進行選擇、接收、修正、詮釋、批評或者甚至拒絕。當然,每一方都有他自己的選擇決策,可以根據另一方來進行調整,因為每一方基本上都對溝通能否實現抱有興趣;傳送者希望被閱讀、被傾聽、被看見,接收者希望可以閱讀、聽見、看見某些東西。媒體提供者因此必須建構和擴充一套縝密複雜的綱要裝置,建構和擴充各種範疇與類型、格式與標題、融資與銷售管道、人事與企業的組織,並且透過公眾研究與市場分析來守護這一切──簡短地說:發展出一個媒體─系統──,來確保他們的告知確實可以實現。
「根據計畫所進行的溝通能否成功,已經不再是仰賴於〔經由直接溝通來進行回送的過程〕。因此,在大眾媒體的領域中,一個自我生產的、自我再生產的系統得以產生。」(1996,34)
「一方面,由於直接接觸的中斷,溝通的高度自由獲得了確保。由此,產生了溝通可能性的過剩,唯有在系統內部透過自我組織以及透過系統自己的實在建構,這樣的過剩才可以獲得控制。另一方面,這裡有兩種選擇因素會產生作用:發送意願和收視興趣,這兩種因素並無法以中央統合的方式來予以協調。生產出大眾媒體溝通的組織,乃是仰賴在對於可期望性與可接受性的臆測上。這不僅導致了標準化的過程,同時也導致了其綱要的分化」。(1996,11 f)
環境指涉的中斷,乃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功能系統得以建立的先決條件,這並不是大眾媒體系統的特殊之處。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所有的社會溝通系統上,而且我們再一次重申,此一事態之所以發生,其背景在於社會的複雜性變得如此之高,以致於如今有許多特殊系統逐漸形成,來因應各種不同的功能。這裡一個普遍通用的公式是:「透過複雜性的化約來提升複雜性」(1997,507)。或者,如同在之前的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中所引述的:「複雜性的化約乃是提升複雜性的條件」(2002b,121)。具體而言:大眾媒體之所以能夠達成如此之多的成效,是因為它們可以充分劃定界限,專心致力於一個特殊的功能──實在的建構以及為社會做出社會的自我描述──上。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系統的分化,以及對環境指涉的斷絕,乃是確保界限,使系統得以建立自身複雜性的先決條件。」(1997,1350)
「透過複雜性的化約來提升複雜性」這個表面上看似弔詭的陳述,我們已經在魯曼的許多其他不同作品中,好比說,在關於媒介(並非:大眾媒體;試比較第八章第三節及第八章第四節)之成效的討論中碰到過:媒介(例如說,一場棋賽)藉由下述的方式來化約複雜性:棋賽規則僅容許在棋盤上走出某些特定的棋步,並且排除其他所有棋步。此外,媒介也經由在規則內激發創造出無限多種的遊戲變體,來擴展複雜性。
一、具有特殊社會功能的傳播媒介
在我們討論過語言,書寫文字、印刷術與電子媒體等「傳播媒介」──所有這些都算是「溝通媒介」(試比較第八章第五節的媒介系統性整理)──之後,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大眾媒體」。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已經按照時代順序介紹過溝通媒介的演化。如今,這樣一個原則將被捨棄。因為大眾媒體絕對不是接續在上述這些媒介之後的下一個發展階段;這裡所要關注的,反而是另一個不同的角度與觀點:大眾媒體的特殊社會功能。
社會在它從早期的形式一直到現代的演化過程中,始終不斷持續分化,而且與此同時,還有許多諸如政治、經濟、法律、科學與藝術等次系統或者子系統或者「功能系統」逐漸形成,它們都是以自我生產的方式進行運作,並且執行特殊的功能。大眾媒體也屬於這些功能系統之一。大眾媒體建構出一個它自己的社會系統,一個現代社會的功能系統。
魯曼的研究興趣在於整體的社會理論。但是,為了檢測他的分析工具,他一個接著一個地在各個不同的次領域中進行操演。因此,諸如《社會的政治》、《社會的經濟》、《社會的法律》、《社會的科學》、《社會的藝術》等專書(試比較之前的第二章第二節)陸陸續續出現。大眾媒體對魯曼而言也是一個可供檢測的領域。他其實也可以將探討大眾媒體的專書命名為:《社會的大眾媒體》;但是,他卻將它命名為《大眾媒體的實在》(1996)。
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討論過的溝通媒介,包括語言、書寫文字、印刷術和電子媒體等等,都是一種媒介,但它們並不是系統;它們服務於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試比較之前的第十章第一節)。而且,它們是屬於大眾媒體的先決條件。唯有當魯曼提到分化出來的功能系統之時,他才會使用「大眾媒體」的概念(試比較1997,1098)。
那麼,現在大眾媒體所執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功能?《大眾媒體的實在》這本書的標題指出了一個核心的命題:大眾媒體的功能在於為全社會觀察與描述「實在」(Realität)。這本書中的第一句話如此表述:
「我們所知道的關於我們的社會、關於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一切,都是透過大眾媒體得知的。」(1996,9)
這樣一個句子相當聳動。魯曼的大眾媒體理論的核心,就像被包裹在一個核桃殼裡一般,包含在這個句子裡面。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準確地解讀這一個句子:我們關於社會與世界的知識來自於大眾媒體──這並非意味著,並沒有其他的知識存在。我們絕對知道某些出自一個除了媒體報導之外的「鄰近世界」(Nahwelt)──好比說,出自與其他人的直接對話,以及出自直接的經驗,例如說,「我給花澆過水了嗎?」──的東西。但是,這類的知識已經不再足夠;它們「僅只揭露出最小限度的(以書寫文字的形式,以及今日可以透過電視來獲得的)知識」(Luhmann in Hagen 2005,81及1997,826)。要由此衍生出必要的、關於社會與世界的認識,是不可能的。就後者這類的知識而言,我們必須仰賴大眾媒體──儘管有著各式各樣隱藏在其中的問題。根據魯曼的第一個句子,大眾媒體傳遞的正是這樣一種「見聞」(Wissen);這裡所要討論的,並不是「意見」(Meinen)的問題:媒體的目標並非在於「製造出一種具有共識的實在建構〔,而是在於生產出〕豐富大量的不同意見」(1996,126)。換句話說,這個句子裡頭同時也包含了這樣一個說法:媒體提供預先規定的見聞,是的,但並不是提供預先規定的意見。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對此做出詳盡的闡述。我們到目前為止根據一般性系統理論的概念──系統/環境、運作、溝通等等──所闡述過的,現在可以用大眾媒體的例子來做更具體的說明。好比說,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大眾媒體究竟是如何進行運作,它們根據什麼東西在它們的社會環境中做出選擇,它們在報導中置入了哪些區分?它們的運作方式對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第十四章至第十九章中,我們所要討論的核心在於「大眾媒體的實在」;其中,我們同樣也會援引《社會的社會》一書中的說明,並且根據不同的需要,援引魯曼其他的出版作品。
二、典型特徵:與大多數的溝通沒有互動
魯曼對於「大眾媒體」的定義如下:
「所有使用複製的技術手法來傳播溝通的社會設置,都應該被包含在大眾媒體的概念之中。我們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藉由印刷術所製成的書籍、雜誌、報紙;但是,我們也可以想到各式各樣攝影的或者電子的複製程序,只要它們是針對尚還無可確定的接收者來製造出大量的產物。即使是透過廣播來予以傳播的溝通,只要它是普遍可及的,也可以包含在這個概念之中。〔…〕
無論如何,這裡的重點在於:在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並沒有出現在場者之間的互動。」(1996,10 f)
科技(Technik)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技術設備創造出被包含在『大眾媒體』這個概念中的大眾的特徵:唯有透過機器,才有可能出現「複製程序」以及「大量的產物」、「複製」以及大量的「傳播」。這些大眾媒體的產物被傳送給「無可確定的接收者」,也就是說,它們並不允許以個別的方式被傳送,而是必須所有人都可以「普遍」、公開達及的。
大眾的特徵很重要,但並不是最主要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在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進行銜接的科技,阻礙了他們之間的互動。在魯曼的理論中,「互動」(Interaktion)一般意味著「在場者之間的接觸」(1997,814)。科技阻礙了互動;傳送者保持為傳送者,接收者保持為接收者。我們也可以將此稱為「單方面的」溝通。兩個主管單位──一方面是出版社、廣播電台與電視台,另一方面是讀者、聽眾、觀眾、公眾──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直接的進入管道。雖然讀者可以投書給報紙,聽眾和觀眾可以打電話和寫電子郵件給廣播電台與電視台,但這些都是例外,而且,即使他們找到了進入節目的入口,他們很明顯也是作為節目的一個組成部分,被整合進入節目之中。
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因為科技造成的接觸中斷,最早是從印刷的書寫文字開始,並且伴隨其持續發生。魯曼將此設定為他所定義的大眾媒體伴隨著印刷術的發明而開始出現的時間。口語溝通與手寫文字的溝通曾經是而且直到今日依然是直接的接觸,它們唯有透過直接的接觸才會成功。相對地,大眾溝通唯有透過接觸的中斷才會成功。
「正是印刷術如此大量地複製書寫文字產品,以致於所有溝通參與者之間的口語互動都被有效地且可見地排除出去。使用者充其量只有透過量化的方式:透過銷售數字,透過收視率,但並不是以抵制的方式,才能讓人察覺到自身的存在。這些讓使用者得以現身的量化數字,可以被標示出來並且被詮釋,但卻無法透過溝通被回送到使用者身上。」(1996,33 f)
換句話說,在大眾媒體的情況下,互動是絕對被排除出去的,但是,溝通卻絕對不會被排除出去。大眾媒體的過程就是溝通的過程。媒介系統的目的在於「傳播溝通」,它服務於「大眾溝通」(1996,10與13;試比較之前的第六章第五節)。在新聞學與溝通科學中,偶爾會出現一種觀點,認為「大眾溝通」的概念是一個畸形的概念,因為傳送者與公眾之間所進行的過程,因其片面性而不被允許標示為「溝通」。對此,魯曼有著另一種不同的看法。在這裡所發生的事情,與魯曼對於溝通的理解以及他對於溝通的定義完全吻合。如同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已經闡述過的一般,參與在溝通的三位元選擇過程中的主管單位,既可以是社會系統,也可以是個體。換句話說,他者/傳送者的角色可以好比說假定為一家出版社、一家電視台、整個媒體系統,或者也可以假定為一個單一的新聞記者;自我/接收者的角色則可以假定為一個公眾族群,或者一個單一的接收者。尤其是在大眾溝通的例子中,我們甚至可以更清楚且更完整地想像這三種選擇的過程(試比較之前的第六章與第七章,尤其是插圖6.1與插圖7.4)。
溝通,有的,互動,沒有──這界定出了什麼稱得上是大眾媒體,以及什麼稱不上是大眾媒體的界限:
◆書籍、報章雜誌、廣播電台以及電視台,都屬於大眾媒體,這非常顯而易見。
◆「互動電視」也屬於大眾媒體,雖然它的名字裡有著互動兩個字。因為「互動」在這裡所標示的,僅僅只是透過科技所擴展出來的使用功能,並不是傳送者與諸接收者們之間直接的互動。
◆相對地,網路並不屬於大眾媒體。魯曼在一次的訪談中提到:「網路並不是大眾媒體」。網路雖然廣為大眾使用,但是許許多多的直接互動發生在電子郵件、聊天室、論壇以及部落格中,這使得網路被排除在大眾媒體之外:
「即使網路被廣泛大量地使用為媒介,但是網路連同其溝通的可能性卻不是大眾媒體,因為它恰恰不是單方面的技術溝通,而是可以被個別使用的。」(Laurin 1997)
三、科技造成了接觸的中斷:接觸的中斷造就了系統
媒體提供者與公眾之間的直接互動,已經被居中介入的科技──印刷機器、錄音錄影裝置、複印和傳播裝置、傳送與接收設備等──所中斷。此所造成的後果影響深遠:首先,由於這樣的中斷,一個自己的、分化出來的大眾媒體功能系統得以產生;一個在魯曼的系統論意義上的系統,以自我生產的方式並且根據系統/環境的差異來進行運作。
「對於大眾媒體系統的分化而言,其決定性的成就可以說在於傳播技術的發明,這些技術不僅省下了在場者之間的互動,並且為了大眾媒體自己的溝通而將互動有效地排除出去。」(1996,33;文中粗體字的部分為瑪格特.博格豪斯所強調。)
那麼,假使傳送者/他者與接收者/自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直接接觸的話,將會發生什麼事?雙方都是自由的,不需要考慮到對直接的面對面做出反應。傳送者可以選擇、告知、印刷、書寫、言說訊息,指出他們想要什麼以及希望怎麼做。接收者同樣可以不受拘束地進行選擇、接收、修正、詮釋、批評或者甚至拒絕。當然,每一方都有他自己的選擇決策,可以根據另一方來進行調整,因為每一方基本上都對溝通能否實現抱有興趣;傳送者希望被閱讀、被傾聽、被看見,接收者希望可以閱讀、聽見、看見某些東西。媒體提供者因此必須建構和擴充一套縝密複雜的綱要裝置,建構和擴充各種範疇與類型、格式與標題、融資與銷售管道、人事與企業的組織,並且透過公眾研究與市場分析來守護這一切──簡短地說:發展出一個媒體─系統──,來確保他們的告知確實可以實現。
「根據計畫所進行的溝通能否成功,已經不再是仰賴於〔經由直接溝通來進行回送的過程〕。因此,在大眾媒體的領域中,一個自我生產的、自我再生產的系統得以產生。」(1996,34)
「一方面,由於直接接觸的中斷,溝通的高度自由獲得了確保。由此,產生了溝通可能性的過剩,唯有在系統內部透過自我組織以及透過系統自己的實在建構,這樣的過剩才可以獲得控制。另一方面,這裡有兩種選擇因素會產生作用:發送意願和收視興趣,這兩種因素並無法以中央統合的方式來予以協調。生產出大眾媒體溝通的組織,乃是仰賴在對於可期望性與可接受性的臆測上。這不僅導致了標準化的過程,同時也導致了其綱要的分化」。(1996,11 f)
環境指涉的中斷,乃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功能系統得以建立的先決條件,這並不是大眾媒體系統的特殊之處。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所有的社會溝通系統上,而且我們再一次重申,此一事態之所以發生,其背景在於社會的複雜性變得如此之高,以致於如今有許多特殊系統逐漸形成,來因應各種不同的功能。這裡一個普遍通用的公式是:「透過複雜性的化約來提升複雜性」(1997,507)。或者,如同在之前的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中所引述的:「複雜性的化約乃是提升複雜性的條件」(2002b,121)。具體而言:大眾媒體之所以能夠達成如此之多的成效,是因為它們可以充分劃定界限,專心致力於一個特殊的功能──實在的建構以及為社會做出社會的自我描述──上。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系統的分化,以及對環境指涉的斷絕,乃是確保界限,使系統得以建立自身複雜性的先決條件。」(1997,1350)
「透過複雜性的化約來提升複雜性」這個表面上看似弔詭的陳述,我們已經在魯曼的許多其他不同作品中,好比說,在關於媒介(並非:大眾媒體;試比較第八章第三節及第八章第四節)之成效的討論中碰到過:媒介(例如說,一場棋賽)藉由下述的方式來化約複雜性:棋賽規則僅容許在棋盤上走出某些特定的棋步,並且排除其他所有棋步。此外,媒介也經由在規則內激發創造出無限多種的遊戲變體,來擴展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