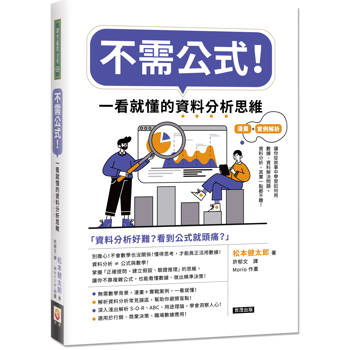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少子化問題相對嚴重的地方政府曾拿著「不結婚的理由」的調查結果來找我諮詢。
這項調查提出了「以下選項中,哪個是不結婚的理由」這個問題,選項包含了「沒機會認識新朋友」「收入不足」「父母親反對」「時間點不對」,其中最多人選擇的選項是「沒機會認識新朋友」。因此政府機關傾全力舉辦配對活動,但一開始沒什麼人參加,反應不太熱烈。
「明明是因為受測者說沒機會認識新朋友才舉辦配對活動的啊……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呢?到底該怎麼做才好?」負責人如此問我時,我心裡想的是「這麼做,當然會這樣啊……」乍看之下「沒機會認識新朋友」是最容易選擇,也最安全的選項,但背後或許藏著「戀愛很麻煩」「結婚制度很老派」「生了小孩,就會失去自由」「父母親或是親戚一直催生小孩很煩,所以討厭結婚」這類不想告訴別人、又很負面的「真心話」才對。如果有這些選項,或許調查結果就會改變。
換言之,有些資料必須將焦點放在人類的內心(原因),再不斷深入探討才能取得。像這樣傾聽這類「無聲之聲」,挖出原本看不見的資料,提出正確的提問,也屬於資料分析的一部分。
在行銷的世界裡,這種傾聽「無聲之聲」的手法稱為定性調查。
具體來說就是「透過詞彙與詞彙的意義了解、分析消費者的調查」「透過某些詞彙向消費者提出問題,或是傾聽消費者的意見後再進行分析的調查」。「詞彙」在這類調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順帶一提,傾聽「無聲之聲」的定性調查能夠察覺受測者是否「不自覺地說謊」。
定性調查的手法非常多元,例如「深度訪談」這種採訪者與受訪者一對一對話的調查手法,或是「民族誌」這種近距離觀察與記錄目標對象行動與環境的手法。之所以能察覺那些「生活過得很精緻」的回答只是在打腫臉充胖子,就是透過「民族誌」這種調查手法。
中島問光顧門市的顧客「為什麼不買蛋糕」其實也是一種定性調查,不過石田卻直接了當地說這是「蠢問題」。
這是因為人類能夠用語言形容的,只限於自己看得見的範圍,看不見的範圍就無法用語言形容。
比方說,有時候顧客會莫名買下某種商品,或買下感覺不怎麼樣的商品,此時若是問顧客:「為什麼買了那項商品?」「為什麼不買那項商品?」也問不出答案,無法聽到「無聲之聲」。
如果此時還一再追問「為什麼不買?」「為什麼會買?」對方就會被迫亂編理由,隨便回答一個答案,而這就是「不自覺地說謊」。
中島被石田問「為什麼不是穿XY 公司的西裝?」「為什麼領帶不是AB 公司的?」「為什麼留瀏海?」的時候,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哪有那麼多理由啊……」接下來就「無」話可說了。之所以只能說明「莫名地就⋯」的情況有無數多種。
如果費盡心思才想出無論如何都想買的東西、非常需要的東西、不得不買的東西,此時只要問對方為什麼購買,通常能夠得到理由。
不過,若只是依照慣性或是過去的經驗法則決定買或不買,恐怕就問不出理由。
春川被問到身上的衣服「是不是在門市或網路商店剛好看到,所以就買了」的時候,也是被問得啞口無言。所以真的很難具體回答這種無法具體描述的理由。
筆者認為,從行為經濟學者丹尼爾康納曼著作《快思慢想》中介紹到的「快思考與慢思考」,可以找到這些理由的線索。
所謂的快思考屬於不假思索與直覺的思考模式,也是憑藉著印象與聯想得出結論,根據習慣採取行動的狀態。
慢思考則屬於經過深思熟慮,符合邏輯,需要注意力,透過複雜的計算或邏輯導出答案的狀態。
我們很難隨時維持慢思考的狀態,大腦會因為過度運轉而疲勞,也會失去專注力,所以基本上大腦都是在捷思法這種快思考的狀態下做出決定。只有在「居然能讓本大爺認真起來啊……」的這種時候才會切換成慢思考的狀態。
這項調查提出了「以下選項中,哪個是不結婚的理由」這個問題,選項包含了「沒機會認識新朋友」「收入不足」「父母親反對」「時間點不對」,其中最多人選擇的選項是「沒機會認識新朋友」。因此政府機關傾全力舉辦配對活動,但一開始沒什麼人參加,反應不太熱烈。
「明明是因為受測者說沒機會認識新朋友才舉辦配對活動的啊……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呢?到底該怎麼做才好?」負責人如此問我時,我心裡想的是「這麼做,當然會這樣啊……」乍看之下「沒機會認識新朋友」是最容易選擇,也最安全的選項,但背後或許藏著「戀愛很麻煩」「結婚制度很老派」「生了小孩,就會失去自由」「父母親或是親戚一直催生小孩很煩,所以討厭結婚」這類不想告訴別人、又很負面的「真心話」才對。如果有這些選項,或許調查結果就會改變。
換言之,有些資料必須將焦點放在人類的內心(原因),再不斷深入探討才能取得。像這樣傾聽這類「無聲之聲」,挖出原本看不見的資料,提出正確的提問,也屬於資料分析的一部分。
在行銷的世界裡,這種傾聽「無聲之聲」的手法稱為定性調查。
具體來說就是「透過詞彙與詞彙的意義了解、分析消費者的調查」「透過某些詞彙向消費者提出問題,或是傾聽消費者的意見後再進行分析的調查」。「詞彙」在這類調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順帶一提,傾聽「無聲之聲」的定性調查能夠察覺受測者是否「不自覺地說謊」。
定性調查的手法非常多元,例如「深度訪談」這種採訪者與受訪者一對一對話的調查手法,或是「民族誌」這種近距離觀察與記錄目標對象行動與環境的手法。之所以能察覺那些「生活過得很精緻」的回答只是在打腫臉充胖子,就是透過「民族誌」這種調查手法。
中島問光顧門市的顧客「為什麼不買蛋糕」其實也是一種定性調查,不過石田卻直接了當地說這是「蠢問題」。
這是因為人類能夠用語言形容的,只限於自己看得見的範圍,看不見的範圍就無法用語言形容。
比方說,有時候顧客會莫名買下某種商品,或買下感覺不怎麼樣的商品,此時若是問顧客:「為什麼買了那項商品?」「為什麼不買那項商品?」也問不出答案,無法聽到「無聲之聲」。
如果此時還一再追問「為什麼不買?」「為什麼會買?」對方就會被迫亂編理由,隨便回答一個答案,而這就是「不自覺地說謊」。
中島被石田問「為什麼不是穿XY 公司的西裝?」「為什麼領帶不是AB 公司的?」「為什麼留瀏海?」的時候,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哪有那麼多理由啊……」接下來就「無」話可說了。之所以只能說明「莫名地就⋯」的情況有無數多種。
如果費盡心思才想出無論如何都想買的東西、非常需要的東西、不得不買的東西,此時只要問對方為什麼購買,通常能夠得到理由。
不過,若只是依照慣性或是過去的經驗法則決定買或不買,恐怕就問不出理由。
春川被問到身上的衣服「是不是在門市或網路商店剛好看到,所以就買了」的時候,也是被問得啞口無言。所以真的很難具體回答這種無法具體描述的理由。
筆者認為,從行為經濟學者丹尼爾康納曼著作《快思慢想》中介紹到的「快思考與慢思考」,可以找到這些理由的線索。
所謂的快思考屬於不假思索與直覺的思考模式,也是憑藉著印象與聯想得出結論,根據習慣採取行動的狀態。
慢思考則屬於經過深思熟慮,符合邏輯,需要注意力,透過複雜的計算或邏輯導出答案的狀態。
我們很難隨時維持慢思考的狀態,大腦會因為過度運轉而疲勞,也會失去專注力,所以基本上大腦都是在捷思法這種快思考的狀態下做出決定。只有在「居然能讓本大爺認真起來啊……」的這種時候才會切換成慢思考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