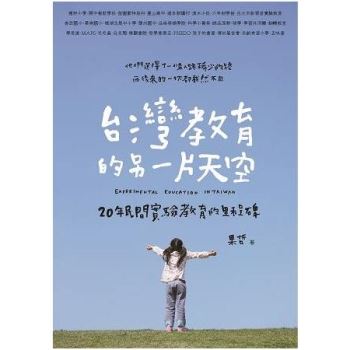〈新北種籽小學:資深教師團治校的實驗小學〉(摘文)
種籽的孩子,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自由選擇自己想上的課,必修課只有國語課、數學課、一週一次的生活討論課和六年級的畢業製作,其餘都是選修課和社團。學校教孩子如何做課程規劃,並建議孩子和家長一起討論。
單車教練永綸(Alan)的單車課,在種籽已經開了十多年,一週一次用兩堂課的時間,帶高年級的孩子去騎山路。「我平時就是看一下孩子的姿勢,」Alan很重視正確的運動觀念,「調整一下他們使力的方式。」遇到下雨天,就會在學校教孩子維修自行車,或教一些單車的機械原理,「我講解一些基本力學,身體的操控,比如說什麼姿勢最省力,是什麼原因;怎麼樣使力才不會造成運動傷害等等。」
每年的畢業挑戰,可以選騎單車或是登大山,如果那年投票結果是騎單車,四天三夜縱走花東公路,也就由Alan負責訓練。「騎公路很輕鬆啦!」Alan估計準備半年就可以培訓了,「平時我們在山區練習,相對困難得多了。」
除了單車社,種籽開過的社團真不少,還有許多是由家長開的社團:亂玩社、小農夫社、電影社、台語歌社、烹飪課、圖書世界和說故事時間等等。阿正開了一年的「造窯課」,為種籽留下了一個麵包窯,成為種籽特殊的景致。「麵包窯是由小孩做,大人輔導,每週一次,做了一年,整個學校都參與了。」阿正忙著跟輪流爬到背上的孩子玩過肩摔,「蓋窯的材料,有的上山找;有的花錢買;有的回收後再利用。」
讓孩子自由選課,對老師確實是個挑戰,也因此老師必須一直保持全力以赴的意志。種籽現任總顧問、政大教育系鄭同僚副教授認為,「老師需要將課程開得有趣、有意義,才能經得起選修門檻的考驗。吸引學生來修課,贏得孩子和家長的口碑,永遠是當老師向上的重要動力。」「空堂」課,讓孩子學到更多
大人習慣把孩子從小到大的每個空檔,都用上課安排得滿滿的,對於孩子可以擁有自己的空閒時間,通常會有不同程度的焦慮不安,倘若孩子有一堂課「無所事事」,像是大人的錯誤與失職。
種籽的孩子,在自己的空堂時間,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或者不想做什麼,大人不會自責,不會擔憂。空堂讓人恢復了自然呼吸,這種安詳的生活態度不但在種籽出現,並一直成功地進行著。種籽畢業生家長余庭妤說,「大人不會敲著一定節奏的鼓聲讓孩子齊步前進,尊重孩子的個別發展勝於一切,這也就是當年我們選擇種籽的最大原因。」
以阡媽媽講起孩子的空堂課:「六年級時,有畢業製作的目標,所以她會利用空堂,先約好和老師談自己的畢製。有時在生活中與同儕之間遇到難題,也會找導師談談,也和同學聊天,交流彼此的家庭以及對事情的看法;或一起解決問題、或在圖書館看書、有時想一個人獨處,不受干擾。」以阡甚至還利用空堂,學會了打桌球和跳舞。以阡媽媽說:「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師長為孩子精心安排規劃的空白時段,竟是豐富孩子生命的時段。」
自己的導師自己選
種籽的孩子可以自由選擇導師,每個孩子依序寫出自己選擇導師的四個志願,「孩子選擇導師,各種情況都有,」宜珮老師笑著說,「有從一而終的,有周遊列國的,還有團體行動的。」經教師團討論後,依孩子的性向需求,再做些調整。所以,同一個導師班上的孩子是混齡的,一到上課時間,孩子們就分頭進各自的課堂教室;同時兼具選課的自由,又保留了導師班的安全港口。
國生班的孩子,利用空堂合力做了一個郵箱,並製作郵票,最後還成立了郵局。國生最初的動機,是希望藉著寄信,來傳遞彼此的關懷。「我們全班有十二人」,全班總動員,一同參與這個班級活動,國生說:「有人專門幫我一起製作郵票;有人專門中午擺攤;有人另外負責週五蓋郵戳;有人負責送信;有人負責賣飛翔郵票;有人當會計——每個人的工作是依照自己的喜好。」目前已經出過的郵票圖案,有全體老師、校徽、種籽日的食物、畢業生、運動會項目、校外教學紀念事件等。正在發行的,是種籽校園常見的五種蛙類,「最初的想法是藉由一項工作,讓我們班上孩子的特性得以發揮。我們像是一起經營一種共同事業,其實也是一種靠近彼此的方式。」這樣混齡的導師班,是種籽重要的基石,導師對孩子的生活教育擔負起重責。「孩子需要導師陪伴他長大,」瑋寧說,「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必須做許多的抉擇;孩子在抉擇時,需要有人在旁邊和他進行合適的對話」。
導師是一座溝通的橋梁,他們建立起孩子的安全感,並與孩子充分的互動。孩子在「種籽法庭」接受判決之後,導師將接續對話與引導的工作。學科老師會把孩子的學習狀況詳細地和導師討論,導師也同時和家長保持充分與良好的交流。
躲在「祕密基地」吃著媽媽現煮的午餐
十二點整的鐘聲響過了,大家開始拿著自己的便當,到廚房去打飯。
「哇!今天的排骨蘿蔔湯,太讚了啦!我可以喝三碗嗎?」種籽的午餐,真是特別美味,因為學校的午餐都是由媽媽爸爸們輪流到學校替孩子們煮出來的!「嗯,咖哩雞好好吃,我還要再吃一碗。」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也能吃到這樣的午餐,家長就必須一個學期排定一日,輪流到學校來煮飯。當然,也可以選擇每天自己帶便當。
最初,因為有媽媽希望孩子能吃到現煮的飯菜,於是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傳統。由於一學期才輪一次,所以家長盡顯手藝,這裡的孩子可真有口福啊。
孩子們等到自己想吃飯時,才進廚房打菜,「我們不能收得太早,因為孩子們想吃飯的時間不一定,」亦樂媽媽說。如果超過中午一點,上課時間到了,還沒去吃怎麼辦?「那就要碰運氣囉,」亦樂媽媽手一攤,「如果沒剩的飯菜,就只能說抱歉了。」
種籽沒有整齊劃一的用餐時間、沒有禁語,老師不會要求孩子盯著時鐘把飯吃完;不為了方便大人而集體管理,也不搬古訓,連餐桌都不用。每個人可以有自己感覺飢餓的時間,自己走進廚房打飯吃。吃飯可以是一件沒有壓力、很輕鬆的事。
吃午飯是一個令人震撼的場景!到處都有人捧著碗吃飯:圖書館前走廊的「老人街」,老藤椅、舊沙發坐滿了聊天的師生,連桂花樹上也夾著幾個在吃便當的孩子。
「祕密基地」,當然也是一個享受午餐的好地方。種籽開放孩子申請自己的「祕密基地」,屬於私人領域,「外人」進入需要經過「基地」申請人同意。其實「基地」的申請,只需要用一張A4的紙,說明哪些是共同申請人,把基地的地點畫出來,領域範圍標清楚,不是學校規定的公共領域、不破壞自然生態,再經過老師同意,張貼在「基地布告欄」上,算是完成了公告,就可以擁有一學期的私人基地了。種籽法庭,生活教育的重要課程
今天中午,種籽的「法官團」要審理一個案件:阿吉把水龍頭開著不關,讓水流個不停。
「如果阿吉確實是像他所說的那樣,因為水龍頭有點故障不容易開,而他為了後面的孩子也可以用水,所以就乾脆讓它開著流」,在這個假設前提之下,大家開始推理分析,討論可能性,有人開始舉證推翻,阿全說:「但是水龍頭是不容易關,不是不能開呀。」「可是開的時候也有一點卡卡的,」家榮舉手發言。
不帶情緒成見,就事論事;大人和孩子,平等而認真的輪流發言,刨根究柢。過程中,沒有上對下的權威,只有依循已經養成的習慣,就是互相尊重,遵守發言規則,大家各自表達意見。
「生活討論課」是種籽的必修課,一週一堂,所有孩子聚在一起討論全校的事,有報告事項、心情時間、提案討論。提案討論可以是新訂校規或是修改舊規,比如新鞦韆的使用規則、在交通車上可不可以播放影片等等。由六年級的學生組成主席團,分擔主持、報告、記錄、搬椅子、管秩序等工作。如果說生活討論課像是在立法,那麼,若是有人違反大家制定的規則時,就會被告到種籽法庭這個司法單位。
中午十二點到一點的午餐時間,也同時是「法庭」的進行時間,所以小法官們都捧著便當盒,一邊吃一邊談。討論的過程,專注卻不嚴厲,認真但不緊繃。生活中,有嬉笑歡樂的時候,也有認真思考的時候。
經過討論後,法官對於可能產生這種行為的假設與研判,心中已經有譜。那麼,對於這樣的行為,應該做什麼判決呢?負責本案的法官徵求大家意見。
李維舉手說:「我可以計算出來,大概浪費了多少水,阿吉應該付多少水費。」安安舉手提了一個點子:「我建議,請他上水利局的網站,自己選一篇文章閱讀,然後寫一份心得報告交出來!」大家頻頻點頭同意。
法官團的學生,是由全校投票選出。每天的法官團由六、七位同學組成,一週五天,由不同的學生輪流,每天也輪兩位不同的老師,協助當日的法庭進行。前半場,先進行法官團的內部會議。如果有收到提告的狀子,當日要審理的案件,會先在內部會議討論,指導法庭的輪值老師,會協助提出各種可能性,讓法官們有更多思考及面對處理的準備。後半場,開庭審理,並開放旁聽席,全校師生都可以自由進場旁聽。有的狀子是學生告老師,也有老師告學生的狀子,統統一視同仁,人權平等。
有的時候,低年級的孩子要告高年級的孩子,或是比較內向的孩子提告,通常導師會坐在他的旁邊陪伴他,協助他陳述事情經過。弱勢者被保護並鼓勵發聲,學習嘗試勇敢面對強勢,爭取公平正義。經常要審理的案子,大都是生活裡的一些相處摩擦,「男生的方式,通常都比較直接,就是會你一拳我一腳的,」宜珮是資深的諮商老師,也擔任過早期校長,「女生就常常會夥同大家一起討厭、排擠某人。」而以種籽的標準,「這就已經接近霸凌了」!
種籽沒有霸凌的問題,「種籽重視人與人互動之間的學習,並不是因為種籽有法庭,而是在可能發生問題的跡象之初,老師就已經開始積極進行對談與處理,」瑋寧說:「如果單單模仿種籽法庭的操作形式,而不了解內涵,恐怕會徒勞而無益。」種籽小學對於人我之間的教學規劃縝密細緻,並環環相扣,最後在法庭這樣的場域中,綜合呈現出來。
由於種籽有空堂的設計,所以導師平時有足夠的時間,和孩子做充分的個別溝通。若是整日埋首於批作業、改考卷、趕進度、處理行政的老師,對於學生性格養成、生活行為與人際的問題,恐怕通常就沒有餘力了。為什麼法庭不厭其煩地去問告訴人或被告各種狀況?「『真實』很重要,是一個變動的狀態,不同角度會看見不一樣的真實,」將新任校長的婉如老師說:「『真實』是永遠需要練習去靠近;靠近需要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對話。」
無論是混齡導師班、空堂、各種活動、畢業挑戰或是校外教學,這裡的孩子有更多機會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從小就開始在碰撞中學習拿捏分寸。進入國中後的種籽畢業生光瑋認為,「和別的學校不同之處是,種籽畢業的孩子,有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這樣的教育成果,是教師們多年來不離不棄、細心耐性的陪著孩子們,走上正確的路。
集體領導的教師團治校
種籽教師團的穩定度,在體制外實驗教育的學校中十分少見。大部分的老師,在種籽都已經任教十幾二十年。
「一旦進入種籽這個工作環境之後,就不會想要離開,」前任校長瑋寧說出自己的感受,「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團隊。在這裡工作,你不會被拋棄,你會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大家會彼此互補互助,協助對方成長;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才會是個好老師。」所以,在這個與人為善的環境裡,老師也同步成長學習,並且也是收穫最多的人。一九九四年,種籽由一群關心教育的家長興學,當時的家長在創辦人李雅卿女士的號召下,在新店燕子湖畔創校,當時的校名是「毛毛蟲學苑」。一九九五年遷至烏來鄉信賢國小的現址,並且更名為「種籽親子實驗學苑」。依據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一九九四至二○○三年計畫主持人,是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二○○三年至今,計畫主持人交棒給政大教育系鄭同僚教授。
二○○四年種籽申請成為台北縣第一所政府委託民間辦理的小學,同時也正名為「台北縣政府委託民間辦理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國民小學」,簡稱「種籽實小」。從此以後,實行教師團辦校至今。雖然稱作公辦民營,但是縣政府並沒有撥款輔助學校經營。
種籽小學,不是由一人領導;教師團治校,可以相互取長補短,集合眾人之智慧與經驗,而不必受制於領導者的個人局限。但是,要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並長久配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校長經由董事會遴選,基本上由教師團輪流擔任,平均三年一任。學校教師之間合作無間,互相補位,共同分擔學校工作。學校的大小事,也是由校長在校務會議中提出討論,大家表決通過後才能執行。
那麼,除了接待外賓、對內聯繫之外,校長感到最憂煩的是些什麼問題呢?「我經常在想種籽的未來,」瑋寧思索著,「在目前教育的演變、法律的變更、少子化這些問題下,種籽該如何運作下去?」這些是對於外在變遷的思考。對學校內部則是:「種籽是不是一直走在自己堅持的路上?如何親師共學?親師懇談會如何和家長溝通?如何把家長的力量拉進來?」
老師AB嶠加入種籽時,他的「梅林」是宜珮老師。「『梅林』是從亞瑟王的傳說來的,梅林教會亞瑟王如何思考、解決問題,具備各種不同的能力。」種籽對於新進老師的培訓,教師團會共推一位資深老師當「梅林」,建議與陪伴新老師處理各種問題。
教師團有異動,請長假或離職,教室團就開始重新「走位」。走位的意思類似補位,依照教師的特質、個性與當時狀態,進行分工調整。二○一五年暑假的颱風蘇迪勒重創烏來山區,道路中斷,種籽被迫遷校一年。這一年中老師之間的完美默契,純熟的互相補位,讓流浪中的校長瑋寧深深地感慨,「從颱風遷校的這一年可看出來,這所學校老師之間的自動補位,真的逐漸成熟了」。教師會議固定每週開一次,前半場有一位家長代表參加開會,關於學校行政事務的討論,家長代表可以方便向家長會轉達。後半場「會小孩」時間,則僅由老師參與討論,對於個別小孩的特殊狀況,集思廣益,提出意見與看法。除了教師會議,另外還有教學會議,安排討論下學期要開的課程,以及每週一次的數學科小組會議,和兩週一次的語文科小組會議。
一個學校的教師團隊的實力,通常決定這個學校的教育執行力,因為,老師是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近二十年來,種籽集合教師群的經驗智慧與努力,累積傳承,經過不斷地縝密交織,才成為牢不可破的種籽教師團隊。
種籽踏實辦學二十三年來,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出了台灣本土教育實驗的路徑。然而,當實驗教育漸漸直接影響台灣教育環境;當這些衝在前鋒的教育場域正在提供台灣滋養、靈感和可能性;當樹漸漸成林,種籽卻依然要為了未定的校地煩惱著,沒有辦法獲得穩定的辦學空間和支援。
種籽的孩子,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自由選擇自己想上的課,必修課只有國語課、數學課、一週一次的生活討論課和六年級的畢業製作,其餘都是選修課和社團。學校教孩子如何做課程規劃,並建議孩子和家長一起討論。
單車教練永綸(Alan)的單車課,在種籽已經開了十多年,一週一次用兩堂課的時間,帶高年級的孩子去騎山路。「我平時就是看一下孩子的姿勢,」Alan很重視正確的運動觀念,「調整一下他們使力的方式。」遇到下雨天,就會在學校教孩子維修自行車,或教一些單車的機械原理,「我講解一些基本力學,身體的操控,比如說什麼姿勢最省力,是什麼原因;怎麼樣使力才不會造成運動傷害等等。」
每年的畢業挑戰,可以選騎單車或是登大山,如果那年投票結果是騎單車,四天三夜縱走花東公路,也就由Alan負責訓練。「騎公路很輕鬆啦!」Alan估計準備半年就可以培訓了,「平時我們在山區練習,相對困難得多了。」
除了單車社,種籽開過的社團真不少,還有許多是由家長開的社團:亂玩社、小農夫社、電影社、台語歌社、烹飪課、圖書世界和說故事時間等等。阿正開了一年的「造窯課」,為種籽留下了一個麵包窯,成為種籽特殊的景致。「麵包窯是由小孩做,大人輔導,每週一次,做了一年,整個學校都參與了。」阿正忙著跟輪流爬到背上的孩子玩過肩摔,「蓋窯的材料,有的上山找;有的花錢買;有的回收後再利用。」
讓孩子自由選課,對老師確實是個挑戰,也因此老師必須一直保持全力以赴的意志。種籽現任總顧問、政大教育系鄭同僚副教授認為,「老師需要將課程開得有趣、有意義,才能經得起選修門檻的考驗。吸引學生來修課,贏得孩子和家長的口碑,永遠是當老師向上的重要動力。」「空堂」課,讓孩子學到更多
大人習慣把孩子從小到大的每個空檔,都用上課安排得滿滿的,對於孩子可以擁有自己的空閒時間,通常會有不同程度的焦慮不安,倘若孩子有一堂課「無所事事」,像是大人的錯誤與失職。
種籽的孩子,在自己的空堂時間,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或者不想做什麼,大人不會自責,不會擔憂。空堂讓人恢復了自然呼吸,這種安詳的生活態度不但在種籽出現,並一直成功地進行著。種籽畢業生家長余庭妤說,「大人不會敲著一定節奏的鼓聲讓孩子齊步前進,尊重孩子的個別發展勝於一切,這也就是當年我們選擇種籽的最大原因。」
以阡媽媽講起孩子的空堂課:「六年級時,有畢業製作的目標,所以她會利用空堂,先約好和老師談自己的畢製。有時在生活中與同儕之間遇到難題,也會找導師談談,也和同學聊天,交流彼此的家庭以及對事情的看法;或一起解決問題、或在圖書館看書、有時想一個人獨處,不受干擾。」以阡甚至還利用空堂,學會了打桌球和跳舞。以阡媽媽說:「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師長為孩子精心安排規劃的空白時段,竟是豐富孩子生命的時段。」
自己的導師自己選
種籽的孩子可以自由選擇導師,每個孩子依序寫出自己選擇導師的四個志願,「孩子選擇導師,各種情況都有,」宜珮老師笑著說,「有從一而終的,有周遊列國的,還有團體行動的。」經教師團討論後,依孩子的性向需求,再做些調整。所以,同一個導師班上的孩子是混齡的,一到上課時間,孩子們就分頭進各自的課堂教室;同時兼具選課的自由,又保留了導師班的安全港口。
國生班的孩子,利用空堂合力做了一個郵箱,並製作郵票,最後還成立了郵局。國生最初的動機,是希望藉著寄信,來傳遞彼此的關懷。「我們全班有十二人」,全班總動員,一同參與這個班級活動,國生說:「有人專門幫我一起製作郵票;有人專門中午擺攤;有人另外負責週五蓋郵戳;有人負責送信;有人負責賣飛翔郵票;有人當會計——每個人的工作是依照自己的喜好。」目前已經出過的郵票圖案,有全體老師、校徽、種籽日的食物、畢業生、運動會項目、校外教學紀念事件等。正在發行的,是種籽校園常見的五種蛙類,「最初的想法是藉由一項工作,讓我們班上孩子的特性得以發揮。我們像是一起經營一種共同事業,其實也是一種靠近彼此的方式。」這樣混齡的導師班,是種籽重要的基石,導師對孩子的生活教育擔負起重責。「孩子需要導師陪伴他長大,」瑋寧說,「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必須做許多的抉擇;孩子在抉擇時,需要有人在旁邊和他進行合適的對話」。
導師是一座溝通的橋梁,他們建立起孩子的安全感,並與孩子充分的互動。孩子在「種籽法庭」接受判決之後,導師將接續對話與引導的工作。學科老師會把孩子的學習狀況詳細地和導師討論,導師也同時和家長保持充分與良好的交流。
躲在「祕密基地」吃著媽媽現煮的午餐
十二點整的鐘聲響過了,大家開始拿著自己的便當,到廚房去打飯。
「哇!今天的排骨蘿蔔湯,太讚了啦!我可以喝三碗嗎?」種籽的午餐,真是特別美味,因為學校的午餐都是由媽媽爸爸們輪流到學校替孩子們煮出來的!「嗯,咖哩雞好好吃,我還要再吃一碗。」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也能吃到這樣的午餐,家長就必須一個學期排定一日,輪流到學校來煮飯。當然,也可以選擇每天自己帶便當。
最初,因為有媽媽希望孩子能吃到現煮的飯菜,於是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傳統。由於一學期才輪一次,所以家長盡顯手藝,這裡的孩子可真有口福啊。
孩子們等到自己想吃飯時,才進廚房打菜,「我們不能收得太早,因為孩子們想吃飯的時間不一定,」亦樂媽媽說。如果超過中午一點,上課時間到了,還沒去吃怎麼辦?「那就要碰運氣囉,」亦樂媽媽手一攤,「如果沒剩的飯菜,就只能說抱歉了。」
種籽沒有整齊劃一的用餐時間、沒有禁語,老師不會要求孩子盯著時鐘把飯吃完;不為了方便大人而集體管理,也不搬古訓,連餐桌都不用。每個人可以有自己感覺飢餓的時間,自己走進廚房打飯吃。吃飯可以是一件沒有壓力、很輕鬆的事。
吃午飯是一個令人震撼的場景!到處都有人捧著碗吃飯:圖書館前走廊的「老人街」,老藤椅、舊沙發坐滿了聊天的師生,連桂花樹上也夾著幾個在吃便當的孩子。
「祕密基地」,當然也是一個享受午餐的好地方。種籽開放孩子申請自己的「祕密基地」,屬於私人領域,「外人」進入需要經過「基地」申請人同意。其實「基地」的申請,只需要用一張A4的紙,說明哪些是共同申請人,把基地的地點畫出來,領域範圍標清楚,不是學校規定的公共領域、不破壞自然生態,再經過老師同意,張貼在「基地布告欄」上,算是完成了公告,就可以擁有一學期的私人基地了。種籽法庭,生活教育的重要課程
今天中午,種籽的「法官團」要審理一個案件:阿吉把水龍頭開著不關,讓水流個不停。
「如果阿吉確實是像他所說的那樣,因為水龍頭有點故障不容易開,而他為了後面的孩子也可以用水,所以就乾脆讓它開著流」,在這個假設前提之下,大家開始推理分析,討論可能性,有人開始舉證推翻,阿全說:「但是水龍頭是不容易關,不是不能開呀。」「可是開的時候也有一點卡卡的,」家榮舉手發言。
不帶情緒成見,就事論事;大人和孩子,平等而認真的輪流發言,刨根究柢。過程中,沒有上對下的權威,只有依循已經養成的習慣,就是互相尊重,遵守發言規則,大家各自表達意見。
「生活討論課」是種籽的必修課,一週一堂,所有孩子聚在一起討論全校的事,有報告事項、心情時間、提案討論。提案討論可以是新訂校規或是修改舊規,比如新鞦韆的使用規則、在交通車上可不可以播放影片等等。由六年級的學生組成主席團,分擔主持、報告、記錄、搬椅子、管秩序等工作。如果說生活討論課像是在立法,那麼,若是有人違反大家制定的規則時,就會被告到種籽法庭這個司法單位。
中午十二點到一點的午餐時間,也同時是「法庭」的進行時間,所以小法官們都捧著便當盒,一邊吃一邊談。討論的過程,專注卻不嚴厲,認真但不緊繃。生活中,有嬉笑歡樂的時候,也有認真思考的時候。
經過討論後,法官對於可能產生這種行為的假設與研判,心中已經有譜。那麼,對於這樣的行為,應該做什麼判決呢?負責本案的法官徵求大家意見。
李維舉手說:「我可以計算出來,大概浪費了多少水,阿吉應該付多少水費。」安安舉手提了一個點子:「我建議,請他上水利局的網站,自己選一篇文章閱讀,然後寫一份心得報告交出來!」大家頻頻點頭同意。
法官團的學生,是由全校投票選出。每天的法官團由六、七位同學組成,一週五天,由不同的學生輪流,每天也輪兩位不同的老師,協助當日的法庭進行。前半場,先進行法官團的內部會議。如果有收到提告的狀子,當日要審理的案件,會先在內部會議討論,指導法庭的輪值老師,會協助提出各種可能性,讓法官們有更多思考及面對處理的準備。後半場,開庭審理,並開放旁聽席,全校師生都可以自由進場旁聽。有的狀子是學生告老師,也有老師告學生的狀子,統統一視同仁,人權平等。
有的時候,低年級的孩子要告高年級的孩子,或是比較內向的孩子提告,通常導師會坐在他的旁邊陪伴他,協助他陳述事情經過。弱勢者被保護並鼓勵發聲,學習嘗試勇敢面對強勢,爭取公平正義。經常要審理的案子,大都是生活裡的一些相處摩擦,「男生的方式,通常都比較直接,就是會你一拳我一腳的,」宜珮是資深的諮商老師,也擔任過早期校長,「女生就常常會夥同大家一起討厭、排擠某人。」而以種籽的標準,「這就已經接近霸凌了」!
種籽沒有霸凌的問題,「種籽重視人與人互動之間的學習,並不是因為種籽有法庭,而是在可能發生問題的跡象之初,老師就已經開始積極進行對談與處理,」瑋寧說:「如果單單模仿種籽法庭的操作形式,而不了解內涵,恐怕會徒勞而無益。」種籽小學對於人我之間的教學規劃縝密細緻,並環環相扣,最後在法庭這樣的場域中,綜合呈現出來。
由於種籽有空堂的設計,所以導師平時有足夠的時間,和孩子做充分的個別溝通。若是整日埋首於批作業、改考卷、趕進度、處理行政的老師,對於學生性格養成、生活行為與人際的問題,恐怕通常就沒有餘力了。為什麼法庭不厭其煩地去問告訴人或被告各種狀況?「『真實』很重要,是一個變動的狀態,不同角度會看見不一樣的真實,」將新任校長的婉如老師說:「『真實』是永遠需要練習去靠近;靠近需要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對話。」
無論是混齡導師班、空堂、各種活動、畢業挑戰或是校外教學,這裡的孩子有更多機會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從小就開始在碰撞中學習拿捏分寸。進入國中後的種籽畢業生光瑋認為,「和別的學校不同之處是,種籽畢業的孩子,有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這樣的教育成果,是教師們多年來不離不棄、細心耐性的陪著孩子們,走上正確的路。
集體領導的教師團治校
種籽教師團的穩定度,在體制外實驗教育的學校中十分少見。大部分的老師,在種籽都已經任教十幾二十年。
「一旦進入種籽這個工作環境之後,就不會想要離開,」前任校長瑋寧說出自己的感受,「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團隊。在這裡工作,你不會被拋棄,你會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大家會彼此互補互助,協助對方成長;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才會是個好老師。」所以,在這個與人為善的環境裡,老師也同步成長學習,並且也是收穫最多的人。一九九四年,種籽由一群關心教育的家長興學,當時的家長在創辦人李雅卿女士的號召下,在新店燕子湖畔創校,當時的校名是「毛毛蟲學苑」。一九九五年遷至烏來鄉信賢國小的現址,並且更名為「種籽親子實驗學苑」。依據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一九九四至二○○三年計畫主持人,是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二○○三年至今,計畫主持人交棒給政大教育系鄭同僚教授。
二○○四年種籽申請成為台北縣第一所政府委託民間辦理的小學,同時也正名為「台北縣政府委託民間辦理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國民小學」,簡稱「種籽實小」。從此以後,實行教師團辦校至今。雖然稱作公辦民營,但是縣政府並沒有撥款輔助學校經營。
種籽小學,不是由一人領導;教師團治校,可以相互取長補短,集合眾人之智慧與經驗,而不必受制於領導者的個人局限。但是,要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並長久配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校長經由董事會遴選,基本上由教師團輪流擔任,平均三年一任。學校教師之間合作無間,互相補位,共同分擔學校工作。學校的大小事,也是由校長在校務會議中提出討論,大家表決通過後才能執行。
那麼,除了接待外賓、對內聯繫之外,校長感到最憂煩的是些什麼問題呢?「我經常在想種籽的未來,」瑋寧思索著,「在目前教育的演變、法律的變更、少子化這些問題下,種籽該如何運作下去?」這些是對於外在變遷的思考。對學校內部則是:「種籽是不是一直走在自己堅持的路上?如何親師共學?親師懇談會如何和家長溝通?如何把家長的力量拉進來?」
老師AB嶠加入種籽時,他的「梅林」是宜珮老師。「『梅林』是從亞瑟王的傳說來的,梅林教會亞瑟王如何思考、解決問題,具備各種不同的能力。」種籽對於新進老師的培訓,教師團會共推一位資深老師當「梅林」,建議與陪伴新老師處理各種問題。
教師團有異動,請長假或離職,教室團就開始重新「走位」。走位的意思類似補位,依照教師的特質、個性與當時狀態,進行分工調整。二○一五年暑假的颱風蘇迪勒重創烏來山區,道路中斷,種籽被迫遷校一年。這一年中老師之間的完美默契,純熟的互相補位,讓流浪中的校長瑋寧深深地感慨,「從颱風遷校的這一年可看出來,這所學校老師之間的自動補位,真的逐漸成熟了」。教師會議固定每週開一次,前半場有一位家長代表參加開會,關於學校行政事務的討論,家長代表可以方便向家長會轉達。後半場「會小孩」時間,則僅由老師參與討論,對於個別小孩的特殊狀況,集思廣益,提出意見與看法。除了教師會議,另外還有教學會議,安排討論下學期要開的課程,以及每週一次的數學科小組會議,和兩週一次的語文科小組會議。
一個學校的教師團隊的實力,通常決定這個學校的教育執行力,因為,老師是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近二十年來,種籽集合教師群的經驗智慧與努力,累積傳承,經過不斷地縝密交織,才成為牢不可破的種籽教師團隊。
種籽踏實辦學二十三年來,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出了台灣本土教育實驗的路徑。然而,當實驗教育漸漸直接影響台灣教育環境;當這些衝在前鋒的教育場域正在提供台灣滋養、靈感和可能性;當樹漸漸成林,種籽卻依然要為了未定的校地煩惱著,沒有辦法獲得穩定的辦學空間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