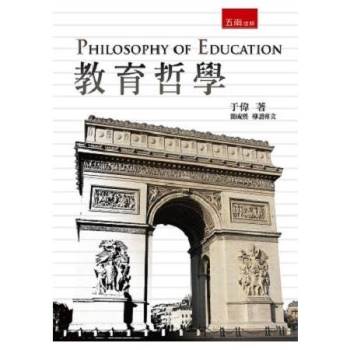台版序
一條大河波浪闊
一
儘管哲學的研究通常被設想為是一項需要在沉靜、寂寞的環境中進行艱苦反思的活動,但知識的生產者不可能“在孤獨中創作自己的作品,他們需要和同行進行辯論和討論,以形成自己的思想。” 這是路易斯•科塞(Lewis Coser)對現代“知識人”角色(科塞稱為“理念人”,Ideas of Man)的準確概括。回顧我自己的教育哲學生涯,學術年會在確保自己與同行之間保持定期的、“制度化”的交往方面至關重要。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哲學專業委員自1986年籌備、1988年成立以來,在黃濟先生、陸有銓先生的帶領下,已經召開了十七次學術年會(截至2016年8月)。正是在歷次的教育哲學年會上,我能有幸與黃濟、陸有銓、石中英、王坤慶、金生鈜、郝文武、陳建華、尚志遠等教育哲學領域內的前輩和同行交流、討論並結緣。也正是在學術年會上,我能夠第一次聆聽到來自海峽對岸的臺灣教育學者的“聲音”和想法。
事實上,我從很早之前就對臺灣教育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又與我在探索中國教育思想史中的學術志趣有密切關係。傳統的教育哲學史往往關注精英的、經典的、在場的、主流的教育思想,按照“大寫歷史”的方式進行“精英列隊”或“經典論述”,這就使得被權威和意識形態邊緣化的文獻資料很難納入研究者的視野。為此,我曾幾次赴台陸續搜集了百餘種臺灣教育哲學著作,它們構成了我感知、分析和勾勒臺灣教育哲學發展現狀的第一手文獻。此後,我又進一步結識了簡成熙、溫明麗、但昭偉、楊洲松、林逢祺、黃藿等臺灣教育哲學研究團隊的專家成員,在“文本”之外、與他們“面對面”地交流、探討兩岸教育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契機。2013年前後,我利用東北師範大學“東師學者”計畫“吸引和彙聚更多海外著名學者來東師講學,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的機會,陸續邀請簡成熙、但昭偉等教育哲學領域內的著名學者來東師講學,使青年教師、年輕學子也能與臺灣學者有當面交流、親聆教誨的機會;最後,我曾幾次赴台參觀、訪問,觀摩間隙也使我對臺灣教育哲學在學術傳統、研究團隊、學術建制和學科特色等方面的發展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二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又譯為布赫迪厄)曾在《自我分析綱要》中提醒人們,學術創作與個體習性、學術場和理論旨趣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因此,對我自己的學術經歷作一介紹和分析也是必要的。我自己的學術興趣主要聚焦在“現代性與教育”、“中國教育哲學百年學科史”和“兒童哲學探索”幾個方面。
我的學術訓練是從“現代性 與教育”這一論題開始的。儘管並不是刻意為之的,但這一論題在我開始撰寫的年代還尚屬時髦,這與時代的狀況密切相關。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及其文化領域出現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現象,它們都事關一種“現代性焦慮”(Anxiety)的不安情緒,一種被稱作“解毒劑”、並冠以“後現代主義”的思潮相繼在文學、藝術、哲學和教育等領域顛覆著人們的傳統觀念。從形式上看,後現代主義是一種與現代性迥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它強調否定性、非中心化、破壞性、反正統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多元性等特徵。如:利奧塔(Lyotard)在《後現代狀況》(1974)一書中寫道:“我把‘後現代’一詞定義為對元敘事的懷疑”;福柯(Foucault)提出對傳統“知識型”批判的觀點;德里達(Derrida)針對“邏各斯中心主義”進行徹底的批判並主張對現代一切文本運用“解構”策略;格裡芬(Griffin)則採取辯證否定的態度反思現代性等等。 這些批判性的觀點共同型構了人們在談論現代性時相互纏繞、眾說紛紜的後現代語境。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迎來政治經濟變革的同時也迎來了後現代思潮的拜訪。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國內學術界開始對我國教育理論研究進行反思、評價、批判。一是反對科學主義、本質主義,宣導反本質主義的教育觀;反對建立在傳統經典科學基礎上的所謂“原子教育學”,反對教育培養理性人、大寫的人,宣導培養遊戲人、生態人和小寫的人。宣導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量子教育學”;反對教育理論研究中的自然科學範式,宣導敘事研究和質化研究。二是反對理性主義教育觀。反對用傳統的認識論來研究教學過程,宣導教學中的體驗和感悟;宣導建構主義的知識觀,強調知識的建構性、社會性、情景性、複雜性和默會性;宣導研究性學習,反對接受式學習。第三,反對教師的權威,反對教師的主體性、主導性,呼喚生命教育觀;反對機器人教育觀。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上述批判性“話語”集中“爆發”的局面必然帶來如下問題:即如何揭示國外熱點思潮影響我國教育基本理論研究的內在機制、動力和途徑?如何為堅持和完善啟蒙運動以來所形成的現代性及其教育觀問題尋找出路?如何合理地審視後現代主義思潮在國內的教育改革和思想傳播中所發揮的作用?為回應上述議題,《現代性與教育》一書的主要論題與邏輯結構從“後現代語境中教育觀的現代性焦慮與哲學應答”這一主題出發,圍繞著現代性的核心理念,從理性、人類中心主義、科學及世俗性四個向度對教育觀的現代性焦慮及其哲學應答進行分析、梳理、論證。本書除關注上述核心議題外,同時也旨在回應如下問題:即在教育觀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爭論中,哪些新的社會文化現象被收進了我們的視野?按照這樣一種新的後現代主義認知範式,先前已形成共識的文化傳統又經過了怎樣的整合?哪些認識被推到了後臺,被淡化了;而哪些認識被移到了前臺,受到強調而突顯了出來?這些問題才是最為重要的。可是我們知道,這場爭論並沒有得出任何現成的結論,它只留下了卷帳浩繁、無異於一片渾濁的話語。因為它們各自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那麼的不相同,這些話語實際上不是處在同一個平面上,這就亟需我們對它們再進行一番梳理整合、總結評介的工作。
《現代性與教育》歷經醞釀十年,系統思考三年,寫作三月而成。雖屬“十年磨一劍”,但就本書的容量與我的功力相比,我仍深感時間苦短,論證粗而不精。不過在王逢賢先生的指導下,通過本書的寫作,我的最大收穫就是進一步澄清了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實現了我的哲學觀、教育觀的轉變。一是由抽象的人性論立場轉向了歷史唯物論,也就是由倫理主義轉向了歷史主義。我曾熱衷於從抽象的人性論和倫理主義出發宣導終極關懷,批判現代性及其教育觀的危機。二是由激進、偏激轉向了穩健和平和。由單純的思辨轉向了跨學科,尤其是吸收了經濟學、生物學和現代科學發展的前沿成果,改變了以往的論辯辭藻華麗而論證蒼白無力的狀況,少了烏托邦式的暢想與感悟,多了對中國現實的關注。 由此也引發了我在學術興趣上的略微轉移。
一條大河波浪闊
一
儘管哲學的研究通常被設想為是一項需要在沉靜、寂寞的環境中進行艱苦反思的活動,但知識的生產者不可能“在孤獨中創作自己的作品,他們需要和同行進行辯論和討論,以形成自己的思想。” 這是路易斯•科塞(Lewis Coser)對現代“知識人”角色(科塞稱為“理念人”,Ideas of Man)的準確概括。回顧我自己的教育哲學生涯,學術年會在確保自己與同行之間保持定期的、“制度化”的交往方面至關重要。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哲學專業委員自1986年籌備、1988年成立以來,在黃濟先生、陸有銓先生的帶領下,已經召開了十七次學術年會(截至2016年8月)。正是在歷次的教育哲學年會上,我能有幸與黃濟、陸有銓、石中英、王坤慶、金生鈜、郝文武、陳建華、尚志遠等教育哲學領域內的前輩和同行交流、討論並結緣。也正是在學術年會上,我能夠第一次聆聽到來自海峽對岸的臺灣教育學者的“聲音”和想法。
事實上,我從很早之前就對臺灣教育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又與我在探索中國教育思想史中的學術志趣有密切關係。傳統的教育哲學史往往關注精英的、經典的、在場的、主流的教育思想,按照“大寫歷史”的方式進行“精英列隊”或“經典論述”,這就使得被權威和意識形態邊緣化的文獻資料很難納入研究者的視野。為此,我曾幾次赴台陸續搜集了百餘種臺灣教育哲學著作,它們構成了我感知、分析和勾勒臺灣教育哲學發展現狀的第一手文獻。此後,我又進一步結識了簡成熙、溫明麗、但昭偉、楊洲松、林逢祺、黃藿等臺灣教育哲學研究團隊的專家成員,在“文本”之外、與他們“面對面”地交流、探討兩岸教育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契機。2013年前後,我利用東北師範大學“東師學者”計畫“吸引和彙聚更多海外著名學者來東師講學,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的機會,陸續邀請簡成熙、但昭偉等教育哲學領域內的著名學者來東師講學,使青年教師、年輕學子也能與臺灣學者有當面交流、親聆教誨的機會;最後,我曾幾次赴台參觀、訪問,觀摩間隙也使我對臺灣教育哲學在學術傳統、研究團隊、學術建制和學科特色等方面的發展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二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又譯為布赫迪厄)曾在《自我分析綱要》中提醒人們,學術創作與個體習性、學術場和理論旨趣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因此,對我自己的學術經歷作一介紹和分析也是必要的。我自己的學術興趣主要聚焦在“現代性與教育”、“中國教育哲學百年學科史”和“兒童哲學探索”幾個方面。
我的學術訓練是從“現代性 與教育”這一論題開始的。儘管並不是刻意為之的,但這一論題在我開始撰寫的年代還尚屬時髦,這與時代的狀況密切相關。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及其文化領域出現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現象,它們都事關一種“現代性焦慮”(Anxiety)的不安情緒,一種被稱作“解毒劑”、並冠以“後現代主義”的思潮相繼在文學、藝術、哲學和教育等領域顛覆著人們的傳統觀念。從形式上看,後現代主義是一種與現代性迥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它強調否定性、非中心化、破壞性、反正統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多元性等特徵。如:利奧塔(Lyotard)在《後現代狀況》(1974)一書中寫道:“我把‘後現代’一詞定義為對元敘事的懷疑”;福柯(Foucault)提出對傳統“知識型”批判的觀點;德里達(Derrida)針對“邏各斯中心主義”進行徹底的批判並主張對現代一切文本運用“解構”策略;格裡芬(Griffin)則採取辯證否定的態度反思現代性等等。 這些批判性的觀點共同型構了人們在談論現代性時相互纏繞、眾說紛紜的後現代語境。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迎來政治經濟變革的同時也迎來了後現代思潮的拜訪。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國內學術界開始對我國教育理論研究進行反思、評價、批判。一是反對科學主義、本質主義,宣導反本質主義的教育觀;反對建立在傳統經典科學基礎上的所謂“原子教育學”,反對教育培養理性人、大寫的人,宣導培養遊戲人、生態人和小寫的人。宣導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量子教育學”;反對教育理論研究中的自然科學範式,宣導敘事研究和質化研究。二是反對理性主義教育觀。反對用傳統的認識論來研究教學過程,宣導教學中的體驗和感悟;宣導建構主義的知識觀,強調知識的建構性、社會性、情景性、複雜性和默會性;宣導研究性學習,反對接受式學習。第三,反對教師的權威,反對教師的主體性、主導性,呼喚生命教育觀;反對機器人教育觀。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上述批判性“話語”集中“爆發”的局面必然帶來如下問題:即如何揭示國外熱點思潮影響我國教育基本理論研究的內在機制、動力和途徑?如何為堅持和完善啟蒙運動以來所形成的現代性及其教育觀問題尋找出路?如何合理地審視後現代主義思潮在國內的教育改革和思想傳播中所發揮的作用?為回應上述議題,《現代性與教育》一書的主要論題與邏輯結構從“後現代語境中教育觀的現代性焦慮與哲學應答”這一主題出發,圍繞著現代性的核心理念,從理性、人類中心主義、科學及世俗性四個向度對教育觀的現代性焦慮及其哲學應答進行分析、梳理、論證。本書除關注上述核心議題外,同時也旨在回應如下問題:即在教育觀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爭論中,哪些新的社會文化現象被收進了我們的視野?按照這樣一種新的後現代主義認知範式,先前已形成共識的文化傳統又經過了怎樣的整合?哪些認識被推到了後臺,被淡化了;而哪些認識被移到了前臺,受到強調而突顯了出來?這些問題才是最為重要的。可是我們知道,這場爭論並沒有得出任何現成的結論,它只留下了卷帳浩繁、無異於一片渾濁的話語。因為它們各自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那麼的不相同,這些話語實際上不是處在同一個平面上,這就亟需我們對它們再進行一番梳理整合、總結評介的工作。
《現代性與教育》歷經醞釀十年,系統思考三年,寫作三月而成。雖屬“十年磨一劍”,但就本書的容量與我的功力相比,我仍深感時間苦短,論證粗而不精。不過在王逢賢先生的指導下,通過本書的寫作,我的最大收穫就是進一步澄清了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實現了我的哲學觀、教育觀的轉變。一是由抽象的人性論立場轉向了歷史唯物論,也就是由倫理主義轉向了歷史主義。我曾熱衷於從抽象的人性論和倫理主義出發宣導終極關懷,批判現代性及其教育觀的危機。二是由激進、偏激轉向了穩健和平和。由單純的思辨轉向了跨學科,尤其是吸收了經濟學、生物學和現代科學發展的前沿成果,改變了以往的論辯辭藻華麗而論證蒼白無力的狀況,少了烏托邦式的暢想與感悟,多了對中國現實的關注。 由此也引發了我在學術興趣上的略微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