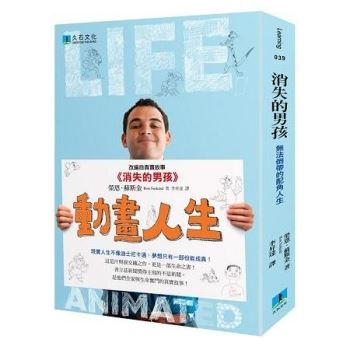1 倒帶
有捲錄影帶內容令我百思不解。
畫面中,一名蹣跚學步的孩子拿著玩具劍跑過落葉。影片顯示的時間為一九九三年十月。男孩跑起來就和一般兩歲半孩童一樣,橫衝直撞又搖搖晃晃,但這模樣很快就會消失了。因為身處二十世紀末影像充斥的年代,我們清楚事物應有的樣貌,能從千變萬化的世界得出各種結論,且多半準確無誤。男孩模樣天真,有著捲髮,身穿綠色燈芯絨褲和鮮艷的冬季外套;從樹的種類和地形可以推斷影片拍攝於美國東北;草木茂盛的庭院座落在略小的房子後頭,不過嶄新的鞦韆倒是精心打造,給人一種年輕父母刻意營造的氣象。男孩後頭追著一名稚氣的黑髮男子,男子手持短樹枝,笑著跪滑進落葉叢中,逼得男孩笑吟吟地轉身準備應戰。兩人劍棍相接,男子開口:「他才不是男孩,他是個會飛的惡魔!」他模仿的是迪士尼《小飛俠》(Peter Pan)裡的虎克船長,還算像樣。
男子和男孩高聲說著一部一九五三年動畫的台詞,透露了錄影機的普及。那是愛迪生發明電影攝影機一世紀以來,當時捕捉影音最新的電子技術。人們不必千里迢迢到電影院,只須放入錄影帶便能一看再看。當時迪士尼開始以錄影帶發行《小飛象》(Dumbo)、《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小飛俠》等經典動畫;嬰兒潮世代的父母可以買下曾經喜愛的電影,和孩子一同重新回味。此商機說明了為何會有這項人為產物:一捲錄影帶記錄著兩人高聲說著另一捲錄影帶的台詞。
現在從這些細節來談談普世的面向吧。這影片說到底似乎就只是父子在打鬧遊戲,然而這過程往往巧妙蘊含豐沛的情感:男孩一步步成為他天馬行空下的英雄;另一方面,爸爸思忖各種創意的死法,他內心深處明白,男孩有一天會長大,繼承他的一切。最後自然是男孩祭出他最厲害最優雅的突刺,男子應聲倒地,如同被壓碎的枯葉般一命嗚呼,隨後把咯咯笑的孩子攬在身上。
‧‧‧
這段平淡無奇但美好的影片裡,爸爸就是我,男孩則是我兒子。帶子我已看了上百遍,我的妻子也是,直到我們看不下去才作罷。
這是他最後的身影,無情地永遠記錄在磁帶上。
一個月後,畫面中的男孩消失了。她在嫁給我之前本名為柯妮莉亞.甘迺迪(Cornelia Kennedy),來自康乃狄克州一個愛爾蘭天主教的大家族。現在她姓蘇斯金(Suskind)。我是她的丈夫榮恩(Ron),來自德拉瓦州的猶太人。我們有兩個兒子,長子叫華特(Walt),今年五歲,是以在我還小便過世的父親命名的;我們的老么,也就是拿著泡棉玩具劍的男孩,名叫歐文(Owen)。片中有著茂盛花草庭院的房子是我們第一個家,位於麻薩諸塞州的戴德姆。我在《華爾街日報》波士頓分社工作了三年,接下來要搬到華府負責為該報報導國內新聞。那捲錄影帶是搬家卡車來的前一天拍的,那時我們仍安逸地生活在正常的國度。我從未多加思索「正常」這個詞,它是那種要以反義來解釋的詞,「不正常」更能突顯其義,如同圓圈是以圈外的東西來界定圓的輪廓。
‧‧‧
我們搬到華府幾個禮拜後,柯妮莉亞最先察覺到異狀,因為她天天陪著歐文。
有些事變得非常不對勁。
歐文情緒失控了。他會哭泣、到處亂跑、停下來後又繼續哭。停下喘口氣時,雙眼便呆滯地向前凝視。
除此之外,他就是直愣愣地看著柯妮莉亞。柯妮莉亞捧著他哭紅的臉頰問他怎麼了,但他似乎無法訴說。他從來不像哥哥那麼多話,但還算正常,總能隨口從已知的幾百個字彙湊成三個字來傳達需求和愛意,甚至是說則短笑話和故事。
我們搬進華府喬治城的租屋處後便處於忙亂的氛圍中:開箱、華特上新學校、身為父親的我則到嘈雜的大新聞社任職。因此,直到歐文會說的話只剩幾個字,大家才注意到他喪失了語言能力。自十一月搬完家後一個月,歐文變得只會說一個詞:果汁。
有時候,他卻不喝杯裡的東西,而且得用上鴨嘴訓練杯。近一年前,他原已進步到會用「大男孩杯子」了,但是搬到喬治城後,他開始會把東西灑出杯外,彷彿失去了方向感。的確是,他會不停旋轉、走路走得彎彎曲曲。因此,柯妮莉亞會坐在搖椅上儘可能摟住他,幾個月下來過得心驚膽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疏忽了什麼嗎?這有如檢視一樁綁票案的線索。記得有一次,是去年八月,我們到麻州南安普敦旅行,歐文整天哭個不停,而他從來不是那樣的愛哭鬼。十月底又有一次,那天搬家公司要將東西搬上車,一位摯友替我照顧孩子,他把小孩送回來時告訴我們歐文一直在睡。他仍在打盹,但是大半天都在睡?柯妮莉亞開箱時發現了一捲錄搬家當天拍的錄影帶。畫面為黃昏時分,華特帶頭巡視空了一半的房子,心情很愉悅,因為這是一趟到華府的遠行。他以最好的兩個朋友命名的金魚阿提和泰勒,已待在封好的球魚缸裡準備上路:「我的金魚也要一起去!」然後看一下歐文,他短暫出現在鏡頭上,睡眼惺忪輕聲地說:「這是我的嬰兒床還有我全部的東西。」
柯妮莉亞在同一個箱子裡找到另一捲叫「小飛俠鬥劍」的帶子。那天晚上我和她看了這捲帶子。這沒有道理啊,看看那孩子的動作,言談自如的模樣。我們倒帶又看了一遍,然後再一遍,尋找蛛絲馬跡。
時值十二月中,柯妮莉亞和歐文躺在他睡的下鋪,上鋪的華特很快就入睡了。書櫃上發亮的小魚缸嗡嗡作響,阿提和泰勒悄然游走在氣泡之間。此刻為凌晨三點,歐文翻來覆去,咕噥著難以理解的話。柯妮莉亞儘可能地抱緊他、安撫他。她在絕望的黑夜中開始禱告,含著淚對著她的孩子耳語,祈求上帝能夠聽見:「請幫幫我們。不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非常愛你,好好地愛你,我會抱著你直到這一切過去。」
‧‧‧
聖誕假期快到了,這個季節有許多要買的禮物,華府也因節慶活動熱鬧起來。
這理應是個充滿期盼的時刻。努力多年的人生規劃看似全都實現了。我和柯妮莉亞是在大學畢業後辦一場競選活動認識的。當時她坐在我的位置上看著我的法學院申請書,她說從內容看來我似乎不太想念法學院(沒錯),不過我的文筆不錯,應該考慮當個作家。那時她已是名年輕出眾的作家,而我聽完隨即愛上這個建議。我的父親四十六歲死於癌症前寫了封信給我和哥哥,懇求我們將生命用來做些「值得做的事」。新聞業似乎符合這份期待,挑戰權威、拼湊零碎真相、建立讀者群。後來我們輔選的候選人輸了,但我們倆開始交往。她在紐約的《人物》雜誌當記者,我則到了哥倫比亞新聞研究所唸書,畢業後在《紐約時報》當了兩年的新聞文書,而她則晉升為一名紐約雜誌的編輯;後來我在佛羅里達的《聖彼得堡時報》當了一年半的記者,我們就是在當地結婚的;然後我來到波士頓,當上一間小型商業雜誌社的編輯,接著一九九○年到《華爾街日報》波士頓分社任職,離公司不遠處就是波士頓老南聚會所。我還在牙牙學語時,便在布魯克林出身且極其自傲的母親督促下編撰故事了,甚至在父親過世後煎熬的歲月裡,還把這些故事編成了單口相聲橋段。不過年復一年,我一直在學習為該報招牌的頭版撰寫長篇報導。現在我被調到了華府專職撰寫報導,這是一份夢幻工作。
因此晚上時,我們將心思放在正面的事情上,談論著例如交到新朋友;替承租的三層樓聯邦式排屋買了價格理想的二手家具;也許有天會在鄰近社區買下房子等。但隨後柯妮莉亞百般不願地道出白天歐文又做了某件令人擔憂的事。「一切會好起來的。」我說道,接著試著找出合理的解釋:歐文正面臨一些苦痛,也許得了胃病,甚至是聽力受損,我們會搞清楚的。
「沒有孩子會失去已獲得的東西。人生不會倒帶。」
‧‧‧
小兒科醫生要求獨自觀察我們的兒子一會兒,他要我們坐在候診室,他想看看少了我們在旁,歐文如何與陌生人互動。由於孩子是沒有戒心的,他們會盯著陌生人看,充滿好奇心。他們就像小型吸塵器,不斷吸收各種訊息,也會與人目光交會,表達想法。這是孩子最起碼應有的樣子。
幾分鐘後,醫生把我們叫進他的看診室,告訴我們歐文並沒有這些表現。我們同意,這也是我們帶他過來的原因。柯妮莉亞簡短向醫生描述一直以來觀察到的狀況以及我們擔心之處,還有生活如何天翻地覆。
他聽完回道:「倘若一件事打亂家庭生活到這種地步,那肯定是個問題。」當小兒科醫生不確定病患的情況,尤其病患又是小孩時,他們會將之歸類為「母親的擔憂」。他說他要抽血做兩項基因檢測。一項是檢測X染色體脆折症,我們後來得知這是一種神經疾病,具可識別的遺傳標記,病徵相當可怕。另一項是檢測黑蒙性癡呆症,我知道這種疾病:它會造成嬰兒身心衰退,病童多於四歲前夭折,好發於東歐猶太裔人,也就是我的族裔。這疾病同大屠殺都是猶太學校裡會教的。後來醫生轉介我們到馬里蘭州羅克威爾一間醫療中心,也許到那會更有幫助。
時間來到二月,我們已坐在勞利嬰幼兒醫療中心(Reginald S. Lourie Center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的候診室。這裡的候診室環境截然不同,一旁便是遊戲室,從一面單面鏡能見到裡頭有彩色方塊、鞦韆、軟墊,孩子能在那玩耍,醫生則可從旁觀察。
我們被帶到一間看診室,等在裡頭的是一名表情嚴肅、身材高大的黑髮女人。她向歐文打招呼,柯妮莉亞無比堅定地牽著他的小手。在我們交談的診間裡有更多玩具,但歐文視而不見。幾分鐘後,她要歐文沿著長廊從我走向柯妮莉亞。我放開他的手,心想:「就這一次筆直好好走吧,就像在戴德姆時那樣。」但他沒有。他晃動雙手走著,倏地轉向又停下,走得曲曲折折,就像閉上雙眼在跑步一樣。柯妮莉亞把他抱了起來,然後我們回到了診間。女醫師表示:「他似乎罹患了廣泛性發展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會影響多數關鍵領域的發展。」又說道:「從他的步伐還有其他特徵可以明顯判斷。」她幾乎沒瞧上一眼坐在地上玩弄手指的歐文,並以冷冰冰的語氣繼續說道。我和柯妮莉亞彷彿從當下的情境中抽離飄浮在半空中,俯視著這對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雞又不時點頭的年輕夫妻,一旁那名孩子則認真在端詳自己的雙手。因此,她提到「自閉症」時,我並不是很清楚她說了什麼。
否認的力量是很強大的。幾年後,有位好友的父親,他是名年邁的精神科醫生,對我說了幾句饒富深意的話:「看重否認的力量,它存在是有道理的:它幫助我們面對無法接受的事物。」三十四歲的我並不看重它,甚至對它很陌生。
開車回家的路上,坐在後頭的歐文在他的汽車座椅上劇烈扭動,我和柯妮莉亞沉默不語。那女醫生一定搞錯了。我們對自閉症的看法就如同當今多數人。我們和所有國人一樣都看過《雨人》(Rain Man),這孩子不是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飾演的雷蒙.巴比特!一個月後,我們在貝賽斯達一間診所找到新的醫生:他是位年輕的小兒發展科醫生,長得和柯妮莉亞的高中老友出奇地像。我是在大學時認識那位朋友,當初也是他介紹我和柯妮莉亞認識的,這給人印象好多了。
艾倫.羅森布拉特(Alan Rosenblatt)醫生將歐文抱在腿上,極其溫柔地對他說:「嗨,小兄弟。」這一次歐文回頭了。他們做了些練習:讓歐文注視醫生移動的雙手並碰觸手指,接著兩人坐到地毯上,歐文似乎很自在。他們用積木蓋小房子,羅森布拉特先蓋了一個,想看歐文是否會接著蓋。
他並沒有,而兩人也沒有太多互動。隨後歐文站了起來開始亂走,羅森布拉特喚了他的名字,他便爬到椅子下看了醫生一眼,眼神似乎在說「來抓我啊」,示意要醫生追他,不過那表情閃現即逝。羅森布拉特草草在筆記板上記下些東西。
羅森布拉特回到坐位上後說道:「歐文恐怕有現今所謂的廣泛性發展障礙,或稱PDD,後頭還會加上縮寫NOS,表示『未分類的』(not otherwise specified)。」這代表歐文除了有「類自閉症的行為」,還有其他不符合典型自閉症範疇的表現,像是露出「來抓我」的神情。
他向我們完整講述了歐文的治療計畫,包括密集的語言治療、職能治療、遊戲治療,並建議我們應儘快展開。另外為了接下來的秋天作打算,他要我們立即找一間適合歐文的學校,也提供了一些建議學校。他說:「早期介入至關重要。」又提道:「有宗教信仰或加入宗教團體的家庭,這方面表現得比較好。」這段話令我們憂心眼前的災難,不過對天主教徒柯妮莉亞來說,宗教的確很快會是她尋求力量的依歸。
歐文沒被貼上「自閉症」的標籤讓我們鬆了口氣,因為照羅森布拉特的說法,歐文的毛病是種「遲緩」。我們後來更加了解到這些委婉語帶給我們的好處,其中一項重要的作用是:我們倆不會想再從診間跑走,開車回家時內心不會痛苦地像斷了四肢。
那一天是四月,前往停車場的路上,我們和羅森布拉特小聊了一下,言談中得知一件事,令我們對他所言更具信心。我們提到過去在波士頓看的小兒科醫生鮑伯.麥可斯(Bob Michaels),他畢業於哈佛,非常出色。羅森布拉特愣了一會,問道他是否來自匹茲堡。沒錯,我們興奮地回道,他是在匹茲堡長大的。「你問我認不認識麥可斯?他爸爸是我的小兒科醫生,很棒的醫生,他是我成為小兒科醫生的主因呢!」我們一到家便打給了人在哈佛的麥可斯醫生,告訴他這段奇遇,也很自然地向他解釋離開麻州後歐文的狀況。他要我們別掛電話,他去拿了歐文的病歷表,將病歷表瀏覽了一遍。「去年夏天我才替他檢查過,完全沒問題,我不懂怎麼會這樣。」
我們也不懂。沒錯,有地方出了差錯,但是連醫生也搞不清楚問題在哪。以羅森布拉特的話來說,歐文是「非典型的」案例,他的症狀屬於各類遲緩,能夠治好。那一晚我們如釋重負,睡得很安穩。我們能在每天睜開雙眼的每一刻拯救這孩子,令他重生!愚蠢。
‧‧‧
隔天早上,柯妮莉亞牽著歐文、帶著華特從我們喬治城的家出發,沿著門前的街道走過七個路口來到海德國小。華特在校很活躍,除了開學日在朝會上以吹口琴的方式報到有點脫序外,他很喜歡學校生活和交朋友;玩樂、學習、成長。那天把華特送到學校後,柯妮莉亞帶著歐文與一小群家長碰了面。海德國小的規模雖不比華府西北區其他小學,但是海德一直致力於跟上他校的腳步。就在這天早晨的茶會上,大家討論著如何籌辦即將到來的海德春季園遊會,這活動應該能為學校募得不少資金。身為園遊會共同主委的柯妮莉亞,則一直忙著整合贊助人、物資之類的事。
一切的努力就是為了讓五月初的園遊日,也就是兩個禮拜後的星期六,成為一個新來乍到家庭的大日子。當天還不到中午,學校旁圍著柵欄的遊樂場已快擠滿了人,設施管理員急忙為氣墊遊樂場打氣。這感覺正是我們所嚮往的華府,應該也是每個人所憧憬的:有快樂的戰士相伴,打造一個充滿歡樂和食物的小小王國,大批親子人馬齊聚於此,為美好的目的歡慶。
當然,我們一直很用心安排讓歐文能與我們一同參加園遊會。進出遊樂場只有一道門,由認識歐文的志工家長把關,他們會提防歐文溜出去;其實只要想到我和柯妮莉亞在他身旁寸步不離,這根本不是問題。幾個小時下來,園遊會忙亂的氣氛時起時落:多點冰塊!有誰知道電源開關在哪裡?熱狗沒有了!而我們的確與歐文形影不離。事情確切發生的時間點已不可考,總之,罪魁禍首是身為爸爸的我,因為全天下的媽媽大概從宇宙大爆炸開始,就內建了一種神經裝置,能立即定位子女的座標。傍晚時分,我放開了歐文的手,好將歐文午餐吃剩的半根熱狗塞到我嘴裡,並拿起放在地上的可樂罐。我一回頭,左手邊一英尺遠鋪著碎石的鞦韆場,剛才歐文待的地方已空無一人。
爸爸也有應付這種情況的配備,不過電路啟動的方式不同。原則一:別慌。冷靜迅速環視四週:九十度、一百八十、二百七十、三百六十。
原則二,開始慌張!我先是快步走,後來快跑至大門詢問門旁的一位父親:「你有沒有看到他,歐文有沒有溜出去?」想不到一個奔跑的男人竟能引起這麼多注意,我這一回頭,後面已跟了一小群家長,帶頭的是柯妮莉亞。
我不必說明歐文走丟了,她看得出來,所以我直接切入重點。「三十秒前我和他還在鞦韆那,他沒出大門!」
幸好園遊會已經進入尾聲,擋住視線的人群較少。然而五分鐘後仍遍尋不著他的下落。我和柯妮莉亞跑得氣喘吁吁,兩人內心拼命壓抑一段共同的回憶:一年前在我們麻州家附近的衛斯理,歐文曾在校園園遊會上走失一下子。我們當時以為就是一起兩歲孩子走失記。這是有可能的,只是頻率不會這麼高。走丟的孩子至少會有一絲分離焦慮,這有助於媽媽的雷達定位,而且他們會逐漸意識到父母不在身旁。此時他們發覺自己走失了,便開始哭泣。無論歐文是否具有這樣的配備,現在肯定是關掉了,更何況我們不在草木蔥鬱的衛斯理,這裡是喬治城,我們身處一片圍著柵欄的水泥地,外頭車子在鋪著鵝卵石的O街上穿梭,疾馳至半個街區外的威斯康辛大道,那可是華府的主要幹道。
十分鐘後恐慌蔓延開來,許多家長開始散開到街上找人,我和柯妮莉亞則跑進了學校。雖然園遊會期間禁止進入校區,但有道門為了供電源線通過是開著的。校舍是一棟世紀之交落成的方形磚房,宏偉空蕩,屋頂的簷口已剝蝕,屋內有兩條走廊,我朝一條跑去,柯妮莉亞奔向另一條。這時屋外傳來喇叭聲,聽起來像是威斯康辛大道出了車禍,我的心臟快停了,心想:拜託,老天,千萬別是他。此刻,柯妮莉亞如鬼魂般無聲無息地飛掠過走道,她的靈魂宛如出了竅,鑽進歐文的腦袋,左顧右盼,然後從歐文的雙眼看出去,兩人意識在此交會,她輕聲問道:「你跑去哪了,親愛的……你想去哪?」大部分的教室上了鎖,但有一間是半開的。
教室裡,有扇面向遊樂場半開的大窗子,遊樂場上大家不斷叫喊:「歐文,歐文!」而歐文就靜靜站在窗邊的玩沙桌旁。外頭找人的家長一片恐慌,歐文則專注地盯著沙粒從指縫中流瀉。
‧‧‧
六月一個非常炎熱的早晨,華府北邊一間飯店的宴會廳才不過八點已人滿為患。宴會廳位於馬里蘭州羅克威爾的皇冠廣場飯店,廳內氣氛高漲,充斥著各種短促的對話和殷切期盼空位的目光。
柯妮莉亞在一張擁擠的桌子旁找到一個單獨座位。就在此時,灰髮藍眼的伊瓦爾.洛瓦斯醫生(O. Ivar Lovaas)笑盈盈地登台,眾人歡聲雷動。六十七歲的他充滿活力,說話時僅帶一絲挪威腔。
他擱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工作以及在加州蒸蒸日上的醫療事業,來到美東鼓勵他的信眾,並贏得更多人支持。他將以一段演出達到這目的。沒多久,舞台因某種心理劇療法熱鬧了起來。劇中治療師在自閉症童身上運用洛瓦斯醫生的應用行為分析法(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簡稱ABA,而洛瓦斯自己則負責主持。
他的核心手法是約束。受過ABA訓練的治療師坐在一名小孩的對面,以獎勵和口頭「嫌惡」,如嚴厲的言詞及不時的吆喝,來迫使小孩改變行為。這是純粹的行為改變技術。洛瓦斯是史金納(B. F. Skinner)的擁護者,推崇以獎懲來制約反應:運用於此,便在於如何減少干擾行為、培養孩子注意力、運用簡潔指令以及有效行為後果、安排教材順序以形塑更複雜的行為等等。在外行人眼裡這像在訓練動物。舉例來說,為了訓練孩子與人眼神接觸,ABA治療師會將獎勵(最常用M&M巧克力)放在孩子的鼻樑上,讓他抬頭看著治療師的臉。接著,下達簡潔的「看我」指令,如果孩子照做便把巧克力塞進他的小嘴裡。另外下簡短指令時,如「停手」(自閉兒常拍手)或是「住嘴」(不准自言自語),會佐以拉扯和操縱孩子的動作,將他們的手放在適當的位置。洛瓦斯最初在他一九七○年代的研究中挑選了四名自閉兒,其篩選標準規定實驗對象必須有好胃口,如此一來拒給食物才有最佳效果。談吐簡潔幽默的洛瓦斯懇求觀眾在孩子滿四歲前,讓孩子接受每週四十小時的密集治療計畫,以期達到最佳療效。
「一旦到了四歲,治療會變得更困難,所以別再遲疑。」說完他又舉了數則鼓舞人心的案例,講述許多人因他的方法扭轉了一生。
洛瓦斯展示了一九八七年一份研究論文中驚人的成果。實驗的對象是十九名孩童,其中九名嚴重自閉兒透過他的手法「治癒」了,順利在主流環境中生活。這項研究成果至一九九四年初尚未有人成功複製,不過,願意嘗試的人依舊絡繹不絕。
有捲錄影帶內容令我百思不解。
畫面中,一名蹣跚學步的孩子拿著玩具劍跑過落葉。影片顯示的時間為一九九三年十月。男孩跑起來就和一般兩歲半孩童一樣,橫衝直撞又搖搖晃晃,但這模樣很快就會消失了。因為身處二十世紀末影像充斥的年代,我們清楚事物應有的樣貌,能從千變萬化的世界得出各種結論,且多半準確無誤。男孩模樣天真,有著捲髮,身穿綠色燈芯絨褲和鮮艷的冬季外套;從樹的種類和地形可以推斷影片拍攝於美國東北;草木茂盛的庭院座落在略小的房子後頭,不過嶄新的鞦韆倒是精心打造,給人一種年輕父母刻意營造的氣象。男孩後頭追著一名稚氣的黑髮男子,男子手持短樹枝,笑著跪滑進落葉叢中,逼得男孩笑吟吟地轉身準備應戰。兩人劍棍相接,男子開口:「他才不是男孩,他是個會飛的惡魔!」他模仿的是迪士尼《小飛俠》(Peter Pan)裡的虎克船長,還算像樣。
男子和男孩高聲說著一部一九五三年動畫的台詞,透露了錄影機的普及。那是愛迪生發明電影攝影機一世紀以來,當時捕捉影音最新的電子技術。人們不必千里迢迢到電影院,只須放入錄影帶便能一看再看。當時迪士尼開始以錄影帶發行《小飛象》(Dumbo)、《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小飛俠》等經典動畫;嬰兒潮世代的父母可以買下曾經喜愛的電影,和孩子一同重新回味。此商機說明了為何會有這項人為產物:一捲錄影帶記錄著兩人高聲說著另一捲錄影帶的台詞。
現在從這些細節來談談普世的面向吧。這影片說到底似乎就只是父子在打鬧遊戲,然而這過程往往巧妙蘊含豐沛的情感:男孩一步步成為他天馬行空下的英雄;另一方面,爸爸思忖各種創意的死法,他內心深處明白,男孩有一天會長大,繼承他的一切。最後自然是男孩祭出他最厲害最優雅的突刺,男子應聲倒地,如同被壓碎的枯葉般一命嗚呼,隨後把咯咯笑的孩子攬在身上。
‧‧‧
這段平淡無奇但美好的影片裡,爸爸就是我,男孩則是我兒子。帶子我已看了上百遍,我的妻子也是,直到我們看不下去才作罷。
這是他最後的身影,無情地永遠記錄在磁帶上。
一個月後,畫面中的男孩消失了。她在嫁給我之前本名為柯妮莉亞.甘迺迪(Cornelia Kennedy),來自康乃狄克州一個愛爾蘭天主教的大家族。現在她姓蘇斯金(Suskind)。我是她的丈夫榮恩(Ron),來自德拉瓦州的猶太人。我們有兩個兒子,長子叫華特(Walt),今年五歲,是以在我還小便過世的父親命名的;我們的老么,也就是拿著泡棉玩具劍的男孩,名叫歐文(Owen)。片中有著茂盛花草庭院的房子是我們第一個家,位於麻薩諸塞州的戴德姆。我在《華爾街日報》波士頓分社工作了三年,接下來要搬到華府負責為該報報導國內新聞。那捲錄影帶是搬家卡車來的前一天拍的,那時我們仍安逸地生活在正常的國度。我從未多加思索「正常」這個詞,它是那種要以反義來解釋的詞,「不正常」更能突顯其義,如同圓圈是以圈外的東西來界定圓的輪廓。
‧‧‧
我們搬到華府幾個禮拜後,柯妮莉亞最先察覺到異狀,因為她天天陪著歐文。
有些事變得非常不對勁。
歐文情緒失控了。他會哭泣、到處亂跑、停下來後又繼續哭。停下喘口氣時,雙眼便呆滯地向前凝視。
除此之外,他就是直愣愣地看著柯妮莉亞。柯妮莉亞捧著他哭紅的臉頰問他怎麼了,但他似乎無法訴說。他從來不像哥哥那麼多話,但還算正常,總能隨口從已知的幾百個字彙湊成三個字來傳達需求和愛意,甚至是說則短笑話和故事。
我們搬進華府喬治城的租屋處後便處於忙亂的氛圍中:開箱、華特上新學校、身為父親的我則到嘈雜的大新聞社任職。因此,直到歐文會說的話只剩幾個字,大家才注意到他喪失了語言能力。自十一月搬完家後一個月,歐文變得只會說一個詞:果汁。
有時候,他卻不喝杯裡的東西,而且得用上鴨嘴訓練杯。近一年前,他原已進步到會用「大男孩杯子」了,但是搬到喬治城後,他開始會把東西灑出杯外,彷彿失去了方向感。的確是,他會不停旋轉、走路走得彎彎曲曲。因此,柯妮莉亞會坐在搖椅上儘可能摟住他,幾個月下來過得心驚膽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疏忽了什麼嗎?這有如檢視一樁綁票案的線索。記得有一次,是去年八月,我們到麻州南安普敦旅行,歐文整天哭個不停,而他從來不是那樣的愛哭鬼。十月底又有一次,那天搬家公司要將東西搬上車,一位摯友替我照顧孩子,他把小孩送回來時告訴我們歐文一直在睡。他仍在打盹,但是大半天都在睡?柯妮莉亞開箱時發現了一捲錄搬家當天拍的錄影帶。畫面為黃昏時分,華特帶頭巡視空了一半的房子,心情很愉悅,因為這是一趟到華府的遠行。他以最好的兩個朋友命名的金魚阿提和泰勒,已待在封好的球魚缸裡準備上路:「我的金魚也要一起去!」然後看一下歐文,他短暫出現在鏡頭上,睡眼惺忪輕聲地說:「這是我的嬰兒床還有我全部的東西。」
柯妮莉亞在同一個箱子裡找到另一捲叫「小飛俠鬥劍」的帶子。那天晚上我和她看了這捲帶子。這沒有道理啊,看看那孩子的動作,言談自如的模樣。我們倒帶又看了一遍,然後再一遍,尋找蛛絲馬跡。
時值十二月中,柯妮莉亞和歐文躺在他睡的下鋪,上鋪的華特很快就入睡了。書櫃上發亮的小魚缸嗡嗡作響,阿提和泰勒悄然游走在氣泡之間。此刻為凌晨三點,歐文翻來覆去,咕噥著難以理解的話。柯妮莉亞儘可能地抱緊他、安撫他。她在絕望的黑夜中開始禱告,含著淚對著她的孩子耳語,祈求上帝能夠聽見:「請幫幫我們。不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非常愛你,好好地愛你,我會抱著你直到這一切過去。」
‧‧‧
聖誕假期快到了,這個季節有許多要買的禮物,華府也因節慶活動熱鬧起來。
這理應是個充滿期盼的時刻。努力多年的人生規劃看似全都實現了。我和柯妮莉亞是在大學畢業後辦一場競選活動認識的。當時她坐在我的位置上看著我的法學院申請書,她說從內容看來我似乎不太想念法學院(沒錯),不過我的文筆不錯,應該考慮當個作家。那時她已是名年輕出眾的作家,而我聽完隨即愛上這個建議。我的父親四十六歲死於癌症前寫了封信給我和哥哥,懇求我們將生命用來做些「值得做的事」。新聞業似乎符合這份期待,挑戰權威、拼湊零碎真相、建立讀者群。後來我們輔選的候選人輸了,但我們倆開始交往。她在紐約的《人物》雜誌當記者,我則到了哥倫比亞新聞研究所唸書,畢業後在《紐約時報》當了兩年的新聞文書,而她則晉升為一名紐約雜誌的編輯;後來我在佛羅里達的《聖彼得堡時報》當了一年半的記者,我們就是在當地結婚的;然後我來到波士頓,當上一間小型商業雜誌社的編輯,接著一九九○年到《華爾街日報》波士頓分社任職,離公司不遠處就是波士頓老南聚會所。我還在牙牙學語時,便在布魯克林出身且極其自傲的母親督促下編撰故事了,甚至在父親過世後煎熬的歲月裡,還把這些故事編成了單口相聲橋段。不過年復一年,我一直在學習為該報招牌的頭版撰寫長篇報導。現在我被調到了華府專職撰寫報導,這是一份夢幻工作。
因此晚上時,我們將心思放在正面的事情上,談論著例如交到新朋友;替承租的三層樓聯邦式排屋買了價格理想的二手家具;也許有天會在鄰近社區買下房子等。但隨後柯妮莉亞百般不願地道出白天歐文又做了某件令人擔憂的事。「一切會好起來的。」我說道,接著試著找出合理的解釋:歐文正面臨一些苦痛,也許得了胃病,甚至是聽力受損,我們會搞清楚的。
「沒有孩子會失去已獲得的東西。人生不會倒帶。」
‧‧‧
小兒科醫生要求獨自觀察我們的兒子一會兒,他要我們坐在候診室,他想看看少了我們在旁,歐文如何與陌生人互動。由於孩子是沒有戒心的,他們會盯著陌生人看,充滿好奇心。他們就像小型吸塵器,不斷吸收各種訊息,也會與人目光交會,表達想法。這是孩子最起碼應有的樣子。
幾分鐘後,醫生把我們叫進他的看診室,告訴我們歐文並沒有這些表現。我們同意,這也是我們帶他過來的原因。柯妮莉亞簡短向醫生描述一直以來觀察到的狀況以及我們擔心之處,還有生活如何天翻地覆。
他聽完回道:「倘若一件事打亂家庭生活到這種地步,那肯定是個問題。」當小兒科醫生不確定病患的情況,尤其病患又是小孩時,他們會將之歸類為「母親的擔憂」。他說他要抽血做兩項基因檢測。一項是檢測X染色體脆折症,我們後來得知這是一種神經疾病,具可識別的遺傳標記,病徵相當可怕。另一項是檢測黑蒙性癡呆症,我知道這種疾病:它會造成嬰兒身心衰退,病童多於四歲前夭折,好發於東歐猶太裔人,也就是我的族裔。這疾病同大屠殺都是猶太學校裡會教的。後來醫生轉介我們到馬里蘭州羅克威爾一間醫療中心,也許到那會更有幫助。
時間來到二月,我們已坐在勞利嬰幼兒醫療中心(Reginald S. Lourie Center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的候診室。這裡的候診室環境截然不同,一旁便是遊戲室,從一面單面鏡能見到裡頭有彩色方塊、鞦韆、軟墊,孩子能在那玩耍,醫生則可從旁觀察。
我們被帶到一間看診室,等在裡頭的是一名表情嚴肅、身材高大的黑髮女人。她向歐文打招呼,柯妮莉亞無比堅定地牽著他的小手。在我們交談的診間裡有更多玩具,但歐文視而不見。幾分鐘後,她要歐文沿著長廊從我走向柯妮莉亞。我放開他的手,心想:「就這一次筆直好好走吧,就像在戴德姆時那樣。」但他沒有。他晃動雙手走著,倏地轉向又停下,走得曲曲折折,就像閉上雙眼在跑步一樣。柯妮莉亞把他抱了起來,然後我們回到了診間。女醫師表示:「他似乎罹患了廣泛性發展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會影響多數關鍵領域的發展。」又說道:「從他的步伐還有其他特徵可以明顯判斷。」她幾乎沒瞧上一眼坐在地上玩弄手指的歐文,並以冷冰冰的語氣繼續說道。我和柯妮莉亞彷彿從當下的情境中抽離飄浮在半空中,俯視著這對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雞又不時點頭的年輕夫妻,一旁那名孩子則認真在端詳自己的雙手。因此,她提到「自閉症」時,我並不是很清楚她說了什麼。
否認的力量是很強大的。幾年後,有位好友的父親,他是名年邁的精神科醫生,對我說了幾句饒富深意的話:「看重否認的力量,它存在是有道理的:它幫助我們面對無法接受的事物。」三十四歲的我並不看重它,甚至對它很陌生。
開車回家的路上,坐在後頭的歐文在他的汽車座椅上劇烈扭動,我和柯妮莉亞沉默不語。那女醫生一定搞錯了。我們對自閉症的看法就如同當今多數人。我們和所有國人一樣都看過《雨人》(Rain Man),這孩子不是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飾演的雷蒙.巴比特!一個月後,我們在貝賽斯達一間診所找到新的醫生:他是位年輕的小兒發展科醫生,長得和柯妮莉亞的高中老友出奇地像。我是在大學時認識那位朋友,當初也是他介紹我和柯妮莉亞認識的,這給人印象好多了。
艾倫.羅森布拉特(Alan Rosenblatt)醫生將歐文抱在腿上,極其溫柔地對他說:「嗨,小兄弟。」這一次歐文回頭了。他們做了些練習:讓歐文注視醫生移動的雙手並碰觸手指,接著兩人坐到地毯上,歐文似乎很自在。他們用積木蓋小房子,羅森布拉特先蓋了一個,想看歐文是否會接著蓋。
他並沒有,而兩人也沒有太多互動。隨後歐文站了起來開始亂走,羅森布拉特喚了他的名字,他便爬到椅子下看了醫生一眼,眼神似乎在說「來抓我啊」,示意要醫生追他,不過那表情閃現即逝。羅森布拉特草草在筆記板上記下些東西。
羅森布拉特回到坐位上後說道:「歐文恐怕有現今所謂的廣泛性發展障礙,或稱PDD,後頭還會加上縮寫NOS,表示『未分類的』(not otherwise specified)。」這代表歐文除了有「類自閉症的行為」,還有其他不符合典型自閉症範疇的表現,像是露出「來抓我」的神情。
他向我們完整講述了歐文的治療計畫,包括密集的語言治療、職能治療、遊戲治療,並建議我們應儘快展開。另外為了接下來的秋天作打算,他要我們立即找一間適合歐文的學校,也提供了一些建議學校。他說:「早期介入至關重要。」又提道:「有宗教信仰或加入宗教團體的家庭,這方面表現得比較好。」這段話令我們憂心眼前的災難,不過對天主教徒柯妮莉亞來說,宗教的確很快會是她尋求力量的依歸。
歐文沒被貼上「自閉症」的標籤讓我們鬆了口氣,因為照羅森布拉特的說法,歐文的毛病是種「遲緩」。我們後來更加了解到這些委婉語帶給我們的好處,其中一項重要的作用是:我們倆不會想再從診間跑走,開車回家時內心不會痛苦地像斷了四肢。
那一天是四月,前往停車場的路上,我們和羅森布拉特小聊了一下,言談中得知一件事,令我們對他所言更具信心。我們提到過去在波士頓看的小兒科醫生鮑伯.麥可斯(Bob Michaels),他畢業於哈佛,非常出色。羅森布拉特愣了一會,問道他是否來自匹茲堡。沒錯,我們興奮地回道,他是在匹茲堡長大的。「你問我認不認識麥可斯?他爸爸是我的小兒科醫生,很棒的醫生,他是我成為小兒科醫生的主因呢!」我們一到家便打給了人在哈佛的麥可斯醫生,告訴他這段奇遇,也很自然地向他解釋離開麻州後歐文的狀況。他要我們別掛電話,他去拿了歐文的病歷表,將病歷表瀏覽了一遍。「去年夏天我才替他檢查過,完全沒問題,我不懂怎麼會這樣。」
我們也不懂。沒錯,有地方出了差錯,但是連醫生也搞不清楚問題在哪。以羅森布拉特的話來說,歐文是「非典型的」案例,他的症狀屬於各類遲緩,能夠治好。那一晚我們如釋重負,睡得很安穩。我們能在每天睜開雙眼的每一刻拯救這孩子,令他重生!愚蠢。
‧‧‧
隔天早上,柯妮莉亞牽著歐文、帶著華特從我們喬治城的家出發,沿著門前的街道走過七個路口來到海德國小。華特在校很活躍,除了開學日在朝會上以吹口琴的方式報到有點脫序外,他很喜歡學校生活和交朋友;玩樂、學習、成長。那天把華特送到學校後,柯妮莉亞帶著歐文與一小群家長碰了面。海德國小的規模雖不比華府西北區其他小學,但是海德一直致力於跟上他校的腳步。就在這天早晨的茶會上,大家討論著如何籌辦即將到來的海德春季園遊會,這活動應該能為學校募得不少資金。身為園遊會共同主委的柯妮莉亞,則一直忙著整合贊助人、物資之類的事。
一切的努力就是為了讓五月初的園遊日,也就是兩個禮拜後的星期六,成為一個新來乍到家庭的大日子。當天還不到中午,學校旁圍著柵欄的遊樂場已快擠滿了人,設施管理員急忙為氣墊遊樂場打氣。這感覺正是我們所嚮往的華府,應該也是每個人所憧憬的:有快樂的戰士相伴,打造一個充滿歡樂和食物的小小王國,大批親子人馬齊聚於此,為美好的目的歡慶。
當然,我們一直很用心安排讓歐文能與我們一同參加園遊會。進出遊樂場只有一道門,由認識歐文的志工家長把關,他們會提防歐文溜出去;其實只要想到我和柯妮莉亞在他身旁寸步不離,這根本不是問題。幾個小時下來,園遊會忙亂的氣氛時起時落:多點冰塊!有誰知道電源開關在哪裡?熱狗沒有了!而我們的確與歐文形影不離。事情確切發生的時間點已不可考,總之,罪魁禍首是身為爸爸的我,因為全天下的媽媽大概從宇宙大爆炸開始,就內建了一種神經裝置,能立即定位子女的座標。傍晚時分,我放開了歐文的手,好將歐文午餐吃剩的半根熱狗塞到我嘴裡,並拿起放在地上的可樂罐。我一回頭,左手邊一英尺遠鋪著碎石的鞦韆場,剛才歐文待的地方已空無一人。
爸爸也有應付這種情況的配備,不過電路啟動的方式不同。原則一:別慌。冷靜迅速環視四週:九十度、一百八十、二百七十、三百六十。
原則二,開始慌張!我先是快步走,後來快跑至大門詢問門旁的一位父親:「你有沒有看到他,歐文有沒有溜出去?」想不到一個奔跑的男人竟能引起這麼多注意,我這一回頭,後面已跟了一小群家長,帶頭的是柯妮莉亞。
我不必說明歐文走丟了,她看得出來,所以我直接切入重點。「三十秒前我和他還在鞦韆那,他沒出大門!」
幸好園遊會已經進入尾聲,擋住視線的人群較少。然而五分鐘後仍遍尋不著他的下落。我和柯妮莉亞跑得氣喘吁吁,兩人內心拼命壓抑一段共同的回憶:一年前在我們麻州家附近的衛斯理,歐文曾在校園園遊會上走失一下子。我們當時以為就是一起兩歲孩子走失記。這是有可能的,只是頻率不會這麼高。走丟的孩子至少會有一絲分離焦慮,這有助於媽媽的雷達定位,而且他們會逐漸意識到父母不在身旁。此時他們發覺自己走失了,便開始哭泣。無論歐文是否具有這樣的配備,現在肯定是關掉了,更何況我們不在草木蔥鬱的衛斯理,這裡是喬治城,我們身處一片圍著柵欄的水泥地,外頭車子在鋪著鵝卵石的O街上穿梭,疾馳至半個街區外的威斯康辛大道,那可是華府的主要幹道。
十分鐘後恐慌蔓延開來,許多家長開始散開到街上找人,我和柯妮莉亞則跑進了學校。雖然園遊會期間禁止進入校區,但有道門為了供電源線通過是開著的。校舍是一棟世紀之交落成的方形磚房,宏偉空蕩,屋頂的簷口已剝蝕,屋內有兩條走廊,我朝一條跑去,柯妮莉亞奔向另一條。這時屋外傳來喇叭聲,聽起來像是威斯康辛大道出了車禍,我的心臟快停了,心想:拜託,老天,千萬別是他。此刻,柯妮莉亞如鬼魂般無聲無息地飛掠過走道,她的靈魂宛如出了竅,鑽進歐文的腦袋,左顧右盼,然後從歐文的雙眼看出去,兩人意識在此交會,她輕聲問道:「你跑去哪了,親愛的……你想去哪?」大部分的教室上了鎖,但有一間是半開的。
教室裡,有扇面向遊樂場半開的大窗子,遊樂場上大家不斷叫喊:「歐文,歐文!」而歐文就靜靜站在窗邊的玩沙桌旁。外頭找人的家長一片恐慌,歐文則專注地盯著沙粒從指縫中流瀉。
‧‧‧
六月一個非常炎熱的早晨,華府北邊一間飯店的宴會廳才不過八點已人滿為患。宴會廳位於馬里蘭州羅克威爾的皇冠廣場飯店,廳內氣氛高漲,充斥著各種短促的對話和殷切期盼空位的目光。
柯妮莉亞在一張擁擠的桌子旁找到一個單獨座位。就在此時,灰髮藍眼的伊瓦爾.洛瓦斯醫生(O. Ivar Lovaas)笑盈盈地登台,眾人歡聲雷動。六十七歲的他充滿活力,說話時僅帶一絲挪威腔。
他擱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工作以及在加州蒸蒸日上的醫療事業,來到美東鼓勵他的信眾,並贏得更多人支持。他將以一段演出達到這目的。沒多久,舞台因某種心理劇療法熱鬧了起來。劇中治療師在自閉症童身上運用洛瓦斯醫生的應用行為分析法(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簡稱ABA,而洛瓦斯自己則負責主持。
他的核心手法是約束。受過ABA訓練的治療師坐在一名小孩的對面,以獎勵和口頭「嫌惡」,如嚴厲的言詞及不時的吆喝,來迫使小孩改變行為。這是純粹的行為改變技術。洛瓦斯是史金納(B. F. Skinner)的擁護者,推崇以獎懲來制約反應:運用於此,便在於如何減少干擾行為、培養孩子注意力、運用簡潔指令以及有效行為後果、安排教材順序以形塑更複雜的行為等等。在外行人眼裡這像在訓練動物。舉例來說,為了訓練孩子與人眼神接觸,ABA治療師會將獎勵(最常用M&M巧克力)放在孩子的鼻樑上,讓他抬頭看著治療師的臉。接著,下達簡潔的「看我」指令,如果孩子照做便把巧克力塞進他的小嘴裡。另外下簡短指令時,如「停手」(自閉兒常拍手)或是「住嘴」(不准自言自語),會佐以拉扯和操縱孩子的動作,將他們的手放在適當的位置。洛瓦斯最初在他一九七○年代的研究中挑選了四名自閉兒,其篩選標準規定實驗對象必須有好胃口,如此一來拒給食物才有最佳效果。談吐簡潔幽默的洛瓦斯懇求觀眾在孩子滿四歲前,讓孩子接受每週四十小時的密集治療計畫,以期達到最佳療效。
「一旦到了四歲,治療會變得更困難,所以別再遲疑。」說完他又舉了數則鼓舞人心的案例,講述許多人因他的方法扭轉了一生。
洛瓦斯展示了一九八七年一份研究論文中驚人的成果。實驗的對象是十九名孩童,其中九名嚴重自閉兒透過他的手法「治癒」了,順利在主流環境中生活。這項研究成果至一九九四年初尚未有人成功複製,不過,願意嘗試的人依舊絡繹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