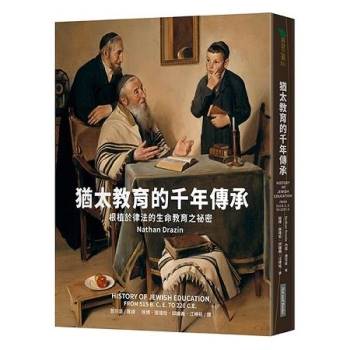第一章:引論
研究及其目的
儘管教育史整體上已被諸多出色的歷史學者和教育者研究過,猶太教育這一特定領域卻尚未有過系統的探究。它的特殊貢獻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後聖經時期尤其如此——諷刺的是,即便出於它只是見證了作為後面我們將要看到的猶太學校制度,以及面向男童的普通初級和中等教育機構的演變原因,教育史學者也本應對這一時期最感興趣,更不用說當時其他諸多教育改革使其成為猶太教育發展過程中的成形時期。
造成這個看似令人費解的情況的原因顯而易見。對於有意研究古代或聖經時期猶太歷史的人來說,他們有全本的舊約聖經譯本可資利用。然而,後來才出現的龐大的拉比文獻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而這些文獻對於古典或後聖經時期的歷史研究不可或缺。要充分理解古老的拉比學問,通曉希伯來語和亞蘭語(Aramaic)仍必不可少。因為這一困難,能夠從事此領域研究的人並不多。此外,大多數教育者幼稚地認為希臘和羅馬已經提供了理想的古典時代的教育理念和實踐。例如,卡伯利(Cubberley)的《教育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中,只有不到三頁講述猶太人的歷史、宗教和教育,而門羅(Monroe)的《教育史中的教科書》(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中,甚至連一頁都沒有。《教育百科全書》(Cyclopedia of Education)此鉅著中,講述全部兩千年古代猶太教育的部分,只有幾乎不到四頁!
然而,如果意識到第二聖殿建立之後數個世紀裡,猶太民族在文學、宗教和道德律法上創造性的天才,人們有理由推測應該曾經有過一個良好的教育體系才足以產生這樣的成果。同樣,猶太人的民族性得以堅持不懈地保持到今天,應當也可以追溯到猶太教育體系的某些因素,這些在後聖經時期已有清晰的體現。因此,對這一時期歷史和教育的研究,頗可預期會產生對當代教育有價值的新理念、新觀點。本研究中,筆者計畫批判性地徹底檢視從公元前五一五年至公元二二○年間約七個半世紀的猶太教育史,這段時間涵蓋第二聖殿時期和到米示拿(Mishnah)這部對猶太民族來說,重要性僅次於聖經的偉大法律彙編編纂完成為止的坦拿時期。之所以選擇上述時間為界,是因為儘管這些時期的年代學仍有爭議,但大多數現代歷史學者同意,最少在公元前五一五年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已建造完成。同樣,採用公元二二○年是因為所有歷史學者至少都同意,到這個日期為止,米示拿已經由尊長猶大拉比(Rabbi Judah the Patriarch,編註:亦稱猶大親王、聖者拉比猶大)彙編完成,許多人進一步主張這個時候米示拿的最後編訂也已經完成。那些有言論被記載在米示拿或其他同時期律法著作中的學者被稱為「坦拿」,即導師的意思。一般認為第一代坦拿出現在約公元十年。因此坦拿時期包括從公元一○年到二二○年為止大約兩個世紀。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三重性質:第一,探究現存的設定時期內的猶太文獻以收集與教育相關的資料,確定它們產生的時間,以便可以按歷史順序採用;第二,考查古代世界普遍的教育體系,為的是找出猶太教育演變過程中究竟有什麼樣的外來影響;最後,考查設定時期的猶太歷史,以確定和可靠評估產生教育改革的原因。
研究進行之前,還有三個方法和原則問題需要澄清。首先,凡是直接從米示拿或其他古代文獻引用作為例證的地方,只給出最重要和最完整的文句,以避免過度重複。其次,必須解釋一下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教育」一詞。儘管本書的重點放在正式的、有目標的教育,其他在本研究涉及的時期對教育產生影響的部門或機構,也在考查範圍之內。本書既包括宗教教育也涵蓋世俗教育。最後,下面給出一個完整的研究概要。
筆者認為把與本書有關的所有教育資料放在六個總括性的標題下比較合適:教育哲學、學校制度的演變、教育的施行、教育的內容、教學方法和原則以及女孩和女性的教育。這其中每個題目都有單獨一章論述。最後一章中,筆者將猶太教育與希臘和羅馬的教育體系做了簡要比較。筆者還總結了重要的猶太教育理念和方法,並指出其中哪些遺留在現代教育中,哪些則沒有。最後所附書目分別列出本書參考的所有原始和二手文獻。為了清楚展示本研究之發現和討論的重要性,這裡簡要敘述第二聖殿和坦拿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然而,與教育直接相關的事情則保留到後面章節。
時代的歷史背景
自耶路撒冷第一聖殿被毀(公元前五八六年)至第二聖殿建立之間經過了七十年的時間。這段時間一般稱為「巴比倫之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時期。如這個名稱所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摧毀第一聖殿並將猶太人掠擄為囚之後,大部分猶太人在巴比倫度過了這些日子。最後,巴比倫被波斯人征服,居魯士(Cyrus)允許猶太人返回故土重建聖殿。第二聖殿的建立完成於公元前五一六年。
然而,當時並非所有猶太人都返回到巴勒斯坦。事實上大部分人留在了巴比倫。回到巴勒斯坦的數萬人發現異族已定居在大片土地上,他們還聲稱擁有這些土地。猶太人被允許重新佔有的土地大都是荒漠,他們需要大量的工作來恢復土壤。當時沒有足夠的土地給所有猶太人,因此一些人不得不另謀生路。由此出現了許多新行業,並產生了一批專門的匠人和手工業者。「禧年」(the Jubilee Year)的功能不再存在,因此土地可以永久買賣。經年累月下來,土地便成為少數人的財產,而大多數人不得不以務工、貿易或商業謀生。
當全體猶太人還在巴比倫哀歎失去聖殿之時,他們就開始建設會堂,在會堂裡人們可以聚而敬神並祈禱。後來在巴勒斯坦的偏遠村鎮也為難以趕赴耶路撒冷參拜聖殿的人建立了類似的會堂。由這些會堂短時間內演化出「訓誨之所」(houses of instruction),本書後面將有全面討論。
猶太人在巴比倫的文化生活中另一重要事件是習得亞蘭語。因為希伯來語和亞蘭語同源,所以這對猶太人來說並非難事。直到希臘化興起,亞蘭語就一直是猶太人之間的通用口語。第二聖殿建成後不久,希伯來文字就發生了變革。新的方體(「亞述體」)字母形式極為簡單,因此易於掌握。後來居住在埃及的猶太人則主要使用希臘語。第二聖殿時期開始,巴勒斯坦還是波斯的屬地。當希臘征服了波斯帝國,猶太人便不得不向這個新的世界強權稱臣納貢。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巴勒斯坦或屬於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或屬於敘利亞的塞琉古王朝,直到馬卡比(Maccabean)起義之時都只是一個朝貢蕃邦。這段時間裡,大祭司(the High Priest)是影響猶太人生活的所有事務的首腦。他最初由大議會成員(the Men of the Great Assembly)輔佐,後來則由被賦予裁決猶太律法疑難問題權力的智者組織「猶太公會」(編註:the Sanhedrin,或譯作猶太人議會)輔佐。公元前一六五年馬卡比起義勝利後,猶太最終成為獨立國家,大祭司亦加冕為王。猶太人享有國家獨立近一個世紀。公元前六三年開始,猶太被羅馬人完全支配,然而神權統治卻沒有長時間中斷地延續到公元前三七年,一位與大祭司階層沒有關係的君主即位,這時政教才正式分離,直到猶太國家滅亡。
馬卡比起義勝利之前就出現了兩個相互對立的猶太人派別:願意接受希臘文化和宗教的希臘化派(the Hellenists),以及哈西典派(Hasidim),他們是抵制希臘化派的虔誠猶太人,還曾援助馬卡比起義。約一個世紀之後,後一派中興起了法利賽派,可能愛色尼派(the Essenes)也興起於此,而撒都該派則在某些方面成為希臘化派的精神繼承者。法利賽派接受先祖傳承下來的口頭律法傳統,他們把它看得跟摩西五經中所記載的書面律法一樣神聖,並極為勤奮細緻地發展猶太律法文獻,由此成為未來以色列的教師和宗師。因此猶太教育史與這些人的學術工作密不可分。
公元七○年羅馬的提圖斯(Titus of Rome)摧毀耶路撒冷及聖殿之後,猶太人便流散各地。然而,仍有許多猶太人留在巴勒斯坦的小村鎮中,試圖多少保存一些他們的文明。第二聖殿時期就定居在巴比倫和埃及的猶太人此時數量大增。而定居在羅馬的猶太人甚至有更大比例的增加。流散異國最初這幾個世紀裡,猶太民族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真的是千差萬別。他們生存的不安定狀況因時代和居住地的不同而改變。巨大的不安常伴隨著整個流散時期。起初,猶太人還抱持著很快就能重新恢復榮耀的希望,像亞基巴(Akiba)拉比和他的門徒這樣有名望的人,都資助了公元一三二至一三五年間的巴爾.科赫巴(Bar Kokba)起義。可惜隨著起義失敗,希望也變得黯淡渺茫了。
然而,使猶太人在不幸中感到慰藉的是,在他們的故國至少還有一個表面上的國家組織被允許存在。由七十位長老組成的猶太公會仍繼續運作,但其功能已經改變。以前它是法庭,現在則基本上是個高等學術機構,只是猶太人仍會向公會尋求與私人生活相關的各種事情的權威指導。其首腦擁有「教長」(編註:Patriarch,或譯族長。)(希伯來文為納西〔nasi〕或拉班〔Rabban〕)稱號,並被帝國政府所承認。教長公署保留在巴勒斯坦長達三個世紀。
研究及其目的
儘管教育史整體上已被諸多出色的歷史學者和教育者研究過,猶太教育這一特定領域卻尚未有過系統的探究。它的特殊貢獻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後聖經時期尤其如此——諷刺的是,即便出於它只是見證了作為後面我們將要看到的猶太學校制度,以及面向男童的普通初級和中等教育機構的演變原因,教育史學者也本應對這一時期最感興趣,更不用說當時其他諸多教育改革使其成為猶太教育發展過程中的成形時期。
造成這個看似令人費解的情況的原因顯而易見。對於有意研究古代或聖經時期猶太歷史的人來說,他們有全本的舊約聖經譯本可資利用。然而,後來才出現的龐大的拉比文獻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而這些文獻對於古典或後聖經時期的歷史研究不可或缺。要充分理解古老的拉比學問,通曉希伯來語和亞蘭語(Aramaic)仍必不可少。因為這一困難,能夠從事此領域研究的人並不多。此外,大多數教育者幼稚地認為希臘和羅馬已經提供了理想的古典時代的教育理念和實踐。例如,卡伯利(Cubberley)的《教育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中,只有不到三頁講述猶太人的歷史、宗教和教育,而門羅(Monroe)的《教育史中的教科書》(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中,甚至連一頁都沒有。《教育百科全書》(Cyclopedia of Education)此鉅著中,講述全部兩千年古代猶太教育的部分,只有幾乎不到四頁!
然而,如果意識到第二聖殿建立之後數個世紀裡,猶太民族在文學、宗教和道德律法上創造性的天才,人們有理由推測應該曾經有過一個良好的教育體系才足以產生這樣的成果。同樣,猶太人的民族性得以堅持不懈地保持到今天,應當也可以追溯到猶太教育體系的某些因素,這些在後聖經時期已有清晰的體現。因此,對這一時期歷史和教育的研究,頗可預期會產生對當代教育有價值的新理念、新觀點。本研究中,筆者計畫批判性地徹底檢視從公元前五一五年至公元二二○年間約七個半世紀的猶太教育史,這段時間涵蓋第二聖殿時期和到米示拿(Mishnah)這部對猶太民族來說,重要性僅次於聖經的偉大法律彙編編纂完成為止的坦拿時期。之所以選擇上述時間為界,是因為儘管這些時期的年代學仍有爭議,但大多數現代歷史學者同意,最少在公元前五一五年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已建造完成。同樣,採用公元二二○年是因為所有歷史學者至少都同意,到這個日期為止,米示拿已經由尊長猶大拉比(Rabbi Judah the Patriarch,編註:亦稱猶大親王、聖者拉比猶大)彙編完成,許多人進一步主張這個時候米示拿的最後編訂也已經完成。那些有言論被記載在米示拿或其他同時期律法著作中的學者被稱為「坦拿」,即導師的意思。一般認為第一代坦拿出現在約公元十年。因此坦拿時期包括從公元一○年到二二○年為止大約兩個世紀。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三重性質:第一,探究現存的設定時期內的猶太文獻以收集與教育相關的資料,確定它們產生的時間,以便可以按歷史順序採用;第二,考查古代世界普遍的教育體系,為的是找出猶太教育演變過程中究竟有什麼樣的外來影響;最後,考查設定時期的猶太歷史,以確定和可靠評估產生教育改革的原因。
研究進行之前,還有三個方法和原則問題需要澄清。首先,凡是直接從米示拿或其他古代文獻引用作為例證的地方,只給出最重要和最完整的文句,以避免過度重複。其次,必須解釋一下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教育」一詞。儘管本書的重點放在正式的、有目標的教育,其他在本研究涉及的時期對教育產生影響的部門或機構,也在考查範圍之內。本書既包括宗教教育也涵蓋世俗教育。最後,下面給出一個完整的研究概要。
筆者認為把與本書有關的所有教育資料放在六個總括性的標題下比較合適:教育哲學、學校制度的演變、教育的施行、教育的內容、教學方法和原則以及女孩和女性的教育。這其中每個題目都有單獨一章論述。最後一章中,筆者將猶太教育與希臘和羅馬的教育體系做了簡要比較。筆者還總結了重要的猶太教育理念和方法,並指出其中哪些遺留在現代教育中,哪些則沒有。最後所附書目分別列出本書參考的所有原始和二手文獻。為了清楚展示本研究之發現和討論的重要性,這裡簡要敘述第二聖殿和坦拿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然而,與教育直接相關的事情則保留到後面章節。
時代的歷史背景
自耶路撒冷第一聖殿被毀(公元前五八六年)至第二聖殿建立之間經過了七十年的時間。這段時間一般稱為「巴比倫之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時期。如這個名稱所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摧毀第一聖殿並將猶太人掠擄為囚之後,大部分猶太人在巴比倫度過了這些日子。最後,巴比倫被波斯人征服,居魯士(Cyrus)允許猶太人返回故土重建聖殿。第二聖殿的建立完成於公元前五一六年。
然而,當時並非所有猶太人都返回到巴勒斯坦。事實上大部分人留在了巴比倫。回到巴勒斯坦的數萬人發現異族已定居在大片土地上,他們還聲稱擁有這些土地。猶太人被允許重新佔有的土地大都是荒漠,他們需要大量的工作來恢復土壤。當時沒有足夠的土地給所有猶太人,因此一些人不得不另謀生路。由此出現了許多新行業,並產生了一批專門的匠人和手工業者。「禧年」(the Jubilee Year)的功能不再存在,因此土地可以永久買賣。經年累月下來,土地便成為少數人的財產,而大多數人不得不以務工、貿易或商業謀生。
當全體猶太人還在巴比倫哀歎失去聖殿之時,他們就開始建設會堂,在會堂裡人們可以聚而敬神並祈禱。後來在巴勒斯坦的偏遠村鎮也為難以趕赴耶路撒冷參拜聖殿的人建立了類似的會堂。由這些會堂短時間內演化出「訓誨之所」(houses of instruction),本書後面將有全面討論。
猶太人在巴比倫的文化生活中另一重要事件是習得亞蘭語。因為希伯來語和亞蘭語同源,所以這對猶太人來說並非難事。直到希臘化興起,亞蘭語就一直是猶太人之間的通用口語。第二聖殿建成後不久,希伯來文字就發生了變革。新的方體(「亞述體」)字母形式極為簡單,因此易於掌握。後來居住在埃及的猶太人則主要使用希臘語。第二聖殿時期開始,巴勒斯坦還是波斯的屬地。當希臘征服了波斯帝國,猶太人便不得不向這個新的世界強權稱臣納貢。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巴勒斯坦或屬於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或屬於敘利亞的塞琉古王朝,直到馬卡比(Maccabean)起義之時都只是一個朝貢蕃邦。這段時間裡,大祭司(the High Priest)是影響猶太人生活的所有事務的首腦。他最初由大議會成員(the Men of the Great Assembly)輔佐,後來則由被賦予裁決猶太律法疑難問題權力的智者組織「猶太公會」(編註:the Sanhedrin,或譯作猶太人議會)輔佐。公元前一六五年馬卡比起義勝利後,猶太最終成為獨立國家,大祭司亦加冕為王。猶太人享有國家獨立近一個世紀。公元前六三年開始,猶太被羅馬人完全支配,然而神權統治卻沒有長時間中斷地延續到公元前三七年,一位與大祭司階層沒有關係的君主即位,這時政教才正式分離,直到猶太國家滅亡。
馬卡比起義勝利之前就出現了兩個相互對立的猶太人派別:願意接受希臘文化和宗教的希臘化派(the Hellenists),以及哈西典派(Hasidim),他們是抵制希臘化派的虔誠猶太人,還曾援助馬卡比起義。約一個世紀之後,後一派中興起了法利賽派,可能愛色尼派(the Essenes)也興起於此,而撒都該派則在某些方面成為希臘化派的精神繼承者。法利賽派接受先祖傳承下來的口頭律法傳統,他們把它看得跟摩西五經中所記載的書面律法一樣神聖,並極為勤奮細緻地發展猶太律法文獻,由此成為未來以色列的教師和宗師。因此猶太教育史與這些人的學術工作密不可分。
公元七○年羅馬的提圖斯(Titus of Rome)摧毀耶路撒冷及聖殿之後,猶太人便流散各地。然而,仍有許多猶太人留在巴勒斯坦的小村鎮中,試圖多少保存一些他們的文明。第二聖殿時期就定居在巴比倫和埃及的猶太人此時數量大增。而定居在羅馬的猶太人甚至有更大比例的增加。流散異國最初這幾個世紀裡,猶太民族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真的是千差萬別。他們生存的不安定狀況因時代和居住地的不同而改變。巨大的不安常伴隨著整個流散時期。起初,猶太人還抱持著很快就能重新恢復榮耀的希望,像亞基巴(Akiba)拉比和他的門徒這樣有名望的人,都資助了公元一三二至一三五年間的巴爾.科赫巴(Bar Kokba)起義。可惜隨著起義失敗,希望也變得黯淡渺茫了。
然而,使猶太人在不幸中感到慰藉的是,在他們的故國至少還有一個表面上的國家組織被允許存在。由七十位長老組成的猶太公會仍繼續運作,但其功能已經改變。以前它是法庭,現在則基本上是個高等學術機構,只是猶太人仍會向公會尋求與私人生活相關的各種事情的權威指導。其首腦擁有「教長」(編註:Patriarch,或譯族長。)(希伯來文為納西〔nasi〕或拉班〔Rabban〕)稱號,並被帝國政府所承認。教長公署保留在巴勒斯坦長達三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