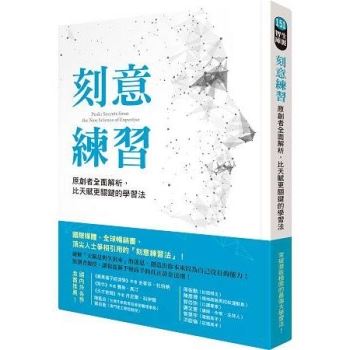第1章 有目標的練習
我當時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史提夫是大學部的學生,被請來執行一項簡單的任務:記憶長串數字。他一週來幾次,我會以一秒一個的速度對他念出一串數字,例如:「7……4……0……1……1……9……」史提夫要試著全數記住,等我念完後重述。實驗目的之一在測試史提夫能藉由練習進步多少。而在進行四回實驗之後,他已經能熟記相當於本地電話號碼長度的七位數,八位數的表現通常也無誤,但九位數的成功機率不太穩定,十位數則完全辦不到。他當時因為頭幾回的表現而感到沮喪,深信自己不可能有進展。
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史提夫卻不知道——當時幾乎所有心理學研究都站在他那一邊。幾十年的研究顯示,人類短期記憶能夠記住的物品數量絕對有極限(短期記憶是大腦用來在短時間內保存少量資訊的一種記憶類型)。我們利用短期記憶把朋友給的地址保留到將它寫下來;在腦海中進行二位數乘法時,短期記憶會記錄中間所有的運算步驟:「好,27乘以14……首先,4乘以7等於28,8留下來,2進到十位,然後4乘以2等於8……」諸如此類。這種記憶類型之所以被稱為「短期」其來有自,因為除非花時間一次次複誦那個地址或中間那些運算的數字,以存入長期記憶中,否則五分鐘後便忘了。
史提夫面對的是短期記憶的問題:大腦靠短期記憶同時記下的物品數量明顯有極限。有些人可以記六項,有些人記七、八項沒問題,不過七項是一般人的極限,所以能夠記住七位數的本地電話號碼,卻記不住九個數字組成的社會安全號碼。長期記憶就沒有這樣的限制,其上限甚至無人知曉,但想有效利用卻得花更長的時間。只要投注足夠的時間,便能記住幾十組,甚至上百組電話號碼,不過我在測試史提夫時故意迅速讀出數字,迫使他只能運用短期記憶。一秒一個數字的速度快到他無法將數字轉存到長期記憶中,難怪他在八位數或九位數的地方會碰壁。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史提夫能有些微的進步。會想進行這項研究,是因為我在閱覽老舊的科學實驗文獻時發現一篇不起眼的報告——寶琳‧馬汀和山謬‧凡保格這兩位賓州大學的心理學家一九二九年發表在《美國心理學期刊》的文章。馬汀和凡保格表示,兩名大學生受試者經過四個月的練習後,成功增加了可以記住的數字位數(聽取的速度也是一秒鐘一個數字),其中一名學生從一般的九位數進步到十三位數,另一個則從十一位數進步到十五位數。
心理學界多忽略或遺忘了這項結果,我卻眼睛為之一亮:這種進步真的有可能嗎?若有可能發生,是怎麼辦到的?馬汀和凡保格並未詳細說明那兩名學生如何增進對數字的記憶,而這正是最令我好奇之處。當時我剛從研究所畢業,主要的研究興趣是人在學習事物或發展一項技能時的心智運作。為了畢業論文,我還修改了「放聲思考法」這項特別設計來研究這種心智運作過程的心理學研究工具。所以,我與知名的卡內基美隆大學心理學教授比爾‧查斯合作,重新進行馬汀和凡保格的實驗,這一次我會仔細觀察實驗對象究竟如何改善數字記憶——假如他辦得到的話。
突破限制,展現驚人記憶力
我們招募到的受試者叫史提夫‧法隆,是典型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部學生。主修心理學的他對幼兒期發展格外有興趣,當時剛完成大三的課程,成就測驗的分數和一般卡內基美隆的學生差不多,成績等級則稍微高於平均。他體型高瘦,有著濃密的深金色頭髮,和善外向又熱情,還熱中跑步,最後這一點當時似乎不具特別意義,後來對我們的研究卻至關重要。
史提夫第一天來執行記憶任務的表現一如平均值。他通常可以記住七位數,八位數有時也不成問題,表現和街上隨機選出的人差不多。星期二、三、四,他稍有進步,可以記住的位數接近九個,卻還是沒有優於平均值。史提夫認為和第一天的主要差異在於他已經熟悉記憶力測試,所以較為自在。那個星期四的測試進行到尾聲時,史提夫向我解釋他為何擔心自己難有進步。接著,星期五發生了一件扭轉全局的事——史提夫找到方法突破瓶頸了。訓練過程如下:我先隨機念出一個五位數數字,如果史提夫一如往常可以正確重述,我便增加到六位數,六位數也正確重述了,就增加到七位數,以此類推,每次重述正確時便增加數字的長度;若重述錯誤,我便減少兩位數,重新再來。如此,史提夫面臨的挑戰持續增加,卻不至於過度,接收到的數字位數正好在他記得住和記不住的極限上。
而在那個星期五,史提夫拓展了極限。在此之前,他僅成功記住九位數幾次,從未能正確重述一個十位數數字,所以根本還沒有機會嘗試十一位數以上的挑戰。但這第五回合的實驗,他一開始就勢如破竹,前三次(五、六、七位數)成功過關,第四次挑戰失敗,重新再來——六位數正確,七位數正確,八位數正確,九位數正確。然後,我念出一個十位數——5718866610——他也重述無誤。接下來的十一位數未能成功,可是重新通過九位數和十位數的測試後,我念出第二個十一位數——90756629867——他從頭到尾完美重述了出來。這一關比他之前的成功紀錄多出兩位數,雖然多兩位數看似沒什麼了不起,卻是一大躍進,因為過去幾天史提夫好像被「天生的」極限困住,頂多能將八、九位數存入短期記憶,現在卻找到了突破極限的方法。
我研究生涯中最令人驚奇的兩年便這麼展開了。從那天起,史提夫記憶一連串數字的能力緩慢但穩定地增強,第十六回合實驗時已可穩穩記住二十位數,遠遠超出比爾和我的預期;到了第一百多回,他便能背下四十位數,不僅打破歷史紀錄,連記憶術專家都望塵莫及,而他依然持續不懈地練習。我們共進行了兩百多回合,最後,他成功記下八十二位數——八十二!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這記憶力多令人稱奇。在此隨機列出一個八十二位數:
0326443449602221328209301020391832373927788917267653245037746120179094345510355530
想像一下,以每秒一個數字的速度聽到這串數字之後,要一個不漏地全數記下。這就是史提夫在參與這項為期兩年的實驗期間教自己做的事,他絲毫沒想過這有可能辦到,只是一週一週地勤下功夫而已。第4章 刻意練習的黃金法則
刻意練習的原則
簡單來說,刻意練習具有下列特色:
‧刻意練習培養的技能已經有其他人知道該怎麼做,也已建立成效頗佳的訓練技巧。設計練習方式及負責監督的老師或教練應該熟悉頂尖專家的能力,並清楚該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培養這些技能。
‧刻意練習只在跨出舒適圈後才能奏效,需要學生不斷嘗試去突破現階段的技能水準。這意味著幾乎得傾盡全力,所以往往不會太有樂趣。
‧刻意練習必須有定義清楚明確的目標,且往往涉及改進想要達到的表現的某個面向,而不能只設定模糊的整體改善目標。整體目標設定完成後,老師或教練會制訂計畫,其中的一連串改善細項便會累積成向前邁進的一大步。改進想要達到的表現的某個面向,可以讓學生看見自身表現已經藉由訓練改善了。
‧刻意練習是「刻意」進行的,也就是必須全神貫注,有意識地行動。光是遵從老師或教練的指導是不夠的,還得專注於自身練習的具體目標,才能適時調整,以掌控練習過程。
‧刻意練習包含意見回饋,並根據該回饋調整努力方向。訓練初期得到的意見回饋多來自老師或教練,他們會監控訓練過程、點出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隨著時間和經驗累積,學生也必須學會自我監督、察覺錯誤,隨之因應調整,而自我監督的本領則仰賴有效的心智表徵。
‧刻意練習既能產生有效的心智表徵,也仰賴心智表徵運作。提升表現和改善心智表徵相輔相成,表現提升了,心智表徵就變得更精細有效,然後反過來讓表現更上一層樓。心智表徵有助於監控練習和實際上場時的狀況,讓人以正確的方式行動,也能察覺錯誤,並加以改正。
‧刻意練習幾乎等於加強或調整先前習得的技能,必須著重該技能的特定面向,努力改善;而隨著時間過去,這一步一步的改善最終會打造出專家級表現。因為新技能以既有技能為基礎,老師必須在一開始就教導正確的基本功,這樣學生後來達到更高階的水準時,才不必從頭學習基本技能。
一萬小時法則根本不是個法則!?我於一九九三年發表了以柏林藝術大學小提琴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許多研究頂尖專家的科學文獻採用了這些發現,而多年來也有許多研究人員加以引用。然而,我們的研究結果卻是在二○○八年麥爾坎‧葛拉威爾出版《異數》一書後,才大大引起科學界以外的矚目。葛拉威爾談到成為某領域佼佼者的必要條件時,提出了聳動的「一萬小時法則」。根據這個法則,想要在多數領域中成為專家,必須花一萬個小時練習。我們的確在研究報告中提到,頂尖小提琴家二十歲前花在獨自練習的平均時數為一萬小時。葛拉威爾自己估計,披頭四樂團於一九六○年代初期在德國漢堡演出時花了約一萬個小時練習,比爾‧蓋茲也投注了約一萬個小時寫程式,發展出的技能才得以建立微軟、拓展企業。葛拉威爾建議,這基本上適用於任何領域:不下功夫練習一萬小時,就無法成為專家。
這個法則非常吸引人,而且很好記,如果那些小提琴家二十歲前投入的練習時間是一萬一千小時,就不那麼朗朗上口了。此外,這個說法也滿足了人對於簡單因果關係的偏好:在任何事物上只要花一萬個小時練習,便能成為高手。
可惜,這個法則有諸多錯誤(其中倒是有一項正確的論述十分重要,稍後會說明),卻是現在許多人對練習成效的唯一了解。
首先,一萬小時毫不特別,也不具任何魔力。葛拉威爾大可提出頂尖小提琴學生到十八歲時平均投入的練習時數,也就是約七千四百小時,結果卻決定採用他們到二十歲時累積的練習時數,就因為那是個漂亮的整數。無論採用哪個數字,那些學生當時的程度絕對不到小提琴大師等級,雖然表現優異、前途看好,的確很可能在該領域出人頭地,但參與我們的研究時,他們還有漫漫長路要走。贏得國際鋼琴競賽的鋼琴家大約都得熬到三十歲才有此成就,那時的他們大概都已投入兩萬到兩萬五千個小時練習,一萬小時等於才走到半路。
而練習時數也因領域不同有所差異。史提夫‧法隆才花了兩百個小時練習,就成為記憶長串數字的世界第一人。雖然我不清楚現今最頂尖的數字記憶專家在成為世界第一之前究竟投資了多少時間,但應該遠低於一萬小時。頁數 6/7
第二,頂尖小提琴家到二十歲時累積的一萬小時只是平均值,該組的十位小提琴學生中,有一半到了二十歲時根本還沒累積一萬小時的練習。葛拉威爾誤解了這一點,還錯誤地宣稱該組小提琴學生「全部」累積了一萬小時的練習時數。
第三,葛拉威爾並未將我們研究的音樂家使用的刻意練習法,和其他任何可稱為「練習」的活動區分開來。例如,他提出的一項重要佐證,是披頭四於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在漢堡一場接一場演出期間,累積的時數符合一萬小時法則。葛拉威爾表示,他們約有一千兩百場表演,每場長達八小時,總計將近一萬小時。馬克‧路威森於二○一三年出版了詳盡描寫披頭四的傳記《調諧》,書中針對這一點提出質疑,並詳細分析,指出一千一百小時的演奏時數比較貼近事實。所以,披頭四花了遠少於一萬小時練習,就成為世界級的成功人物。然而,更重要的是,「演奏」和「練習」並不相同。當然,披頭四必定因為在漢堡長時間的演奏而功力大增,夜復一夜地演奏同樣的樂曲格外有幫助,這讓他們有機會從聽眾或自身得到演奏方面的意見回饋,並尋找方法改進。不過,在聽眾面前演奏一小時的重點在於傾全力完美演出,這不同於有目標地專注練習一小時,全心放在處理某些弱點,改善某些部分,而這種練習正是讓柏林藝術大學小提琴學生進步的關鍵。
路威森還提出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披頭四的成功不在於完美演出他人的樂曲,而在於樂團本身的音樂創作能力。因此,如果要從練習的角度解釋披頭四為何成功,必須找出約翰‧藍儂和保羅‧麥卡尼兩大創作主力的作曲能力是如何發展、改善而來的。披頭四在漢堡一場場演出累積的時數對藍儂和麥卡尼的作曲能力幾乎沒有幫助,所以披頭四的成功應該從別的角度解釋。
鎖定特定目標的刻意練習和一般練習法之間的差異顯著,因為並非每種練習方式都能帶來我們在音樂學生和芭蕾舞者身上看見的技能進步。一般而言,刻意練習和設計來達成特定目標的相關練習法,都包含個人化訓練,這些多得獨自進行的訓練活動就是為了加強某部分的表現。一萬小時法則還有最後一個漏洞。儘管葛拉威爾自己並未表示只要練習一萬個小時,幾乎人人都能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許多人卻將之詮釋為一個「承諾」,以為這麼做絕對奏效。可是,我的研究完全沒有暗示這一點。若要呈現這樣的結果,我當初就必須讓隨機選出的受試者以刻意練習法練習小提琴一萬個小時,然後探究成果。我們的研究其實只單純指出,在程度好到足以進入柏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就讀的學生中,頂尖學生花在獨自練習的時間平均比傑出組的學生多很多,而頂尖組和傑出組的學生又比優等組學生花了更多時間獨自練習。
是否人人都能透過足夠的費心練習成為自身領域中的頂尖專家,這點有待討論,我也會在下一章就此分享想法,不過當初的研究絕對沒有提出這一點。
葛拉威爾倒是說對了一件事,也是值得重述的關鍵:如果所處領域有著人們努力變成專家的歷史背景,想有卓越表現,就得長年投入極大量的精力,就算未必是整整一萬小時,也必定是非常可觀的時數。
我當時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史提夫是大學部的學生,被請來執行一項簡單的任務:記憶長串數字。他一週來幾次,我會以一秒一個的速度對他念出一串數字,例如:「7……4……0……1……1……9……」史提夫要試著全數記住,等我念完後重述。實驗目的之一在測試史提夫能藉由練習進步多少。而在進行四回實驗之後,他已經能熟記相當於本地電話號碼長度的七位數,八位數的表現通常也無誤,但九位數的成功機率不太穩定,十位數則完全辦不到。他當時因為頭幾回的表現而感到沮喪,深信自己不可能有進展。
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史提夫卻不知道——當時幾乎所有心理學研究都站在他那一邊。幾十年的研究顯示,人類短期記憶能夠記住的物品數量絕對有極限(短期記憶是大腦用來在短時間內保存少量資訊的一種記憶類型)。我們利用短期記憶把朋友給的地址保留到將它寫下來;在腦海中進行二位數乘法時,短期記憶會記錄中間所有的運算步驟:「好,27乘以14……首先,4乘以7等於28,8留下來,2進到十位,然後4乘以2等於8……」諸如此類。這種記憶類型之所以被稱為「短期」其來有自,因為除非花時間一次次複誦那個地址或中間那些運算的數字,以存入長期記憶中,否則五分鐘後便忘了。
史提夫面對的是短期記憶的問題:大腦靠短期記憶同時記下的物品數量明顯有極限。有些人可以記六項,有些人記七、八項沒問題,不過七項是一般人的極限,所以能夠記住七位數的本地電話號碼,卻記不住九個數字組成的社會安全號碼。長期記憶就沒有這樣的限制,其上限甚至無人知曉,但想有效利用卻得花更長的時間。只要投注足夠的時間,便能記住幾十組,甚至上百組電話號碼,不過我在測試史提夫時故意迅速讀出數字,迫使他只能運用短期記憶。一秒一個數字的速度快到他無法將數字轉存到長期記憶中,難怪他在八位數或九位數的地方會碰壁。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史提夫能有些微的進步。會想進行這項研究,是因為我在閱覽老舊的科學實驗文獻時發現一篇不起眼的報告——寶琳‧馬汀和山謬‧凡保格這兩位賓州大學的心理學家一九二九年發表在《美國心理學期刊》的文章。馬汀和凡保格表示,兩名大學生受試者經過四個月的練習後,成功增加了可以記住的數字位數(聽取的速度也是一秒鐘一個數字),其中一名學生從一般的九位數進步到十三位數,另一個則從十一位數進步到十五位數。
心理學界多忽略或遺忘了這項結果,我卻眼睛為之一亮:這種進步真的有可能嗎?若有可能發生,是怎麼辦到的?馬汀和凡保格並未詳細說明那兩名學生如何增進對數字的記憶,而這正是最令我好奇之處。當時我剛從研究所畢業,主要的研究興趣是人在學習事物或發展一項技能時的心智運作。為了畢業論文,我還修改了「放聲思考法」這項特別設計來研究這種心智運作過程的心理學研究工具。所以,我與知名的卡內基美隆大學心理學教授比爾‧查斯合作,重新進行馬汀和凡保格的實驗,這一次我會仔細觀察實驗對象究竟如何改善數字記憶——假如他辦得到的話。
突破限制,展現驚人記憶力
我們招募到的受試者叫史提夫‧法隆,是典型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部學生。主修心理學的他對幼兒期發展格外有興趣,當時剛完成大三的課程,成就測驗的分數和一般卡內基美隆的學生差不多,成績等級則稍微高於平均。他體型高瘦,有著濃密的深金色頭髮,和善外向又熱情,還熱中跑步,最後這一點當時似乎不具特別意義,後來對我們的研究卻至關重要。
史提夫第一天來執行記憶任務的表現一如平均值。他通常可以記住七位數,八位數有時也不成問題,表現和街上隨機選出的人差不多。星期二、三、四,他稍有進步,可以記住的位數接近九個,卻還是沒有優於平均值。史提夫認為和第一天的主要差異在於他已經熟悉記憶力測試,所以較為自在。那個星期四的測試進行到尾聲時,史提夫向我解釋他為何擔心自己難有進步。接著,星期五發生了一件扭轉全局的事——史提夫找到方法突破瓶頸了。訓練過程如下:我先隨機念出一個五位數數字,如果史提夫一如往常可以正確重述,我便增加到六位數,六位數也正確重述了,就增加到七位數,以此類推,每次重述正確時便增加數字的長度;若重述錯誤,我便減少兩位數,重新再來。如此,史提夫面臨的挑戰持續增加,卻不至於過度,接收到的數字位數正好在他記得住和記不住的極限上。
而在那個星期五,史提夫拓展了極限。在此之前,他僅成功記住九位數幾次,從未能正確重述一個十位數數字,所以根本還沒有機會嘗試十一位數以上的挑戰。但這第五回合的實驗,他一開始就勢如破竹,前三次(五、六、七位數)成功過關,第四次挑戰失敗,重新再來——六位數正確,七位數正確,八位數正確,九位數正確。然後,我念出一個十位數——5718866610——他也重述無誤。接下來的十一位數未能成功,可是重新通過九位數和十位數的測試後,我念出第二個十一位數——90756629867——他從頭到尾完美重述了出來。這一關比他之前的成功紀錄多出兩位數,雖然多兩位數看似沒什麼了不起,卻是一大躍進,因為過去幾天史提夫好像被「天生的」極限困住,頂多能將八、九位數存入短期記憶,現在卻找到了突破極限的方法。
我研究生涯中最令人驚奇的兩年便這麼展開了。從那天起,史提夫記憶一連串數字的能力緩慢但穩定地增強,第十六回合實驗時已可穩穩記住二十位數,遠遠超出比爾和我的預期;到了第一百多回,他便能背下四十位數,不僅打破歷史紀錄,連記憶術專家都望塵莫及,而他依然持續不懈地練習。我們共進行了兩百多回合,最後,他成功記下八十二位數——八十二!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這記憶力多令人稱奇。在此隨機列出一個八十二位數:
0326443449602221328209301020391832373927788917267653245037746120179094345510355530
想像一下,以每秒一個數字的速度聽到這串數字之後,要一個不漏地全數記下。這就是史提夫在參與這項為期兩年的實驗期間教自己做的事,他絲毫沒想過這有可能辦到,只是一週一週地勤下功夫而已。第4章 刻意練習的黃金法則
刻意練習的原則
簡單來說,刻意練習具有下列特色:
‧刻意練習培養的技能已經有其他人知道該怎麼做,也已建立成效頗佳的訓練技巧。設計練習方式及負責監督的老師或教練應該熟悉頂尖專家的能力,並清楚該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培養這些技能。
‧刻意練習只在跨出舒適圈後才能奏效,需要學生不斷嘗試去突破現階段的技能水準。這意味著幾乎得傾盡全力,所以往往不會太有樂趣。
‧刻意練習必須有定義清楚明確的目標,且往往涉及改進想要達到的表現的某個面向,而不能只設定模糊的整體改善目標。整體目標設定完成後,老師或教練會制訂計畫,其中的一連串改善細項便會累積成向前邁進的一大步。改進想要達到的表現的某個面向,可以讓學生看見自身表現已經藉由訓練改善了。
‧刻意練習是「刻意」進行的,也就是必須全神貫注,有意識地行動。光是遵從老師或教練的指導是不夠的,還得專注於自身練習的具體目標,才能適時調整,以掌控練習過程。
‧刻意練習包含意見回饋,並根據該回饋調整努力方向。訓練初期得到的意見回饋多來自老師或教練,他們會監控訓練過程、點出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隨著時間和經驗累積,學生也必須學會自我監督、察覺錯誤,隨之因應調整,而自我監督的本領則仰賴有效的心智表徵。
‧刻意練習既能產生有效的心智表徵,也仰賴心智表徵運作。提升表現和改善心智表徵相輔相成,表現提升了,心智表徵就變得更精細有效,然後反過來讓表現更上一層樓。心智表徵有助於監控練習和實際上場時的狀況,讓人以正確的方式行動,也能察覺錯誤,並加以改正。
‧刻意練習幾乎等於加強或調整先前習得的技能,必須著重該技能的特定面向,努力改善;而隨著時間過去,這一步一步的改善最終會打造出專家級表現。因為新技能以既有技能為基礎,老師必須在一開始就教導正確的基本功,這樣學生後來達到更高階的水準時,才不必從頭學習基本技能。
一萬小時法則根本不是個法則!?我於一九九三年發表了以柏林藝術大學小提琴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許多研究頂尖專家的科學文獻採用了這些發現,而多年來也有許多研究人員加以引用。然而,我們的研究結果卻是在二○○八年麥爾坎‧葛拉威爾出版《異數》一書後,才大大引起科學界以外的矚目。葛拉威爾談到成為某領域佼佼者的必要條件時,提出了聳動的「一萬小時法則」。根據這個法則,想要在多數領域中成為專家,必須花一萬個小時練習。我們的確在研究報告中提到,頂尖小提琴家二十歲前花在獨自練習的平均時數為一萬小時。葛拉威爾自己估計,披頭四樂團於一九六○年代初期在德國漢堡演出時花了約一萬個小時練習,比爾‧蓋茲也投注了約一萬個小時寫程式,發展出的技能才得以建立微軟、拓展企業。葛拉威爾建議,這基本上適用於任何領域:不下功夫練習一萬小時,就無法成為專家。
這個法則非常吸引人,而且很好記,如果那些小提琴家二十歲前投入的練習時間是一萬一千小時,就不那麼朗朗上口了。此外,這個說法也滿足了人對於簡單因果關係的偏好:在任何事物上只要花一萬個小時練習,便能成為高手。
可惜,這個法則有諸多錯誤(其中倒是有一項正確的論述十分重要,稍後會說明),卻是現在許多人對練習成效的唯一了解。
首先,一萬小時毫不特別,也不具任何魔力。葛拉威爾大可提出頂尖小提琴學生到十八歲時平均投入的練習時數,也就是約七千四百小時,結果卻決定採用他們到二十歲時累積的練習時數,就因為那是個漂亮的整數。無論採用哪個數字,那些學生當時的程度絕對不到小提琴大師等級,雖然表現優異、前途看好,的確很可能在該領域出人頭地,但參與我們的研究時,他們還有漫漫長路要走。贏得國際鋼琴競賽的鋼琴家大約都得熬到三十歲才有此成就,那時的他們大概都已投入兩萬到兩萬五千個小時練習,一萬小時等於才走到半路。
而練習時數也因領域不同有所差異。史提夫‧法隆才花了兩百個小時練習,就成為記憶長串數字的世界第一人。雖然我不清楚現今最頂尖的數字記憶專家在成為世界第一之前究竟投資了多少時間,但應該遠低於一萬小時。頁數 6/7
第二,頂尖小提琴家到二十歲時累積的一萬小時只是平均值,該組的十位小提琴學生中,有一半到了二十歲時根本還沒累積一萬小時的練習。葛拉威爾誤解了這一點,還錯誤地宣稱該組小提琴學生「全部」累積了一萬小時的練習時數。
第三,葛拉威爾並未將我們研究的音樂家使用的刻意練習法,和其他任何可稱為「練習」的活動區分開來。例如,他提出的一項重要佐證,是披頭四於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在漢堡一場接一場演出期間,累積的時數符合一萬小時法則。葛拉威爾表示,他們約有一千兩百場表演,每場長達八小時,總計將近一萬小時。馬克‧路威森於二○一三年出版了詳盡描寫披頭四的傳記《調諧》,書中針對這一點提出質疑,並詳細分析,指出一千一百小時的演奏時數比較貼近事實。所以,披頭四花了遠少於一萬小時練習,就成為世界級的成功人物。然而,更重要的是,「演奏」和「練習」並不相同。當然,披頭四必定因為在漢堡長時間的演奏而功力大增,夜復一夜地演奏同樣的樂曲格外有幫助,這讓他們有機會從聽眾或自身得到演奏方面的意見回饋,並尋找方法改進。不過,在聽眾面前演奏一小時的重點在於傾全力完美演出,這不同於有目標地專注練習一小時,全心放在處理某些弱點,改善某些部分,而這種練習正是讓柏林藝術大學小提琴學生進步的關鍵。
路威森還提出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披頭四的成功不在於完美演出他人的樂曲,而在於樂團本身的音樂創作能力。因此,如果要從練習的角度解釋披頭四為何成功,必須找出約翰‧藍儂和保羅‧麥卡尼兩大創作主力的作曲能力是如何發展、改善而來的。披頭四在漢堡一場場演出累積的時數對藍儂和麥卡尼的作曲能力幾乎沒有幫助,所以披頭四的成功應該從別的角度解釋。
鎖定特定目標的刻意練習和一般練習法之間的差異顯著,因為並非每種練習方式都能帶來我們在音樂學生和芭蕾舞者身上看見的技能進步。一般而言,刻意練習和設計來達成特定目標的相關練習法,都包含個人化訓練,這些多得獨自進行的訓練活動就是為了加強某部分的表現。一萬小時法則還有最後一個漏洞。儘管葛拉威爾自己並未表示只要練習一萬個小時,幾乎人人都能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許多人卻將之詮釋為一個「承諾」,以為這麼做絕對奏效。可是,我的研究完全沒有暗示這一點。若要呈現這樣的結果,我當初就必須讓隨機選出的受試者以刻意練習法練習小提琴一萬個小時,然後探究成果。我們的研究其實只單純指出,在程度好到足以進入柏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就讀的學生中,頂尖學生花在獨自練習的時間平均比傑出組的學生多很多,而頂尖組和傑出組的學生又比優等組學生花了更多時間獨自練習。
是否人人都能透過足夠的費心練習成為自身領域中的頂尖專家,這點有待討論,我也會在下一章就此分享想法,不過當初的研究絕對沒有提出這一點。
葛拉威爾倒是說對了一件事,也是值得重述的關鍵:如果所處領域有著人們努力變成專家的歷史背景,想有卓越表現,就得長年投入極大量的精力,就算未必是整整一萬小時,也必定是非常可觀的時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