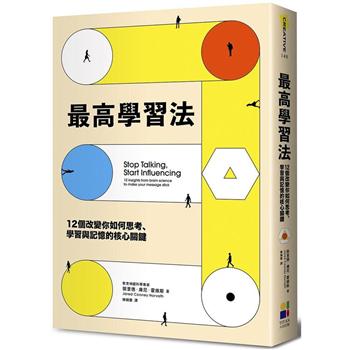文本和口語
閱讀即是靜默的對談,除此無他。—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
想像現在是星期五晚上,你跟朋友坐在擁擠的酒吧,兩人各自點了杯貴森森的精釀啤酒。周遭的人扯著嗓門暢談過去這一星期的大小事,環境嘈雜不休。不過,儘管整個酒吧鬧哄哄,你們卻還能維持脈絡清晰的對談。沒錯,身邊幾十個人同時在說話,你們可能得大聲嚷嚷,對方才聽得見,可是你輕易就能鎖定目標,聽懂你朋友的話。
接著想像現在是星期三下午,你與同事圍坐在大型會議桌旁,在你的人體工學滑輪辦公椅上輕輕搖呀晃的。有個人在前面做簡報,PowerPoint投影片上滿是標題、要點和參考文獻。簡報的人肯定知識豐富幽默風趣,可是不管你怎麼努力,卻好像始終沒辦法專心,很難理解簡報內容。
表面上看來,以上兩種假想情境可說天差地別,但如果我告訴你,你在熱鬧的酒吧之所以還能跟人順暢談天,原因就跟你記不住簡報大多數內容相同,你會怎麼想?要了解這兩種情境之間的相關性,你只需要把注意力轉移到你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閱讀。
閱讀的祕史
我們傾向認為閱讀主要是一種無聲活動。除了偶爾的輕聲咳嗽或尷尬竊笑,圖書館給人的印象向來不是喧譁場所。
因此,當你知道無聲閱讀並非自古皆然,可能會覺得詫異。事實上,在第七世紀末以前,大聲朗讀是最普遍的閱讀方式。古代的圖書館並不是寧靜安詳的避風港,反倒可能充滿喋喋不休的話語,因為就連個別讀者也會對自己念念有詞。過去的時代無聲閱讀太稀有,聖‧奧古斯丁因此認為值得在他影響深遠的著作《懺悔錄》裡一提。「安波羅斯讀書的時候,他的眼睛掃視一行行文字,他的心靈搜尋那些文字的意義,他的嗓子和舌頭都靜止不動。經常……我看著他默默地閱讀—其實從沒見過他閱讀時發出聲音—不禁自問:他為什麼用這種方式閱讀?」
古代文字的書寫方式有助於有聲閱讀的發展說得更明確點古代文本單字與單字之間沒有空格沒有標點符號也沒有大寫字母事實上如果你走一趟住家附近的圖書館或博物館可能會找到很多以這種方式書寫的古希臘與拉丁文手稿這種書寫方式名為「連書」(scriptura continua),它證明閱讀主要是一種口頭活動。如果文本是拿來大聲朗誦的,那又何必使用空格、標點符號或大寫?要了解這話的意思,只要回頭大聲念出上一段文字:你可能會發現,即使你只有一丁點或完全不刻意,語言裡的很多面向,比如速度、抑揚頓挫或意圖,都自然而然在你的話聲中流露出來。閱讀是一種有聲活動,如果你覺得這個概念怪異或古老,只要看看四周:現代文明裡到處都看得到這種概念的傳承。大學課程(lecture)的基本型態就是某個人對一群聆聽者大聲讀出重要資訊(事實上,法文的lecture字面意思正是「閱讀」)。教會的儀式通常是某個人大聲對會眾閱讀。科學研討會、政治演說,甚至每週進度會報,都是根據古代個人在公共場合對群眾朗讀的模式演變而來。
到了第八世紀初,愛爾蘭修道士開始在字與字之間留出空格。後來這個潮流傳播到歐洲各地,無聲閱讀也隨之興起。所以,多虧一群古代修道士,你可以放心品讀這本書接下來的內容,不需要大聲念出來……
……真是這樣嗎?
只要稍加思索,就知道「無聲」閱讀這個概念不完全正確。你讀這個句子的時候,如果把注意力收回來,留意你大腦裡的狀態,很可能會立刻發現你聽見某個聲音。或者,更準確地說,聽見某個人的聲音。
有個聲音發自你大腦深處,隨著你的視線讀出每個字。你聽見的十之八九是你自己的聲音,但未必總是如此:
「我吃掉他的肝,配點蠶豆和上等奇揚地葡萄酒。」
「我沒有跟那位女士發生性行為。」
「那是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
假使你熟悉這幾句話,那麼你讀的時候很可能會聽見霍普金斯令人背脊發涼的清晰口吻、柯林頓慢條斯理的自信語氣,以及阿姆斯壯伴隨雜訊的聲音。原來,我們讀的文字如果跟某個特定的人有強烈連結,我們就會聽見他或她的聲音(當然,這種現象只限於我們對寫那些文字的人夠熟悉。我在想,此時此刻聽見我聲音的人,大概只有我母親。嗨,媽!)
很顯然,無聲閱讀原來並非無聲。可是,對於本章主題,這有什麼重要的嗎?為了弄明白我為什麼帶著你旋風似的回顧閱讀歷史,我們需要暫時換個檔,探討另一個看似無關的話題。
事倍,功半
實驗一
做這個實驗你需要兩種口語的聲音來源(我發現最便利的組合是一台電視加一台收音機)。
1、打開電視,找個「人頭在說話」的節目。
內容不重要,可以是新聞報導,可以是運動論壇,可以是天氣預報,只要找個有人說話的頻道就行。
2、打開收音機,轉到某個調幅電台的「談話」節目。同樣地,有人說話就好,內容無所謂。
3、你的目標是同時聽懂電視和收音機裡的人各自在說什麼。試試吧……
你可能會發現你辦不到(而且覺得煩躁)。或許你也發現你能夠聽懂電視裡的人說的話,但你必須忽略收音機的聲音才能辦得到。或許你還發現你能察覺得到你的注意力在兩種聲源之間「跳接」的時刻,幾乎就像你腦子裡有個實體開關。
科學家稱這種實驗為雙耳分聽(dichotic listening),它證明我們雖然可以同時聆聽很多人說話,同一時間卻只能真正理解一個人的說話內容。重點來了:我們想要同時聽懂兩串不同的口語(如上述實驗),結果卻是什麼都聽不懂!那有點像同時觀看兩集你最喜歡的電視劇:雖然兩集內容彼此相關(同樣的人物、同樣的音樂、同樣的劇情),你的注意力可能會被迫快速來回移轉。你這麼做的時候,很容易就會錯過兩集的重要訊息。一段時間以後,你看過的內容變得支離破碎、沒有意義,你只覺得不確定又困惑(剛才說這個人是誰來著?她為什麼突然發脾氣?等等,艾德.史塔克上哪兒去了?)
要了解雙耳分聽為什麼行不通,我們需要快速參觀一下我們的大腦。
我們的大腦有三個主要區域幫助我們理解口說語言。第一個是聽覺皮質區(auditory cortex)。這個部分負責處理聲音的基本特性,比如音調與音量。重點在於,你的大腦兩邊都有這個區域。這就是為什麼剛才的實驗裡你能同時聽見電視和收音機的聲音:你的大腦有足夠的神經資產,可以輕而易舉處理來自左右耳的聲音。當然,實驗的目標不只是聽見兩種聲源,而是理解那兩串聲音訊息。
下一個幫助我們理解口語的區域是布洛卡╲威尼克網絡(Broca/Wernicke network)。這個區域處理並理解口說語言。重點在於,這個網絡只存在你大腦的單側(大多數人在左側)。意思是,雖然口說語言的基本聲音一開始是在大腦的左右兩側處理,最後還是得匯集到這個單一腦部網絡。相信你已經猜到了,這很容易形成瓶頸。
負責控制這個瓶頸的,是大腦協助我們理解口說語言的第三個區域:左額下迴(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我們同時聽兩個人說話時,一般認為這個區域有效攔阻其中一個聲音,允許另一個聲音通過布洛卡╲威尼克瓶頸。這就是你在實驗裡可能感受到的那個「開關」。基本上,當你的注意力在電視與收音機之間來回跳動,你的左額下迴也忙著輪流攔阻兩道聲音訊息。我經常把這個瓶頸想像成幾十個趕路的旅客爭相擠進機場的安檢隊伍。這個比喻有個地方不恰當,因為只要時間足夠,所有旅客最後都能順利通關,搭上各自的飛機。然而,布洛卡╲威尼克網絡卻不是這樣。當下沒能通過瓶頸的資訊徹底消失,沒有備份、也沒有等待區。事實上,被左額下迴擋駕的口說語言永遠消失了,你再也無法取得或處理那些訊息。
好了,我們來整理一下。
給領導人、教學者與教練的提示
1、投影片不使用(或只用極少)文字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如今的會議室、教室或球員休息室是投影片當道。遺憾的是,很多人只是把這些工具當成小抄卡的懶人替代品,在每一張投影片裡填滿大量文字(「如果我忘了提到某個重要話題,聽講的人可以在我背後的投影片裡讀到。」)
現在你應該已經明白這種做法為什麼沒用。正如你沒辦法邊讀這本書邊聽電視,台下的人也沒辦法邊讀投影片邊聽你說話:某些東西一定會在布洛卡╲威尼克瓶頸被阻擋、消除。結果會怎樣?聽講者的注意力通常會在你與投影片之間轉換,因此錯過兩邊的重要訊息。事實上,不少研究證實,以單一方式(口頭或書面)接收訊息的人,在理解與記憶方面的表現,總是優於同時以兩種方式(口頭及書面)接收訊息的人。
因此,下回你做簡報的時候,別在PowerPoint投影片裡放太多文字(假如你擔心記不住簡報過程中想討論的所有重點,不妨製作一系列方便拿在手上讀的小抄卡)。
等一等,如果在投影片裡置入文字會妨礙學習,那麼我們該在投影片放些什麼來增進學習效果?這個我們下一章再討論。
緊迫問題一:關鍵字
「如果投影片裡有一些字,但不多呢?比如說,我能不能在投影片裡放些關鍵字?」
有趣的是,我們只有在連續閱讀大量文字,比如完整的句子、段落或塞滿文字的投影片,才需要在腦海裡把書面文字轉換為口說語言。
如果讀的是少量非常熟悉的文字,我們不需要在心裡默念,可以直接理解它們的意思。
基於這個理由,在每張投影片裡放進極少量的關鍵字(通常不超過七個字),也許不至於干擾聽講者聽你說話。
然而,就像上面說的,下一章我們會探討哪些附加教材可以幫助聽講者理解簡報內容。
多工能力
一個人能一面安穩地開車、一面接吻,只是因為接吻不夠認真。—無名氏
這章開始先來個小遊戲。玩這個遊戲你需要紙、筆和計時器。 第一回合
這個回合你的目標是在十秒內完成兩項不同任務。
1、將紙張分為左右兩欄。
2、計時器設定十秒。
3、計時器開始後,在左邊那欄由上而下依序寫出從A到L十二個英文字母。用最快的速度完成。
4、字母完成後,在右邊那欄由上而下依序寫出1到12的阿拉伯數字。同樣地,用最快的速度完成。
看看你能不能在十秒內寫出共二十四個字母與數字。
預備……開始!
我猜時間結束前你順利完成,或者接近尾聲。接下來我們再玩一次,不過這回我們做個小小改變......
第二回合
這個回合你的目標是完成跟上面一樣的兩項任務,只是這次你要在兩項任務之間快速輪動。
1、紙張分成左右兩欄。
2、計時器設定十秒。
3、計時器開始後,在左邊欄位寫第一個英文字母(A),接著在右邊寫第一個數字(1),接著左邊寫第二個字母(B),右邊寫第二個數字(2),以此類推。
同樣地,看看你能不能在十秒內寫出全部二十四個字母與數字。
預備……開始!
如果你跟大多數人一樣,這回可能兩邊各完成大約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雖然這項任務不算特別困難,你卻可能發現自己愈來愈慌,出了幾個錯,也許重複同一個數字,或需要在心裡默念英文字母,才能想起下一個字母。
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第二回合難度比第一回合高?
注意力過濾器
這個世界混亂無序。
我寫這些字的時候,坐在擁擠的咖啡館裡,幾十個顧客川流不息從我桌子旁走過,義式濃縮咖啡機在我耳畔嘶嘶作響,兩個女孩嘰嘰喳喳爭論某個名叫查德的男孩的課外活動。
周遭這麼多喧囂,能夠完成任何事都算奇蹟。然而,我們不知怎的竟能穿越那片喧鬧,專注在那些當時對我們有意義的景象、聲音、滋味、氣味和感受。
這就是注意力的力量。
要了解注意力如何運作,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它想像成過濾器。
注意力很像我們小時候戴的那種只允許特定波長的光線通過的3D眼鏡,它只容許相關資訊進入有意識的覺知(conscious awareness),阻擋不相關的資訊。
我們在上一章學過,被判定為不相關的資訊同樣會進入我們的記憶(情境與狀態依賴),卻不會被有意識地處理。這就引出一個重要問題:什麼東西判定某筆資訊有相關性?答案取決於我們從事的特定任務。
正如桌遊,我們從事的所有任務(不管是寫電子郵件、統計帳單,或只是出門遛狗)都伴隨一組獨特的規則,限定需要哪些行動才算「達成」。
比方說,為了順利讀完目前這些文字,你的閱讀規則集(ruleset)限定你的視線必須沿著每一行由上而下移動、在句子結束前記住每一個字、用手指翻頁等等。
我們從事某項任務時,相關規則集必須先載入腦部一個名為側前額葉皮質(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我們簡稱LatPFC)的小區域。
載入LatPFC的特定規則集會決定哪些資訊相關、哪些又不相關。
比方說,此刻你的閱讀規則集載入你的LatPFC,調整你的注意力過濾器,允許這些橫橫豎豎的黑色筆畫進入有意識的覺知,在此同時阻擋紙頁在你指尖的觸感、本頁底部的章名,以及你周遭的任何聲響等等。
我經常以一九八○年代的舊式電視遊樂器系統比喻這整個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款遊戲(任務)有一組獨特的角色、控制鈕和目標(規則集)。
任何時候你想玩某一款遊戲,就把相關的卡匣插入遊戲機(LatPFC)。遊戲載入後,電視螢幕就會顯示那款遊戲的主角、壞蛋、武器等等(注意力過濾器)。
有個簡單的方法可以了解這兩套網絡如何運作,那就是想像汽車駕訓班那種有兩套方向盤的教練車。
大多數時候汽車由學員駕駛(背側網絡),有意識地專心以某種特定方式行駛、轉彎。
然而,默默坐在旁邊的教練(腹側網絡)始終提高警覺,隨時覺察周遭世界,萬一發生危險,可以立刻接手。
緊迫問題一:邊走邊說
「如果不可能一心多用,那麼我為什麼可以邊走路邊嚼口香糖?」
說得對!
真相是,我們每天都一心多用。我們邊吃東西邊聊天;邊淋浴邊唱歌;邊慢跑邊思考工作計畫。
有趣的來了。如果你細看這些例子,每個都包含紋狀體操控的慣性動作。
很可能你已經精通吃東西、淋浴和慢跑這些事,也就是可以不假思索地執行這些技能。
這代表我們可以同時執行兩項任務,只要其中一項出於習慣,不需要太多思考。
話說回來,你是否曾吃飯時跟人聊天,聊著聊著忘了吃?或者唱歌唱得太投入、心不在焉地倒了兩次洗髮精?或者太擔心某個計畫,慢跑時意外絆跤?
即使其中一項任務是慣性動作,仍然不能確保一心多用的效率。規則集、過濾器和目標還是可能混淆,以至於影響反應速度、表現與記憶。
甚至,超過某個年齡之後,就連邊走路邊說話這種慣性任務都可能互相干擾(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上了年紀的人會站在原地聊天)。
所以說,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當然辦得到,但這不代表我們能一心多用。
緊迫問題三:記憶抹除
「有時候我走進某個房間,會突然忘記進去做什麼。這是怎麼回事?」
正如我們稍早學到,腹側注意力網絡一旦察覺威脅,就會自動卸除我們當下的規則集。這種狀況發生時,所有來不及送進海馬迴的資訊都會被有效抹除。這就像你每次翻到這本書的下一頁,就會忘記前一頁的最後一句。學者稱這種機制為事件模式清除(event-model purge),不過更通用的說法是記憶抹除(mind wipe)。
如果有隻飢餓的熊走近你,啟動這個機制還有點道理(畢竟小命不保,誰還在乎剛才在想什麼?)但我們只是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為什麼也會發生呢?
原來我們的腹側網絡有時候會把門口判定為威脅。雖然沒有人確定這是怎麼回事,但一般認為,當門框快速閃過我們的視野,大腦就會意識到危險,我們的規則集會重新設定,前一刻思考的任何資訊因此被抹除,這叫門口效應(doorway effect)。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打開冰箱,冰箱門快速在我們眼前晃過,我們突然忘記要拿什麼。
幸好,如果我們回到原本在的地方(或關上冰箱門),就能利用空間、情境和狀態三種引導提示,重建原有的思路,想起原本想做的事。
閱讀即是靜默的對談,除此無他。—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
想像現在是星期五晚上,你跟朋友坐在擁擠的酒吧,兩人各自點了杯貴森森的精釀啤酒。周遭的人扯著嗓門暢談過去這一星期的大小事,環境嘈雜不休。不過,儘管整個酒吧鬧哄哄,你們卻還能維持脈絡清晰的對談。沒錯,身邊幾十個人同時在說話,你們可能得大聲嚷嚷,對方才聽得見,可是你輕易就能鎖定目標,聽懂你朋友的話。
接著想像現在是星期三下午,你與同事圍坐在大型會議桌旁,在你的人體工學滑輪辦公椅上輕輕搖呀晃的。有個人在前面做簡報,PowerPoint投影片上滿是標題、要點和參考文獻。簡報的人肯定知識豐富幽默風趣,可是不管你怎麼努力,卻好像始終沒辦法專心,很難理解簡報內容。
表面上看來,以上兩種假想情境可說天差地別,但如果我告訴你,你在熱鬧的酒吧之所以還能跟人順暢談天,原因就跟你記不住簡報大多數內容相同,你會怎麼想?要了解這兩種情境之間的相關性,你只需要把注意力轉移到你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閱讀。
閱讀的祕史
我們傾向認為閱讀主要是一種無聲活動。除了偶爾的輕聲咳嗽或尷尬竊笑,圖書館給人的印象向來不是喧譁場所。
因此,當你知道無聲閱讀並非自古皆然,可能會覺得詫異。事實上,在第七世紀末以前,大聲朗讀是最普遍的閱讀方式。古代的圖書館並不是寧靜安詳的避風港,反倒可能充滿喋喋不休的話語,因為就連個別讀者也會對自己念念有詞。過去的時代無聲閱讀太稀有,聖‧奧古斯丁因此認為值得在他影響深遠的著作《懺悔錄》裡一提。「安波羅斯讀書的時候,他的眼睛掃視一行行文字,他的心靈搜尋那些文字的意義,他的嗓子和舌頭都靜止不動。經常……我看著他默默地閱讀—其實從沒見過他閱讀時發出聲音—不禁自問:他為什麼用這種方式閱讀?」
古代文字的書寫方式有助於有聲閱讀的發展說得更明確點古代文本單字與單字之間沒有空格沒有標點符號也沒有大寫字母事實上如果你走一趟住家附近的圖書館或博物館可能會找到很多以這種方式書寫的古希臘與拉丁文手稿這種書寫方式名為「連書」(scriptura continua),它證明閱讀主要是一種口頭活動。如果文本是拿來大聲朗誦的,那又何必使用空格、標點符號或大寫?要了解這話的意思,只要回頭大聲念出上一段文字:你可能會發現,即使你只有一丁點或完全不刻意,語言裡的很多面向,比如速度、抑揚頓挫或意圖,都自然而然在你的話聲中流露出來。閱讀是一種有聲活動,如果你覺得這個概念怪異或古老,只要看看四周:現代文明裡到處都看得到這種概念的傳承。大學課程(lecture)的基本型態就是某個人對一群聆聽者大聲讀出重要資訊(事實上,法文的lecture字面意思正是「閱讀」)。教會的儀式通常是某個人大聲對會眾閱讀。科學研討會、政治演說,甚至每週進度會報,都是根據古代個人在公共場合對群眾朗讀的模式演變而來。
到了第八世紀初,愛爾蘭修道士開始在字與字之間留出空格。後來這個潮流傳播到歐洲各地,無聲閱讀也隨之興起。所以,多虧一群古代修道士,你可以放心品讀這本書接下來的內容,不需要大聲念出來……
……真是這樣嗎?
只要稍加思索,就知道「無聲」閱讀這個概念不完全正確。你讀這個句子的時候,如果把注意力收回來,留意你大腦裡的狀態,很可能會立刻發現你聽見某個聲音。或者,更準確地說,聽見某個人的聲音。
有個聲音發自你大腦深處,隨著你的視線讀出每個字。你聽見的十之八九是你自己的聲音,但未必總是如此:
「我吃掉他的肝,配點蠶豆和上等奇揚地葡萄酒。」
「我沒有跟那位女士發生性行為。」
「那是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
假使你熟悉這幾句話,那麼你讀的時候很可能會聽見霍普金斯令人背脊發涼的清晰口吻、柯林頓慢條斯理的自信語氣,以及阿姆斯壯伴隨雜訊的聲音。原來,我們讀的文字如果跟某個特定的人有強烈連結,我們就會聽見他或她的聲音(當然,這種現象只限於我們對寫那些文字的人夠熟悉。我在想,此時此刻聽見我聲音的人,大概只有我母親。嗨,媽!)
很顯然,無聲閱讀原來並非無聲。可是,對於本章主題,這有什麼重要的嗎?為了弄明白我為什麼帶著你旋風似的回顧閱讀歷史,我們需要暫時換個檔,探討另一個看似無關的話題。
事倍,功半
實驗一
做這個實驗你需要兩種口語的聲音來源(我發現最便利的組合是一台電視加一台收音機)。
1、打開電視,找個「人頭在說話」的節目。
內容不重要,可以是新聞報導,可以是運動論壇,可以是天氣預報,只要找個有人說話的頻道就行。
2、打開收音機,轉到某個調幅電台的「談話」節目。同樣地,有人說話就好,內容無所謂。
3、你的目標是同時聽懂電視和收音機裡的人各自在說什麼。試試吧……
你可能會發現你辦不到(而且覺得煩躁)。或許你也發現你能夠聽懂電視裡的人說的話,但你必須忽略收音機的聲音才能辦得到。或許你還發現你能察覺得到你的注意力在兩種聲源之間「跳接」的時刻,幾乎就像你腦子裡有個實體開關。
科學家稱這種實驗為雙耳分聽(dichotic listening),它證明我們雖然可以同時聆聽很多人說話,同一時間卻只能真正理解一個人的說話內容。重點來了:我們想要同時聽懂兩串不同的口語(如上述實驗),結果卻是什麼都聽不懂!那有點像同時觀看兩集你最喜歡的電視劇:雖然兩集內容彼此相關(同樣的人物、同樣的音樂、同樣的劇情),你的注意力可能會被迫快速來回移轉。你這麼做的時候,很容易就會錯過兩集的重要訊息。一段時間以後,你看過的內容變得支離破碎、沒有意義,你只覺得不確定又困惑(剛才說這個人是誰來著?她為什麼突然發脾氣?等等,艾德.史塔克上哪兒去了?)
要了解雙耳分聽為什麼行不通,我們需要快速參觀一下我們的大腦。
我們的大腦有三個主要區域幫助我們理解口說語言。第一個是聽覺皮質區(auditory cortex)。這個部分負責處理聲音的基本特性,比如音調與音量。重點在於,你的大腦兩邊都有這個區域。這就是為什麼剛才的實驗裡你能同時聽見電視和收音機的聲音:你的大腦有足夠的神經資產,可以輕而易舉處理來自左右耳的聲音。當然,實驗的目標不只是聽見兩種聲源,而是理解那兩串聲音訊息。
下一個幫助我們理解口語的區域是布洛卡╲威尼克網絡(Broca/Wernicke network)。這個區域處理並理解口說語言。重點在於,這個網絡只存在你大腦的單側(大多數人在左側)。意思是,雖然口說語言的基本聲音一開始是在大腦的左右兩側處理,最後還是得匯集到這個單一腦部網絡。相信你已經猜到了,這很容易形成瓶頸。
負責控制這個瓶頸的,是大腦協助我們理解口說語言的第三個區域:左額下迴(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我們同時聽兩個人說話時,一般認為這個區域有效攔阻其中一個聲音,允許另一個聲音通過布洛卡╲威尼克瓶頸。這就是你在實驗裡可能感受到的那個「開關」。基本上,當你的注意力在電視與收音機之間來回跳動,你的左額下迴也忙著輪流攔阻兩道聲音訊息。我經常把這個瓶頸想像成幾十個趕路的旅客爭相擠進機場的安檢隊伍。這個比喻有個地方不恰當,因為只要時間足夠,所有旅客最後都能順利通關,搭上各自的飛機。然而,布洛卡╲威尼克網絡卻不是這樣。當下沒能通過瓶頸的資訊徹底消失,沒有備份、也沒有等待區。事實上,被左額下迴擋駕的口說語言永遠消失了,你再也無法取得或處理那些訊息。
好了,我們來整理一下。
給領導人、教學者與教練的提示
1、投影片不使用(或只用極少)文字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如今的會議室、教室或球員休息室是投影片當道。遺憾的是,很多人只是把這些工具當成小抄卡的懶人替代品,在每一張投影片裡填滿大量文字(「如果我忘了提到某個重要話題,聽講的人可以在我背後的投影片裡讀到。」)
現在你應該已經明白這種做法為什麼沒用。正如你沒辦法邊讀這本書邊聽電視,台下的人也沒辦法邊讀投影片邊聽你說話:某些東西一定會在布洛卡╲威尼克瓶頸被阻擋、消除。結果會怎樣?聽講者的注意力通常會在你與投影片之間轉換,因此錯過兩邊的重要訊息。事實上,不少研究證實,以單一方式(口頭或書面)接收訊息的人,在理解與記憶方面的表現,總是優於同時以兩種方式(口頭及書面)接收訊息的人。
因此,下回你做簡報的時候,別在PowerPoint投影片裡放太多文字(假如你擔心記不住簡報過程中想討論的所有重點,不妨製作一系列方便拿在手上讀的小抄卡)。
等一等,如果在投影片裡置入文字會妨礙學習,那麼我們該在投影片放些什麼來增進學習效果?這個我們下一章再討論。
緊迫問題一:關鍵字
「如果投影片裡有一些字,但不多呢?比如說,我能不能在投影片裡放些關鍵字?」
有趣的是,我們只有在連續閱讀大量文字,比如完整的句子、段落或塞滿文字的投影片,才需要在腦海裡把書面文字轉換為口說語言。
如果讀的是少量非常熟悉的文字,我們不需要在心裡默念,可以直接理解它們的意思。
基於這個理由,在每張投影片裡放進極少量的關鍵字(通常不超過七個字),也許不至於干擾聽講者聽你說話。
然而,就像上面說的,下一章我們會探討哪些附加教材可以幫助聽講者理解簡報內容。
多工能力
一個人能一面安穩地開車、一面接吻,只是因為接吻不夠認真。—無名氏
這章開始先來個小遊戲。玩這個遊戲你需要紙、筆和計時器。 第一回合
這個回合你的目標是在十秒內完成兩項不同任務。
1、將紙張分為左右兩欄。
2、計時器設定十秒。
3、計時器開始後,在左邊那欄由上而下依序寫出從A到L十二個英文字母。用最快的速度完成。
4、字母完成後,在右邊那欄由上而下依序寫出1到12的阿拉伯數字。同樣地,用最快的速度完成。
看看你能不能在十秒內寫出共二十四個字母與數字。
預備……開始!
我猜時間結束前你順利完成,或者接近尾聲。接下來我們再玩一次,不過這回我們做個小小改變......
第二回合
這個回合你的目標是完成跟上面一樣的兩項任務,只是這次你要在兩項任務之間快速輪動。
1、紙張分成左右兩欄。
2、計時器設定十秒。
3、計時器開始後,在左邊欄位寫第一個英文字母(A),接著在右邊寫第一個數字(1),接著左邊寫第二個字母(B),右邊寫第二個數字(2),以此類推。
同樣地,看看你能不能在十秒內寫出全部二十四個字母與數字。
預備……開始!
如果你跟大多數人一樣,這回可能兩邊各完成大約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雖然這項任務不算特別困難,你卻可能發現自己愈來愈慌,出了幾個錯,也許重複同一個數字,或需要在心裡默念英文字母,才能想起下一個字母。
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第二回合難度比第一回合高?
注意力過濾器
這個世界混亂無序。
我寫這些字的時候,坐在擁擠的咖啡館裡,幾十個顧客川流不息從我桌子旁走過,義式濃縮咖啡機在我耳畔嘶嘶作響,兩個女孩嘰嘰喳喳爭論某個名叫查德的男孩的課外活動。
周遭這麼多喧囂,能夠完成任何事都算奇蹟。然而,我們不知怎的竟能穿越那片喧鬧,專注在那些當時對我們有意義的景象、聲音、滋味、氣味和感受。
這就是注意力的力量。
要了解注意力如何運作,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它想像成過濾器。
注意力很像我們小時候戴的那種只允許特定波長的光線通過的3D眼鏡,它只容許相關資訊進入有意識的覺知(conscious awareness),阻擋不相關的資訊。
我們在上一章學過,被判定為不相關的資訊同樣會進入我們的記憶(情境與狀態依賴),卻不會被有意識地處理。這就引出一個重要問題:什麼東西判定某筆資訊有相關性?答案取決於我們從事的特定任務。
正如桌遊,我們從事的所有任務(不管是寫電子郵件、統計帳單,或只是出門遛狗)都伴隨一組獨特的規則,限定需要哪些行動才算「達成」。
比方說,為了順利讀完目前這些文字,你的閱讀規則集(ruleset)限定你的視線必須沿著每一行由上而下移動、在句子結束前記住每一個字、用手指翻頁等等。
我們從事某項任務時,相關規則集必須先載入腦部一個名為側前額葉皮質(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我們簡稱LatPFC)的小區域。
載入LatPFC的特定規則集會決定哪些資訊相關、哪些又不相關。
比方說,此刻你的閱讀規則集載入你的LatPFC,調整你的注意力過濾器,允許這些橫橫豎豎的黑色筆畫進入有意識的覺知,在此同時阻擋紙頁在你指尖的觸感、本頁底部的章名,以及你周遭的任何聲響等等。
我經常以一九八○年代的舊式電視遊樂器系統比喻這整個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款遊戲(任務)有一組獨特的角色、控制鈕和目標(規則集)。
任何時候你想玩某一款遊戲,就把相關的卡匣插入遊戲機(LatPFC)。遊戲載入後,電視螢幕就會顯示那款遊戲的主角、壞蛋、武器等等(注意力過濾器)。
有個簡單的方法可以了解這兩套網絡如何運作,那就是想像汽車駕訓班那種有兩套方向盤的教練車。
大多數時候汽車由學員駕駛(背側網絡),有意識地專心以某種特定方式行駛、轉彎。
然而,默默坐在旁邊的教練(腹側網絡)始終提高警覺,隨時覺察周遭世界,萬一發生危險,可以立刻接手。
緊迫問題一:邊走邊說
「如果不可能一心多用,那麼我為什麼可以邊走路邊嚼口香糖?」
說得對!
真相是,我們每天都一心多用。我們邊吃東西邊聊天;邊淋浴邊唱歌;邊慢跑邊思考工作計畫。
有趣的來了。如果你細看這些例子,每個都包含紋狀體操控的慣性動作。
很可能你已經精通吃東西、淋浴和慢跑這些事,也就是可以不假思索地執行這些技能。
這代表我們可以同時執行兩項任務,只要其中一項出於習慣,不需要太多思考。
話說回來,你是否曾吃飯時跟人聊天,聊著聊著忘了吃?或者唱歌唱得太投入、心不在焉地倒了兩次洗髮精?或者太擔心某個計畫,慢跑時意外絆跤?
即使其中一項任務是慣性動作,仍然不能確保一心多用的效率。規則集、過濾器和目標還是可能混淆,以至於影響反應速度、表現與記憶。
甚至,超過某個年齡之後,就連邊走路邊說話這種慣性任務都可能互相干擾(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上了年紀的人會站在原地聊天)。
所以說,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當然辦得到,但這不代表我們能一心多用。
緊迫問題三:記憶抹除
「有時候我走進某個房間,會突然忘記進去做什麼。這是怎麼回事?」
正如我們稍早學到,腹側注意力網絡一旦察覺威脅,就會自動卸除我們當下的規則集。這種狀況發生時,所有來不及送進海馬迴的資訊都會被有效抹除。這就像你每次翻到這本書的下一頁,就會忘記前一頁的最後一句。學者稱這種機制為事件模式清除(event-model purge),不過更通用的說法是記憶抹除(mind wipe)。
如果有隻飢餓的熊走近你,啟動這個機制還有點道理(畢竟小命不保,誰還在乎剛才在想什麼?)但我們只是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為什麼也會發生呢?
原來我們的腹側網絡有時候會把門口判定為威脅。雖然沒有人確定這是怎麼回事,但一般認為,當門框快速閃過我們的視野,大腦就會意識到危險,我們的規則集會重新設定,前一刻思考的任何資訊因此被抹除,這叫門口效應(doorway effect)。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打開冰箱,冰箱門快速在我們眼前晃過,我們突然忘記要拿什麼。
幸好,如果我們回到原本在的地方(或關上冰箱門),就能利用空間、情境和狀態三種引導提示,重建原有的思路,想起原本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