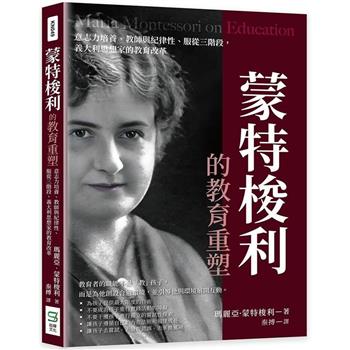第二篇 蒙特梭利教育方法的由來
我感受到了這樣一種啟示,一開始對孩子進行教育的時候,老師一定要將自己的聲音和教具結合起來,以此來呼喚、誘導孩子。不論是遭受了不幸的孩子,還是不開心的 孩子,都要尊重他們、熱愛他們。因為當別人靠近他們時,能夠將他們的熱情點燃。
要想建立一套科學的教育學體系,就必須另闢蹊徑──尋找一條與以前的教育學完全不同的路。學校的轉變和教師的培訓兩項工作是必須要同時進行的。要讓教師變成一個觀察者,讓她熟悉各種做實驗的方法,而且要讓她到學校裡去觀察和做實驗。在科學教育學中,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學生可以獲得充分的自由,即允許兒童個性得到發展,讓他們在展露個性的時候不會受到任何的阻礙。假如這門新的學科需要對兒童的個體展開研究,那麼它所選擇的觀察的對象就必須是那些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兒童。
實驗科學的每一個分支學科,最終都會形成一種方法並將它應用於自身。細菌學這門科學就是採用了隔離方法對細菌進行研究,而由於人們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應用於諸如罪犯、精神病人、臨床患者和學者等各式各樣的人身上,才獲得了犯罪人類學、醫學人類學、教育人類學方面的進步。所以,從出發點來看,實驗心理學需要對實驗過程中用到的技術做出精準的定義,然後在實驗科學的具體實踐中獲得準確的結論,這種結論只能透過實驗獲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對實驗進行闡述時,實驗科學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絕對不會帶著任何成見去匯出一個最終的實驗結論。舉個例子,人的大腦與智力的差異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假如我們想要對大腦的情況進行研究,那麼在進行實驗的時候就一定要具備如下條件:在對被研究者進行測試的時候,不能對其中最聰明的人和最遲鈍的人帶有絲毫的偏見。如果認為一個人是聰明人,他的大腦肯定就發育得完善,那麼這種先入為主的看法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採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那麼做實驗的這個人首先要做的就是丟掉此前的所有信念,去除所有成見。換言之,千萬不能有任何的教條思想──在兒童心理學方面,我們也許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拋棄已經存在的教條思想,盡可能的讓孩子獲得完全的自由。要想透過觀察孩子的自然行為來獲取一些有用的結果,而且這些結果有助於我們創建真正符合科學精神的兒童教育學,我們就必須將自己腦子裡所有的教條思想全都丟掉。只有不斷的透過實驗的方法來戰勝各種偏見,才能建構起兒童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的科學內容。
所以,我們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建立一套非常適合實驗教育學的方法,這套方法不能是其他實驗科學中已經使用的方法。科學教育學處在人類學、衛生學和心理學的範圍之內,儘管它將自己的研究範圍局限在受教育的個體上,所做的也都是一些特殊的研究,但它卻用到了上述三個學科的部分技術、方法和特性,這的確是事實。目前的研究工作有一部分與實驗教育學所採用的方法有關,這是我在「兒童之家」工作的兩年間,透過不斷總結經驗得出的結果。在這種研究方法上,我只是抛磚引玉,將它用來研究3~6歲兒童的教育。我相信這些試驗性的研究能夠在這項工作的後續研究過程中為人們提供有益的啟示──它們確實提供了一些讓人吃驚的研究結論。
其實,經驗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這一點已經被證實了。儘管到目前為止,教育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而且還很不完善,在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對孩子們進行管理和教育的學校裡,這一體系還不能完全應用。
還有,我說自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自過去兩年我在「兒童之家」的工作經驗,或許這句話不太確切。事實上,這種教育體系的使用由來已久,我們需要記住的是,它源於以前對畸形兒童的教育,從中獲得的實踐經驗,展現出了人們為探索科學的教育體系所付出的長久的努力。
大約15年之前,那時的我在羅馬大學的精神病治療診所擔任助理醫生,因此經常有機會進出精神病院,進行精神病方面的研究並且為診所挑選合適的精神病人作為研究對象。由於這項工作,我開始對智障兒童產生了興趣,當時他們還在普通的精神病醫院進行治療。當時甲狀腺器官療法已經非常發達,這使得外科醫生注意到了那些身體有缺陷的兒童。在我完成了醫院的日常工作之後,也將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這一方面。
就這樣,我懷著極大的興趣開始研究智障兒童。我深入鑽研了愛德華‧塞金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針對這些不幸的兒童,設計出了一些特殊的教育方法,並總結了這套教育方法的核心思想。「教育療法」對耳聾、白痴、佝僂、中風之類的精神性疾病有著非常顯著的療效,在外科醫生中間,這種思想也開始廣泛流行起來。人們覺得在治病時一定要將教育學和醫學兩種方式結合起來。這種觀點的產生,可以說是時代進步的結果。由於這種思想傾向的影響,採用體育鍛鍊來干預疾病治療的方法也逐漸流行開來。但是我與同行們在觀點上的不同之處在於,我覺得一個智力有缺陷的人應該解決的是教育問題,而非醫學上的問題。人們在如何對智障兒童進行研究和教育的醫學研討大會上已經發表了大量不同的觀點。西元1898年,在杜林舉辦的一場教育學大會上,我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精神教育」,闡述了一種全新的觀點。我認為,有一根正在振動的琴弦再次被撥動,在教師和外科醫生中間,這一觀點產生了很大的迴響,它也因為向學校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而被迅速傳播開來。
圭多‧巴切利(Guido Bacelli)──我的導師,偉大的教育部長,曾經來拜訪我,並請我向羅馬大學的教師們講一講如何針對智障兒童進行教育。然後我又在州立行為心理學學校──我在這裡已經做了兩年多的管理工作,開設了一門關於智障兒童的教育課程。
在這座學校,我每天都會對孩子們上課。在小學裡,他們被認為是頭腦愚鈍、無藥可治的學生。後來,慈善機構幫助我們成立了一所醫學教育學院,除了接收公立學校的孩子之外,羅馬所有精神病院裡正在接受治療的智障兒童也都被我們接收了。
在同事的幫助下,我用了兩年的時間設計出了一種特別的方法,幫助羅馬的教師們對智障兒童進行觀察和教育。我不但要培訓教師,而且還有更重要的工作──為了研究這種方法,我還在巴黎、倫敦待了一段時間,然後我就開始全身心的投入到兒童教育的具體工作中。
從某種角度說,我就是一位小學教師,因為我從上午8點到晚上7點要一直不間斷的向孩子們講課。這兩年的實踐也讓我在教育學方面獲得了第一個學位,其實這也是我獲得的第一個真正的學位。在我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所採用的方法在智障兒童的教育方面確實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我堅持認為,與人們目前正在使用的教育方法相比,我的教育方法在原理上更加合理,透過這一方法的採用,兒童低下的智力可以獲得進步與發展。我在這一方面投入的感情極為深厚,甚至進入我的內心深處,當我為了探尋更好的教育智障兒童的方法而離開這座學校之後,這種情感幾乎全部控制了我的思想。我漸漸產生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如果將同樣的方法用在正常兒童的身上,它們就會在發展和解放兒童天性方面展現出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議的效果。
自此之後,我就開始對矯正教育學展開了真正的、詳盡的研究,希望對正常的兒童進行教育學及原理方面的研究。因此我還在大學哲學系註冊成為一名學生。雖然我不確定能否夠讓自己的想法得到驗證,但在這樣一種偉大信念的鼓舞下,為了深挖、拓展這種思想,我放下了其他所有工作。為了完成這項結果未知的工作,我幾乎已經做好了全部的準備。
我感受到了這樣一種啟示,一開始對孩子進行教育的時候,老師一定要將自己的聲音和教具結合起來,以此來呼喚、誘導孩子。不論是遭受了不幸的孩子,還是不開心的 孩子,都要尊重他們、熱愛他們。因為當別人靠近他們時,能夠將他們的熱情點燃。
要想建立一套科學的教育學體系,就必須另闢蹊徑──尋找一條與以前的教育學完全不同的路。學校的轉變和教師的培訓兩項工作是必須要同時進行的。要讓教師變成一個觀察者,讓她熟悉各種做實驗的方法,而且要讓她到學校裡去觀察和做實驗。在科學教育學中,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學生可以獲得充分的自由,即允許兒童個性得到發展,讓他們在展露個性的時候不會受到任何的阻礙。假如這門新的學科需要對兒童的個體展開研究,那麼它所選擇的觀察的對象就必須是那些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兒童。
實驗科學的每一個分支學科,最終都會形成一種方法並將它應用於自身。細菌學這門科學就是採用了隔離方法對細菌進行研究,而由於人們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應用於諸如罪犯、精神病人、臨床患者和學者等各式各樣的人身上,才獲得了犯罪人類學、醫學人類學、教育人類學方面的進步。所以,從出發點來看,實驗心理學需要對實驗過程中用到的技術做出精準的定義,然後在實驗科學的具體實踐中獲得準確的結論,這種結論只能透過實驗獲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對實驗進行闡述時,實驗科學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絕對不會帶著任何成見去匯出一個最終的實驗結論。舉個例子,人的大腦與智力的差異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假如我們想要對大腦的情況進行研究,那麼在進行實驗的時候就一定要具備如下條件:在對被研究者進行測試的時候,不能對其中最聰明的人和最遲鈍的人帶有絲毫的偏見。如果認為一個人是聰明人,他的大腦肯定就發育得完善,那麼這種先入為主的看法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採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那麼做實驗的這個人首先要做的就是丟掉此前的所有信念,去除所有成見。換言之,千萬不能有任何的教條思想──在兒童心理學方面,我們也許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拋棄已經存在的教條思想,盡可能的讓孩子獲得完全的自由。要想透過觀察孩子的自然行為來獲取一些有用的結果,而且這些結果有助於我們創建真正符合科學精神的兒童教育學,我們就必須將自己腦子裡所有的教條思想全都丟掉。只有不斷的透過實驗的方法來戰勝各種偏見,才能建構起兒童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的科學內容。
所以,我們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建立一套非常適合實驗教育學的方法,這套方法不能是其他實驗科學中已經使用的方法。科學教育學處在人類學、衛生學和心理學的範圍之內,儘管它將自己的研究範圍局限在受教育的個體上,所做的也都是一些特殊的研究,但它卻用到了上述三個學科的部分技術、方法和特性,這的確是事實。目前的研究工作有一部分與實驗教育學所採用的方法有關,這是我在「兒童之家」工作的兩年間,透過不斷總結經驗得出的結果。在這種研究方法上,我只是抛磚引玉,將它用來研究3~6歲兒童的教育。我相信這些試驗性的研究能夠在這項工作的後續研究過程中為人們提供有益的啟示──它們確實提供了一些讓人吃驚的研究結論。
其實,經驗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這一點已經被證實了。儘管到目前為止,教育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而且還很不完善,在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對孩子們進行管理和教育的學校裡,這一體系還不能完全應用。
還有,我說自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自過去兩年我在「兒童之家」的工作經驗,或許這句話不太確切。事實上,這種教育體系的使用由來已久,我們需要記住的是,它源於以前對畸形兒童的教育,從中獲得的實踐經驗,展現出了人們為探索科學的教育體系所付出的長久的努力。
大約15年之前,那時的我在羅馬大學的精神病治療診所擔任助理醫生,因此經常有機會進出精神病院,進行精神病方面的研究並且為診所挑選合適的精神病人作為研究對象。由於這項工作,我開始對智障兒童產生了興趣,當時他們還在普通的精神病醫院進行治療。當時甲狀腺器官療法已經非常發達,這使得外科醫生注意到了那些身體有缺陷的兒童。在我完成了醫院的日常工作之後,也將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這一方面。
就這樣,我懷著極大的興趣開始研究智障兒童。我深入鑽研了愛德華‧塞金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針對這些不幸的兒童,設計出了一些特殊的教育方法,並總結了這套教育方法的核心思想。「教育療法」對耳聾、白痴、佝僂、中風之類的精神性疾病有著非常顯著的療效,在外科醫生中間,這種思想也開始廣泛流行起來。人們覺得在治病時一定要將教育學和醫學兩種方式結合起來。這種觀點的產生,可以說是時代進步的結果。由於這種思想傾向的影響,採用體育鍛鍊來干預疾病治療的方法也逐漸流行開來。但是我與同行們在觀點上的不同之處在於,我覺得一個智力有缺陷的人應該解決的是教育問題,而非醫學上的問題。人們在如何對智障兒童進行研究和教育的醫學研討大會上已經發表了大量不同的觀點。西元1898年,在杜林舉辦的一場教育學大會上,我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精神教育」,闡述了一種全新的觀點。我認為,有一根正在振動的琴弦再次被撥動,在教師和外科醫生中間,這一觀點產生了很大的迴響,它也因為向學校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而被迅速傳播開來。
圭多‧巴切利(Guido Bacelli)──我的導師,偉大的教育部長,曾經來拜訪我,並請我向羅馬大學的教師們講一講如何針對智障兒童進行教育。然後我又在州立行為心理學學校──我在這裡已經做了兩年多的管理工作,開設了一門關於智障兒童的教育課程。
在這座學校,我每天都會對孩子們上課。在小學裡,他們被認為是頭腦愚鈍、無藥可治的學生。後來,慈善機構幫助我們成立了一所醫學教育學院,除了接收公立學校的孩子之外,羅馬所有精神病院裡正在接受治療的智障兒童也都被我們接收了。
在同事的幫助下,我用了兩年的時間設計出了一種特別的方法,幫助羅馬的教師們對智障兒童進行觀察和教育。我不但要培訓教師,而且還有更重要的工作──為了研究這種方法,我還在巴黎、倫敦待了一段時間,然後我就開始全身心的投入到兒童教育的具體工作中。
從某種角度說,我就是一位小學教師,因為我從上午8點到晚上7點要一直不間斷的向孩子們講課。這兩年的實踐也讓我在教育學方面獲得了第一個學位,其實這也是我獲得的第一個真正的學位。在我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所採用的方法在智障兒童的教育方面確實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我堅持認為,與人們目前正在使用的教育方法相比,我的教育方法在原理上更加合理,透過這一方法的採用,兒童低下的智力可以獲得進步與發展。我在這一方面投入的感情極為深厚,甚至進入我的內心深處,當我為了探尋更好的教育智障兒童的方法而離開這座學校之後,這種情感幾乎全部控制了我的思想。我漸漸產生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如果將同樣的方法用在正常兒童的身上,它們就會在發展和解放兒童天性方面展現出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議的效果。
自此之後,我就開始對矯正教育學展開了真正的、詳盡的研究,希望對正常的兒童進行教育學及原理方面的研究。因此我還在大學哲學系註冊成為一名學生。雖然我不確定能否夠讓自己的想法得到驗證,但在這樣一種偉大信念的鼓舞下,為了深挖、拓展這種思想,我放下了其他所有工作。為了完成這項結果未知的工作,我幾乎已經做好了全部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