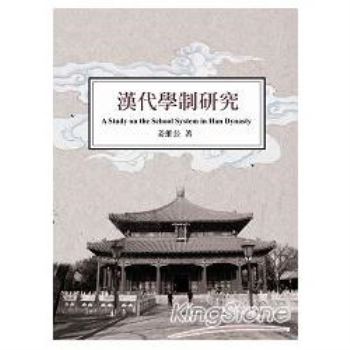【結語】
學校制度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官學和私學為其主要表現形式。本文詳盡地考察了漢代官學與私學的產生、發展乃至演變過程,同時,也對學校的施教人員、教學內容及教學形式進行了細緻分析,並以附論的形式探討了漢代學校教育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漢代的官學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種:中央的官學以太學為主,到東漢又出現了針對特定人群的宮邸學和鴻都門學;地方官學指州、郡國、縣道的學校。漢代太學創建的時間,是個爭議較大的問題,至今聚訟紛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理清了漢代太學的發展脈絡,發現矛盾的焦點集結在西漢太學館舍上。在漢代教育史研究中,絕大多數學者都是把早期太學是否擁有館舍作為判斷太學創建時間的依據。筆者根據多方面史料,確認西漢太學是有館舍的,就在太常官署內。太學是太常下屬機構的一支,因而沒有獨立的辦公機構。但是,以獨立的辦公機構來判斷一個機構是否建立,無疑是受了「以今律古」的教條主義思想的影響,並不足以否認其時太學已經創建的事實,許多誤解和成見也因此得到澄清。西漢肇建,對宗室、外戚子弟的培養力度不夠,對國家的穩定一度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漢武帝及其以後諸帝,除了從權力上加強了對宗室、外戚子弟的制約外,也相應加強了思想教育工作。宗室、外戚子弟都是統治階級未來接班人裡的中堅力量,也是在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方面最容易受到腐化的人群,對他們的教育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到了東漢,國家在君主的直接干預下,建立了針對宗室、外戚子弟的學校—四姓小侯學與宮邸學。另外還有兩所針對特殊人群的學校—東觀和鴻都門學。東觀是東漢最大的皇家圖書館,同時也是妃嬪、宦官、宮女的教育基地。鴻都門學是在太學諸生與宦官對抗背景下誕生的一所學校,專門收一些以書法、畫藝擅稱的士人。由於鴻都門學存在時間短、文獻資料又比較貧乏,因而研究中出現的分歧也較多。特別是在建國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影響,對鴻都門學的定性、辦學影響等方面的評價都有過度拔高之嫌,這些是應該加以糾正的。皇帝、皇儲、諸侯王的教育也在發展中逐漸完善。皇帝和皇太子都擁有自己的講師團,其主要人物都是當時儒家某一學派學說的菁英。二者所受教育的區別在於,皇帝接受的教育有其個人的喜好成份,而太子的教育則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模式。諸侯王的教育則有一定的強迫性,教師在傳道授業的同時也負有監督之責;國家也追究諸侯王傅、相的失職之責。地方官學分三級,其實相互之間並無制約關係,州學興起最晚,在東漢末州牧權力膨脹時才出現。在地方官學中,除了儒家教育素來發達的山東地區外,蜀郡官學可以說是地方官學的典範,已經有了近代學校的雛形。蜀郡官學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為其創始人文翁建立了一套能夠保證學校持續運作的制度,成功地解決了辦學資金、師資培訓及生源問題。筆者也注意到,漢代地方官學屢有衰廢,即使在儒學發達地區也不例外,前人對此沒有做出相應的解釋。經過探討,筆者認為,這是由於兩漢時期生產力比較落後,地方官學有一定的季節性,辦學時間一般都集中在春種秋收之外的農閒時節,這樣,師資、生源在一年內需要兩次的重新招集,這取決於地方長官的組織能力及對教育的關心程度;一旦地方長官不得其人,地方官學是很容易衰廢的。
其次,私學教育在兩漢時期也有其鮮明的特色。漢初的私學教育仍然繼承了春秋時「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流派的學術都能通過私學的方式得到傳播。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由於儒家經典得到了統治者的承認,儒生在仕途中得到了其他學派無法企及的特殊關照,詩書成為傳家守業的最佳方式,因而儒學不但壟斷了官學的教學內容,也為私學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動力。相較之下,諸子之學明顯地衰弱下來,只能通過家傳或吏師這兩種途徑得以傳承。漢人極重視家庭教育,也培育出不少早慧兒童。然就全國大多數家庭而言,知識家庭畢竟是少數,普通人知識的獲得需要到書館、精舍或官學中去。書館教育相當於現在的小學,其教育內容除了識字、書寫、計算能力外,也教授淺白易曉的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孝經》幾乎是必學的教材。精舍是私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種方式,精舍可大可小,有教學、生活的場所,辦學方式靈活,學員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理的,年長學深的學員作為老師的助教,向新學員傳授基本的知識。精舍主持人只有一個,多是名師大儒,幾個經師聯合授學的情況幾乎沒有,傳授的內容取決於經師知識面,招徠生徒的主要手段是精舍主人的聲名。漢代儒師通過精舍授學的方式招聚門徒,坐養聲名,以求進取,不但解決了生資所需,也為他年步入仕途積累了資本。漢代女子教育較後世為易,但針對女子的教條、教材也逐漸增加,對女子的束縛力也隨之增強,這些教條、教材所提倡的女子立身處世的道德標準及行為準則對後世影響深遠。再次,漢代學校中師長與學生的情況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也是本文探討的內容。太學的師資力量最為雄厚,骨幹教師是官方承認諸經博士,教材是博士所傳的五經章句。由於官立博士只有十數人,主要教學任務是由都講、講郎、主事等教學輔助人員擔任的,帝王、儒學大師只是偶爾步入太學講壇。有關博士的史料比較多,便於比較、分析,對博士的職掌、選任、待遇、升遷都做了探討和總結。特殊學校的師資大多是由帝王指定的,沒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地方官學的教學人員較多,其職稱也頗為繁復,由於史料的闕略,還無法展開細節研究。私學的施教人員成份比較復雜,介入辦學的身份也各有不同,辦學動機則較為一致,都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聲望,從而獲取各自的利益。通過排比漢代官、私學校學生的出身籍貫、生活條件、求學經歷、畢業出路等諸多方面資料,可以發現漢代的學生及其求學都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太學最初創建的目的是為了養士,因而西漢太學生基本上都是平民。東漢時,太學成了仕途上直步青云的捷徑,在君主的宣導下,貴族子弟紛紛加入,從而使太學生的成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太學生的學籍管理、考試制度都比較嚴格。兩漢以「祿利之途」作為創辦官學吸引力,太學生的出路較好,成績優異者可以擔任朝中或地方上的學術官。沒有通過課試的學生也可以通過察舉之路出仕。地方官學為達到招徠學生的目的,一般都提供某種經濟或政治上的保障,比如說,免除學生家庭的徭役,免費提供深造的機會,畢業後安排到郡縣任職等等。西漢時的私學學生受條件限制,一般都是就近求學,而東漢時遊學風氣極盛,萬里求學的事例比較多。在私學中,師生之間等級森嚴,儼如群臣,門生有依附化的趨勢。學生之間也有等級,有門徒和著錄之分。
第四,兩漢官私學都是以儒家經典為教學內容的。經學是漢代教育的核心。經學可以分為訓詁學、章句學和義理學。其中章句學由於與官學課試直接掛鈎,從而得到了官、私學的高度重視。太學的教學內容主要以官立博士所授的五經章句為主,地方官學似乎沒有這麼嚴格,主要是五經章句。書館教育屬於蒙學階段,主要學習內容是識字和書寫,也教授一些簡單的儒家經典。精舍的教學內容一般以專經為主,因為博通五經的通儒畢竟是少數。學生如果在求知上得不到滿足,也可以廣求名師,博學多通。兩漢最基本的教學形式以書本知識的傳授為主。儒師講授一般採取大課堂開放式教學,弟子眾多則由高足弟子遞相傳授,有的學生甚至終年未嘗一睹師容。集會討論是漢代太學特有的一種教學方式,學生固然受到教誨,儒師也在爭論中受益匪淺。教學方法有傳授式,側重於講解文字、經義和音聲;有辯難式,藉以探討經文異同,闡明經文大義;有演示式,漢代重禮,禮節多繁縟,所以必須有實習式的演練,才能掌握每個環節。師法和家法是漢代教育史研究難度較大,觀點紛歧的一個問題。本文對這一研究做了回顧,分析了研究者們各種觀點的優劣,從歷史的角度嘗試著得出結論。總之,前漢重師法有如下幾方面原因,一是受先秦師法傳統的影響,守師法是在先秦時代就已形成的一個傳統。二是受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影響,經過這一浩劫,五經傳本不但有限,而且受損嚴重,不得不依靠碩果僅存的幾個儒師口耳相傳。三是物質條件的制約,當時生產力落後,文化載體不便於書本知識的傳授。四是漢武帝出於統一思想的策略,有意樹立正統並維護其權威。師法的淆亂始於宣帝,他出於政治目的扶持了一些以前未受國家承認的儒家流派,不自覺地破壞了傳統師法。師法在西漢是一種觀念,而家法則由於涉及考試答案的標準性而成為一項制度,博士傳經的過程中要恪守家法,學生在課試也必須嚴格遵守家法。總的來說,師法和家法對教育是有利有弊的,對漢代教育起了很大的影響。
近代學者對秦漢時期的文化地理興趣頗濃,基於不同的研究角度與不同的基礎資料,其文化地理分區也各有不同。由於沒有學者討論過教育文化分區的問題,本文以附論的形式總結了漢代教育的地域特徵,將其分為三個教育文化區。一是漢初傳統的教育盛地—鄒魯、齊燕、三晉,這一地區有著悠久的教育傳統,在兩漢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二是中央官學的大本營—長安、洛陽,由於京師文化機構的發展,由於儒生迅速成為統治階級的新生力量,也由於大量知識份子移民首都,兩漢首都成為文化教育的先進地區。三是地方官學的典範—巴蜀。蜀郡太守文翁創建了一套能夠保持官學持久運作的制度,這一制度得到巴蜀地區的繼承和推廣,從而使巴蜀地區的教育蒸蒸日上。
總之,西漢教育制度的研究已經進入細化研究,本文在澄清誤解,細節考證、別創新知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嘗試,希望有助於推進這一研究的發展。
學校制度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官學和私學為其主要表現形式。本文詳盡地考察了漢代官學與私學的產生、發展乃至演變過程,同時,也對學校的施教人員、教學內容及教學形式進行了細緻分析,並以附論的形式探討了漢代學校教育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漢代的官學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種:中央的官學以太學為主,到東漢又出現了針對特定人群的宮邸學和鴻都門學;地方官學指州、郡國、縣道的學校。漢代太學創建的時間,是個爭議較大的問題,至今聚訟紛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理清了漢代太學的發展脈絡,發現矛盾的焦點集結在西漢太學館舍上。在漢代教育史研究中,絕大多數學者都是把早期太學是否擁有館舍作為判斷太學創建時間的依據。筆者根據多方面史料,確認西漢太學是有館舍的,就在太常官署內。太學是太常下屬機構的一支,因而沒有獨立的辦公機構。但是,以獨立的辦公機構來判斷一個機構是否建立,無疑是受了「以今律古」的教條主義思想的影響,並不足以否認其時太學已經創建的事實,許多誤解和成見也因此得到澄清。西漢肇建,對宗室、外戚子弟的培養力度不夠,對國家的穩定一度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漢武帝及其以後諸帝,除了從權力上加強了對宗室、外戚子弟的制約外,也相應加強了思想教育工作。宗室、外戚子弟都是統治階級未來接班人裡的中堅力量,也是在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方面最容易受到腐化的人群,對他們的教育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到了東漢,國家在君主的直接干預下,建立了針對宗室、外戚子弟的學校—四姓小侯學與宮邸學。另外還有兩所針對特殊人群的學校—東觀和鴻都門學。東觀是東漢最大的皇家圖書館,同時也是妃嬪、宦官、宮女的教育基地。鴻都門學是在太學諸生與宦官對抗背景下誕生的一所學校,專門收一些以書法、畫藝擅稱的士人。由於鴻都門學存在時間短、文獻資料又比較貧乏,因而研究中出現的分歧也較多。特別是在建國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影響,對鴻都門學的定性、辦學影響等方面的評價都有過度拔高之嫌,這些是應該加以糾正的。皇帝、皇儲、諸侯王的教育也在發展中逐漸完善。皇帝和皇太子都擁有自己的講師團,其主要人物都是當時儒家某一學派學說的菁英。二者所受教育的區別在於,皇帝接受的教育有其個人的喜好成份,而太子的教育則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模式。諸侯王的教育則有一定的強迫性,教師在傳道授業的同時也負有監督之責;國家也追究諸侯王傅、相的失職之責。地方官學分三級,其實相互之間並無制約關係,州學興起最晚,在東漢末州牧權力膨脹時才出現。在地方官學中,除了儒家教育素來發達的山東地區外,蜀郡官學可以說是地方官學的典範,已經有了近代學校的雛形。蜀郡官學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為其創始人文翁建立了一套能夠保證學校持續運作的制度,成功地解決了辦學資金、師資培訓及生源問題。筆者也注意到,漢代地方官學屢有衰廢,即使在儒學發達地區也不例外,前人對此沒有做出相應的解釋。經過探討,筆者認為,這是由於兩漢時期生產力比較落後,地方官學有一定的季節性,辦學時間一般都集中在春種秋收之外的農閒時節,這樣,師資、生源在一年內需要兩次的重新招集,這取決於地方長官的組織能力及對教育的關心程度;一旦地方長官不得其人,地方官學是很容易衰廢的。
其次,私學教育在兩漢時期也有其鮮明的特色。漢初的私學教育仍然繼承了春秋時「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流派的學術都能通過私學的方式得到傳播。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由於儒家經典得到了統治者的承認,儒生在仕途中得到了其他學派無法企及的特殊關照,詩書成為傳家守業的最佳方式,因而儒學不但壟斷了官學的教學內容,也為私學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動力。相較之下,諸子之學明顯地衰弱下來,只能通過家傳或吏師這兩種途徑得以傳承。漢人極重視家庭教育,也培育出不少早慧兒童。然就全國大多數家庭而言,知識家庭畢竟是少數,普通人知識的獲得需要到書館、精舍或官學中去。書館教育相當於現在的小學,其教育內容除了識字、書寫、計算能力外,也教授淺白易曉的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孝經》幾乎是必學的教材。精舍是私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種方式,精舍可大可小,有教學、生活的場所,辦學方式靈活,學員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理的,年長學深的學員作為老師的助教,向新學員傳授基本的知識。精舍主持人只有一個,多是名師大儒,幾個經師聯合授學的情況幾乎沒有,傳授的內容取決於經師知識面,招徠生徒的主要手段是精舍主人的聲名。漢代儒師通過精舍授學的方式招聚門徒,坐養聲名,以求進取,不但解決了生資所需,也為他年步入仕途積累了資本。漢代女子教育較後世為易,但針對女子的教條、教材也逐漸增加,對女子的束縛力也隨之增強,這些教條、教材所提倡的女子立身處世的道德標準及行為準則對後世影響深遠。再次,漢代學校中師長與學生的情況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也是本文探討的內容。太學的師資力量最為雄厚,骨幹教師是官方承認諸經博士,教材是博士所傳的五經章句。由於官立博士只有十數人,主要教學任務是由都講、講郎、主事等教學輔助人員擔任的,帝王、儒學大師只是偶爾步入太學講壇。有關博士的史料比較多,便於比較、分析,對博士的職掌、選任、待遇、升遷都做了探討和總結。特殊學校的師資大多是由帝王指定的,沒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地方官學的教學人員較多,其職稱也頗為繁復,由於史料的闕略,還無法展開細節研究。私學的施教人員成份比較復雜,介入辦學的身份也各有不同,辦學動機則較為一致,都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聲望,從而獲取各自的利益。通過排比漢代官、私學校學生的出身籍貫、生活條件、求學經歷、畢業出路等諸多方面資料,可以發現漢代的學生及其求學都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太學最初創建的目的是為了養士,因而西漢太學生基本上都是平民。東漢時,太學成了仕途上直步青云的捷徑,在君主的宣導下,貴族子弟紛紛加入,從而使太學生的成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太學生的學籍管理、考試制度都比較嚴格。兩漢以「祿利之途」作為創辦官學吸引力,太學生的出路較好,成績優異者可以擔任朝中或地方上的學術官。沒有通過課試的學生也可以通過察舉之路出仕。地方官學為達到招徠學生的目的,一般都提供某種經濟或政治上的保障,比如說,免除學生家庭的徭役,免費提供深造的機會,畢業後安排到郡縣任職等等。西漢時的私學學生受條件限制,一般都是就近求學,而東漢時遊學風氣極盛,萬里求學的事例比較多。在私學中,師生之間等級森嚴,儼如群臣,門生有依附化的趨勢。學生之間也有等級,有門徒和著錄之分。
第四,兩漢官私學都是以儒家經典為教學內容的。經學是漢代教育的核心。經學可以分為訓詁學、章句學和義理學。其中章句學由於與官學課試直接掛鈎,從而得到了官、私學的高度重視。太學的教學內容主要以官立博士所授的五經章句為主,地方官學似乎沒有這麼嚴格,主要是五經章句。書館教育屬於蒙學階段,主要學習內容是識字和書寫,也教授一些簡單的儒家經典。精舍的教學內容一般以專經為主,因為博通五經的通儒畢竟是少數。學生如果在求知上得不到滿足,也可以廣求名師,博學多通。兩漢最基本的教學形式以書本知識的傳授為主。儒師講授一般採取大課堂開放式教學,弟子眾多則由高足弟子遞相傳授,有的學生甚至終年未嘗一睹師容。集會討論是漢代太學特有的一種教學方式,學生固然受到教誨,儒師也在爭論中受益匪淺。教學方法有傳授式,側重於講解文字、經義和音聲;有辯難式,藉以探討經文異同,闡明經文大義;有演示式,漢代重禮,禮節多繁縟,所以必須有實習式的演練,才能掌握每個環節。師法和家法是漢代教育史研究難度較大,觀點紛歧的一個問題。本文對這一研究做了回顧,分析了研究者們各種觀點的優劣,從歷史的角度嘗試著得出結論。總之,前漢重師法有如下幾方面原因,一是受先秦師法傳統的影響,守師法是在先秦時代就已形成的一個傳統。二是受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影響,經過這一浩劫,五經傳本不但有限,而且受損嚴重,不得不依靠碩果僅存的幾個儒師口耳相傳。三是物質條件的制約,當時生產力落後,文化載體不便於書本知識的傳授。四是漢武帝出於統一思想的策略,有意樹立正統並維護其權威。師法的淆亂始於宣帝,他出於政治目的扶持了一些以前未受國家承認的儒家流派,不自覺地破壞了傳統師法。師法在西漢是一種觀念,而家法則由於涉及考試答案的標準性而成為一項制度,博士傳經的過程中要恪守家法,學生在課試也必須嚴格遵守家法。總的來說,師法和家法對教育是有利有弊的,對漢代教育起了很大的影響。
近代學者對秦漢時期的文化地理興趣頗濃,基於不同的研究角度與不同的基礎資料,其文化地理分區也各有不同。由於沒有學者討論過教育文化分區的問題,本文以附論的形式總結了漢代教育的地域特徵,將其分為三個教育文化區。一是漢初傳統的教育盛地—鄒魯、齊燕、三晉,這一地區有著悠久的教育傳統,在兩漢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二是中央官學的大本營—長安、洛陽,由於京師文化機構的發展,由於儒生迅速成為統治階級的新生力量,也由於大量知識份子移民首都,兩漢首都成為文化教育的先進地區。三是地方官學的典範—巴蜀。蜀郡太守文翁創建了一套能夠保持官學持久運作的制度,這一制度得到巴蜀地區的繼承和推廣,從而使巴蜀地區的教育蒸蒸日上。
總之,西漢教育制度的研究已經進入細化研究,本文在澄清誤解,細節考證、別創新知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嘗試,希望有助於推進這一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