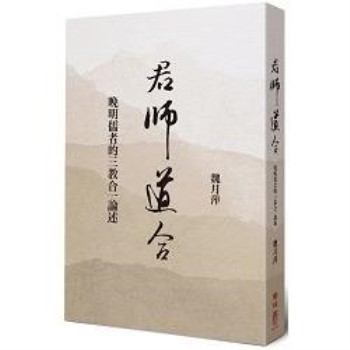第一章 導論
「三教合一」的命題猶如一口古井,看似陳舊,往深處提煉,又可伸觸潛藏於井底的水脈,水理通達四方。正因為其豐沛的水源,學界累積頗為豐碩的成果。我所關注的不僅是長時段中三教交涉所呈現的不同形態,而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究竟三教問題和哪些重要問題相互關聯,可供窺探儒者的時代關懷和思想實踐?在三教交涉或合流當中,三者如何溝通以及安排各自的位置?尤其是處於三教合流高峰的晚明時期,不同思想社群的三教思想和實踐,都有各自的思想依據和判準,實無法劃一而論。因此如何把握研究三教交涉的視野,提出新的問題思考,便至關重要。例如徐聖心在《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一書,以莊子思想作為三教會通的主要關注點,考察三教交涉間統攝、批判、取捨或兼融的基點,反思「三教」追求的是一個渾然的整體而非三者之間的整合。另外,該書也關注三教之間互相跨越的界限、概念的互文性,統攝的標準以及理與行的關係等議題,凸顯其嚴密的方法視野。這樣一種深潛文本的方式,勾勒出三教統攝的結構、判準與形態,不外是冀能解答其所念茲在茲的問題:「一以貫之的中樞究竟為何?」
這實是大哉問。但我認為這樣的叩問,實際上提醒在處理三教會通或合一的問題時,不應滯留於三教語言表面的溝通,而是把問題內在化到思想肌理,把握貫通三教的「中樞」或「點穴處」。這讓人聯想到莊子的「道樞」觀念,「樞」一詞有著轉動開關機樞的意思,而莊子的「道樞」更具體是指向「環中」,意味沒有固定中心的一種狀態,或是所謂的「無中之中」(the center of a non-center)。把「道樞」的觀念引入三教的問題脈絡,旨在說明當三教處於相對化的關係,「彼」和「此」可以隨時轉化,形成沒有一個固定的主體。這樣的主體浮動現象,可以破除一種固定化視域拘限的詮說方式,重新找到詮釋的支點。這其實切合晚明三教合流的形態,過去所說的「內」、「外」的二分法,抑或外儒內佛、援儒重佛、軒佛輕佛等,雖能說明三教交涉的基本形態,但難以涵蓋其中多元、豐富和充滿歧義的層次。晚明三教交涉問題繁複、紛雜,皆因涉及許多不同的問題關懷,除了以上所論,欲考察貫串三教的樞紐以外,要如何潛入儒者「援佛道」或「資二氏」思想背後的動機和目的,也是不易的事。究竟三教合流者如何認知和安排三教的地位?是以其中一教為優越主體進而統攝二教,抑或三教皆具有平等的地位?再者,若論及「三教合一」,也須先梳理所謂的「合一」意涵,是否指向三個不同教義的「整合」和「融貫」,還是趨向「同源」的意思?前者關注的是「同」(same)和「異」(difference)的問題,後者則指向「道一」的概念。簡單而言,「道一」是指三教涵括在一個整體性的「道」以內,具有一個共同關懷的「道」的思想基礎,它是大部分晚明儒者的共同意識。
我在寫碩士論文〈羅近溪破光景義蘊〉時,未真正碰觸到「三教合一」問題,但仍脫離不了三教交涉的問題,尤其是羅汝芳(一五一五─一五八八)思想與禪宗的會通,於是論文其中一章,曾以「佛心與赤子之心」、「一念悟佛與一覺成聖」、「平常心是道與捧茶童子是道」及「頓漸相資」這四組概念的對比,探討羅汝芳如何借鑑禪宗「破執破空」和「破妄顯真」的工夫,以達致「顯現真性」和「真妄雙泯」的目的。研究中發現不少儒者仍延續宋儒闢佛道的判準意識,攻擊羅汝芳的思想駁雜與不純。在儒家衛道者的眼裡,佛道是屬於「異端」,必須傾注全力捍衛儒家的正統性以及儒家思想的純正性。可是從羅汝芳以降,我們可以察覺出現一些新的思想變動。有關正統和異端之間的爭辯不再像以往那麼尖銳,換言之,「辨異」不一定占據最重要的位置。不但如此,不少認同三教合流的儒者,開始思及如何擬定合流原則、設立判準依據,以及建立規範意識。此外,晚明亦出現明顯的「三教合一」主張,標榜更明確的合一意識。這迫使我重新思考明中葉至晚明的三教合流和合一論述,是否只著重於義理或工夫的互涉、三教思維與語言的建構,還是另有機竅和門徑可探?特別是「三教合一」背後隱含的思想命題,以及和歷史、政治及社會文化的關聯,如何可以勾勒出晚明獨特的三教思想關懷與學術風潮。第一節 syncretism與「合一」的歧義
可是在研究當中,首先會遇到三教語言理解和表述的難題。無論是在閱讀或詮釋古典文獻,都會面對語言困境的潛在難題,其中包括不同三教語言思維和邏輯,以及不同三教觀所對應的歷史現實。舉例而言:(一)從古代學者的典籍記載,可了解他們對三教關係有各種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三教同源、三教為一、三教一致及三教合一等概念,究竟如何把握它確切的意涵?(二)當代學者在討論三教調和、會通、融合和合一等問題,如何保持高度的語言自覺,使不同的詮說能貼近文本情境、歷史和思想脈絡?儒釋道之間的溝通,無論是長時段的歷史演變或三教思維的建構,各有不同的形態,反思當代學界的三教論述,常發現文中使用的詞彙意義模糊,對於「融合」、「會通」、「混合」或「合一」的概念範圍缺乏嚴謹的界定,抑或嘗試回到歷史脈絡和思想內在理路去把握文本的脈絡意涵或語意範圍。例如對於syncretism一詞,在中文學界常被看待為會通、調和、融合或折衷等意涵。以下將通過錢新祖(Edward T. Chien)和卜正民(Timothy Brook)對syncretism詞彙把握的比較說明以上的問題。
錢新祖在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中文本譯為《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一書,曾指出中國傳統思想有一個悠遠的「宗教折衷」(syncretism)的傳統。他以魏晉道士王浮(生卒年不詳)的《老子化胡經》為例,說明這本書可作為最早的「三教一源」和「三教合一」起源的文本依據。在書中,他也指出:晚明的宗教折衷出現了新的融合邏輯語言,改變過去三教「分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現象,繼而走向「非分隔化」(non-compartmentalization)的路向。錢新祖以焦竑(一五四○─一六二○)為例,說明焦竑的「非分隔化」思想強調三教之間可以「兼存」(coexist)和「混合」(intermix)。(余英時對這個說法則存疑,後文將詳述)有關「宗教折衷」一詞,實是錢新祖中文譯本的詞彙,主要是指焦竑不把三教分列為三,並嘗試作出調和和綜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參照另一位西方學者卜正民對syncretism的看法,卻發現他的詮釋和錢新祖大不相同。卜正民認為syncretism這個詞彙,在西方語境裡,更多是用來解釋宗教的調和狀態,尤其是在基督教內部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調和。二者的根本性差異在於:(1)兩人對於syncretism的指涉認知不同,分別具「折衷」和「調和」的意思,這又和他們個別的宗教和思想視角有關;(2)對於syncretism所預設的思想基礎有所不同,關鍵在於把syncretism看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抑或是具有清晰目的的「結果」。明顯的,錢新祖關注前者,而卜正民則注重後者。錢新祖認為焦竑的三教觀,尤其是「天無二月」所揭示的「兼存」的看法,貫通儒釋,互為義疏,重構晚明的新儒思想。相反的,卜正民從嚴格的角度審視,他不認為中國曾經歷宗教調和的歷史進程,對他而言,syncretism發生在不同的宗教思想源流或系統的相互融合之中,一般上較強的宗教傳統將吸納或整合較弱的思想,最終調和的結果是:只有一種世界觀的宗教系統。卜正民最基本的判別是,三教之間並沒有呈現「一體化」的體系,尤其是仍可以維持三教各自的世界觀。
第二章 明中葉三教合流之衍變
關於三教之間的交涉,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末年牟融的《理惑論》。《理惑論》反映的是佛教東傳初期的思想狀態,當時人們多以黃老道家的視野來理解佛教,甚至以《老子》之說來批判道教和神仙方術。而漢代道教經書如《太平經》和《老子想爾注》則吸收不少儒家思想,前者著重「尊陽陰卑」、三綱六紀的思想,後者把忠孝仁義等道德規範,都納入在「道」的統屬之下。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之間的認識相應提高,義理的互涉和交融,才有實質的開展,但爭論也益發激烈。西晉道士王浮以《老子化胡經》揚道抑佛,東晉釋慧遠(三三四─四一六)的〈沙門不敬王者論〉則為佛教尋求超脫世俗的獨立地位。這時期佛教備受儒道批評,出現大量反佛和護佛的文章。縱然如此,亦有不少主張三教一致和融合的聲音,例如釋道安(三一二─三八五)在〈二教論〉說:「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跡誠異,理會則同」、宗炳(三七五─四四三)〈明佛論〉言:「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道士陶弘景(四四四─四九七)也認同「百法分湊,無越三教之境」。至唐代,無論是官方或民間都熱中於佛道,尤其是官方舉辦的講論活動更促進了三教的交融,遂引起儒家衛道者的批評。韓愈嚴厲批判佛道,以〈原道〉一文樹立儒家仁義之道,以區別於佛老之道。李翱(七七四─八三六)的《復性書》,融三教於道德修養,對宋明思想影響深遠。宋代以後,不少儒者都有「出入二氏,返回六經」的共同經驗,一方面吸收佛道的思維和工夫,一方面又闢佛道,尤對佛教嚴苛,其理由是:(一)佛教是出世之學,遺棄人倫;(二)佛教視天地為幻妄;(三)佛道以生死動人(老氏貪生,釋氏畏死),例如朱熹(一一三○─一二○○)曾言:「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而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因此在宋元時期,不少代表性的著作,如契嵩(一○○七─一○七二)《輔教編》、張商英(一○四三─一一二一)《護法論》、夏元鼐(生卒年不詳)《三教歸一圖說》以及陶宗儀(一三二○ ─一四○二)《三教一源圖》等書,都帶有護教的色彩。此外,宋代道士張伯端(九八七─一○八二)融三教於道教修行思想,提倡「三教歸一」理論;另有融合儒家「大中至正之道」和佛教「明心見性」的道教宗派淨明道。而金代道士王重陽(一一一三─一一七○)隨後更創立了三教同源的全真道。由此可知宋儒嚴厲闢佛,佛道之間卻相互吸收,甚至融合儒家義理來豐富自己的內容。
三教交流在明代又有另一種轉向,明太祖以三教合一理念為治國意識形態,並著有《三教論》、《釋道論》等以宗教信仰立說的著作,以佛道思想輔助王道,開啟明代「三教合一」政教化的端緒,對後來的政教發展影響深遠。之後明儒沈士榮(生卒年不詳)《續原教論》、屠隆(一五四三─一六○五)《佛法金湯錄》、雲棲袾宏(一五三五─一六一五)《緇門崇行錄》等均主三教調和之說,儒釋道之間相互援引的風氣,已蔚為風潮。明中葉以後,三教合流可以說已進入一個巔峰時期,「合一觀」儼然成為明中葉以後的思想基調。這時期出現了像林兆恩這等人物,試圖把三教合一變成一種「正統思想」,推廣至各個宗教領域與社會階層,以致後人多半把他看作是一名「宗教家」而非「思想家」。當時主張三教融合最大的儒者群體,應屬陽明學一脈諸子。他們除了涉足三教以外,與僧人道士也有頻密的互動,尤其是不少儒者和僧人的密切關係,使儒佛儼然形成一種「聯盟關係」。當時屬陽明學派的儒者與僧人的交往,除了論學與聯誼以外,也在思想情感上互相支援,攜手抑制在「朱子學」影響下所產生的強大排佛壓力。這樣的一種聯盟關係,無疑更加速了三教合流的狀態。從義理角度而言,陽明學者和佛教的親合關係,可從「良知」和「無善無惡」了解二者相似的內在思維邏輯。此外,不少陽明後學感悟良知失去抗衡現實的能力,而程朱之「理」又失去約束力,因此轉向佛教尋求思想資源,並強調「學佛以知儒」。另一方面,佛教尋求復興過程中,也吸收陽明一脈的心學抑或儒家義理,以達到「學儒知佛」。無論是宋代僧人智圓(九七六─一○二二)、契嵩(一○○七─一○七二)或於明中葉以後致力於佛教改革的憨山德清、紫柏真可(一五四三─一六○三)等僧人都具有「援儒解佛」的思想特色。
「三教合一」的命題猶如一口古井,看似陳舊,往深處提煉,又可伸觸潛藏於井底的水脈,水理通達四方。正因為其豐沛的水源,學界累積頗為豐碩的成果。我所關注的不僅是長時段中三教交涉所呈現的不同形態,而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究竟三教問題和哪些重要問題相互關聯,可供窺探儒者的時代關懷和思想實踐?在三教交涉或合流當中,三者如何溝通以及安排各自的位置?尤其是處於三教合流高峰的晚明時期,不同思想社群的三教思想和實踐,都有各自的思想依據和判準,實無法劃一而論。因此如何把握研究三教交涉的視野,提出新的問題思考,便至關重要。例如徐聖心在《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一書,以莊子思想作為三教會通的主要關注點,考察三教交涉間統攝、批判、取捨或兼融的基點,反思「三教」追求的是一個渾然的整體而非三者之間的整合。另外,該書也關注三教之間互相跨越的界限、概念的互文性,統攝的標準以及理與行的關係等議題,凸顯其嚴密的方法視野。這樣一種深潛文本的方式,勾勒出三教統攝的結構、判準與形態,不外是冀能解答其所念茲在茲的問題:「一以貫之的中樞究竟為何?」
這實是大哉問。但我認為這樣的叩問,實際上提醒在處理三教會通或合一的問題時,不應滯留於三教語言表面的溝通,而是把問題內在化到思想肌理,把握貫通三教的「中樞」或「點穴處」。這讓人聯想到莊子的「道樞」觀念,「樞」一詞有著轉動開關機樞的意思,而莊子的「道樞」更具體是指向「環中」,意味沒有固定中心的一種狀態,或是所謂的「無中之中」(the center of a non-center)。把「道樞」的觀念引入三教的問題脈絡,旨在說明當三教處於相對化的關係,「彼」和「此」可以隨時轉化,形成沒有一個固定的主體。這樣的主體浮動現象,可以破除一種固定化視域拘限的詮說方式,重新找到詮釋的支點。這其實切合晚明三教合流的形態,過去所說的「內」、「外」的二分法,抑或外儒內佛、援儒重佛、軒佛輕佛等,雖能說明三教交涉的基本形態,但難以涵蓋其中多元、豐富和充滿歧義的層次。晚明三教交涉問題繁複、紛雜,皆因涉及許多不同的問題關懷,除了以上所論,欲考察貫串三教的樞紐以外,要如何潛入儒者「援佛道」或「資二氏」思想背後的動機和目的,也是不易的事。究竟三教合流者如何認知和安排三教的地位?是以其中一教為優越主體進而統攝二教,抑或三教皆具有平等的地位?再者,若論及「三教合一」,也須先梳理所謂的「合一」意涵,是否指向三個不同教義的「整合」和「融貫」,還是趨向「同源」的意思?前者關注的是「同」(same)和「異」(difference)的問題,後者則指向「道一」的概念。簡單而言,「道一」是指三教涵括在一個整體性的「道」以內,具有一個共同關懷的「道」的思想基礎,它是大部分晚明儒者的共同意識。
我在寫碩士論文〈羅近溪破光景義蘊〉時,未真正碰觸到「三教合一」問題,但仍脫離不了三教交涉的問題,尤其是羅汝芳(一五一五─一五八八)思想與禪宗的會通,於是論文其中一章,曾以「佛心與赤子之心」、「一念悟佛與一覺成聖」、「平常心是道與捧茶童子是道」及「頓漸相資」這四組概念的對比,探討羅汝芳如何借鑑禪宗「破執破空」和「破妄顯真」的工夫,以達致「顯現真性」和「真妄雙泯」的目的。研究中發現不少儒者仍延續宋儒闢佛道的判準意識,攻擊羅汝芳的思想駁雜與不純。在儒家衛道者的眼裡,佛道是屬於「異端」,必須傾注全力捍衛儒家的正統性以及儒家思想的純正性。可是從羅汝芳以降,我們可以察覺出現一些新的思想變動。有關正統和異端之間的爭辯不再像以往那麼尖銳,換言之,「辨異」不一定占據最重要的位置。不但如此,不少認同三教合流的儒者,開始思及如何擬定合流原則、設立判準依據,以及建立規範意識。此外,晚明亦出現明顯的「三教合一」主張,標榜更明確的合一意識。這迫使我重新思考明中葉至晚明的三教合流和合一論述,是否只著重於義理或工夫的互涉、三教思維與語言的建構,還是另有機竅和門徑可探?特別是「三教合一」背後隱含的思想命題,以及和歷史、政治及社會文化的關聯,如何可以勾勒出晚明獨特的三教思想關懷與學術風潮。第一節 syncretism與「合一」的歧義
可是在研究當中,首先會遇到三教語言理解和表述的難題。無論是在閱讀或詮釋古典文獻,都會面對語言困境的潛在難題,其中包括不同三教語言思維和邏輯,以及不同三教觀所對應的歷史現實。舉例而言:(一)從古代學者的典籍記載,可了解他們對三教關係有各種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三教同源、三教為一、三教一致及三教合一等概念,究竟如何把握它確切的意涵?(二)當代學者在討論三教調和、會通、融合和合一等問題,如何保持高度的語言自覺,使不同的詮說能貼近文本情境、歷史和思想脈絡?儒釋道之間的溝通,無論是長時段的歷史演變或三教思維的建構,各有不同的形態,反思當代學界的三教論述,常發現文中使用的詞彙意義模糊,對於「融合」、「會通」、「混合」或「合一」的概念範圍缺乏嚴謹的界定,抑或嘗試回到歷史脈絡和思想內在理路去把握文本的脈絡意涵或語意範圍。例如對於syncretism一詞,在中文學界常被看待為會通、調和、融合或折衷等意涵。以下將通過錢新祖(Edward T. Chien)和卜正民(Timothy Brook)對syncretism詞彙把握的比較說明以上的問題。
錢新祖在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中文本譯為《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一書,曾指出中國傳統思想有一個悠遠的「宗教折衷」(syncretism)的傳統。他以魏晉道士王浮(生卒年不詳)的《老子化胡經》為例,說明這本書可作為最早的「三教一源」和「三教合一」起源的文本依據。在書中,他也指出:晚明的宗教折衷出現了新的融合邏輯語言,改變過去三教「分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現象,繼而走向「非分隔化」(non-compartmentalization)的路向。錢新祖以焦竑(一五四○─一六二○)為例,說明焦竑的「非分隔化」思想強調三教之間可以「兼存」(coexist)和「混合」(intermix)。(余英時對這個說法則存疑,後文將詳述)有關「宗教折衷」一詞,實是錢新祖中文譯本的詞彙,主要是指焦竑不把三教分列為三,並嘗試作出調和和綜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參照另一位西方學者卜正民對syncretism的看法,卻發現他的詮釋和錢新祖大不相同。卜正民認為syncretism這個詞彙,在西方語境裡,更多是用來解釋宗教的調和狀態,尤其是在基督教內部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調和。二者的根本性差異在於:(1)兩人對於syncretism的指涉認知不同,分別具「折衷」和「調和」的意思,這又和他們個別的宗教和思想視角有關;(2)對於syncretism所預設的思想基礎有所不同,關鍵在於把syncretism看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抑或是具有清晰目的的「結果」。明顯的,錢新祖關注前者,而卜正民則注重後者。錢新祖認為焦竑的三教觀,尤其是「天無二月」所揭示的「兼存」的看法,貫通儒釋,互為義疏,重構晚明的新儒思想。相反的,卜正民從嚴格的角度審視,他不認為中國曾經歷宗教調和的歷史進程,對他而言,syncretism發生在不同的宗教思想源流或系統的相互融合之中,一般上較強的宗教傳統將吸納或整合較弱的思想,最終調和的結果是:只有一種世界觀的宗教系統。卜正民最基本的判別是,三教之間並沒有呈現「一體化」的體系,尤其是仍可以維持三教各自的世界觀。
第二章 明中葉三教合流之衍變
關於三教之間的交涉,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末年牟融的《理惑論》。《理惑論》反映的是佛教東傳初期的思想狀態,當時人們多以黃老道家的視野來理解佛教,甚至以《老子》之說來批判道教和神仙方術。而漢代道教經書如《太平經》和《老子想爾注》則吸收不少儒家思想,前者著重「尊陽陰卑」、三綱六紀的思想,後者把忠孝仁義等道德規範,都納入在「道」的統屬之下。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之間的認識相應提高,義理的互涉和交融,才有實質的開展,但爭論也益發激烈。西晉道士王浮以《老子化胡經》揚道抑佛,東晉釋慧遠(三三四─四一六)的〈沙門不敬王者論〉則為佛教尋求超脫世俗的獨立地位。這時期佛教備受儒道批評,出現大量反佛和護佛的文章。縱然如此,亦有不少主張三教一致和融合的聲音,例如釋道安(三一二─三八五)在〈二教論〉說:「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跡誠異,理會則同」、宗炳(三七五─四四三)〈明佛論〉言:「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道士陶弘景(四四四─四九七)也認同「百法分湊,無越三教之境」。至唐代,無論是官方或民間都熱中於佛道,尤其是官方舉辦的講論活動更促進了三教的交融,遂引起儒家衛道者的批評。韓愈嚴厲批判佛道,以〈原道〉一文樹立儒家仁義之道,以區別於佛老之道。李翱(七七四─八三六)的《復性書》,融三教於道德修養,對宋明思想影響深遠。宋代以後,不少儒者都有「出入二氏,返回六經」的共同經驗,一方面吸收佛道的思維和工夫,一方面又闢佛道,尤對佛教嚴苛,其理由是:(一)佛教是出世之學,遺棄人倫;(二)佛教視天地為幻妄;(三)佛道以生死動人(老氏貪生,釋氏畏死),例如朱熹(一一三○─一二○○)曾言:「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而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因此在宋元時期,不少代表性的著作,如契嵩(一○○七─一○七二)《輔教編》、張商英(一○四三─一一二一)《護法論》、夏元鼐(生卒年不詳)《三教歸一圖說》以及陶宗儀(一三二○ ─一四○二)《三教一源圖》等書,都帶有護教的色彩。此外,宋代道士張伯端(九八七─一○八二)融三教於道教修行思想,提倡「三教歸一」理論;另有融合儒家「大中至正之道」和佛教「明心見性」的道教宗派淨明道。而金代道士王重陽(一一一三─一一七○)隨後更創立了三教同源的全真道。由此可知宋儒嚴厲闢佛,佛道之間卻相互吸收,甚至融合儒家義理來豐富自己的內容。
三教交流在明代又有另一種轉向,明太祖以三教合一理念為治國意識形態,並著有《三教論》、《釋道論》等以宗教信仰立說的著作,以佛道思想輔助王道,開啟明代「三教合一」政教化的端緒,對後來的政教發展影響深遠。之後明儒沈士榮(生卒年不詳)《續原教論》、屠隆(一五四三─一六○五)《佛法金湯錄》、雲棲袾宏(一五三五─一六一五)《緇門崇行錄》等均主三教調和之說,儒釋道之間相互援引的風氣,已蔚為風潮。明中葉以後,三教合流可以說已進入一個巔峰時期,「合一觀」儼然成為明中葉以後的思想基調。這時期出現了像林兆恩這等人物,試圖把三教合一變成一種「正統思想」,推廣至各個宗教領域與社會階層,以致後人多半把他看作是一名「宗教家」而非「思想家」。當時主張三教融合最大的儒者群體,應屬陽明學一脈諸子。他們除了涉足三教以外,與僧人道士也有頻密的互動,尤其是不少儒者和僧人的密切關係,使儒佛儼然形成一種「聯盟關係」。當時屬陽明學派的儒者與僧人的交往,除了論學與聯誼以外,也在思想情感上互相支援,攜手抑制在「朱子學」影響下所產生的強大排佛壓力。這樣的一種聯盟關係,無疑更加速了三教合流的狀態。從義理角度而言,陽明學者和佛教的親合關係,可從「良知」和「無善無惡」了解二者相似的內在思維邏輯。此外,不少陽明後學感悟良知失去抗衡現實的能力,而程朱之「理」又失去約束力,因此轉向佛教尋求思想資源,並強調「學佛以知儒」。另一方面,佛教尋求復興過程中,也吸收陽明一脈的心學抑或儒家義理,以達到「學儒知佛」。無論是宋代僧人智圓(九七六─一○二二)、契嵩(一○○七─一○七二)或於明中葉以後致力於佛教改革的憨山德清、紫柏真可(一五四三─一六○三)等僧人都具有「援儒解佛」的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