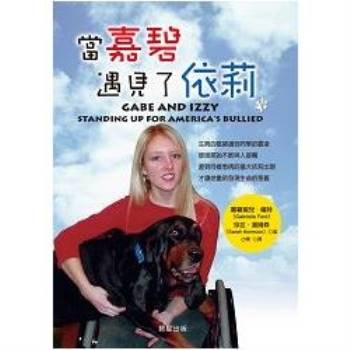第三章
霸凌
生病之後,我只見過丹尼斯幾次。過了好一段時間後,我終於了解到,他並沒多大興趣保持聯絡。這是我和母親必須自己解決的事。
得知診斷結果後的幾個星期,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母親在身後幫我梳頭。自從上次丹尼斯帶我去剪短後,頭髮已經變長許多,雖然還不到以前的長度,但已足夠讓母親為我梳頭。我靜靜享受梳子上下滑過髮絲。
「嘉碧,」母親說:「我一直想著妳的病,還有它對妳造成的影響。」
我明白接下來將展開「母親的教誨」,但因為太喜歡她幫我梳頭,我選擇留下來繼續聽。
「嘉碧,我們都知道,有一天妳將不能行走,」她繼續說:「但是我們要接受命運,我們不能總是回頭看,我們要繼續向前,並讓每天都過得很值得。每個我們一起度過的日子,都會是最棒的一天。」
「我知道,我會努力的,」我回答:「但你們要答應我一件事。我不想聽見任何和這疾病有關的事,我沒辦法去想。只要一想起,我就覺得沮喪。」
母親完全理解我所說的。從這天起,所有相關的字眼,像是輪椅、助行器、拐杖、腿部支撐器、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都不再出現在屋子裡。當我在的時候,我甚至不讓他們觀看由傑瑞.路易斯主持的,為肌肉萎縮症患者募款的節目。這節目太讓我害怕了。我沒辦法看見那些人受到折磨的樣子,畢竟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其中一員。
所以我不再談論生病的事,絕不。不知為何我深信,只要不再提到這個病,或提到任何相關的字眼,病魔就不會來找我。症狀不會加重,我仍然能做任何以前能做的事。這想法毫無邏輯可言,但我必須這樣想,才能幫助自己走下去。不然我可能會直接放棄。
母親要我知道,我並不是唯一罹患此病的人。她幫我找到幾個罹患相同疾病的青少年。但經過幾次會面,我告訴母親我並不想和他們來往。並不是他們不好,但顯然地,大家都只想談和這疾病有關的事,而我並不想。我根本不願意想起這件事。
除此之外,在我心中還有一個煩惱。九月即將到來,我將升上八年級,而我將進入一所新的學校。我將在那兒度過八到十二年級,我要成為高中生了。在新學校的生活即將展開,伴隨而來的是許多新面孔。這會是我第一次帶著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上學。我非常肯定,若他們知道我的病,一定不會想和我做朋友。有誰會喜歡這麼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我為自己定下目標:我在整個高中生涯,絕對不用輪椅。當然,也包含拐杖、助行器、支撐器那些東西。我的學校很小,要是使用這類器具,就會顯得十分醒目,而我絕不想引人注意。有少數幾位好友知道我的病情,但絕大多數同學都不知道─我要讓旁人看到一個「正常」的我。
這應該不會很難吧?只需走過長廊到教室,坐到位子上,然後回答老師的問題。
這些事曾經很容易,但是一切都不一樣了。走路對我來說愈來愈吃力,階梯變成了障礙,有著大階梯的講臺更糟。我已經無法保持平衡,愈來愈容易跌跤。甚至我的聲帶也開始改變,從口中發出的聲音變得古怪,就彷彿剛學說話的兒童一般。
但這些我都假裝沒有發生。我試圖忽略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的所有症狀,並且希望其他同學也這麼做。
但他們並沒有。他們清楚看到我拒絕面對的事。我認為自己就是嘉碧,就像從前一樣,但同學們看見的卻是一個掙扎著走路的女孩,說話也含糊不清。我的成績一落千丈,因為我必須把精力挪到每一個動作上。
在他們的眼中,只看見一個「與大家不同」的人。
但我無法隱藏說話和走路的樣子,甚至是成績。老師總是把改好的考卷和作業發給每排第一個同學,再傳到後排。如此一來,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偷瞄後面同學的分數。我真的萬分痛恨這件事,痛恨前面的同學看見我考得多糟。這讓他們覺得我很笨,但我不是,我只是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將精神集中在學業上,因為我必須戰戰兢兢,讓自己每分每秒都看起來「正常」。
我的成績、我說話的樣子、我走路的方式都讓我成為醒目的標的。
最初聽見那些惡劣的批評時,我都把它當作是玩笑,畢竟我是個新生,這種事很常發生。但幾個月過去了,情況只變得更糟。當然,每個人的高中時期,多少有些不開心的往事,可能是個批評、一次惡意的嘲弄、一個侮辱的動作。但對我而言,這些事天天上演,甚至一天發生好幾次。從八年級到十二年級,我根本不記得哪天沒被嘲笑過。老實說,之前我就曾被霸凌過。七年級時,合唱團有個女孩,這裡就叫她「蘿絲」吧。每當我走進教室,準備開始唱歌時,蘿絲就開始批評我的穿著。為何我的牛仔褲是雜牌?能不能穿得酷一點啊?某天和母親逛街時,我在特價出清的櫃位上,發現一條名牌牛仔褲。我立刻興奮地買下,迫不及待要到學校炫耀一番。但隔天到了學校,卻只引來更多訕笑。蘿絲冷冷地說,這是男款的牛仔褲!後來我把褲子塞到衣櫃最深處,死也不穿第二次。母親不斷問我為什麼不穿了?畢竟我央求了好久才讓她買的。但我要如何告訴她,自己因為穿到男款的衣服而被大家嘲笑?
後來換座位時,我的運氣很差,蘿絲就坐我正後方。這使她能很輕易地用那本又厚又重的樂譜打我的頭。我並不想承認後來的發展,但面對一次次攻擊,我卻無力反抗,只是變得更加畏縮,枯等著樂譜一次次落下,之後還得忍受隨之而來的笑聲。每個旁觀者似乎都覺得有趣,但是這到底哪裡有趣?你身邊正有人遭受傷害!
終於我忍無可忍了,我告訴母親發生了什麼事。
母親認識蘿絲的媽媽,她馬上撥了電話。那個女人說她會和女兒談談。之後,蘿絲道歉了。從那天起,再也沒有硬皮書落在我的頭上。
但上了高中,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不只是要面對某個惡劣女孩而已。我還必須和自己的身體纏鬥,別人想都不用想就能完成的事,我則需要花上好大力氣才能做到。每當我掙扎著前進時,感覺就像是全校都在跟我作對。
總是不斷地有同學愛用手圍住嘴巴,並前後移動,來嘲笑我說話結巴的樣子。疾病使我的眼球不自主抖動,他們就說我看起來像個低能兒。
隨著平衡感逐漸喪失,肌肉也變得更加無力,走廊像是永遠走不完,教室無比遙遠。即使是打開置物櫃之類的簡單動作,對我都是一種折磨,每當我好不容易打開門,總會有人故意來把它關上。有一次,一個男孩甚至越過我的頭,拿走放在櫃子最上層的CD。他在我面前揮舞那些CD,一邊嘲笑我,然後心滿意足地離開。我再也沒有拿回那些CD。
有一次,老師要我們到戶外拍攝班級照片。如此簡單的事─走出教室,坐在看臺上,微笑。對我來說卻絕不簡單。因為要到達拍照的場地,必須先穿過一段碎石子路。我吃力地移動身體到路口。看見那些石子,我心中升起恐懼,這就像穿過一公尺深的沼澤一樣難。走一般的平路已經不容易,像這樣高低不平又顛簸的路段,我一定會絆倒的。但我別無選擇。所有同學都已經向前走,若此時說我辦不到,就會顯得引人注目─這是我一直以來極力避免的。
我決定邁開步伐了。但每跨出一步,我都彷彿看見自己在全班面前跌倒的樣子。那會是多麼丟臉啊!萬一正面朝下跌在碎石堆,看起來就完全像個低能兒了。若是這樣,那我寧可死了算了。
還好這次我成功了,靠著自己的雙腳,我平安抵達看臺。然而,在大家面前跌倒的恐懼就跟真正跌倒一樣糟糕。在此之後數年,這恐懼一直不曾遠離我。
我恐懼跌倒是有原因的,不只因身體上的疼痛,我還會被大家所恥笑。會這麼糾結,也是因為這事常常發生。有次我正奮力翻過三個階梯時,不小心跌坐在地,正巧一個愛嘲弄我的男孩經過。這件事很快傳遍校園,他不斷向大家宣傳,「嘉碧連個樓梯都走不好!」他很賣力地不讓任何人遺忘這件事。
其實我跌倒的原因並不全是自己造成。同學們總愛站在我身後,突然間我就失去了平衡。有些人會默默推我一把,甚至把我用力推向另一個同學,然後笑聲便哄然響起。我的書常被從手中打落,某人會接著把書踢走,讓我在地上跌跌撞撞地找尋,這是他們的樂趣。
還有許許多多飛彈攻擊─對我吐口水,丟橡皮擦、釘書針、鉛筆、粉筆、咬過的口香糖等等。他們甚至會打我的臉或者拉扯我的頭髮,並對我丟出各種難聽的字眼。
「妳喝醉了嗎?」
「妳活像個醉鬼。」
「妳說話也像個醉鬼!嘉碧,妳喝酒該節制了!」
當然我並沒喝酒。是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造成我走路不穩、說話口齒不清。但我並不想告訴這些人,他們只會笑得更大聲。
我也曾想要解釋一切,若他們了解我與眾不同的原因,也許就會放過我了?也有可能,這會讓他們有更多理由嘲笑我。我無法確定是哪種結果,所以選擇保持沉默。反正我本來就不想提起這個病,也不認為有必要告訴大家。健康是個人的隱私,難道只為了能平靜地穿過走廊,我就必須向全校宣布自己努力隱藏的祕密?即使下課鈴聲響起,霸凌也未結束。回家的最短路徑是條繁忙的馬路,而且沒有人行道可走。我必須小心翼翼地專注在每一個腳步上,以穿越那顛簸又充滿碎石的路肩。此時,經常有一些孩子會跟著我,或者他們會站在路的另一頭,不斷地用侮辱性的字眼罵我。
「妳怎麼回事啊,嘉碧?」有人會這麼說:「妳得腦瘤了嗎?」或者他們會嘲笑我的青春痘是「比薩臉!」我當然有青春痘─每個孩子都有,我們是青少年啊。但不知為何,我的青春痘使我成為霸凌的目標,而其他人卻不會。
霸凌甚至波及我親愛的妹妹。我絕不會忘記那天,七歲的凱特琳哭著從校車上跑回家。「我們是一群垃圾窮人嗎?」她抽抽噎噎地問。這對我來說只是家常便飯,但從未直接發生在家人身上。我們居住的這一側有個公園,不遠處還有個美麗的湖泊,湖邊林立著許多大別墅,都是有錢人家的豪宅。我的學校正好位於兩個社區中間。雖然說不出什麼道理,但住在湖邊的孩子總瞧不起住公園那頭的孩子。我愛那公園,那兒是我的家,我一點也不因住在那裡而感到羞恥,直到今天我仍然懷念那裏。只是我真的對小妹很抱歉,她哭得那樣厲害,只因為跟我有相同的姓氏。
看到凱特琳那樣傷心,我感到很難受。那些難聽的字眼落在家人身上,像一根根尖刺折磨著我。然而情況還在持續惡化,並演變成威脅恐嚇。「剛才和妳講話的男生,他是我朋友的菜。」某天午餐後,有個女孩來找我,當時我正坐在體育館,全心都在想自己的事。「所以,若妳敢再跟他講話,我就要賞妳耳光。」她惡狠狠地說。賞我耳光?為了什麼?只因我和自己的朋友說話?然後她還加上一句:「嘉碧是個醜八怪。」
生物課時,兩個女孩老是纏住我,她們指控我向老師告密,所以老師才會知道她們抄別人作業。我發誓我絕對沒有,但她們完全不聽,還威脅要狠狠揍我一頓。當時的我完全不懷疑她們真的敢這麼做。我極需幫助。遭遇霸凌使我又倦又累,卻不知道能逃去哪裡,或能找誰幫忙。我想到母親,若她知道我這樣被人欺負、被辱罵,甚至被打,她絕對會非常生氣。她會馬上衝到學校告訴校長,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有沒有可能,當其他孩子知道她這樣做,反而會更變本加厲地欺負我呢?我也想過向老師或諮商師尋求幫助,但找哪一位呢?要是學校有專責處理霸凌的人員,說不定就能設法和他見面,但學校裡並沒有這樣的角色。在學校,沒有人公開談論霸凌這件事。
而且我也無法信任大人。七年級時,我向學校的諮商師傾訴一切,她是除了家人之外,我第一個訴說的人。但她背叛了我的信任,還告訴許多學生。高中的老師們會不會也一樣?還是算了吧!我不想冒著讓祕密洩漏的風險。
可以肯定的說,我其實不認為大人會幫我。我很確定有老師看到這些霸凌,但他們並不想涉入。沒有人主動伸出援手,我不認為有哪個地方是安全的,或者能讓我訴說困擾。於是,我選擇默默承擔一切。
我只是個被霸凌者圍繞的女孩,哪裡有讓情況改變的能力?
霸凌
生病之後,我只見過丹尼斯幾次。過了好一段時間後,我終於了解到,他並沒多大興趣保持聯絡。這是我和母親必須自己解決的事。
得知診斷結果後的幾個星期,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母親在身後幫我梳頭。自從上次丹尼斯帶我去剪短後,頭髮已經變長許多,雖然還不到以前的長度,但已足夠讓母親為我梳頭。我靜靜享受梳子上下滑過髮絲。
「嘉碧,」母親說:「我一直想著妳的病,還有它對妳造成的影響。」
我明白接下來將展開「母親的教誨」,但因為太喜歡她幫我梳頭,我選擇留下來繼續聽。
「嘉碧,我們都知道,有一天妳將不能行走,」她繼續說:「但是我們要接受命運,我們不能總是回頭看,我們要繼續向前,並讓每天都過得很值得。每個我們一起度過的日子,都會是最棒的一天。」
「我知道,我會努力的,」我回答:「但你們要答應我一件事。我不想聽見任何和這疾病有關的事,我沒辦法去想。只要一想起,我就覺得沮喪。」
母親完全理解我所說的。從這天起,所有相關的字眼,像是輪椅、助行器、拐杖、腿部支撐器、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都不再出現在屋子裡。當我在的時候,我甚至不讓他們觀看由傑瑞.路易斯主持的,為肌肉萎縮症患者募款的節目。這節目太讓我害怕了。我沒辦法看見那些人受到折磨的樣子,畢竟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其中一員。
所以我不再談論生病的事,絕不。不知為何我深信,只要不再提到這個病,或提到任何相關的字眼,病魔就不會來找我。症狀不會加重,我仍然能做任何以前能做的事。這想法毫無邏輯可言,但我必須這樣想,才能幫助自己走下去。不然我可能會直接放棄。
母親要我知道,我並不是唯一罹患此病的人。她幫我找到幾個罹患相同疾病的青少年。但經過幾次會面,我告訴母親我並不想和他們來往。並不是他們不好,但顯然地,大家都只想談和這疾病有關的事,而我並不想。我根本不願意想起這件事。
除此之外,在我心中還有一個煩惱。九月即將到來,我將升上八年級,而我將進入一所新的學校。我將在那兒度過八到十二年級,我要成為高中生了。在新學校的生活即將展開,伴隨而來的是許多新面孔。這會是我第一次帶著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上學。我非常肯定,若他們知道我的病,一定不會想和我做朋友。有誰會喜歡這麼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我為自己定下目標:我在整個高中生涯,絕對不用輪椅。當然,也包含拐杖、助行器、支撐器那些東西。我的學校很小,要是使用這類器具,就會顯得十分醒目,而我絕不想引人注意。有少數幾位好友知道我的病情,但絕大多數同學都不知道─我要讓旁人看到一個「正常」的我。
這應該不會很難吧?只需走過長廊到教室,坐到位子上,然後回答老師的問題。
這些事曾經很容易,但是一切都不一樣了。走路對我來說愈來愈吃力,階梯變成了障礙,有著大階梯的講臺更糟。我已經無法保持平衡,愈來愈容易跌跤。甚至我的聲帶也開始改變,從口中發出的聲音變得古怪,就彷彿剛學說話的兒童一般。
但這些我都假裝沒有發生。我試圖忽略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的所有症狀,並且希望其他同學也這麼做。
但他們並沒有。他們清楚看到我拒絕面對的事。我認為自己就是嘉碧,就像從前一樣,但同學們看見的卻是一個掙扎著走路的女孩,說話也含糊不清。我的成績一落千丈,因為我必須把精力挪到每一個動作上。
在他們的眼中,只看見一個「與大家不同」的人。
但我無法隱藏說話和走路的樣子,甚至是成績。老師總是把改好的考卷和作業發給每排第一個同學,再傳到後排。如此一來,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偷瞄後面同學的分數。我真的萬分痛恨這件事,痛恨前面的同學看見我考得多糟。這讓他們覺得我很笨,但我不是,我只是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將精神集中在學業上,因為我必須戰戰兢兢,讓自己每分每秒都看起來「正常」。
我的成績、我說話的樣子、我走路的方式都讓我成為醒目的標的。
最初聽見那些惡劣的批評時,我都把它當作是玩笑,畢竟我是個新生,這種事很常發生。但幾個月過去了,情況只變得更糟。當然,每個人的高中時期,多少有些不開心的往事,可能是個批評、一次惡意的嘲弄、一個侮辱的動作。但對我而言,這些事天天上演,甚至一天發生好幾次。從八年級到十二年級,我根本不記得哪天沒被嘲笑過。老實說,之前我就曾被霸凌過。七年級時,合唱團有個女孩,這裡就叫她「蘿絲」吧。每當我走進教室,準備開始唱歌時,蘿絲就開始批評我的穿著。為何我的牛仔褲是雜牌?能不能穿得酷一點啊?某天和母親逛街時,我在特價出清的櫃位上,發現一條名牌牛仔褲。我立刻興奮地買下,迫不及待要到學校炫耀一番。但隔天到了學校,卻只引來更多訕笑。蘿絲冷冷地說,這是男款的牛仔褲!後來我把褲子塞到衣櫃最深處,死也不穿第二次。母親不斷問我為什麼不穿了?畢竟我央求了好久才讓她買的。但我要如何告訴她,自己因為穿到男款的衣服而被大家嘲笑?
後來換座位時,我的運氣很差,蘿絲就坐我正後方。這使她能很輕易地用那本又厚又重的樂譜打我的頭。我並不想承認後來的發展,但面對一次次攻擊,我卻無力反抗,只是變得更加畏縮,枯等著樂譜一次次落下,之後還得忍受隨之而來的笑聲。每個旁觀者似乎都覺得有趣,但是這到底哪裡有趣?你身邊正有人遭受傷害!
終於我忍無可忍了,我告訴母親發生了什麼事。
母親認識蘿絲的媽媽,她馬上撥了電話。那個女人說她會和女兒談談。之後,蘿絲道歉了。從那天起,再也沒有硬皮書落在我的頭上。
但上了高中,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不只是要面對某個惡劣女孩而已。我還必須和自己的身體纏鬥,別人想都不用想就能完成的事,我則需要花上好大力氣才能做到。每當我掙扎著前進時,感覺就像是全校都在跟我作對。
總是不斷地有同學愛用手圍住嘴巴,並前後移動,來嘲笑我說話結巴的樣子。疾病使我的眼球不自主抖動,他們就說我看起來像個低能兒。
隨著平衡感逐漸喪失,肌肉也變得更加無力,走廊像是永遠走不完,教室無比遙遠。即使是打開置物櫃之類的簡單動作,對我都是一種折磨,每當我好不容易打開門,總會有人故意來把它關上。有一次,一個男孩甚至越過我的頭,拿走放在櫃子最上層的CD。他在我面前揮舞那些CD,一邊嘲笑我,然後心滿意足地離開。我再也沒有拿回那些CD。
有一次,老師要我們到戶外拍攝班級照片。如此簡單的事─走出教室,坐在看臺上,微笑。對我來說卻絕不簡單。因為要到達拍照的場地,必須先穿過一段碎石子路。我吃力地移動身體到路口。看見那些石子,我心中升起恐懼,這就像穿過一公尺深的沼澤一樣難。走一般的平路已經不容易,像這樣高低不平又顛簸的路段,我一定會絆倒的。但我別無選擇。所有同學都已經向前走,若此時說我辦不到,就會顯得引人注目─這是我一直以來極力避免的。
我決定邁開步伐了。但每跨出一步,我都彷彿看見自己在全班面前跌倒的樣子。那會是多麼丟臉啊!萬一正面朝下跌在碎石堆,看起來就完全像個低能兒了。若是這樣,那我寧可死了算了。
還好這次我成功了,靠著自己的雙腳,我平安抵達看臺。然而,在大家面前跌倒的恐懼就跟真正跌倒一樣糟糕。在此之後數年,這恐懼一直不曾遠離我。
我恐懼跌倒是有原因的,不只因身體上的疼痛,我還會被大家所恥笑。會這麼糾結,也是因為這事常常發生。有次我正奮力翻過三個階梯時,不小心跌坐在地,正巧一個愛嘲弄我的男孩經過。這件事很快傳遍校園,他不斷向大家宣傳,「嘉碧連個樓梯都走不好!」他很賣力地不讓任何人遺忘這件事。
其實我跌倒的原因並不全是自己造成。同學們總愛站在我身後,突然間我就失去了平衡。有些人會默默推我一把,甚至把我用力推向另一個同學,然後笑聲便哄然響起。我的書常被從手中打落,某人會接著把書踢走,讓我在地上跌跌撞撞地找尋,這是他們的樂趣。
還有許許多多飛彈攻擊─對我吐口水,丟橡皮擦、釘書針、鉛筆、粉筆、咬過的口香糖等等。他們甚至會打我的臉或者拉扯我的頭髮,並對我丟出各種難聽的字眼。
「妳喝醉了嗎?」
「妳活像個醉鬼。」
「妳說話也像個醉鬼!嘉碧,妳喝酒該節制了!」
當然我並沒喝酒。是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造成我走路不穩、說話口齒不清。但我並不想告訴這些人,他們只會笑得更大聲。
我也曾想要解釋一切,若他們了解我與眾不同的原因,也許就會放過我了?也有可能,這會讓他們有更多理由嘲笑我。我無法確定是哪種結果,所以選擇保持沉默。反正我本來就不想提起這個病,也不認為有必要告訴大家。健康是個人的隱私,難道只為了能平靜地穿過走廊,我就必須向全校宣布自己努力隱藏的祕密?即使下課鈴聲響起,霸凌也未結束。回家的最短路徑是條繁忙的馬路,而且沒有人行道可走。我必須小心翼翼地專注在每一個腳步上,以穿越那顛簸又充滿碎石的路肩。此時,經常有一些孩子會跟著我,或者他們會站在路的另一頭,不斷地用侮辱性的字眼罵我。
「妳怎麼回事啊,嘉碧?」有人會這麼說:「妳得腦瘤了嗎?」或者他們會嘲笑我的青春痘是「比薩臉!」我當然有青春痘─每個孩子都有,我們是青少年啊。但不知為何,我的青春痘使我成為霸凌的目標,而其他人卻不會。
霸凌甚至波及我親愛的妹妹。我絕不會忘記那天,七歲的凱特琳哭著從校車上跑回家。「我們是一群垃圾窮人嗎?」她抽抽噎噎地問。這對我來說只是家常便飯,但從未直接發生在家人身上。我們居住的這一側有個公園,不遠處還有個美麗的湖泊,湖邊林立著許多大別墅,都是有錢人家的豪宅。我的學校正好位於兩個社區中間。雖然說不出什麼道理,但住在湖邊的孩子總瞧不起住公園那頭的孩子。我愛那公園,那兒是我的家,我一點也不因住在那裡而感到羞恥,直到今天我仍然懷念那裏。只是我真的對小妹很抱歉,她哭得那樣厲害,只因為跟我有相同的姓氏。
看到凱特琳那樣傷心,我感到很難受。那些難聽的字眼落在家人身上,像一根根尖刺折磨著我。然而情況還在持續惡化,並演變成威脅恐嚇。「剛才和妳講話的男生,他是我朋友的菜。」某天午餐後,有個女孩來找我,當時我正坐在體育館,全心都在想自己的事。「所以,若妳敢再跟他講話,我就要賞妳耳光。」她惡狠狠地說。賞我耳光?為了什麼?只因我和自己的朋友說話?然後她還加上一句:「嘉碧是個醜八怪。」
生物課時,兩個女孩老是纏住我,她們指控我向老師告密,所以老師才會知道她們抄別人作業。我發誓我絕對沒有,但她們完全不聽,還威脅要狠狠揍我一頓。當時的我完全不懷疑她們真的敢這麼做。我極需幫助。遭遇霸凌使我又倦又累,卻不知道能逃去哪裡,或能找誰幫忙。我想到母親,若她知道我這樣被人欺負、被辱罵,甚至被打,她絕對會非常生氣。她會馬上衝到學校告訴校長,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有沒有可能,當其他孩子知道她這樣做,反而會更變本加厲地欺負我呢?我也想過向老師或諮商師尋求幫助,但找哪一位呢?要是學校有專責處理霸凌的人員,說不定就能設法和他見面,但學校裡並沒有這樣的角色。在學校,沒有人公開談論霸凌這件事。
而且我也無法信任大人。七年級時,我向學校的諮商師傾訴一切,她是除了家人之外,我第一個訴說的人。但她背叛了我的信任,還告訴許多學生。高中的老師們會不會也一樣?還是算了吧!我不想冒著讓祕密洩漏的風險。
可以肯定的說,我其實不認為大人會幫我。我很確定有老師看到這些霸凌,但他們並不想涉入。沒有人主動伸出援手,我不認為有哪個地方是安全的,或者能讓我訴說困擾。於是,我選擇默默承擔一切。
我只是個被霸凌者圍繞的女孩,哪裡有讓情況改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