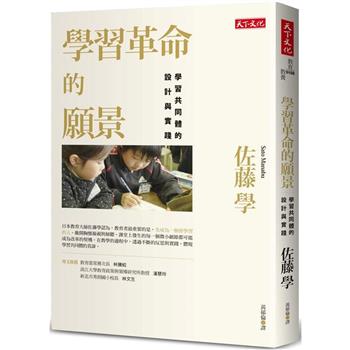課例:「先乘除後加減」
這堂是由涉谷昌道老師指導的小學四年級數學課,為了教導學生四則運算先乘除後加減的概念,將主題設定為「讓人信賴的收銀員」,由學生扮演超市收銀員操作計算機。題目是「購買四○○圓的水彩一盒與一八○圓的水彩筆三隻,總共多少錢?」如果直接按計算機「400+180×3 =?」會出現「一七四○圓」的錯誤答案。教師希望學生透過發現上述的錯誤,理解「必須先計算乘法」的意義,同時促進「機械性計算的反思」。
仔細檢視涉谷老師所設計與實踐的課堂,會發現在認知性、社會性、倫理性三個過程中產生了許多複雜的綜合性問題。而課堂與學習就是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進行。
首先,從認知性的過程來看,涉谷老師原本希望學生在操作計算機計算「400+180×3」時產生「一七四○圓」的錯誤答案,再探究錯誤的原因發現應該要「先乘除後加減」,成長為熟知四則運算順序的「讓人信賴的收銀員」(熟知計算的人)。然而,過程中發生了兩件出乎涉谷老師預料的事件。其一,一位有學習障礙的男學生,由於他遇到每個乘法問題都以加法計算,所以上述問題他也用計算機操作「400+180+180+180」,即得到正確答案「九四○圓」,跳脫出涉谷老師原先希望學生從錯誤中學習的計畫。其二,班上有好幾名學生已事先在補習班學到「先乘除」,因此立即發現了計算機的錯誤而中斷思考。透過在課堂中即興發生的這兩個狀況,涉谷老師因此提醒學生「以『大約』的量感進行計算的重要性」及「用其他計算方式再次確認的重要性」,讓數學思考的幅度變得更加寬廣。像這樣的發展,完全是規畫課程時所未預料到的結果。如果從數學性的認知來看,會發現在這堂課中登場的「三種數學」十分有趣。第一種是涉谷老師所設定,並希望學生思考學習的「推理與論證的數學」(真正的數學),旨在透過具體的活動建構數學的意義,並以一貫的理論思考。第二種則是有學習障礙的男學生所提出的「日常生活的數學」(直接的數學)。這個「日常生活的數學」,就如男學生所言,並非以計算方式的意義或理論為基礎,而是以「大約」的感覺來推測,是土法煉鋼、簡易、絕不出錯的計算方式。第三種則是由已懂得要先算乘法的幾位學生的「考試數學」(補習班的數學)。這種數學捨棄了數學推論的一貫性,或數學意義(量的意義與技術的意義)的建構,重視背誦能得到正確答案的手續與應用。在涉谷老師這個以「四則運算」為主題的課堂中,出現了以上三種不同文化的數學,因而發展出各自爭奪主導權、相互衝突的狀況。在教育內容的文化中,這樣的困境可說是所有課堂的共通現象。
從社會性過程(人際關係的過程)來看,我們首先注目的是,學習障礙的男學生與涉谷老師的關係。據說這名學生常在上課中離開座位在教室走動,因此涉谷老師上課前都會煩惱著要如何應對這孩子突如其來的行動、如何與他培養關係。不過在這堂數學課中根本不需要煩惱,關鍵在於課堂一開始,老師向學生說明超市收銀員的工作時,這名學生就率先發言說道:「我知道怎麼當收銀員喔!」涉谷老師也隨即給予回應及讚許,這名學生與涉谷老師的關係因此得到有趣的開展。因受到讚許而高興的學生聽到每一個題目,都用加法代替乘法來計算,以致答案完全正確,並未掉入老師所設的陷阱中。即使教室中其他的學生都掉入計算機的「陷阱」而得到錯誤答案,也不改其想法。在這堂課中,這個孩子與教室中其他學生的關係與平常不同,轉換為另一種新的關連。這名學生與教師的關係則進入更複雜的關連。針對這名學生的計算方式及發言,涉谷老師積極讚許「抱持『大約』的量感來計算相當重要」、「不要只用一種方式計算,用別的方式計算也很重要」,藉以提醒教室中的其他學生。在這堂課中,這名學生的思考順利的與其他同學的思考相互交流影響,也就是在尊重思考的多樣性下,透過每位學生各自不同的理解,再次深入咀嚼自己的思考。在這種情況下所交織出來的社會性關係,明確指示教室應被重新打造為「相互探究、議論的共同體(discourse community)」。
建立起上述意義與關係的認知性、社會性的過程,同時也是倫理性過程。這裡所說的倫理性過程,指的是重新審視自我認同,導向更好的自己的過程。也就是自我的重建。這名學生之所以熱心投入課程的原因就在於,常常陷入危機的自我認同,在這堂課中終於得以伸張,他能夠看到自己投入學習的樣貌。特別的是,只會加法的他,居然是教室中唯一完全沒有算錯的人,這樣的經驗對於他重建原本認知的自我形象,意義極為重大。只是到了課堂尾聲,老師的總結變成抽象的說明時,這名學生又回復到平常上課的樣子,閉上眼睛,兩手做出忍者般的動作,整個人好像處於其他時空。這個例子如實訴說著,所謂的課堂就是激勵孩子的自我認同,使其面臨自我存在的危機,並促使他們加以重新調整的倫理性過程。
對教師來說也是這樣。涉谷老師也在這堂課中賭上自己,挑戰放下「資深教師的身段」,不按照計畫授課,不以自己的意志控制孩子的學習。其實,涉谷老師在這次挑戰之前,曾經在別的學校用同一教材授課,在那堂課中也有學生以加法計算出正確答案,但因為這樣會妨礙教師用意與課堂策略,所以當時涉谷老師採取了忽視的對應方式。為了超越自己的界限,涉谷老師再次挑戰同一課程。這一次,他希望自己能從單方面用自己的思考方式控制學生的教師,蛻變成能與各式各樣的孩子相互交流學習的教師。這堂課即是涉谷老師重建自我認同感的實踐,也是他改變生存方式的倫理性實踐。在反省的過程中,涉谷老師仍持續進行自我認同的重建。課後涉谷老師觀看課堂的影片紀錄,一方面對自己能即興對應教室中出乎意料的事件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也重新發現在與學生對應之間,身體的形式化反應。首先是手部的動作。涉谷老師發現,自己在跟學生說話或聽取學生意見時,手部只有單調的兩個動作,不是雙手抱胸,就是交叉放在背後。他希望自己能以更柔軟的肢體語言與孩子接觸。此外涉谷老師也很在意自己的表情「只有嘴角在笑」,他期許自己是能夠在課堂中身心都能完全投入,與學生共同享受學習的教師。從這堂課的進行過程與發生的事件,即能看出教師省視自我存在的倫理性實踐。
這個課例明白顯示,課堂的過程除了是認知的實踐,透過構成對象(教育內容)的意義,養成特定的概念或意義的連結;同時也是社會的實踐,將認知的實踐在教室中與教師、同學形成關連;更是倫理的實踐,透過反思吟味自己的思考或態度,重建自我認同。所謂教育的實踐(課堂與學習),就是「構築世界(重建認知內容=與對象世界的對話)」、「構築同伴(重建人際關係=與他人的對話)」、「構築自我(重建自我概念=與自己的對話)」涵蓋這三種對話的複合式實踐。
這堂是由涉谷昌道老師指導的小學四年級數學課,為了教導學生四則運算先乘除後加減的概念,將主題設定為「讓人信賴的收銀員」,由學生扮演超市收銀員操作計算機。題目是「購買四○○圓的水彩一盒與一八○圓的水彩筆三隻,總共多少錢?」如果直接按計算機「400+180×3 =?」會出現「一七四○圓」的錯誤答案。教師希望學生透過發現上述的錯誤,理解「必須先計算乘法」的意義,同時促進「機械性計算的反思」。
仔細檢視涉谷老師所設計與實踐的課堂,會發現在認知性、社會性、倫理性三個過程中產生了許多複雜的綜合性問題。而課堂與學習就是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進行。
首先,從認知性的過程來看,涉谷老師原本希望學生在操作計算機計算「400+180×3」時產生「一七四○圓」的錯誤答案,再探究錯誤的原因發現應該要「先乘除後加減」,成長為熟知四則運算順序的「讓人信賴的收銀員」(熟知計算的人)。然而,過程中發生了兩件出乎涉谷老師預料的事件。其一,一位有學習障礙的男學生,由於他遇到每個乘法問題都以加法計算,所以上述問題他也用計算機操作「400+180+180+180」,即得到正確答案「九四○圓」,跳脫出涉谷老師原先希望學生從錯誤中學習的計畫。其二,班上有好幾名學生已事先在補習班學到「先乘除」,因此立即發現了計算機的錯誤而中斷思考。透過在課堂中即興發生的這兩個狀況,涉谷老師因此提醒學生「以『大約』的量感進行計算的重要性」及「用其他計算方式再次確認的重要性」,讓數學思考的幅度變得更加寬廣。像這樣的發展,完全是規畫課程時所未預料到的結果。如果從數學性的認知來看,會發現在這堂課中登場的「三種數學」十分有趣。第一種是涉谷老師所設定,並希望學生思考學習的「推理與論證的數學」(真正的數學),旨在透過具體的活動建構數學的意義,並以一貫的理論思考。第二種則是有學習障礙的男學生所提出的「日常生活的數學」(直接的數學)。這個「日常生活的數學」,就如男學生所言,並非以計算方式的意義或理論為基礎,而是以「大約」的感覺來推測,是土法煉鋼、簡易、絕不出錯的計算方式。第三種則是由已懂得要先算乘法的幾位學生的「考試數學」(補習班的數學)。這種數學捨棄了數學推論的一貫性,或數學意義(量的意義與技術的意義)的建構,重視背誦能得到正確答案的手續與應用。在涉谷老師這個以「四則運算」為主題的課堂中,出現了以上三種不同文化的數學,因而發展出各自爭奪主導權、相互衝突的狀況。在教育內容的文化中,這樣的困境可說是所有課堂的共通現象。
從社會性過程(人際關係的過程)來看,我們首先注目的是,學習障礙的男學生與涉谷老師的關係。據說這名學生常在上課中離開座位在教室走動,因此涉谷老師上課前都會煩惱著要如何應對這孩子突如其來的行動、如何與他培養關係。不過在這堂數學課中根本不需要煩惱,關鍵在於課堂一開始,老師向學生說明超市收銀員的工作時,這名學生就率先發言說道:「我知道怎麼當收銀員喔!」涉谷老師也隨即給予回應及讚許,這名學生與涉谷老師的關係因此得到有趣的開展。因受到讚許而高興的學生聽到每一個題目,都用加法代替乘法來計算,以致答案完全正確,並未掉入老師所設的陷阱中。即使教室中其他的學生都掉入計算機的「陷阱」而得到錯誤答案,也不改其想法。在這堂課中,這個孩子與教室中其他學生的關係與平常不同,轉換為另一種新的關連。這名學生與教師的關係則進入更複雜的關連。針對這名學生的計算方式及發言,涉谷老師積極讚許「抱持『大約』的量感來計算相當重要」、「不要只用一種方式計算,用別的方式計算也很重要」,藉以提醒教室中的其他學生。在這堂課中,這名學生的思考順利的與其他同學的思考相互交流影響,也就是在尊重思考的多樣性下,透過每位學生各自不同的理解,再次深入咀嚼自己的思考。在這種情況下所交織出來的社會性關係,明確指示教室應被重新打造為「相互探究、議論的共同體(discourse community)」。
建立起上述意義與關係的認知性、社會性的過程,同時也是倫理性過程。這裡所說的倫理性過程,指的是重新審視自我認同,導向更好的自己的過程。也就是自我的重建。這名學生之所以熱心投入課程的原因就在於,常常陷入危機的自我認同,在這堂課中終於得以伸張,他能夠看到自己投入學習的樣貌。特別的是,只會加法的他,居然是教室中唯一完全沒有算錯的人,這樣的經驗對於他重建原本認知的自我形象,意義極為重大。只是到了課堂尾聲,老師的總結變成抽象的說明時,這名學生又回復到平常上課的樣子,閉上眼睛,兩手做出忍者般的動作,整個人好像處於其他時空。這個例子如實訴說著,所謂的課堂就是激勵孩子的自我認同,使其面臨自我存在的危機,並促使他們加以重新調整的倫理性過程。
對教師來說也是這樣。涉谷老師也在這堂課中賭上自己,挑戰放下「資深教師的身段」,不按照計畫授課,不以自己的意志控制孩子的學習。其實,涉谷老師在這次挑戰之前,曾經在別的學校用同一教材授課,在那堂課中也有學生以加法計算出正確答案,但因為這樣會妨礙教師用意與課堂策略,所以當時涉谷老師採取了忽視的對應方式。為了超越自己的界限,涉谷老師再次挑戰同一課程。這一次,他希望自己能從單方面用自己的思考方式控制學生的教師,蛻變成能與各式各樣的孩子相互交流學習的教師。這堂課即是涉谷老師重建自我認同感的實踐,也是他改變生存方式的倫理性實踐。在反省的過程中,涉谷老師仍持續進行自我認同的重建。課後涉谷老師觀看課堂的影片紀錄,一方面對自己能即興對應教室中出乎意料的事件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也重新發現在與學生對應之間,身體的形式化反應。首先是手部的動作。涉谷老師發現,自己在跟學生說話或聽取學生意見時,手部只有單調的兩個動作,不是雙手抱胸,就是交叉放在背後。他希望自己能以更柔軟的肢體語言與孩子接觸。此外涉谷老師也很在意自己的表情「只有嘴角在笑」,他期許自己是能夠在課堂中身心都能完全投入,與學生共同享受學習的教師。從這堂課的進行過程與發生的事件,即能看出教師省視自我存在的倫理性實踐。
這個課例明白顯示,課堂的過程除了是認知的實踐,透過構成對象(教育內容)的意義,養成特定的概念或意義的連結;同時也是社會的實踐,將認知的實踐在教室中與教師、同學形成關連;更是倫理的實踐,透過反思吟味自己的思考或態度,重建自我認同。所謂教育的實踐(課堂與學習),就是「構築世界(重建認知內容=與對象世界的對話)」、「構築同伴(重建人際關係=與他人的對話)」、「構築自我(重建自我概念=與自己的對話)」涵蓋這三種對話的複合式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