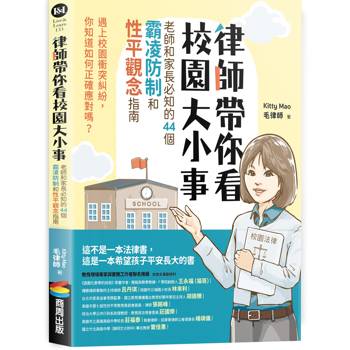〈自序〉老師守法,孩子不受傷:用溫暖的法律,守護校園裡的每一個人
校園,應該是孩子快樂學習、安心成長的地方。但我在參與多起校園事件調查與法律輔導的過程中,看到太多令人遺憾的誤解與衝突。有時,是孩子之間不懂分寸的互動,演變成傷害;有時,是老師原本出於善意的舉動,卻在不知情中踩到法律紅線;有時,是家長急切想要為孩子討回公道,卻在資訊不明中感到無助與憤怒。
懂法律,是為了更好地愛孩子
我是律師,但我從不以審判者的姿態面對教育現場。我深信,絕大多數的校園問題,不是惡意造成的傷害,而是資訊不對等、制度複雜、溝通斷裂的苦果。我寫這本書,不為指責任何人,而是想為校園中的每一個靈魂―從風雨中守護孩子的老師、日夜牽掛的家長、肩負制度重擔的行政人員―提供一張清晰的法律地圖,讓我們能在同一片星空下,找到共同的北極星。這不是一本法律書,是一本希望孩子平安長大的書。
2023 年8 月23 日,是我人生的轉捩點。那天,參加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及輔導人才庫」培訓時,聽見一個個真實故事在教室迴盪:孩子的淚水、老師的無奈、家長的怒吼。這些不就是我日日面對的縮影嗎?那一刻,我明白了——有時候,最危險的不是違法,而是不知道自己正在違法;最遺憾的不是沒有愛,而是愛的方式出了錯。
於是,我創立了臉書粉專「律師帶您看校園裡的大小事」,用平凡人的語言,講述法律背後的故事。讓老師知道界線在哪裡、讓家長明白權利如何維護、讓行政人員在人情與制度間找到平衡點。粉專目前已經累積超過四萬人追蹤,每一則貼文下的熱烈迴響,都在訴說著:我們同樣渴望一個既有規範、又有溫度的校園。這股共鳴告訴我,這條路不只值得繼續走下去,更需要我們攜手同行。
守住法律的界線,才守得住教育的本心
在少子化寒冬與社會高期待的烈日下,教職早已不再是單純傳道授業的旅程。昨日的「慣例」,今日可能變成讓老師失去一切的陷阱。法律的天秤,往往比我們想像的更精準、更不留情面。但也正因如此,我更渴望讓法律有血有肉、貼近人心。
有些錯誤,老師不是故意的;有些傷害,孩子卻真的會記一輩子。
這本書,獻給每一位站在教育第一線的勇者,獻給每一顆為孩子未來而跳動的心。我們將一起探索:霸凌的真正定義是什麼?性平事件該如何妥善處理?管教與處罰的界線在哪裡?什麼是真正的程序正義?我會用故事呈現法條,讓實務解析有溫度,讓你不必穿梭法律迷宮,也能找到答案。
不是責備,是提醒;不是對立,是同行。
教育的根本永遠是愛。而法律,不該是凍結這份愛的冰霜,而是讓這份愛更穩固的地基。讓我們攜手同行,在校園中找回溫度、守住底線,一起編織每個孩子心中真正安全又溫暖的成長記憶。
願每位老師,都能安心站在講台上。
願每個孩子,都能快樂走進教室。
你守法律,我守你;我們一起守住孩子的世界。
用法律溫暖守護教育現場的每一顆心。
——2025 年6 月於高雄文化中心
1-1同學對我惡作劇,算不算霸凌?——霸凌行為的關鍵特徵
明儒是國小五年級生,有一群好朋友,經常在課間一起玩耍、打鬧,平時也會互相開玩笑、搞些小惡作劇。明儒是這群朋友中的孩子王。華敏是明儒的好朋友之一,個性較為內向,但和大家相處得也很融洽。
有一天,華敏帶來了一個他跟家人去東京旅遊買回來的庫洛米鉛筆盒。這個鉛筆盒不僅外觀亮眼,還有一些獨特的功能,比如按鈕式開關和秘密夾層。明儒看見後覺得這個鉛筆盒很有趣,便打算趁著華敏去廁所的時候,來個小惡作劇。他把鉛筆盒悄悄藏了起來,心裡想著等華敏發現鉛筆盒不見時,一定會露出驚訝的表情。
果不其然,華敏回來後發現鉛筆盒不見了,頓時驚慌失措,四處尋找,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忘了帶。看到華敏那焦急的模樣,明儒忍不住笑出了聲,從書桌下拿出鉛筆盒,笑著說:「嘿!在這裡啦! 我只是想逗你玩。」
華敏雖然有些不高興,但看到鉛筆盒完好無損地回到自己手中,也就沒有多說什麼,心裡明白這只是明儒的惡作劇。
毛律師來解惑
你認為明儒是在霸凌華敏嗎?
在學校的場域裡,像明儒這樣的惡作劇,並不罕見。對於許多學生來說,這種小惡作劇和開玩笑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們表達友誼的一種方式。
明儒只是想逗華敏,看他緊張的樣子好玩,並沒有想要真的傷害他或讓他難堪。雖然華敏一開始有點不自在,但後來發現只是朋友間的玩笑, 就不太在意了。其實,大多數孩子都能理解這種打鬧方式,不會因為這樣的玩笑而受傷害。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惡作劇都能被視為無害或是可以接受的行為。當惡作劇變得過分,或是經常針對同一個人時,它就可能會引起更深層的問題,甚至演變為霸凌。
霸凌行為的關鍵特徵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 條第1 項第6 款定義了「生對生霸凌」:即「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之間,於校園內、外發生的霸凌行為。」這一規定旨在防止學生之間因長期的言語或肢體暴力而產生的負面影響。
根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 條第1 項第4 款的規定,霸凌指的是「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進行故意的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的環境,進而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的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的進行」。
從以上法規定義來看,霸凌行為有四個關鍵特徵:
1. 持續性(非單一事件)
霸凌行為通常不是單一偶發的事件,而是具有持續性或重複發生的特徵。本案例中,當明儒發現華敏焦急,並四處找尋鉛筆盒的樣子後,就立即還給他,這樣的行為僅發生一次,沒有持續進行類似行為。
2. 故意性
在評估行為是否具有「故意性」時,不應僅依賴行為人自述的動機,而應從多方面進行客觀綜合判斷:
1受害者的感受與陳述:受害者如何解讀和感受該行為是判斷的重要依據。若受害者反覆表示感到被針對、羞辱或恐懼,即使行為人宣稱「只是開玩笑」,也應重視受害者的主觀感受。
2旁觀者的觀察與證詞:同學、老師等第三方的觀察可提供更客觀的視角。他們能描述行為發生的頻率、方式,以及受害者當時的反應和後續影響。
3行為的情境與方式:考量行為發生的背景、時機和方式。例如,若行為是在公開場合進行,使受害者當眾難堪,或是選在受害者特別脆弱的時刻,這些都可能顯示出故意性。
4 是否有權力不對等:評估行為人與受害者之間是否存在權力不對等關係(如年齡差距、社交地位高低、體型差異等)。權力不對等可能強化行為的故意性與傷害性。
5 行為模式與歷史:檢視是否有類似行為的歷史模式。重複針對同一對象的行為,即使每次都宣稱是「玩笑」,累積起來可能顯示出具有故意性的模式。透過以上多元角度的評估,能更全面客觀地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霸凌的故意性,避免單憑行為人的自我解釋或動機辯解來做決定,更能保護潛在的受害者。
在本案中,明儒確實是「故意」進行這個行為(想逗華敏),這符合霸凌中「行為故意」的要素。然而,霸凌的認定不應僅看行為人主觀動機,而應從整體情境客觀判斷:
1受害者感受:華敏雖「有些不高興」,但理解這只是惡作劇,並無持續不適。
2行為情境:明儒迅速歸還物品,未造成公開難堪或延長華敏的不安。
3權力關係:雖然明儒是「孩子王」,華敏較內向,但明儒未利用這種差異造成長期壓力。
4行為模式:這似乎是單一事件,未見針對華敏的重複行為模式。
綜合判斷,明儒的行為雖有「行為故意」,但根據客觀情境和華敏的實際反應,更符合一般同儕間的惡作劇性質。
3. 敵意或不友善環境
霸凌的核心在於讓被害人長期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的環境,例如透過貶抑、排擠、欺負或騷擾,使其在學校或社交生活中感受到壓力、孤立或恐懼。本案例中,明儒的行為並未讓華敏長期處於這種環境,雙方仍維持友誼,沒有出現社交排擠的情況。
4. 造成損害(精神、生理、財產、學習影響)
霸凌行為通常會對被害人造成具體的損害,例如:
1精神損害:焦慮、恐懼、壓力、失去自信。
2生理損害:身體傷害、健康影響。
3財產損害:物品損毀、財物被奪走。
4學習影響:成績下降、逃學、拒學。
本案例中,華敏雖然一開始感到焦急,但當他意識到這只是朋友的玩笑後,並未產生持續的精神壓力或學習適應問題,因此難以認定為霸凌。
毛律師建議你
藉由明儒和華敏的故事,我想和大家聊聊「惡作劇」和「霸凌」的差別。其實,不是所有惡作劇都是霸凌,尤其當只是一時興起的玩笑,沒有惡意也沒讓別人受到長期傷害的時候。
身為老師或家長,要怎麼分辨這兩種行為呢?霸凌會一直持續發生,而且是有意傷害別人,會讓受害的孩子在心理、課業或生活上都受到嚴重影響。如果把一般的玩笑或偶發的衝突都叫做霸凌,反而會看不清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不管大人還是小孩,動不動就說:「這是霸凌」。結果學校調查後發現不是霸凌時,家長可能會認為學校在包庇,不處理問題。此外,被說是「霸凌者」,對孩子來說也是很大的壓力,可能會影響他的心理發展。不過,如果發現孩子一直很不安、不想上學,我們當然還是要認真關心和處理。
或許學校老師和家長可以一起教孩子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如何影響別人,學會用善意和尊重的方式和同學相處。這樣既能預防霸凌,又不會讓孩子失去和朋友互動的樂趣,讓他們在快樂、安全的環境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