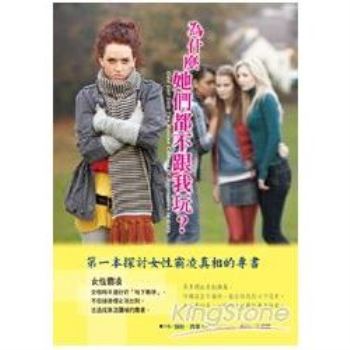第六節課快下課了,珍妮的胃隨著牆上時鐘的滴答聲而緊縮,不是因為她要快點衝出教室。其實她的功課不錯,上課也很專心,但在下課前五分鐘她就分心了,愈接近下課,她的呼吸就愈急促。她從棕色的直髮底下偷偷看著其他七年級生,珍妮慢慢收拾書包假裝很忙碌的樣子,再過一會兒她就自由了,珍妮告訴我這個故事:
兩個月前,梅森高中的某些人決定了兩件事:第一、珍妮威脅到她們的地位,第二、她們要使她的生活過得很慘。
珍妮在結束六年級課程後不久,就不情願地跟著家人搬到懷俄明州的一個小農村社區。之前在聖地牙哥時,珍妮就讀在大城市裡的學校,大部分好友是墨西哥人。她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非常喜愛溫暖的墨西哥友誼和文化,從不介意自己是少數在那邊唸書的白人。沒想到進入梅森高中後什麼都改變了,當地只有八百個白人,每個人都互相認識,在這裡,外來者並不受歡迎。即便珍妮的家人都在梅森長大,即便她以前常在暑假時和在鎮上當議員的祖父駕著拖引機逛農地,但對當地人來說,她就是個外星人。
尤其是布雅娜和麥肯琪。她們控制著整個七年級。布雅娜是學校最漂亮的女生,而麥肯琪則對運動非常在行,她們最大的嗜好是交男朋友。珍妮雖然對交男朋友不太有興趣,但是喜歡和男生混在一起,通常是在下課後和他們踢踢足球或打籃球,比起化妝和迷你裙,她比較喜歡牛仔褲和T恤。在她們罵珍妮是「賤貨」之前,她們三人幾乎不認識。她們告訴每個人,珍妮和男生在足球場後的樹林亂搞。珍妮知道,一旦被稱為「賤貨」就永無翻身之日,但她連初吻都還沒獻出去,這真是低級。
她們甚至組了個「反賤貨有限公司」(Hate Harriet the Hore Incorporated Whore),除了兩個不感興趣的人之外,幾乎每個女生都加入了。所有加入的女生必須在經過珍妮身旁時對她大叫:「HHHiiiiiiiiii」(「反賤貨有限公司」的縮寫)通常這些女生會在這麼做後相視而笑,有時甚至還沒說完就狂笑起來。
布雅娜還想出在走廊上推擠珍妮的主意。女生會在休息時間用身體撞她或碰掉她的書,甚至把她推倒在地。如果有人在旁,她們會表現得像是意外。珍妮如果反擊,只會導致一堆瘀青、作業不見,或是只能在鐘響時趕快走避。然而這一切都沒有老師看見過。
剛開始幾天,她想置之不理,但是一個星期下來滿是難堪和恐懼。她不懂自己到底做錯什麼?珍妮從未遇過這種事,在聖地牙哥時她有三個好友,她總能將每件事處理好,她相信父親的教導:「只要妳夠努力,就可以完成任何事。」這次是她第一次失敗,她覺得是自己的錯。
七年級有另外兩個和她同時轉進這所學校的女生,她們都適應得很好。她們和其他人穿同樣的衣服,聽同樣的音樂。但是珍妮喜歡穿加州式服裝和墨西哥刺繡上衣,她不想改變自己。她心想:也許父親說的對,自己不夠努力。
珍妮逐漸了解這種折磨不會有結束的一天,她開始在房裡偷偷哭泣。每天寫完作業後,她就用枕頭蒙住頭哭泣,她沒法告訴母親她被排斥,更別說是父親。
每天都是無止境的戰爭,她在走廊被攻擊時努力站穩腳步,孤獨地吃完午餐,同年級中沒人願意和她做朋友,每個人都討厭她,這讓她精疲力盡。她的表姊相當同情珍妮的處境,有時她會讓珍妮和一群最受歡迎的八年級生在一起玩,但是這麼做讓布雅娜和麥肯琪更加憤怒。終於有一晚,珍妮的悲傷超越了恐懼,她拿起電話打給布雅娜、麥肯琪和其他女生,「為何妳們那麼恨我?」她問道。但是那些女生否認一切。「那妳們為何加入反賤貨有限公司?」珍妮不放棄。
在電話中,她們的聲音響亮又甜美,每個人都說根本沒有「反賤貨有限公司」這回事,她們對珍妮的態度之好,幾乎讓珍妮相信一切都已雨過天晴。隔天早晨,她滿心期待地去上學,結果,「HHHiiiiiii」。
珍妮咬緊牙關,忍住眼淚,她居然相信了!她早該知道的!她的心碎了。布雅娜和麥肯琪在電話中聽起來是如此真誠。笨珍妮、笨珍妮,她開始喃喃自語,還幻想過跟她們一起在學校餐廳吃午餐哩!她咬著牙不斷重複,用書遮著臉跑進指導室12。
幾個月後的某一天,她在指導室的桌上找到女生們在傳的東西。她發現一張請願書上面寫著:「我,麥肯琪,發誓要永遠恨那個賤貨。」每個女生都簽了名,後面則附上一堆恨她的理由,珍妮厭惡地盯著那些文字,直到覺得有點暈眩。她實在是太生氣了,不想再忍下去,她走向校長室。
校長威廉斯先生約談了布雅娜、麥肯琪和其他女生。之後的幾個星期,她們總是瞪著珍妮,但沒說什麼。「反賤貨有限公司」正式解散。
珍妮獨自熬完國一。同學可惡的行為很難被察覺,老師並不知道這個轉學生之前的個性,也沒察覺異樣。她的父母問珍妮在學校有沒有問題,但珍妮告訴我:「我會告訴他們,『沒事!』。」
「反賤貨有限公司」沒有再度復活,珍妮在接下來的幾年適應得很好,她是壘球隊的靈魂人物,也是啦啦隊隊長。但她所受的創傷並沒有消逝,並耐心等待復仇的機會。
布雅娜後來和夏安高中最受歡迎的男生約會。「事情就是這樣,」珍妮說,「如果妳國中長得很漂亮,在離開懷俄明州之前,就會和某個特定對象約會。」「艾瑞克是籃球隊長,這是夏安高中最重要的位子。布雅娜把第一次給了他,還認為一定會跟他結婚。」
珍妮高中三年級那個秋天,機會來了。她奉命接洽男子高中籃球隊,很快地和艾瑞克成為朋友。「我一定要把艾瑞克搶過來,而我也做到了。」珍妮說,「我知道這與艾瑞克無關,但對布雅娜就不一樣了,這等於是奪走她最重要的東西。」在逼艾瑞克從珍妮的臥房打給布雅娜說要分手前,珍妮已經和他約會一個月了。
***************
我問珍妮:「妳當時感覺如何?」
「我覺得我贏了。我真想把這種感覺砸在她臉上。我很高興自己終於反擊了,狠狠地傷害她。」她說,「這是復仇,雖然很悲哀,但到今天我還是很恨那個女生,我還是會那麼做。」今年三十二歲的珍妮說。她一點都不覺得丟臉或後悔,二十年後,憤怒還在心中悶燒。
友誼就像是救生艇
乍看之下,女生的問題從不一起吃午餐到不被邀請參加聚會等不一而足,這些行為看似幼稚。但吉莉根的研究指出,女生認為生活中的危機是被孤立,特別是因太突出而被孤立;男生則是恐懼被壓迫的窒息感。這種差異,吉莉根認為可以證明「女性的依附關係、壓力來源和男性不同,女生願意改變自己,不願被取代或翻臉。感情、依附以及失落感在女性生活中也指向不同的經驗和意義。」情感是女生生活的重心,也是侵略性和霸凌中的重要角色,值得另闢專題研究。
要了解女生的衝突,就要先了解女生間的親密關係,親密和憤怒經常是一體的;女生之間的緊密程度與侵略多寡有關。在愛上男生之前,女生都很喜歡彼此。
跟男生不同,女生喜歡不受限制的親密感,社會期望女兒能學習母親的形象,卻鼓勵兒子儘早脫離母親,發展成為不情緒化的男性。女生的整個童年都在練習照顧彼此,她們從最好的朋友身上尋找親密感和依附感的喜悅。
但我們的文化長期忽視女性情誼,認為女生只應該對男生有情感,女生應該將照顧他人的能力投注在丈夫和小孩身上,超出這個範圍的情感都是不重要的。
女生間彼此的關係,以及她們投入同性的情誼和侵略性相關的程度,是門深奧的學問。最難承受的就是至交好友用妳所分享的祕密及弱點來攻擊妳。
尤有甚者,交情是女生用來威脅對方的武器。社會慣於對侵略性避而不談,一味認為女生都應該溫柔可人,造成女生無法處理衝突,一點小爭議就會懷疑這段友誼。
這意味著什麼?在正常的衝突之中,雙方會用言語、聲調甚至拳頭來捍衛自己的立場,再來才是修復感情。但如果其中一人不知衝突的來源,就無法說出憤怒,當然也找不到處理衝突的方法。如果每個女生都想當好人,這樣的關係就會成為問題;當無法處理衝突時,交情自然會成為一種武器。
既然人緣的好壞可以定義一個女生,所以「孤立」似乎是個隱藏的利器。在訪談成人時,安.坎培爾發現男性視侵略性為控制環境的手段,然而女性卻認為這會破壞人際關係。在和女生的訪談中,我也發現相同的情形,女生甚至會因為害怕失去自己在意的人而處處小心翼翼,別說顯現出主見,連稍微會引起衝突的話題都不敢提。這個等式很簡單:衝突=失去。
週而復始,女生們接二連三告訴我:「如果說出我真正的感受,她們就不會再和我做朋友了。」結論就是:「我不想傷害任何人,我想當每個人的朋友。」
害怕被孤立的恐懼實在太強大了,大多數遭到霸凌的女性大部分的回憶都是寂寞。雖然各種低俗的電子郵件和匿名紙條、謠言、在桌上牆上亂寫都很殘酷,但最大傷害其實是在背後被說壞話的那種孤寂,這種悲痛和恐懼幾乎會毀了一個女生。(待續)
為了避免被孤立,女生寧可繼續被詆毀也要維繫彼此的關係。
我曾問過一個六年級女生為何還要維持與壞朋友的友誼,她這麼回答:「誰想要休息時間孤單一人?有祕密也沒人可說?」一個高二生哀怨地說:「沒有同伴的母獅會很快死掉,牠們必須過群體生活。」
當女生長大後,孤獨更是令人沮喪。她們認為所謂的好女生就應該人緣好。「走在走廊上,感覺每個人都瞪著妳,那很慘的。」一個林登高三年學生說,「孤單超慘的,沒人想那樣。大家會認為她一定有問題,孤單是我們最大的恐懼。」因為害怕被孤立,所以求學時期,友誼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救生艇,每個女生都想要爬上去。
不論男生或女生,每個孩子都希望被人接納,大部分的男生不想當獨行俠。但是當女生長大,友誼就像空氣般重要。「我很沮喪,」莎菈說,「我孤單地坐在教室,覺得世界崩潰了。」另一位五年級生形容孤獨的感覺,「心都碎了。」
真的只是過程而已嗎?
雪莉十三歲時,她的朋友突然都不跟她說話了。她的爸爸因為擔心女兒被欺負,轉而詢問女兒朋友的媽媽,那個媽媽冷漠地說:「女生就是這樣嘛!你小題大做了,你在擔心什麼?」
這位媽媽的對女生霸凌的說詞很具代表性:這是一種必經的過程,會讓她們成長。有位學校輔導員對我說:「我們沒法做什麼,以前是這樣,以後也是這樣。」多數人相信隱性霸凌就像暴風的形成,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就是這樣的想法造成女生現今的行為,更重要的是,這種想法阻礙了對女生霸凌的處理對策的發展。
這種理論有幾個假設:第一,對於這種情形我們無能為力,因為這是蛻變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因為許多女生都有這類經驗,所以她們知道如何處理。這個理論甚至認為隱性霸凌是必要且正面的,會讓女生學習處理人際關係。第二,這意味著在未來的生命中,女生也該學得如何維持關係。成熟女人都做得很好,因此這個過程可以被接受。(在訪談中,許多絕望的母親和一些不太在意隱性霸凌的女性認為,女兒只是在經歷人生必經的歷程。)第三,認為隱性霸凌舉世皆然,所以女生間的可惡行為不過是社會結構的一環,是可以忍受的。結論就是:女生以這種方式互動,所以根本不算是霸凌。
然而學校以不干涉女生的人際關係為由,對女生的人緣做出下列兩種價值判斷:第一,不像那些訴諸法律或出現在晚間新聞的暴力行為,發生在女生間的霸凌並不重要,只要開始對男生有興趣,這些問題就會消失了。
第二,有些學校將童年視為一種生命課題,而非生命本身,這種不干涉政策拒絕正視女生問題的情感,無法直指問題核心。
學校也會因為必須維持課堂秩序而忽視女生的隱性攻擊。老師總在和時間賽跑,他們要完成授課進度、做好行政工作、常態的考試,還要找時間辦生日宴會。較能感受大人壓力的女生知道傳紙條或用眼神傷人,比較不會引起精疲力盡的老師注意。即便老師看見了,也不見得會花時間處理。比起斥責不聽話的男生,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會花更多的精力。
學校對於隱性霸凌缺乏應對之道。在缺少對隱性霸凌的定義下,政策多只針對看得見的肢體暴力,即使展現出來,對公眾而言也稱不上是社會問題。(待續)
被排擠很容易被誤認為缺乏社交技巧
多數學校認為,「如果你不這樣做,就不是我的朋友」這類威脅被稱為同儕壓力,而非人際上的侵略。學術研究則視女生對人際關係的操縱為早熟或「為了在團體中建立領導地位,以界定團體的領域」。也有些心理學家認為,捉弄和齷齪的玩笑是成長過程中的正常經驗,他們視散播謠言和八卦是為了鞏固團體。
除此之外,校方常會覺得是那些小孩有問題,否則不會被欺負。學校將責任往受害者身上推,認為她應該學習正確的社交技巧,包括聽懂別人的意思、更注意穿著,或是她因為太渴求友誼而笨拙的說:「我們當朋友好嗎?」而不是有技巧地說:「週末一起去逛街吧!」
被排擠很容易被誤認為缺乏社交技巧。如果一個形象良好的女生突然變得殘酷、佔有慾強或反應過度,這些行為會被解釋成還沒穩定。這問題很弔詭,大家反而是勸受害者要有同情心,或是多給對方一些尊重;加害者被認為是一時迷失,被害者的感受卻被忽略。
在大部分的情形中,大人們不認為受害者受到的折磨是傷害,這是因為加害者通常是受害者的朋友。在本書第二章就有一例,珊曼莎曾是安妮的朋友,也曾讓安妮整晚哭泣,「現在珊曼莎有許多朋友,她的人緣也更好了。」安妮解釋道,「但那時做為她的朋友只要講錯一點話,她就會認為那是很大的侮辱。我不敢跟珊曼莎講那樣想是不對的,她用自己的方式去交朋友。」為了當珊曼莎的好朋友,安妮表現出同情,卻隱藏起自己的痛苦。
把霸凌和社交技巧畫上等號,使女生不計代價要有好人緣。人緣好就意味著良好的互動,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就會被認為是有教養的女生。大多數的女性霸凌都會有個主導者,她會維持表面不著痕跡,但是暗地裡進行欺負,還能製造團體共識。
學校重視學生的人際關係,等於是幫了女性霸凌的忙。為了維持或得到好人緣,女生被迫和內心的侵略性拔河;當人緣好的女生無法控制憤怒時,一下是天使一下又是魔鬼時,這很容易讓同儕感到困惑,朋友間常要猜測彼此真正的心意,長久下來,她們就不再相信朋友說的表面話。
隱藏的憤怒不僅形式各異,被認知的方式也不同。一閃而過的憤怒,常讓受害者疑惑這會不會是自己的錯覺?當我那麼說時她在看我嗎?她在開玩笑嗎?她是否在使眼色?故意佔著那個位子?故意騙我?說她有邀請我,其實並沒有?
當我們描繪出隱性霸凌各種公開或隱藏的方法時,女生會產生對抗的力量。我們必須在當下馬上指出,讓事情發生的當時,女生不再認為那是她們的錯。
家長和老師該如何面對
想為孩子討回公道的家長都會遇到阻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社會不認為隱性霸凌是問題,而且大多數的學校都會掩蓋問題,或歸罪於受害者。
蘇珊娜被六歲女兒的老師緊急找去學校,她覺得很不舒服。蘇珊娜站在緊閉的教室門前,準備討論女兒被同學霸凌的事,「如果我指控那些孩子很會操縱人、鬥爭心強又狡猾,會讓我覺得自己像個瘋子!」她說。
這個社會對隱性霸凌毫無概念,會有這種反應是正常的。家長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也會和自己的小孩同樣心煩意亂,因為缺乏恰當的語言,他們只好用「騙子」、「狡猾」或「操縱」這類很重的字眼來形容孩子間的霸凌。孩子害怕坦承所帶來的友誼問題,而家長則害怕被學校認為「歇斯底里」或「反應過度」。除此之外,家長也擔心自己的錯誤行為造成孩子傷害。
在這一章,我主要想呈現家長向老師說明孩子被欺負的經驗。在華盛頓的咖啡廳裡,我和四位經常見面的母親聊天,請她們解釋這種心態。艾倫說:「身為家長,妳很清楚老師對孩子的影響是很大的,妳不想害別人的小孩。」她的朋友點頭同意。克莉斯汀娜這麼表示:「擔心老師會因別的家長講的話,而對別人的小孩產生偏見。」向老師抱怨隱性霸凌,很容易被誤會成過度反應,每個母親都害怕變成教室裡最「歇斯底里的媽媽」,她們一定要保持冷靜。(待續)
我該不該替孩子調解?
在處理孩子問題中,在學校被霸凌可能是最讓家長頭痛的:我該不該替孩子調解?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孩子準備好面對問題了嗎?夠成熟解決麻煩嗎?而這些答案又經常與家長及校方的反應有關。對方家長會反駁嗎?學校會負起責任嗎,還是反而會處罰孩子?老師很繁忙,又經常找不到。
想為孩子討回公道的家長都會遇到阻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社會不認為隱性霸凌是問題,而且大多數的學校都會掩蓋問題,或歸罪於受害者。許多家長表示,雖然問題不出在自己女兒身上,但最後都會被送到心理諮詢室接受治療,且被認定為需要加強人際關係,但事實上,需要接受治療的應該是欺負者。還有一種常見的情形是欺負者否認,結果演變成各說各話的局面。最後許多家長寧願保持沉默。
家長覺得羞恥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發現女兒人際關係有問題常令家長難過,即使問題不在女兒也一樣。每個家庭處理的方式都不同,對琳達來說,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她覺得既羞恥又荒謬,「這好像很小題大做,我從未有過這種經驗,甚至很難啟齒,但我又覺得這件事很重要。我沒跟女兒談過這件事,我滿腦子都是『我的小孩不受歡迎,她不是很棒的嗎?』。雖然我不是只想要她很棒,但我還是希望我的孩子是最好的。」蘇珊娜也是鼓起勇氣才能說出事情的始末,「我偷偷地想著,也許有人會質問我,為何漢娜不自己說?為何妳不教導她要為自己爭取權益?為何她會讓這一切發生?」雖然遇到這種事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但當社會不認為這是問題時,這會更讓人羞愧。
家長很清楚,事情一開始就很棘手
如果孩子有學習上的問題,通常有專家幫忙解決,如果家長不放心,還可以翻書、跟專家討論,家長會盡可能地提供各式幫助,讓孩子可以表現得更好。但是,當孩子成為隱性霸凌的目標時,沒有人可以幫助她們,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孩子所承受的痛苦,家長很清楚,事情一開始就很棘手。「如果我過度強調她的人際關係,老師就會說:『怎麼啦!妳的孩子無法處處理自己的問題?為何她不能自己解決?』我覺得很難堪,所以不敢說出自己的感覺。」蘇珊娜說。
沉默是家庭一貫逃避問題的方式,然而這方式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我們常常將孩子的困難怪罪家長,而中產階級家庭更是將孩子的人際關係、情感和學習問題列為最高機密,更不談論心理上的痛苦。某個母親不想將孩子遇到的問題說出來,「我害怕大家會因為孩子不夠完美而質疑母親,說我過度保護或不夠保護她。」這位母親說。
家長會盡其所能地誇耀自己的孩子,以塑造快樂和諧的家庭形象,她們會舉辦炫麗的生日宴會,送禮物給大家,但就是沒辦法分擔孩子被欺負的痛苦。瑪格麗特說:「如果我告訴別人,她們會不會傳出去?還有多少人會知道?最後會變成怎樣?我不想聽到別人說:『喔!她們家有問題。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我們過得很好。』」蘇珊娜曾經聯合其他家長,成功地要求學校增加藝術課程,但是當我建議她組織團體解決隱性霸凌的問題時,她苦笑著說:「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四十一歲的母親蘇珊娜表示,在瑞吉沃這個小鎮,一件小事都會變成茶餘飯後的話題。她在知道孩子被好友欺負後,就不跟鎮上的人往來,她壓抑自己想站出來的衝動,把苦往肚子裡吞,也拒絕接受我的建議,只是感到絕望。「這個鎮很八卦,她們一早起床就想知道誰離婚了,或誰跟誰上床,這就是鎮上一直以來的生活方式。」她激動地說,「我不斷要求女兒自己解決問題,希望她是獨立的女性。我一直欺騙自己事情沒那麼糟,不想把事情想得那麼糟,但它就是那麼糟。」
研究者在討論校園暴力時,通常很少提及家長,我們的焦點都集中在加害者、受害者和沉默的同儕,電視或電影在討論校園暴力時也常將焦點錯置。然而,做得太多、太遲或什麼都不做的家長,才是左右這場災難的結局的關鍵。
本章會呈現五位母親的經驗,如同當事者,每位家長都有自己的想法。這些案例說明家長對孩子的行動有多大的影響,也說明了文化對女性侵略的沉默和忽視,如何影響家長的反應。(待續)
除了指責女兒,她什麼忙也幫不上
派翠西亞在瑞吉沃開了一家托兒所。某天傍晚我去拜訪她,那天她穿著長袖T恤和皺皺的卡其褲,身材高大壯碩。她看著草坪上獨自玩耍的孩子,聲音出奇地溫和低沉。數年前,她先生班受聘為藥師時,他們帶著女兒搬到小鎮來,但鎮上的人還是跟他們不熟,當時女兒霍普小學三年級還沒唸完,派翠西亞開始說:
寒假結束後,霍普開始上學。她的加入讓同學們驚訝、懷疑,視她為威脅,從此展開被欺負的命運。霍普雖知道是因為外地人的身分才被刁難,可是時間一久她就開始責怪自己。五年級時,霍普加入主日學校唱詩班,班長卻叫她去別的地方或是批評她的長相或穿著。媽媽派翠西亞問霍普為何還要跟她們當朋友,她說她們都上同一個教堂,這樣比較好。
六年級的某天,那群人跟霍普說不想再跟她當朋友了,之後的幾個星期,她們都無視霍普的存在。「她就這樣被拋棄了,每天她都會哭著回家,不斷問我:『她們不喜歡我,不想再跟我做朋友了,我應該怎麼辦?為何她們不喜歡我?我做了什麼?為何她們不想跟我做朋友?』換做妳是我,妳會怎麼回答?」派翠西亞的眼裡充滿淚水。
**********
「那妳怎麼做?」我問她。
「那段時期時非常情緒化。」她清了清喉嚨,身體向後傾,伸直長腿,「我確定這和她成長有關,她的初經來了,所有的情緒也跟著來了。」我懷疑派翠西亞其實並不知道孩子痛苦的原因,所以才會認為那是「正常」發展的一部分。
「我問她們都怎麼批評她?霍普自己是不是該調整什麼?」霍普說了幾種可能性,但無法解決問題。我問派翠西亞,她是否覺得霍普應該做些改變?「霍普非常活潑,」但她的語氣聽起來像是在道歉,「還有點迷糊有點笨,我不太知道怎麼形容她的個性,但我覺得她有可能會惹別人生氣,可能真的惹火她們了,讓人家厭煩了。霍普覺得自己應該冷靜點,不要那麼活潑,少說點話。」派翠西亞沒說霍普有多痛苦,除了指責女兒,她什麼忙也幫不上。派翠西亞希望霍普去交其他朋友,但她拒絕了,因為她只有那群朋友。
怕激怒其他家長,覺得她會偏袒自己的小孩
派翠西亞想叫女兒禱告來減輕痛苦,「雖然現在很艱辛,上帝要妳經歷這些,是要為了要妳得到更好的生活,雖然妳可能不會在今天或明天就看到。」她停頓一會兒說,「我控制自己不要哭。」我們安靜地坐著。「我問那些女生說:『妳知道妳們在做什麼嗎?』我想去跟她們的媽媽說,但是,我又會想這會不會只是霍普的一面之詞,我相信霍普不會騙我,但妳的孩子可能做錯事啊。如果我早知道霍普這樣痛苦沮喪,身心都受創,我也許會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但我比較覺得這是生活的一部分,妳必須學會應付對妳不公平的事。」派翠西亞以社會對隱性霸凌的看法以及家長特有的育兒哲學來解釋這件事,即使她坐在我面前流淚,她還是懷疑自己的話。
我問她有什麼不同的方式。她說:「我希望去找那些孩子的母親,和她們坐下來,在咖啡廳好好聊聊。我會用很溫和的方式,不會讓她們覺得我認為我女兒比較好。如果我當時那麼做了,結果可能會好一點。」她嘆了口氣。
派翠西亞因為怕激怒其他家長,覺得她會偏袒自己的小孩,所以合理化霍普的折磨。大多數我訪談過的母親,都有這個問題。她們都有兩條養育守則:第一條,家長不想要別人告訴他們如何教育孩子:第二條,批評別人的孩子是不智的。許多家長認為,自己的孩子被批評就等於自己的養育方式被批評,他們有時會因此生氣,大多數受害者的家長都說他們不會這樣做。
去警告對方的孩子,反而讓孩子遭受到二度隱性霸凌
事實上,母親比父親更害怕面對這種衝突,住在小鎮的家庭又比住在城市者更甚。母親們可能一起工作、自願到學校或教堂幫忙,她們經常碰面,甚至是朋友。父親也許是處理這種事的較佳人選,但是無論如何,找對方家長談就會在孩子的圈子裡引發震盪。
有時,因為母親去警告對方的孩子,反而讓孩子遭受到二度隱性霸凌。家長乍聽孩子被欺負,通常會本能地保護孩子而去指責對方;由於沒有確切的證據,對方會全盤否認,這反倒讓擔驚受怕的母親更加無理可說,也成為被霸凌的對象。
因為處理吉兒被霸凌的事件,讓吉兒的母親菲雅想起高中時她最好的朋友也突然不理她。吉兒的受害,證實了菲雅的看法,惡劣的女生很多,難以避免。吉兒自從被好友孤立,行為就出現很大的轉變,菲雅告訴我,「吉兒曾經是最快樂的女生,無憂無慮。」一年級時,漸漸變得害羞起來,自從幼稚園第一個好友嫌她常說錯話而不理她後,她就愈來愈沒自尊心。現在吉兒五年級了,她的新朋友只在私底下對她好,菲雅也不打算干涉,因為她覺得這是常態。
這會影響她一輩子……
這一次,欺負女兒的人是菲雅好友的小孩,那個母親強勢人脈又廣,她的小孩因此交很多朋友。「我們討論過孩子的交友情形,但我又不能跟她說,妳的小孩很壞。」吉兒也不是第一次和朋友有問題,而菲雅相信,因為吉兒常被欺負才會缺乏自尊,「如果妳覺得自己不夠好,那麼其他人也會這樣覺得,然後她們就不會喜歡妳,沒有人會喜歡妳。」我問她是否跟學校談過女兒的困境,她困窘地回答:「其他母親可能會打電話給對方的母親,問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我沒有。現在,我不斷問自己:『我應該打電話嗎?我應該查清楚發生什麼事嗎?』畢竟我媽從未幫我做過什麼,她還有其他事情要忙,這對她來說是個不重要的問題,甚至根本不是問題。妳看,如果把問題分成一到十個等級,比起有人死於癌症,這真的不是大問題。孩子會長大,她會交到好朋友,她會沒事的。」
講完這番忽視女兒痛苦的話後,她停了幾分鐘,絕望地只說了句:「但這會影響她一輩子,我們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