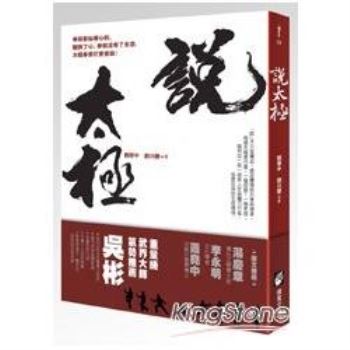第四章 武林就在身邊(摘)
由文入武的老記者——楊氏太極拳第六代傳人何華雲
二十年的辦報經歷,當過報社印刷廠揀字員、記者、編輯、總編室主任。本是地地道道的文人,卻因為一次偶然的音樂為媒,一頭栽進太極拳的武學懷抱,臨到如今退休,成了專業的太極拳傳播者。
這就是楊氏太極拳第六代傳人何華雲,丹道與內家拳大師張義尚的親傳弟子,一個執著的內家拳理論與實踐的佈道人。
六十多歲的何華雲,走起路來,腳步輕盈,臉上帶著和善的笑容,內斂而飽滿。和他搭手,感覺手如扶柳,空空如也,身子也處處不得力,如臨深淵,東倒西歪,真是動也不對,不動也不對,前進也錯,後退也錯,隨時有被打翻在地的危險。
二○○九年七月在重慶渝北黃泥塝,有緣聽何老師將自己的太極拳學藝經歷,以及對太極的精到理解,娓娓道來。
武術奇緣:初識太極為音樂
常言道: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練武。許多武林高人都是因為幼年身體不好,為了治病走進武術大道。
何華雲練武卻是個例外,竟然是音樂為媒。
何華雲在六○年代末就任職於四川《萬縣日報》(今重慶市《萬州日報》),做文字工作。精益求精地錘煉文字,寫出好文章是何華雲的理想,業餘時間他只是喜歡拉二胡,絕對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迷戀上內家拳。
他有個同事是重慶著名的小提琴師張義敬的表弟,見何華雲喜歡音樂,就說起願意介紹他到重慶學習小提琴。一九七一年何華雲請假一個月,順著長江而上,到了重慶。在山城七星崗附近,遠道而來的何華雲虔誠地坐在首席小提琴手張義敬的小屋子裡,聽著新疆之春、西藏音詩、漁舟唱晚等經典曲子從張老師的指尖流出,他如癡如醉。
何華雲表達了要拜師學小提琴的意願。張義敬並未答應他:「你二十四歲了,學小提琴不會有更大的成就,只可能是個業餘愛好,而說到業餘愛好,我建議你學另一個可以受用終身的東西——太極拳。」
「太極?」何華雲很是疑惑,不知張老師為什麼會突然提出這個令他意外的東西。
「這樣吧,我就站在床邊,你能將我推到床上去坐著,就可以放棄學太極。」張老師叫血氣方剛的何華雲上前。何華雲告訴筆者,當時他很不信邪,一下就衝上去,準備將身材高的張老師推到床上,他覺得這是十拿九穩的事情。沒想到,手還沒伸到張老師身體,自己就莫名其妙地騰空飛出,倒在虛掩的門上。
以為是自己沒準備好,何華雲又不服輸地上前試了幾次,每次都是一樣的結果,莫名其妙挨打,什麼也沒看清楚。
「我就學這個!」何華雲告訴張義敬老師。
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他每天和張老師到枇杷山公園練拳,聽到張老師講他的師父李雅軒宗師的故事,講太極拳的奇妙之處。何華雲堅定了信念,要堅持把太極拳學下去。
隱居的「國寶級」高人
從萬縣到重慶搭船要一天一夜,在接下來的六年時間,何華雲堅持每半年到重慶拜見張老師一次,每次都要請假幾天才行。
張義敬見他刻苦且悟性甚高,有一天終於告訴何華雲:「重慶太遠,你上來一次不容易,我寫封信,你去忠縣找我哥張義尚,他的功夫在我之上。」
一位資深的傳播界人士說,張義尚如果健在,應是「國寶級」人物。
張義尚,一九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於四川忠縣(今重慶市忠縣),別名虛一,號悟通居士,瑩陽子;晚年號惜陰居士、知非子。用張義尚先生遺作《養生蠡測》一書中海印子的話來說:觀師(張義尚)一生,於道、佛、密、醫、術、武、文學等,無不參究。陳兵老師(現任四川大學宗教學博士生導師)也說:「集國粹於一身,可謂國寶。其所知之廣,鑽研之深,為數百年來所罕見,當世蓋無堪與比肩者。」誠不謬之言。二十世紀以來,孜孜於道者非道即密,而曉道者未必知密,知密者未必探道,道密皆知者又未必全得真傳,得傳者又未必契證;金剛拳與太極金家也是如此,尚師一身而兼俱,實屬罕見。
何華雲說,張義尚出生當地大地主家庭,幼年受到很好的教育,曾就讀於民國時期的復旦大學,跟隨鄭曼青、李雅軒等人學太極拳。特別是李雅軒,讓張義尚在晚年感慨說道:「太極拳是武學的最精華拳種之一。」
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張義尚忝居小鎮,為人低調,家中六個孩子,負擔很重。除了看病,回家還有繁重的耕田、種地等農活,沒有人知道張義尚是一個修煉金家與形意、內丹外丹、醫藥匯宗、東派西派、悟真諸家、道密武功的大師。
靠著張義尚親弟弟張義敬的一封信,何華雲被接納為弟子。在此之前,張義尚已關門不授徒多年。張義尚看了何華雲所學後說:「太極是雅人做雅事,你是記者,性情又溫和,沒有人比你更適合習這種拳術的了。就學太極拳吧。」
學武甘苦:和水牛同車去尋師
何華雲回憶起自己的學藝過程,點點滴滴仍記憶猶新。
從萬州到汝溪,班車很少,有時為了省錢,就搭乘貨車。有一次,在朋友的幫助下,何華雲搭上了一輛載著水牛的大貨車。車子的大貨廂內五頭牛並排站著,後面用幾根大木棍攔住,留下一個小小的空間,何華雲就站在這裡。
鄉間山路崎嶇顛簸,每次上坡時,牛就站不穩往後退,何華雲唯恐水牛沉重的蹄子踩了自己,緊緊地抓住車廂扶把,膽戰心驚。
這些都沒能擋住何華雲學藝的步伐,他照例兩個月從萬州去一趟汝溪。每次到來,都要等師父忙完工作,往往是夜深人靜時,才有機會向老師請教太極拳的問題。他隨身攜帶一個筆記本,將自己回家練拳的困惑寫在上面,一個個向老師請教。
「老師和我的感情,情同父子。」何華雲說起老師,眉宇間透出深深的懷念。
何華雲二○○七年曾去給過世六年的張義尚師父掃墓,回來後,寫了篇文章〈汝溪寄情〉。一個傳統武術的徒弟對師父的濃濃情誼,流淌在文字之中,感人至深。
不思量,自難忘。師父仙逝已六年多了,今年春節前夕,我與數同好來到重慶市忠縣汝溪鎮九亭鄉憑弔師尊,但見落葉孤塚,山冷草黃,一片蕭瑟,心中不免萬分感慨。
……那時師還隱居在九亭鄉他家祖居的一個寨子裡,這寨子位於汝溪鎮旁一突兀的山峰上,晴則綠樹掩映,陰則雲遮霧繞,走進寨門方見巨石嵯峨,高牆壁壘,十分險峻,是他家當年躲避兵匪襲擾的地方。寨後有一塊平壩,青石鋪地,四周茂林修竹、古樹橫斜、野草山花、鳥鳴蟲吟,加之石凳石桌 石盆石洞,頗有幾分仙家之氣。師就在這塊空地上糾正我的拳架,並手把手地講解太極拳技擊要領,每次都直至師母一聲「吃飯了!」我們才罷手,穿過那扇石質的寨後門,圍坐在一張已不見顏色的木桌旁,舉手抓紅苕棒兒。
……我與他過手,他輕輕一籠即止,我自知無出路時他便放手,只在教我發勁時動了幾次真,如電光火石地一閃,我就像呆子一樣站在那裡,似乎心子已被打掉了。
何華雲說,從一九七七年到師父去世,他跟張義尚老師主要學習太極拳。後來師父在八○年代後招了幾個學其他拳種的徒弟,他只是偶爾從其他師兄弟處側面瞭解一些關於金家功夫(心意六合拳一支)、八卦掌。
很遺憾沒能學到師父的丹道、中醫等絕學。一個國寶級人物的離世,帶走了很多不可複製的瑰寶。這又豈止是何華雲一個人的感慨!
內家奧祕:太極拳不是玄學,是科學
太極拳技擊的核心原理,就是破壞對方的「重心」。
何華雲說,太極技擊,就是盡力維護自己的平衡,守住重心,同時透過剛柔、輕重、虛實、快慢等手法去破壞對方的重心。只要對方的重心被掌控,就穩操勝券。而不要被對方控制重心,用力不行,用招不行,反抗不行,逃跑不行,只能隨對方的意圖。要隨勁力的方向、大小,及時調整自己的重心,維護平衡,並同時體察及感知對方的重心,以順勢反控制。
現在練太極拳的部分拳家,動輒說得很玄,氣啊、大周天、小周天的,對太極拳沒什麼好處。「太極拳不是玄學,是科學。」何華雲說。
為什麼是科學,何華雲說:「太極拳技擊,就是破壞對方重心,符合力學原理。」他又說:「太極拳推手中有兩種平衡值得重視:一種是拱橋平衡,兩人一搭手,黏住就容易形成依托平衡——拱橋原理。另一種是隨遇平衡,人隨時只有一個點與地面接觸,不會形成雙重,也能自由轉換重心。」他說,球在地面旋轉就是隨意平衡,因而我們不能說球倒了,只能說球滾了。球要在地面滾動,與地面的接觸只能有一個點,否則就動不了或者不是球。太極拳要求不犯雙重,即盡量少用雙腳同時扎地,其目的就在於此。
聽完理論,和何老師搭手,感覺其腳下確只有一個點觸地,陰陽轉換特別隱蔽。
何老師說:「太極拳同樣也是一個熟能生巧的學問。並不神祕。然而其修煉過程中,卻需要師父的口傳身授,親自讓徒弟在身上感悟,才能取得進步。」
武學比喻:意是燈光,不是手電筒
何華雲說:「太極拳的修煉不缺乏拳論,因為網際網路的崛起,無論多麼保守的拳論,都已暴露無遺。缺的是對拳論的真切理解,並能將這個理解用現實的話準確表達與演示出來,讓人能夠在身體上領悟。太極拳論有:在力則僵,在氣則滯,在意則活之說。」
何華雲強調意,他回憶自己師父張義尚曾打譬喻說:意就像屋頂的燈光,可以照在屋子的每一處,不像手電筒的光,只能照出一束光,照到一部分地方。
就筆者對練習內家拳的認識,這樣的譬喻對於練拳者的幫助,有時會勝過刻板的描述與講解。
何華雲說:「不管是對於初學者,還是多年修煉者,一個『鬆』字永無止境。而鬆又以肩鬆最難。只有鬆做好了,才能將對方的來力傳導到足底——根。」
他拿導電性做比喻,銀的傳導性最好,其次是銅,再來是鋁,再是鐵,而電阻越小的,傳導性越好,硬度越小。銀,無疑是「鬆」得最好的。
說到身體在競技中的狀態時,何華雲用象棋來做比喻:「頭是帥,兩肩是士,雙肘是象,兩手是車,胯是馬,膝是砲,腳是卒子。推手時,腳是不能退的,就和象棋的卒子一樣。」
筆者感嘆自己最近修煉太極拳進入瓶頸,難以突破。何華雲解讀說:「這就像進入了一個物質形態轉換的臨界點,比如說,冰塊加熱變成水,雖然一部分已經融化了,但溫度還是攝氏○度,一定要等全部變成水後加熱一陣子,溫度才會上升。」
每個人做事都有自己的臨界點,在臨界點不要因為溫度不變,就否定加溫的作用。太極拳的練習,也是一樣的道理。
專業拳師必須更看重養生
由文入武算起來已近四十年,何華雲現在長期在重慶萬州、四川成都、北京等地雲遊授徒。他笑言自己過的是專業拳師的生活。
在他的徒弟中,三分之二都是因為身體不好前來拜師習拳,總是各有收穫。從何老師的面容已不容置疑太極拳的養生功效,看著自己以前的部分同事退休後,或沉迷於麻將,或因為地位變化而心態不佳,患病去世,何華雲欷歔不已。
一位愛徒的孩子,考上大學不久就休學回到老家,因為極度的封閉和抑鬱,影響到了身體健康,走幾步路就會嘔吐。孩子有了厭世情緒,覺得活不下去了。在嘗試過各種藥物及看過幾個心理醫生後還是不見效,後來就讓孩子學打太極拳。
最初打拳,孩子需要人攙扶才能到達拳場,經過一段時間的鍛鍊,孩子身體上的不適消失了,面色從慘白到紅潤,性格也開朗許多。幾個月後,就重返大學校園。這位愛徒事後感觸良多地告訴何華雲:「師父,你救了我們兩代人啊。」
(未完 後續詳情請見書內文)
由文入武的老記者——楊氏太極拳第六代傳人何華雲
二十年的辦報經歷,當過報社印刷廠揀字員、記者、編輯、總編室主任。本是地地道道的文人,卻因為一次偶然的音樂為媒,一頭栽進太極拳的武學懷抱,臨到如今退休,成了專業的太極拳傳播者。
這就是楊氏太極拳第六代傳人何華雲,丹道與內家拳大師張義尚的親傳弟子,一個執著的內家拳理論與實踐的佈道人。
六十多歲的何華雲,走起路來,腳步輕盈,臉上帶著和善的笑容,內斂而飽滿。和他搭手,感覺手如扶柳,空空如也,身子也處處不得力,如臨深淵,東倒西歪,真是動也不對,不動也不對,前進也錯,後退也錯,隨時有被打翻在地的危險。
二○○九年七月在重慶渝北黃泥塝,有緣聽何老師將自己的太極拳學藝經歷,以及對太極的精到理解,娓娓道來。
武術奇緣:初識太極為音樂
常言道: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練武。許多武林高人都是因為幼年身體不好,為了治病走進武術大道。
何華雲練武卻是個例外,竟然是音樂為媒。
何華雲在六○年代末就任職於四川《萬縣日報》(今重慶市《萬州日報》),做文字工作。精益求精地錘煉文字,寫出好文章是何華雲的理想,業餘時間他只是喜歡拉二胡,絕對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迷戀上內家拳。
他有個同事是重慶著名的小提琴師張義敬的表弟,見何華雲喜歡音樂,就說起願意介紹他到重慶學習小提琴。一九七一年何華雲請假一個月,順著長江而上,到了重慶。在山城七星崗附近,遠道而來的何華雲虔誠地坐在首席小提琴手張義敬的小屋子裡,聽著新疆之春、西藏音詩、漁舟唱晚等經典曲子從張老師的指尖流出,他如癡如醉。
何華雲表達了要拜師學小提琴的意願。張義敬並未答應他:「你二十四歲了,學小提琴不會有更大的成就,只可能是個業餘愛好,而說到業餘愛好,我建議你學另一個可以受用終身的東西——太極拳。」
「太極?」何華雲很是疑惑,不知張老師為什麼會突然提出這個令他意外的東西。
「這樣吧,我就站在床邊,你能將我推到床上去坐著,就可以放棄學太極。」張老師叫血氣方剛的何華雲上前。何華雲告訴筆者,當時他很不信邪,一下就衝上去,準備將身材高的張老師推到床上,他覺得這是十拿九穩的事情。沒想到,手還沒伸到張老師身體,自己就莫名其妙地騰空飛出,倒在虛掩的門上。
以為是自己沒準備好,何華雲又不服輸地上前試了幾次,每次都是一樣的結果,莫名其妙挨打,什麼也沒看清楚。
「我就學這個!」何華雲告訴張義敬老師。
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他每天和張老師到枇杷山公園練拳,聽到張老師講他的師父李雅軒宗師的故事,講太極拳的奇妙之處。何華雲堅定了信念,要堅持把太極拳學下去。
隱居的「國寶級」高人
從萬縣到重慶搭船要一天一夜,在接下來的六年時間,何華雲堅持每半年到重慶拜見張老師一次,每次都要請假幾天才行。
張義敬見他刻苦且悟性甚高,有一天終於告訴何華雲:「重慶太遠,你上來一次不容易,我寫封信,你去忠縣找我哥張義尚,他的功夫在我之上。」
一位資深的傳播界人士說,張義尚如果健在,應是「國寶級」人物。
張義尚,一九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於四川忠縣(今重慶市忠縣),別名虛一,號悟通居士,瑩陽子;晚年號惜陰居士、知非子。用張義尚先生遺作《養生蠡測》一書中海印子的話來說:觀師(張義尚)一生,於道、佛、密、醫、術、武、文學等,無不參究。陳兵老師(現任四川大學宗教學博士生導師)也說:「集國粹於一身,可謂國寶。其所知之廣,鑽研之深,為數百年來所罕見,當世蓋無堪與比肩者。」誠不謬之言。二十世紀以來,孜孜於道者非道即密,而曉道者未必知密,知密者未必探道,道密皆知者又未必全得真傳,得傳者又未必契證;金剛拳與太極金家也是如此,尚師一身而兼俱,實屬罕見。
何華雲說,張義尚出生當地大地主家庭,幼年受到很好的教育,曾就讀於民國時期的復旦大學,跟隨鄭曼青、李雅軒等人學太極拳。特別是李雅軒,讓張義尚在晚年感慨說道:「太極拳是武學的最精華拳種之一。」
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張義尚忝居小鎮,為人低調,家中六個孩子,負擔很重。除了看病,回家還有繁重的耕田、種地等農活,沒有人知道張義尚是一個修煉金家與形意、內丹外丹、醫藥匯宗、東派西派、悟真諸家、道密武功的大師。
靠著張義尚親弟弟張義敬的一封信,何華雲被接納為弟子。在此之前,張義尚已關門不授徒多年。張義尚看了何華雲所學後說:「太極是雅人做雅事,你是記者,性情又溫和,沒有人比你更適合習這種拳術的了。就學太極拳吧。」
學武甘苦:和水牛同車去尋師
何華雲回憶起自己的學藝過程,點點滴滴仍記憶猶新。
從萬州到汝溪,班車很少,有時為了省錢,就搭乘貨車。有一次,在朋友的幫助下,何華雲搭上了一輛載著水牛的大貨車。車子的大貨廂內五頭牛並排站著,後面用幾根大木棍攔住,留下一個小小的空間,何華雲就站在這裡。
鄉間山路崎嶇顛簸,每次上坡時,牛就站不穩往後退,何華雲唯恐水牛沉重的蹄子踩了自己,緊緊地抓住車廂扶把,膽戰心驚。
這些都沒能擋住何華雲學藝的步伐,他照例兩個月從萬州去一趟汝溪。每次到來,都要等師父忙完工作,往往是夜深人靜時,才有機會向老師請教太極拳的問題。他隨身攜帶一個筆記本,將自己回家練拳的困惑寫在上面,一個個向老師請教。
「老師和我的感情,情同父子。」何華雲說起老師,眉宇間透出深深的懷念。
何華雲二○○七年曾去給過世六年的張義尚師父掃墓,回來後,寫了篇文章〈汝溪寄情〉。一個傳統武術的徒弟對師父的濃濃情誼,流淌在文字之中,感人至深。
不思量,自難忘。師父仙逝已六年多了,今年春節前夕,我與數同好來到重慶市忠縣汝溪鎮九亭鄉憑弔師尊,但見落葉孤塚,山冷草黃,一片蕭瑟,心中不免萬分感慨。
……那時師還隱居在九亭鄉他家祖居的一個寨子裡,這寨子位於汝溪鎮旁一突兀的山峰上,晴則綠樹掩映,陰則雲遮霧繞,走進寨門方見巨石嵯峨,高牆壁壘,十分險峻,是他家當年躲避兵匪襲擾的地方。寨後有一塊平壩,青石鋪地,四周茂林修竹、古樹橫斜、野草山花、鳥鳴蟲吟,加之石凳石桌 石盆石洞,頗有幾分仙家之氣。師就在這塊空地上糾正我的拳架,並手把手地講解太極拳技擊要領,每次都直至師母一聲「吃飯了!」我們才罷手,穿過那扇石質的寨後門,圍坐在一張已不見顏色的木桌旁,舉手抓紅苕棒兒。
……我與他過手,他輕輕一籠即止,我自知無出路時他便放手,只在教我發勁時動了幾次真,如電光火石地一閃,我就像呆子一樣站在那裡,似乎心子已被打掉了。
何華雲說,從一九七七年到師父去世,他跟張義尚老師主要學習太極拳。後來師父在八○年代後招了幾個學其他拳種的徒弟,他只是偶爾從其他師兄弟處側面瞭解一些關於金家功夫(心意六合拳一支)、八卦掌。
很遺憾沒能學到師父的丹道、中醫等絕學。一個國寶級人物的離世,帶走了很多不可複製的瑰寶。這又豈止是何華雲一個人的感慨!
內家奧祕:太極拳不是玄學,是科學
太極拳技擊的核心原理,就是破壞對方的「重心」。
何華雲說,太極技擊,就是盡力維護自己的平衡,守住重心,同時透過剛柔、輕重、虛實、快慢等手法去破壞對方的重心。只要對方的重心被掌控,就穩操勝券。而不要被對方控制重心,用力不行,用招不行,反抗不行,逃跑不行,只能隨對方的意圖。要隨勁力的方向、大小,及時調整自己的重心,維護平衡,並同時體察及感知對方的重心,以順勢反控制。
現在練太極拳的部分拳家,動輒說得很玄,氣啊、大周天、小周天的,對太極拳沒什麼好處。「太極拳不是玄學,是科學。」何華雲說。
為什麼是科學,何華雲說:「太極拳技擊,就是破壞對方重心,符合力學原理。」他又說:「太極拳推手中有兩種平衡值得重視:一種是拱橋平衡,兩人一搭手,黏住就容易形成依托平衡——拱橋原理。另一種是隨遇平衡,人隨時只有一個點與地面接觸,不會形成雙重,也能自由轉換重心。」他說,球在地面旋轉就是隨意平衡,因而我們不能說球倒了,只能說球滾了。球要在地面滾動,與地面的接觸只能有一個點,否則就動不了或者不是球。太極拳要求不犯雙重,即盡量少用雙腳同時扎地,其目的就在於此。
聽完理論,和何老師搭手,感覺其腳下確只有一個點觸地,陰陽轉換特別隱蔽。
何老師說:「太極拳同樣也是一個熟能生巧的學問。並不神祕。然而其修煉過程中,卻需要師父的口傳身授,親自讓徒弟在身上感悟,才能取得進步。」
武學比喻:意是燈光,不是手電筒
何華雲說:「太極拳的修煉不缺乏拳論,因為網際網路的崛起,無論多麼保守的拳論,都已暴露無遺。缺的是對拳論的真切理解,並能將這個理解用現實的話準確表達與演示出來,讓人能夠在身體上領悟。太極拳論有:在力則僵,在氣則滯,在意則活之說。」
何華雲強調意,他回憶自己師父張義尚曾打譬喻說:意就像屋頂的燈光,可以照在屋子的每一處,不像手電筒的光,只能照出一束光,照到一部分地方。
就筆者對練習內家拳的認識,這樣的譬喻對於練拳者的幫助,有時會勝過刻板的描述與講解。
何華雲說:「不管是對於初學者,還是多年修煉者,一個『鬆』字永無止境。而鬆又以肩鬆最難。只有鬆做好了,才能將對方的來力傳導到足底——根。」
他拿導電性做比喻,銀的傳導性最好,其次是銅,再來是鋁,再是鐵,而電阻越小的,傳導性越好,硬度越小。銀,無疑是「鬆」得最好的。
說到身體在競技中的狀態時,何華雲用象棋來做比喻:「頭是帥,兩肩是士,雙肘是象,兩手是車,胯是馬,膝是砲,腳是卒子。推手時,腳是不能退的,就和象棋的卒子一樣。」
筆者感嘆自己最近修煉太極拳進入瓶頸,難以突破。何華雲解讀說:「這就像進入了一個物質形態轉換的臨界點,比如說,冰塊加熱變成水,雖然一部分已經融化了,但溫度還是攝氏○度,一定要等全部變成水後加熱一陣子,溫度才會上升。」
每個人做事都有自己的臨界點,在臨界點不要因為溫度不變,就否定加溫的作用。太極拳的練習,也是一樣的道理。
專業拳師必須更看重養生
由文入武算起來已近四十年,何華雲現在長期在重慶萬州、四川成都、北京等地雲遊授徒。他笑言自己過的是專業拳師的生活。
在他的徒弟中,三分之二都是因為身體不好前來拜師習拳,總是各有收穫。從何老師的面容已不容置疑太極拳的養生功效,看著自己以前的部分同事退休後,或沉迷於麻將,或因為地位變化而心態不佳,患病去世,何華雲欷歔不已。
一位愛徒的孩子,考上大學不久就休學回到老家,因為極度的封閉和抑鬱,影響到了身體健康,走幾步路就會嘔吐。孩子有了厭世情緒,覺得活不下去了。在嘗試過各種藥物及看過幾個心理醫生後還是不見效,後來就讓孩子學打太極拳。
最初打拳,孩子需要人攙扶才能到達拳場,經過一段時間的鍛鍊,孩子身體上的不適消失了,面色從慘白到紅潤,性格也開朗許多。幾個月後,就重返大學校園。這位愛徒事後感觸良多地告訴何華雲:「師父,你救了我們兩代人啊。」
(未完 後續詳情請見書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