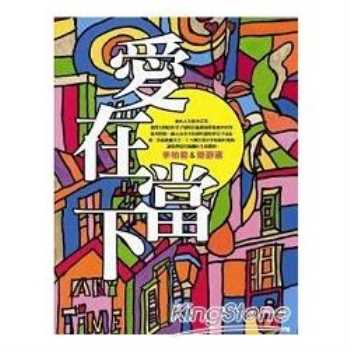●太陽與向日葵
一開始,我只覺得我生了一個科學家。
這個孩子才一歲多,手指頭就動個不停。每一個孩子都會胡亂塗鴉,一隻筆握在手中,就在任何可以畫的東西上天馬行空的畫線條,畫圓圈,畫房子,畫天空,畫大頭人。不想畫了,把筆一扔跑去玩玩具,不然就衝到屋外找別的孩子打打鬧鬧,我社區裡的孩子每個都這樣。我真愛看孩子們畫畫。
但柏毅不太一樣,忽然之間,好像睡了一覺醒來,他就變成了一個你不按停止鍵就不會停止畫畫的小小孩。
為了按下他的停止鍵,我每天都抱著他,再牽著三歲的哥哥柏雄去參加社區的唱歌或遊戲課程,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不把他的注意力引開,他的手指頭就不停的動,凌空比劃,像在構圖,在勾勒某種東西的形狀。
這個小孩怎麼回事?媽媽沒有教他嗎?旁人疑問的眼光像針一樣扎在我的身上。
總不能這樣比劃下去吧,我想。於是就買了紙筆給他。一拿到工具,才幾秒鐘他就在紙上畫出了太陽和有笑臉的花。後來我才知道,高掛天空的太陽和院子裡的向日葵,對他來說應該就是最強烈的視覺印記吧。
但只給他紙還是不夠,他還要往牆上畫。
他不斷的以鮮麗濃烈的色彩畫太陽和花,用色之大膽純粹,我解釋為那就是屬於孩子的單純和明亮。有些晚上和他同房的哥哥都已經睡著,他還會自己爬起來在牆上畫,安安靜靜的不吵不鬧,就是一直畫,像有天使對著他耳語:畫呀,畫呀,你要一直畫。
我想起那個一穿上紅舞鞋就不停跳舞的安徒生童話。天使對女孩說:「妳要跳舞呀,穿著妳的紅舞鞋不停的跳……」紅舞鞋的女孩在雨裡跳,在太陽下跳,在黑夜裡跳。
柏毅,是不是也有一雙紅舞鞋?畫畫就是他的舞蹈?
「紅舞鞋」是悲傷的故事,柏毅的畫卻是明亮如正午的天光。
有樣學樣,哥哥大概覺得這位弟弟太有趣了,也跟著他畫起來,兩人聯手把房間牆壁當做畫布大畫特畫,起先他們一畫完我就擦掉,但今天擦明天又被畫上去,再擦再畫,擦了一段時間,我厭煩了,就告訴自己,「好吧,隨你們畫,看看這面牆壁會怎樣。」這樣累積一段時間沒擦,有一天我仔仔細細看著牆上柏毅的畫,雖然千篇一律的太陽和花朵,但卻看出了細微的變化,像有簡單劇情的動畫片,也就是說,他不是一成不變的畫著,他是有系列的在表達一些事情。
但是除了不停的畫,他不開口說話,眼睛不注視人,不管什麼東西都要拿來聞一聞,每天用蓮篷頭幫他沖澡時會哭鬧不休。沒問題,我告訴自己,我會好好教他,矯正他,等他長大一些就全改過來了。
我不知道那些行為表現就等於自閉兒的正字標記。
柏毅十八個月時,醫生確診他有自閉症。
柏毅是個在期待下出生的寶寶。才滿一歲,想喝奶的時候他就會發出「ㄋㄟ ㄋㄟ」的音,比柏雄還快學會表達,而且有種特別的專注。美國的衣服後面不是常常都有一根棒子嗎?柏毅可以抓著棒子以各種速度和方向反覆把玩好幾個小時,帶著一種像在測試和研究什麼的眼神。哇,將來一定和爸爸一樣,是個科學家,我暗自想著。
一歲半以後的柏毅好似變了另一個人,原來的那個天使不見了,除了不停的用手指頭比劃,他變得很「灰」,很「番」,極度的黏我,一分鐘看不到我就大哭大鬧。此外,他經常上吐下瀉,我猜想他的哭鬧可能來自身體的不舒服,無法好好睡覺,精神萎頓像個縮成嬰兒的老頭。
他的吐奶情況非常嚴重,每天衣服要換四五回,有時我來不及躲就被吐在頭髮上。平常時候吐,搭飛機更是鐵定吐,知道他會吐,當然備妥好幾套衣服以便隨時替換,哪知道他會吐到已無乾淨衣服可換的地步,只好忍到下飛機,當我抱他,一對又酸又臭的母子要通過海關時,每回都只見海關人員捏著鼻子用濃濃的鼻音揮著手說:「過、過、過」,連檢查行李都免了。
我才逐漸意識到柏毅某個地方出了問題,他是個不一樣的孩子。
●用拍立得學「刷牙」
未來不可知,但回頭看,一路的摸索與跌撞,多少暗夜裡無聲的淚水,莫名的恐懼,還有柏毅成名之後的屢遭中傷,以及「你們有錢人才做得到」的惡意評論,我害怕我一開口就疼痛。
確認柏毅有自閉症,而且被判定為重度自閉以後,我的狀態,只能用「瘋狂」兩個字來形容。那時的我既無知又自負,我告訴自己,自閉症噢,它就像感冒,也許是嚴重一點的感冒,只要我找到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方法,少則幾個月,多則幾年,一定可以治好我的孩子。愛的力量無堅不摧,感天動地,這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難得倒我,一個為了孩子無所畏懼的母親。
我的耳畔不時傳來這樣的雜音,「妳應該專心去上班,反正自閉症無藥可醫,就不要浪費心思了。」但我依舊沒有動搖。
美國貴為醫學大國,還是流傳著不少關於治療自閉症的偏方或另類療法,我照單全收,中西合併,主流與另類雙管齊下。有人說針灸有用,我就帶柏毅去針灸;有人說可以吃中藥,我就煎中藥給他喝;甚至還聽說瑜伽和體操很有幫助……總而言之,從美國到歐洲,我耳聽八方,馬力全開,只要能力所及,那怕用盡力氣,我也要去做。
教導自閉症孩子的方式,專業用語稱為「分解式操作訓練」,譬如要教他說「門」,就必須牽著他的手,走到真正的「門」的前面,指著「門」說:「門」。這樣的動作也不是一兩次就能搞定,需要反覆的教,但即使如此,他也無法以此類推,當遇到不同形式的「門」,相同的程序就要再重複。有個例子是我從書上看到的,一個自閉症孩子已經學會要等綠燈才能過馬路,但僅限於家門口那條馬路,帶他到阿公阿嬤家門前那條馬路,他又回復原形,看都不看就往前衝,必須重新一步一步教。
車水馬龍與熙來攘往,在我們看來是正常,但對他們來說,卻是無法認知的危險。一小步一小步,重複重複再重複,教導自閉症孩子從來都是如此。「門」、「水」、「狗」、「學校」……每一個單字我都必須煞費苦心的教,這樣一直到三歲多,柏毅仍舊只能發出聲音,冒出幾個單字,沒有辦法說出一個完整的句子。每當他想要什麼東西,就抓著我的手去指一指,譬如說「糖」,我必須狠下心,不能直接拿糖給他,要先半逼半哄他發出「糖」的音。「湯」、「忙」、「打」……一開始他會發出一個個接近「糖」卻不是「糖」的音,「糖」、「糖」、「糖」,我就一遍兩遍三四五遍的重覆,一直到他發出正確的「糖」為止。
從詞彙到完整的句子則更加困難,譬如從「杯子」和「水」,進化到「用杯子喝水」。二十年前沒有智慧型手機,我便買了一台拍立得,拍下各式各樣的杯子,告訴他這些統統都是「杯子」,然後再抓著他的手去拍拍水,把「杯子」和「水」連結起來,讓他知道「杯子是用來喝水的」。
接下來我開始教他早上起床後固定要做的事,上廁所、刷牙、洗臉、換衣服,把每個步驟一一用拍立得拍下來,將照片一張一張按照順序貼在板子上。先下床,再走到洗手間,然後是到馬桶小便,接下來再到鏡子前,拿起牙刷和牙膏刷牙,最後是漱口。
我依然記得,這一個刷牙的動作,我用了七張拍立得,而柏毅花了八個月的時間,總算才學會。
出門則有另一套,先穿鞋,所以要拍鞋子,再坐車,我的車子也要拍一張。如此當我跟柏毅說:「要出門囉」,他就知道要去穿鞋子,準備搭我的車。
是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要教。每一件小事,對一般孩子來說,不學而能,或者兩三下就會的事;對柏毅來説,都是無比困難的大事。也許可以這樣類比,別人的一百公尺,到了柏毅那會延伸成一千公尺、一萬公尺,我必須陪著他努力地跑,用力地跑,如果不在腦神經正在快速發展連結的五歲以前拼命的教,盡可能的訓練,那一千公尺、一萬公尺,恐怕就要發展到十萬公尺的高空去了。
因此,我必須和時間賽跑。
他無法學習是有原因的。有時候是因為懼怕,柏毅懼怕小嬰兒,也許是嬰兒的哭聲,也許是嬰兒在他眼裡看來像「怪物」,我發現他害怕嬰兒後,便用拍立得拍下許多的嬰兒照片讓他看,看到「習慣」後,一遇到「真正」的嬰兒,我就拉著他手去撫摸,一邊撫摸,一邊說「好香」、「好軟」。嬰兒哭了,他的馬上手縮回去,後退兩步,我必須立刻告訴他,寶寶是因為肚子餓了啊,是因為尿布濕了,這樣一點一滴,反反覆覆的教,直到他確認,或者說是相信,嬰兒香香的,軟軟的,他們並不可怕。二十年過去,他還是害怕小孩的哭聲。把握黃金時間,把握黃金時間,這幾個字無時無刻纏繞著我,在我腦中不停的放送,我多麼害怕,只要一個鬆懈,柏毅就退步了。
但即使這麼努力了,柏毅還是不開口說話。他不說,那就由我來說。每天睡前,無論他聽得懂或聽不懂,想聽或不想聽,我一定要講故事給他聽。我們的書及錄音帶都是從圖書館借來的,一個故事我總要重複的講十遍一百遍,我告訴他房子蓋在沙地上會被風吹倒,告訴他白雪公主吃了毒蘋果。他總是安靜的聽,沒有反應,不像別的孩子會搶著和媽咪講話,「接下來呢?」、「然後呢?」、「為什麼?」的問個不停,我從來都不知道,他喜歡三隻小豬還是白雪公主。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後的某一天,當柏毅一字不漏的把我說過的故事背出來,我才知道,他其實都聽進去了,一刀未剪的照單全收。
●藝想天開的天才
柏毅三歲的時候,經過幾番打探,我得知芭芭拉老師是洛衫磯西區教導自閉兒首屈一指的名師,她任教的班級是一個專門收三到十歲自閉症孩子的特別班。
我下定決心讓芭芭拉成為柏毅的老師。
是芭芭拉老師,發現了柏毅獨特的天賦。
在我被制約的想像裡,人生應該有一條「正常」的軌道,有所謂的主流價值,生而為人,最終目標就是自我管理,獨立生存,不需要仰賴人,但同時又能與他人合作,融入社會。達不到目標,是因為不夠努力。
所以有一段時間,大約是柏毅四歲以後,我真的狠下心來奪走他的紙和筆,不讓他畫。
我不讓他畫,他就用手指頭在空氣中畫,好像這世界上沒有東西是不能用來當畫布的。
直到芭芭拉老師有一次下課時,收到柏毅送給她的「禮物」,那是他即席畫下的上一堂課的上課情景。在觀察柏毅一段時日後,她以一種發現珍寶的心情欣賞這個無時刻不在畫畫的小孩,她發現他雖然無法和正常人一樣表達,但卻有「接收」的能力,他對於自己經歷的事情是有感觸的,只是他轉譯的工具不是語言,而是畫。
「柏毅具有與生俱來的繪畫天分,」她一臉嚴肅的告訴我,「請妳不要阻止,不要扼殺了他珍貴的天賦。」
同一個柏毅,同樣不停止的畫,不管他畫了什麼,畫得如何,我看到的是他的強迫行為,這讓我忍無可忍,想出手制止,剝奪、矯正,改造,芭芭拉老師卻說他的作品非常奇妙,獨具風格,一眼就能辨識,這就是天賦;她說真正的天賦藏不住,無法壓抑,只能順從。我知道柏毅愛畫,如果不帶他去做點別的,他可以一整天都在畫,可是當芭芭拉老師提出建議,要我帶柏毅去接受加州州立大學的美術資優天才的鑑定,我心想,對一個連話都說不好、無法表達的孩子,這怎麼可能?這不是天方夜譚是什麼?
在這之前,我從來不曾聽說過有這種評鑑。
評鑑過程遠比我想像的複雜,我原來以為,只要送作品過去讓專家們研究審核一番,結果審閱作品只是第一關,第一關通過後,接下來還要接受當場測試,他們擔心有人代筆。連續七天,我開車帶他到考場,我以柏毅有自閉症為由請求特別通融,允許家人陪伴測試,但未獲准,我看著柏毅一個人走進教室後,低頭禱告。
測試內容就是看他們當場畫出來的作品,每天給不同的題目,用不同的媒材,我猜柏毅應該畫得如魚得水吧,畢竟這是他的「常態」,七天之後,柏毅竟然被鑑定為資優天才,我說他有自閉症呀,他們說這裡只問藝術天分有無,不問他有沒有自閉症。
資優天才也不只是一個認定,往後十年的每個星期六,我必須帶著柏毅和一群資優天才們到加州州立大學上課,學校安排的課程非常多元,素描、寫生、油畫、花藝、黏土,陶藝,總之你所能想像以及不能想像的藝術相關課程應有盡有,柏毅喜歡和一大群人一起上課,會好奇其他人在畫些什麼,這應該歸功於後天的訓練。有一次老師出了一個題目,要同學模擬一幅必須用左手畫的黑白畫,我才知道柏毅原來也可以用左手畫,交作業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一張和原畫一樣的黑白畫,只有柏毅,還是彩色的。
如今回想起來,那十年的歲月,柏毅接受到各個老師、各種風格的衝擊,我們看過無數展覽,踏遍洛杉磯所有的美術館。柏毅後來豐富多元的創作,應該是源自這個時期的滋養及訓練。
●一鳴驚人的「吶喊」
柏毅一鳴驚人,被鑑定為美術資優,都要感謝畢卡索阿公。
「畢卡索大展」來到LA時正是柏毅七歲那年。到底要不要去看,我猶豫很久,一張門票要價三十美元,其實不便宜,柏毅當然沒有錢的觀念,但我也不能太任性。
但是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最後我還是說服自己,咬牙買票進場,展場人潮洶湧,雖然沒有人大聲說話,但我們還是被四面八方的交談聲包圍,柏毅一進去就皺起眉頭,一張臉變成苦瓜,我只好配合他的速度,匆匆巡過一圈就回家了。
回家後沒多久,他就畫出這幅The scream,這是他自己下的標題。
畫中的人穿著西裝,這應該來自他從小都穿西裝上教堂做禮拜,穿西裝的人佔領整個畫面,張大嘴巴叫喊,整張臉因為聲廝力竭而漲紅。
自畫像被認為是通往創作者內心世界的一條路,畢卡索可能是現代藝術家中創作自畫像最多的人,他把自己想像成各種角色,花花公子、戀人、藝術家、朋友、猴子……
柏毅這幅畫引起評論家的高度興趣,每個人都不敢相信這是一個七歲小孩的畫,每個人都在分析畫出這幅畫的七歲小孩,到底要透過畫表達什麼?他內心是不是藏著一口深不見底的井?井裡埋著多少我們無法窺見的情緒?柏毅的畫在說什麼?
那時候他其實還不太會說話,只聽得懂簡單的指令,當我對他說「我們去吃飯」,他可以了解,但如果我說「我們待會兒到明星去吃飯」,因為包含的訊息太多,他會陷入混亂。
然而,自閉症通常是不會寫在臉上的,因為他長得很「正常」,所以大多數人就像對待正常孩子一樣跟他說話,等他回應,我猜這使得柏毅很挫折,備感壓力,這種情況下他就會尖叫,用尖叫逃離情境。
這個世界逼迫他們以各種方法逃遁。
我又猜,他也許是在想,我不會像你們這樣流暢表達,也聽不太懂,請你們跟我講話時請要有耐性,請你們用我可以懂的方式對我說話。
所以畫中那個穿西裝的人就是他自己。
也有很多人指出這張畫的意境和孟克的〈吶喊〉很相似。挪威表現主義大師孟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一組吟誦生命、愛情與死亡的系列畫,其中以〈吶喊〉最具代表性,畫中一具骷髏般的人形,他站在一座長橋上,眼睛圓睜睜,兩手托頰,又像是在捂著耳朵尖叫,背景的天空流動著不祥的雲朵,詭異的氛圍,抑鬱的顏色,整幅圖看起來像天旋地轉,論者公認〈吶喊〉具體而微表現出現代人的焦慮感,但也有人認為這很能代表自閉症者的心境。
我確定,畫這幅畫之前,柏毅沒有看過〈吶喊〉。
柏毅這幅畫並不若以往「漂亮」,但他畫中有話,這就是他想要告訴這個世界的話。面對周遭嘈雜的聲音,他其實是焦慮無助的,他很想跟大家對話,但卻沒有辦法。畫中人的手臂朝外阻擋,好像是在說:Stop,我了解你們在跟我說什麼,但可以聽聽我,別再說了嗎?
柏毅無從解釋他的畫,其實也不需要特別解釋,他用〈The Scream〉證明了一件事,他的思想,遠遠超過他所能表達的,這也是詩人羅智成在看過柏毅的畫之後說:「他的畫需要翻譯。」
這幅〈The Scream〉是柏毅第一次用畫表達他心中的困境,也讓他大家第一次注意到他。
●第一次的畫展
十三歲,柏毅第一次開畫展,地點在聖塔摩尼卡的BGH GALLERY,這是一個金字塔頂端的藝術中心,場租費用一個月一萬美金,只有被認可為一流藝術家才有機會到這裡展畫,在這裡開過畫展,就等於拿到了藝術界的入門證,加州自閉症基金會為柏毅爭取在此辦展,對我來說,這代表他的畫獲得大家的肯定。在這一次畫展,柏毅賣出了二十多幅畫,我們把一部分款項捐給加州自閉症基金會。
也就是說,柏毅有了賺錢的能力,只是他毫無所覺。
第二次畫展,他的畫就調整為一幅一萬美金,這當然是經過專家評估,不是我自己隨意定的價錢。
柏毅的「畫展人生」於焉展開,十四歲那年,他第一次回台灣開「從不可能到可能」個展,地點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大稻埕美術館,展出四十多幅作品,其中一幅畫了兩仙布袋戲偶的「門神」還被李登輝主持的群策會收藏。
二十多年來,從美國到台灣,從台灣到法國,到威尼斯,到維也納,到中國大陸……從未歇息,馬不停蹄,他為自閉症學會募款,為教會募款,為許多的公益活動募款,他是二○一一年「第五十四屆威尼斯雙年展」的《未來通行證從亞洲到全球》,百分之百以藝術家身分而非自閉症。而在上海和北京的資優天才研討會上,他被中外媒體包圍,要求拍照,要求他談談自己的畫作,那場面太大太混亂,我頓時緊張起來,還好有師大特教系教授郭靜姿及台大精神科醫師高淑芬在場,緩和了我的情緒。
我總是比柏毅緊張,然而對柏毅來說,這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畫畫,畫畫,繼續畫畫。畫畫是他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同時也是他回應這個世界的方式。
也是因為柏毅,二○一四年三月,世界自閉症大會選擇在台灣召開,紐約、洛杉磯的醫學研究教授全自費來台北共襄盛舉,柏毅宛如「自閉症大使」,串連起世界各地每一個關注自閉症的醫師和學者,期許這個世界能夠對這些孩子更友善,對這些孩子的父母多一些支持!
●把他的人生畫進畫裡
我經常被問到柏毅到底畫過多少幅畫,而我總是無回答。太多了,我們每天有多少念頭閃過,他就有多少幅畫。
有人用文字寫日記,有人用照片寫日記,有人每天每小時把心情的陰晴圓缺po在臉書,柏毅則是用畫。他的畫,就是文字、聲音、味道,就是感情,是個人生活的紀錄和情緒的出口。
據說畢卡索說過,他要盡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人生畫進畫哩,以留給後世一份盡可能完整的紀錄。
在我看來,柏毅也一樣,他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人生畫進畫裡,但和畢卡索不同的是,驅使柏毅的動力來自內建的基因,而畢卡索除了受到內在驅使,還有對實驗創新永不止息的渴求,他知道自己在翻攪藝術史,知道自己站在藝術的浪尖上。
而我能做的,就是做一個內容的提供者,盡最大努力帶給柏毅不同的生活體會和視覺經驗,除了旅行之外,我們到北藝大、台藝大和師大特教中心上課,去音樂會及國家劇院,去陽明山二子坪賞花觀葉看天空,去萬里飛滑翔翼,去平溪放天燈,去坪林逛茶園,在三峽與老井和梯田不期而遇,在宜蘭跟著黃春明老師做稻草人,在路邊吃辦桌大快朵頤……每一天,我都放一點新的東西到他生命的容器裡,有點像農夫播種,把種子從四面八方撒下,即使我從來不知道它們會長出什麼。
●當他們長大成年
我經常思索一個問題,究竟是自閉症的人辛苦,還是他們的家人?
那一天,我一直提心吊膽的事終於發生,柏毅不見了。
他去板橋台藝大上課,正在等車回家時,伴讀臨時接到電話,稍稍移動了位置講話,柏毅一轉頭沒看到人,也不懂得問,不懂得找,或者留在原地等待,他的直覺雷達告訴他,走,自己走回家去。
他就開始走,從板橋走到華翠大橋,從艋舺大道走到中華路,從中華路走到仁愛路,最後走回家。從下午走到天黑,走了五個小時,二十多公里路。
我這一頭,一接到伴讀的電話,就立刻報警,親朋好友總動員,聽說廣播電台播出了這一則「明星第三代」的新聞。
那五個小時,對我來說就像五個世紀的煎熬,我禱告,禱告,再禱告,只祈求柏毅平安。
當他走到店裡,出現在我面前那一刻,我忍了五個小時的淚如暴雨狂洩。
我問他怎麼認得路?
「上帝帶我回家。」他說。
那晚半夜我甚至接到恐嚇電話,說你的兒子在我手上,拿贖金來。
我怎麼能夠不保護柏毅呢?
會有一天,我再也不能保護他,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我必須盡可能訓練他獨立的能力,為他找到可信任也愛他的「保母」,但不會讓他孤獨一個人走下去。
沒有人可以替代母親,母親終究不是神。
我必須趁著還有力氣,還走得動的時候,多帶他到處去玩,去看,去嘗試,我喜歡看他開心的樣子,笑的樣子,為換取那樣純潔無邪的笑容,我願意付出一切所有。我是單純的媽媽,當每一個人都反對,說這樣不行那樣不對時,我還是傻傻地做,傻傻地往前走,我相信單純的力量,會獲得神的眷顧。
但我不知道柏毅還能畫幾年,不知道明年他還是不是有名,有沒有人邀他展畫,我只知道,不管他會不會畫,是不是藝術家,有沒有人欣賞他的畫,我永遠是他的母親,對他的愛是無條件的。
全世界都一樣,自閉症的家人,都有山高海深的苦,盼望不到天明的辛酸,但我們仍然各自努力。當我們絕望,說要放棄的時候,其實是在求救,尋找支撐下去的力量。
《Far from the tree》一書中提到一個故事,一個母親為了訓練自閉症兒子,她日復一日,把自己修練成為大學生、研究生都必須來跟她學習的專家,當她把兒子訓練到終於能夠上學,交給學校後,便倒下了,檢查之下,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全身。她在病床上接受作者採訪。美國有一個統計,兒童非自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父母所為,這一半中的一半,他們的孩子有自閉症。
真相很殘酷,但不能不面對。
很多電影或電視劇裡都喜歡穿插一個自閉症角色,但這似乎不能增加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了解,最負面的狀況是帶動「正常人」去模仿自閉症,引起滿場大樂。
自閉紀錄片更逼近真實。
林正盛的紀錄片《一閃一閃亮晶晶》,紀錄柏毅在內,四個有繪畫天賦的自閉症孩子和他們的家庭,一年多的拍攝,長時間的接觸,林正盛導演丟出一個另類思考:
「這些特別的孩子和大多數號稱正常人所規範建構的這個世界,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呢?難道只因為他們是那麼的不同,那麼的異於我們為數眾多的正常人,因而我們就以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社會生活方式去要求他們,說是『為他們好』的教導他們,要他們融入我們正常人建構規範起來的生活方式。」
「然而,是否可能一不小心就同時導正了他們與生特有的言語、行為、思考、感情表達方式,導正掉了屬於他們跟這個世界特有的互動方式,最終導正掉的是他們對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無法以他們與生俱來特有的生命狀態,去煥發出他們的生命光采。」
林導演看到的比較是高功能自閉症。
沈可尚《遙遠星球的孩子》深入自閉症患者內心孤獨的世界,讓觀眾正視自閉症患者難以和外界溝通,經常被誤解的問題,獲得二○一三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築巢人》則延續自閉症議題,把鏡頭轉向照顧者,自閉症者的父親,它呈現自閉症患者的黑暗面,片中三十歲的陳立夫,他有蒐物癖,收集各種廢紙、磚瓦和蜂巢,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自言自語,憤怒時會拍桌子,對父親爆粗口,甚至暴力相向。六十歲的父親陳鴻棟,一開始他決定以「家庭的溫暖」盡父親的責任,但經常力不從心,心力交瘁,「我終究不是有那種偉大性格的人」,「我們終究是一般人」,「我可不可以放棄」,這些都是他面對鏡頭說的話。
沈可尚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因此沒有辦法在片尾時配上溫馨的音樂,給一個感人的結局。
每一天我們都要面對新的挑戰,都在戰鬥。
我們需要更多的同理心,更多的理解,以及更多的資源,一條讓自閉症的孩子在長大後,可以繼續走下去的路。
希望每一天,我與所有自閉症者的父母,我們都要微笑著醒來。
●我的兒子有自閉症,他當選了二○一三年台灣十大傑出青年。
想起社會大眾對自閉症孩子的閒言閒語,「啊,他們都是不事生產的『米蟲』啦,消耗這個社會的資源!」
「他是自閉症。」很多人這樣介紹柏毅。
「他是人,他不是自閉症。」然後,柏毅的哥哥柏雄會立刻嚴厲糾正,我可以感覺他變成一頭暴龍,一股怒火即將噴出。
我了解柏雄的憤怒來自何處。多數人總是輕率的使用語言,不覺察語言是思維的外顯。「他是自閉症。」當人們這樣指說,在意義脈絡裡,就等於「他整個人就是自閉症」,自閉症之外什麼都不是。「他是自閉症」是一種負面的、隱含放棄的表述,反正是自閉症,無藥可醫,努力也沒有用。
「他有自閉症」則不同。「他是一個有自閉症的人」,當人們這樣說,看見的不只是自閉症,還包括了他被禁錮的潛力,以及對他的期許。每一個自閉症患者都有不同的潛能,給他們機會學習,從微小的事情做起,從中發掘天賦,他們就會進步,潛能就得以發揮。他們可以成為一流的品管員、麵包師傅、電腦工程師、景觀設計師、鋼琴家、畫家、作家……如果他們有機會學習。
如果我們,自閉症的家人夠堅強。如果社會更了解自閉症,接納自閉症。如果國家和社會能夠做我們的後盾。
在這個分工繁複已經回不去的地球,每一個人都必須靠別人才能活下去,不是只有自閉症患者。
我的兒子有自閉症,還有繪畫和運動的天賦,現在他是一名畫家,展覽的邀請來自世界各國,一年到頭都不間斷;他的作品也被美術館和收藏家收藏。他從來不知道自己擁有強大的募款能力。二○一三年十月他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上台領獎的時候,連站在旁邊的人都看不出來他有自閉症。但我實在無法對他解釋這個獎的意義,有多麼不容易,多麼難能可貴。
有人問我:「柏毅得獎後可以為台灣貢獻什麼?」我不知如何回答,因為這是柏毅一直以來在做的事啊,他辦過無數畫展,外國人因而知道這些畫背後的作者是來自台灣的Leland Lee。除此之外,我們也以自閉症患者和家長的身分,代表台灣參加過無數國際性研討會,就是期盼能讓更多人了解,自閉症並不可怕。
因為不瞭解自閉症,大多數人覺得這些孩子一無是處。也許「十大傑出青年」這個頭銜真的可以作為證明,他們不是「米蟲」,他們是我們的榮耀。
柏毅從王金平院長手中接獲這個獎,他其實沒什麼概念,不知道這個榮耀的「價值」。王院長說:「李柏毅雖有自閉症,但他的畫呈現對社會的獨到見解,他得這個獎是實至名歸!」
大部分人或許會說柏毅是個「自閉症+畫家」,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個畫家,一個用全部生命在作畫,純粹的畫家,只是剛好有自閉症。
這是一個漫長的歷程,我們熬過長夜,迎接黎明,但黎明之後,還要對抗隨時可能來襲的風暴,挑戰永遠不會停止,
但就算大雨我們也要走出去,就算大雨也會有天晴的時候。就算大雨,雨後也會出現彩虹。
我們期待雨後的彩虹。
一開始,我只覺得我生了一個科學家。
這個孩子才一歲多,手指頭就動個不停。每一個孩子都會胡亂塗鴉,一隻筆握在手中,就在任何可以畫的東西上天馬行空的畫線條,畫圓圈,畫房子,畫天空,畫大頭人。不想畫了,把筆一扔跑去玩玩具,不然就衝到屋外找別的孩子打打鬧鬧,我社區裡的孩子每個都這樣。我真愛看孩子們畫畫。
但柏毅不太一樣,忽然之間,好像睡了一覺醒來,他就變成了一個你不按停止鍵就不會停止畫畫的小小孩。
為了按下他的停止鍵,我每天都抱著他,再牽著三歲的哥哥柏雄去參加社區的唱歌或遊戲課程,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不把他的注意力引開,他的手指頭就不停的動,凌空比劃,像在構圖,在勾勒某種東西的形狀。
這個小孩怎麼回事?媽媽沒有教他嗎?旁人疑問的眼光像針一樣扎在我的身上。
總不能這樣比劃下去吧,我想。於是就買了紙筆給他。一拿到工具,才幾秒鐘他就在紙上畫出了太陽和有笑臉的花。後來我才知道,高掛天空的太陽和院子裡的向日葵,對他來說應該就是最強烈的視覺印記吧。
但只給他紙還是不夠,他還要往牆上畫。
他不斷的以鮮麗濃烈的色彩畫太陽和花,用色之大膽純粹,我解釋為那就是屬於孩子的單純和明亮。有些晚上和他同房的哥哥都已經睡著,他還會自己爬起來在牆上畫,安安靜靜的不吵不鬧,就是一直畫,像有天使對著他耳語:畫呀,畫呀,你要一直畫。
我想起那個一穿上紅舞鞋就不停跳舞的安徒生童話。天使對女孩說:「妳要跳舞呀,穿著妳的紅舞鞋不停的跳……」紅舞鞋的女孩在雨裡跳,在太陽下跳,在黑夜裡跳。
柏毅,是不是也有一雙紅舞鞋?畫畫就是他的舞蹈?
「紅舞鞋」是悲傷的故事,柏毅的畫卻是明亮如正午的天光。
有樣學樣,哥哥大概覺得這位弟弟太有趣了,也跟著他畫起來,兩人聯手把房間牆壁當做畫布大畫特畫,起先他們一畫完我就擦掉,但今天擦明天又被畫上去,再擦再畫,擦了一段時間,我厭煩了,就告訴自己,「好吧,隨你們畫,看看這面牆壁會怎樣。」這樣累積一段時間沒擦,有一天我仔仔細細看著牆上柏毅的畫,雖然千篇一律的太陽和花朵,但卻看出了細微的變化,像有簡單劇情的動畫片,也就是說,他不是一成不變的畫著,他是有系列的在表達一些事情。
但是除了不停的畫,他不開口說話,眼睛不注視人,不管什麼東西都要拿來聞一聞,每天用蓮篷頭幫他沖澡時會哭鬧不休。沒問題,我告訴自己,我會好好教他,矯正他,等他長大一些就全改過來了。
我不知道那些行為表現就等於自閉兒的正字標記。
柏毅十八個月時,醫生確診他有自閉症。
柏毅是個在期待下出生的寶寶。才滿一歲,想喝奶的時候他就會發出「ㄋㄟ ㄋㄟ」的音,比柏雄還快學會表達,而且有種特別的專注。美國的衣服後面不是常常都有一根棒子嗎?柏毅可以抓著棒子以各種速度和方向反覆把玩好幾個小時,帶著一種像在測試和研究什麼的眼神。哇,將來一定和爸爸一樣,是個科學家,我暗自想著。
一歲半以後的柏毅好似變了另一個人,原來的那個天使不見了,除了不停的用手指頭比劃,他變得很「灰」,很「番」,極度的黏我,一分鐘看不到我就大哭大鬧。此外,他經常上吐下瀉,我猜想他的哭鬧可能來自身體的不舒服,無法好好睡覺,精神萎頓像個縮成嬰兒的老頭。
他的吐奶情況非常嚴重,每天衣服要換四五回,有時我來不及躲就被吐在頭髮上。平常時候吐,搭飛機更是鐵定吐,知道他會吐,當然備妥好幾套衣服以便隨時替換,哪知道他會吐到已無乾淨衣服可換的地步,只好忍到下飛機,當我抱他,一對又酸又臭的母子要通過海關時,每回都只見海關人員捏著鼻子用濃濃的鼻音揮著手說:「過、過、過」,連檢查行李都免了。
我才逐漸意識到柏毅某個地方出了問題,他是個不一樣的孩子。
●用拍立得學「刷牙」
未來不可知,但回頭看,一路的摸索與跌撞,多少暗夜裡無聲的淚水,莫名的恐懼,還有柏毅成名之後的屢遭中傷,以及「你們有錢人才做得到」的惡意評論,我害怕我一開口就疼痛。
確認柏毅有自閉症,而且被判定為重度自閉以後,我的狀態,只能用「瘋狂」兩個字來形容。那時的我既無知又自負,我告訴自己,自閉症噢,它就像感冒,也許是嚴重一點的感冒,只要我找到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方法,少則幾個月,多則幾年,一定可以治好我的孩子。愛的力量無堅不摧,感天動地,這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難得倒我,一個為了孩子無所畏懼的母親。
我的耳畔不時傳來這樣的雜音,「妳應該專心去上班,反正自閉症無藥可醫,就不要浪費心思了。」但我依舊沒有動搖。
美國貴為醫學大國,還是流傳著不少關於治療自閉症的偏方或另類療法,我照單全收,中西合併,主流與另類雙管齊下。有人說針灸有用,我就帶柏毅去針灸;有人說可以吃中藥,我就煎中藥給他喝;甚至還聽說瑜伽和體操很有幫助……總而言之,從美國到歐洲,我耳聽八方,馬力全開,只要能力所及,那怕用盡力氣,我也要去做。
教導自閉症孩子的方式,專業用語稱為「分解式操作訓練」,譬如要教他說「門」,就必須牽著他的手,走到真正的「門」的前面,指著「門」說:「門」。這樣的動作也不是一兩次就能搞定,需要反覆的教,但即使如此,他也無法以此類推,當遇到不同形式的「門」,相同的程序就要再重複。有個例子是我從書上看到的,一個自閉症孩子已經學會要等綠燈才能過馬路,但僅限於家門口那條馬路,帶他到阿公阿嬤家門前那條馬路,他又回復原形,看都不看就往前衝,必須重新一步一步教。
車水馬龍與熙來攘往,在我們看來是正常,但對他們來說,卻是無法認知的危險。一小步一小步,重複重複再重複,教導自閉症孩子從來都是如此。「門」、「水」、「狗」、「學校」……每一個單字我都必須煞費苦心的教,這樣一直到三歲多,柏毅仍舊只能發出聲音,冒出幾個單字,沒有辦法說出一個完整的句子。每當他想要什麼東西,就抓著我的手去指一指,譬如說「糖」,我必須狠下心,不能直接拿糖給他,要先半逼半哄他發出「糖」的音。「湯」、「忙」、「打」……一開始他會發出一個個接近「糖」卻不是「糖」的音,「糖」、「糖」、「糖」,我就一遍兩遍三四五遍的重覆,一直到他發出正確的「糖」為止。
從詞彙到完整的句子則更加困難,譬如從「杯子」和「水」,進化到「用杯子喝水」。二十年前沒有智慧型手機,我便買了一台拍立得,拍下各式各樣的杯子,告訴他這些統統都是「杯子」,然後再抓著他的手去拍拍水,把「杯子」和「水」連結起來,讓他知道「杯子是用來喝水的」。
接下來我開始教他早上起床後固定要做的事,上廁所、刷牙、洗臉、換衣服,把每個步驟一一用拍立得拍下來,將照片一張一張按照順序貼在板子上。先下床,再走到洗手間,然後是到馬桶小便,接下來再到鏡子前,拿起牙刷和牙膏刷牙,最後是漱口。
我依然記得,這一個刷牙的動作,我用了七張拍立得,而柏毅花了八個月的時間,總算才學會。
出門則有另一套,先穿鞋,所以要拍鞋子,再坐車,我的車子也要拍一張。如此當我跟柏毅說:「要出門囉」,他就知道要去穿鞋子,準備搭我的車。
是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要教。每一件小事,對一般孩子來說,不學而能,或者兩三下就會的事;對柏毅來説,都是無比困難的大事。也許可以這樣類比,別人的一百公尺,到了柏毅那會延伸成一千公尺、一萬公尺,我必須陪著他努力地跑,用力地跑,如果不在腦神經正在快速發展連結的五歲以前拼命的教,盡可能的訓練,那一千公尺、一萬公尺,恐怕就要發展到十萬公尺的高空去了。
因此,我必須和時間賽跑。
他無法學習是有原因的。有時候是因為懼怕,柏毅懼怕小嬰兒,也許是嬰兒的哭聲,也許是嬰兒在他眼裡看來像「怪物」,我發現他害怕嬰兒後,便用拍立得拍下許多的嬰兒照片讓他看,看到「習慣」後,一遇到「真正」的嬰兒,我就拉著他手去撫摸,一邊撫摸,一邊說「好香」、「好軟」。嬰兒哭了,他的馬上手縮回去,後退兩步,我必須立刻告訴他,寶寶是因為肚子餓了啊,是因為尿布濕了,這樣一點一滴,反反覆覆的教,直到他確認,或者說是相信,嬰兒香香的,軟軟的,他們並不可怕。二十年過去,他還是害怕小孩的哭聲。把握黃金時間,把握黃金時間,這幾個字無時無刻纏繞著我,在我腦中不停的放送,我多麼害怕,只要一個鬆懈,柏毅就退步了。
但即使這麼努力了,柏毅還是不開口說話。他不說,那就由我來說。每天睡前,無論他聽得懂或聽不懂,想聽或不想聽,我一定要講故事給他聽。我們的書及錄音帶都是從圖書館借來的,一個故事我總要重複的講十遍一百遍,我告訴他房子蓋在沙地上會被風吹倒,告訴他白雪公主吃了毒蘋果。他總是安靜的聽,沒有反應,不像別的孩子會搶著和媽咪講話,「接下來呢?」、「然後呢?」、「為什麼?」的問個不停,我從來都不知道,他喜歡三隻小豬還是白雪公主。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後的某一天,當柏毅一字不漏的把我說過的故事背出來,我才知道,他其實都聽進去了,一刀未剪的照單全收。
●藝想天開的天才
柏毅三歲的時候,經過幾番打探,我得知芭芭拉老師是洛衫磯西區教導自閉兒首屈一指的名師,她任教的班級是一個專門收三到十歲自閉症孩子的特別班。
我下定決心讓芭芭拉成為柏毅的老師。
是芭芭拉老師,發現了柏毅獨特的天賦。
在我被制約的想像裡,人生應該有一條「正常」的軌道,有所謂的主流價值,生而為人,最終目標就是自我管理,獨立生存,不需要仰賴人,但同時又能與他人合作,融入社會。達不到目標,是因為不夠努力。
所以有一段時間,大約是柏毅四歲以後,我真的狠下心來奪走他的紙和筆,不讓他畫。
我不讓他畫,他就用手指頭在空氣中畫,好像這世界上沒有東西是不能用來當畫布的。
直到芭芭拉老師有一次下課時,收到柏毅送給她的「禮物」,那是他即席畫下的上一堂課的上課情景。在觀察柏毅一段時日後,她以一種發現珍寶的心情欣賞這個無時刻不在畫畫的小孩,她發現他雖然無法和正常人一樣表達,但卻有「接收」的能力,他對於自己經歷的事情是有感觸的,只是他轉譯的工具不是語言,而是畫。
「柏毅具有與生俱來的繪畫天分,」她一臉嚴肅的告訴我,「請妳不要阻止,不要扼殺了他珍貴的天賦。」
同一個柏毅,同樣不停止的畫,不管他畫了什麼,畫得如何,我看到的是他的強迫行為,這讓我忍無可忍,想出手制止,剝奪、矯正,改造,芭芭拉老師卻說他的作品非常奇妙,獨具風格,一眼就能辨識,這就是天賦;她說真正的天賦藏不住,無法壓抑,只能順從。我知道柏毅愛畫,如果不帶他去做點別的,他可以一整天都在畫,可是當芭芭拉老師提出建議,要我帶柏毅去接受加州州立大學的美術資優天才的鑑定,我心想,對一個連話都說不好、無法表達的孩子,這怎麼可能?這不是天方夜譚是什麼?
在這之前,我從來不曾聽說過有這種評鑑。
評鑑過程遠比我想像的複雜,我原來以為,只要送作品過去讓專家們研究審核一番,結果審閱作品只是第一關,第一關通過後,接下來還要接受當場測試,他們擔心有人代筆。連續七天,我開車帶他到考場,我以柏毅有自閉症為由請求特別通融,允許家人陪伴測試,但未獲准,我看著柏毅一個人走進教室後,低頭禱告。
測試內容就是看他們當場畫出來的作品,每天給不同的題目,用不同的媒材,我猜柏毅應該畫得如魚得水吧,畢竟這是他的「常態」,七天之後,柏毅竟然被鑑定為資優天才,我說他有自閉症呀,他們說這裡只問藝術天分有無,不問他有沒有自閉症。
資優天才也不只是一個認定,往後十年的每個星期六,我必須帶著柏毅和一群資優天才們到加州州立大學上課,學校安排的課程非常多元,素描、寫生、油畫、花藝、黏土,陶藝,總之你所能想像以及不能想像的藝術相關課程應有盡有,柏毅喜歡和一大群人一起上課,會好奇其他人在畫些什麼,這應該歸功於後天的訓練。有一次老師出了一個題目,要同學模擬一幅必須用左手畫的黑白畫,我才知道柏毅原來也可以用左手畫,交作業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一張和原畫一樣的黑白畫,只有柏毅,還是彩色的。
如今回想起來,那十年的歲月,柏毅接受到各個老師、各種風格的衝擊,我們看過無數展覽,踏遍洛杉磯所有的美術館。柏毅後來豐富多元的創作,應該是源自這個時期的滋養及訓練。
●一鳴驚人的「吶喊」
柏毅一鳴驚人,被鑑定為美術資優,都要感謝畢卡索阿公。
「畢卡索大展」來到LA時正是柏毅七歲那年。到底要不要去看,我猶豫很久,一張門票要價三十美元,其實不便宜,柏毅當然沒有錢的觀念,但我也不能太任性。
但是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最後我還是說服自己,咬牙買票進場,展場人潮洶湧,雖然沒有人大聲說話,但我們還是被四面八方的交談聲包圍,柏毅一進去就皺起眉頭,一張臉變成苦瓜,我只好配合他的速度,匆匆巡過一圈就回家了。
回家後沒多久,他就畫出這幅The scream,這是他自己下的標題。
畫中的人穿著西裝,這應該來自他從小都穿西裝上教堂做禮拜,穿西裝的人佔領整個畫面,張大嘴巴叫喊,整張臉因為聲廝力竭而漲紅。
自畫像被認為是通往創作者內心世界的一條路,畢卡索可能是現代藝術家中創作自畫像最多的人,他把自己想像成各種角色,花花公子、戀人、藝術家、朋友、猴子……
柏毅這幅畫引起評論家的高度興趣,每個人都不敢相信這是一個七歲小孩的畫,每個人都在分析畫出這幅畫的七歲小孩,到底要透過畫表達什麼?他內心是不是藏著一口深不見底的井?井裡埋著多少我們無法窺見的情緒?柏毅的畫在說什麼?
那時候他其實還不太會說話,只聽得懂簡單的指令,當我對他說「我們去吃飯」,他可以了解,但如果我說「我們待會兒到明星去吃飯」,因為包含的訊息太多,他會陷入混亂。
然而,自閉症通常是不會寫在臉上的,因為他長得很「正常」,所以大多數人就像對待正常孩子一樣跟他說話,等他回應,我猜這使得柏毅很挫折,備感壓力,這種情況下他就會尖叫,用尖叫逃離情境。
這個世界逼迫他們以各種方法逃遁。
我又猜,他也許是在想,我不會像你們這樣流暢表達,也聽不太懂,請你們跟我講話時請要有耐性,請你們用我可以懂的方式對我說話。
所以畫中那個穿西裝的人就是他自己。
也有很多人指出這張畫的意境和孟克的〈吶喊〉很相似。挪威表現主義大師孟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一組吟誦生命、愛情與死亡的系列畫,其中以〈吶喊〉最具代表性,畫中一具骷髏般的人形,他站在一座長橋上,眼睛圓睜睜,兩手托頰,又像是在捂著耳朵尖叫,背景的天空流動著不祥的雲朵,詭異的氛圍,抑鬱的顏色,整幅圖看起來像天旋地轉,論者公認〈吶喊〉具體而微表現出現代人的焦慮感,但也有人認為這很能代表自閉症者的心境。
我確定,畫這幅畫之前,柏毅沒有看過〈吶喊〉。
柏毅這幅畫並不若以往「漂亮」,但他畫中有話,這就是他想要告訴這個世界的話。面對周遭嘈雜的聲音,他其實是焦慮無助的,他很想跟大家對話,但卻沒有辦法。畫中人的手臂朝外阻擋,好像是在說:Stop,我了解你們在跟我說什麼,但可以聽聽我,別再說了嗎?
柏毅無從解釋他的畫,其實也不需要特別解釋,他用〈The Scream〉證明了一件事,他的思想,遠遠超過他所能表達的,這也是詩人羅智成在看過柏毅的畫之後說:「他的畫需要翻譯。」
這幅〈The Scream〉是柏毅第一次用畫表達他心中的困境,也讓他大家第一次注意到他。
●第一次的畫展
十三歲,柏毅第一次開畫展,地點在聖塔摩尼卡的BGH GALLERY,這是一個金字塔頂端的藝術中心,場租費用一個月一萬美金,只有被認可為一流藝術家才有機會到這裡展畫,在這裡開過畫展,就等於拿到了藝術界的入門證,加州自閉症基金會為柏毅爭取在此辦展,對我來說,這代表他的畫獲得大家的肯定。在這一次畫展,柏毅賣出了二十多幅畫,我們把一部分款項捐給加州自閉症基金會。
也就是說,柏毅有了賺錢的能力,只是他毫無所覺。
第二次畫展,他的畫就調整為一幅一萬美金,這當然是經過專家評估,不是我自己隨意定的價錢。
柏毅的「畫展人生」於焉展開,十四歲那年,他第一次回台灣開「從不可能到可能」個展,地點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大稻埕美術館,展出四十多幅作品,其中一幅畫了兩仙布袋戲偶的「門神」還被李登輝主持的群策會收藏。
二十多年來,從美國到台灣,從台灣到法國,到威尼斯,到維也納,到中國大陸……從未歇息,馬不停蹄,他為自閉症學會募款,為教會募款,為許多的公益活動募款,他是二○一一年「第五十四屆威尼斯雙年展」的《未來通行證從亞洲到全球》,百分之百以藝術家身分而非自閉症。而在上海和北京的資優天才研討會上,他被中外媒體包圍,要求拍照,要求他談談自己的畫作,那場面太大太混亂,我頓時緊張起來,還好有師大特教系教授郭靜姿及台大精神科醫師高淑芬在場,緩和了我的情緒。
我總是比柏毅緊張,然而對柏毅來說,這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畫畫,畫畫,繼續畫畫。畫畫是他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同時也是他回應這個世界的方式。
也是因為柏毅,二○一四年三月,世界自閉症大會選擇在台灣召開,紐約、洛杉磯的醫學研究教授全自費來台北共襄盛舉,柏毅宛如「自閉症大使」,串連起世界各地每一個關注自閉症的醫師和學者,期許這個世界能夠對這些孩子更友善,對這些孩子的父母多一些支持!
●把他的人生畫進畫裡
我經常被問到柏毅到底畫過多少幅畫,而我總是無回答。太多了,我們每天有多少念頭閃過,他就有多少幅畫。
有人用文字寫日記,有人用照片寫日記,有人每天每小時把心情的陰晴圓缺po在臉書,柏毅則是用畫。他的畫,就是文字、聲音、味道,就是感情,是個人生活的紀錄和情緒的出口。
據說畢卡索說過,他要盡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人生畫進畫哩,以留給後世一份盡可能完整的紀錄。
在我看來,柏毅也一樣,他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人生畫進畫裡,但和畢卡索不同的是,驅使柏毅的動力來自內建的基因,而畢卡索除了受到內在驅使,還有對實驗創新永不止息的渴求,他知道自己在翻攪藝術史,知道自己站在藝術的浪尖上。
而我能做的,就是做一個內容的提供者,盡最大努力帶給柏毅不同的生活體會和視覺經驗,除了旅行之外,我們到北藝大、台藝大和師大特教中心上課,去音樂會及國家劇院,去陽明山二子坪賞花觀葉看天空,去萬里飛滑翔翼,去平溪放天燈,去坪林逛茶園,在三峽與老井和梯田不期而遇,在宜蘭跟著黃春明老師做稻草人,在路邊吃辦桌大快朵頤……每一天,我都放一點新的東西到他生命的容器裡,有點像農夫播種,把種子從四面八方撒下,即使我從來不知道它們會長出什麼。
●當他們長大成年
我經常思索一個問題,究竟是自閉症的人辛苦,還是他們的家人?
那一天,我一直提心吊膽的事終於發生,柏毅不見了。
他去板橋台藝大上課,正在等車回家時,伴讀臨時接到電話,稍稍移動了位置講話,柏毅一轉頭沒看到人,也不懂得問,不懂得找,或者留在原地等待,他的直覺雷達告訴他,走,自己走回家去。
他就開始走,從板橋走到華翠大橋,從艋舺大道走到中華路,從中華路走到仁愛路,最後走回家。從下午走到天黑,走了五個小時,二十多公里路。
我這一頭,一接到伴讀的電話,就立刻報警,親朋好友總動員,聽說廣播電台播出了這一則「明星第三代」的新聞。
那五個小時,對我來說就像五個世紀的煎熬,我禱告,禱告,再禱告,只祈求柏毅平安。
當他走到店裡,出現在我面前那一刻,我忍了五個小時的淚如暴雨狂洩。
我問他怎麼認得路?
「上帝帶我回家。」他說。
那晚半夜我甚至接到恐嚇電話,說你的兒子在我手上,拿贖金來。
我怎麼能夠不保護柏毅呢?
會有一天,我再也不能保護他,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我必須盡可能訓練他獨立的能力,為他找到可信任也愛他的「保母」,但不會讓他孤獨一個人走下去。
沒有人可以替代母親,母親終究不是神。
我必須趁著還有力氣,還走得動的時候,多帶他到處去玩,去看,去嘗試,我喜歡看他開心的樣子,笑的樣子,為換取那樣純潔無邪的笑容,我願意付出一切所有。我是單純的媽媽,當每一個人都反對,說這樣不行那樣不對時,我還是傻傻地做,傻傻地往前走,我相信單純的力量,會獲得神的眷顧。
但我不知道柏毅還能畫幾年,不知道明年他還是不是有名,有沒有人邀他展畫,我只知道,不管他會不會畫,是不是藝術家,有沒有人欣賞他的畫,我永遠是他的母親,對他的愛是無條件的。
全世界都一樣,自閉症的家人,都有山高海深的苦,盼望不到天明的辛酸,但我們仍然各自努力。當我們絕望,說要放棄的時候,其實是在求救,尋找支撐下去的力量。
《Far from the tree》一書中提到一個故事,一個母親為了訓練自閉症兒子,她日復一日,把自己修練成為大學生、研究生都必須來跟她學習的專家,當她把兒子訓練到終於能夠上學,交給學校後,便倒下了,檢查之下,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全身。她在病床上接受作者採訪。美國有一個統計,兒童非自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父母所為,這一半中的一半,他們的孩子有自閉症。
真相很殘酷,但不能不面對。
很多電影或電視劇裡都喜歡穿插一個自閉症角色,但這似乎不能增加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了解,最負面的狀況是帶動「正常人」去模仿自閉症,引起滿場大樂。
自閉紀錄片更逼近真實。
林正盛的紀錄片《一閃一閃亮晶晶》,紀錄柏毅在內,四個有繪畫天賦的自閉症孩子和他們的家庭,一年多的拍攝,長時間的接觸,林正盛導演丟出一個另類思考:
「這些特別的孩子和大多數號稱正常人所規範建構的這個世界,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呢?難道只因為他們是那麼的不同,那麼的異於我們為數眾多的正常人,因而我們就以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社會生活方式去要求他們,說是『為他們好』的教導他們,要他們融入我們正常人建構規範起來的生活方式。」
「然而,是否可能一不小心就同時導正了他們與生特有的言語、行為、思考、感情表達方式,導正掉了屬於他們跟這個世界特有的互動方式,最終導正掉的是他們對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無法以他們與生俱來特有的生命狀態,去煥發出他們的生命光采。」
林導演看到的比較是高功能自閉症。
沈可尚《遙遠星球的孩子》深入自閉症患者內心孤獨的世界,讓觀眾正視自閉症患者難以和外界溝通,經常被誤解的問題,獲得二○一三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築巢人》則延續自閉症議題,把鏡頭轉向照顧者,自閉症者的父親,它呈現自閉症患者的黑暗面,片中三十歲的陳立夫,他有蒐物癖,收集各種廢紙、磚瓦和蜂巢,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自言自語,憤怒時會拍桌子,對父親爆粗口,甚至暴力相向。六十歲的父親陳鴻棟,一開始他決定以「家庭的溫暖」盡父親的責任,但經常力不從心,心力交瘁,「我終究不是有那種偉大性格的人」,「我們終究是一般人」,「我可不可以放棄」,這些都是他面對鏡頭說的話。
沈可尚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因此沒有辦法在片尾時配上溫馨的音樂,給一個感人的結局。
每一天我們都要面對新的挑戰,都在戰鬥。
我們需要更多的同理心,更多的理解,以及更多的資源,一條讓自閉症的孩子在長大後,可以繼續走下去的路。
希望每一天,我與所有自閉症者的父母,我們都要微笑著醒來。
●我的兒子有自閉症,他當選了二○一三年台灣十大傑出青年。
想起社會大眾對自閉症孩子的閒言閒語,「啊,他們都是不事生產的『米蟲』啦,消耗這個社會的資源!」
「他是自閉症。」很多人這樣介紹柏毅。
「他是人,他不是自閉症。」然後,柏毅的哥哥柏雄會立刻嚴厲糾正,我可以感覺他變成一頭暴龍,一股怒火即將噴出。
我了解柏雄的憤怒來自何處。多數人總是輕率的使用語言,不覺察語言是思維的外顯。「他是自閉症。」當人們這樣指說,在意義脈絡裡,就等於「他整個人就是自閉症」,自閉症之外什麼都不是。「他是自閉症」是一種負面的、隱含放棄的表述,反正是自閉症,無藥可醫,努力也沒有用。
「他有自閉症」則不同。「他是一個有自閉症的人」,當人們這樣說,看見的不只是自閉症,還包括了他被禁錮的潛力,以及對他的期許。每一個自閉症患者都有不同的潛能,給他們機會學習,從微小的事情做起,從中發掘天賦,他們就會進步,潛能就得以發揮。他們可以成為一流的品管員、麵包師傅、電腦工程師、景觀設計師、鋼琴家、畫家、作家……如果他們有機會學習。
如果我們,自閉症的家人夠堅強。如果社會更了解自閉症,接納自閉症。如果國家和社會能夠做我們的後盾。
在這個分工繁複已經回不去的地球,每一個人都必須靠別人才能活下去,不是只有自閉症患者。
我的兒子有自閉症,還有繪畫和運動的天賦,現在他是一名畫家,展覽的邀請來自世界各國,一年到頭都不間斷;他的作品也被美術館和收藏家收藏。他從來不知道自己擁有強大的募款能力。二○一三年十月他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上台領獎的時候,連站在旁邊的人都看不出來他有自閉症。但我實在無法對他解釋這個獎的意義,有多麼不容易,多麼難能可貴。
有人問我:「柏毅得獎後可以為台灣貢獻什麼?」我不知如何回答,因為這是柏毅一直以來在做的事啊,他辦過無數畫展,外國人因而知道這些畫背後的作者是來自台灣的Leland Lee。除此之外,我們也以自閉症患者和家長的身分,代表台灣參加過無數國際性研討會,就是期盼能讓更多人了解,自閉症並不可怕。
因為不瞭解自閉症,大多數人覺得這些孩子一無是處。也許「十大傑出青年」這個頭銜真的可以作為證明,他們不是「米蟲」,他們是我們的榮耀。
柏毅從王金平院長手中接獲這個獎,他其實沒什麼概念,不知道這個榮耀的「價值」。王院長說:「李柏毅雖有自閉症,但他的畫呈現對社會的獨到見解,他得這個獎是實至名歸!」
大部分人或許會說柏毅是個「自閉症+畫家」,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個畫家,一個用全部生命在作畫,純粹的畫家,只是剛好有自閉症。
這是一個漫長的歷程,我們熬過長夜,迎接黎明,但黎明之後,還要對抗隨時可能來襲的風暴,挑戰永遠不會停止,
但就算大雨我們也要走出去,就算大雨也會有天晴的時候。就算大雨,雨後也會出現彩虹。
我們期待雨後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