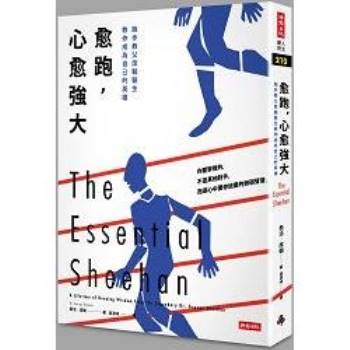舒服的速度
當我沿著濱海的路邊跑步時,一位年輕人跟上前問我:「你跑多快?」他顯然期待我回答一哩跑幾分鐘這種答案。他問的是一個新手的問題。我給了他一個老手的答案。
「舒服的速度。」我說。
我的步調不是用來測量能跑多遠,或者是能跑多快。我與身體商量出一個強度,而不是與碼錶或里程標示商量。我將身體調整到跑起來覺得舒適的步調,既不考慮、也不在乎每哩實際的速度。
剛開始跑步時,我就像先前提問的年輕人一樣,很想知道我到底跑了多遠,以便能算出速度。我計算在跑道上跑了幾圈,甚至用開車的方式行駛跑過的路線,以便精準知道正確的距離。
有時候,這讓人很沮喪。我會忘了到底是數到第幾圈。我用手指計算,從一隻手到另一隻手時,這樣很容易錯亂。我記不得我是跑了二十圈?二十一圈?或是這前後的哪一圈。現在回想起來,我發現這種計數真是可笑!待身心日漸成熟後,我明白,距離和速度都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能以舒適的速度跑步的時間。
當這位跑者追上我時,我不清楚我是每哩跑八分鐘(每公里五分鐘)或是十分鐘(每公里六分十五秒)。我也不在意。我把身體調到自動駕駛模式後,便隨思緒神遊了。這是我思考的步調,也是我可以一直保持的速度。有時候會快一點或慢一點,但永遠是舒適的速度。
我希望他會停下來聊幾句,但他加速跑遠了,我目送他離開。若和他一起跑步會帶我離開舒適圈,我的訓練很少需要多費那樣的力氣。我訓練的時間是用來思考或說話,沈思或對話。若我加快速度,將一事無成。
平常的跑步練習中,我不會出現痛苦或上氣不接下氣的情形,我不會勉強自己挑戰極限。那些酷刑只發生在周末,它們充斥每一場比賽中。而在星期週間的跑步,則給予我能遠離所有身心壓力的片刻休息。它們成了我能躲進內心的避風港,或是和朋友傾吐心事的好時機。
有天,我和另一位跑者完成了一趟來回跑後,他告訴我:「這是我最近跑過時間最短的一次。」我們一邊跑,一邊意氣相投地聊天。我們進入到超脫於汗水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在那裡,能力和自尊讓我感覺超好;平常認為太隱私的想法與感受,自然而然地從嘴角溜出。近來,當我和女兒一起慢跑一小時的時光中,我們也擁有最難忘的聊天回憶。要享受這些跑步的意外贈禮,我該跑多快呢?只限定每哩得跑幾分鐘時,才會有這驚喜嗎?非也。只需要以一種舒服的速度跑。可能是快到讓我能抛開世俗的煩惱,是快到讓我能享受身體的運作;也可能是慢到讓我能觀察周遭的世界,慢到讓我能逃進內心的世界。
舒服的步調超越生理狀態,與心理和情感狀態也相關。舒服能碰觸我整個人,舒服時,我終於能與自己安然相處,我變成一隻快樂地回到領地的動物,我對自己與人生充滿了正向的能量。舒服的步調讓我能夠沈思人生的挑戰帶回一些收獲,讓我面對人生。透過這種方式,我能挺過人生的困境,直到明天再次舒服自在地跑步。
《跑者世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踢到鐵板也是高峰經驗
第二天,大家都不停地問我到底是怎麼了。剛開始,我回說我沒跑完。後來,我開始說我無法跑完。其實我應該說的是:「我踢到鐵板了。」我早就應該這樣說,那麼他們可能就會懂了。
無論如何,事情是這樣的。在這次一九八○年的波士頓馬拉松,我終於踢到鐵板了。
關於波士頓馬拉松,我讀了很多,聽了很多,演講也曾多次提及之後,我徹底地、無可奈何地,踢到鐵板了。我有十七年的時間都成功跑完波士頓馬拉松,但這次我無法完賽。我搭電車抵達保誠大樓(Prudential),而不是用我的雙腳。
剛經過二十一哩(三十四公里)里程標示,在波士頓學院下坡時,我就知道我完了。其實,那一整天已經出現了好幾個災難的徵兆。這次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時,我帶著最佳的馬拉松成績參賽,而且我想要複製那次成功的經驗。但在任何時候,這麼做都是件危險的事,尤其是在華氏七十幾度(攝氏二十一至二十七度)的氣溫下。那天萬里無雲,所以陽光又貢獻了另外的十至二十度(攝氏六至十二度)。迎面吹來的風實際上像是冷氣機排出的散熱氣。
在這種天氣裡,起初的步伐極為重要。天氣過熱時,速度會加速脫水作用、提高體溫,而且最重要的是,會很快用盡肌糖原的庫存。在這種天氣裡,我每哩的速度應該要比平常慢三十秒,我卻反過來想快三十秒。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以謹慎自豪的我,就像其他許多跑者一樣,開始想著明年的資格成績,而忘了應該要視身體狀況跑,不該和時鐘比賽。那是我跑過最有競爭性的波士頓馬拉松。在十五哩(約二十四公里)附近的牛頓下瀑布(Newton Lower Falls),我開始對結果感到不安。那裡的長下坡跑起來比往年辛苦許多;之後上坡時,我發現自己正逐漸失去雙腳的推進力量。沒有彈力,沒有精神,我聽見了自己的腳步聲,這是失去跑姿與協調性的明顯徵兆。我像是個發現自己丟出的球完全無力的投手,我麻煩大了!
雖然如此,我克服牛頓坡,勉強跑過了心碎坡。我是在跑過波士頓學院人群後的下坡,身體開始垮下的。我的步伐慢到成了慢動作,兩隻手臂動得比雙腿還頻繁。直到山腳下,我還是用跑的,更正確地說,是用一種漫畫式的可笑跑姿在移動,我一邊跑,一邊希望一旦到了平地就恢復正常,能繼續跑。
當跑下坡時,我沿路都在痛,前大腿的肌肉不斷抗議,每一步都變得極度痛苦。我之前也有過同樣的經驗,而且後來恢復正常,跑到了終點。但願這樣的好運會再降臨一次,讓我安然跑到最後。
我告訴我自己:「現在,會漸入佳境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情況變得更糟了。痛苦仍在,現在還加上揮之不去的憂慮。肌肉變得毫無生命力,不僅失去力氣和協調性,也失去了避震能力。跨出的每一步讓我不只是大腿痛,膝蓋也痛苦不堪。
即使如此,我仍堅持著。雖然一步比一步慢,但我拒絕用走的,而且完全不考慮用走的。不論發生什麼事,我告訴自己,我絕不用走的。我從來不在波士頓馬拉松走一步,也絕對不會有第一次。
我聽見群眾為我加油打氣。有些人喊著:「很棒!」其他人也大喊:「你可以的!」眼尖的觀眾大叫:「撐過去!」、「加油!」。三不五時,我似乎都聽到了今年比賽的激勵口號:「向前挺進!」(Go for it.)
就是這向前挺進的精神,讓我陷入目前的狀態。如果前半段路跑得更謹慎些,我現在應該還能負荷,雖然仍會精疲力竭,但至少能完賽。如今我身陷在狹小的地獄裡,定睛在眼前的影子上,看著這齣啞劇。我看起來在跑,實際上並沒有。我只是上下動著,但並未往前,我其實只在原地跑。同時,我已經完全失去所有的意識,包括對於觀眾、對於比賽,甚至對自己身在何處。我的生命只剩下唯一的想法:繼續跑。這時,我感覺到一隻手碰了我一下,我往上看了一眼,是一位朋友在我旁邊。她看著比賽,看見我目前的狀況,便衝出人群。「你不想走一下嗎,喬治?」她問我,有如一位母親對著孩子說話。她已經用手攙住我,免得我跌倒。我還繼續跑著,她在一旁扶著。我不再繼續往前跑了,但我不願意用走的。
「喬治,你不想用走的嗎?」她又問了一次。她從人群中跑出來,將我從不能自拔的境地救出來。我看她站在那裡,臉上充滿了同情、關心和愛。我知道,這是該結束的時候了。「尼娜,」我說:「我只想要有個人帶我回家。」
這時,一台電車出現了,彷彿她早已傳喚它待命,她扶我上去。當我上了電車,車裡的二十幾個人都歡呼起來。起初,這令我很沮喪。「為什麼要為我喝采?」我問他們:「我根本沒有完賽。」
顯然,這並不重要。有人上前遞給我一瓶果汁,有人讓位給我,所以我搭電車到了保誠大樓,開始覺得一切都非常美好。我心想,這塊鐵板,也可以算是種高峰經驗。
《跑者世界》,一九八○年六月
P.179-180
成長的軌跡
對我另一位跑友而言,場景則是在祖父山(Grandfather Mountain,位於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蘇格蘭賽事。這個馬拉松是全國最困難的馬拉松之一,全長穿越山區的二十六•二哩(四十二•一六五公尺)路的考驗,是其他比賽無法比擬的。
我的朋友跑完了全程,征服了這段路線。跑到最後一個上坡,就快抵達終點時,他聽見了風笛的樂聲。現在,如同每個人所知,風笛的樂聲所能引起的熱情和感動無與倫比。所以當我的朋友已經因為抵達這場考驗終點激動不已,聽到風笛時,更讓他熱淚盈眶。
現在,他發現自己站在一大片平地上,被蘇格蘭不同種族的營帳圍繞。當他經過時,每一個營帳的朋友都向他大聲歡呼。他可能會忘記跑過了哪些地方,但他永遠不會忘記在那座祖父山頂平台時,時間驟然靜止,四周圍繞著快樂歡呼的人們,以及風笛悠揚的樂音。
當然,所有這些都與比賽輸贏完全無關,輸贏是你在團體比賽中的表現。跑者不是在一場比賽(game)裡,他是在一場競賽(contest)中。競賽(contest)這個字的拉丁文字根意謂「目睹」或「見證」,其他的跑者是他的見證人。因此,即便使出渾身解數,還是不夠。比賽時,你是宣誓過的;比賽時,你正在見證自己是誰。長跑選手了解這一點。他是最謙虛的人,安靜、脾氣好、鮮少與人爭執。他避免與別人衝突,尋找自己私密的世界;但在馬拉松裡,他會變成一頭兇猛的老虎。他將跑出生理機能的極致,發掘自己是誰,能耐到哪裡?他將自己推進痛苦的深淵。只要是必要的,就有可能成真,不論要花費的力氣有多荒謬。
但這些詰問,如果它們是有意義的,發生的頻率也應該不高。因為,如果馬拉松能衡量一個人的能耐,也該要與他的成長周期同步。成熟是一段崎嶇不平、令人沮喪的過程,要成為自己,沒有時間表可依循,可能有好幾年都停滯在某處。但無可否認,馬拉松能在人生中留下與眾不同的回憶,這就足以當作每個月跑一次馬拉松的理由。當坐搖椅的時候到了,你已經有萬全的準備。
《如何維持一天二十四小時神清氣爽?》,一九八三年
當我沿著濱海的路邊跑步時,一位年輕人跟上前問我:「你跑多快?」他顯然期待我回答一哩跑幾分鐘這種答案。他問的是一個新手的問題。我給了他一個老手的答案。
「舒服的速度。」我說。
我的步調不是用來測量能跑多遠,或者是能跑多快。我與身體商量出一個強度,而不是與碼錶或里程標示商量。我將身體調整到跑起來覺得舒適的步調,既不考慮、也不在乎每哩實際的速度。
剛開始跑步時,我就像先前提問的年輕人一樣,很想知道我到底跑了多遠,以便能算出速度。我計算在跑道上跑了幾圈,甚至用開車的方式行駛跑過的路線,以便精準知道正確的距離。
有時候,這讓人很沮喪。我會忘了到底是數到第幾圈。我用手指計算,從一隻手到另一隻手時,這樣很容易錯亂。我記不得我是跑了二十圈?二十一圈?或是這前後的哪一圈。現在回想起來,我發現這種計數真是可笑!待身心日漸成熟後,我明白,距離和速度都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能以舒適的速度跑步的時間。
當這位跑者追上我時,我不清楚我是每哩跑八分鐘(每公里五分鐘)或是十分鐘(每公里六分十五秒)。我也不在意。我把身體調到自動駕駛模式後,便隨思緒神遊了。這是我思考的步調,也是我可以一直保持的速度。有時候會快一點或慢一點,但永遠是舒適的速度。
我希望他會停下來聊幾句,但他加速跑遠了,我目送他離開。若和他一起跑步會帶我離開舒適圈,我的訓練很少需要多費那樣的力氣。我訓練的時間是用來思考或說話,沈思或對話。若我加快速度,將一事無成。
平常的跑步練習中,我不會出現痛苦或上氣不接下氣的情形,我不會勉強自己挑戰極限。那些酷刑只發生在周末,它們充斥每一場比賽中。而在星期週間的跑步,則給予我能遠離所有身心壓力的片刻休息。它們成了我能躲進內心的避風港,或是和朋友傾吐心事的好時機。
有天,我和另一位跑者完成了一趟來回跑後,他告訴我:「這是我最近跑過時間最短的一次。」我們一邊跑,一邊意氣相投地聊天。我們進入到超脫於汗水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在那裡,能力和自尊讓我感覺超好;平常認為太隱私的想法與感受,自然而然地從嘴角溜出。近來,當我和女兒一起慢跑一小時的時光中,我們也擁有最難忘的聊天回憶。要享受這些跑步的意外贈禮,我該跑多快呢?只限定每哩得跑幾分鐘時,才會有這驚喜嗎?非也。只需要以一種舒服的速度跑。可能是快到讓我能抛開世俗的煩惱,是快到讓我能享受身體的運作;也可能是慢到讓我能觀察周遭的世界,慢到讓我能逃進內心的世界。
舒服的步調超越生理狀態,與心理和情感狀態也相關。舒服能碰觸我整個人,舒服時,我終於能與自己安然相處,我變成一隻快樂地回到領地的動物,我對自己與人生充滿了正向的能量。舒服的步調讓我能夠沈思人生的挑戰帶回一些收獲,讓我面對人生。透過這種方式,我能挺過人生的困境,直到明天再次舒服自在地跑步。
《跑者世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踢到鐵板也是高峰經驗
第二天,大家都不停地問我到底是怎麼了。剛開始,我回說我沒跑完。後來,我開始說我無法跑完。其實我應該說的是:「我踢到鐵板了。」我早就應該這樣說,那麼他們可能就會懂了。
無論如何,事情是這樣的。在這次一九八○年的波士頓馬拉松,我終於踢到鐵板了。
關於波士頓馬拉松,我讀了很多,聽了很多,演講也曾多次提及之後,我徹底地、無可奈何地,踢到鐵板了。我有十七年的時間都成功跑完波士頓馬拉松,但這次我無法完賽。我搭電車抵達保誠大樓(Prudential),而不是用我的雙腳。
剛經過二十一哩(三十四公里)里程標示,在波士頓學院下坡時,我就知道我完了。其實,那一整天已經出現了好幾個災難的徵兆。這次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時,我帶著最佳的馬拉松成績參賽,而且我想要複製那次成功的經驗。但在任何時候,這麼做都是件危險的事,尤其是在華氏七十幾度(攝氏二十一至二十七度)的氣溫下。那天萬里無雲,所以陽光又貢獻了另外的十至二十度(攝氏六至十二度)。迎面吹來的風實際上像是冷氣機排出的散熱氣。
在這種天氣裡,起初的步伐極為重要。天氣過熱時,速度會加速脫水作用、提高體溫,而且最重要的是,會很快用盡肌糖原的庫存。在這種天氣裡,我每哩的速度應該要比平常慢三十秒,我卻反過來想快三十秒。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以謹慎自豪的我,就像其他許多跑者一樣,開始想著明年的資格成績,而忘了應該要視身體狀況跑,不該和時鐘比賽。那是我跑過最有競爭性的波士頓馬拉松。在十五哩(約二十四公里)附近的牛頓下瀑布(Newton Lower Falls),我開始對結果感到不安。那裡的長下坡跑起來比往年辛苦許多;之後上坡時,我發現自己正逐漸失去雙腳的推進力量。沒有彈力,沒有精神,我聽見了自己的腳步聲,這是失去跑姿與協調性的明顯徵兆。我像是個發現自己丟出的球完全無力的投手,我麻煩大了!
雖然如此,我克服牛頓坡,勉強跑過了心碎坡。我是在跑過波士頓學院人群後的下坡,身體開始垮下的。我的步伐慢到成了慢動作,兩隻手臂動得比雙腿還頻繁。直到山腳下,我還是用跑的,更正確地說,是用一種漫畫式的可笑跑姿在移動,我一邊跑,一邊希望一旦到了平地就恢復正常,能繼續跑。
當跑下坡時,我沿路都在痛,前大腿的肌肉不斷抗議,每一步都變得極度痛苦。我之前也有過同樣的經驗,而且後來恢復正常,跑到了終點。但願這樣的好運會再降臨一次,讓我安然跑到最後。
我告訴我自己:「現在,會漸入佳境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情況變得更糟了。痛苦仍在,現在還加上揮之不去的憂慮。肌肉變得毫無生命力,不僅失去力氣和協調性,也失去了避震能力。跨出的每一步讓我不只是大腿痛,膝蓋也痛苦不堪。
即使如此,我仍堅持著。雖然一步比一步慢,但我拒絕用走的,而且完全不考慮用走的。不論發生什麼事,我告訴自己,我絕不用走的。我從來不在波士頓馬拉松走一步,也絕對不會有第一次。
我聽見群眾為我加油打氣。有些人喊著:「很棒!」其他人也大喊:「你可以的!」眼尖的觀眾大叫:「撐過去!」、「加油!」。三不五時,我似乎都聽到了今年比賽的激勵口號:「向前挺進!」(Go for it.)
就是這向前挺進的精神,讓我陷入目前的狀態。如果前半段路跑得更謹慎些,我現在應該還能負荷,雖然仍會精疲力竭,但至少能完賽。如今我身陷在狹小的地獄裡,定睛在眼前的影子上,看著這齣啞劇。我看起來在跑,實際上並沒有。我只是上下動著,但並未往前,我其實只在原地跑。同時,我已經完全失去所有的意識,包括對於觀眾、對於比賽,甚至對自己身在何處。我的生命只剩下唯一的想法:繼續跑。這時,我感覺到一隻手碰了我一下,我往上看了一眼,是一位朋友在我旁邊。她看著比賽,看見我目前的狀況,便衝出人群。「你不想走一下嗎,喬治?」她問我,有如一位母親對著孩子說話。她已經用手攙住我,免得我跌倒。我還繼續跑著,她在一旁扶著。我不再繼續往前跑了,但我不願意用走的。
「喬治,你不想用走的嗎?」她又問了一次。她從人群中跑出來,將我從不能自拔的境地救出來。我看她站在那裡,臉上充滿了同情、關心和愛。我知道,這是該結束的時候了。「尼娜,」我說:「我只想要有個人帶我回家。」
這時,一台電車出現了,彷彿她早已傳喚它待命,她扶我上去。當我上了電車,車裡的二十幾個人都歡呼起來。起初,這令我很沮喪。「為什麼要為我喝采?」我問他們:「我根本沒有完賽。」
顯然,這並不重要。有人上前遞給我一瓶果汁,有人讓位給我,所以我搭電車到了保誠大樓,開始覺得一切都非常美好。我心想,這塊鐵板,也可以算是種高峰經驗。
《跑者世界》,一九八○年六月
P.179-180
成長的軌跡
對我另一位跑友而言,場景則是在祖父山(Grandfather Mountain,位於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蘇格蘭賽事。這個馬拉松是全國最困難的馬拉松之一,全長穿越山區的二十六•二哩(四十二•一六五公尺)路的考驗,是其他比賽無法比擬的。
我的朋友跑完了全程,征服了這段路線。跑到最後一個上坡,就快抵達終點時,他聽見了風笛的樂聲。現在,如同每個人所知,風笛的樂聲所能引起的熱情和感動無與倫比。所以當我的朋友已經因為抵達這場考驗終點激動不已,聽到風笛時,更讓他熱淚盈眶。
現在,他發現自己站在一大片平地上,被蘇格蘭不同種族的營帳圍繞。當他經過時,每一個營帳的朋友都向他大聲歡呼。他可能會忘記跑過了哪些地方,但他永遠不會忘記在那座祖父山頂平台時,時間驟然靜止,四周圍繞著快樂歡呼的人們,以及風笛悠揚的樂音。
當然,所有這些都與比賽輸贏完全無關,輸贏是你在團體比賽中的表現。跑者不是在一場比賽(game)裡,他是在一場競賽(contest)中。競賽(contest)這個字的拉丁文字根意謂「目睹」或「見證」,其他的跑者是他的見證人。因此,即便使出渾身解數,還是不夠。比賽時,你是宣誓過的;比賽時,你正在見證自己是誰。長跑選手了解這一點。他是最謙虛的人,安靜、脾氣好、鮮少與人爭執。他避免與別人衝突,尋找自己私密的世界;但在馬拉松裡,他會變成一頭兇猛的老虎。他將跑出生理機能的極致,發掘自己是誰,能耐到哪裡?他將自己推進痛苦的深淵。只要是必要的,就有可能成真,不論要花費的力氣有多荒謬。
但這些詰問,如果它們是有意義的,發生的頻率也應該不高。因為,如果馬拉松能衡量一個人的能耐,也該要與他的成長周期同步。成熟是一段崎嶇不平、令人沮喪的過程,要成為自己,沒有時間表可依循,可能有好幾年都停滯在某處。但無可否認,馬拉松能在人生中留下與眾不同的回憶,這就足以當作每個月跑一次馬拉松的理由。當坐搖椅的時候到了,你已經有萬全的準備。
《如何維持一天二十四小時神清氣爽?》,一九八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