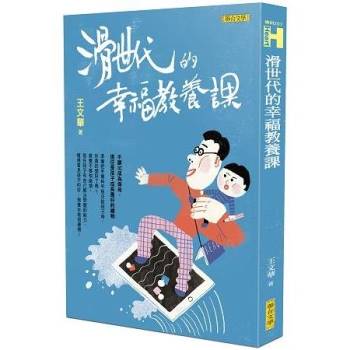踮腳尖的女孩
曾經遇過一個女孩,她叫做蓉蓉,她家就在我們社區的巷子口。
少子化的年代,社區每個孩子誕生都是大事,她一出生,大家都去看過她。她長得很可愛,兩個小酒窩,讓人不由自主想要抱一抱,她是社區年紀最小的女孩,大家對她的未來充滿了期待。
後來,她開始學走路了,這一走,她的奶奶就搖頭,蓉蓉走路是踮起腳尖來走的,奶奶說:「這囝仔有問題,哪有人走路走這款的呢,按呢不行啦!」
奶奶的話是聖旨,蓉蓉的媽媽聽了也只能拚命點頭,回頭勸女兒:「蓉蓉,把腳放下,像這樣子走!」
為了讓女兒符合奶奶口中的正常人,媽媽帶著她躲在房間裡練走路。媽媽在前頭走,蓉蓉在後頭跟,但是媽媽一不注意,蓉蓉就會踮起腳尖走,看她走得那麼快樂,連媽媽都忍不住揉揉她的頭,替她拍拍手。
奶奶生氣呀,認為媽媽沒把孩子教好:「妳這款媳婦,是要把我氣死呀?」
從此之後,奶奶對媽媽總是疾言厲色,從此之後,無數個夜晚,奶奶的話,讓蓉媽抱著女兒痛哭:「蓉蓉,把腳放下嘛,為什麼妳不把腳放下?」
蓉蓉搖搖頭,她也不知道呀。不過,她很快就學會一個本事,奶奶在的場合,她得提醒自己不要踮腳尖,不能害媽媽被奶奶念。奶奶不在家時,她才能踮著腳尖走,踮著腳尖跑。
我們曾在社區看過她踮腳尖走路的樣子(當然,奶奶不在身旁),那時的她好快活,好開心,彷彿,這麼踮一下,離天更近了,離自由更近了。
時間飛逝,一晃數年,後來蓉蓉開始學長笛了。吹長笛要有肺活量,蓉蓉的肺活量不夠大,一首曲子總是吹得「零零落落」,明顯中氣不足。老師鼓勵她長跑,可是蓉蓉跑不動;要她學游泳,蓉蓉怕下水。
「那就先踮著腳尖吹吹看。」長笛老師說。別人練長笛,最怕踮腳尖,踮一下就受不了;蓉蓉一踮半小時,吹出來的音色好極了,聲音高亢漂亮,別人吹不上的音,她吹得輕輕鬆鬆。
長笛老師拍拍她的肩:「好了,好了,累了吧,趕快把腳放下。」
蓉蓉搖搖頭:「我不累。」
一旁的媽媽跟著點點頭:「老師,沒錯,要她踮多久都可以。」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長笛老師不可置信地說。更想不到的是,蓉蓉後來在學校學芭蕾。芭蕾老師忍不住打電話給媽媽,說她旋轉時,那姿態之優美,舞動時的平衡感,沒有一個同學比得上,好像練了好久好久:「尤其是踮起腳跳舞的時候,踮再久她都不怕似的。」
蓉媽輕輕掛上電話,忍不住拭了拭眼角。她知道,這些她都知道,蓉蓉從學走路那天開始就不斷地練習,彷彿就在等著這一天。
天生我才必有用,只是我們太平庸,猜不透天機。最好的方法,就是持續鼓勵他們,然後耐心等待。
因為,不到機緣來的那天,誰也不知道上帝在孩子們身上,藏了一顆什麼樣偉大的種子。
有學問的香蕉
阿宏從小就不愛讀書。
他長得壯,小五時,一張標準課桌椅已經塞不下他了,校工特別找來最粗勇的老課桌,他才勉強坐得下。
阿宏家裡四個兄弟,他是老么,父母工作忙,平時也不怎麼管他的功課,好了,他既然不愛讀書,爸媽又不管,我是老師,我得管。
我找到機會就跟父母說,回家要盯孩子看點書。父母說,三個哥哥都是品學兼優,就出這一個不愛看書的。
阿宏媽媽還安慰我:「沒關係啦,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有讀書基因,這一個,就留下來替家裡種香蕉。」阿宏媽媽以一種完全接受孩子特質的媽媽口吻說。
他們家,有偌大一片香蕉園,那是阿宏從小的樂園,不必爸媽催,他回家一放下書包就去果園幫忙,扛香蕉、送肥料,爸爸讓他學開小怪手,他也開得有模有樣。
對阿宏來說,種香蕉、做家事不困難,他唯一煩惱的是課業,打開書本就想睡覺,數學題只能教最簡單的,國語也寫不出一段流暢的話。跟他講,要他加加油,多看看書嘛,他總是笑一笑:「我長大要種香蕉,不必懂數學。」
說得好像有道理,但我擔心他上國中。國中課業重,上了國中怎麼辦?沒想到,他到了國中,依然如魚得水,早早就向班導宣佈他的大計劃:「我國中畢業就要去種香蕉。」班導開導不了他,只能由他。
果然,這孩子國中畢業,真的去種香蕉了,偶爾路上遇見了,他還會丟串香蕉給我,要我帶回家去加菜。
誰家會用香蕉來加菜?
他不理,香蕉繼續丟給我,快樂爽朗的笑聲,和小時候一模一樣。
倒是過了兩年後,有一天我赫然發現,他背著夜校的書包,站在橋頭等公車。我把車停下,免不了要問:「你不是說讀到國中就好,不是說你再也不想讀書了?」他很老實地說,種香蕉還是要懂肥料和農藥:「不然種不出好的香蕉。」
「所以要去讀書了?」我問。
他點點頭,加一句:「吳寶春也要去讀書了啊。」看來他真的有讀了一點書,連寶春師傅的故事都知道。揀自己想讀的書去讀,讀有所需要的書,我想,阿宏以後種出來的香蕉,一定會更有滋味吧?
因為香蕉種不好,所以要開始讀書。「需要」是強烈的動機,家長應該善用它。
讓孩子幫忙算帳,孩子就得學好數學;請孩子幫忙寫封信給奶奶,孩子的作文就得好好寫。生活中時常製造「需要」的情境,小朋友會發現:原來,學問就是用來解決問題的嘛。
曾經遇過一個女孩,她叫做蓉蓉,她家就在我們社區的巷子口。
少子化的年代,社區每個孩子誕生都是大事,她一出生,大家都去看過她。她長得很可愛,兩個小酒窩,讓人不由自主想要抱一抱,她是社區年紀最小的女孩,大家對她的未來充滿了期待。
後來,她開始學走路了,這一走,她的奶奶就搖頭,蓉蓉走路是踮起腳尖來走的,奶奶說:「這囝仔有問題,哪有人走路走這款的呢,按呢不行啦!」
奶奶的話是聖旨,蓉蓉的媽媽聽了也只能拚命點頭,回頭勸女兒:「蓉蓉,把腳放下,像這樣子走!」
為了讓女兒符合奶奶口中的正常人,媽媽帶著她躲在房間裡練走路。媽媽在前頭走,蓉蓉在後頭跟,但是媽媽一不注意,蓉蓉就會踮起腳尖走,看她走得那麼快樂,連媽媽都忍不住揉揉她的頭,替她拍拍手。
奶奶生氣呀,認為媽媽沒把孩子教好:「妳這款媳婦,是要把我氣死呀?」
從此之後,奶奶對媽媽總是疾言厲色,從此之後,無數個夜晚,奶奶的話,讓蓉媽抱著女兒痛哭:「蓉蓉,把腳放下嘛,為什麼妳不把腳放下?」
蓉蓉搖搖頭,她也不知道呀。不過,她很快就學會一個本事,奶奶在的場合,她得提醒自己不要踮腳尖,不能害媽媽被奶奶念。奶奶不在家時,她才能踮著腳尖走,踮著腳尖跑。
我們曾在社區看過她踮腳尖走路的樣子(當然,奶奶不在身旁),那時的她好快活,好開心,彷彿,這麼踮一下,離天更近了,離自由更近了。
時間飛逝,一晃數年,後來蓉蓉開始學長笛了。吹長笛要有肺活量,蓉蓉的肺活量不夠大,一首曲子總是吹得「零零落落」,明顯中氣不足。老師鼓勵她長跑,可是蓉蓉跑不動;要她學游泳,蓉蓉怕下水。
「那就先踮著腳尖吹吹看。」長笛老師說。別人練長笛,最怕踮腳尖,踮一下就受不了;蓉蓉一踮半小時,吹出來的音色好極了,聲音高亢漂亮,別人吹不上的音,她吹得輕輕鬆鬆。
長笛老師拍拍她的肩:「好了,好了,累了吧,趕快把腳放下。」
蓉蓉搖搖頭:「我不累。」
一旁的媽媽跟著點點頭:「老師,沒錯,要她踮多久都可以。」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長笛老師不可置信地說。更想不到的是,蓉蓉後來在學校學芭蕾。芭蕾老師忍不住打電話給媽媽,說她旋轉時,那姿態之優美,舞動時的平衡感,沒有一個同學比得上,好像練了好久好久:「尤其是踮起腳跳舞的時候,踮再久她都不怕似的。」
蓉媽輕輕掛上電話,忍不住拭了拭眼角。她知道,這些她都知道,蓉蓉從學走路那天開始就不斷地練習,彷彿就在等著這一天。
天生我才必有用,只是我們太平庸,猜不透天機。最好的方法,就是持續鼓勵他們,然後耐心等待。
因為,不到機緣來的那天,誰也不知道上帝在孩子們身上,藏了一顆什麼樣偉大的種子。
有學問的香蕉
阿宏從小就不愛讀書。
他長得壯,小五時,一張標準課桌椅已經塞不下他了,校工特別找來最粗勇的老課桌,他才勉強坐得下。
阿宏家裡四個兄弟,他是老么,父母工作忙,平時也不怎麼管他的功課,好了,他既然不愛讀書,爸媽又不管,我是老師,我得管。
我找到機會就跟父母說,回家要盯孩子看點書。父母說,三個哥哥都是品學兼優,就出這一個不愛看書的。
阿宏媽媽還安慰我:「沒關係啦,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有讀書基因,這一個,就留下來替家裡種香蕉。」阿宏媽媽以一種完全接受孩子特質的媽媽口吻說。
他們家,有偌大一片香蕉園,那是阿宏從小的樂園,不必爸媽催,他回家一放下書包就去果園幫忙,扛香蕉、送肥料,爸爸讓他學開小怪手,他也開得有模有樣。
對阿宏來說,種香蕉、做家事不困難,他唯一煩惱的是課業,打開書本就想睡覺,數學題只能教最簡單的,國語也寫不出一段流暢的話。跟他講,要他加加油,多看看書嘛,他總是笑一笑:「我長大要種香蕉,不必懂數學。」
說得好像有道理,但我擔心他上國中。國中課業重,上了國中怎麼辦?沒想到,他到了國中,依然如魚得水,早早就向班導宣佈他的大計劃:「我國中畢業就要去種香蕉。」班導開導不了他,只能由他。
果然,這孩子國中畢業,真的去種香蕉了,偶爾路上遇見了,他還會丟串香蕉給我,要我帶回家去加菜。
誰家會用香蕉來加菜?
他不理,香蕉繼續丟給我,快樂爽朗的笑聲,和小時候一模一樣。
倒是過了兩年後,有一天我赫然發現,他背著夜校的書包,站在橋頭等公車。我把車停下,免不了要問:「你不是說讀到國中就好,不是說你再也不想讀書了?」他很老實地說,種香蕉還是要懂肥料和農藥:「不然種不出好的香蕉。」
「所以要去讀書了?」我問。
他點點頭,加一句:「吳寶春也要去讀書了啊。」看來他真的有讀了一點書,連寶春師傅的故事都知道。揀自己想讀的書去讀,讀有所需要的書,我想,阿宏以後種出來的香蕉,一定會更有滋味吧?
因為香蕉種不好,所以要開始讀書。「需要」是強烈的動機,家長應該善用它。
讓孩子幫忙算帳,孩子就得學好數學;請孩子幫忙寫封信給奶奶,孩子的作文就得好好寫。生活中時常製造「需要」的情境,小朋友會發現:原來,學問就是用來解決問題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