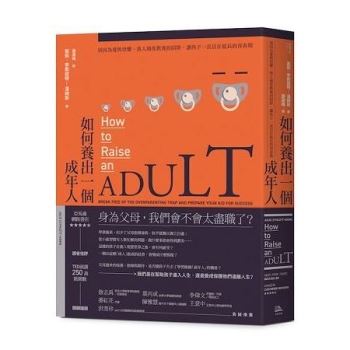我們不可能永遠為孩子守望
童年是被研究最多的階段,在任何稍有規模的書店,教養類書籍總是占據相當大的書架空間。對於任何關注小孩的父母(我們全都非常關注), 能立刻接收到的訊息是:保護孩子的安全與健康,是我們的職責。這是最基本的,是生物本能。
在我兒子莎耶的嬰兒相本中,有一張他七個月大時凝視著相機、臉上沒有表情的照片。相機只拍到一個小嬰兒躺在溜滑梯的斜面上,但我憶起那時我強壯的手,正從相機鏡頭外把他穩穩地撐住。
那是莎耶第一次去公園,第一次玩溜滑梯。當我看著這張照片時,依然可以聽到自己和丈夫都輕快地對兒子說:「沒問題的,寶貝,我們在這裡。」但從兒子的表情看起來,我們的說服力似乎不太夠。
這讓我回憶起那天我的小寶貝躺在溜滑梯頂端時,自己心中滿布的恐懼。那座溜滑梯離地面應該不到一百二十公分,我和先生一人站一邊,但我還是擔心。莎耶溜下那短短的距離時,會害怕嗎?他溜到底時,會不會撲到橡膠地板上,說不定還撞到頭?他會不會有不愉快的體驗, 而這是我們原本可能(或應該)預防的?
長久以來,每當我和莎耶一起坐在沙發上看著他最初的兒時照片,我總是把他眼裡的恐懼,歸結為是他的恐懼。但經過這些年以後,我開始納悶,我的寶貝會不會只是反映了他在爸爸與我的眼睛裡看到的恐懼?父母要如何從想要完全保護嬰兒,進化到讓孩子走出去,進入正在等待他們的世界?
在一個富足而且有著先進科技的世界,我們自認能確保,沒有一個孩子會受到任何傷害,對於施展控制的能力深具信心。為了孩子,我們讓世界變得更安全、更可預測、更友善。這種防護措施從孩子還在我們的子宮裡就開始了。母親懷孕時,寶寶的每個部分都被監測追蹤;孩子一旦出生,就進入完全保護他們的家庭。
然而,為人父母的我們卻更進一步,把自己當成孩子與世界之間的保險桿和護欄,彷彿只要我們在,孩子就會完全安然無恙。我會想到這件事,是因為有一天,我看到一對母子一起過馬路, 這在任何城市或鄉鎮都是常見景象。母親自信地走著,而她兒子,一個大約八歲的孩子,則落後一步,頭上戴著耳塞,一路盯著他的手機。母親先是左右看看,又朝左看了一次,然後和孩子一起穿越十字路口。孩子自始至終都沒有抬起頭來。後來,我看到一種為孩子的自行車設計的產品,稱為MiniBrake(「迷你煞車」),可以讓父母透過遙控器,在孩子騎車接近繁忙的交通要道時,控制自行車的後輪煞車。
當孩子還小時,我們護送他們到學校,確定他們是安全的,而且常幫忙拿東西,減輕他們的負擔。最近,我看到一個爸爸寬厚的肩膀上掛了一個淺粉紅色的書包,他踩著腳踏車,跟在他那頂多七、八歲的女兒後面,騎到離家三個街區外的當地小學。看到這一幕,我忍不住輕聲笑出來。這個畫面很可愛。但是,那天下午,以及更多之前與之後的下午,我不禁想著,孩子要長到什麼年紀,才有能力拿自己的東西?對於一個小學生來說,什麼程度的獨立才是適切的?
然後是手機。這是親子溝通過程中新近的發展,所以並非是導致直升機教養的成因,但只要這種趨勢存在,確實會助長父母盤旋的能力。研究人員稱它為「全世界最長的臍帶」。
例如,有個比佛利山莊高中學生的母親,堅持要兒子在跟朋友到海邊玩的去程與返程中,每小時傳簡訊給她。讓她擔心害怕的是行車安全,而不是在太平洋裡衝浪。另外,有一位史丹佛的家長打電話給學校,說他認為女兒失蹤了,因為他已經超過一天沒有她的訊息。還有一位到紐西蘭參加海外學程的美國大學生的家長,打電話給計畫主任,非常擔心她兒子自從到山上健行返校之後,就沒有接聽電話(她知道他已經回到校園,因為是GPS告訴她的)。
父母的警覺與科技,為我們的孩子緩衝了世界的撞擊,但我們不可能永遠為他們守望。養育小孩獨立自主,是我們生物上的必然,而在環境中認識自己,是孩子需要發展的重要生活技能。當我們試圖讓自己的存在成為守護他們的保證,我們必須要問,這是為了什麼?我們要如何預防和保護,同時又教導孩子所需的技能?我們該如何教他們自己完成這些事?給他們機會練習失敗
父母一直想為孩子處理生活上的雜事:叫他們起床、接送、提醒期限和該做的事、繳帳單、問問題、做決定、承擔責任、與陌生人說話以及面對權威人士等,孩子一旦被鬆綁而進入大學或職場時,可能會受到相當的驚嚇。他們將體驗挫折,感覺自己像個失敗者。而殘酷的反諷是,他們將無法好好應付這種失敗,因為他們向來沒有太多機會練習失敗。
當一個看似身心完全健康,但受到過度教養的孩子上了大學,而且不知如何因應可能遇到的各種新狀況:和他對「乾淨」有不同認知的室友;要求修改報告,但不會具體說明哪裡「有錯」的教授;想參加暑期研討會或服務計畫,但不能兩者都參加的選擇……他們可能會面臨真正的困難,不知道如何處理分歧、不確定性、情感受傷,或者如何決策的過程。沒有能力處理事情——調適不安、思考選項、和某人詳談、做決定——本身就成為問題。
凱倫.艾伯博士是中西部一所公立大學輔導與心理服務中心的專任心理醫師,她根據臨床經驗表示:「過度教養嚴重傷害了大學生的心理健康,使他們無法在向父母諮詢與獨立做決定之間取得平衡。」
她說明了自己會如何與學生展開會談。「剛開始他們會覺得,如果自己需要幫助,就應該立即與父母聯繫。從心理學來看,我們知道他們不是真的需要協助,如果他們可以熬過不知所措的苦惱與焦慮,基本上就是在練習這種技能,而且到了某個時間點就能學會自己解決。我會與學生一起練習他們尚未具備的批判思考、信心與獨立技能。但如果他們最後還是打電話或發訊息給父母,就不是以我對他們的期望來練習這些技能,這也意味著他們還是沒有獲得這些技能。」
我們並不是建議成年孩子永遠別打電話給父母。惡魔就在談話的細節裡。如果他們打電話來問問題、或不知如何做決定,我們是告訴他們該怎麼辦?或者,我們會仔細聆聽,根據對情況的認知問一些問題,然後說:「所以,你認為該怎麼處理?」
在事事都需要求助的問題背後,潛伏的隱憂是學生無法自外於父母而建立自我。「當孩子沒有被給予空間,靠自己的努力通過考驗,便無法好好學習解決問題。他們無法學會對自己的能力保持信心,而這可能影響他們的自尊。從來不必奮鬥的另一個問題是,你就無從經歷失敗,而且對失敗、讓他人失望感到無比恐懼。低度自信和恐懼失敗,都可能導致憂鬱或焦慮。」艾伯說。
心理學家兼作者麥德琳.雷文博士(Dr. Madeline Levine)因暢銷書《給孩子,金錢買不到的富足》躍升為全國知名人物並進行巡迴演講。她提醒父母要冷靜下來退一步想,潛伏在孩子生命中最大的傷害,恐怕是父母為孩子做了太多,因而導致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受損。
在二○一四年一月的演講中,雷文曾以一段觀念為到場聆聽的父母熱身:「現在有個廣為流傳、很有說服力的故事,說成功是從正確的學校到正確的大學、然後到正確的實習、正確的研究所、然後到你命定的天職,一整條筆直的路線。如果這是你走過的路徑,請舉手。」約有五%的人舉起了手。
「是的,」她說:「無論是哪一群人,其中都只有一到十%的人走的是直線軌道。大多數更常見的路線都是迂迴繞道的。」
「但孩子們不知道這件事,」雷文繼續說:「對孩子來說,你看起來像個天才。他們不知道你掙扎過、失敗過;這是我們對孩子隱藏的最大祕密。孩子需要聽到我們每天都會面臨的挑戰。我們應該分享自己走過的軌跡,尤其是失敗的時刻。」當父母想到自己的經驗與態度並不相稱,緊張地傻笑了起來。
雷文釋出的訊息是,我們應該提供適合孩子的機會,支持孩子成為自己,而不是試圖讓孩子符合我們認為他們應該是什麼樣的想法,而且,要擁抱嘗試和犯錯的好處。接著她分享了我們可能正在過度教養的三種形式,這些作法會在無意中導致心理傷害:
◎當我們為孩子做他們已經可以自己做的事。
◎當我們為孩子做他們幾乎可以為自己做的事。
◎當我們的教養行為,是從我們的自我出發。
雷文說,當我們採取這種教養方式,就剝奪了孩子發揮創意、解決問題、發展應對技能、建立韌性、思考什麼會令他們快樂,以及明白他們是誰的機會。簡而言之,這剝奪了他們成為一個人的機會。雖然我們過度干涉以保護孩子,實際上也達成了短期效益,但這樣的行為其實傳遞了某種極度摧毀靈魂的訊息:「孩子,沒有我,你根本無法做任何事情。」這會加重孩子的憂鬱與焦慮,甚至使他們成為攻擊者,或抱有自殺的念頭。
當雷文說完這些,室內的氣氛已經從緊張轉移成更濃重的「我們全都身陷其中」的感受。我也意識到,或許有些人已經找到勇氣,在自己家裡的餐桌上——也就是我所說最根本的基石——做出一些改變。在餐桌上,父母可以相當程度影響孩子的生活品質,即使我們不能改變家門外的社會規則。
這是父母的權利和責任,請不要退縮
「工作倫理」是要照料好基本事務以外的事。這意指主動投入以協助某種情況,即使那對你沒有直接的好處。這也跟我母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老話有關:「如果一份工作值得做,就值得把它做好。」如果建立生活技能意味著,你知道孩子可以為自己倒些柳橙汁,萬一灑出來了,他也會清理乾淨;那麼工作倫理就是指,你知道孩子會在別人灑出一些東西時,主動投入、提供協助,而不是暗想著「這不關我的事」,然後轉身走開。
我們如何要讓孩子萌生這股衝動,想去幫忙基本上跟他們無關的事?除非他們是那種難得一見,天生充滿同情心或有助人義務感的孩子,否則他們都需要被教導。要讓孩子放下做越少越好的安逸想法,轉而善盡自己的職責,以下是身為父母的我們可以做的事:
1. 以身作則。不要叫孩子去做事,而你自己卻躺在長椅上。教導工作倫理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則。主動幫忙是每個家庭成員都該做的事,不論年齡、性別或頭銜。讓孩子看到你工作,要求他們主動幫忙。當你準備在廚房、院子或車庫裡做點什麼,把孩子叫過來:「我需要你幫這個忙。」
2. 期待他們的幫助。身為父母的你不是孩子的管家,而是第一個老師。在孩子身上灌輸工作倫理的最大障礙,可能就是我們自己,尤其我們如果一向是教養光譜上放縱/放任的這一邊,十分重視孩子的幸福和享受,也深切意識到他們的家庭作業和課外活動有多麼繁重。但我們正努力要養出成年人,孩子會需要從家務中學到的技能。家事就像是職場裡的「蠢工」——那些枯燥無趣,但他們為了善盡職責、爬上升遷階梯必須做的事。他們可能會不喜歡被要求或被告知做東做西,而且肯定比較喜歡掛在手機或3C產品旁邊,或去找朋友、做其他的事,但他們會因為完成你請他們做的工作,而產生成就感。
3. 不要道歉或過度解釋。今日現代都會家庭的教養特點,就是父母一直說—說—說。正如之前所說,談論孩子在學校的一天,以解析他們體驗和學習的事物,是建立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絕佳方法;和孩子討論問題,也是幫助他們做出決定、展現你關心的良方。但是,家事是威信型父母闡明家庭規則和價值的場域。喋喋不休地說明你請他們做家事的原因和道理,或者你知道他們有多不喜歡,但他們真的需要做,還是你請他們做家事時自己感覺多抱歉,都是毫無用處的。過度解釋會讓你像是需要為自己的要求辯解。而如果你在要求孩子時、孩子執行的當下,或是孩子做完後道歉,都會削弱你身為父母的權威,因為父母有權利和責任要求孩子幫忙。短期內孩子可能會抱怨,但長遠來看他們將會感謝你。
4. 給予清楚、直接的指示。找出你想做的事,並且說出來。當這項任務對孩子是陌生的,先解釋步驟,然後退到後面。他們做的時候,不要在旁邊徘徊。不要做微觀管理。你不需要他們完全用你的方式來做,你只是讓他們去做這件事。如果你在那裡推著他們這樣做、或者那樣試,他們就學不會自己做。如果不是由他們真正親手完成,他們就不會有成就感,也不會希望再做一次,或者做更多。如果你在那兒下指導棋,他們也不會學到積極主動。讓他們嘗試、失敗,然後再試一次。告訴他們:「完成的時候讓我知道,我會過來看看你做得如何。」除非這件事有危險性而需要你的監督,不然便走開。
5. 給予適當的感謝與回饋。不要過度讚美。當孩子完成最簡單的事,例如倒垃圾、收拾碗盤、餵狗,我們常會發出:「幹得好,小子!」或「太完美了!」這種誇張的讚美。然而,一句簡單、溫和、明確的「謝謝你」或「你做得很好」就已十分足夠。把你的甜言蜜語保留下來,等到他們真的有所超越與突破,或者締造真正不同凡響的成就再來說。
也許他們做了一件不錯的差事,甚至可能做得相當好,但他們還是需要一些建設性的回饋,知道下次如何精益求精,將來在職場上也是如此。你有很多時間,能指出一、兩件他們下次可以換個方式做的事:「如果你這樣拿垃圾袋,小東西會掉下去。」或者,「你有看到你灰色襯衫上的條紋嗎?這是因為你把它和新的牛仔褲一起洗。新牛仔褲第一次最好單獨洗,不然會讓其他衣服染色。」
如果孩子沒有確實完成任務,或者做完了但品質不夠好,你需要讓他們知道。你可以說:「晚餐後的清潔工作是個好的開始。我看到你洗了碗,但那些鍋子還是得手洗,而且流理台要用抹布擦乾。」然後微笑。你不是氣他們,而是在教他們。然後再回去做你正在做的事。
當孩子越來越習慣幫忙家裡的事、開始主動投入,就更要好好運用言語、眼神接觸和肢體動作來傳達:「我注意到妳做了什麼,我真的很感激。」即使在這個時候,這樣做也就夠了。不用加油添醋。只要走開或回去做你正在做的事,你會知道孩子心裡其實很開心。6. 讓它成為例行公事。如果你設定期望,有些家事是每天做,有些是每週做,其他的是每三個月做一次,孩子會習慣生活中總有些事需要完成,而主動幫忙會讓他感覺自己有用、愉快,並得到認可。如果你一直對孩子說:「嘿,我想要你伸出援手,幫我這個忙。」而你看到他們遭遇困難時,也主動幫他們的忙,那麼,當你的孩子發現其他家庭成員、朋友、鄰居或同事有需要時,也會開始設法主動協助。
童年是被研究最多的階段,在任何稍有規模的書店,教養類書籍總是占據相當大的書架空間。對於任何關注小孩的父母(我們全都非常關注), 能立刻接收到的訊息是:保護孩子的安全與健康,是我們的職責。這是最基本的,是生物本能。
在我兒子莎耶的嬰兒相本中,有一張他七個月大時凝視著相機、臉上沒有表情的照片。相機只拍到一個小嬰兒躺在溜滑梯的斜面上,但我憶起那時我強壯的手,正從相機鏡頭外把他穩穩地撐住。
那是莎耶第一次去公園,第一次玩溜滑梯。當我看著這張照片時,依然可以聽到自己和丈夫都輕快地對兒子說:「沒問題的,寶貝,我們在這裡。」但從兒子的表情看起來,我們的說服力似乎不太夠。
這讓我回憶起那天我的小寶貝躺在溜滑梯頂端時,自己心中滿布的恐懼。那座溜滑梯離地面應該不到一百二十公分,我和先生一人站一邊,但我還是擔心。莎耶溜下那短短的距離時,會害怕嗎?他溜到底時,會不會撲到橡膠地板上,說不定還撞到頭?他會不會有不愉快的體驗, 而這是我們原本可能(或應該)預防的?
長久以來,每當我和莎耶一起坐在沙發上看著他最初的兒時照片,我總是把他眼裡的恐懼,歸結為是他的恐懼。但經過這些年以後,我開始納悶,我的寶貝會不會只是反映了他在爸爸與我的眼睛裡看到的恐懼?父母要如何從想要完全保護嬰兒,進化到讓孩子走出去,進入正在等待他們的世界?
在一個富足而且有著先進科技的世界,我們自認能確保,沒有一個孩子會受到任何傷害,對於施展控制的能力深具信心。為了孩子,我們讓世界變得更安全、更可預測、更友善。這種防護措施從孩子還在我們的子宮裡就開始了。母親懷孕時,寶寶的每個部分都被監測追蹤;孩子一旦出生,就進入完全保護他們的家庭。
然而,為人父母的我們卻更進一步,把自己當成孩子與世界之間的保險桿和護欄,彷彿只要我們在,孩子就會完全安然無恙。我會想到這件事,是因為有一天,我看到一對母子一起過馬路, 這在任何城市或鄉鎮都是常見景象。母親自信地走著,而她兒子,一個大約八歲的孩子,則落後一步,頭上戴著耳塞,一路盯著他的手機。母親先是左右看看,又朝左看了一次,然後和孩子一起穿越十字路口。孩子自始至終都沒有抬起頭來。後來,我看到一種為孩子的自行車設計的產品,稱為MiniBrake(「迷你煞車」),可以讓父母透過遙控器,在孩子騎車接近繁忙的交通要道時,控制自行車的後輪煞車。
當孩子還小時,我們護送他們到學校,確定他們是安全的,而且常幫忙拿東西,減輕他們的負擔。最近,我看到一個爸爸寬厚的肩膀上掛了一個淺粉紅色的書包,他踩著腳踏車,跟在他那頂多七、八歲的女兒後面,騎到離家三個街區外的當地小學。看到這一幕,我忍不住輕聲笑出來。這個畫面很可愛。但是,那天下午,以及更多之前與之後的下午,我不禁想著,孩子要長到什麼年紀,才有能力拿自己的東西?對於一個小學生來說,什麼程度的獨立才是適切的?
然後是手機。這是親子溝通過程中新近的發展,所以並非是導致直升機教養的成因,但只要這種趨勢存在,確實會助長父母盤旋的能力。研究人員稱它為「全世界最長的臍帶」。
例如,有個比佛利山莊高中學生的母親,堅持要兒子在跟朋友到海邊玩的去程與返程中,每小時傳簡訊給她。讓她擔心害怕的是行車安全,而不是在太平洋裡衝浪。另外,有一位史丹佛的家長打電話給學校,說他認為女兒失蹤了,因為他已經超過一天沒有她的訊息。還有一位到紐西蘭參加海外學程的美國大學生的家長,打電話給計畫主任,非常擔心她兒子自從到山上健行返校之後,就沒有接聽電話(她知道他已經回到校園,因為是GPS告訴她的)。
父母的警覺與科技,為我們的孩子緩衝了世界的撞擊,但我們不可能永遠為他們守望。養育小孩獨立自主,是我們生物上的必然,而在環境中認識自己,是孩子需要發展的重要生活技能。當我們試圖讓自己的存在成為守護他們的保證,我們必須要問,這是為了什麼?我們要如何預防和保護,同時又教導孩子所需的技能?我們該如何教他們自己完成這些事?給他們機會練習失敗
父母一直想為孩子處理生活上的雜事:叫他們起床、接送、提醒期限和該做的事、繳帳單、問問題、做決定、承擔責任、與陌生人說話以及面對權威人士等,孩子一旦被鬆綁而進入大學或職場時,可能會受到相當的驚嚇。他們將體驗挫折,感覺自己像個失敗者。而殘酷的反諷是,他們將無法好好應付這種失敗,因為他們向來沒有太多機會練習失敗。
當一個看似身心完全健康,但受到過度教養的孩子上了大學,而且不知如何因應可能遇到的各種新狀況:和他對「乾淨」有不同認知的室友;要求修改報告,但不會具體說明哪裡「有錯」的教授;想參加暑期研討會或服務計畫,但不能兩者都參加的選擇……他們可能會面臨真正的困難,不知道如何處理分歧、不確定性、情感受傷,或者如何決策的過程。沒有能力處理事情——調適不安、思考選項、和某人詳談、做決定——本身就成為問題。
凱倫.艾伯博士是中西部一所公立大學輔導與心理服務中心的專任心理醫師,她根據臨床經驗表示:「過度教養嚴重傷害了大學生的心理健康,使他們無法在向父母諮詢與獨立做決定之間取得平衡。」
她說明了自己會如何與學生展開會談。「剛開始他們會覺得,如果自己需要幫助,就應該立即與父母聯繫。從心理學來看,我們知道他們不是真的需要協助,如果他們可以熬過不知所措的苦惱與焦慮,基本上就是在練習這種技能,而且到了某個時間點就能學會自己解決。我會與學生一起練習他們尚未具備的批判思考、信心與獨立技能。但如果他們最後還是打電話或發訊息給父母,就不是以我對他們的期望來練習這些技能,這也意味著他們還是沒有獲得這些技能。」
我們並不是建議成年孩子永遠別打電話給父母。惡魔就在談話的細節裡。如果他們打電話來問問題、或不知如何做決定,我們是告訴他們該怎麼辦?或者,我們會仔細聆聽,根據對情況的認知問一些問題,然後說:「所以,你認為該怎麼處理?」
在事事都需要求助的問題背後,潛伏的隱憂是學生無法自外於父母而建立自我。「當孩子沒有被給予空間,靠自己的努力通過考驗,便無法好好學習解決問題。他們無法學會對自己的能力保持信心,而這可能影響他們的自尊。從來不必奮鬥的另一個問題是,你就無從經歷失敗,而且對失敗、讓他人失望感到無比恐懼。低度自信和恐懼失敗,都可能導致憂鬱或焦慮。」艾伯說。
心理學家兼作者麥德琳.雷文博士(Dr. Madeline Levine)因暢銷書《給孩子,金錢買不到的富足》躍升為全國知名人物並進行巡迴演講。她提醒父母要冷靜下來退一步想,潛伏在孩子生命中最大的傷害,恐怕是父母為孩子做了太多,因而導致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受損。
在二○一四年一月的演講中,雷文曾以一段觀念為到場聆聽的父母熱身:「現在有個廣為流傳、很有說服力的故事,說成功是從正確的學校到正確的大學、然後到正確的實習、正確的研究所、然後到你命定的天職,一整條筆直的路線。如果這是你走過的路徑,請舉手。」約有五%的人舉起了手。
「是的,」她說:「無論是哪一群人,其中都只有一到十%的人走的是直線軌道。大多數更常見的路線都是迂迴繞道的。」
「但孩子們不知道這件事,」雷文繼續說:「對孩子來說,你看起來像個天才。他們不知道你掙扎過、失敗過;這是我們對孩子隱藏的最大祕密。孩子需要聽到我們每天都會面臨的挑戰。我們應該分享自己走過的軌跡,尤其是失敗的時刻。」當父母想到自己的經驗與態度並不相稱,緊張地傻笑了起來。
雷文釋出的訊息是,我們應該提供適合孩子的機會,支持孩子成為自己,而不是試圖讓孩子符合我們認為他們應該是什麼樣的想法,而且,要擁抱嘗試和犯錯的好處。接著她分享了我們可能正在過度教養的三種形式,這些作法會在無意中導致心理傷害:
◎當我們為孩子做他們已經可以自己做的事。
◎當我們為孩子做他們幾乎可以為自己做的事。
◎當我們的教養行為,是從我們的自我出發。
雷文說,當我們採取這種教養方式,就剝奪了孩子發揮創意、解決問題、發展應對技能、建立韌性、思考什麼會令他們快樂,以及明白他們是誰的機會。簡而言之,這剝奪了他們成為一個人的機會。雖然我們過度干涉以保護孩子,實際上也達成了短期效益,但這樣的行為其實傳遞了某種極度摧毀靈魂的訊息:「孩子,沒有我,你根本無法做任何事情。」這會加重孩子的憂鬱與焦慮,甚至使他們成為攻擊者,或抱有自殺的念頭。
當雷文說完這些,室內的氣氛已經從緊張轉移成更濃重的「我們全都身陷其中」的感受。我也意識到,或許有些人已經找到勇氣,在自己家裡的餐桌上——也就是我所說最根本的基石——做出一些改變。在餐桌上,父母可以相當程度影響孩子的生活品質,即使我們不能改變家門外的社會規則。
這是父母的權利和責任,請不要退縮
「工作倫理」是要照料好基本事務以外的事。這意指主動投入以協助某種情況,即使那對你沒有直接的好處。這也跟我母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老話有關:「如果一份工作值得做,就值得把它做好。」如果建立生活技能意味著,你知道孩子可以為自己倒些柳橙汁,萬一灑出來了,他也會清理乾淨;那麼工作倫理就是指,你知道孩子會在別人灑出一些東西時,主動投入、提供協助,而不是暗想著「這不關我的事」,然後轉身走開。
我們如何要讓孩子萌生這股衝動,想去幫忙基本上跟他們無關的事?除非他們是那種難得一見,天生充滿同情心或有助人義務感的孩子,否則他們都需要被教導。要讓孩子放下做越少越好的安逸想法,轉而善盡自己的職責,以下是身為父母的我們可以做的事:
1. 以身作則。不要叫孩子去做事,而你自己卻躺在長椅上。教導工作倫理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則。主動幫忙是每個家庭成員都該做的事,不論年齡、性別或頭銜。讓孩子看到你工作,要求他們主動幫忙。當你準備在廚房、院子或車庫裡做點什麼,把孩子叫過來:「我需要你幫這個忙。」
2. 期待他們的幫助。身為父母的你不是孩子的管家,而是第一個老師。在孩子身上灌輸工作倫理的最大障礙,可能就是我們自己,尤其我們如果一向是教養光譜上放縱/放任的這一邊,十分重視孩子的幸福和享受,也深切意識到他們的家庭作業和課外活動有多麼繁重。但我們正努力要養出成年人,孩子會需要從家務中學到的技能。家事就像是職場裡的「蠢工」——那些枯燥無趣,但他們為了善盡職責、爬上升遷階梯必須做的事。他們可能會不喜歡被要求或被告知做東做西,而且肯定比較喜歡掛在手機或3C產品旁邊,或去找朋友、做其他的事,但他們會因為完成你請他們做的工作,而產生成就感。
3. 不要道歉或過度解釋。今日現代都會家庭的教養特點,就是父母一直說—說—說。正如之前所說,談論孩子在學校的一天,以解析他們體驗和學習的事物,是建立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絕佳方法;和孩子討論問題,也是幫助他們做出決定、展現你關心的良方。但是,家事是威信型父母闡明家庭規則和價值的場域。喋喋不休地說明你請他們做家事的原因和道理,或者你知道他們有多不喜歡,但他們真的需要做,還是你請他們做家事時自己感覺多抱歉,都是毫無用處的。過度解釋會讓你像是需要為自己的要求辯解。而如果你在要求孩子時、孩子執行的當下,或是孩子做完後道歉,都會削弱你身為父母的權威,因為父母有權利和責任要求孩子幫忙。短期內孩子可能會抱怨,但長遠來看他們將會感謝你。
4. 給予清楚、直接的指示。找出你想做的事,並且說出來。當這項任務對孩子是陌生的,先解釋步驟,然後退到後面。他們做的時候,不要在旁邊徘徊。不要做微觀管理。你不需要他們完全用你的方式來做,你只是讓他們去做這件事。如果你在那裡推著他們這樣做、或者那樣試,他們就學不會自己做。如果不是由他們真正親手完成,他們就不會有成就感,也不會希望再做一次,或者做更多。如果你在那兒下指導棋,他們也不會學到積極主動。讓他們嘗試、失敗,然後再試一次。告訴他們:「完成的時候讓我知道,我會過來看看你做得如何。」除非這件事有危險性而需要你的監督,不然便走開。
5. 給予適當的感謝與回饋。不要過度讚美。當孩子完成最簡單的事,例如倒垃圾、收拾碗盤、餵狗,我們常會發出:「幹得好,小子!」或「太完美了!」這種誇張的讚美。然而,一句簡單、溫和、明確的「謝謝你」或「你做得很好」就已十分足夠。把你的甜言蜜語保留下來,等到他們真的有所超越與突破,或者締造真正不同凡響的成就再來說。
也許他們做了一件不錯的差事,甚至可能做得相當好,但他們還是需要一些建設性的回饋,知道下次如何精益求精,將來在職場上也是如此。你有很多時間,能指出一、兩件他們下次可以換個方式做的事:「如果你這樣拿垃圾袋,小東西會掉下去。」或者,「你有看到你灰色襯衫上的條紋嗎?這是因為你把它和新的牛仔褲一起洗。新牛仔褲第一次最好單獨洗,不然會讓其他衣服染色。」
如果孩子沒有確實完成任務,或者做完了但品質不夠好,你需要讓他們知道。你可以說:「晚餐後的清潔工作是個好的開始。我看到你洗了碗,但那些鍋子還是得手洗,而且流理台要用抹布擦乾。」然後微笑。你不是氣他們,而是在教他們。然後再回去做你正在做的事。
當孩子越來越習慣幫忙家裡的事、開始主動投入,就更要好好運用言語、眼神接觸和肢體動作來傳達:「我注意到妳做了什麼,我真的很感激。」即使在這個時候,這樣做也就夠了。不用加油添醋。只要走開或回去做你正在做的事,你會知道孩子心裡其實很開心。6. 讓它成為例行公事。如果你設定期望,有些家事是每天做,有些是每週做,其他的是每三個月做一次,孩子會習慣生活中總有些事需要完成,而主動幫忙會讓他感覺自己有用、愉快,並得到認可。如果你一直對孩子說:「嘿,我想要你伸出援手,幫我這個忙。」而你看到他們遭遇困難時,也主動幫他們的忙,那麼,當你的孩子發現其他家庭成員、朋友、鄰居或同事有需要時,也會開始設法主動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