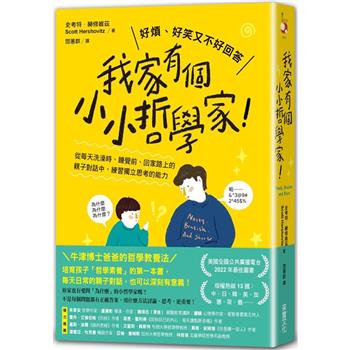第一章 權利:為什麼不能全照我想的做?
我很喜歡放洗澡水,但不是我自己要泡澡,因為我是個在上世紀社會化的直男,所以我不泡澡,而且我的情緒表達也很簡單。但我兒子喜歡泡澡,而且必須有大人幫他們放好洗澡水,所以我會儘量爭取做這個工作。
為什麼?因為浴缸在樓上,而樓下是個吵翻天的瘋人院,當孩子越來越疲憊時就會越來越躁動,他們的自制力蕩然無存,吵嘈程度直逼搖滾音樂會。一下子有人大喊著該練琴了,或是沒時間練琴了;接著有人大喊我們還沒吃甜點,或是我們已經吃過甜點了,但是弟弟把甜點沾到衣服上了;再來是莫名其妙地尖叫,尖叫是宇宙的常態。
像這種時候,我就會選擇遁逃到樓上。「我去幫漢克放洗澡水囉。」說完後立刻衝上樓,接下來便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光,我關上浴室門,打開水龍頭,用手試試水溫,不能太熱也不能太冷。我來來回回地用手攪水,好像真有辦法把水調到適溫,但不管我多用心,最後水溫總是被嫌太熱或太冷,因為孩子拒絕接受不矛盾法則。雖然我的服務注定無法讓太子爺滿意,但我很淡定,因為在浴室裡聽不見尖叫聲,我可以坐在浴室的瓷磚地板上,與我的思想獨處(其實就是手機啦)。
但我老婆識破了我的詭計,所以有時她會先發制人:「我來幫漢克放洗澡水。」這句話立刻令我的靈魂崩潰,因為她是個在上世紀社會化的直女,所以她會白白浪費這個獨處的大好機會。她打開水龍頭開始放水後,不是趁著水滿前的空檔滑手機,而是跑去做其他家事,例如洗衣服。我知道我應該慚愧,但獨處真的是為人父母者負擔得起的最佳奢侈品,反正,總得有人享受這段忙裡偷閒的時光,要是老婆大人沒空享受,那就我來囉。
正當我坐在浴室的地板上滑手機時,朦朧間感覺到樓下的騷動程度更勝於平時,五歲的漢克正在哭天搶地,肯定是發生了天大的小事。浴缸的水也快滿了,我只好把水龍頭關掉,寧靜時光到此為止。
我在樓梯上大喊:「漢克,洗澡水放好了。」
沒有回應。
我在他的尖叫聲中又喊了一次:「漢克,洗澡水放好了。」
他哥哥雷克斯非常滿意地接著喊道:「漢克,洗澡水放好了。」
接著他媽媽很生氣地喊道:「漢克,洗澡水放好了!」
然後我聽到了嗚咽聲,小傢伙正一步一步慢吞吞地爬上二樓,精神恍惚地走進浴室。
我試圖讓他平靜下來,輕聲地對他說:「漢克,怎麼啦?」沒有反應,我更輕聲地問他:「漢克,發生什麼事了?」他還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我幫他脫掉衣服,最後他終於進了浴缸,我再問一次:「漢克,你到底怎麼了?」
「我……我沒……我沒有……」
「你沒有什麼,漢克?」
「我沒有任何權利!」漢克又開始嚎啕大哭。
「漢克,」我再度輕聲細語地希望能安撫他,不過我現在更好奇了,「什麼權利?」
「我不知道,」他抽抽噎噎地說,「但我什麼都沒有。」
孩子擁有權利嗎?
這次,漢克確實需要一個哲學家,而他很幸運,眼前就有一個。
「漢克,你有權利啊。」
這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還稍微止住了他的淚水。
「漢克,你真的擁有權利啊,而且很多哦。」
「我有嗎?」漢克的情緒總算平靜了些。
「你有,你想了解它們嗎?」
他點了點頭。
「那好,我們就來聊聊虎子吧。」虎子是從漢克出生後,就一直陪伴他的小白虎絨毛玩具,「別人可以把虎子從你身邊帶走嗎?」
「不行。」
「別人可以沒問過你就和虎子玩嗎?」
「不行,虎子是我的。」漢克的淚水幾乎快要止住了。
「沒錯,虎子是你的,這就表示你對它有權利,除非你說可以,否則沒有人可以帶走虎子,或是和它一起玩。」
「但有人能帶走虎子。」漢克提出反駁,而且眼淚似乎又要流下來了。
「你說得沒錯,確實有人能帶走虎子,但那麼做是對的?還是錯的?」
「是錯的。」
「你說對了,這就是擁有權利的意思;如果有人帶走虎子是錯的,那麼你就有權利不讓他們這麼做。」
漢克的小臉終於亮了起來:「我對我所有的物動擁有權利!」他還故意把動物講成物動,來逗我開心。
「你說得沒錯!你確實擁有權利!這就是它們屬於你的意思。」
「我對我所有的玩具擁有權利!」漢克開心地說著。
「是的,你有!」
但是,他那可愛的小臉突然又垮了下來,而且還開始抽泣。
「漢克,你為什麼這麼難過?」
「因為我對雷克斯沒有權利。」
原來這就是剛才樓下鬧哄哄的根源,漢克想和雷克斯一起玩,但雷克斯想讀書,而漢克確實對雷克斯沒有權利。
我趕緊解釋:「是的,你對雷克斯沒有權利,他可以決定他是否想玩;除非別人對我們做出承諾,否則我們無法對其他人主張權利。」
這樣的說明有點過於簡化,因為有時候即使別人沒有對我們做出承諾,我們仍可對他們提出要求。不過,我決定等漢克不那麼心煩意亂的時候,再好好跟他說個分明。所以現在我只告訴漢克,當雷克斯想讀書時,漢克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事。
漢克在淚眼婆娑間對權利做了一番敏銳的觀察。我一開始便問他,是否有人可以未經他的允許帶走虎子,他說不能;但他隨即想到,還是有人有辦法未經他的允許便帶走虎子,其實這就是之前漢克對雷克斯幹的「好事」。
虎子本來是雷克斯的,而且雷克斯把它命名為傑瑞非;當漢克剛學會爬時,他一有機會就爬到雷克斯的房間,然後用下巴夾住傑瑞非,並以最快的速度溜走。雷克斯對傑瑞非的權利,明明一點也不輸給漢克對虎子的權利,但漢克還是搶走了傑瑞非。
這件事對權利有什麼啟示?漢克對虎子的權利,保護了他對虎子的占有,但這種權利提供的保護不是「物理性」的,在虎子的周圍,沒有任何力場可以阻止其他人奪走他。用哲學家的話來說,權利提供的保護是「規範性」(normative)的,也就是說,它是由規範良好行為的常規或標準所產生的。一個行事正派的人,不會未經漢克的允許便拿走虎子(除非他能提出一個很好的理由,我們稍後會再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奉公守法、行事端正,所以權利所提供的保護,繫乎於其他人是否願意承認和尊重它。
在我們繼續深入探討之前,我先簡單說明一下有些人會過度拘泥於文字的情況。我問漢克,是否有人「可以」在未經他允許的情況下帶走虎子,他說不可以,然後他想了一想後又說「能」,他第一次的說法是對的,第二次也是對的。
何以如此?這是因為「can」和「could」這種字眼太有彈性了,各位且先聽我說個小故事,就能明白我想要表達的意思。
當年,我還在牛津大學念書時,有個朋友帶我去他們學校的酒吧。他跟吧檯點了兩杯啤酒。
酒保說:「大哥,不好意思,我們已經打烊了。」
我的朋友看了看他的手錶,當時是晚上十一點零一分,酒吧的打烊時間是十一點。
「別這樣,就來兩杯啤酒嘛。」
「抱歉,不行啦(can’t),這是規定。」
「欸,你可~以~的(coooould)。」我的朋友說。
故事就說到這裡。我的朋友是在說那個酒保不懂「could」這個字的意思嗎?當然不是,他刻意用那冗長的「coooould」是要告訴酒保,他不賣酒給我們是「不為也」,而非「不能也」。雖然酒保說沒有老闆的允許(permissible),他是不能賣酒給我們的,但我的朋友點出了賣酒給我們是可能的(possible),因為旁邊並沒有其他人,所以他不會被舉報。結果我的朋友說服成功,那酒保給了我們兩杯啤酒,因為他能(不會被發現),所以他便順勢而為了。
我跟漢克的對話也有同樣的情況,他明白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在問他,是否有人可以(在未獲得允許的情況下)帶走虎子,所以他正確地回答說不可以。但他又想到有人「可能」會帶走虎子,所以他才又開始哭了起來。
為什麼要對文字如此吹毛求疵呢?因為這就是哲學家的工作,我們非常注意文字的運用方式,況且,各位肯定遇過那種覺得這樣回話很厲害的人──
你很有禮貌地問:「我能(Can I)喝杯茶嗎?」
「你能嗎?這我可不知道。」
那個人認為你應該更客氣地問:「敝人在下我能否(May I)喝杯茶呢?」這傢伙是個混球,把他從你的人生中剔除吧,並且告訴他應該向一個幼兒學習英語,因為他的英語還不如一個小娃兒呢。
權利是一種關係
現在話題回到權利上,權利到底是什麼?這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的。某天,我跟漢克又聊到了這個話題,當時八歲的他花了一下午打掃房間,然後邀請我去看他的成果。
「哇,看起來好棒啊。」我說。
「謝謝!差不多所有的東西都收好了。」
「那你把你的權利放在哪裡了?」我問。
「什麼意思?」
「你的權利啊──比如你對虎子的權利,你放在哪裡?」
「那個我沒有把它收起來,它在我的身體裡。」
「是嗎?在哪裡?在你的肚子裡嗎?」
「不是,它不在一個特定的地方,它只是在我的身體裡。」
「你為什麼不把它拿出來?放在身體裡很重吧。」
「它不是那種你可以拿在手上的東西。」
「那你能用打嗝把它弄出來嗎?」
「不能,權利是不能打嗝打出來的。」
說完他就跑了,所以我倆仍未弄清楚權利究竟是什麼,唯一確定的是我們沒辦法把它們嗝出來。
接下來就由我來完成這個任務吧,漢克只說對了一半,權利並不是那種你可以拿在手上的東西,但權利也不在你的身體裡,權利是一種關係。
請容我解釋給你聽,假設你有個權利是我必須付給你一千美元,那麼你的權利就是對這筆錢的支付請求(claim),這個請求是針對我的,如果我是唯一欠你錢的人,那就只有我必須付錢給你;但有時你的權利會及於好幾個人(例如茱莉和我都欠你錢),有時候你擁有的權利甚至及於所有人,例如你有個不被打臉的權利,要是任何人提出要打你的臉,你可以提醒他們有義務不能這麼做。
正如上段的最後一句話所示,當你擁有某個權利時,別人就會有個義務,所以我才會說權利是一種關係。每項權利至少有兩個當事人:權利擁有者和義務承擔者,權利和義務永遠結伴同行,它們是從不同當事人的角度來描述的同一關係。
這種關係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可以從我一直以來最喜歡的哲學家之一茱蒂斯.賈維斯.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那裡得到幫助,她是位倫理學專家,很會設計思想實驗──那是哲學家用來測試想法的短篇故事,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她寫的一些故事,不過湯姆森的權利理論也很有名。
湯姆森指出,當你擁有一項權利時,你就會跟承擔相應義務的人處於一種複雜的關係中。此一關係有許多特點,僅舉其中幾個例子:假設我得在下週二還你一千美元,要是我認為到時候恐怕付不出錢來,那麼我該預先警告你;如果時間到了,而且我真的沒付錢,那我就該向你道歉,並尋求用某種方式補償你。但最重要的是,在其他條件都沒變的情況下(all things equal),我應該如期在下週二付給你一千美元。
我說「在其他條件都沒變的情況下」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哲學家用來說明「天有不測風雲」的一種說法。我必須在週二付給你一千美元,現在週二已經到了,結果我需要用那筆錢來付房租,否則我們全家就要露宿街頭,我該付你錢嗎?或許吧,如果我沒付你錢,你遭受的痛苦可能比我更大;但如果你沒什麼大麻煩,那麼我就該拿這筆錢去付房租,並為了沒有付錢給你而鄭重道歉,並想辦法盡快補償你。
道德哲學中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究竟要發生多大的事才能凌駕一項權利?其中一個答案是:其實不多,只要忽視這項權利會比尊重它獲得更好的結果,或許我們就該忽視它。根據這個觀點,如果打我臉產生的好處多於壞處,那你就該打下去。
有些人覺得這個觀點很有道理,但請大家注意,這麼一來,權利就變得無關緊要了,與其擔心誰擁有什麼權利,還不如直接問:「你正在考慮的行動,會產生好結果還是壞後果?」如果是好結果,那就去做;如果是壞後果,那就別做了。權利並不會影響你該做什麼。
此種觀點被稱為後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因為它主張一個行為的道德地位取決於其後果。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是大家最熟悉的後果主義,它主張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追求福祉(welfare)或效益(utility)的最大化,所以它有時也被稱為效益主義。功利主義是什麼?它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最常見的觀點是:這是宇宙中快樂與痛苦的平衡。如果你想知道該不該打我的臉,某種類型的功利主義者會鼓勵你,只要想想人們在打臉之後體驗到的快樂,是否會超過此事帶來的痛苦即可,權利完全沒有被列入考慮。
但美國法學家朗諾.德沃金(Ronald Dworkin)並不喜歡用那樣的方式思考道德,所以他寫了《認真對待權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一書(德沃金堪稱是過去數十年來最有影響力的一位法律哲學家,我的哲學工作在某些方面便是延伸自他的主張)。德沃金從紙牌遊戲(例如橋牌)借用了一個概念,來解釋權利的相關性。他曾在一場道德辯論中指出,權利的地位高過對福祉的關注。
想要了解德沃金的想法,請看這個通稱為「器官移植」的故事:你在某家醫院工作,你有五個亟需做器官移植的病人,每個人需要的器官都不一樣,要是他們不能立刻得到需要的器官,五個人都會死。此時,有個男人走進了急診室,他只是手臂骨折,並沒有生命危險,但你心中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殺了他,你就可以摘取他的器官,拯救其他五個人。你問他是否介意,他說他非常介意。
你應該這麼做嗎?雖然這件事可以這麼說:失去一人的生命,讓整體(五個人)的福祉增加,但那又怎樣?此人擁有活下去的權利,而他的權利高過其他病人的福祉。
要讓五個人死,還是讓一個人死?
但真是這樣嗎?我們現在來到了當代哲學中最難解的難題之一──「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
要搞懂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故事──我們需要湯姆森的故事,第一個故事稱為「轉轍器旁的路人甲」,故事是這樣的:
軌道上有輛剎車失靈的電車,正朝著五名工人飛馳而去,那五名工人正在前方施工,如果電車繼續行駛,就會撞死這五人。好消息是你就站在轉轍器附近,你可以讓電車轉到另一條軌道上;但壞消息是──那條軌道上也有一名工人在施工,如果你讓電車改道,他肯定會死。
你會怎麼做?
大多數人會選擇讓電車轉換軌道,這樣電車就只會壓死一個人,而不是五個人。
且慢!剛剛的「器官移植」案不是才說過,那個人的生存權高於別人的福祉,所以不能為了拯救其他五個人而殺死他,那為什麼同樣孤身一人的電車工人,卻沒有同樣的生存權?
我最近剛好教到電車難題,因為是在我家上課,所以我兒子也可以旁聽,他們用玩具火車的零件組,打造了「轉轍器旁的路人甲」的場景。他們還會在我們討論到故事的變化時,幫忙調整模型。
但他們最喜歡的故事是湯姆森所寫的「胖子」(這個名字確實不好聽,但他的肥胖是案情的關鍵)。故事是這樣的:同樣有輛失控的電車朝著五名工人駛去,但這次你不是站在轉轍器旁,而是站在一座天橋上,目睹整個事件的發展;然後你注意到旁邊有個胖子就靠在欄杆上,如果你推他一把,他就會墜落在軌道上,他的龐大身軀應當能讓電車停下來,並且救下那五名工人,胖子即便不是當場摔死,也會被電車撞死。
你會怎麼做?把胖子推下去以便拯救五名工人?還是任憑電車壓死那五名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