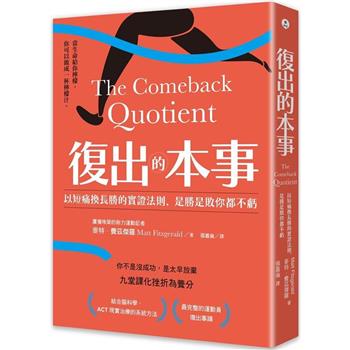6從不幸的厄運再起
如何成為打不倒的野獸
潔咪・惠特摩爾的故事真正體現了人如何從不幸的厄運中東山再起。她的復出歷程有四個特點,可作為我們效仿的榜樣。其中三項特點——控制可控的事物、坦然面對不確定性和賦予敘事,我們在前幾章已有涉獵,不過值得檢視一下它們在不幸的厄運中具體應用的範例。另一項特點是沒有特權(non-entitlement),這是新的概念,在面對不幸的厄運時,尤其有助於正視現實。
一、沒有特權
出問題時,許多人總會問:「為什麼是我?」超越現實者不然。會有此提問,通常源自於隱藏的特權意識(entitlement)——自以爲特別,所以壞事不會臨頭。此種心態讓人難以接受現實的困境,更別說要盡力化險為夷了。潔咪如同我們所有人,並不喜歡事情出錯,但她也不認為必須解決不是她造成的問題有損尊嚴,我們也應該如此。
我問潔咪,對她來說,身為身障運動員獲勝,是否和擊敗世界頂尖的健全運動員一樣重要。她回答,確實如此。有鑑於她先前對我所述的萊德維爾一百英里登山車大賽的經歷(「對我來說,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我相信她的話。至於她的抗癌歷程,潔咪邊喝著加了打發鮮奶油的白摩卡邊說:「我只允許自己每天替我的處境難過或生氣十五分鐘,再多也不會有任何幫助。憤怒不會讓你成為世界冠軍。」或救你一命。
二、專注於可控的事物
面對困境時,人很容易聚焦在眼前的問題,但把注意力放在尋找解決方案上會更有幫助。不妨再度回想,二〇〇二年XTERRA世界錦標賽時,潔咪和當地分齡組選手在自行車賽轉換至路跑時,裝備袋都遺失了,但兩人反應天差地別。另一名選手過度執著於問題,像燈罩裡的飛蛾一樣,搞得帳篷裡雞飛狗跳,但問題並沒有解決,而潔咪則專心於解決問題,盡其所能協助大家化解難關。
潔咪向我解釋:「我的個性一直都是會問『有什麼是我能控制的?』的人。即使罹癌,我也是自問『好吧,我能做什麼?』,畢竟無能為力的事實在太多了。」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之中,相對較少有人會有因疾病而永久改變身體或運動能力的經歷,但即便是面對更常見的問題,如過度使用造成的傷害等,專注於解決方案也能帶來重大影響。例如,許多跑者在診斷出足底筋膜炎後,會花許多時間沉浸在無法跑步的沮喪當中,除了不跑步之外,幾乎沒有採取其他方法解決問題。但是,潔咪診斷出足底筋膜炎後,她尋求治療,全心接受物理治療,並進行交叉訓練,盡可能地減低受傷對她大學跑步生涯的影響。
三、坦然面對不確定性
面臨困境時,雪上加霜的並不總是只有痛苦、壓力或失望,通常還有不確定性。當事情不太對勁,而我們不確定問題獲得解決的時間點或方式時,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壓力來源。但並非所有運動員都會因為不確定性而備感壓力。
若要我用一句話來形容潔咪的心態,我會選擇「我會想到辦法」。我們在咖啡館共度的九十分鐘裡,她重複了這句話無數次。從她年輕時尋找真正擅長的運動,到她罹癌後重新回歸自行車的努力,這句話概括了潔咪面對問題的一貫態度。她在擺脫癌症但尚未重新開始騎車時,告訴一名採訪人員:「就算有人跟我說這不可能,我也不信世上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法。我告訴家父,『也許我再也無法從甲地直接抵達乙地,但我無論如何都會從甲地到達乙地。』」
因為不確定性而感到壓力,絕大部分是選擇,而非必然。基本上,這就是在說,「除非我現在確知如何從甲地到乙地,否則我會假設自己永遠不會知道」。超越現實者不會以這種方式扭曲現實,我鼓勵各位以他們為榜樣。若不知道,就接受這種不確定性,並專心致力於找出解決方法。
四、賦予敘事
我在第四章中,曾提及超越現實者傾向為所經歷的創傷賦予新的敘事,將其重塑為個人歷程中有意義的插曲,藉此發掘其中的益處。潔咪正是從基督徒的角度這樣做,她告訴我:「我相信自己遭遇的一切都有其目的。我的痛苦有目的,我的挫折也有目的。也許有人聽聞我的經歷和克服的困難,會因此對他們有所幫助。」
使用這項工具,就是將你的生活當作一則故事,而你是故事的作者,抑或至少是共同作者,你有能力將看似不快樂的結局,變成通往幸福結局的另一篇章。潔咪雖然歷經磨難和失去,但她深信自己正過著她的幸福結局。為何不呢?一切都出自她的選擇。
(部分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