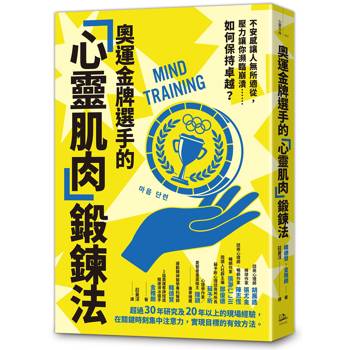【摘文1】陷入自我貶低的人
某天,一位綽號叫做「亞軍專家」的高爾夫選手來找我諮詢。成為職業高爾夫選手已經四年的她,雖然被視為一位實力和人品兼具的選手,每次卻都距離冠軍寶座只差一步。因為在最後一輪的比賽中,她總是會犯下荒唐的失誤,最後被擠到第二或第三名。
她來找我的那天,又是一個錯失冠軍的日子。首日與外國選手並列領先地位的她,卻在第二天因為惡劣天氣退居第四。雖然最後一天成功減少一桿,但是僅此而已。最終再度屈居亞軍的她,實在是氣憤不已。
出現所謂「二把手魔咒」的原因是,在關鍵時刻,執行能力卻反而下降。如果這種失敗反覆發生,每次比賽都會陷入可能犯下失誤的不安,注意力也會更難集中。
成為職業選手後,她共參加了八十場比賽。雖然有三十幾次進入前十名的紀錄,卻總是與冠軍無緣。因為每次比賽時,發球、鐵桿擊球、推桿等動作都會輪流出現問題。在比賽執行能力上沒有太大問題的她,只能認為是自己「運氣不好」,所以更加鬱悶。
在她剛開始打高爾夫沒幾年的時候,身邊許多人都對當時年幼的她讚不絕口,認為如果她成為職業選手,一定無人能敵。實際上,她也以優異的成績,比同齡選手更早成為職業高爾夫球選手。
然而,這就是問題所在。小小年紀就必須和在電視或雜誌上看到的優秀選手們比賽,這樣的壓力阻礙了她的發展。每次比賽都承受著巨大壓力的她,連自己的主要絕技──發球都沒能發揮出來,鐵桿擊球的機率也降低了。更嚴重的是,在業餘時期不曾出現過的失誤也越來越多。在這之後,她的隊友開始用「膽子不夠大」、「膽小如鼠」等方式形容她,而她自己也開始產生這樣的想法。這是一種自我貶低。
「自我貶低」的另一種說法就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貧乏」。自我概念是辨別並評價自己的心理學用語。通常,自我概念會透過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小時候的對象是父母,不過在長大後,對象會無時無刻發生變化。
人們常說:「環境對一個人來說很重要。」這是因為形成自我概念的環境將決定認同感。這樣的自我概念比起外部環境,更容易被內在力量的影響。因為接受並調整與外部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主體就是自己。
因此,自我概念的中心是「自我」(self)。盛裝「我」的第一個器皿就是自己。這個概念如果貧乏或充斥著自我貶低,連定義認同感的後續資訊也會被污染。就好比朝著被油覆蓋的大海注入頂級的清水,這麼做不僅無法淨化大海,反而會增加受污染海水的體積。自我概念也可以用相同的道理來解釋。
不僅運動員容易掉入自我貶低陷阱,身為有經驗者進入通訊公司的民九也因為同樣的理由來找我諮詢。他從外縣市的大學畢業後,任職於首爾的某家新創企業累積經驗。後來,他被與該公司有合作關係的大型通訊公司相關人士挖角後離職。因為跳槽到大企業,當時的他被很多人羨慕,不過進入該公司第二年的他再次考慮跳槽。
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們中,「學歷最差的畢業於首爾大學,最優秀的則來自哈佛大學」,這項事實讓他過得很辛苦。雖然他也自認具備競爭力,但是職場生活並不容易。在撰寫報告書、進行會議、做出決策、執行專案等方面沒有取得什麼成果後,他開始為自己設下限制。
像這樣失去自信後,民九雖然正在開發好的技術,卻無法在做重要的報告時,向公司高層展示自己的成果。「比我優秀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就算我做得再好,你有可能會認可我嗎?」這種失敗感讓他裹足不前。
每年都止步於亞軍的高爾夫選手,以及在進行重要的報告時經常滑鐵盧的上班族,這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讓人在關鍵時刻投降的「怪物」不是別人,而是自己製造出來的事實。
乍看之下,似乎是「那個選手很膽小」、「他為什麼一上台報告就那麼緊張」之類的言語讓他們感到畏縮。但是,為別人的影響出一份力的正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不傾聽自己的內心,反而為別人裝上擴音器,才會養大心中的怪物。
經常自我貶低的人擁有的特徵之一,就是完全接受對方的話。他們不會考慮對方說的話是否妥當,而是直接選擇全盤接受,結果卻壓迫了自己,招致不好的結果。如果是因為客觀的實力和練習量不足,而造成不理想的結果,那只需要努力填補這一部分就可以了。然而,若是心理因素導致反覆失敗,就應該先找出造成心理壓力(under pressure)的原因,並尋求解決對策。
【摘文2】擺脫嚴重的「預期性」焦慮
「每當心臟劇烈跳動的時候,我都覺得胸口快要爆炸了。」
「呼吸越來越困難,感覺快要不能喘氣了。」
「雖然很難用言語形容,但是我的心裡有一股非常不好的感覺,陷入好像會發生某種嚴重錯誤的恐懼之中。」
有些人帶著一副快沒命的表情,來到診療室求助。他們是患有「恐慌症」的人。只要經歷過一次恐慌發作,這些人都非常害怕再次經歷同樣的症狀。
在精神醫學上,這被稱為「預期性焦慮」(anticipatory anxiety)。陷入這種情緒狀態的人會因為微小的心跳或心悸,甚至在沒有任何刺激的情況下,光是想像自己可能面臨的最壞情況,就被推入焦慮之中。
預期性焦慮是在經歷恐慌發作或重大事故後,就算沒有再次發作或發生類似的事故,不合邏輯的想法也會讓我們經歷與症狀首次出現時強度相似的不安。在有過不好的經歷後,因為細微的徵兆或線索,容易面臨這種與過去恐懼情境發生時相同的心理狀態。就像搭上一班朝著極度恐懼奔馳,名為「思想錯誤」的電車一樣;而且,這是一班由微小的契機發動、可以瞬間抵達最壞結果的超高速列車。
預期性焦慮與通常被稱為「精神創傷」的「心理創傷」不同,心理創傷是在遭過暴力、交通事故、墜落或地震等重大事故時產生;然而,從感覺到任何人都無法預測的恐懼和害怕這一點來看,預期性焦慮和心理創傷則很相似。
那些因為些微差異而錯過重大成果的人,或是因為一時失誤而投資股票失利,或者是被公司淘汰、或在經濟上無法東山再起的這些人,很容易內心產生極端的想法。而且,如果這種狀態越來越嚴重,就會出現暴力、過度酗酒,甚至試圖自殺等行為。
一位當時正在經歷過度酗酒、暴力行為、暴飲暴食等症狀的選手,曾經要求我替其諮商。曾在奧運獲得銅牌的這位選手,長期被拿來與另一位年齡相仿的金牌得主相比、甚至受到差別待遇;他因為這樣的壓力而開始酗酒並暴飲暴食,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彷徨不已。
同時,身為非人氣項目的選手,他在經濟上也陷入困境。即使現在已經到了對該項運動相當熟悉的年齡,但是能獲得的支援,導致他遲早要放棄運動的現實,讓這位選手陷入了困境。如今即使參加比賽,似乎也對自己喪失了自信。
奧運的參賽選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如預期般贏得金牌的選手、沒能如預期般贏得金牌的選手,以及意外贏得金牌的選手,其餘選手則是志在參加。人們通常只把焦點放在取得好成績的運動員身上。在這種氛圍下,他們容易陷入注重結果而非過程的風險。
即使是擁有著強韌精神的國家代表,那些「萬一無法贏得金牌,一切就完了」的極端想法,也會成為他們的負擔。
如果這種負擔超過幫助我們承受失敗的「緩衝作用」,就會出現預期性焦慮,降低人們的專注力和執行能力。這種預期性焦慮很難由選手獨自克服。尤其是大型比賽結束後,許多選手會陷入長期低潮或熱情枯竭的狀態。
因為裁判不公或些微的比數差距,結果遺憾錯失獎牌的選手,他們感受到的預期性焦慮會更加強烈。由於惋惜和委屈深深烙印在心中,只要遇見稍微類似的環境,當時的情況就會在腦海中重現。
金雅朗選手也曾因為些微的差距而錯過獎牌。這是她在德國某次世界盃上,首次參加復活賽時發生的事。雖然跟著前面的人越過了終點線,但由於緊追在後的選手不但加速衝刺直到最後一刻,甚至在終點線前伸腳,最後那位選手反而比她還要早通過終點。據說,金雅朗原本帶著有點安逸的心情踏進比賽場地:「我隸屬的分組要晉級相較容易,而且這一回合有三個人能晉級,於是我心想,可以節省力氣用在下一輪,只要守住晉級門票就好。」
沒想到遇到這種狀況,她不知道有多慌張。金雅朗說,她當時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慚愧;對手盡了最大的努力,自己卻一副悠哉的樣子,所以這是理所當然的結果,她至今仍舊忘不了那個瞬間。從那天之後,就算只是預賽,金選手始終都沒有放鬆警惕。
預期性焦慮和準備狀態只有一線之隔,結果卻正好相反。同樣是擔心未來結果會危險或不好,結局卻恰恰相反。這其中的理由就在於「行動」。預期性焦慮只擔心出現不好的結果,而不會為了解決而採取行動。就算偶爾有所作為,也都是與解決問題無關的荒唐行為。就像是害怕心臟跳得太快,所以穿上緊緊束住胸口的厚重緊身衣。這樣一來,反而會讓人感到胸悶、心跳加速。
相反地,也有人像金雅朗選手一樣選擇做好準備。如果擔心其他選手會在終點線前伸出腿來,那就在賽前做出預測,在比賽時距離終點線前一公尺處搶先其他選手伸出腿──這就是準備狀態。雖然只是單純表示:「就算只是預賽,我也不會放鬆警惕。」實際上卻已經為了奪冠,做好萬全的準備。
【摘文3】如何不受周遭視線與評價動搖?
有時候,我們會非常在意身邊的人對自己的評價。而且,比起做得好的時候,做得不好或實力不如從前的時候更是如此。運動選手在比賽中發生失誤或成績不佳時,會對媒體的評價變得相當敏感。偶爾還會偷偷翻看不想看的新聞,結果導致自己內心受傷。承受觀眾赤裸裸的辱罵或來自粉絲的嚴厲目光時,總覺得自己是個大逆不道的罪人。
金雅朗選手也有類似的經歷。她說:「大家好像都不喜歡我,感覺他們都期待看我的笑話。」從貶低她出身地區的留言,到要她「走著瞧」的話,再到只要成績稍微不如預期,就會出現的「我就知道會那樣」的馬後炮,惡意留言實在非常多。甚至還有人會臆測她從未說過的話、不曾有過,然後留下惡意留言的情況。金雅朗選手這麼回應:「感覺好像在心上插了一把匕首。雖然我故作堅強,不過真的很受傷。」
如果因此受到傷害,肯定會不禁認為:「原來這就是我的真實面貌!我的程度只有這樣而已。」讓人容易感到挫折。長期持續這種負面情緒並不好,所以要盡快擺脫。我會建議對自己有負面情緒的選手,多和親近的隊友或教練進行對話。即使不說明自身情況,他們也明白這位選手為何覺得疲累,或是因為什麼事感到傷心。一些無法和家人或朋友分享的事,也可以毫無隱瞞地吐露出來。像這樣傾吐心聲後,選手本身能得到安慰,同時也可以整理好情感。
金雅朗選手因惡意留言而感到傷心時,我對她說的並不是「沒關係」、「那則惡意留言是假的」、「你不可能會這樣」等安慰。我們談論的重點,一直放在她對於自己當下的身體狀態和實力的感覺,以及因應未來的準備過程。我們把別人所評價的「看似合理但其實扭曲」的形象,轉換為「完全了解真實自我的自己」所下的評價。這麼一來,觀點發生了轉變,變成是「客觀的我」在評估自己的狀態,使得自己的判斷成為核心,而他人的批評只是附加的聲音。而且,那些附加的內容之中,有一定道理的忠言,則成了能夠當成回饋的訊號。
結果,金雅朗選手現在對惡意留言不再那麼在意了。「好像變得更堅強了。大家常說:『惡意留言也是一種關心。』現在從某種角度來看,其他人的負面評價和視線,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關心和支持。他們支持我、並對我抱有期待,而我卻沒有取得好成績時,這些惡意留言有可能是源於傷心的情緒。」現在的她,可以專注在自己應該做的事和想做的事。
如果對自己有嚴重的負面情緒,此時就必須思考:自己對於他人的評價是否過於敏感?此種類型的人對於自己犯下的任何錯誤或失誤,都會展現過度敏感的反應。一位在證券公司擔任分析師的朋友,他業績好到曾一度被選為最佳分析師而過得如魚得水,卻在股價下跌時因勉強製作投資報表,使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一次的失敗成了致命的打擊,他因而躲藏了將近一年,逃避與身邊的人對話。不過,這種封閉的態度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越是萎縮,情況只會越變越糟。
某天,一位綽號叫做「亞軍專家」的高爾夫選手來找我諮詢。成為職業高爾夫選手已經四年的她,雖然被視為一位實力和人品兼具的選手,每次卻都距離冠軍寶座只差一步。因為在最後一輪的比賽中,她總是會犯下荒唐的失誤,最後被擠到第二或第三名。
她來找我的那天,又是一個錯失冠軍的日子。首日與外國選手並列領先地位的她,卻在第二天因為惡劣天氣退居第四。雖然最後一天成功減少一桿,但是僅此而已。最終再度屈居亞軍的她,實在是氣憤不已。
出現所謂「二把手魔咒」的原因是,在關鍵時刻,執行能力卻反而下降。如果這種失敗反覆發生,每次比賽都會陷入可能犯下失誤的不安,注意力也會更難集中。
成為職業選手後,她共參加了八十場比賽。雖然有三十幾次進入前十名的紀錄,卻總是與冠軍無緣。因為每次比賽時,發球、鐵桿擊球、推桿等動作都會輪流出現問題。在比賽執行能力上沒有太大問題的她,只能認為是自己「運氣不好」,所以更加鬱悶。
在她剛開始打高爾夫沒幾年的時候,身邊許多人都對當時年幼的她讚不絕口,認為如果她成為職業選手,一定無人能敵。實際上,她也以優異的成績,比同齡選手更早成為職業高爾夫球選手。
然而,這就是問題所在。小小年紀就必須和在電視或雜誌上看到的優秀選手們比賽,這樣的壓力阻礙了她的發展。每次比賽都承受著巨大壓力的她,連自己的主要絕技──發球都沒能發揮出來,鐵桿擊球的機率也降低了。更嚴重的是,在業餘時期不曾出現過的失誤也越來越多。在這之後,她的隊友開始用「膽子不夠大」、「膽小如鼠」等方式形容她,而她自己也開始產生這樣的想法。這是一種自我貶低。
「自我貶低」的另一種說法就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貧乏」。自我概念是辨別並評價自己的心理學用語。通常,自我概念會透過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小時候的對象是父母,不過在長大後,對象會無時無刻發生變化。
人們常說:「環境對一個人來說很重要。」這是因為形成自我概念的環境將決定認同感。這樣的自我概念比起外部環境,更容易被內在力量的影響。因為接受並調整與外部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主體就是自己。
因此,自我概念的中心是「自我」(self)。盛裝「我」的第一個器皿就是自己。這個概念如果貧乏或充斥著自我貶低,連定義認同感的後續資訊也會被污染。就好比朝著被油覆蓋的大海注入頂級的清水,這麼做不僅無法淨化大海,反而會增加受污染海水的體積。自我概念也可以用相同的道理來解釋。
不僅運動員容易掉入自我貶低陷阱,身為有經驗者進入通訊公司的民九也因為同樣的理由來找我諮詢。他從外縣市的大學畢業後,任職於首爾的某家新創企業累積經驗。後來,他被與該公司有合作關係的大型通訊公司相關人士挖角後離職。因為跳槽到大企業,當時的他被很多人羨慕,不過進入該公司第二年的他再次考慮跳槽。
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們中,「學歷最差的畢業於首爾大學,最優秀的則來自哈佛大學」,這項事實讓他過得很辛苦。雖然他也自認具備競爭力,但是職場生活並不容易。在撰寫報告書、進行會議、做出決策、執行專案等方面沒有取得什麼成果後,他開始為自己設下限制。
像這樣失去自信後,民九雖然正在開發好的技術,卻無法在做重要的報告時,向公司高層展示自己的成果。「比我優秀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就算我做得再好,你有可能會認可我嗎?」這種失敗感讓他裹足不前。
每年都止步於亞軍的高爾夫選手,以及在進行重要的報告時經常滑鐵盧的上班族,這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讓人在關鍵時刻投降的「怪物」不是別人,而是自己製造出來的事實。
乍看之下,似乎是「那個選手很膽小」、「他為什麼一上台報告就那麼緊張」之類的言語讓他們感到畏縮。但是,為別人的影響出一份力的正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不傾聽自己的內心,反而為別人裝上擴音器,才會養大心中的怪物。
經常自我貶低的人擁有的特徵之一,就是完全接受對方的話。他們不會考慮對方說的話是否妥當,而是直接選擇全盤接受,結果卻壓迫了自己,招致不好的結果。如果是因為客觀的實力和練習量不足,而造成不理想的結果,那只需要努力填補這一部分就可以了。然而,若是心理因素導致反覆失敗,就應該先找出造成心理壓力(under pressure)的原因,並尋求解決對策。
【摘文2】擺脫嚴重的「預期性」焦慮
「每當心臟劇烈跳動的時候,我都覺得胸口快要爆炸了。」
「呼吸越來越困難,感覺快要不能喘氣了。」
「雖然很難用言語形容,但是我的心裡有一股非常不好的感覺,陷入好像會發生某種嚴重錯誤的恐懼之中。」
有些人帶著一副快沒命的表情,來到診療室求助。他們是患有「恐慌症」的人。只要經歷過一次恐慌發作,這些人都非常害怕再次經歷同樣的症狀。
在精神醫學上,這被稱為「預期性焦慮」(anticipatory anxiety)。陷入這種情緒狀態的人會因為微小的心跳或心悸,甚至在沒有任何刺激的情況下,光是想像自己可能面臨的最壞情況,就被推入焦慮之中。
預期性焦慮是在經歷恐慌發作或重大事故後,就算沒有再次發作或發生類似的事故,不合邏輯的想法也會讓我們經歷與症狀首次出現時強度相似的不安。在有過不好的經歷後,因為細微的徵兆或線索,容易面臨這種與過去恐懼情境發生時相同的心理狀態。就像搭上一班朝著極度恐懼奔馳,名為「思想錯誤」的電車一樣;而且,這是一班由微小的契機發動、可以瞬間抵達最壞結果的超高速列車。
預期性焦慮與通常被稱為「精神創傷」的「心理創傷」不同,心理創傷是在遭過暴力、交通事故、墜落或地震等重大事故時產生;然而,從感覺到任何人都無法預測的恐懼和害怕這一點來看,預期性焦慮和心理創傷則很相似。
那些因為些微差異而錯過重大成果的人,或是因為一時失誤而投資股票失利,或者是被公司淘汰、或在經濟上無法東山再起的這些人,很容易內心產生極端的想法。而且,如果這種狀態越來越嚴重,就會出現暴力、過度酗酒,甚至試圖自殺等行為。
一位當時正在經歷過度酗酒、暴力行為、暴飲暴食等症狀的選手,曾經要求我替其諮商。曾在奧運獲得銅牌的這位選手,長期被拿來與另一位年齡相仿的金牌得主相比、甚至受到差別待遇;他因為這樣的壓力而開始酗酒並暴飲暴食,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彷徨不已。
同時,身為非人氣項目的選手,他在經濟上也陷入困境。即使現在已經到了對該項運動相當熟悉的年齡,但是能獲得的支援,導致他遲早要放棄運動的現實,讓這位選手陷入了困境。如今即使參加比賽,似乎也對自己喪失了自信。
奧運的參賽選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如預期般贏得金牌的選手、沒能如預期般贏得金牌的選手,以及意外贏得金牌的選手,其餘選手則是志在參加。人們通常只把焦點放在取得好成績的運動員身上。在這種氛圍下,他們容易陷入注重結果而非過程的風險。
即使是擁有著強韌精神的國家代表,那些「萬一無法贏得金牌,一切就完了」的極端想法,也會成為他們的負擔。
如果這種負擔超過幫助我們承受失敗的「緩衝作用」,就會出現預期性焦慮,降低人們的專注力和執行能力。這種預期性焦慮很難由選手獨自克服。尤其是大型比賽結束後,許多選手會陷入長期低潮或熱情枯竭的狀態。
因為裁判不公或些微的比數差距,結果遺憾錯失獎牌的選手,他們感受到的預期性焦慮會更加強烈。由於惋惜和委屈深深烙印在心中,只要遇見稍微類似的環境,當時的情況就會在腦海中重現。
金雅朗選手也曾因為些微的差距而錯過獎牌。這是她在德國某次世界盃上,首次參加復活賽時發生的事。雖然跟著前面的人越過了終點線,但由於緊追在後的選手不但加速衝刺直到最後一刻,甚至在終點線前伸腳,最後那位選手反而比她還要早通過終點。據說,金雅朗原本帶著有點安逸的心情踏進比賽場地:「我隸屬的分組要晉級相較容易,而且這一回合有三個人能晉級,於是我心想,可以節省力氣用在下一輪,只要守住晉級門票就好。」
沒想到遇到這種狀況,她不知道有多慌張。金雅朗說,她當時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慚愧;對手盡了最大的努力,自己卻一副悠哉的樣子,所以這是理所當然的結果,她至今仍舊忘不了那個瞬間。從那天之後,就算只是預賽,金選手始終都沒有放鬆警惕。
預期性焦慮和準備狀態只有一線之隔,結果卻正好相反。同樣是擔心未來結果會危險或不好,結局卻恰恰相反。這其中的理由就在於「行動」。預期性焦慮只擔心出現不好的結果,而不會為了解決而採取行動。就算偶爾有所作為,也都是與解決問題無關的荒唐行為。就像是害怕心臟跳得太快,所以穿上緊緊束住胸口的厚重緊身衣。這樣一來,反而會讓人感到胸悶、心跳加速。
相反地,也有人像金雅朗選手一樣選擇做好準備。如果擔心其他選手會在終點線前伸出腿來,那就在賽前做出預測,在比賽時距離終點線前一公尺處搶先其他選手伸出腿──這就是準備狀態。雖然只是單純表示:「就算只是預賽,我也不會放鬆警惕。」實際上卻已經為了奪冠,做好萬全的準備。
【摘文3】如何不受周遭視線與評價動搖?
有時候,我們會非常在意身邊的人對自己的評價。而且,比起做得好的時候,做得不好或實力不如從前的時候更是如此。運動選手在比賽中發生失誤或成績不佳時,會對媒體的評價變得相當敏感。偶爾還會偷偷翻看不想看的新聞,結果導致自己內心受傷。承受觀眾赤裸裸的辱罵或來自粉絲的嚴厲目光時,總覺得自己是個大逆不道的罪人。
金雅朗選手也有類似的經歷。她說:「大家好像都不喜歡我,感覺他們都期待看我的笑話。」從貶低她出身地區的留言,到要她「走著瞧」的話,再到只要成績稍微不如預期,就會出現的「我就知道會那樣」的馬後炮,惡意留言實在非常多。甚至還有人會臆測她從未說過的話、不曾有過,然後留下惡意留言的情況。金雅朗選手這麼回應:「感覺好像在心上插了一把匕首。雖然我故作堅強,不過真的很受傷。」
如果因此受到傷害,肯定會不禁認為:「原來這就是我的真實面貌!我的程度只有這樣而已。」讓人容易感到挫折。長期持續這種負面情緒並不好,所以要盡快擺脫。我會建議對自己有負面情緒的選手,多和親近的隊友或教練進行對話。即使不說明自身情況,他們也明白這位選手為何覺得疲累,或是因為什麼事感到傷心。一些無法和家人或朋友分享的事,也可以毫無隱瞞地吐露出來。像這樣傾吐心聲後,選手本身能得到安慰,同時也可以整理好情感。
金雅朗選手因惡意留言而感到傷心時,我對她說的並不是「沒關係」、「那則惡意留言是假的」、「你不可能會這樣」等安慰。我們談論的重點,一直放在她對於自己當下的身體狀態和實力的感覺,以及因應未來的準備過程。我們把別人所評價的「看似合理但其實扭曲」的形象,轉換為「完全了解真實自我的自己」所下的評價。這麼一來,觀點發生了轉變,變成是「客觀的我」在評估自己的狀態,使得自己的判斷成為核心,而他人的批評只是附加的聲音。而且,那些附加的內容之中,有一定道理的忠言,則成了能夠當成回饋的訊號。
結果,金雅朗選手現在對惡意留言不再那麼在意了。「好像變得更堅強了。大家常說:『惡意留言也是一種關心。』現在從某種角度來看,其他人的負面評價和視線,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關心和支持。他們支持我、並對我抱有期待,而我卻沒有取得好成績時,這些惡意留言有可能是源於傷心的情緒。」現在的她,可以專注在自己應該做的事和想做的事。
如果對自己有嚴重的負面情緒,此時就必須思考:自己對於他人的評價是否過於敏感?此種類型的人對於自己犯下的任何錯誤或失誤,都會展現過度敏感的反應。一位在證券公司擔任分析師的朋友,他業績好到曾一度被選為最佳分析師而過得如魚得水,卻在股價下跌時因勉強製作投資報表,使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一次的失敗成了致命的打擊,他因而躲藏了將近一年,逃避與身邊的人對話。不過,這種封閉的態度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越是萎縮,情況只會越變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