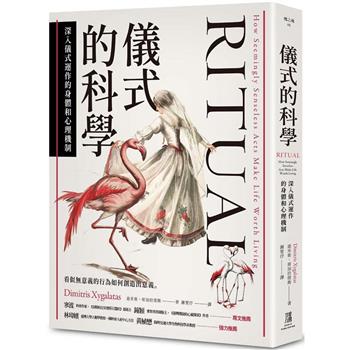第一章 儀式的悖論
在愛琴海,嬌小的希臘島嶼蒂諾斯(Tinos)上,每日由比雷埃夫斯(Piraeus)開來的渡輪正危危顫顫地駛進主港。岸邊站著成排粉刷得泛白的方形小屋,與後方險峻的山丘形成強烈對比。幾台卡車和客車從渡輪下方的甲板駛出,遊客湧上過道。碼頭這邊,計程車司機和旅行社人員圍在遊客旁,手舉寫著旅館名稱的告示,還有些旅館廣告著最後清倉價。觀光客大多都會前往當地的海灘及博物館,很快便隱去了蹤跡。此刻,假日氛圍發生了奇怪的變化。
剩下的遊客大多身著黑色,以一種不同的步調移動著。他們看起來莊嚴肅穆且目標堅定。他們在碼頭集合後,便一個個手腳著地,開始在城鎮主街上爬行。當中有些人腹部著地,僅用手肘拉著自己匍匐前行。其他人則以與街行方向垂直的方式躺下,以一種近乎薛西弗斯式的動作滾上陡坡,不斷扭身翻轉著身體,用手肘推著自己上行。這時有一名婦人突然向後倒下,兩名男子過來用手拉著她前進。還有人將孩子揹在背上,手腳並用地爬行。
此時正值仲夏時分。街上沒有多少陰涼處,鵝卵石鋪成的街道被陽光炙烤著。當這群人吋吋緩慢地爬上陡坡時,整個場景開始變得像戰場一樣:流血的膝蓋和手肘、燙傷的手腳、布滿淤血的身體以及滿是痛苦的臉龐。許多人因為高溫及體力耗盡而崩潰。但他們堅持繼續。陪同的家屬衝上前給他們水喝,等他們恢復神智,便又繼續攀爬。
他們的目的地是蒂諾斯聖母堂。這座壯觀的教堂坐落山頂上,建築全由從鄰近提洛島進口的白色大理石建成。教堂的正面綴飾著無數拱型柱廊,上頭雕刻著欄杆及花窗,從遠處看起來就像是精緻的刺繡蕾絲。傳說此處在1823年挖出了一尊古聖像,聖像埋藏的位置來自當地一名修女從夢中得到的啟示。隨後他們原地興建了教堂來收藏這尊聖像,此處很快就成為了朝聖的主要地標。每年都有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們湧入蒂諾斯,前來瞻仰這尊據說能行聖蹟的聖像。
在四肢著地爬到山頂後,朝聖者還得把自己跩上兩段大理石階梯才能禮敬聖像。聖像上精密細緻地雕刻出天使報喜的場景。但在聖像上已幾乎看不見這幅場景,因為訪客捐獻的珠寶覆蓋了整幅圖像。數以百計的的銀質還願祭品從屋頂上懸掛下來,見證著各種誓言與奇蹟,從一顆心、一條腿、一雙眼睛、一個搖籃到一艘船。
這些看似無意義的自我折磨可能十分引人注目,實則在全世界都可找到類似的行為。在中東,什葉派穆斯林用刀刃削砍己肉,以悼念烈士伊瑪目胡賽因(Imam Husayn)。在菲律賓,天主教徒將針鎚進手掌與腳掌,以紀念耶穌基督所受的折磨。在泰國,道教徒會慶祝崇拜中國神祇的九皇節,慶祝方式包括放血和用各種物品包括刀、串叉甚至鹿角或雨傘刺進自己的身體。在中美洲,馬雅人進行放血儀式,方式是用魟魚骨穿刺男性的生殖器。而在今日的美國阿帕拉契山南部,五旬節教派團體會在教會中手持致命毒蛇狂喜地跳舞。這些蛇被從尾巴懸空抓起,隨時有機會咬人——牠們確實經常發動攻擊。已有超過百起持蛇者死亡的意外登記在案。但由於這些儀式通常是祕密進行,實際人數可能更高。根據研究這些社群的社會心理學家胡德(Ralph Hood)的說法:「去到任何一間進行持蛇儀式的教會,你都會看到手部萎縮或失去手指的教眾。所有參加持蛇儀式的家庭都遭遇過這樣的事。」
在其他地方,人們會進行痛苦比較少、但代價並沒有比較輕的儀式。西藏僧侶會花數十年光陰完善他們的靜坐修行,讓自己遠離塵世,追求沉靜冥想的生活。在齋戒月時,全球各地的穆斯林從日出到日暮時分不進任何飲水食物。印度的婚禮儀式可以持續一整週,邀請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賓客參加,前期準備要花上好幾個月;對一般家庭來說,婚禮的花費可能讓人傾家蕩產。根據一個當地的非政府組織,進步村落企業及社會福利機構(Progressive Village Enterprises and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估計,超過60%的印度家庭會借錢來為子女的婚禮籌措資金,借款的利率通常過高。那些沒有其他方式來擔保貸款的人常被迫為奴來支付債務。
到目前為止,我提到的還只是宗教儀式而已。事實上,儀式對幾乎所有的社會制度來說都很重要。試想法官敲下法槌或是新總統就職前的宣誓。軍隊、政府和企業都會舉行各種儀式,以入伍典禮、遊行以及花費浩大的忠誠展示來呈現。那些在重要比賽上總是穿同一雙襪子的運動員會運用儀式,賭注越來越大時會親吻骰子或緊握幸運符的賭徒也是如此。甚至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每個人也都在進行儀式,就如我們舉杯敬酒、參加畢業典禮或是參加慶生會。對儀式的需求是原始的,如同我們將會看見的,這個需求也可能在人類文明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但究竟是何物驅使我們沉浸在這些帶有明確代價,而無任何直接明顯利益的行為中?又為何,這些行動的目的通常不明,卻具有深刻的涵義呢?
***
數年前,我在丹麥當交換學生時,拜訪了哥本哈根一座令人嘆為觀止的美術館――新嘉世伯美術館(Ny Carlsberg Glyptotek)。當我漫步在古地中海文化工藝品的展廳內時,我遇到一群來自美國的考古學學生。他們正圍繞著他們的教授,一名高挑、充滿活力的中年女性,聆聽她評論著展品。她的熱情似乎會感染,學生們看得很專注,像是對她說的每件事都很感興趣似的。於是我決定要跟著他們,獲得一次免費導覽的機會。
教授採用的是所謂的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她並未講課給學生聽,而是向學生提問,以此探究他們已知的知識,幫助他們做出新的推理。在針對數個物件討論其來源及目的之後,最終輪到一個看似古怪的古希臘陶器。「這是什麼?」她問道。學生們看來陷入了疑惑。這個物件呈中空角狀,但很明顯並非酒器,因為它體積太小,且底部有個洞。物件上刻有精細的裝飾細節,但儘管它看起來在製作上用盡心力,卻沒有實際用途。教授特別轉向其中一名學生。「你覺得這是做什麼的?它的目的是什麼?」她問。「我不知道。」學生看似窘迫地回答。「我們都不知道。」教授重覆他的話後,繼續說,「當我們不知道其功能為何時我們會說什麼?」該名學生突然間得到靈感。「和宗教崇拜有關!」他叫喊著。「沒錯,這和宗教崇拜有關!」老師同意地說道。「這可能是用在某種儀式的脈絡之下。」
教授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共鳴,因為此番言論認同了人性中最令人好奇的一個面向:儀式是人類間真正普遍存在的事實。無一例外,所有的人類社會,無論過去現在,都有一些傳統涉及高度精心設計、程式化且被準確執行的行為,這些行為標誌了人類生活的關鍵時刻。這些被我們稱為儀式的行為,要麼一點明確目的都沒有,要麼這些儀式的進行方式,與它們所宣稱的目標或行為並沒有太大的關聯。進行祈雨舞並不會讓雨水從天上落下,針刺巫毒娃娃無法從遠處傷害他人,而塔羅占卜者唯一能夠確切預測的就是在你結束諮詢時錢包會變薄些。就是這種媒介與目標之間的鴻溝,讓那名教授做出這樣的推斷:若有一個需要大量勞力來完成,卻沒有明確功能的物件,那它可能帶有宗教性的目的。
儘管在行動和目標之間存在著令人困惑的不一致,人們已經持續從事各種儀式上千年。事實上,不管是再怎麼樣世俗的社群,儀式在今日就如同在古代一樣普遍,無論我們是否有意識到。從敲敲木頭到輕喃祈願詞,從新年慶典到總統就職,儀式滲透我們私人及公共生活的每一個重要面向。無論是在宗教或是世俗脈絡下進行,儀式都是所有人類活動中特別的一類,重要且飽含意義。
這些特徵區別了儀式與其他諸如習慣之類等較不重要的行為。雖然兩者可能都是刻板化的行為,牽涉固定且重覆的模式。習慣會對世界有直接的影響,而儀式行為擁有的則是象徵意義,通常是為進行而進行。在我們還沒有發展出上床睡覺前先刷牙的習慣時,這個行為的目標在於其當下可見的功能——這在因果上是顯而易見的。在空中揮動象徵性的刷子並不會讓牙齒變乾淨。透過將這個程序變成例行公事,習慣讓我們規律且不經思考就從事這些活動。
相反地,儀式則在因果上不透明,它讓我們全神貫注,因為牽涉到的是必須記憶的象徵行為,這些行為一定被準確執行。舉例來說,在一場希臘東正教婚禮上,伴郎或伴娘會交換婚戒,然後將戒指戴到新娘新郎的手指上,並在他們頭上戴上王冠,如此重覆三次;神父必須朗讀禱詞三次;新婚夫妻必須共用一個酒杯,喝三口酒,要環繞祭壇三次。這些是一套長以小時計的複雜程序,必須精準地完成,而且需要一絲不茍的指示及排練以確保每個動作的準確度。在進行儀式時,這些行動中沒有一個具有任何法律效果:真正讓一對夫妻成婚的是另外的程序,包括在法律文件上簽名蓋章。然而婚禮的象徵意義以及盛況,才是讓這起事件如此重大難忘的原因——它讓我們產生這段婚姻其實是由這些儀式認定,而非由法律文件認可的印象。習慣會將重要任務變為例行公事、讓它們變得單調,藉此幫助我們組織這些任務;相對地,儀式則是透過從事某些特殊行為,來讓我們的生活充滿意義。
換句話說,儀式具體上就像社會學家荷曼斯(George C. Homans)說的:「儀式行為並不對外在世界造成實際結果——這是我們稱之為儀式的其中一個原因。」事實上,在許多宗教社群中,舉行儀式通常帶有被視為法術的確切目的。「然而這麼說並不表示儀式不具功能……它給予社群成員信心,驅散他們的焦慮,規訓他們的社會組織。」
人類學家探究儀式的功能已經超過一個世紀。他們認為,儀式極可能是作為個人滿足、賦權以及轉變的載體而存在,同時也是合作及維護社會秩序的機制。他們構想了許多有洞見的理論,但他們鮮少能夠、亦不願意對這些理論進行測試。這是因為文化人類學家的推論來自於一個假設:社會是複雜且混亂的場所,且有些在人類生活中最具意義的事物,是無法輕易被量化的。他們在田野進行民族誌研究,觀察在自然脈絡下進行的人類儀式。他們最首要的焦點,是嘗試去瞭解在這樣的脈絡下,儀式的操作者如何體驗這些風俗。
另一方面,心理學家和其他具實驗精神的學者認為測量需要高度控制,在實際的生活環境中無法輕易達到這種控制。他們一般都在實驗室中工作,每一刻只專注在單一個微小的行為上。要這麼做,他們得將人們帶出習慣的環境,帶到實驗室中,遠離任何可能會讓研究變複雜的外來因素。無可避免地,大多數附著於這個脈絡的意義將在這個過程中變得無法獲取。
儀式從未成為心理學研究的熱門主題,部分原因可能正是這類充滿意義的行為難以在實驗室中進行研究。它不是被當成人類行為的一個世俗面向,一種終究會消失的心理毛病,就是被視為一個無法被科學化調查的虛幻主題。因此,儀式雖然是人類本性中最為普遍的其中一個面向,針對它的科學知識在過去卻既稀少又片面。
直到近年,這個現象才開始有所改變。隨著人類學發展成熟,民族學家逐漸意識到他們有必要嚴肅看待人們的主張,需要尋求實證性的方法來驗證他們的主張。而心理學家也開始瞭解到,人類心靈所涵蓋的面向,遠比受試對象在大學實驗室的窄小隔間中所透露的更多,從而開始對文化輸入產生更多的興趣。
在許多案例中,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家開始彼此合作,互相學習。新科技與研究方法的發展,讓科學家們能夠探索過去無法企及的問題。穿戴式感應設備讓科學家可以研究實際參與儀式的人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生物化學及腦部造影技術,讓研究者能在實驗室內及田野中檢視人類的大腦活動;認知科學的創新提供了評估人們腦海中想法的新方法;而日益增強的電腦功能和嶄新的軟體設施,則能夠統計那些複雜的資料。這是第一次,對於儀式的科學研究有了完整的進展。我們終於可以開始將這個古老謎題的答案拼湊出來:這一切古怪的東西,到底有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