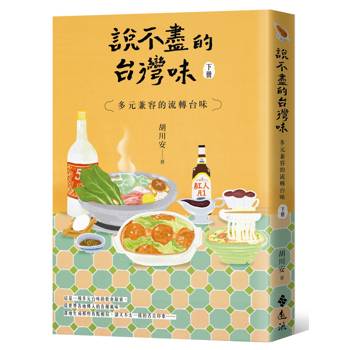米干
──來自異域的味道
我還記得以前中學的老師問我:「你哪省人?」
我不知道他在問什麼,回答:「台灣啊!」
後來我到中國,他們好像聽到我講話,也很少將我視為台灣來的,只知道是從南方來的,但沒有跟台灣聯想在一起。在四川的時候,也很多人一直跟我講四川話,以為我的川安跟四川有關係。
爸爸出身鹿港,媽媽是南投人。祖父和祖母都講著很典型的鹿港海口腔閩南語,外祖父母講台語,無法用北京話溝通。
後來我才知道自己語言上發音的特色。父親離開鹿港,在中壢高商教書的時候,我們住在龍岡地區,這裡是全台灣外省族群比例最高的地方,所以我從小對於附近的外省口味也很熟悉,除了麵食類,最有特色的就是米干。
台灣的滇緬記憶
龍岡在哪?在中壢南邊,還包含了八德和平鎮的部分地區,其實就是三不管地帶。一九五一年從泰緬邊境「金三角」來的孤軍大部分移居這裡,剛好也是鄉鎮的邊緣地帶。
這裡有很多軍區,路上很多軍人。父親因為是公教人員,以往常帶我去附近的軍公教福利中心或忠貞市場買東西。以前的米干店都沒有招牌,非常簡陋,只有散發出各式各樣的香氣,混和著香料的味道。
米干據說來自雲南,但我在昆明飲食考察的時候沒有看過。米干是來自中國、緬甸和寮國邊界的普洱市,普洱人早上就跟米干結緣,但他們吃的是「豆湯米干」。米干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如果在廣州,會把它叫成腸粉;如果在西安,會把它叫成米皮,就是米做成的粉餅。
普洱的「豆湯米干」是用豌豆磨製而成,不是我們一般豆漿中所用的黃豆。豌豆粉熬煮的濃厚豆湯,將米干泡在湯中,加入豬肉和豆芽韭菜,成為普洱人早餐的重要記憶。雲南大山大水,豆湯好吃的原因在於用山泉水將豌豆粉和水一起混合,再用鐵鍋將豌豆味熬煮出來,成為「豆湯米干」香味濃郁和營養的祕訣。然而,「橘逾淮為枳」,所有東西跨越了文化邊境就不同了。
米干的原料是米,所以來台灣的米干很多都用在來米製成米漿,接著在圓盤上鋪米漿隔水蒸熟,米皮脫下之後掛到桿子上冷卻,切成一條一條像麵的樣子。有些店家會用緬甸的米製作,有些用手做,有些則用機器。
龍岡的米干比較有特色的店像是「國旗屋」,原來矮小的房子外面掛滿國旗,旗海飄揚,甚至附近桃園市政府規劃的「雲南文化公園」沒有什麼雲南的文化,只有滿滿的國旗。如果不知道的人,還會以為雲南文化跟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有關係。但米干或許就是台灣人的「雲南文化」記憶吧!
流轉的米干
本來叫「九旺米干」的這間店,為什麼改稱「國旗屋」呢?在店內的介紹中可以知道,民國三十五到四十一年,老闆的父親在緬甸打游擊戰,隨身帶著一面母親縫製的國旗。後來到了忠貞新村,父親死後二十年,在遺物中發現那面有血跡的國旗,成為國旗屋的由來。
國旗屋對於國旗的信仰或許比製作米干更有興趣,現在每年十月十日在雲南文化公園有升旗典禮,都是由國旗屋帶頭。來此看到國旗飄揚成為一種特色,但米干還有別家可以吃。
我個人喜歡的是「阿美米干」。老闆跟著國軍打游擊,認識了傈僳族姑娘阿美,就把米干店叫「阿美米干」。創業超過四十年的阿美米干,仍然堅持用手工製作,湯頭是用黑豬的大骨熬的,雖然說是雲南的「傳統」,但米是用台灣的在來米,豬也是台灣豬,所以可以說都在地化了。
米干中會加豬肝、蛋花或荷包蛋,但在營養已經頗豐富的湯頭中,為什麼還要加這麼多蛋白質呢?如果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應該是當年孤軍在雲南顛沛流離,沒得吃,也缺乏營養,饑荒餓死了數千人。來到龍岡之後,生活條件改善了,本來沒有這些營養食材的米干也增加了這些東西,那是對於飢餓回憶的反應,對於吃飽穿暖的想望。所以龍岡米干已經不是雲南的米干,而是屬於台灣這塊土地上融合出來的新食物。
異域故事
龍岡有幾十家的米干店,其中阿美米干的第二代,也是金三角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李福英,我都叫她福英姐。她小時候住在金三角,中學的時候才來到台灣。有一次我因為文化部的專案計畫,帶著攝影團隊去採訪。
「你必須問你自己是誰,才知道你要往哪裡去。」福英姐說。
有故事的人,說起故事就不同。
福英姐說,在龍岡附近的米干和雲南菜,很多都是他們的企業經營的,整個街區都是當年滇緬異域的孤軍。因為有著共同的背景,凝聚力強,在新的時代才能說出不一樣的飲食文化故事。
民國六十五年,福英姐跟著媽媽饒八妹從金三角來到桃園忠貞新村,出身雲南傈僳族的媽媽,過年過節的時候都會做米干,後來擺起了小攤。
如果來龍岡的話,會發現米干店不只午餐的時候開,往往早上八點就開門,可以當早餐,還有些六點就開,一直開到晚上十點。如果是六點開店,四點就要起床準備。
「我以前一輩子最討厭米干,想要掙脫這些東西。雲南的、戰爭的記憶,有很重要嗎?」福英姐說:「民國八十年,麥當勞或三商巧福的連鎖店快速展店時,我看著麥當勞的員工手冊,想著米干店怎麼進去百貨公司的地下街。」
明亮的百貨公司,吸引著從金三角來的福英。然而,跟隨著別人創業,那畢竟不是自己,展店的結果還讓米干店差點倒閉。重新盤整後,她才知道自己從小的戰爭記憶,才是帶不走的東西。
重新思考自己的故事後,整合了龍岡附近的街區,讓每家米干和雲南菜都有特色,而且結合新的飲食文化,讓年輕人也喜歡來。異域故事館中有一間「癮食聖堂」,以前忠貞召會所改的餐酒館。以雲南菜為基底的餐酒館,腐乳臘肉手桿薄餅,其實就是混合雲南氣味的披薩,配上起司,兩者的味道神奇絕配。
再點了一個聖堂布丁,布丁與焦糖網格都是手作的,華麗的色彩,的確適合在教堂中感受。本來是雲南緬甸移民的米干味,化身為西式與滇緬的混合,不斷創造的飲食傳統,從金三角到台灣,融合出新的口味。
──來自異域的味道
我還記得以前中學的老師問我:「你哪省人?」
我不知道他在問什麼,回答:「台灣啊!」
後來我到中國,他們好像聽到我講話,也很少將我視為台灣來的,只知道是從南方來的,但沒有跟台灣聯想在一起。在四川的時候,也很多人一直跟我講四川話,以為我的川安跟四川有關係。
爸爸出身鹿港,媽媽是南投人。祖父和祖母都講著很典型的鹿港海口腔閩南語,外祖父母講台語,無法用北京話溝通。
後來我才知道自己語言上發音的特色。父親離開鹿港,在中壢高商教書的時候,我們住在龍岡地區,這裡是全台灣外省族群比例最高的地方,所以我從小對於附近的外省口味也很熟悉,除了麵食類,最有特色的就是米干。
台灣的滇緬記憶
龍岡在哪?在中壢南邊,還包含了八德和平鎮的部分地區,其實就是三不管地帶。一九五一年從泰緬邊境「金三角」來的孤軍大部分移居這裡,剛好也是鄉鎮的邊緣地帶。
這裡有很多軍區,路上很多軍人。父親因為是公教人員,以往常帶我去附近的軍公教福利中心或忠貞市場買東西。以前的米干店都沒有招牌,非常簡陋,只有散發出各式各樣的香氣,混和著香料的味道。
米干據說來自雲南,但我在昆明飲食考察的時候沒有看過。米干是來自中國、緬甸和寮國邊界的普洱市,普洱人早上就跟米干結緣,但他們吃的是「豆湯米干」。米干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如果在廣州,會把它叫成腸粉;如果在西安,會把它叫成米皮,就是米做成的粉餅。
普洱的「豆湯米干」是用豌豆磨製而成,不是我們一般豆漿中所用的黃豆。豌豆粉熬煮的濃厚豆湯,將米干泡在湯中,加入豬肉和豆芽韭菜,成為普洱人早餐的重要記憶。雲南大山大水,豆湯好吃的原因在於用山泉水將豌豆粉和水一起混合,再用鐵鍋將豌豆味熬煮出來,成為「豆湯米干」香味濃郁和營養的祕訣。然而,「橘逾淮為枳」,所有東西跨越了文化邊境就不同了。
米干的原料是米,所以來台灣的米干很多都用在來米製成米漿,接著在圓盤上鋪米漿隔水蒸熟,米皮脫下之後掛到桿子上冷卻,切成一條一條像麵的樣子。有些店家會用緬甸的米製作,有些用手做,有些則用機器。
龍岡的米干比較有特色的店像是「國旗屋」,原來矮小的房子外面掛滿國旗,旗海飄揚,甚至附近桃園市政府規劃的「雲南文化公園」沒有什麼雲南的文化,只有滿滿的國旗。如果不知道的人,還會以為雲南文化跟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有關係。但米干或許就是台灣人的「雲南文化」記憶吧!
流轉的米干
本來叫「九旺米干」的這間店,為什麼改稱「國旗屋」呢?在店內的介紹中可以知道,民國三十五到四十一年,老闆的父親在緬甸打游擊戰,隨身帶著一面母親縫製的國旗。後來到了忠貞新村,父親死後二十年,在遺物中發現那面有血跡的國旗,成為國旗屋的由來。
國旗屋對於國旗的信仰或許比製作米干更有興趣,現在每年十月十日在雲南文化公園有升旗典禮,都是由國旗屋帶頭。來此看到國旗飄揚成為一種特色,但米干還有別家可以吃。
我個人喜歡的是「阿美米干」。老闆跟著國軍打游擊,認識了傈僳族姑娘阿美,就把米干店叫「阿美米干」。創業超過四十年的阿美米干,仍然堅持用手工製作,湯頭是用黑豬的大骨熬的,雖然說是雲南的「傳統」,但米是用台灣的在來米,豬也是台灣豬,所以可以說都在地化了。
米干中會加豬肝、蛋花或荷包蛋,但在營養已經頗豐富的湯頭中,為什麼還要加這麼多蛋白質呢?如果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應該是當年孤軍在雲南顛沛流離,沒得吃,也缺乏營養,饑荒餓死了數千人。來到龍岡之後,生活條件改善了,本來沒有這些營養食材的米干也增加了這些東西,那是對於飢餓回憶的反應,對於吃飽穿暖的想望。所以龍岡米干已經不是雲南的米干,而是屬於台灣這塊土地上融合出來的新食物。
異域故事
龍岡有幾十家的米干店,其中阿美米干的第二代,也是金三角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李福英,我都叫她福英姐。她小時候住在金三角,中學的時候才來到台灣。有一次我因為文化部的專案計畫,帶著攝影團隊去採訪。
「你必須問你自己是誰,才知道你要往哪裡去。」福英姐說。
有故事的人,說起故事就不同。
福英姐說,在龍岡附近的米干和雲南菜,很多都是他們的企業經營的,整個街區都是當年滇緬異域的孤軍。因為有著共同的背景,凝聚力強,在新的時代才能說出不一樣的飲食文化故事。
民國六十五年,福英姐跟著媽媽饒八妹從金三角來到桃園忠貞新村,出身雲南傈僳族的媽媽,過年過節的時候都會做米干,後來擺起了小攤。
如果來龍岡的話,會發現米干店不只午餐的時候開,往往早上八點就開門,可以當早餐,還有些六點就開,一直開到晚上十點。如果是六點開店,四點就要起床準備。
「我以前一輩子最討厭米干,想要掙脫這些東西。雲南的、戰爭的記憶,有很重要嗎?」福英姐說:「民國八十年,麥當勞或三商巧福的連鎖店快速展店時,我看著麥當勞的員工手冊,想著米干店怎麼進去百貨公司的地下街。」
明亮的百貨公司,吸引著從金三角來的福英。然而,跟隨著別人創業,那畢竟不是自己,展店的結果還讓米干店差點倒閉。重新盤整後,她才知道自己從小的戰爭記憶,才是帶不走的東西。
重新思考自己的故事後,整合了龍岡附近的街區,讓每家米干和雲南菜都有特色,而且結合新的飲食文化,讓年輕人也喜歡來。異域故事館中有一間「癮食聖堂」,以前忠貞召會所改的餐酒館。以雲南菜為基底的餐酒館,腐乳臘肉手桿薄餅,其實就是混合雲南氣味的披薩,配上起司,兩者的味道神奇絕配。
再點了一個聖堂布丁,布丁與焦糖網格都是手作的,華麗的色彩,的確適合在教堂中感受。本來是雲南緬甸移民的米干味,化身為西式與滇緬的混合,不斷創造的飲食傳統,從金三角到台灣,融合出新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