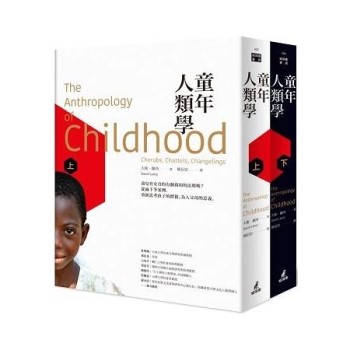1
兒童來自何處?
人類學家的否決
美國人是全世界最講究個人主義的民族。
發展心理學這門領域充滿了種族優越感,完全受到歐美觀點的宰制。
人類學裡有一項源遠流長的傳統,至少可追溯到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這項傳統提醒了我們心理學存在著受限於特定文化的缺陷。米德的著作削弱了心理學家霍爾聲稱壓力是青年期無可避免的一部分的說法。另一個比較不為人知的例子,則是馬凌諾斯基在更早之前根據自己在特羅布里恩群島從事的田野調查以批判佛洛伊德的伊底帕斯理論。放諸四海皆準的認知發展階段論(例如皮亞傑的理論)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原因是跨文化比較研究,揭露了文化與學校教育的經驗具有深遠而且出人意料的影響。歐克絲與席埃芙琳對於成人與兒童間的語言互動所進行的分析,也顯示了在非西方社會所得到的民族誌研究,可以用來「打破」對主流發展心理學文獻當中的「看似放諸四海皆準」的主張。羅伯.勒文挑戰了心理學當中最神聖不可批判的教條:母嬰依附關係。勒文從觀察非洲務農的古西人發現,母嬰之間是有可能只存在「弱依附」關係(即不是普世皆是「強依附」),而由此也是有可能導致嬰兒長大後情感能力發展不全。古西族的母親雖然對嬰兒發出的求救訊號回應迅速,對於嬰兒的其他口語發聲,例如牙牙學語,卻是置之不理。她們極少看著嬰兒或是對嬰兒說話,甚至在哺乳期間也不會。等到她們開始會對孩子說話的時候,她們使用的語言也都是命令與威脅,而不是讚美或問句。儘管古西族的母親具有這些明顯可見的「病理」徵象,勒文和他的同僚(他們研究古西族村民已有數十年之久)卻未發現廣泛情感缺陷的跡證。他因此提出,過度宣稱四海皆準定律的問題來自於「兒童發展領域的雙重身分,一方面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倡議運動,宣揚以人道方式對待兒童;另一方面又是一種科學研究活動,致力於尋求知識與理解」。
另一個人類學家急需顛覆的神聖教條是「教養方式」理論。中非的波非族農民合乎所謂的「威權型」教養方式,因為他們注重兒童對父母的尊敬與順從,也對子女施予強制性的控制。根據理論,波非族的兒童應當表現出孤僻、缺乏同理心、高攻擊性以及欠缺進取的性格。然而,他們表現出來的特性卻是恰恰相反。芙茨因此斷言指出,那種理論套用在美國人身上也許有效,但「在波非人當中卻幾無解釋能力」。在本書中,讀者將會看見其他許多這種人類學家「行使否決權」的例子。
這種觀點認為心理學當中許多根深蒂固的論點,其實都不能如其作者所認定的那樣普遍適用於全人類。後來,這種觀點又受到二○一○年發表的一篇論述詳盡的論文所強化。亨利奇與他的同僚質疑了這門學科的根基,指稱心理學家並未針對文化或養育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提出解釋。藉由一場大規模的調查,他們確認了絕大多數的心理學研究都是以教育發達、工業化而且富裕的西方民主國家(簡稱「怪異」國家,原因是這幾個條件的英文詞語:「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Democracies」,首字母拼合起來即是「WEIRD」——「怪異」)的公民為對象,尤其又以大學生為多。他們指出,在能夠取得比較性資料的領域中,「【怪異】社會的成員經常處於資料分布的極端……因此若要對人類得出概括性的結論,研究這個次族群絕對是最不恰當的選擇」。
靈長類動物學家也指責高度仰賴在實驗室裡做實驗的西方心理學家將若干特質宣稱為人類所獨有,但證據卻顯示這些特質其實可見於自由生長的非人類靈長類動物身上。「對實驗心理學觀察性資料的鄙夷,導致有些人忽略了動物認知成就的實際現象」。
幾年前,我也曾經對這項矛盾有所感觸:我們對童年的理解,不論是一般的通俗理解還是科學上的理解,都僅是奠基於單一、個別文化的經驗與資料。我在賴比瑞亞內陸一座偏遠村莊研究克佩勒族兒童的時候,就注意到了他們的童年體驗和我讀過的教科書所描述的有多不同。為了突顯這種差異,我便將童年的大多數概括性觀點所來自的社會與世界其他地區列出了一份對比。最能充分體現這些對比的字眼,就是「幼兒至上」與「老人統治」。
本書中的許多討論都會受到此一對比的引導,也將一再提及怪異社會的非典型性以及猿類的田調結果。我的目標是修正一般的種族中心觀點,也就是只將兒童視為寶貴、天真而且異常可愛的小天使。立足於史學、人類學以及靈長類動物學研究的堅實基礎上,我希望能夠對兒童及其照顧者的生活找出近似於常態的描述。我也會說明其他不同的觀點,也就是兒童可能被視為沒人要而且礙手礙腳的調換兒,或是具有商品化的實用價值而備受渴求的私人財產。
不過,我的意圖不僅在於否決非人類學家的理論主張。我認為民族誌的龐大檔案含有一批幾乎完全沒有被人發現的資料,可以從中發掘有關童年本質的洞見:幼兒至上觀點以外的洞見。民族誌的特點使民族誌「資料」特別有價值。其中一項優點是藉由參與觀察者的身分蒐集資訊,民族誌學者能夠將三種不同脈絡的資訊交織在一起。第一,民族誌學者描述所見,匯集出一套令人讚嘆的觀察紀錄(並且附有照片與影音紀錄),能夠讓人從中找出特定的模式。第二,藉著訪問或者與受訪者討論他們所目睹的現象,民族誌學者可能會獲得圈內人(主位)的觀點,而這種觀點經常可讓人理解陌生的異國行為。這些觀點通常會集結起來,構成所謂的文化模式或者族群理論。這些模式的有用之處在於將特定的育兒做法放置於比較廣泛也比較全面性的文化脈絡當中。第三,民族誌學者也會記錄他們自己(客位)的觀點。身為民族誌紀錄的讀者,我特別會留意人類學家感到吃驚的時刻,也就是他們發現某種現象違反他們自身的童年文化模式而不禁為之詫異的情形。
我採取的做法是比較(這種方法稱為民族學)與歸納。舉第二章的一個例子說明,就是在我針對民族誌裡為新生兒與嬰兒的照顧與對待方式所留下的許多陳述進行評註的過程中,一種模式逐漸浮現了出來。儘管具體細節存在許多差異,但全世界大多數的社會都會延遲人格的授予,而這種模式又對弒嬰、依附理論、兒童疾病的診斷以及幼兒埋葬方式等等具有極大的影響。這些模式即是本書的主要組織軸心與主題。
不過,首先要談一些歷史。
真的有童年這種東西嗎?
「兒童」本身其實是個頗為複雜的字眼。
如同冰冷的一月之於等待播種的農夫,兒童在以往也被視為一段毫無價值的季節,「不具才智、力氣與機靈」。
在中世紀期間,兒童通常只有在成長到不再是兒童之後才會受到重視。
為了展開我們的工作,我們必須從一片空白著手。設想童年原來根本不存在,而是直到最近才出現的概念。這是法國哲學家暨史學家阿希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一本深富影響力的著作所提出的論點。他在那本書裡指出,把童年視為一種特殊狀態,是近數百年來才出現的概念。他的論據主要是根據具象藝術的分析。
十二世紀之前,中世紀藝術根本沒有童年的概念,也不曾試圖描繪童年。我們很難相信這種疏忽是因為能力不足;比較可信的看法是中世紀時期的世界根本沒有童年存在的空間。
我們如果把研究資料侷限於肖像畫中的兒童形象,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這類肖像畫不是極為罕見,就是看起來不太像兒童。兒童在藝術中極少被描繪出來,應視為一種判斷基準,說明當時他們的地位無足輕重,而且這點也反映在葬禮習俗當中。在嬰幼兒埋葬方式的研究中發現了一項典型的模式,顯示兒童都只是草草埋在房屋的地板下、牆壁裡或是菜園的邊緣,而且沒有任何特殊處理或者陪葬品。基本上,阿希耶的意思是說成年前有兩個人生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嬰幼兒階段,這時個體缺乏語言、禮儀與適當運動能力,因此還不是完全的人;第二個階段是原型成人階段,這時個體被當成體型較小而且能力比較不足的成人看待。這種描述對文明史上大多數時間的農民社會而言大概是八九不離十,也可能符合不少人類學家研究過的部落社會。而骨學分析雖然稀少,卻也在少年骨骸當中發現了從事成人活動(粗重、危險的工作以及打仗)的證據。
不過,學者立刻就接下了阿希耶拋出的挑戰。桑莫維爾記錄了從埃及時代以來幾乎連續不斷的證據,顯示童年一直是一個特殊的階段。實際上,皮特里挖掘出拉罕這座埃及中王國時期(公元前一九○○年左右)的村莊之時,就發現了許多兒童玩具,包括放在現代玩具店裡也不會顯得格格不入的圓球與拖行玩具。
漢娜沃特探究各種文獻資料,發現在中世紀期間有眾多關於兒童的證據,記錄了一種一貫的現象,且顯示兒童的生活反映了父母的社會地位:「到了一四○○年,職業玩具製造匠已在紐倫堡與奧格斯堡開設店舖,也開始將產品外銷至義大利與法國。莊園地主的子女也會玩西洋棋與雙陸棋,並且學習馴鷹術與擊劍」。
誠然,如同夏哈爾的嚴謹研究所顯示的,疾病、嬰兒的高死亡率,以及在幼年就必須學習自立(或者至少不對父母造成負擔)表示無憂無慮而且備受寵愛的童年時期必定相當短暫;舉例而言,「受到指定必須過隱修生活的兒童,在五歲就被送入修道院與修女院,有些特例甚至更早」。過往時代的童年證據確實無可否認,但童年的時間長度與兒童在家庭與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卻與我們這個幼兒至上社會的情形非常不同。
人類童年有什麼特別?
絕大多數的哺乳類動物都順暢無礙地從嬰兒期進展至成年期,沒有任何過渡階段。
對於身處於幼兒至上社會當中的人士而言,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想到這個問題:「人類童年有什麼特別?」不過,對於關注人類生活史的獨特面向以及童年在不同文化中存有巨大差異的人類學家而言,這個問題卻是人類演化當中最至關緊要的議題之一。在地球面臨人口過剩的威脅之際,身為我們最近親的黑猩猩為什麼卻瀕臨絕種?針對童年初期是「人類生命週期當中的一個獨特階段,在現存其他哺乳類動物的生命週期當中都不存在」的這種巨大差異,博金找出了一項解釋。相較於其他猿類,人類的生殖力高出許多,博金把這種現象歸功於童年那種如同托兒所般的特性。童年的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停滯狀態,讓兒童在仍然必須依賴別人的時候就能夠斷奶,從而讓母親能夠生育另一個孩子。
相對於黑猩猩,人類斷奶的時間很早,在體重達到出生體重的二.一倍左右,差不多二十四個月大或甚至更早就會斷奶。黑猩猩在五到六歲才斷奶,但斷奶後就隨即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與達到性成熟。所以,母黑猩猩在生育每一胎之間必須等待至少六到七年,人類在順利的情況下則是每兩年就可以生一胎。不過,人類兒童雖然在兩歲或不到就斷奶,斷奶之後卻仍然需要成人的幫助與供養。人類兒童的大腦仍處於發展階段,成長得非常迅速,消耗極多的熱量。實際上,在其他動物身上用於促成身體成長的營養素,在人類身上都是用於供應大腦所需。嬰兒欠缺各種維繫生命所需的技能,例如口語能力。他們體型小巧,動作緩慢,極易受到獵捕。他們沒有辦法咀嚼或者消化成人的食物。所以,黑猩猩母親通常是幼仔唯一的照顧者,但人類母親卻仰賴子女的最近親(父親、兄姊與祖父母)提供兒童照顧上的協助。由於這些最近親的基因都隨著他們的妻子∕母親∕女兒所生育的每一個子女而增殖,所以他們在照顧這些兒童方面的基因利益也就和她幾乎相同。
不過,人類的童年不僅從六個月延長至別人能夠幫忙照顧的四年。童年中期也是其他猿類的生活史當中找不到的一個「額外」階段,而且人類的青年期也比猿類的類似階段來得長。最能解釋這段延長幼年期的模型稱為「具體資本」。人類雖然有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必須依賴別人,而且在這段期間來不及把自己的基因傳承給下一代即告死亡的風險也比較高,卻可由更長、更健康也更具生殖力的成年時期所彌補。人類兒童的大腦與身體成長速度雖比其他動物慢,卻能夠因此取得對病原體的重要免疫力與抵抗力,並且針對他們的文化長期累積而來的生存與繁殖確保手段發展出必要的技能與知識。隨著年輕人逐漸成熟,他們的身體也變得愈來愈強壯、脂肪愈來愈多、能力愈來愈好、社會連結愈來愈緊密。累積了大量具體資本之後才展開成年期的個體,比較有可能擁有較長的壽命,也會生育比較多的後代,而且那些後代也會比較健康,存活的機會比較高。這種生命史進程應該是受到自然汰擇的偏好。
不過,本書將會充分證實,不論是童年的整體還是其中各個階段的長度,都會隨著每個人而有極大的差異。在第七章,我探討童年受到縮短的現象,以便兒童能夠「加速長大」,填補因為喪失年紀較大的成員所出現的家庭勞動力缺口(例如母親去世而由大女兒接替母親的角色)。在漫長的童年期間,兒童會獲得大量來自生物與社會方面的「儲備能力」,以便在逆境中啟用。舉例而言,失去父母或是其中一人可能會促成擇偶與家庭組成行為提早發生。兒童會「提早成長」,從「緩慢」的生命史軌跡轉變為「快速」軌跡。這種軌跡的轉變可以在較短的成年時期與比較不那麼健壯的情況下有助於個人複製自己的基因。目前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童年中期代表了一個決定點,充滿壓力與危險的生活將在這個時刻造成青春期提早來臨、青年期縮短,以及投機式擇偶。儘管生育後代的前景不太好,處於這種狀況下的年輕人卻可能已經對自身所屬文化的適應系統有了相當程度的嫻熟,所以能夠保持自己以及至少部分後代活命。「街童」的生命史無疑也合乎此一軌跡。這種雙軌跡模式可能有助於我們了解人類在不利狀況下如何維繫人口數。
如同我先前指出的,我的目標是徹底探查民族誌紀錄以找出新興模式,尤其是那些與各種「大」問題有關的模式,例如幼年期各個時期造成的後果。歷史上,人類生命史學者必然會採取比較狹隘的探查過程,原因是一般認為我們如果要從演化觀點理解童年,就應該特別把關注焦點集中在狩獵採集(hunting and gathering society)與搜食社會(foraging society)上,原因是我們猜測那些社會比較接近於「演化適應環境」。也就是說,如果人類演化的化石紀錄揭露了一種以搜食為主的謀生方式,那麼我們就應該把焦點集中在保有那種原始生活方式的當代社會上。南非孔族大概是全世界受到最詳盡研究的搜食社會,所以針對他們的童年所從事的開創性研究也奠定了「準則」。不過,這種觀點已經逐漸褪流行了。儘管當代搜食民族之間存在著毋庸置疑的共通性,他們之間的差異卻也相當明顯可見。此外,現在孔族也被視為有點異於尋常,原因是孔族兒童不需要為自己與家人承擔糧食供應責任的時期,和其他搜食族群比較起來其實相當長。
現在,許多學者都認為晚更新世(Late Pleistocene)是現代人的起源,因為那是智人的人口出現巨大成長與全球擴散的時期。那些移動人口的謀生策略樣態,就是遷徙和居住都選擇在接近水的地方,善用現成的海洋資源,例如甲殼類動物。這種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於飲食向來缺乏蛋白質(肉類)的孔族,而是比較接近於馬瑞母人(托勒斯海峽的島嶼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同於孔族兒童,穆雷島上的馬瑞母人兒童只要長到比幼兒稍大一點的年紀,即可輕易取得可食用的海洋資源。目前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演化適應也同樣發生在人類人口於全新世(Holocene)快速擴張的期間。在那段時期,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文化出現規模龐大的多樣化發展。所以,我的立場認為,藉著研究街童文化所能夠對童年「本質」獲得的瞭解,並不亞於研究非洲的旱地搜食者。
人類學當中雖有豐富的童年材料,但讀者應當要理解那些資訊可能是艱苦得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