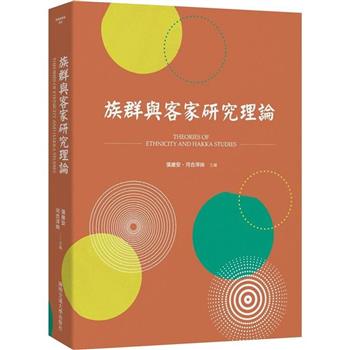導論/張維安
一、前言
理論,固然可以在字典上查到定義。不過在讀者的心中,可能並非只有一個說法。記得在學校讀社會學時,從大學生到博士生,每個階段都要修一門「社會學理論」,有時又分成古典社會學理論和當代社會學理論,或進階的選讀批判理論、系統理論,古典時期的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學理論流派,在當代社會學理論中又有功能論、衝突論、互動論……除了西方的社會學理論,還發展本土社會學理論,有時還把理論分成巨型理論、中程理論。這樣的「理論」仍每日在繼續創造中。不同的理論各有其解釋歷史社會的角度,彼此之間時而互補,時而存在截然不同的論點,這些理論的提出涉及獨特的學術思想脈絡、獨特的歷史社會情境,當然也和發展理論的政治經濟環境、理論家的學養有關。也許沒有接近真理(如果有的話)的理論,不過理論的閱讀,了解理論之間的對話,相互之間的評論、反思,卻有助於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與闡明。《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一書的「理論」概念,適合用上述的觀點來理解。「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並沒有提供一個研究族群或客家的框架或指導原則,本書各篇論文也非在一個內部一致的理論典範之下進行寫作,彼此之間有些存有共識,但也存在不同的立場與觀點。
本書的出版作為建構客家學術研究的一環,如韋伯所說,學術工作和一個進步的過程不可分離⋯⋯在學術園地裡,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10、20、50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的「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它要求過時(Weber, 1946: 138;轉引自黃瑞祺,2013:141),期待未來有其他的研究來補充、來超越。客家族群身分的浮現和學術理念的論述息息相關,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發問方式,不同觀點與證據成就了不同的客家樣貌。19世紀中國客籍縣認同的客家,20世紀全球化架構下的客家,其所存在的樣貌,其所具有的客家性,需要不同的理論來詮釋。
客家研究這個領域被提出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不過客家研究要成為像社會學或人類學這樣的學科,目前還沒有足夠的基礎,現在仍屬於吸收各學科養分的階段,各種社會科學的理論中,有些對於客家議題的關心與思考具有較強的選擇性、親近性,可逐漸吸收或轉化為客家學核心知識的訓練基礎,這些知識可能來自於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語言學等等;其相應的研究方法,例如田野考察、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口述歷史、敘事分析、文化論述等等,也是要做好客家研究所不能缺少的訓練(張維安,2005:3)。相對於客家研究,族群研究似乎要更成熟一些,熟悉各種族群研究的觀點與方法,對客家研究的進程,有一定的幫助。
從實務上來說,在客家研究作為一個專業領域的目標下,最少需要有嚴謹的課程規劃,學術社群組織的建立,專業的客家研究期刊,客家研究專門領域的讀本,專業的學術研討會,客家研究專業的學術單位,更重要的是學術界要有源源不斷的客家研究專書出版。在這個脈絡下,過往客家學界已經做了相當程度的努力,幾年前《全球客家研究》期刊曾經做過許多研究成果的統計,有助於想像客家研究的成績,例如〈客家研究臺灣相關期刊論文書目彙編:2010-2013年〉(陳璐誼,2014)、〈中文客家叢書目錄整理〉(劉堉珊,2014)、〈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目錄整理〉(劉堉珊,2015)、〈2015年中國客家研究期刊論文書目彙編〉(張珈瑜,2016),特別是〈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彙編〉(2011-8)(許維德,2013;張珈瑜,2015,2017,2019)。從許維德等的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統計來看,從2011至2018年的8年間,一共有1,990篇與客家研究相關的碩博士論文產出,平均每年248篇。易言之,平均每3天就有2本碩博士論文產出,年輕學子的投入,對客家研究學界實是莫大的鼓舞。
臺灣客家研究已經累積相當多的成果,甚至在研究典範上經歷了一些轉移(蕭新煌,2018)。近年來我們則努力在全球客家方面進行比較研究,例如與日本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合辦會議,出版《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河合洋尚、張維安,2020),甚至成立全球客家研究聯盟(2019年12月),出版《全球客家研究的實踐與發展》(張維安、簡美玲,2021)。研究方法方面的成果則出版了《客家與族群研究的技藝》(張維安、潘美玲、許維德,2021),如今《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的出版,則進一步補充了客家研究領域的一塊拼圖。希望本書相關論文的見解可以成為「思考族群或客家研究」的參考。
二、工作坊
作為建構客家學術研究的一塊拼圖,我們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分別在2021年10月17日、23日、30日、31日四天,以線上會議的方式進行「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工作坊」。工作坊之初的構想是希望邀請相關學者引介目前比較常見且有助於研究族群或客家的學說。當時心裡設想的議題大致包括原生論、情境論(工具論)、建構論、集體記憶理論、想像共同體、族群邊界理論、發明的傳統、後殖民論述、多元文化主義、王甫昌的族群想像理論,或王明珂華夏邊緣理論,甚至於系統與生活世界、中間少數族裔理論(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等等。很意外的是,所有工作坊論文投件的摘要,沒有一篇落在我們想像的範圍之內。
本書大部分篇章來自工作坊所發表的論文,部分則是另外邀請而來。工作坊的論文除了在發表時,評論人所提供的意見之外,論文完稿之後均另外提交匿名審查、修訂才收錄於本書。全書共13篇,除了兩位編者的導論與後記之外,區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族群與客家研究的基礎理論,第二部分是關於東南亞客家的案例及不容易歸類在前兩部分的3篇論文。依序簡述如後。
三、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的二階觀察
胡正光所著〈族群研究的若干二階觀察〉,試圖以社會系統理論對族群研究的若干議題進行二階觀察。他指出,社會系統理論的族群研究不是告訴我們「什麼是族群?」而是觀察「社會如何觀察族群?」胡正光指出二階觀察是觀察的觀察,一階觀察可說是「運作的觀察」,系統觀察「某些事正在發生」,於此同時也就進行著溝通。這是一種尋找確定性的觀察,尋找事物的「本質」。相對的,觀察可以觀察任何事物,也可以觀察另一個觀察,即所謂的二階觀察。該文在「族群界線的二階觀察」一節中指出:不論如何用原生性劃分族群界線,都會被看見弔詭,也就是「不能區分」的問題,看見弔詭的二階觀察者試圖解開弔詭,可能提出了新的說法,例如Barth提出邊界論將族群界線從原本文化特徵的描述轉換成互動模式的對照,可說樹立了一個族群界線的典範,在社會系統理論來說,就是試圖解開區分弔詭的嘗試。
看見族群界線弔詭的二階觀察者不再將劃分族群界線當成重點,而有建構論的說法,所謂「原生論」與「建構論」的爭辯,其實是一階觀察與二階觀察的差異。建構論代表的是對「區分」弔詭的發現,進而宣稱原生性只是一種「想像」,不是一種「實在」。因為從族群的客觀特質中無法區分族群,觀察者放棄描述族群界線,建構論者轉向「族群如何建構」的提問,例如「客家何以是客家」,不再將客家當作理所當然的存在,而去考掘「客家之前的客家」,觀察客家認同、客家意識的塑造過程。答案通常以一個過程呈現。此文的論點可和張維安一文的觀點對照討論。
張維安的〈客家族群源流理論之知識社會學分析〉一文,處理的議題是北方漢人客家源流學說浮現的時代脈絡。過去客家源流學說中,客家本質主義者假定有一個客觀的、本體論的客家族群存在,所以有「客家的本真性」。該文認為客家成為一個族群是時代的產物,並不存在自然科學式「客家本質」的提問,「先驗的」客家社會實體本來並不存在,客家族群所普遍接受的客家北方漢人說是一個「社會真實」(相對於歷史事實)。該文從知識社會學觀點,探索此種客家源流的知識如何被創造出來?為何創造?誰創造出來的?首先,從韋伯社會學理念型的方法論指出,認識社會現象的部分性、有限性及主觀性;其次從知識社會學的旨趣分析,客家源流知識除了要探索其經驗性、歷史性內容外,更需了解其產生的社會條件跟時代背景。社會科學固然要討論「真實」是什麼,更需要了解產生這種知識見解的社會脈絡與社會背景。
客家北方漢人說使我們思考,客家為什麼想要作為漢人,相對於作為非漢人又如何?客家要作為血統純正的漢人,作為血統沒有這麼純正的漢人又會怎樣?客家作為貴冑之後,客家為何不能主張出身於相對平庸的一般平民?客家如何和其他人群劃界?判準為何?在每一個問題和答案的背後,都可以發現其思想的運作模式,再深入探究就會發現它和客家團體的社會處境,與當時支配社會的意識形態有關。相關細節的討論,請參見該文內容。
河合洋尚的〈客家族群研究的人類學知識分析:從民系論、族群論到空間論?〉一文,為了讓讀者理解客家理論研究的基礎,梳理了客家族群研究史。該文以人類學和歷史學為中心,特別關注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之間逐漸發生的從民系論到族群論的轉換。20世紀前期客家學的開山鼻祖羅香林提倡的民系論以及客家中原起源說,後來被廣大的社會接受為關於客家的「常識」,但另一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川學等學者開始懷疑羅香林的學說,90年代房學嘉提出了客家土著起源說。同時,社會人類學家瀬川昌久借用巴爾特(Fredrik Barth)的族群邊界論,指出了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廣府人、福佬人、畲族等)的族群範圍不是固定的,會依隨社會背景而變化。加之,日本、中國大陸、臺灣的歷史學家逐漸地探討在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前期的社會背景下客家族群認同產生的過程,推進了客家建構論的能見度。
該文支持客家族群建構論,但指出這個理論範例較缺乏關注20世紀後期之後客家族群認同產生的過程。不管中國大陸還是臺灣,客家這個詞語在民間被普遍接受,都是20世紀後期之後的事情。在20世紀前期、中期之前強調客家概念的主要是精英階層,現在被稱為客家的居民,當時民間則稱之為「客人」、「廣東人」、「艾人」、「麻介人」等。一些人類學家指出,「客人」、「廣東人」等的範圍和今日的客家人不一定完全一致。因而,21世紀10年代之後日本等地客家界開始關注客家族群的「再創生」過程。客家族群的「創生」就是20世紀前半客家族群認同產生的過程,對此「再創生」是20世紀後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客家族群認同重新產生的過程。該文還論述了「再創生」的課題以及最近的研究動向。
接下來,河合洋尚在〈客家文化研究的空間論轉向緒論〉一文梳理客家文化研究的理論動向。一般被想像的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在生活當中形成的精神或物質結晶。可是,河合洋尚指出,有人一說起客家文化就形容客家民系具有的—與其他民系不同的—特色,這樣的文化概念與作為生活方式的古典客家文化概念相乖離。以圓樓的例子來講,對梅縣或者臺灣的居民來說,圓樓不是他們在生活當中製造的物質文化,但由於開發商等認為這是客家的特色文化,便建設模仿圓樓形狀的建築。就這樣,客家文化這個概念其實有不同含義。
河合洋尚在回顧客家文化研究當中論述,雖然客家文化研究的成果相當豐富,但學者們卻很少討論客家文化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河合洋尚強調,「客家文化」是在學術上發明的,往往是學者將客家和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進行區分時運用的概念,後來作為族群特色的客家文化成為被媒體、政府、開發商、商人,甚至居民等利用的資源。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內外一些被視為是客家人居住地的區域。雖然這些區域(粵閩贛交界區、廣西博白、陸川、四川成都的洛帶鎮、臺灣南部六堆地區等)裡有不少非客家人居住,但在社會上依然被視為是客家地區。由於政府、開發商、商人、居民等利用客家文化這個論述來描述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地區便成為充滿著客家文化符號的「客家空間」。河合洋尚通過關注客家文化這個概念製造客家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一面,促進客家文化研究的空間論轉向。可以說他的論調是客家文化研究的二階觀察。
張維安所寫的〈族群主流化理念之探討〉,以楊長鎮的研究為主軸,引介族群主流化的理念。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進程,臺灣的族群認同開始崛起,族群在社會構成的議題中,逐漸成為論述的軸心。族群議題除了檢視公共體制的偏差與「社會」對於原住民族與客家文化的陌生,甚至於扭曲與偏見外,還與國家認同的向度相互交織。儘管族群部會已經成立多時,族群媒體也相繼設立,不過當前臺灣多元族群理念的加法模式,族群權益嘉年華化的思維,忽略族群權益的結構性問題。多元族群文化認識的表面化,產生許多無助於解決族群權力結構的「多元歡樂」政策,徒有節慶活動(如所謂聯合豐年祭、客家的桐花節、移工的潑水節與開齋節)及觀光消費、歌舞表演的「多元」表象,卻難以翻轉既有權力關係上的不平等。
有鑑於此,族群主流化的概念最早出現在2011年民主進步黨《十年政綱》的族群篇。族群主流化理念主張族群政策的想像不應囿限於個別族群支持的範疇,也不是科層體系的部門政策足以因應。⋯⋯族群政策應轉向以族群關係為中心的想像,並參考「性別主流化運動」的思維,進行「族群主流化」的政策重構,其目標是建立一般性公共政策的族群敏感度、建構跨族群文化的公共領域及國家象徵資源的共享共構。族群主流化希望各級政府部門、民間社群都要具備基本的族群敏銳度,並讓社會大眾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族群關係的當事人,進而促使多元族群都能共同參與社會主流的建構。該文提到幾個理念,對於了解族群主流化的主張有一定程度的幫助:族群人、第四代人權(共同權與群體權)、分族分工的族群行政之不足、族群存在於族群關係之間(族群關係需要從社會脈絡來理解)、弱勢群體的主流化、弱勢議題的主流化。
楊國鑫在〈試論客家學的方法論與理論〉一文中,處理客家學的定義、發生、方法論與理論等大概念,作者認為「客家學」是指研究某一時間點的客家,研究某一地理空間的客家歷史、文化以及生存發展事情的學問。通常是緣於要去解決一些問題,舉例客家語言被打壓,客家文化被流失甚至於被消失時,為了回應、解決這些問題,從而進行相關的研究,而有客家學的產生。除了解決客家族群面臨的問題之外,為了個人的疑惑、驚奇,甚至是為了一些利益,而對客家進行研究,因其對客家問題有所回應、對客家的驚奇有所解讀,或者具有探究客家自我的意義,該文認為這些研究一樣也可稱之為「客家學」。為什麼會有客家學?該文主張客家學的出現緣於回應客家問題或客家驚奇的探究。首先是回應客家族群面臨的問題,不同時空會出現不同的客家問題。其次是解讀客家族群本身內涵的問題,這種研究的客家學有時候具有工具性價值,可以幫助傳教、支持僑政、爭取客家選票等等。
客家學的方法論方面,楊國鑫指出建構客家學理論,需要先探究客家學的方法論。客家學的方法論是以跨領域研究取徑為基礎,來理解這個世界;以長期關注探究客家問題與原因,加上哲學探究來回應客家問題的規範之學;以多元社會文化理論與文化創新理論等來回應客家問題的適應之學;最後,是以將客家驚奇之說放入括弧,將驚奇之說作為研究的議題,不是在毫無反思與研究的情況下,理所當然的接受,將日常生活的「自然態度」,轉化成反思與研究的議題。在客家學理論方面,作者認為凡是能夠理解客家世界的皆是可以運用的理論,皆是客家學的理論。基本上,這代表作者多年來的看法,和本書其他篇章的切入點有一些不同。
王保鍵的〈「國家制度化的族群」概念建構:族群優惠性差別待遇與族群認同〉,指出國家政策對於族群形塑的效果,「國家制度化的族群」概念指涉,國家法律可以建構族群,如《戶籍法》的省籍登記,造成本省人、外省人的族群之別。原住民身分的認同則是從根據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採認日治戶口調查簿登記資料,2022年時從單純的「血統」標準,納入文化特徵、族群認同、客觀歷史紀錄作為認定原住民身分的要件。國家法律可以肯認族群,可以再重新定義族群的範圍。在國家制度安排下的人群類屬,及因族群身分所享有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有助於提升族群身分認同。
相對於過去習慣從本質論、工具論等角度來看族群的形成,這種由國家的政策、法規所形塑出來的族群分類的案例,卻提供了另外一個族群分類的政治經濟基礎解讀。關於臺灣國家制度化族群的形成,該文區分為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府時期加以分析,從具體的案例以及制度性的資源分配來看,國家政策後果以及制度性的設計,甚至於是人口調查問卷的分類,都可能是形成族群的動因。該文針對國府時期的各項制度安排有詳細的分析,其各種公職考試的分配,正如清領時期省籍與學額的制度設計那樣,牽涉到不同人群的資源分配,制度的資源分配助長了族群認同的歸屬。雖然族群的分類與認同往往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不過王保鍵的論文也提到族群的能動性,他以臺灣原住民的民族正名、還我土地等社會運動的訴求為例,看到原住民族對於國家制度安排的影響。當然這種情形之所以可能發生的民主環境條件,是不可或缺的。
(未完.詳全書)
一、前言
理論,固然可以在字典上查到定義。不過在讀者的心中,可能並非只有一個說法。記得在學校讀社會學時,從大學生到博士生,每個階段都要修一門「社會學理論」,有時又分成古典社會學理論和當代社會學理論,或進階的選讀批判理論、系統理論,古典時期的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學理論流派,在當代社會學理論中又有功能論、衝突論、互動論……除了西方的社會學理論,還發展本土社會學理論,有時還把理論分成巨型理論、中程理論。這樣的「理論」仍每日在繼續創造中。不同的理論各有其解釋歷史社會的角度,彼此之間時而互補,時而存在截然不同的論點,這些理論的提出涉及獨特的學術思想脈絡、獨特的歷史社會情境,當然也和發展理論的政治經濟環境、理論家的學養有關。也許沒有接近真理(如果有的話)的理論,不過理論的閱讀,了解理論之間的對話,相互之間的評論、反思,卻有助於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與闡明。《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一書的「理論」概念,適合用上述的觀點來理解。「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並沒有提供一個研究族群或客家的框架或指導原則,本書各篇論文也非在一個內部一致的理論典範之下進行寫作,彼此之間有些存有共識,但也存在不同的立場與觀點。
本書的出版作為建構客家學術研究的一環,如韋伯所說,學術工作和一個進步的過程不可分離⋯⋯在學術園地裡,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10、20、50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的「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它要求過時(Weber, 1946: 138;轉引自黃瑞祺,2013:141),期待未來有其他的研究來補充、來超越。客家族群身分的浮現和學術理念的論述息息相關,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發問方式,不同觀點與證據成就了不同的客家樣貌。19世紀中國客籍縣認同的客家,20世紀全球化架構下的客家,其所存在的樣貌,其所具有的客家性,需要不同的理論來詮釋。
客家研究這個領域被提出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不過客家研究要成為像社會學或人類學這樣的學科,目前還沒有足夠的基礎,現在仍屬於吸收各學科養分的階段,各種社會科學的理論中,有些對於客家議題的關心與思考具有較強的選擇性、親近性,可逐漸吸收或轉化為客家學核心知識的訓練基礎,這些知識可能來自於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語言學等等;其相應的研究方法,例如田野考察、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口述歷史、敘事分析、文化論述等等,也是要做好客家研究所不能缺少的訓練(張維安,2005:3)。相對於客家研究,族群研究似乎要更成熟一些,熟悉各種族群研究的觀點與方法,對客家研究的進程,有一定的幫助。
從實務上來說,在客家研究作為一個專業領域的目標下,最少需要有嚴謹的課程規劃,學術社群組織的建立,專業的客家研究期刊,客家研究專門領域的讀本,專業的學術研討會,客家研究專業的學術單位,更重要的是學術界要有源源不斷的客家研究專書出版。在這個脈絡下,過往客家學界已經做了相當程度的努力,幾年前《全球客家研究》期刊曾經做過許多研究成果的統計,有助於想像客家研究的成績,例如〈客家研究臺灣相關期刊論文書目彙編:2010-2013年〉(陳璐誼,2014)、〈中文客家叢書目錄整理〉(劉堉珊,2014)、〈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目錄整理〉(劉堉珊,2015)、〈2015年中國客家研究期刊論文書目彙編〉(張珈瑜,2016),特別是〈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彙編〉(2011-8)(許維德,2013;張珈瑜,2015,2017,2019)。從許維德等的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統計來看,從2011至2018年的8年間,一共有1,990篇與客家研究相關的碩博士論文產出,平均每年248篇。易言之,平均每3天就有2本碩博士論文產出,年輕學子的投入,對客家研究學界實是莫大的鼓舞。
臺灣客家研究已經累積相當多的成果,甚至在研究典範上經歷了一些轉移(蕭新煌,2018)。近年來我們則努力在全球客家方面進行比較研究,例如與日本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合辦會議,出版《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河合洋尚、張維安,2020),甚至成立全球客家研究聯盟(2019年12月),出版《全球客家研究的實踐與發展》(張維安、簡美玲,2021)。研究方法方面的成果則出版了《客家與族群研究的技藝》(張維安、潘美玲、許維德,2021),如今《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的出版,則進一步補充了客家研究領域的一塊拼圖。希望本書相關論文的見解可以成為「思考族群或客家研究」的參考。
二、工作坊
作為建構客家學術研究的一塊拼圖,我們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分別在2021年10月17日、23日、30日、31日四天,以線上會議的方式進行「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工作坊」。工作坊之初的構想是希望邀請相關學者引介目前比較常見且有助於研究族群或客家的學說。當時心裡設想的議題大致包括原生論、情境論(工具論)、建構論、集體記憶理論、想像共同體、族群邊界理論、發明的傳統、後殖民論述、多元文化主義、王甫昌的族群想像理論,或王明珂華夏邊緣理論,甚至於系統與生活世界、中間少數族裔理論(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等等。很意外的是,所有工作坊論文投件的摘要,沒有一篇落在我們想像的範圍之內。
本書大部分篇章來自工作坊所發表的論文,部分則是另外邀請而來。工作坊的論文除了在發表時,評論人所提供的意見之外,論文完稿之後均另外提交匿名審查、修訂才收錄於本書。全書共13篇,除了兩位編者的導論與後記之外,區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族群與客家研究的基礎理論,第二部分是關於東南亞客家的案例及不容易歸類在前兩部分的3篇論文。依序簡述如後。
三、族群與客家研究理論的二階觀察
胡正光所著〈族群研究的若干二階觀察〉,試圖以社會系統理論對族群研究的若干議題進行二階觀察。他指出,社會系統理論的族群研究不是告訴我們「什麼是族群?」而是觀察「社會如何觀察族群?」胡正光指出二階觀察是觀察的觀察,一階觀察可說是「運作的觀察」,系統觀察「某些事正在發生」,於此同時也就進行著溝通。這是一種尋找確定性的觀察,尋找事物的「本質」。相對的,觀察可以觀察任何事物,也可以觀察另一個觀察,即所謂的二階觀察。該文在「族群界線的二階觀察」一節中指出:不論如何用原生性劃分族群界線,都會被看見弔詭,也就是「不能區分」的問題,看見弔詭的二階觀察者試圖解開弔詭,可能提出了新的說法,例如Barth提出邊界論將族群界線從原本文化特徵的描述轉換成互動模式的對照,可說樹立了一個族群界線的典範,在社會系統理論來說,就是試圖解開區分弔詭的嘗試。
看見族群界線弔詭的二階觀察者不再將劃分族群界線當成重點,而有建構論的說法,所謂「原生論」與「建構論」的爭辯,其實是一階觀察與二階觀察的差異。建構論代表的是對「區分」弔詭的發現,進而宣稱原生性只是一種「想像」,不是一種「實在」。因為從族群的客觀特質中無法區分族群,觀察者放棄描述族群界線,建構論者轉向「族群如何建構」的提問,例如「客家何以是客家」,不再將客家當作理所當然的存在,而去考掘「客家之前的客家」,觀察客家認同、客家意識的塑造過程。答案通常以一個過程呈現。此文的論點可和張維安一文的觀點對照討論。
張維安的〈客家族群源流理論之知識社會學分析〉一文,處理的議題是北方漢人客家源流學說浮現的時代脈絡。過去客家源流學說中,客家本質主義者假定有一個客觀的、本體論的客家族群存在,所以有「客家的本真性」。該文認為客家成為一個族群是時代的產物,並不存在自然科學式「客家本質」的提問,「先驗的」客家社會實體本來並不存在,客家族群所普遍接受的客家北方漢人說是一個「社會真實」(相對於歷史事實)。該文從知識社會學觀點,探索此種客家源流的知識如何被創造出來?為何創造?誰創造出來的?首先,從韋伯社會學理念型的方法論指出,認識社會現象的部分性、有限性及主觀性;其次從知識社會學的旨趣分析,客家源流知識除了要探索其經驗性、歷史性內容外,更需了解其產生的社會條件跟時代背景。社會科學固然要討論「真實」是什麼,更需要了解產生這種知識見解的社會脈絡與社會背景。
客家北方漢人說使我們思考,客家為什麼想要作為漢人,相對於作為非漢人又如何?客家要作為血統純正的漢人,作為血統沒有這麼純正的漢人又會怎樣?客家作為貴冑之後,客家為何不能主張出身於相對平庸的一般平民?客家如何和其他人群劃界?判準為何?在每一個問題和答案的背後,都可以發現其思想的運作模式,再深入探究就會發現它和客家團體的社會處境,與當時支配社會的意識形態有關。相關細節的討論,請參見該文內容。
河合洋尚的〈客家族群研究的人類學知識分析:從民系論、族群論到空間論?〉一文,為了讓讀者理解客家理論研究的基礎,梳理了客家族群研究史。該文以人類學和歷史學為中心,特別關注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之間逐漸發生的從民系論到族群論的轉換。20世紀前期客家學的開山鼻祖羅香林提倡的民系論以及客家中原起源說,後來被廣大的社會接受為關於客家的「常識」,但另一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川學等學者開始懷疑羅香林的學說,90年代房學嘉提出了客家土著起源說。同時,社會人類學家瀬川昌久借用巴爾特(Fredrik Barth)的族群邊界論,指出了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廣府人、福佬人、畲族等)的族群範圍不是固定的,會依隨社會背景而變化。加之,日本、中國大陸、臺灣的歷史學家逐漸地探討在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前期的社會背景下客家族群認同產生的過程,推進了客家建構論的能見度。
該文支持客家族群建構論,但指出這個理論範例較缺乏關注20世紀後期之後客家族群認同產生的過程。不管中國大陸還是臺灣,客家這個詞語在民間被普遍接受,都是20世紀後期之後的事情。在20世紀前期、中期之前強調客家概念的主要是精英階層,現在被稱為客家的居民,當時民間則稱之為「客人」、「廣東人」、「艾人」、「麻介人」等。一些人類學家指出,「客人」、「廣東人」等的範圍和今日的客家人不一定完全一致。因而,21世紀10年代之後日本等地客家界開始關注客家族群的「再創生」過程。客家族群的「創生」就是20世紀前半客家族群認同產生的過程,對此「再創生」是20世紀後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客家族群認同重新產生的過程。該文還論述了「再創生」的課題以及最近的研究動向。
接下來,河合洋尚在〈客家文化研究的空間論轉向緒論〉一文梳理客家文化研究的理論動向。一般被想像的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在生活當中形成的精神或物質結晶。可是,河合洋尚指出,有人一說起客家文化就形容客家民系具有的—與其他民系不同的—特色,這樣的文化概念與作為生活方式的古典客家文化概念相乖離。以圓樓的例子來講,對梅縣或者臺灣的居民來說,圓樓不是他們在生活當中製造的物質文化,但由於開發商等認為這是客家的特色文化,便建設模仿圓樓形狀的建築。就這樣,客家文化這個概念其實有不同含義。
河合洋尚在回顧客家文化研究當中論述,雖然客家文化研究的成果相當豐富,但學者們卻很少討論客家文化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河合洋尚強調,「客家文化」是在學術上發明的,往往是學者將客家和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進行區分時運用的概念,後來作為族群特色的客家文化成為被媒體、政府、開發商、商人,甚至居民等利用的資源。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內外一些被視為是客家人居住地的區域。雖然這些區域(粵閩贛交界區、廣西博白、陸川、四川成都的洛帶鎮、臺灣南部六堆地區等)裡有不少非客家人居住,但在社會上依然被視為是客家地區。由於政府、開發商、商人、居民等利用客家文化這個論述來描述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地區便成為充滿著客家文化符號的「客家空間」。河合洋尚通過關注客家文化這個概念製造客家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一面,促進客家文化研究的空間論轉向。可以說他的論調是客家文化研究的二階觀察。
張維安所寫的〈族群主流化理念之探討〉,以楊長鎮的研究為主軸,引介族群主流化的理念。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進程,臺灣的族群認同開始崛起,族群在社會構成的議題中,逐漸成為論述的軸心。族群議題除了檢視公共體制的偏差與「社會」對於原住民族與客家文化的陌生,甚至於扭曲與偏見外,還與國家認同的向度相互交織。儘管族群部會已經成立多時,族群媒體也相繼設立,不過當前臺灣多元族群理念的加法模式,族群權益嘉年華化的思維,忽略族群權益的結構性問題。多元族群文化認識的表面化,產生許多無助於解決族群權力結構的「多元歡樂」政策,徒有節慶活動(如所謂聯合豐年祭、客家的桐花節、移工的潑水節與開齋節)及觀光消費、歌舞表演的「多元」表象,卻難以翻轉既有權力關係上的不平等。
有鑑於此,族群主流化的概念最早出現在2011年民主進步黨《十年政綱》的族群篇。族群主流化理念主張族群政策的想像不應囿限於個別族群支持的範疇,也不是科層體系的部門政策足以因應。⋯⋯族群政策應轉向以族群關係為中心的想像,並參考「性別主流化運動」的思維,進行「族群主流化」的政策重構,其目標是建立一般性公共政策的族群敏感度、建構跨族群文化的公共領域及國家象徵資源的共享共構。族群主流化希望各級政府部門、民間社群都要具備基本的族群敏銳度,並讓社會大眾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族群關係的當事人,進而促使多元族群都能共同參與社會主流的建構。該文提到幾個理念,對於了解族群主流化的主張有一定程度的幫助:族群人、第四代人權(共同權與群體權)、分族分工的族群行政之不足、族群存在於族群關係之間(族群關係需要從社會脈絡來理解)、弱勢群體的主流化、弱勢議題的主流化。
楊國鑫在〈試論客家學的方法論與理論〉一文中,處理客家學的定義、發生、方法論與理論等大概念,作者認為「客家學」是指研究某一時間點的客家,研究某一地理空間的客家歷史、文化以及生存發展事情的學問。通常是緣於要去解決一些問題,舉例客家語言被打壓,客家文化被流失甚至於被消失時,為了回應、解決這些問題,從而進行相關的研究,而有客家學的產生。除了解決客家族群面臨的問題之外,為了個人的疑惑、驚奇,甚至是為了一些利益,而對客家進行研究,因其對客家問題有所回應、對客家的驚奇有所解讀,或者具有探究客家自我的意義,該文認為這些研究一樣也可稱之為「客家學」。為什麼會有客家學?該文主張客家學的出現緣於回應客家問題或客家驚奇的探究。首先是回應客家族群面臨的問題,不同時空會出現不同的客家問題。其次是解讀客家族群本身內涵的問題,這種研究的客家學有時候具有工具性價值,可以幫助傳教、支持僑政、爭取客家選票等等。
客家學的方法論方面,楊國鑫指出建構客家學理論,需要先探究客家學的方法論。客家學的方法論是以跨領域研究取徑為基礎,來理解這個世界;以長期關注探究客家問題與原因,加上哲學探究來回應客家問題的規範之學;以多元社會文化理論與文化創新理論等來回應客家問題的適應之學;最後,是以將客家驚奇之說放入括弧,將驚奇之說作為研究的議題,不是在毫無反思與研究的情況下,理所當然的接受,將日常生活的「自然態度」,轉化成反思與研究的議題。在客家學理論方面,作者認為凡是能夠理解客家世界的皆是可以運用的理論,皆是客家學的理論。基本上,這代表作者多年來的看法,和本書其他篇章的切入點有一些不同。
王保鍵的〈「國家制度化的族群」概念建構:族群優惠性差別待遇與族群認同〉,指出國家政策對於族群形塑的效果,「國家制度化的族群」概念指涉,國家法律可以建構族群,如《戶籍法》的省籍登記,造成本省人、外省人的族群之別。原住民身分的認同則是從根據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採認日治戶口調查簿登記資料,2022年時從單純的「血統」標準,納入文化特徵、族群認同、客觀歷史紀錄作為認定原住民身分的要件。國家法律可以肯認族群,可以再重新定義族群的範圍。在國家制度安排下的人群類屬,及因族群身分所享有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有助於提升族群身分認同。
相對於過去習慣從本質論、工具論等角度來看族群的形成,這種由國家的政策、法規所形塑出來的族群分類的案例,卻提供了另外一個族群分類的政治經濟基礎解讀。關於臺灣國家制度化族群的形成,該文區分為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府時期加以分析,從具體的案例以及制度性的資源分配來看,國家政策後果以及制度性的設計,甚至於是人口調查問卷的分類,都可能是形成族群的動因。該文針對國府時期的各項制度安排有詳細的分析,其各種公職考試的分配,正如清領時期省籍與學額的制度設計那樣,牽涉到不同人群的資源分配,制度的資源分配助長了族群認同的歸屬。雖然族群的分類與認同往往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不過王保鍵的論文也提到族群的能動性,他以臺灣原住民的民族正名、還我土地等社會運動的訴求為例,看到原住民族對於國家制度安排的影響。當然這種情形之所以可能發生的民主環境條件,是不可或缺的。
(未完.詳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