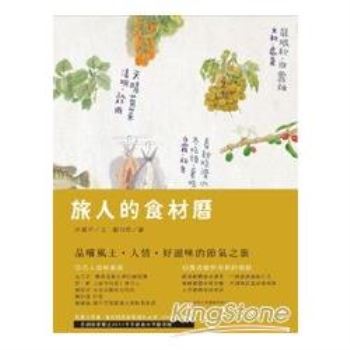小暑.國曆七月七日或八日|大暑.國曆七月廿三日或廿四日
花生.絲瓜.小管.南瓜
暑氣如潮的七月,我到美濃一遊。
當晚與朋友到小吃店吃飯,我們吃了粄條、豬腳、冬瓜封,最後老闆端上一盤花生豆腐,我嚐了一口,冰冰涼涼的綿綿口感,不僅消除暑氣,竟發現那股濃郁滋味好熟悉啊,記憶突然湧上心頭,我想起十多年前的往事。
那時我在屏東服預官役,曾北上找尋一個逾假未歸的逃兵,後來被我順利找到,我們在深夜搭遊覽車回屏東,在台中中清休息站下車休息,他利用我跟他母親講電話,稍一不留神,轉身拔腿就跑。我摔下電話,在黑夜中一路狂奔,但始終差他一大段距離,最後看到他在交流道攔下計程車後迅速消失無蹤。
我沮喪地回到部隊,被長官罵到臭頭,家長甚至責怪我,要部隊負責,這個打擊讓我對人性失去信心。一個跟我蠻談得來的新兵剛收假,帶了家鄉特產、用花生跟米做的花生豆腐為我打氣。我好奇吃了一口,很有彈性,不像一般豆腐軟塌易碎,淡淡花生香還帶點奶香,口感細緻扎實有彈性,很像奶酪,他還建議我淋上醬油膏試試看,鹹鹹甜甜反而讓滋味更奇特。
意外的美食,以及新兵的熱誠,我當下的低落心情突然得到釋懷。
大地母親的滋味
故事過了十多年,此刻的我更好奇花生豆腐的美好滋味怎麼來的?客家人米食文化原本就很獨特,像粄條、米苔目,或是發粿,但是將花生與米結合的傳統客家花生豆腐更特別,除了吃原味,淋上醬油膏、撒蔥薑蒜末,或加上用蒜頭爆香的蝦米、菜脯與碎肉,甚至當成甜點,都各有好滋味。
隔天清早,我騎腳踏車到菜市場閒逛,好幾攤都在賣花生豆腐,其中一個中年太太笑容可掬,我上前閒聊,她大方告訴我這是自家種的當令花生,將花生泡水與米磨成米漿,加入地瓜粉、糖與鹽之後,再倒入滾燙熱水。調勻後,將濃稠的乳白米漿舀到鐵盤裡,蓋上鐵蓋用大火蒸熟,再用電風扇吹涼約三、四個小時,就可以切塊食用。
食材簡單,手續簡單但耗時,卻更凸顯花生的樸實味道,「那是我媽媽傳承的味道。」她說。
鍾鐵民在〈祈福〉這篇小說,描寫母親大熱天在花生田摘花生,兒子陪她一起工作,母親額際鼻尖都是晶瑩汗珠,卻沒喊熱,只是親切詢問兒子學校狀況,鎮撫他的浮動心情。兒子好奇問:「媽,你不熱嗎?」母親愕然片刻,微笑地看看天,隨即擦擦汗,像告訴他祕密似地說:「怎麼不熱啊,你這憨古。」母親似乎把曬在兒身上的光和熱承擔起來,還當作是莫大快樂。
也許我懷念的,就是像花生這種帶著盛夏熱情的大地母親味道吧。
小暑花生正逢時
七月節氣是小暑與大暑,農諺說:「小暑過,一日熱三分。」說明小暑之後,天氣一天比一天熱,到大暑達到極致。農諺也說:「小暑大暑,有米也懶煮。」這種大熱天,讓人發懶到連三餐都懶得動手。我在美濃的清晨卻看到農家勤勞地在院子曬花生,遠山的山影,似乎將農人的腰壓得更低。
一年兩作,春秋播種,夏冬收成,耐旱耐熱耐雨的花生,此刻也是盛產節令。花生是早期台灣跟常民生活最密切的作物之一,詩人吳晟在〈意象〉這首詩提到:「在濁水溪畔廣大溪埔地/我的足跡仍仔細刻寫的田土上/水稻、蕃薯、花生或玉米/奮力蔓延根鬚,伸展枝葉/那就是我最直接最鮮活的詩作意象」。
花生埋在土裡,沒有豔果張揚,卻安分守己,誠誠懇懇,早在明清時代的台灣移民社會,就扮演重要的生活功能。例如環境惡劣的澎湖人以花生為主要作物,用來榨油,油渣可以肥田,花生藤蔓可以當柴火,枝葉能餵養牛羊。
康熙晚年、大約是十八世紀初,花生油也繼芝麻油之後成為民生用油,花生油俗稱「火油」,是燃燈油料,乾隆之後花生油搖身一變,成為台灣重要出口貿易產品,後來花生油才從燃料轉變成食用油。
花生也是平民重要的零食。《本草綱目》說,落花生炒熟辛香,辛能潤肺,香能舒脾,是果中佳品。因此,康熙年間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在這本被譽為是描寫台灣風土隨筆代表作的《台海使槎錄》,其中一篇〈赤崁筆談〉就描寫花生是百姓的重要零食:「居人非口嚼檳榔,即啖落花生。童稚將炒熟者用紙包裹,鬻於街頭,名落花生包。」
原來當時百姓不是吃檳榔,就是吃花生閒磕牙,小孩在街頭賣炒熟的落花生包的場景,宛如在目,很有意思。
像雲林就是花生主要產區,其中元長鄉花生產量居雲林之冠,台灣發展史上的政經與宗教重鎮的北港,則以花生油、花生加工品聞名。北港溪沖積出來的沙埔地,成為種植花生的最佳產地,北港花生顆粒大,油脂多,加上位於雲林、嘉義、台南與彰化的中心,成為海運與陸運的樞紐,讓北港花生油成為北港重要的經濟產品。
比方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北港的花生油工廠就有三十多家,全盛時期甚至高達上百家。十多年前北港推出新產品黑金剛,體型結實碩大、深紫色的花生仁跟傳統褐色花生仁大不同,口感香酥濃郁,像個胖娃娃,馬上就贏得台灣人的喜愛。
澎湖土豆粿,百年家鄉味
除了本島雲林之外,外島澎湖也是花生知名產地。澎湖的朋友常說,澎湖花生最有家鄉味道,連來台定居之後,也忘不了那個老滋味。
從台灣發展史來看,花生是從大陸先引進到澎湖,再傳到台灣本島。澎湖花生栽植歷史早,但環境最惡劣。由於澎湖土壤是玄武岩風化而成,屬於鹽分含量高的土壤,養分不足,花生一年僅能一穫,每年六、七月是產季,也許因為時間醞釀較久,加上海風淬鍊的生命力,讓澎湖花生外形又大又長,結實飽滿,因此澎湖花生酥就是知名觀光伴手禮。
在澎湖吃飯,花生幾乎無所不在,一道清炒高麗菜,是用碎花生來拌炒,能嚐到菜甜與花生顆粒香。因為早期澎湖人沒有什麼動物油可用,藉著花生碾碎的油就能用來炒菜。即使是吃臭肉鮭,還能用花生米沾臭肉鮭汁,咀嚼鹹甜鹹甜的滋味。
但讓我著迷的卻是澎湖用來祭祖拜神、平常少見的土豆粿。
那是一個謎樣村落的特產,位在西嶼、有百年歷史的二崁村。這是澎湖少見的單姓聚落,陳姓宗族四百年前從金門夏興村移民來此,傳承十五代的二崁,是澎湖現今保存完整,擁有四十多棟古厝、六十多人居住的村莊。
二崁過去被稱為中醫村,因為一百多年前曾發生瘟疫,有族人到台灣學中醫想要幫族人治病,慢慢吸引其他族人前往台灣學中醫,他們在高雄、嘉義等地行醫發達之後,返鄉興建陳家宗祠,也運送上等建材打造家園。
有了宗祠,人口仍大量外流,因為他鄉的富庶,更顯家鄉的貧乏。前幾年一群陳家第十四代的後人,決定中年轉業,一同返鄉整修恢復聚落外貌,並開設民宿與舉辦文化活動,將沒落的二崁重塑成觀光重鎮。
二崁村跟花生一樣老,老得有樸拙的人生智慧,老得跟花生一樣散發清香。
烈日下,我在老街上閒晃,看到一個小雜貨店,老阿嬤坐在外頭乘涼,見我路過,輕聲招呼買土豆粿。土豆粿看起來不太起眼,我仍好奇買來吃吃看,花生餡又香又細,糯米粿皮很有彈性,詢問後,才知道這是二崁人傳統祭拜的供品,因為要拜神明,點心不能隨便做,花生要先炒過,接著用石杵搗花生,將花生搗碎搗成細粉,再用麵粉與糯米粉、地瓜攪拌製成粿皮來包花生粉,除了增加地瓜香氣,口感也比較好。
我問為何不用機器碾花生粉?滿臉風霜、皮膚黝黑的老阿嬤說,手工才細,也有誠意,這是傳統。
我走到隔壁的小吃店,吃了包裹竹筍與碎肉的金瓜粿,老闆也招待我吃花生。聊到他們從台灣回到老家定居,老闆說這裡夏天熱、冬天冷,土地貧瘠,作物都養不活,只有花生產最多,但是他們懷念家鄉,用在地食材做點小生意,就能養活一家人。
探頭看他們家裡的廚房,大灶正在蒸粿,熱氣四散,太太則在炒花生,觀光客經常來此休息,吃花生、吃金瓜粿,聽老闆講二崁故事,返鄉的生活蠻寫意自在。
抬頭望去,眼前是盛夏青綠的草原,再過去就是湛藍大海,海天共長一色,回頭則是澎湖?石搭建的古宅,還有為了防風,用珊瑚礁與玄武岩混合的? 石當建材,圍牆種花生的「菜宅」。
這個壯麗景色,讓小小西嶼在歷史留名。西嶼在大航海時代被荷蘭人稱為漁翁島,大陸移民東渡來台,一定會經過西嶼再到澎湖,或選擇在西嶼停泊休息,清代就以「西嶼落霞」之美成為全台八景之一,與基隆、鹿耳門、安平齊名。乾隆時期的台南籍詩人章甫,搭船路過西嶼,就寫下:「五色文章天上降,九光錦繡水中鋪」的浪漫詩句。
錦繡美景一直未變,只是我們未曾駐足停留。作家梁容若在〈落花生的性格〉這篇散文提到,落花生每棵長的果子並不多,但每顆果子都有發展為一棵新生命的可能,相對柳樹的飛絮這種充滿野心的植物,隨風飄舞,要把種子鋪滿世界,卻不見得有一顆能長成。「落花生安分守己,發展得很慢,腳步卻踏得最堅實。」也許就是這種落葉歸根的力量,讓曾經以為是柳樹飛絮的二崁村民,重新回到家鄉,落地成為堅實的落花生。
不過種花生的腳步,真的需要踏得堅實才行。二崁村人說,三月春雨過後,原本乾硬的土地因雨水滋潤而鬆軟,正是種花生的時刻。儘管此刻風大,二崁村民會一同用牛犁田,將花生均勻灑在凹槽中,再用腳輕輕將兩邊的土踢向凹槽。
踢土也是一門學問。由於得低頭踢土,鬆軟田土踢起來其實很費力,單腳踢時容易被風吹得重心不穩,因此每一步都得將土踏平,又不能太密,腳步要輕盈,力道得均勻,播完種之後,可以看到一排排淺淺的腳印。
聽村人訴說種花生的故事,我猛然想起小時候在高雄林園的鄉下,跟著祖父與家人種花生的情景,我和弟弟跟在牛後頭嬉戲,家人則是撒花生播種,貪玩的弟弟還被牛口水滴到頭髮上,味道又臭又稠,被我嘲笑許久。
也許,當年的田裡,也曾留下我與弟弟淺淺小小的足印吧。
礁溪絲瓜好溫潤
如果說春天要嚐大地甦醒的根莖作物,夏天則要品味清涼去火的瓜類。小暑大暑,天氣越熱,瓜越熟越甜,農諺說「五月瓠、六月瓜」,貼切形容此時該吃各種瓜類,從瓠瓜、絲瓜、南瓜到苦瓜,還有西瓜、哈密瓜,真是瓜瓜相連到天邊。
瓜跟落花生一樣,是農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陳冠學在《田園之秋》說,不管世界怎樣地改變,寧願守著過去老傳統,種田,養牛養狗養貓養雞,種稻種地瓜花生芝麻與玉米,屋角籬邊總有瓜、豆開花結實,大概是菜瓜、瓠瓜與皇帝豆。
這種生活跟兩千多年前《詩經》歌詠的農村文化一脈相承,四時而作。夏天時序要吃瓜,《詩經》寫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南有木,甘瓠累之。」瓠瓜成熟未摘取,老了就變成葫蘆,還是要趁熟吃其甘味。
客語的絲瓜發音聽起來像「瘦瓜」,但絲瓜一點都不瘦,削皮切片後,用小火燜煮,口感多汁多水又柔嫩飽滿。鍾鐵民在〈菜瓜布〉這篇短文說,絲瓜料理不加水最清甜,聽說下莊人煮菜瓜是放水的,所以美濃地區形容東西多得可以盡情享用時,有歇後語說:「下莊嬤煮菜瓜有吃水了!」
台灣的礁溪溫泉絲瓜與澎湖絲瓜,是最特別、又能大口吃水享用的夏季獻禮。
有一次到礁溪,車上跟交通小巴士司機聊天,他提到礁溪絲瓜清炒又甜又不易變黑的特質,跟家鄉具有礦物質的溫泉水有關,我說那不就跟溫泉空心菜一樣,司機說種絲瓜比種空心菜更省空間,而且不需要太花時間照顧,說著說著,他索性載我們到他老家看看溫泉絲瓜。
他開車穿越田間小路,幾經轉折後,到了田邊小路的盡頭,只見眼前一條條筆直巨大的瘦長絲瓜,像吊單槓一樣從棚架上懸掛下來,每個絲瓜尾端還掛著一罐伯朗咖啡,這是要讓它們的身形更筆直挺拔,不會彎彎曲曲影響賣相。
司機大哥說他已住在鎮上,這裡是想泡湯時就跑來棚架旁的浴室洗溫泉,順便看看絲瓜成長進度。過去曾在台北開公車的大哥說,他們礁溪人打開水龍頭,都是流出溫泉水,讓他一直以為自來水都是熱的,一直到台北生活,才知道熱水是需要瓦斯,還要付錢。
離開前,司機大哥摘了好幾條絲瓜給我們,還把浴室鑰匙掛在門上,他說只要我們想泡湯,就自行來此開門、放水,想吃絲瓜就自己摘。不過這個泡湯妙地實在很難找,而那一排排壯觀的翠綠絲瓜則更難忘。
我在宜蘭羅東吃過最有創意的絲瓜料理,是在朋友擔任主廚的饗宴鐵板燒餐廳,主廚程智勇用母親菜園剛摘下的絲瓜,切成圓圓的薄片,再撒上鹽巴煎一下,圓片絲瓜上放上一小捲先燙好的紫蘇麵線,鹽巴激發的絲瓜甜味,加上紫蘇清香,非常清爽特別。
另一道他把宜蘭傳統小吃、用雞高湯熬成再炸過的糕渣做了創新的結合,將雞湯、鹽、雞蛋、絲瓜丁與甜蝦放在一起凝結成凍,再下鍋去炸,外酥內熱口感中,帶有絲瓜清香與蝦子甜味,很有意思。
澎湖絲瓜真甘脆
如果說礁溪絲瓜是圓潤高雅的美人,外形劍拔弩張,有稜有角,身形清瘦的澎湖絲瓜就像一個個性鮮明的戰士。不只是絲瓜,澎湖的瓜類大概是台灣最特殊的瓜類作物。就像澎湖花生一樣,澎湖獨特的生長環境,雕琢出瓜果的海島個性。
古籍《澎湖紀略》記載:「澎湖冬季風大,所以風聲、水聲,無日不聒耳,甚至飛沙走石。冬春則頻旱,自立春至清明,凡所種草芽不發,盡枯焦,至夏方生,立秋以後,草則漸黃,更無花草。」難怪澎湖只適合栽種夏天當令的瓜果,由於一年只有一穫,瓜果生長也比較緩慢。先不談絲瓜,光是澎湖西瓜嘉寶瓜就讓人驚奇,外形小小圓圓,綠色外皮叫翠嘉寶,黃色的則是黃金寶,果肉竟是橘色的,口感清脆,水分又多。
我在澎湖吃的絲瓜料理,方式簡單乾脆。其中一道絲瓜沙西米,先削去稜角外皮,稍微清燙一下,藉著過一下水來降低生絲瓜的腥味,接著泡冰水冰鎮一下,讓外皮更翠綠光滑。
料理後的絲瓜口感很特別,甜甜脆脆,不加沾料就非常好吃。廚師說澎湖絲瓜肉脆皮韌,冰鎮後皮更脆,水分更飽滿,但是台灣絲瓜外皮比較軟,比較不適合生吃。
絲瓜麵線應該就是澎湖美食的最高境界。澎湖的絲瓜麵線很豪邁,先放一點水讓絲瓜滾一下,接著快炒,炒出絲瓜甜味,再放入麵線燙一下,絲瓜的甜,絲瓜的水,不用任何調味料,絲瓜麵線就超清甜好吃,如果再放入海鮮,像小管、鮮魚,真是無與倫比的鮮甜。
記得那天是一大清早出發,我搭乘一艘觀光漁船,先聽船長導覽解說澎湖獨特的玄武岩地質。看著黝黑方正的岩石,經過日曬風吹、海水侵蝕,淬鍊成各種壯觀巨岩奇景,呈現造物者磅礡的鬼斧神工。接著是到員貝嶼附近的漁家定置網區域捕魚,在船長一聲令下,乘客十多人合力拉起定置繩網,撈起花枝、小管與各種魚類,這就是我們的午餐。
夏天的漁產因為都過了產卵期,魚體又瘦又小,缺乏過冬儲存的脂肪,但是澎湖小管卻正當令,中午回到漁船停泊處,等廚師將我們撈起的海鮮料理好,鮮魚麵線、蒸魚與炸花枝就上桌了,其中的鮮魚麵線加了絲瓜,果然又鮮又甜。
有次我參加夜釣小管活動也很有趣,由於小管具有趨光性,從六月到中秋節就成為澎湖人夏季夜晚的漁撈經濟活動跟主食。那天傍晚六點出海,漁船停泊在釣小管海域之後,打開照明燈,發給遊客假餌,讓遊客在漁船兩側下餌垂釣。
小管剛被釣出水時,還會機靈的吐墨汁、吐水。小管剛釣上來身體還是呈現紅色,過陣子就變成透明,船長就開始做小管生魚片,或是煮成小管絲瓜麵線。
同治年間渡海來台編纂《淡水廳志》、《澎湖廳志》的舉人林豪,在〈篝火宵魚〉這首詩描寫澎湖夜釣的樂趣:「絕島潮迴夜色清,滿船風月釣竿輕。細鱗巨口誰分得,為有波心一點明。」
無限量供應的甜脆口感的小管,加上絲瓜的清甜,搭配夜空繁星,跟百年前夜釣相比,更是風月無邊啊。
金瓜米粉甜鬆鮮
夏天也是南瓜成熟的季節。南瓜在西方是童話跟節慶的象徵,在台灣俗名金瓜的南瓜,大概是台灣蔬菜中唯一有「金」的尊榮,這不是金馬車的浪漫童話,而是具有豐富的生活意涵。詩人夏宇在〈南瓜載我來的〉這首詩就傳達南瓜的務實個性:「金黃/澎湃/一棵南瓜/在牆角/暗暗成熟/如我 辛德瑞拉」。
金瓜的金字招牌,除了是營養價值最豐富的瓜果,以及豐沛溫暖的金黃色色澤,金瓜全身都是寶,從根藤葉花果皮到籽都能吃,只要放在涼爽乾燥的地方,還可以儲存很久,成為老一代度過荒年的重要食物。
張詠捷在《食物戀》說,將金瓜、地瓜與菜豆混在一起煮,再加入花生碎塊增加油潤感的金瓜雜煮,是阿嬤那一輩的傳統菜色。我想到早期澎湖人以海藻、魚蝦與地瓜、小米煮成的「糊塗粥」,類似金瓜雜煮,把只要當令能吃的東西都放在一起煮,是離島的營養食品。
金瓜具有點石成金的魔力,透過煎炒煮炸就能變出許多美味營養好菜。金瓜米粉就是將最普通的食材變成最濃香的好味,在澎湖經常是在地人祭祖的食品,將金瓜切成細條狀,加蝦米、花枝與米粉一起炒,澎湖金瓜特色是不易糊掉,可以吃到金瓜的甜度跟濃稠口感,加上海鮮滋味與鬆而不爛的米粉,令我一碗接一碗。
我去苗栗南庄吃到客家人的家常菜金瓜飯,記憶格外深刻。端上桌時,這一大盤金黃色的飯就讓人引起食欲,口感帶著濃厚南瓜香,微甜中還有黏稠口感,我還以為是燉飯。客家媽媽說這是用生米加上一點糯米,增加稠度,然後和南瓜一起在鍋裡拌炒,每隔幾分鐘就要翻炒一下,直到南瓜與飯完全交融,大約要兩、三個小時才能完成。
金瓜飯看似簡單,卻需要火候、時間與耐心,整盤金瓜飯我幾乎一個人就吃掉一半以上,回程還打包,客家媽媽的用心,我當然也要用胃回饋啊。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清晨在二崁村落散步,才不到七點,太陽已經露臉。我看到絲瓜竟然長在菜宅內的土地上,再沿著菜宅?石牆蔓延而上,這跟傳統長在瓜棚上的絲瓜不大同。正在附近巡田的阿嬤說,澎湖風太大了,絲瓜棚會被風吹垮,只能長在有菜宅擋風的地上。
「長在地上,但是瓜葉遮住怎麼找絲瓜?」我問。阿嬤笑了一下,拿出剛以為她要打掃的掃把,她說用掃把輕輕撥葉,就可以找到絲瓜,只要摸摸絲瓜外殼稜角,如果變硬就是熟了。
長在棚架的輕盈絲瓜,到了澎湖竟是匍匐在地上,不論在哪裡,過了採收季之後的絲瓜,即使老了,絲絡粗了,還能貢獻身軀成為菜瓜布。
就像無怨無悔的母親一樣,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嗎?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說:「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越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越沉重,我們的生命就越貼近地面,生命就越寫實也越真實。」
他說的是愛情,也是親情。
我想起主廚好友阿嬌,她曾開過非常知名的台菜料理「食方餐廳」,有一道「碧玉瓠瓜」,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用黃椒與鯷魚熬煮的醬汁,淋在煮熟的瓠瓜上,這個醬汁她試了四十多種,研發三個月才完成,呈現平凡瓠瓜雅緻豐富的視覺與味覺。
這是一道充滿生命營養的碧玉瓠瓜。阿嬌離過兩次婚,曾經在懷孕六個月時,兩手各提一桶二十公斤重的瓦斯桶,爬到公寓三樓送瓦斯,後來負債兩千萬,靠賣蝦仁羹還清債務。她的生命艱辛,卻堅持親自哺育三個女兒,等到孩子斷奶之後,她用豬肋骨與瓠瓜燉煮,營養豐富易入口,再一口一口餵給孩子吃。
她懷念這段養育過程,花心思做出這道好菜。吃過阿嬌無數次的美味料理,這道菜尤其讓我難忘。
如果生命是一個隱喻,也許就是絲瓜與花生,默默蔓延枝藤根鬚,靜靜開花結果,跟夏天對話,跟土地對話,也跟生命對話。
夏天就是這麼美好!
私房推薦
西嶼二崁村土豆粿與金瓜粿 二崁村聚落協進會,澎湖縣西嶼鄉二崁村14號 06-9982776
到澎湖西嶼二崁村,可以吃到柑仔店的土豆粿,與隔壁小店的金瓜粿、炒花生,喝在地的「風茹草茶」解渴。逛累了,也可在老宅院裡歇歇腳,喝碗香醇的杏仁茶。
建議別只待幾個小時,要認識這個保存完整的澎湖老聚落,可以住在有老宅風味的民宿,慢慢感受澎湖的生活方式。至於民宿提供的早餐,我推薦選燒餅油條,因為燒餅的口感彈性有嚼勁,很像甜甜圈,不像台灣脆脆的容易掉屑,這是馬公北辰市場「鐘記燒餅」的獨特口味。
龍門口田媽媽餐廳 苗栗縣南庄鄉獅山村15鄰165號 037-822829
這裡的金瓜飯與花生豆腐,是很棒的客家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