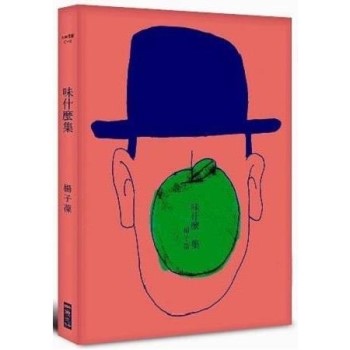附錄之五,楊子葆X焦桐紙上對談——鹹
焦桐:鹽堪稱食物的靈魂,食物可以不酸、不甜、不苦、不辣,卻不能沒有鹹味。五味鹹為首,《尚書》早已斷言:「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去年捧讀《味無味集》,「鹽之花的純淨特性,搭配的食材越是新鮮,越能讓人感受到兩者在口中撞擊迸出的微妙火花。」〈詩意鹽之花〉一文的描述,十分精采:「放一點鹽之花在器皿底部,再盛上湯,也許冷湯,也許溫湯、熱湯,不同溫度與稠度的湯與鹽之花攜手跳著對位舞步,淡雅的鹹香隨著湯的原味或溫柔波動、或優雅蒸氳,飲食成為一種詩意的演出。」
從前我僅知道鹽之花是一種非常細緻的結晶,為中空的倒金字塔形,極輕,能漂浮在鹽水表面;由於含大量的鎂,沒有工業鹽的苦味,堪稱頂級海鹽,相當細緻,不是用來加熱烹調的鹽,而是直接撒在食物上,增添風味。
讀到你這篇文章,增長了見識,更驚豔你的飲食書寫功力。原來鹽之花如此深邃,趣味,美妙。我似乎還讀到你隱含的生活哲學?
楊子葆:多謝溢美。其實我的生活哲學,如果我有生活哲學的話,都是從過去生命經驗裡不斷犯錯獲得教訓累積傷疤而來。譬如怎麼面對鹹,怎麼用鹽?
最早做菜,就是胡亂撒鹽。後來才知道,鹽應該最後再加,因為氯化鈉是一種電解質,有較高的滲透壓,與菜同炒容易造成水分與維生素大量流失,應有的鮮嫩爽脆口感因此付之闕如:與肉同煮,不但水分流失,還會引發肉蛋白質過早凝固,最後既乾且柴,美味蕩然無存。所以做菜不能急著完成所有程序,要學習忍耐,要學習等待,在最後一秒鐘才畫龍點睛。西方人甚至稱食鹽為「桌上鹽」,是菜上桌了要入口之前才撒上的,不能急,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等待,最美好的事物則必須等到最後一刻!
鹽的用量,宜少不宜多,它的功能甚至不是調味,而是提味--把應有美味從雲深不知處給提起來,浮出來。就像槓桿作用以小搏大,阿基米德不是曾這麼說?「給我立足之地,我就可以推動地球。」鹽也一樣。還有,鹽與糖從某個角度上來看很相似:精煉過的,或是工業合成的鹽或糖都已失去天然成分裡的微量元素。直截了當地說,一旦微量元素缺席,鹽,不過就是氯化鈉。吸收、積存過多的鈉會造成人體沉重負擔,引發許多問題,而鎂和鉀可以幫助代謝體內的鈉含量,鎂和鉀同時是維持水分含量和肌肉神經運作的重要動力。其實即使我們沒有清楚意識到某些威脅,我們的身體都會隱約感受到危機,而隱諱地反映出偏好,譬如,漸漸地更喜歡鹽之花,或岩鹽,或其他含有豐富微量元素的天然鹽。
天然鹽很容易辨認,即使品級最高的鹽之花,也不可能達到精鹽那般的雪白潔亮,因為還含有各種礦物質成分,所以通常帶點灰色,混濁的白色,黯淡的黃色、暗沉玫瑰色等。
所以怎麼怎麼面對鹹,怎麼用鹽?Less is more,少即是多,而且,不妨徐志摩一點:「黯淡是夢裡的光輝。」
焦桐:鹽接近一種生活哲學,能誘引出深刻的原味,難怪荷馬喟歎:鹽具有神性。聖經上說世間的鹽(the salt of the earth),指的是社會的中堅份子。
天然食品帶著鹹味者皆美,像螃蟹、蛤蜊、鱘魚卵,你在《喫東西集》裡談到魚子醬帶著大海的滋味,「一點點鹹味、一點點獨特的腥味,以及完整魚卵在口腔中迸裂噴漿的獨特感覺。」裡面的鹹味表情很豐富。好吧好吧,我承認可能就是你書裡所說的「魚子醬左派」,貪圖奢華享受的左派分子。
可魚子醬真美,咱臺灣的烏魚子也美。魚子取出後以鹽醃約50分鐘,即洗去鹽分,進行壓形;鹽醃/脫鹽的過程,是美味最初的生成。優質的烏魚子卵粒均勻,乾濕、軟硬適度,不會死鹹,而是鹹中帶甘,那甘味在咀嚼間悄然透露出來。魚子醬和烏魚子都是多情的食物,那濃厚的香氣總是纏綿在口腔,只要送進嘴裡,彷彿就緊緊擁抱著牙齒,捨不得離去,那是味覺的饗宴,口腔的派對。
鹽,帶著一種永恆的企盼。《堂吉訶德》:「人們只有在一起吃過鹽之後才能交上朋友」,
楊子葆:最早的鹹,也許未必來自鹽,更可能是來自殺生:「血肉有情,皆充養身中形質」,尤其中醫咸以為畜肉甘鹹,甘能益氣,鹹入血分,陰陽氣血俱補。而我覺得最美的甘鹹無非火腿了。在沒有冰箱的時代,將新鮮食物鹽醃、風乾、燻烤加工,是防止腐敗變質而得以長期儲存的最佳方法。火腿是人類最古老的肉食加工品,東西方都有食用火腿的悠久歷史,也都有經典好火腿,例如金華火腿、宣威火腿、伊比利火腿、巴黎火腿等等。它們共通點之一,是好火腿醃製一定要用粗鹽,也許海鹽,也許磨碎了的岩鹽,大量的粗鹽。不完全是為了粗鹽便宜,更因為粗鹽天然,天然富含的礦物質在長時間的風乾與發酵過程中,會發生不能完全控制因此更顯不可思議的驚喜變化,一年,兩年,三年或更久,原來的粗鹽從苦澀到甘鹹,原來的鮮肉則從青春到熟成,時間推移之力成就火腿雋永之美。
血肉有情,雋永甘鹹,我不由聯想夏宇〈甜蜜的復仇〉短詩:
把你的影子加點鹽
醃起來
風乾
老的時候
下酒
鹹鹽,其實也可以轉換成甜蜜,只是需要時間,需要時間。
焦桐:醃,真是一個深沈的動詞,那裡面有權宜策略,有美學手段,又對時光充滿了期盼。除了火腿,醃水產也是很尋常的食品加工,如馬介休(Bacalhau)。這是葡文直譯的廣東話,是一種以鹽巴醃製的深海銀鱈,簡單講就是「葡萄牙鹹魚」,乃葡人常吃的名菜。我們很容易理解,在大航海時代,航行的生涯太長太遠,為免船上所需的魚肉腐壞,葡萄牙人將新鮮的鱈魚切片,用厚厚的鹽醃漬起來保存。馬介休之美在於鹹香,陳香,就像老酒、老朋友一樣雋永;那鹹,毫不呆板、輕浮,挽留了海洋的氣息,有一種飄浪之後的成熟感,滄桑感。
這種成熟感是高明的鹹,會回甘,鹿港的地標小吃「蝦猴」也是。人類自古即知鹽醃食物,像肉醬。然則肉醬處理不慎,易導致肉毒桿菌滋生,造成食物中毒。我就曾在美食之都里昂吃壞肚子,同行的李育霖教授甚至到醫院急診。我懷疑是某一餐館的醃漬魚惹禍,那碟漬小魚下手極重,已吃不出魚是否腐敗,完全淹沒在醬料味中,鹹得要命,更甚於鹽。《風俗通》:「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生活中有太多不誠懇的食品,像巧言令色之徒,誘我們習慣重口味,重口味的舌頭,重口味的甜言蜜語,重口味的友誼,重口味的愛情,我們習以為常了,不免就排斥清淡的本味。
然則各種醃漬菜、肉品都因為有了鹽,而對美味有了等待。瘂弦名作〈鹽〉一詠三嘆:「鹽啊,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可見鹽是生活的基礎,是生命之光,照亮萬物。瑪麗皇后的嘆息
朋友邀宴法國料理,點了一瓶香檳酒開場。餐廳侍酒師非常專業,以手掌按握瓶塞緩慢旋轉上提卻同時留力下壓的複雜方式開瓶,軟木塞離開瓶口的剎那,清脆地發出「啵」的一聲內斂輕響,侍酒師自己也非常滿意這場表演似地笑開了,解釋說:「這是少女的輕吻。」
「少女輕吻」?好鮮活的比喻。詢問典出何處?他倒答不出來,只說圈內都這麼形容。
餐桌上開香檳的禮儀其實頗有講究,既要斯文流暢,又不能發出過大音響破壞氣氛,但我卻是第一次聽到「少女輕吻」說法。在法國,香檳開瓶時,軟木塞應以近四十五度角離開瓶口,微微發出一縷像是吹口哨的輕柔「嘶」聲,似有若無,猶如情人耳邊細語,因此有人說是「愛情之嘆」(le soupir amoureux),更多人喜歡稱為「瑪麗•安東芮特的嘆息」(le soupir de Marie-Antoinette)。
瑪麗•安東芮特即法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瑪麗皇后,原名Maria Antonia Josepha Johanna von Habsbourg-Lorraine,是出生在奧地利霍布斯堡皇宮中的公主,年僅十四歲就政治聯姻嫁給十六歲的法國皇太子,1774年皇太子登基成為路易十六,瑪麗•安東芮特因此成為皇后,絕大部分人生都在深宮內院度過。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路易十六夫婦雙雙以「叛國罪」被送上斷頭台,路易王朝結束,共和開啟。許多文學作品都以瑪麗皇后的傳奇為主題,最近比較知名的一部是2002年獲法國Prix Femina文學獎的小說《再見吾后》(Les adieux a la reine),2012年拍成電影,臺灣上映時中譯片名為「情慾凡爾賽」。
相傳瑪麗皇后1793年10月16日被送上斷頭台時,仍不失鎮靜優雅。畫家Jacques-Louis David曾畫下一幅瑪麗皇后死刑前在馬車上遊街示眾的著名素描,畫中的她雖身穿囚衣,但腰桿挺直、雙眸低垂、下巴微抬,在最糟糕的時刻,卻仍保持高貴的模樣。
抵達現今名為「協和廣場」的革命刑場後,瑪麗皇后無須攙扶自己走上斷頭台,一陣混亂中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皇后仍保有禮貌地轉頭致歉:「請原諒我,先生,我不是故意這麼做的。」(Excusez-moi, Monsieur, je ne l’ai point fait expres.)――深愛香檳的瑪麗•安東芮特在斷頭刀鍘落下那一剎那,是否曾發出嘆息?沒有人知道。大革命之後,貴族在法國似乎式微了,但某些風範與影響卻隱而不顯地流傳下來,例如瑪麗皇后的淡出身影,就給我們一種有距離感的認同:即使無可奈何也要保持尊嚴與從容,即使所有的人都覺得沒有必要了,還是堅持禮儀與教養的,淒美。
因為這個天地之間再無可追索的淒美,所以當我們輕巧地開啟香檳,如果能僅僅發出如「瑪麗•安東芮特嘆息」一般、恍惚而朦朧的低吟,庶幾碰觸到餐桌禮儀最高境界。
從「少女輕吻」到「瑪麗皇后的嘆息」,從法國香檳酒想像重溫法國歷史,未必是葡萄酒功力的提升,卻是另一重尚未被開發見知的文化境界。
猴標蘇維埃香檳
當年法國留學時的俄羅斯同學遠道來訪,帶來猴標「蘇維埃香檳」(Sovetskoye Shampanskoye,英文作Soviet Champagne)伴手,說是祝賀丙申猴年,禮輕情意重。這千里迢迢而來的酒禮,其實並不輕微。
一來在西方世界裡,Champagne這個字受到智慧財產法律嚴格保護的,除了在法國香檳產區以傳統方式釀造出來的氣泡酒之外,其他氣泡酒絕不可使用這個名字。這個法律隨著歐盟影響力的蔓延而擴大,到今天,「蘇維埃香檳」應是僅有化外之民。二來,酒也真好。
「蘇維埃香檳」歷史並不悠久,最早據說是由深愛法國香檳的沙皇保羅一世(Tsar Pavel I, 1754-1801)鼓吹釀造俄羅斯香檳之理念,而由戈理津家族(Golitsyn)十九世紀末在黑海之濱阿伯勞.杜爾索(Abrau-Dyurso)建立與法國香檳相同製程技法的氣泡酒廠,並命名為Novy Svet Champagne(新世界香檳,英譯為New World Champagne)。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來自俄羅斯的Novy Svet Champagne居然在盲目品評會上打敗所有參賽的法國香檳,得到世博「香檳大獎」,震驚當時歐洲上流社會。
1917年從聖彼得堡爆發的俄羅斯革命,改變了這個國家的一切,原來的貴族香檳也因此消失。1920年代初期蘇聯建立時,列寧提出生產廉價、易釀、毋須陳年,所有無產工人們都能歡樂享用Champagne for the people的構想,並在1928年由蘇聯地區經濟委員會推出「蘇維埃香檳」新品牌。蘇維埃香檳之父是當年戈理津家族(Golitsyn)香檳酒廠的倖存老員工Anton Frolov-Bagreyev,他因為新創香檳有功而獲得史達林國家獎章。1953年,釀酒學教授Georgy Agabalyanc則因為有效改善蘇維埃香檳品質並降低生產成本,獲得列寧國家獎章,並相對於同樣被歐盟列為智慧財產的「香檳釀造法」,分庭抗禮確立所謂的「蘇維埃釀造法」(Soviet method)──「蘇維埃釀造法」之妙,法國香檳第一大廠Moet & Chandon竟在1975年不惜以高價購得秘方授權。
蘇聯曾經是全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有22,402,200平方公里,覆蓋地球陸地表面六分之一,在這片橫跨11個時區的廣袤土地上,很長一段時間「蘇維埃香檳」獨尊。但1991年蘇聯崩解之後,許多古老品牌重新擦亮面世,而一些前蘇聯加盟國在21世紀更制定「去共黨化」(Decommunization)法律,一時之間,原意為「人民代表大會」的Soviet居然成了一個髒字眼,「蘇維埃香檳」不但不再討人喜歡,甚至被禁止使用。
有趣的是,2007年一群香檳愛好者與專家們在莫斯科舉辦了一場五款法國偉大香檳與五款俄羅斯「香檳」的盲目品評PK賽,號稱The Judgement of Moscow,結果再一次讓人跌破眼鏡:第一名是重啟生產的俄羅斯歷史名廠Novy Svet Pinot Noir 2002,二、三、四、五名分別是法國Salon、Bollinger、Billecart-Salmon、Louis Roederer Cristal逸品,第六名Novy Svet Prince Golitsyn,第七名就是朋友帶來的蘇維埃香檳Abrau Durso Brut,它們都勝過第八名的Egly-Ouriet Brut Millesime 1998!
世界變動不居,好東西就像好人,有時也會蒙塵、被低估、被錯過,我們必須學會自處自得。我和俄羅斯同學一起舉杯,互祝新年看得開,過得好。
小英國宴葡萄酒
臺灣第三次政黨輪替,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日宣誓就職,當晚國宴用酒引我注意:晚宴餐桌上只有葡萄酒,依序是Miguel Torres Chile Santa Digna Chardonnay 2014 智利白葡萄酒、J. Lohr South Ridge Syrah 2013美國紅葡萄酒,以及作為甜酒的臺中后里樹生酒莊埔桃酒。
智利是新世界葡萄酒代表國之一,近年因為生產許多物美價廉葡萄酒而為世人稱道,但國宴中為什麼以它為首呢?難道只是巧合?我穿鑿附會地想像:南美智利本乃「帝力於我何有哉」世外桃源,十五世紀以前歐洲人所繪的世界地圖甚至不見美洲大陸,十六世紀起西班牙人發現並開始殖民智利,1541年在聖地牙哥建城;而當1544年葡萄牙船艦經過臺灣海域時,水手從海上遠眺臺灣,驚艷島嶼之美,由衷呼喊Ilha Formosa!葡萄牙語Formosa係「美麗」之意,Ilha則為「島嶼」,臺灣舊名「福爾摩沙」即脫胎於此;兩者都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走入世界」。
Miguel Torres為西班牙家族在智利創立之酒莊,值得注意的是,它屬於瑞士Fair for Life所認證「公平貿易」酒款,產品符合環保、勞動人權以及第三世界發展利益等標準,正可以映照小英總統揭櫫社會公平與永續發展價值觀。
回歸葡萄酒本質,這款年輕Chardonnay單一品種白葡萄酒初段有芒果與成熟芭樂等熱帶果香撲鼻,中段洋溢檸檬與鳳梨氣息,濃郁口感與酸度達成完美平衡,並能與臺灣特產水果呼應。尤其突顯的礦物質香氣與餘韻,彷彿呈現親吻土地的謙卑意象。
第二款紅葡萄酒來自美國加州,2010年曾獲Wine Enthusiast》雜誌選為「年度最佳美國酒廠」。雖名Syrah,卻是混釀葡萄酒,由93% Syrah、3% Petit Syrah、3% Grenache,以及1% 其他葡萄品種調配而成,具有多元文化意涵。
2013 係加州超級年分,呈現飽滿的黑醋栗、成熟櫻桃、榛果、香草與巧克力多層次濃香,單寧細膩,品質無可挑剔。有趣的是,也許因為採用美國橡木桶陳年,這款酒隱約飄盪南洋椰子香氣,讓人聯想到小英總統的家鄉屏東。
甜酒總算本土獨有。不過因為臺灣屬亞熱帶氣候,本來就不適合種植釀酒葡萄,尤其因為高溫多雨,葡萄往往一年兩穫,甚至三穫,果實不夠濃郁集中,釀出來的酒也就淡而無味了。
既然原料無法與歐美相比,樹生酒莊乾脆另闢蹊徑,釀出一款不一樣的酒,「最大關鍵是發揮自己的特色,因為模仿就是否定自己。」釀酒顧問陳千浩曾如此說明。陳千浩採用Madeira wine釀造法:「在酒精發酵過程中加入白蘭地阻斷發酵,經過三個月特殊的太陽熱能熟成,再放在一般室溫熟成,至少五年。」經歷法國橡木桶陳年的埔桃酒,琥珀色酒體甜香瀰漫,有一種屬於臺灣的自信。
小英國宴葡萄酒之設計,讓我想起法國布根地文人Jean-François Bazin名言:「葡萄酒只有在伴隨政治與經濟的偉大企圖心時,才能展現偉大。」(Le vin n’acquiert de la grandeur que s’il est porte par une grande ambition politique et economique.)
焦桐:鹽堪稱食物的靈魂,食物可以不酸、不甜、不苦、不辣,卻不能沒有鹹味。五味鹹為首,《尚書》早已斷言:「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去年捧讀《味無味集》,「鹽之花的純淨特性,搭配的食材越是新鮮,越能讓人感受到兩者在口中撞擊迸出的微妙火花。」〈詩意鹽之花〉一文的描述,十分精采:「放一點鹽之花在器皿底部,再盛上湯,也許冷湯,也許溫湯、熱湯,不同溫度與稠度的湯與鹽之花攜手跳著對位舞步,淡雅的鹹香隨著湯的原味或溫柔波動、或優雅蒸氳,飲食成為一種詩意的演出。」
從前我僅知道鹽之花是一種非常細緻的結晶,為中空的倒金字塔形,極輕,能漂浮在鹽水表面;由於含大量的鎂,沒有工業鹽的苦味,堪稱頂級海鹽,相當細緻,不是用來加熱烹調的鹽,而是直接撒在食物上,增添風味。
讀到你這篇文章,增長了見識,更驚豔你的飲食書寫功力。原來鹽之花如此深邃,趣味,美妙。我似乎還讀到你隱含的生活哲學?
楊子葆:多謝溢美。其實我的生活哲學,如果我有生活哲學的話,都是從過去生命經驗裡不斷犯錯獲得教訓累積傷疤而來。譬如怎麼面對鹹,怎麼用鹽?
最早做菜,就是胡亂撒鹽。後來才知道,鹽應該最後再加,因為氯化鈉是一種電解質,有較高的滲透壓,與菜同炒容易造成水分與維生素大量流失,應有的鮮嫩爽脆口感因此付之闕如:與肉同煮,不但水分流失,還會引發肉蛋白質過早凝固,最後既乾且柴,美味蕩然無存。所以做菜不能急著完成所有程序,要學習忍耐,要學習等待,在最後一秒鐘才畫龍點睛。西方人甚至稱食鹽為「桌上鹽」,是菜上桌了要入口之前才撒上的,不能急,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等待,最美好的事物則必須等到最後一刻!
鹽的用量,宜少不宜多,它的功能甚至不是調味,而是提味--把應有美味從雲深不知處給提起來,浮出來。就像槓桿作用以小搏大,阿基米德不是曾這麼說?「給我立足之地,我就可以推動地球。」鹽也一樣。還有,鹽與糖從某個角度上來看很相似:精煉過的,或是工業合成的鹽或糖都已失去天然成分裡的微量元素。直截了當地說,一旦微量元素缺席,鹽,不過就是氯化鈉。吸收、積存過多的鈉會造成人體沉重負擔,引發許多問題,而鎂和鉀可以幫助代謝體內的鈉含量,鎂和鉀同時是維持水分含量和肌肉神經運作的重要動力。其實即使我們沒有清楚意識到某些威脅,我們的身體都會隱約感受到危機,而隱諱地反映出偏好,譬如,漸漸地更喜歡鹽之花,或岩鹽,或其他含有豐富微量元素的天然鹽。
天然鹽很容易辨認,即使品級最高的鹽之花,也不可能達到精鹽那般的雪白潔亮,因為還含有各種礦物質成分,所以通常帶點灰色,混濁的白色,黯淡的黃色、暗沉玫瑰色等。
所以怎麼怎麼面對鹹,怎麼用鹽?Less is more,少即是多,而且,不妨徐志摩一點:「黯淡是夢裡的光輝。」
焦桐:鹽接近一種生活哲學,能誘引出深刻的原味,難怪荷馬喟歎:鹽具有神性。聖經上說世間的鹽(the salt of the earth),指的是社會的中堅份子。
天然食品帶著鹹味者皆美,像螃蟹、蛤蜊、鱘魚卵,你在《喫東西集》裡談到魚子醬帶著大海的滋味,「一點點鹹味、一點點獨特的腥味,以及完整魚卵在口腔中迸裂噴漿的獨特感覺。」裡面的鹹味表情很豐富。好吧好吧,我承認可能就是你書裡所說的「魚子醬左派」,貪圖奢華享受的左派分子。
可魚子醬真美,咱臺灣的烏魚子也美。魚子取出後以鹽醃約50分鐘,即洗去鹽分,進行壓形;鹽醃/脫鹽的過程,是美味最初的生成。優質的烏魚子卵粒均勻,乾濕、軟硬適度,不會死鹹,而是鹹中帶甘,那甘味在咀嚼間悄然透露出來。魚子醬和烏魚子都是多情的食物,那濃厚的香氣總是纏綿在口腔,只要送進嘴裡,彷彿就緊緊擁抱著牙齒,捨不得離去,那是味覺的饗宴,口腔的派對。
鹽,帶著一種永恆的企盼。《堂吉訶德》:「人們只有在一起吃過鹽之後才能交上朋友」,
楊子葆:最早的鹹,也許未必來自鹽,更可能是來自殺生:「血肉有情,皆充養身中形質」,尤其中醫咸以為畜肉甘鹹,甘能益氣,鹹入血分,陰陽氣血俱補。而我覺得最美的甘鹹無非火腿了。在沒有冰箱的時代,將新鮮食物鹽醃、風乾、燻烤加工,是防止腐敗變質而得以長期儲存的最佳方法。火腿是人類最古老的肉食加工品,東西方都有食用火腿的悠久歷史,也都有經典好火腿,例如金華火腿、宣威火腿、伊比利火腿、巴黎火腿等等。它們共通點之一,是好火腿醃製一定要用粗鹽,也許海鹽,也許磨碎了的岩鹽,大量的粗鹽。不完全是為了粗鹽便宜,更因為粗鹽天然,天然富含的礦物質在長時間的風乾與發酵過程中,會發生不能完全控制因此更顯不可思議的驚喜變化,一年,兩年,三年或更久,原來的粗鹽從苦澀到甘鹹,原來的鮮肉則從青春到熟成,時間推移之力成就火腿雋永之美。
血肉有情,雋永甘鹹,我不由聯想夏宇〈甜蜜的復仇〉短詩:
把你的影子加點鹽
醃起來
風乾
老的時候
下酒
鹹鹽,其實也可以轉換成甜蜜,只是需要時間,需要時間。
焦桐:醃,真是一個深沈的動詞,那裡面有權宜策略,有美學手段,又對時光充滿了期盼。除了火腿,醃水產也是很尋常的食品加工,如馬介休(Bacalhau)。這是葡文直譯的廣東話,是一種以鹽巴醃製的深海銀鱈,簡單講就是「葡萄牙鹹魚」,乃葡人常吃的名菜。我們很容易理解,在大航海時代,航行的生涯太長太遠,為免船上所需的魚肉腐壞,葡萄牙人將新鮮的鱈魚切片,用厚厚的鹽醃漬起來保存。馬介休之美在於鹹香,陳香,就像老酒、老朋友一樣雋永;那鹹,毫不呆板、輕浮,挽留了海洋的氣息,有一種飄浪之後的成熟感,滄桑感。
這種成熟感是高明的鹹,會回甘,鹿港的地標小吃「蝦猴」也是。人類自古即知鹽醃食物,像肉醬。然則肉醬處理不慎,易導致肉毒桿菌滋生,造成食物中毒。我就曾在美食之都里昂吃壞肚子,同行的李育霖教授甚至到醫院急診。我懷疑是某一餐館的醃漬魚惹禍,那碟漬小魚下手極重,已吃不出魚是否腐敗,完全淹沒在醬料味中,鹹得要命,更甚於鹽。《風俗通》:「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生活中有太多不誠懇的食品,像巧言令色之徒,誘我們習慣重口味,重口味的舌頭,重口味的甜言蜜語,重口味的友誼,重口味的愛情,我們習以為常了,不免就排斥清淡的本味。
然則各種醃漬菜、肉品都因為有了鹽,而對美味有了等待。瘂弦名作〈鹽〉一詠三嘆:「鹽啊,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可見鹽是生活的基礎,是生命之光,照亮萬物。瑪麗皇后的嘆息
朋友邀宴法國料理,點了一瓶香檳酒開場。餐廳侍酒師非常專業,以手掌按握瓶塞緩慢旋轉上提卻同時留力下壓的複雜方式開瓶,軟木塞離開瓶口的剎那,清脆地發出「啵」的一聲內斂輕響,侍酒師自己也非常滿意這場表演似地笑開了,解釋說:「這是少女的輕吻。」
「少女輕吻」?好鮮活的比喻。詢問典出何處?他倒答不出來,只說圈內都這麼形容。
餐桌上開香檳的禮儀其實頗有講究,既要斯文流暢,又不能發出過大音響破壞氣氛,但我卻是第一次聽到「少女輕吻」說法。在法國,香檳開瓶時,軟木塞應以近四十五度角離開瓶口,微微發出一縷像是吹口哨的輕柔「嘶」聲,似有若無,猶如情人耳邊細語,因此有人說是「愛情之嘆」(le soupir amoureux),更多人喜歡稱為「瑪麗•安東芮特的嘆息」(le soupir de Marie-Antoinette)。
瑪麗•安東芮特即法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瑪麗皇后,原名Maria Antonia Josepha Johanna von Habsbourg-Lorraine,是出生在奧地利霍布斯堡皇宮中的公主,年僅十四歲就政治聯姻嫁給十六歲的法國皇太子,1774年皇太子登基成為路易十六,瑪麗•安東芮特因此成為皇后,絕大部分人生都在深宮內院度過。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路易十六夫婦雙雙以「叛國罪」被送上斷頭台,路易王朝結束,共和開啟。許多文學作品都以瑪麗皇后的傳奇為主題,最近比較知名的一部是2002年獲法國Prix Femina文學獎的小說《再見吾后》(Les adieux a la reine),2012年拍成電影,臺灣上映時中譯片名為「情慾凡爾賽」。
相傳瑪麗皇后1793年10月16日被送上斷頭台時,仍不失鎮靜優雅。畫家Jacques-Louis David曾畫下一幅瑪麗皇后死刑前在馬車上遊街示眾的著名素描,畫中的她雖身穿囚衣,但腰桿挺直、雙眸低垂、下巴微抬,在最糟糕的時刻,卻仍保持高貴的模樣。
抵達現今名為「協和廣場」的革命刑場後,瑪麗皇后無須攙扶自己走上斷頭台,一陣混亂中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皇后仍保有禮貌地轉頭致歉:「請原諒我,先生,我不是故意這麼做的。」(Excusez-moi, Monsieur, je ne l’ai point fait expres.)――深愛香檳的瑪麗•安東芮特在斷頭刀鍘落下那一剎那,是否曾發出嘆息?沒有人知道。大革命之後,貴族在法國似乎式微了,但某些風範與影響卻隱而不顯地流傳下來,例如瑪麗皇后的淡出身影,就給我們一種有距離感的認同:即使無可奈何也要保持尊嚴與從容,即使所有的人都覺得沒有必要了,還是堅持禮儀與教養的,淒美。
因為這個天地之間再無可追索的淒美,所以當我們輕巧地開啟香檳,如果能僅僅發出如「瑪麗•安東芮特嘆息」一般、恍惚而朦朧的低吟,庶幾碰觸到餐桌禮儀最高境界。
從「少女輕吻」到「瑪麗皇后的嘆息」,從法國香檳酒想像重溫法國歷史,未必是葡萄酒功力的提升,卻是另一重尚未被開發見知的文化境界。
猴標蘇維埃香檳
當年法國留學時的俄羅斯同學遠道來訪,帶來猴標「蘇維埃香檳」(Sovetskoye Shampanskoye,英文作Soviet Champagne)伴手,說是祝賀丙申猴年,禮輕情意重。這千里迢迢而來的酒禮,其實並不輕微。
一來在西方世界裡,Champagne這個字受到智慧財產法律嚴格保護的,除了在法國香檳產區以傳統方式釀造出來的氣泡酒之外,其他氣泡酒絕不可使用這個名字。這個法律隨著歐盟影響力的蔓延而擴大,到今天,「蘇維埃香檳」應是僅有化外之民。二來,酒也真好。
「蘇維埃香檳」歷史並不悠久,最早據說是由深愛法國香檳的沙皇保羅一世(Tsar Pavel I, 1754-1801)鼓吹釀造俄羅斯香檳之理念,而由戈理津家族(Golitsyn)十九世紀末在黑海之濱阿伯勞.杜爾索(Abrau-Dyurso)建立與法國香檳相同製程技法的氣泡酒廠,並命名為Novy Svet Champagne(新世界香檳,英譯為New World Champagne)。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來自俄羅斯的Novy Svet Champagne居然在盲目品評會上打敗所有參賽的法國香檳,得到世博「香檳大獎」,震驚當時歐洲上流社會。
1917年從聖彼得堡爆發的俄羅斯革命,改變了這個國家的一切,原來的貴族香檳也因此消失。1920年代初期蘇聯建立時,列寧提出生產廉價、易釀、毋須陳年,所有無產工人們都能歡樂享用Champagne for the people的構想,並在1928年由蘇聯地區經濟委員會推出「蘇維埃香檳」新品牌。蘇維埃香檳之父是當年戈理津家族(Golitsyn)香檳酒廠的倖存老員工Anton Frolov-Bagreyev,他因為新創香檳有功而獲得史達林國家獎章。1953年,釀酒學教授Georgy Agabalyanc則因為有效改善蘇維埃香檳品質並降低生產成本,獲得列寧國家獎章,並相對於同樣被歐盟列為智慧財產的「香檳釀造法」,分庭抗禮確立所謂的「蘇維埃釀造法」(Soviet method)──「蘇維埃釀造法」之妙,法國香檳第一大廠Moet & Chandon竟在1975年不惜以高價購得秘方授權。
蘇聯曾經是全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有22,402,200平方公里,覆蓋地球陸地表面六分之一,在這片橫跨11個時區的廣袤土地上,很長一段時間「蘇維埃香檳」獨尊。但1991年蘇聯崩解之後,許多古老品牌重新擦亮面世,而一些前蘇聯加盟國在21世紀更制定「去共黨化」(Decommunization)法律,一時之間,原意為「人民代表大會」的Soviet居然成了一個髒字眼,「蘇維埃香檳」不但不再討人喜歡,甚至被禁止使用。
有趣的是,2007年一群香檳愛好者與專家們在莫斯科舉辦了一場五款法國偉大香檳與五款俄羅斯「香檳」的盲目品評PK賽,號稱The Judgement of Moscow,結果再一次讓人跌破眼鏡:第一名是重啟生產的俄羅斯歷史名廠Novy Svet Pinot Noir 2002,二、三、四、五名分別是法國Salon、Bollinger、Billecart-Salmon、Louis Roederer Cristal逸品,第六名Novy Svet Prince Golitsyn,第七名就是朋友帶來的蘇維埃香檳Abrau Durso Brut,它們都勝過第八名的Egly-Ouriet Brut Millesime 1998!
世界變動不居,好東西就像好人,有時也會蒙塵、被低估、被錯過,我們必須學會自處自得。我和俄羅斯同學一起舉杯,互祝新年看得開,過得好。
小英國宴葡萄酒
臺灣第三次政黨輪替,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日宣誓就職,當晚國宴用酒引我注意:晚宴餐桌上只有葡萄酒,依序是Miguel Torres Chile Santa Digna Chardonnay 2014 智利白葡萄酒、J. Lohr South Ridge Syrah 2013美國紅葡萄酒,以及作為甜酒的臺中后里樹生酒莊埔桃酒。
智利是新世界葡萄酒代表國之一,近年因為生產許多物美價廉葡萄酒而為世人稱道,但國宴中為什麼以它為首呢?難道只是巧合?我穿鑿附會地想像:南美智利本乃「帝力於我何有哉」世外桃源,十五世紀以前歐洲人所繪的世界地圖甚至不見美洲大陸,十六世紀起西班牙人發現並開始殖民智利,1541年在聖地牙哥建城;而當1544年葡萄牙船艦經過臺灣海域時,水手從海上遠眺臺灣,驚艷島嶼之美,由衷呼喊Ilha Formosa!葡萄牙語Formosa係「美麗」之意,Ilha則為「島嶼」,臺灣舊名「福爾摩沙」即脫胎於此;兩者都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走入世界」。
Miguel Torres為西班牙家族在智利創立之酒莊,值得注意的是,它屬於瑞士Fair for Life所認證「公平貿易」酒款,產品符合環保、勞動人權以及第三世界發展利益等標準,正可以映照小英總統揭櫫社會公平與永續發展價值觀。
回歸葡萄酒本質,這款年輕Chardonnay單一品種白葡萄酒初段有芒果與成熟芭樂等熱帶果香撲鼻,中段洋溢檸檬與鳳梨氣息,濃郁口感與酸度達成完美平衡,並能與臺灣特產水果呼應。尤其突顯的礦物質香氣與餘韻,彷彿呈現親吻土地的謙卑意象。
第二款紅葡萄酒來自美國加州,2010年曾獲Wine Enthusiast》雜誌選為「年度最佳美國酒廠」。雖名Syrah,卻是混釀葡萄酒,由93% Syrah、3% Petit Syrah、3% Grenache,以及1% 其他葡萄品種調配而成,具有多元文化意涵。
2013 係加州超級年分,呈現飽滿的黑醋栗、成熟櫻桃、榛果、香草與巧克力多層次濃香,單寧細膩,品質無可挑剔。有趣的是,也許因為採用美國橡木桶陳年,這款酒隱約飄盪南洋椰子香氣,讓人聯想到小英總統的家鄉屏東。
甜酒總算本土獨有。不過因為臺灣屬亞熱帶氣候,本來就不適合種植釀酒葡萄,尤其因為高溫多雨,葡萄往往一年兩穫,甚至三穫,果實不夠濃郁集中,釀出來的酒也就淡而無味了。
既然原料無法與歐美相比,樹生酒莊乾脆另闢蹊徑,釀出一款不一樣的酒,「最大關鍵是發揮自己的特色,因為模仿就是否定自己。」釀酒顧問陳千浩曾如此說明。陳千浩採用Madeira wine釀造法:「在酒精發酵過程中加入白蘭地阻斷發酵,經過三個月特殊的太陽熱能熟成,再放在一般室溫熟成,至少五年。」經歷法國橡木桶陳年的埔桃酒,琥珀色酒體甜香瀰漫,有一種屬於臺灣的自信。
小英國宴葡萄酒之設計,讓我想起法國布根地文人Jean-François Bazin名言:「葡萄酒只有在伴隨政治與經濟的偉大企圖心時,才能展現偉大。」(Le vin n’acquiert de la grandeur que s’il est porte par une grande ambition politique et econom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