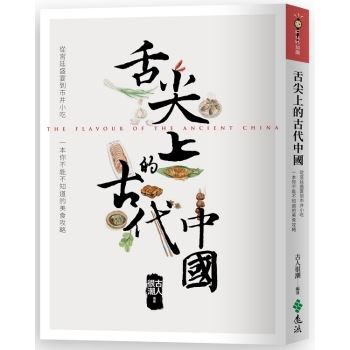歷史悠久的在地食材
外來食材大軍浩浩蕩蕩,對中餐文化和格局產生過巨大衝擊。 那麼問題來了:外來食材傳入之前,先民們究竟吃什麼?
粟:因肚子餓吃草而發現的美食
吃草!
其實早在七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是名副其實的種草拔草小能手了。
如上一章所說,小麥是外來的、玉米是外來的、紅薯是外來的,那麼,小麥、玉米、紅薯傳入前,先民們如何解決主食問題?
在那個荒蕪的時代,以採集野果和漁獵裹腹的時代,食材可遇不可求,當時廣袤大地上最常見的是大片大片的野草。
一旦採不到果子,打不到獵物,就要坐在草叢裡挨餓。
餓扁了肚子的先民,淚眼汪汪地瞧著綠油油的野草,不由咽了口唾沫。
先民們有一樣優秀的品質:什麼都敢吃,什麼都能吃,絕不挑食。在那樣的時代,挑食基本上相當於絕食。
生計所迫,他們決定嘗試著吃草。祖先何等英明,在嘗過幾種草後,他們很快就發現,有一種狗尾草的子實,不僅能吃,而且香甜又充飢。更重要的是,這些狗尾草相當好養活,春天撒一把種子,稍加打理,秋天就能採收了。先祖們領悟到了細水長流的道理:靠打獵養家,飢一頓飽一頓,到底不是長久之計,哪有種狗尾草可靠?於是乎,全國流行起大規模種草,以漁獵獲取食物的生活,逐漸向農耕生活轉變,一個偉大的農耕文明,悄然誕生。
這種劃時代的植物,就是狗尾粟。直到今天,它的子實依然是常見食物,我們通常稱之為——小米。
聽過但不一定吃過的美食
在吃這件事情上,今人比古人幸福太多:明代之前,倘若有人看到女朋友滿頭大汗、涕淚橫流、咧著嘴巴直吸涼氣,大約會嚇得半死,以為什麼急病突然發作,二話不說抱起來直奔郎中家。而不會像如今,輕描淡寫瞅一眼,嘟囔一句:「活該,誰叫妳吃那麼多辣椒!」然後繼續打怪。
當真世風日下。
今天的食物之豐富,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
照理說,古人能吃到的東西,今人也能吃到。除非法律不允許,或者該物種滅絕,否則饕客們就算上窮碧落、掘地三尺,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味美食。
但其實存在這樣一類食物,它們是古代餐桌上的常客,今人卻難得一飽口福。
菰米:因病被拋棄的主食
菰米也叫「雕胡米」,是水生植物「菰」的種子。作為食物,它的命運很可憐——它並沒有真的滅絕,而是被人為給「做掉」了。
歷史上的菰米曾經風光無限,與稻、黍、稷、麥、菽這五穀地位相差無幾,是主食界的超級巨星。它被人類拋棄,要從它的一次生病說起。西周時期,一個偶然的機會,栽培菰的人發現,當菰染上黑粉菌,會發生病變,莖部膨大,變成一種美食—— 茭白,但代價是無法抽穗結實,產出菰米。
也就是說,饕客們面臨一個痛苦的抉擇—— 在菰米和茭白之間二選一。到了唐宋時期,水稻、小麥產量越來越高,採收不方便、產量有限的菰米無法適應人口增長的需要,終於江湖地位不保,越來越多的種植者選擇培育茭白,放棄菰米。今天市面上雖偶爾還能見到它,但是高昂的價格,使之完全變成「嘗一嘗圖個新鮮」的存在。
外來食材大軍浩浩蕩蕩,對中餐文化和格局產生過巨大衝擊。 那麼問題來了:外來食材傳入之前,先民們究竟吃什麼?
粟:因肚子餓吃草而發現的美食
吃草!
其實早在七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是名副其實的種草拔草小能手了。
如上一章所說,小麥是外來的、玉米是外來的、紅薯是外來的,那麼,小麥、玉米、紅薯傳入前,先民們如何解決主食問題?
在那個荒蕪的時代,以採集野果和漁獵裹腹的時代,食材可遇不可求,當時廣袤大地上最常見的是大片大片的野草。
一旦採不到果子,打不到獵物,就要坐在草叢裡挨餓。
餓扁了肚子的先民,淚眼汪汪地瞧著綠油油的野草,不由咽了口唾沫。
先民們有一樣優秀的品質:什麼都敢吃,什麼都能吃,絕不挑食。在那樣的時代,挑食基本上相當於絕食。
生計所迫,他們決定嘗試著吃草。祖先何等英明,在嘗過幾種草後,他們很快就發現,有一種狗尾草的子實,不僅能吃,而且香甜又充飢。更重要的是,這些狗尾草相當好養活,春天撒一把種子,稍加打理,秋天就能採收了。先祖們領悟到了細水長流的道理:靠打獵養家,飢一頓飽一頓,到底不是長久之計,哪有種狗尾草可靠?於是乎,全國流行起大規模種草,以漁獵獲取食物的生活,逐漸向農耕生活轉變,一個偉大的農耕文明,悄然誕生。
這種劃時代的植物,就是狗尾粟。直到今天,它的子實依然是常見食物,我們通常稱之為——小米。
聽過但不一定吃過的美食
在吃這件事情上,今人比古人幸福太多:明代之前,倘若有人看到女朋友滿頭大汗、涕淚橫流、咧著嘴巴直吸涼氣,大約會嚇得半死,以為什麼急病突然發作,二話不說抱起來直奔郎中家。而不會像如今,輕描淡寫瞅一眼,嘟囔一句:「活該,誰叫妳吃那麼多辣椒!」然後繼續打怪。
當真世風日下。
今天的食物之豐富,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
照理說,古人能吃到的東西,今人也能吃到。除非法律不允許,或者該物種滅絕,否則饕客們就算上窮碧落、掘地三尺,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味美食。
但其實存在這樣一類食物,它們是古代餐桌上的常客,今人卻難得一飽口福。
菰米:因病被拋棄的主食
菰米也叫「雕胡米」,是水生植物「菰」的種子。作為食物,它的命運很可憐——它並沒有真的滅絕,而是被人為給「做掉」了。
歷史上的菰米曾經風光無限,與稻、黍、稷、麥、菽這五穀地位相差無幾,是主食界的超級巨星。它被人類拋棄,要從它的一次生病說起。西周時期,一個偶然的機會,栽培菰的人發現,當菰染上黑粉菌,會發生病變,莖部膨大,變成一種美食—— 茭白,但代價是無法抽穗結實,產出菰米。
也就是說,饕客們面臨一個痛苦的抉擇—— 在菰米和茭白之間二選一。到了唐宋時期,水稻、小麥產量越來越高,採收不方便、產量有限的菰米無法適應人口增長的需要,終於江湖地位不保,越來越多的種植者選擇培育茭白,放棄菰米。今天市面上雖偶爾還能見到它,但是高昂的價格,使之完全變成「嘗一嘗圖個新鮮」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