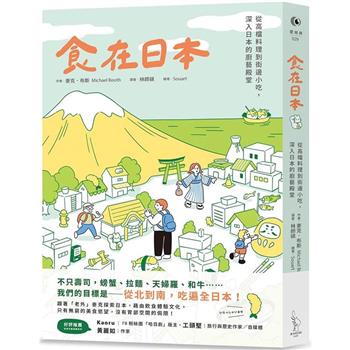01 阿利
「哈哈!你胖到好多年沒看到你的小雞雞吧!而且你的褲子太小,胖到彎個腰,太陽都下山了!」
這是標準霸凌,而且我必須強調,這絕對不是準確結論,畢竟一開始只是討論法國與日本料理的優點。
最近我在倍受讚譽的法式料理餐廳沙卡納(Sa.Qua.Na)享用晚餐,地點是諾曼地海岸的翁弗勒爾。主廚亞歷山大.布達(Alexandre Bourdas)是迅速竄紅的法國廚藝之星,我不經意地提起他的清爽風格、新鮮的食材,輕率地拿他的作品與日式料理相比。我知道布達在日本工作過三年,說他的廚藝受到日本飲食的影響並不突兀。
但我應該料到,這段話會讓好友近藤勝利(Katsotoshi Kondo)火冒三丈。
「你懂什麼日本料理,蛤?」他抓狂大叫,「你覺得你懂日本料理?只有在日本才地道!你在歐洲才吃不到。這個人的餐點完全不像日本食物,吃得出傳統嗎?吃得出季節變化嗎?吃得出食物裡的含義嗎?Tu connais rien de la cuisine Japonaise. Pas du tout!(你完全不懂日本料理,一點都不懂!)」我從過往的經驗知道,別人突然切換成另一種語言不是好兆頭,況且他嘴巴嘟得老高。我得在他完全炸開之前好好回敬一番。
「我知道的夠多,所以了解日本料理有多無趣,」我說,「日本料理只注重美觀,你們根本不懂什麼是風味,吃得出暖心、溫度、款待之情嗎?就只是沒脂肪、沒味道,你們還有什麼?生魚片、麵條、炸蔬菜─不全都從泰國料理、中華料理、葡萄牙料理偷來的,有什麼了不起?反正就是把食材泡醬油,吃起來還不都一樣?你只需要一把鋒利的刀、一位好漁夫,就能做出好吃的日本料理,有什麼了不起?喔,別告訴我還有鱈魚白子和鯨魚肉,嗯哼,這些菜絕不能錯過。」
我兩年前在巴黎的藍帶廚藝學院受訓認識阿利,當時他將近三十歲、身材瘦高、是個一臉正經八百的日韓混血兒,看起來難以捉摸,但在北野武似的冷漠外表下,有種不形於色的幽默感。
我和其他人的廚師白制服總穿上好幾天,最後猶如活生生的傑克森.波拉克(Jackson Pollock)滴畫作品,阿利卻永遠一身純白無瑕。他的菜色完美無缺:擺盤一絲不苟,菜色一定放在中間,露出大片白色餐盤,刀具也是隨時保持鋒利。但是他和教導我們的法國主廚多次起衝突,他們每次都扣他的分數,因為他烹調魚的時間不肯超過幾秒鐘,而且蔬菜一定清脆爽口,不願意聽從老師將蔬菜燉得軟爛。這些老師導致阿利始終不喜歡法國人、法式料理,但他依舊留在巴黎。我懷疑,有部分原因是他下定決心要獨自教育法國人了解更高超的日本料理。
「法國人對日本料理的認識,就像她對性愛的瞭解。」某次他指著路過的修女這麼說。
畢業之後,阿利到第六區真正道地的日式餐廳工作─站在街上看不到室內,進去之後有種靜謐氛圍,這只有日本遊客會發現。我們保持聯絡,偶爾碰面就是聊餐飲、聚餐,最後都是一陣幼稚的辱罵。
這次的收場不太一樣。「閉嘴,好嗎?」阿利彎腰低頭到桌下的包包裡撈東西,「有樣東西給你,笨蛋,回去看。」
他遞上一本精裝書,封面模糊地畫著一條跳躍的魚。我一時語塞,答應回去會看並謝過阿利。氣氛有點尷尬,他從未給我任何東西。我以前花了好一番功夫,他才明白輪流請喝酒的概念。而且這本書顯然所費不貲,但是阿利常指著我的鼻子罵,又說我是「無腦老外」。
搭公車回家,將書放在腿上時,我才恍然大悟,他一定覺得我和法國藍帶廚藝學校的老師格外瞧不起他。那本書是辻靜雄著的《日本料理:極簡餐飲藝術》(Japanese Cooking: A Simple Art)
新版,第一版是一九七九年。寫序的是《美食》主編露絲.雷舒爾(Ruth Reichl)和美國傳奇美食作家M.F.K.費雪(Mary Frances Kennedy Fisher),更證明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料理書籍。後來我才發現,這本書至今都是卓越的日本料理參考書,世界各地的日式料理迷都奉為圭臬。
「這不只是食譜,」雷舒爾評論。「而是充滿哲理的著作。」
書裡當然有食譜,兩百多份食譜涵蓋烤、蒸、煨、沙拉、油炸、麵條、醃漬─有許多菜色都是我前所未聞;從米飯的精神意義,到日式料理的餐具,辻靜雄都一一說明。「無論身分貴賤,日本人絕對不會隨便用陳舊盤子盛菜,不會只靠食物味道取勝。」他寫。辻靜雄強調日式料理注重季節更迭:廚師或客人都以虔敬的心情享受為時不長的當令食材。我也發現,日本人會使用幾乎沒有味道的食材,只是取其質地、口感,例如豆腐、牛蒡、蒟蒻(以鬼芋根剝皮、燉煮、磨碎、凝固之後製成,富含膠質的深棕色或灰黑色的餅狀物。)其他無論是「蒸煮過的鰹魚片,焙乾到硬如木材,最後刨成薄片」,或是聽起來就令我毛骨悚然、卻是早餐菜色的發酵黃豆納豆等等,在在都讓我困惑不解。日本料理似乎有各式各樣的發酵食物,從味噌、醬油到納豆,更別忘了(誰忘得了?)海參花,我更覺得日本人過份講究「腐爛」的食物,例如乳酪或優格。
我知道日本人很注重如何加熱食材,但辻靜雄雲淡風輕地寫到「骨頭邊的雞肉帶點粉紅色」(原來生的雞刺身在日本很普遍),也常提到日本人非常注重食材的鮮度,並反對過度加熱的簡單料理方法。
有時我又覺得他口氣有點紆尊降貴,儘管表面包著一層謙遜的薄膜:「我們有許多餐點看來又少又單薄,」他在序中這麼寫。「但諸君得學會觀察食材細膩、天然的香氣和味道。」日後的世界美食潮流有時認為,辻靜雄認定西方人口味神經兮兮的看法略嫌過時:「日本人最愛的刺身─生魚片。往往令人覺得異常奇特,幾近野蠻,恐怕需要饕客莫大的好奇心和勇氣才吃得下!」
更教人困惑的莫過於《日本料理》一書中鮮少甜點的篇幅,幾乎完全沒著墨。如果這本書反映一般的日式料理,難怪日本人常常一臉嚴肅、憂鬱。我彷彿聽到有一支民族從來不展顏歡笑。我心想,也許只是辻靜雄本人不愛吃甜,便繼續往下讀。
在費雪稱為「精緻饗宴排場」的五百多頁中,辻靜雄這本書最讓我驚訝之處是內容洞燭先機。文中不斷重複食材在地、新鮮、當令;特徵是少奶酪、少肉類,多蔬果;料理過程盡量保持食材原狀,尊重食材;這都符合現代西方思維。儘管這本書寫於幾十年前,至今依舊不過時,對所有人而言都點出重要、也許是至關緊要的課題。辻靜雄的食譜果真如書名一樣簡單,我頓時發現,儘管我們在家會烹調印度、泰式、中華、法式、義式,甚至墨西哥或匈牙利料理(我甚至做過德式餐點),卻幾乎沒做過日式料理,就算做了,了不起也只是類似壽司的食物。即使去日本料理餐廳,一定不脫握壽司、捲壽司,而且就那五、六種配料,否則就是點做法生硬的天婦羅。但辻靜雄說,日本料理不只格外健康、美味,做起來也不費吹灰之力,不需要小火慢燉高湯或烹調方法複雜的醬料,也不需要費時耗力的前置作業。根據辻靜雄的說法,天婦羅的麵糊甚至不必攪拌均勻─本來就應該不勻。
當然,我無法坦率地告訴阿利,辻靜雄的書對我有深遠的影響。我聽過許多名廚含糊其辭地糊弄料理要從簡,「讓食材自己發聲」,或聲稱他們只用當季、在地食材等等,每一個的說法都一模一樣。我幫報章雜誌採訪撰文,常目光呆滯地聽他們滔滔不絕,但是那些裝模作樣又複雜的餐點總是削弱了這番老生常談。然而這個作家、這個國家的料理,竟然具體呈現上述所有觀點。
《日本料理:極簡餐飲藝術》令我著迷還有另一個原因。三年來在巴黎當個認真吃貨的報應來了,我的膽固醇超高─我每去一家米其林餐廳,似乎就把一個米其林輪胎套上身。
只要爬幾階樓梯,我便喘不過氣,而且已經開始擔心早上無法自己穿上襪子。阿利很愛戳我的肚腩,然後假裝找不到手指。想當然爾,他苗條又結實。他說他的奶奶最近滿九十七歲,還自己打理庭院。他問我,我知道日本人是最長壽的民族嗎?我知道原因嗎?就是飲食。
「你現在開始吃日本料理,也許還能活到六十歲,」阿利嘲笑我。「我可以活到一百歲,因為我常吃豆腐、魚、醬油、味噌和米飯。」他舉了幾道日本菜為例,說明它們如何促進健康:顯然香菇可以治療癌症,而白蘿蔔可以預防青春痘。蓮藕降膽固醇,他說,然後拍拍我光禿禿的額頭,說我應該開始吃海帶芽,因為這種食材治禿頭。(「你看過日本人禿頭嗎?嗯?」)根據阿利的說法,大豆是神奇農產品,可以降膽固醇、預防癌症,還有延年益壽之功。
我開始多方涉獵日式料理書籍。或者應該說,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這本書雖然是一九七九年出版,但是說到用英文寫成的權威日本料理書,辻靜雄這本著作是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提到壽司的書當然很多(但我後來發現,沒有多少人了解壽司師傅手藝的博大精深);有些人寫到日式料理對健康有益;有幾本敘述西化的日本料理,也就是洋食(例如《Wagamama食譜》),卻沒有幾本討論時下的日式料理,討論日本人目前都吃什麼,以及美食潮流。
可惜辻靜雄在幾十年前就發現,傳統日式料理逐漸式微:「我很遺憾,但我們自己的菜色都不正統了,已經被冷凍食品汙染。」他寫道,後文又補充西方食物已經破壞了日本人的味蕾。他悲嘆,尤其是年輕人迷上冷凍鮪魚,更「毀了日式料理的傳統」。
自從他寫下那些文字之後,實情究竟如何呢?我納悶著。日本還有辻靜雄描述的正宗日式料理嗎?或是日本人已經和我們其他人一樣,拜倒在上校和小丑的麾下?
讀完這本書之後不久,其實就是阿利給我的當天,我做了一個魯莽、衝動的決定,後來顯然因此改變了我的人生。我決定親自去日本調查現代日式料理,盡力研究他們的料理方法、食材,查清楚辻靜雄的恐怖預言是否成真。我們是否還能向日本人學習,或是《日本料理:極簡餐飲藝術》只是悼念某種失傳的烹調傳統?阿利說日本人特別長壽,他們的飲食對健康有益,如果屬實,我能將這些優點介紹給西方人嗎?日式料理與西方生活相容嗎?日本人真的如阿利所說,用膠水黏住襪子,而不是用吊襪帶?
我要飛到日本,慢慢有系統地從最北邊的北海道往南吃到東京、京都、大阪、福岡和沖繩,我要一邊吃、一邊明查暗訪、一邊學習、一邊研究。我想品嚐當地食材,了解日式料理的哲學、技巧,當然還包括對健康的好處。我也需要盡快減重,開始吃得更健康,但是西方的減肥餐─低脂優格、慧優體餐點,根本毫無吸引力。辻靜雄的書卻囊括琳瑯滿目的健康、簡單又美麗的食物,我可以想像自己吃得開心盡興,但我得先學會做法。當晚,我便試探性地和妻子麗森提起這個想法。
「天啊,這個主意太棒了,」她說。「我很想去日本。你能想像我們帶孩子去有多棒嗎?他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想想!」
「慢著,不是欸。我沒有……妳知道,我覺得……我要去研究、調查……」我說。來不及了,我從她遙望的眼神看出她的魂魄已經飄到另一個地方,悠遊在華麗的和服中,想像自己盤腿而坐,面前就是一絲不苟的枯山水宅院,或扛著金漆盒子,忘情地逛著免稅店的化妝品。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知道無須掙扎,只能直接放棄。
其實無所謂,因為我和現代爸爸一樣,對自己陪小孩─應該說是沒陪小孩的時間感到愧疚。我沒有正職,所以也沒有真正的假期。我大概已經五年沒度假,但是想到去住租來的別墅,癱在泳池邊兩週,或是更慘,去迪士尼樂園,我光想都覺得渾身發癢、心情沮喪。但這次我可以結合家庭與工作,和孩子分享我對美食的熱情,甚至可以在他們心中種下好奇的種子,成為一家往後的共同話題。其實就許多方面看來,這個決定很自私,我們家長只是假裝情操高貴,為孩子犧牲。我很想去日本住一陣子,卻又受不了幾天見不到家人。
八月初那晚,我不只訂一張,而是訂四張機票去日本,而且回程日期未定。我開始規劃路線,依序造訪阿利所謂的日本美食文化重鎮。我們要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老饕家庭自由行。先飛到東京,花三星期的時間適應(事後回顧,這個想法頗荒謬)。阿利告訴我,東京是日本的餐飲首都,也是全國飲食文化最多元的城市。我們會在那裡找到日本最棒的壽司、天婦羅餐廳,還會體驗到各式各樣的驚喜(他說最後這句話時露出得意的笑容)。
接著再飛往北海道,那裡幅員遼闊、空曠,與人口眾多的東京截然不同,生活步調較悠閒、而且有令人驚豔的海鮮。我們預計在札幌住十天。
然後再飛回東京所在的本州,只是這次要往南前往京都,那裡是日本從前的皇都,至今依舊是精神、文化重鎮。阿利說,京都是懷石料理重鎮─這種料理由許多道精緻的餐點組成,是日本的高檔料理,只是更精緻、複雜,而且阿利說,等級更高。他要我務必品嚐豆腐,因為其他地方都沒有日本的上等、新鮮。
在京都停留三週,白天可以到處去走走(阿利說我們一定要去聖地高野山,而且神戶與歐美有其相似之處),搭一小段火車就能抵達大阪。不必勞煩阿利,我就知道這裡的食物與京都有極大的差異。我那年稍早採訪《世界報》著名的美食評論家馮索瓦.西蒙(François Simon)時,他就說得興高采烈,甚至說大阪是全球最令人激賞的美食之都。
接著我們會搭上翹首盼望的子彈列車到九州的福岡。阿利對這個地方的著墨不多,只說我們一定喜歡,要我別忘了吃當地的拉麵。然而我們聊起最後的目的地沖繩時,他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說,那裡不算日本,雖然是日本領土,卻截然不同,飲食文化和生活習俗都與其他地方南轅北轍。如果我想知道活到一百歲的祕密,就得在沖繩找答案,顯然當地超過一百歲的人瑞之多,超過世界各地。我們會在這裡住兩週。
最後再從沖繩回東京待幾天才回家。
我不知道帶著幼童踏上這趟旅程是否不切實際,但我希望他們多看看、多了解日本與日本人。
艾斯格六歲,艾米爾四歲,他們從未離開歐洲。艾斯格像我小時候一樣挑剔,多半只吃削成恐龍形狀的馬鈴薯類。艾米爾則有極其脆弱的食道,所以我們已經習慣衣服或家具上乾掉的嘔吐物味道,甚至不以為意。他們究竟能吃什麼?除了電影《愛情,不用翻譯》以及風格完全不同的黑澤明電影所呈現的日本,我其實不了解這個國家,我會的日文也只有阿利教我的幾句問候語,但我懷疑恐怕是髒話(知道嗎?我果真沒料錯)。
真正的日本是什麼模樣?我可以通行無阻嗎?日本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在這個充滿液晶螢幕、水泥大廈、幾何形狀的庭園、覆雪山脈、哥德裝扮的蘿莉塔女孩和藝妓的國度,容得下一個來自西方的小家庭,歡迎我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