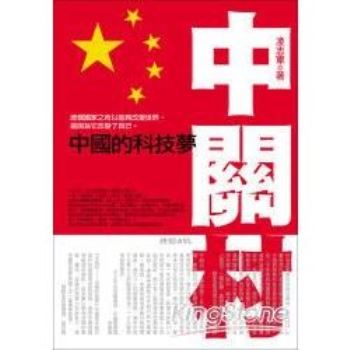前 言
《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撩人的。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最新一期,用了一幅血紅色的圖片來展示中國:一個巨大的五星升起在萬里長城之上,金光閃閃,在風起雲湧的大千世界投下萬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來:「中國:一個新王朝的出現」(China: Dawn of a New Dynasty)。兩位作者是《時代》雜誌執行主編助理邁克‧艾略特(Michael Elliott)和《時代》北京分社社長西蒙‧艾勒根(Simon Elegant),為這期封面寫出的故事長達十一頁,按照他們的描述,在這個剛剛開始的世紀裡,美國的力量會走下坡,而中國的力量將上揚。中國正將它的經濟影響轉變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一點也不誇張。」
這是好幾年來世界性持續不斷的「中國話題」的最新表述。在這個世紀的最初幾年裡,全世界的人都在湧向中國。他們面對這個急劇變化的國家,每天都在問:中國的崛起會成為事實嗎?這會是一個和平過程嗎?這會成為國際化浪潮的一部分嗎?會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嗎?這個擁有强大經濟實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會同西方發生衝突嗎?
「你也要告訴我們一個中國崛起的故事嗎?」在北京城中心一個寫字樓的午餐廳裡,瑪莎‧艾佛瑞(Martha Avery)這樣問我。她是個美國人,作家和翻譯家,也是我過去一本書的英文版譯者。她對世界富有責任感,對中國充滿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樣,她只能站在很遠的地方打量這個國家,所以才會有此一問:「你能否告訴我們,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須用我自己的方式。」雖然我將著眼於整個國家的大歷史,但是在描述這個歷史進程的時候,我的重點仍將是具體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將由內部而不是由外部來觀察。這一回我選擇的樣本是中關村。
就歷史來說,中關村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這個國家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饑餓,又讓自己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製造業基地」。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術的高地,把「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這是新一代人的夢想,激勵著整個國家再接再厲,進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這拓展了中國和西方大國的合作,也增加彼此間的疑慮。而中關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它迄今為止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自己。
我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接觸中關村,但是存心把它寫出,是過去兩年的事。在這之前,我用了大約十八個月追踪微軟亞洲研究院,又用六個月調查聯想集團。這兩個機構都在中關村,相距不到兩公里。一個是典型的美國公司,一個是典型的中國公司。那時我希望從公司內部來觀察時代的融匯演進,而把大部分中關村的故事抛諸身後。直到二○○五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當時我來到雙清路上,在清華創業園A座三○二房看到一個場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開。這間屋子裝著三十八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過占有其中一個方格,由一張簡易電腦捉和一把旋轉椅組成,和大公司裡那種員工座位沒有什麼差別,只不過,在通常鑲嵌員工姓名的地方,貼著公司名稱,一律由普通道林紙列印而成,凌亂一片,讓我想起滿天繁星。電腦桌後面坐著的那些人,個個年輕。他們是老闆,也是會計,還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員工。只要花五百塊錢,就能在這裡坐一個月,而他們在這裡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半年。很多人失敗了,但總會有人成長起來,擴大隊伍,搬到樓上。那裡有單間辦公室,沿著走廊排列,是為他們這些人準備的。室內空間略大,可以擺下四、五張桌子,門外掛著一塊公司招牌。站在走廊裡,可以看到兩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筆直地伸到盡頭。十二個月,也許十八個月之後,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會垮臺,但必定有幾家繼續成長,將搬到更大的寫字樓去,占據整整一層。我對公司的創業景象並不生疏,可眼前這一切竟是聞所未聞。微軟和聯想都是擁有數萬員工的龐大公司,但是說老實話,都沒有「A座三○二房」那樣讓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氣,看到壓力和不確定性,看到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張桌」,「一間房」,「一層樓」,「一幢樓」。這個脈絡直觀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長過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資本關係、技術路線和公司結構,已經和他們的前輩完全不同,節奏也更快。中關村的公司還是成者少,敗者多。就像書中所描述的那樣,當中有七七%在三年內消逝,有九○%在五年內消逝,有九九%在十年內消逝。但這並不能阻止創業者前赴後繼、一代接著一代地走過來。他們已經走了二十七年,直到今天。先行者為後來者提供了範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所有這些構成了中關村的故事,也成為這個國家歷史的一部分。
我意識到,我所看到的中關村的一些事情,為公衆所不知,而公開輿論中很多深入人心的東西,又與其本來面目相去很遠。於是我便生出一個念頭,想把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對我的想法不以為然,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中關村有什麼高科技?應當說,在對它的種種批評中,這是客氣的。我們都知道,還有人堅定地認為,「中關村就要死亡。」這個說法比較專業的表述是,它「已無力領導中國的高科技走向」;比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噴湧的死火山」。這種輿論自二○○四年春天以來特別强大,以致引發一場激烈的討論。贊成者和反對者全都理直氣壯,實際進程中則充斥著相互對立的證據。這讓故事更加生動,富有衝突、懸疑和戲劇性,但同時也增加了我們討論問題的難度。這些問題有:中國為什麼出了個中關村?中關村為什麼變成今天這樣子?它的精神源泉來自何處?究竟是民族主義的伸張,還是西方思想的產物?它的商業體系是如何形成?它掀起的三次技術浪潮是怎樣影響整個中國?民間資本為什麼能夠戰勝國家資本,成為主導力量?它也經歷了原始積累的階段嗎?它有原罪嗎?有欺騙嗎?有無法無天嗎?有勾心鬥角嗎?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樣遞進?它究竟是個新技術的聖地,或者只不過是個大集市?它究竟是技術第一,還是市場第一?究竟是科學家更重要,還是企業家更重要?為什麼中關村的公司總是長不大?好不容易長大了又為何不能避免盛極而衰的命運?政府應當介入嗎?應當干預嗎?應當憑藉行政權力去支援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嗎?如果不應當,那麼怎樣制止它的混亂和無法無天?如果應當,又該以怎樣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經過氣了嗎?「海歸」將要成為它的主力軍嗎?當跨國公司紛紛進駐之時,它還是小公司的天堂嗎?它還是新技術的發源地嗎?它還是國家創新的一面旗幟嗎?它將會成為一個世界創新中心嗎?也許,它的歷史已經中斷,將被上海、深圳這樣的地方取代?
就中關村而言,要想把所有問題都解釋清楚是一件困難的事。生機勃勃、充滿變化的新世界總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關村這樣的地區,不僅中國僅有,而且全世界難能有二。它的時間延續至今,跨越中國全部改革歷程。從官方立場上看,它作為科技園的歷史是從一九八八年開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間研究者看來,自從陳春先一九八○年自行其是地創辦了第一家公司,中關村的新革命就已經開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這個國家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以致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窮人、博士和文盲、外來人和本地人、高官顯貴和三教九流,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機會在這裡譜寫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紛繁複雜: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技術問題、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傳統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人的本性問題。每個故事的結局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還在繼續,所有人物都是「進行式」。世界每天都在變化,誰也不能預見他們面對變化將會如何行動。即使你整天生活在這裡,要想說清楚一些事情還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評論活著的人們非常困難,實在是因為他們距離我們太近的緣故。我常常想,也許敘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會更容易些,不禁佩服那些每天品評前朝往事、抒發思古幽情的學者與作家是那麼聰明知趣。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就會失去信譽;如果我迎合民間輿論,也有譁眾取寵之嫌。總之,無論唯上還是媚俗,都會離開公正從容的立場,使得人們更加簡單化和更誇張地評估某些問題。我並不期望本書的描述能和中關村的正史合拍,那是歷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職業是記者,對於人物和事件的取捨,更多的是出於記者本能。我希望讓讀者瞭解這裡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我想對讀者說:「它在高科技之路蹣跚而行的曲折歷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國崛起的真相。」這包括它的陽光和陰暗,包括它的英明之舉和愚蠢行為,也包括它的混亂和秩序。
資料的來源是當事人的回憶、政府和公司的檔案,以及公開出版物。中關村色彩斑斕的歷史既存在人們心中,也存在浩繁的文獻中。為此我用八個月的時間在中關村調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對聯想集團和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採訪,那麼我在這裡已經花費三十二個月。我採訪了大約三百個人,包括企業經理、科學家、工程師、銷售人員、會計、商販、教師、學生、留學生、農民工、政府領導者。這些採訪幾乎全是一對一的談話。他們相當坦率和真誠,給了我那麼多的故事和思想。儘管如此,我知道記憶通常夾雜個人情感,而且會因時間的推移而產生偏差,所以還用很多精力查閱原始資料。應當感謝中關村管委會和海澱區的領導者們,他們為我開放了兩個政府檔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應當感謝中關村園區志編寫小組的那些專業人員,他們把自己掌握的資料毫無保留地讓我使用。同時我還要感謝互聯網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術,讓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開輿論中的有關部分。舉個簡單的例子,當我用「百度」搜索「中關村+盜版」的時候,就會顯示至少四十萬個網頁。所有這些,都成為我的重要參考。
由於資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對於事實的選擇和駕馭要比收集這些事實更加困難。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價值判斷,而價值準則卻隨著國家的進步不斷變化。昨天的天經地義,今天也許就會讓人貽笑大方。我只是盡可能地以忠實於歷史原貌的方式組織和敘述這個故事。初稿的長度遠遠超出預期,後來又經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壓縮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不是整段整頁地删節,而是逐字逐句地濃縮,為此用掉更多時間,只是希望讀者在减少閱讀負擔的同時不致於丟失有用有趣的情節。
把這麼多精力和熱情投入這個話題,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實說,它影響了我的職業經歷。我要學習很多新東西,還要讓自己多年的閱歷得到伸張,因此承擔更多壓力,獲得新的表達空間。這在我本人也是一個成長經歷。它很艱辛,但充滿魅力。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寫作者。在採訪和寫作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人來告訴我應當做什麼和不應當做什麼。我有許多辦法既不違反遊戲規則,又讓讀者明白我的意思。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任何人都不可能隨心所欲地表達自己,我也一樣。如果有人認為我的敘述只不過是以偏概全,有粉飾之嫌,或者過於刻薄。我只能說,依據目前可以獲得的資料和開放程度,這是我能做到最接近事實的描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仍是關於事實的。本書所有內容,包括細節、資料、人物對話和心理活動,都有確鑿根據,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極大精力用在事實的校正上,盡可能地避免錯誤,但我深知本書時間跨度極長,內容如此浩瀚,有些間接得來的材料無法一一核實確認,即使是事件親歷者的敘述也難免發生偏差,所以發生事實方面的錯誤也許是難免的。如果讀者發現其中有任何問題,我希望能夠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凌志軍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一章: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國。」
在出現人們所謂「電子一條街」之前的兩年裡,白頤路被一種神經質的緊張氣氛籠罩著。幾乎人人都能看出,總有一些事情要發生了。這種預感就像瘟疫一樣,在這條狹窄的街道緩慢而又堅定地彌漫開來。
緊張氣氛來自那個聞名遐邇的大院子。用今天的京城地圖來比照,這是靠近四環北路的一片土地,高樓林立,巨大的玻璃帷幕構成一幅幅誇張的幾何圖形,在藍天的襯托下散發出眩目的光芒。而在當時,這裡還是一片灰色建築,被農田分割包圍。它在行政上隸屬於中國科學院,包括計算所、物理所、數學所和電子所。自一九五○年代以來,它一直都是這個國家的某種象徵,神聖,寧靜,單調,猶如一潭深水。而現在,也即一九八二年冬,竟由於兩個人的衝突,蕩起層層漣漪。
陳春先和他的上級管惟炎,成為這場衝突的兩個極端的代表。前者是個理論物理學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可惜他的熱情已經背離既定道路。當時他正在傾心盡力地經營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公司,自詡為「科技游擊隊」。作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管惟炎一點也不喜歡他的這個同行和下屬,這種情緒在過去兩年漸漸積累,直到開始懷疑陳春先的人品。他先是指控陳在牟取金錢方面的私利,乃至玷污神聖的科學殿堂,接著又要求審查陳的公司賬目。審查行動在一九八二年三月開始,到年終還是沒有一點停下來的跡象。
在這個命運攸關的冬天,關於陳春先和他的公司,白頤路上謠言紛紛。這些謠言每句話都是一項嚴重指控,在當時也並非沒有一點根據,可是按照今天的條律和實情,卻又是荒誕不經和可笑的。有的謠言說,這個人正在收買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其基本方法就是恣意發放「紅包」,數額超過國家工資,又全部隱匿不報。有的謠言說,這個人把國家科研經費竊為私有。還有人聲稱,已經看到一份非法獲取收入者的名單,牽涉至少二十個科學家和大學教師。攻擊的矛頭無一例外地指向陳春先和他的兩個合夥者,紀世瀛和崔文棟。一九八三年元旦前後的幾個星期,這三人躲在物理研究所院內那間藍色的木板小屋裡,個個神情緊張,坐立不安。「科技游擊隊的指揮部擱淺了」,紀世瀛在後來撰寫的一篇回憶錄中說,「藍色板房墜入緊張而窒息的氣氛之中……」
陳春先儘管神情沮喪,仍然堅定不移,期待他的時辰很快到來。他一直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對抗管惟炎所長代表的力量,可惜無法穩定自己的隊伍。公司員工不是大學教師就是科學院的研究員,只在八小時之外投入進來,所以被叫做「星期日工程師」。對他們來說,職業的穩定是天經地義,辭職跳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他們在所長的壓力下很容易地被瓦解了。現在,陳春先面前只剩下紀世瀛和崔文棟。三人相顧無言,彼此心照,誰都不知道怎樣超越那個無形屏障。根據紀世瀛後來的回憶,當時場面「冷清得怕人」。最後還是陳春先打破沈默:「我說要幹下去,你們倆也說要幹下去。我們態度一堅決,就會有第四人、第五人。」
不幸的是,這個冬天陳春先期待的「第四人」始終沒來。如果有人再次走進藍色小屋,那也是偷偷來告別的。保存至今的公司檔案中有一些文件,表明員工們紛紛退還津貼。這些錢原本只是他們辛勤工作的報酬,其數額為每人每月三十元。但現在人人都說,這是「非法所得」,難免貪污之嫌,倘若不能如數退還,說不定什麼時候警察就會拿著手銬出現在門口。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是個星期二。破曉時分,物理所大院的西北角上忽然一片喧嘩。聲音湧進八十八號樓,穿過狹窄漫長的走廊,不出所料,是朝著紀世瀛家來的。他聽到人聲、掌聲、腳步聲,接著是敲門聲,當即「嚇了一跳」,而他的妻子則是「心裡一緊」。這兩年讓這夫妻倆心驚肉跳的事情太多了,「天曉得又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許真的是警察來了!」
慌張中的紀世瀛聽清了幾句話:「快打開收音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電臺裡說,你們是對的。」「這下子你們翻身了!」
他奪門而出,回到兩個風雨同舟的夥伴中間。三人相擁一處,眼裡掛著淚,就像惡夢醒來,互相詢問這消息是不是真的。
千真萬確,這是真的!大家終於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彼此祝賀,看著同事們圍攏過來,時而拱手,時而大笑,腳下踏著有力的節奏,齊聲高喊「解放了!解放了!」
日後那些研究中關村的歷史家們,是應當為這個早晨留下一頁的,因為它是一場新革命的無數轉捩點中的第一個。情勢急轉直下。陳春先,這個圓臉、小眼、面相柔和、沒有稜角的南方人,這個在童年時代挨過餓的窮光蛋,這個在中國和蘇聯的蜜月時代赴莫斯科大學專攻核子物理的留學生,這個衣衫不整、扣子常常對錯的邋遢鬼,這個在東方和西方的冷戰時代為國家原子物理科學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這個對抗上級因而被冷落的倒楣蛋,這個掛著研究員頭銜卻在搗騰小買賣的不務正業者,這個已有三十年共產黨黨齡卻揮舞著金錢引誘科學家紅杏出牆的叛逆者,就從這時起,成了中關村的英雄。
然而當時沒人想到他會成為英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不過感到陽光回到心裡,陰霾一掃而光。這種感覺,只有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一天有過一次(註1)。可是他們對於驟然發生的變故還有疑問,不知究竟出了什麼事。中國科學院正在流傳一個新故事,說中南海知道了陳春先的遭遇,指斥管惟炎的行為是在壓制科技人員的創新激情。在這個傳言的散布者看來,媒體都是黨的「喉舌」,國家電臺既然敢於出頭露面,那麼這傳言就算經過添油加醋,也必然會有根據。
陳春先回到家裡,已是深夜,雖然很累,但很快活,心中唯有一個懸念揮之不去,徹夜不眠:「難道真是什麼有來頭的人說話了?」
這個早晨發生的事情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是我們將要講述的這個故事的起點。在後來那些回顧歷史的人們中間,陳春先常常被說成是「中關村第一人」。他的那個根本不像公司的公司一共存在五年,在技術方面乏善可陳,在管理方面一塌糊塗,但是在中關村迄今為止的歷史上,它的確產生了一種顛覆性的力量,雖然是緩慢地擴展著它的影響,但其性質和激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它把科技人員送到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境地,讓他們的熱情和智慧在金錢、物欲和普通人的需求中得到滿足,就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裡說的,是「一條新路」。
成為「第一人」的這個人,那年四十八歲。這個在中國科學院的一潭死水般的院子裡扔進一塊石頭的人,肯定是個見異思遷的天才。
陳春先開創的歷史,始於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天,他創辦了一個別出心裁的組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很難說它是一間企業,因為它在當時既無工商註冊,也無法人代表,甚至連他的上級也被蒙在鼓裡。紀世瀛說它是「偷偷成立的」,這並非故作神秘。因為當時他們如果報告上級,可以肯定不會獲得批准。創業的動議最初只在三人之間商討,性質類似於密謀。其中最富戲劇性的情節,是整件事情完全在中關村八十八號樓醞釀而成。這座建築因為住著眾多成就非凡的科學家而在當日中國享有盛名,其中包括陳景潤、楊樂和張廣厚。紀世瀛一家人住在一層最東頭的房間,門牌「一○三」。那是一個以「振興中華」號令全國的年代。記者們頻繁出入,把這群科學家弄到報紙、電臺、電視臺上去張揚,當作為國奉獻的榜樣。他們居然沒有發現,這樓房裡正在進行一項對抗國家體制的計畫。
密謀者的隊伍漸漸擴大,到一九八○年秋天已有十人。為首者陳春先是物理所一室主任、中國科學院裡最年輕的研究員,還是中國有機半導體和原子能受控熱核聚變融合(@台灣通稱「熱核融合」@)研究領域的領先人物。此外還有紀世瀛,自詡為「嚴濟慈的關門弟子」,如果這話有些誇張,那麼「第一批參加原子彈設計的大學生中的一個」,以及「中國科學院裡最年輕的工程師」,則是真的。那年他三十八歲,喜歡張揚,花樣百出,誇誇其談,而且還將隨著年齡的增長更加偏執和疾惡如仇。有崔文棟,他是物理所高壓電氣技師;有曹永仙,力學研究所工程師;有陳首燊,電工研究所研究員;吳德順,電子研究所工程師;羅承沐,清華大學講師;劉春城,物理研究所技師;潘英,物理所會計;還有汪詩金,他是北京等離子體協會秘書長,也是這支隊伍中唯一不屬於中國科學院的人。
這天晚上,十個人聚在物理所,宣告成立「服務部」。因為是個週末,院子裡空無一人,沒有張燈結彩,沒有鮮花,沒有賀詞,沒有鞭炮齊鳴,甚至連個公司的牌子也沒有。他們經過辦公樓,再繞到核聚變實驗樓的東北角上。這裡有個小屋子,木板結構,鐵門,原本是個堆放廢舊實驗物資的庫房,現在經過一番打掃,就成了「服務部」的第一個辦公地點。
根據學者們後來的考證,這是中關村第一個民營科技企業。當時的一切都像是美國矽谷學生創業故事的翻版:幾個文化人,舉債五百元,還有一間舊倉庫。倉庫的窗戶掛著一塊蔚藍色的塑膠布,權作窗簾。從外面看去分外顯眼,所以被他們叫做「藍色小屋」。多年以後,服務部早已不復存在,陳春先已不在人世,藍色小屋也在中關村的大規模拆建中夷為平地,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只有紀世瀛仍舊對它一往情深。就在小屋將被拆除的那一刻,他跑去為它留下照片。他還清楚記得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沒想到它會成為歷史」,他逢人就說。遇到喜歡聽他說話的人,他就繪聲繪色地描述這段「歷史」。
所謂「中關村第一個民營科技企業」,其實也是中國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當日中國的科技企業數以千計,不是「國家的」,就是「集體的」,還沒有哪一家是屬於私人的。多年以後中關村聲譽鵲起,每年一度在白頤路舉行盛大「慶典」,成為慣例。在那些情緒激昂、如痴如狂的日子裡,我們在這裡看到人流如織,熙熙攘攘,他們是來自全國的官員、學生、工程師、經銷商、消費者和媒體記者。大街小巷彩旗招展、巨大的條幅橫跨在馬路上方,上面的寫的是,「中關村——伴您進入資訊時代」。因此中關村不僅被描繪成一個電腦樂園,而且還是一個把整個國家引向新世界的開拓者。陳春先的別出心裁是中國歷史合乎邏輯的延伸,這一點暗示對中關村不是沒有影響的。甚至「中關村」這個名稱本身,也是借助於這種邏輯才超越了地理的局限。
《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撩人的。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最新一期,用了一幅血紅色的圖片來展示中國:一個巨大的五星升起在萬里長城之上,金光閃閃,在風起雲湧的大千世界投下萬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來:「中國:一個新王朝的出現」(China: Dawn of a New Dynasty)。兩位作者是《時代》雜誌執行主編助理邁克‧艾略特(Michael Elliott)和《時代》北京分社社長西蒙‧艾勒根(Simon Elegant),為這期封面寫出的故事長達十一頁,按照他們的描述,在這個剛剛開始的世紀裡,美國的力量會走下坡,而中國的力量將上揚。中國正將它的經濟影響轉變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一點也不誇張。」
這是好幾年來世界性持續不斷的「中國話題」的最新表述。在這個世紀的最初幾年裡,全世界的人都在湧向中國。他們面對這個急劇變化的國家,每天都在問:中國的崛起會成為事實嗎?這會是一個和平過程嗎?這會成為國際化浪潮的一部分嗎?會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嗎?這個擁有强大經濟實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會同西方發生衝突嗎?
「你也要告訴我們一個中國崛起的故事嗎?」在北京城中心一個寫字樓的午餐廳裡,瑪莎‧艾佛瑞(Martha Avery)這樣問我。她是個美國人,作家和翻譯家,也是我過去一本書的英文版譯者。她對世界富有責任感,對中國充滿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樣,她只能站在很遠的地方打量這個國家,所以才會有此一問:「你能否告訴我們,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須用我自己的方式。」雖然我將著眼於整個國家的大歷史,但是在描述這個歷史進程的時候,我的重點仍將是具體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將由內部而不是由外部來觀察。這一回我選擇的樣本是中關村。
就歷史來說,中關村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這個國家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饑餓,又讓自己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製造業基地」。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術的高地,把「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這是新一代人的夢想,激勵著整個國家再接再厲,進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這拓展了中國和西方大國的合作,也增加彼此間的疑慮。而中關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它迄今為止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自己。
我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接觸中關村,但是存心把它寫出,是過去兩年的事。在這之前,我用了大約十八個月追踪微軟亞洲研究院,又用六個月調查聯想集團。這兩個機構都在中關村,相距不到兩公里。一個是典型的美國公司,一個是典型的中國公司。那時我希望從公司內部來觀察時代的融匯演進,而把大部分中關村的故事抛諸身後。直到二○○五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當時我來到雙清路上,在清華創業園A座三○二房看到一個場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開。這間屋子裝著三十八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過占有其中一個方格,由一張簡易電腦捉和一把旋轉椅組成,和大公司裡那種員工座位沒有什麼差別,只不過,在通常鑲嵌員工姓名的地方,貼著公司名稱,一律由普通道林紙列印而成,凌亂一片,讓我想起滿天繁星。電腦桌後面坐著的那些人,個個年輕。他們是老闆,也是會計,還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員工。只要花五百塊錢,就能在這裡坐一個月,而他們在這裡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半年。很多人失敗了,但總會有人成長起來,擴大隊伍,搬到樓上。那裡有單間辦公室,沿著走廊排列,是為他們這些人準備的。室內空間略大,可以擺下四、五張桌子,門外掛著一塊公司招牌。站在走廊裡,可以看到兩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筆直地伸到盡頭。十二個月,也許十八個月之後,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會垮臺,但必定有幾家繼續成長,將搬到更大的寫字樓去,占據整整一層。我對公司的創業景象並不生疏,可眼前這一切竟是聞所未聞。微軟和聯想都是擁有數萬員工的龐大公司,但是說老實話,都沒有「A座三○二房」那樣讓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氣,看到壓力和不確定性,看到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張桌」,「一間房」,「一層樓」,「一幢樓」。這個脈絡直觀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長過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資本關係、技術路線和公司結構,已經和他們的前輩完全不同,節奏也更快。中關村的公司還是成者少,敗者多。就像書中所描述的那樣,當中有七七%在三年內消逝,有九○%在五年內消逝,有九九%在十年內消逝。但這並不能阻止創業者前赴後繼、一代接著一代地走過來。他們已經走了二十七年,直到今天。先行者為後來者提供了範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所有這些構成了中關村的故事,也成為這個國家歷史的一部分。
我意識到,我所看到的中關村的一些事情,為公衆所不知,而公開輿論中很多深入人心的東西,又與其本來面目相去很遠。於是我便生出一個念頭,想把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對我的想法不以為然,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中關村有什麼高科技?應當說,在對它的種種批評中,這是客氣的。我們都知道,還有人堅定地認為,「中關村就要死亡。」這個說法比較專業的表述是,它「已無力領導中國的高科技走向」;比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噴湧的死火山」。這種輿論自二○○四年春天以來特別强大,以致引發一場激烈的討論。贊成者和反對者全都理直氣壯,實際進程中則充斥著相互對立的證據。這讓故事更加生動,富有衝突、懸疑和戲劇性,但同時也增加了我們討論問題的難度。這些問題有:中國為什麼出了個中關村?中關村為什麼變成今天這樣子?它的精神源泉來自何處?究竟是民族主義的伸張,還是西方思想的產物?它的商業體系是如何形成?它掀起的三次技術浪潮是怎樣影響整個中國?民間資本為什麼能夠戰勝國家資本,成為主導力量?它也經歷了原始積累的階段嗎?它有原罪嗎?有欺騙嗎?有無法無天嗎?有勾心鬥角嗎?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樣遞進?它究竟是個新技術的聖地,或者只不過是個大集市?它究竟是技術第一,還是市場第一?究竟是科學家更重要,還是企業家更重要?為什麼中關村的公司總是長不大?好不容易長大了又為何不能避免盛極而衰的命運?政府應當介入嗎?應當干預嗎?應當憑藉行政權力去支援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嗎?如果不應當,那麼怎樣制止它的混亂和無法無天?如果應當,又該以怎樣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經過氣了嗎?「海歸」將要成為它的主力軍嗎?當跨國公司紛紛進駐之時,它還是小公司的天堂嗎?它還是新技術的發源地嗎?它還是國家創新的一面旗幟嗎?它將會成為一個世界創新中心嗎?也許,它的歷史已經中斷,將被上海、深圳這樣的地方取代?
就中關村而言,要想把所有問題都解釋清楚是一件困難的事。生機勃勃、充滿變化的新世界總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關村這樣的地區,不僅中國僅有,而且全世界難能有二。它的時間延續至今,跨越中國全部改革歷程。從官方立場上看,它作為科技園的歷史是從一九八八年開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間研究者看來,自從陳春先一九八○年自行其是地創辦了第一家公司,中關村的新革命就已經開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這個國家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以致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窮人、博士和文盲、外來人和本地人、高官顯貴和三教九流,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機會在這裡譜寫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紛繁複雜: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技術問題、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傳統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人的本性問題。每個故事的結局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還在繼續,所有人物都是「進行式」。世界每天都在變化,誰也不能預見他們面對變化將會如何行動。即使你整天生活在這裡,要想說清楚一些事情還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評論活著的人們非常困難,實在是因為他們距離我們太近的緣故。我常常想,也許敘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會更容易些,不禁佩服那些每天品評前朝往事、抒發思古幽情的學者與作家是那麼聰明知趣。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就會失去信譽;如果我迎合民間輿論,也有譁眾取寵之嫌。總之,無論唯上還是媚俗,都會離開公正從容的立場,使得人們更加簡單化和更誇張地評估某些問題。我並不期望本書的描述能和中關村的正史合拍,那是歷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職業是記者,對於人物和事件的取捨,更多的是出於記者本能。我希望讓讀者瞭解這裡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我想對讀者說:「它在高科技之路蹣跚而行的曲折歷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國崛起的真相。」這包括它的陽光和陰暗,包括它的英明之舉和愚蠢行為,也包括它的混亂和秩序。
資料的來源是當事人的回憶、政府和公司的檔案,以及公開出版物。中關村色彩斑斕的歷史既存在人們心中,也存在浩繁的文獻中。為此我用八個月的時間在中關村調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對聯想集團和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採訪,那麼我在這裡已經花費三十二個月。我採訪了大約三百個人,包括企業經理、科學家、工程師、銷售人員、會計、商販、教師、學生、留學生、農民工、政府領導者。這些採訪幾乎全是一對一的談話。他們相當坦率和真誠,給了我那麼多的故事和思想。儘管如此,我知道記憶通常夾雜個人情感,而且會因時間的推移而產生偏差,所以還用很多精力查閱原始資料。應當感謝中關村管委會和海澱區的領導者們,他們為我開放了兩個政府檔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應當感謝中關村園區志編寫小組的那些專業人員,他們把自己掌握的資料毫無保留地讓我使用。同時我還要感謝互聯網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術,讓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開輿論中的有關部分。舉個簡單的例子,當我用「百度」搜索「中關村+盜版」的時候,就會顯示至少四十萬個網頁。所有這些,都成為我的重要參考。
由於資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對於事實的選擇和駕馭要比收集這些事實更加困難。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價值判斷,而價值準則卻隨著國家的進步不斷變化。昨天的天經地義,今天也許就會讓人貽笑大方。我只是盡可能地以忠實於歷史原貌的方式組織和敘述這個故事。初稿的長度遠遠超出預期,後來又經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壓縮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不是整段整頁地删節,而是逐字逐句地濃縮,為此用掉更多時間,只是希望讀者在减少閱讀負擔的同時不致於丟失有用有趣的情節。
把這麼多精力和熱情投入這個話題,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實說,它影響了我的職業經歷。我要學習很多新東西,還要讓自己多年的閱歷得到伸張,因此承擔更多壓力,獲得新的表達空間。這在我本人也是一個成長經歷。它很艱辛,但充滿魅力。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寫作者。在採訪和寫作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人來告訴我應當做什麼和不應當做什麼。我有許多辦法既不違反遊戲規則,又讓讀者明白我的意思。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任何人都不可能隨心所欲地表達自己,我也一樣。如果有人認為我的敘述只不過是以偏概全,有粉飾之嫌,或者過於刻薄。我只能說,依據目前可以獲得的資料和開放程度,這是我能做到最接近事實的描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仍是關於事實的。本書所有內容,包括細節、資料、人物對話和心理活動,都有確鑿根據,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極大精力用在事實的校正上,盡可能地避免錯誤,但我深知本書時間跨度極長,內容如此浩瀚,有些間接得來的材料無法一一核實確認,即使是事件親歷者的敘述也難免發生偏差,所以發生事實方面的錯誤也許是難免的。如果讀者發現其中有任何問題,我希望能夠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凌志軍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一章: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國。」
在出現人們所謂「電子一條街」之前的兩年裡,白頤路被一種神經質的緊張氣氛籠罩著。幾乎人人都能看出,總有一些事情要發生了。這種預感就像瘟疫一樣,在這條狹窄的街道緩慢而又堅定地彌漫開來。
緊張氣氛來自那個聞名遐邇的大院子。用今天的京城地圖來比照,這是靠近四環北路的一片土地,高樓林立,巨大的玻璃帷幕構成一幅幅誇張的幾何圖形,在藍天的襯托下散發出眩目的光芒。而在當時,這裡還是一片灰色建築,被農田分割包圍。它在行政上隸屬於中國科學院,包括計算所、物理所、數學所和電子所。自一九五○年代以來,它一直都是這個國家的某種象徵,神聖,寧靜,單調,猶如一潭深水。而現在,也即一九八二年冬,竟由於兩個人的衝突,蕩起層層漣漪。
陳春先和他的上級管惟炎,成為這場衝突的兩個極端的代表。前者是個理論物理學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可惜他的熱情已經背離既定道路。當時他正在傾心盡力地經營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公司,自詡為「科技游擊隊」。作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管惟炎一點也不喜歡他的這個同行和下屬,這種情緒在過去兩年漸漸積累,直到開始懷疑陳春先的人品。他先是指控陳在牟取金錢方面的私利,乃至玷污神聖的科學殿堂,接著又要求審查陳的公司賬目。審查行動在一九八二年三月開始,到年終還是沒有一點停下來的跡象。
在這個命運攸關的冬天,關於陳春先和他的公司,白頤路上謠言紛紛。這些謠言每句話都是一項嚴重指控,在當時也並非沒有一點根據,可是按照今天的條律和實情,卻又是荒誕不經和可笑的。有的謠言說,這個人正在收買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其基本方法就是恣意發放「紅包」,數額超過國家工資,又全部隱匿不報。有的謠言說,這個人把國家科研經費竊為私有。還有人聲稱,已經看到一份非法獲取收入者的名單,牽涉至少二十個科學家和大學教師。攻擊的矛頭無一例外地指向陳春先和他的兩個合夥者,紀世瀛和崔文棟。一九八三年元旦前後的幾個星期,這三人躲在物理研究所院內那間藍色的木板小屋裡,個個神情緊張,坐立不安。「科技游擊隊的指揮部擱淺了」,紀世瀛在後來撰寫的一篇回憶錄中說,「藍色板房墜入緊張而窒息的氣氛之中……」
陳春先儘管神情沮喪,仍然堅定不移,期待他的時辰很快到來。他一直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對抗管惟炎所長代表的力量,可惜無法穩定自己的隊伍。公司員工不是大學教師就是科學院的研究員,只在八小時之外投入進來,所以被叫做「星期日工程師」。對他們來說,職業的穩定是天經地義,辭職跳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他們在所長的壓力下很容易地被瓦解了。現在,陳春先面前只剩下紀世瀛和崔文棟。三人相顧無言,彼此心照,誰都不知道怎樣超越那個無形屏障。根據紀世瀛後來的回憶,當時場面「冷清得怕人」。最後還是陳春先打破沈默:「我說要幹下去,你們倆也說要幹下去。我們態度一堅決,就會有第四人、第五人。」
不幸的是,這個冬天陳春先期待的「第四人」始終沒來。如果有人再次走進藍色小屋,那也是偷偷來告別的。保存至今的公司檔案中有一些文件,表明員工們紛紛退還津貼。這些錢原本只是他們辛勤工作的報酬,其數額為每人每月三十元。但現在人人都說,這是「非法所得」,難免貪污之嫌,倘若不能如數退還,說不定什麼時候警察就會拿著手銬出現在門口。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是個星期二。破曉時分,物理所大院的西北角上忽然一片喧嘩。聲音湧進八十八號樓,穿過狹窄漫長的走廊,不出所料,是朝著紀世瀛家來的。他聽到人聲、掌聲、腳步聲,接著是敲門聲,當即「嚇了一跳」,而他的妻子則是「心裡一緊」。這兩年讓這夫妻倆心驚肉跳的事情太多了,「天曉得又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許真的是警察來了!」
慌張中的紀世瀛聽清了幾句話:「快打開收音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電臺裡說,你們是對的。」「這下子你們翻身了!」
他奪門而出,回到兩個風雨同舟的夥伴中間。三人相擁一處,眼裡掛著淚,就像惡夢醒來,互相詢問這消息是不是真的。
千真萬確,這是真的!大家終於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彼此祝賀,看著同事們圍攏過來,時而拱手,時而大笑,腳下踏著有力的節奏,齊聲高喊「解放了!解放了!」
日後那些研究中關村的歷史家們,是應當為這個早晨留下一頁的,因為它是一場新革命的無數轉捩點中的第一個。情勢急轉直下。陳春先,這個圓臉、小眼、面相柔和、沒有稜角的南方人,這個在童年時代挨過餓的窮光蛋,這個在中國和蘇聯的蜜月時代赴莫斯科大學專攻核子物理的留學生,這個衣衫不整、扣子常常對錯的邋遢鬼,這個在東方和西方的冷戰時代為國家原子物理科學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這個對抗上級因而被冷落的倒楣蛋,這個掛著研究員頭銜卻在搗騰小買賣的不務正業者,這個已有三十年共產黨黨齡卻揮舞著金錢引誘科學家紅杏出牆的叛逆者,就從這時起,成了中關村的英雄。
然而當時沒人想到他會成為英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不過感到陽光回到心裡,陰霾一掃而光。這種感覺,只有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一天有過一次(註1)。可是他們對於驟然發生的變故還有疑問,不知究竟出了什麼事。中國科學院正在流傳一個新故事,說中南海知道了陳春先的遭遇,指斥管惟炎的行為是在壓制科技人員的創新激情。在這個傳言的散布者看來,媒體都是黨的「喉舌」,國家電臺既然敢於出頭露面,那麼這傳言就算經過添油加醋,也必然會有根據。
陳春先回到家裡,已是深夜,雖然很累,但很快活,心中唯有一個懸念揮之不去,徹夜不眠:「難道真是什麼有來頭的人說話了?」
這個早晨發生的事情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是我們將要講述的這個故事的起點。在後來那些回顧歷史的人們中間,陳春先常常被說成是「中關村第一人」。他的那個根本不像公司的公司一共存在五年,在技術方面乏善可陳,在管理方面一塌糊塗,但是在中關村迄今為止的歷史上,它的確產生了一種顛覆性的力量,雖然是緩慢地擴展著它的影響,但其性質和激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它把科技人員送到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境地,讓他們的熱情和智慧在金錢、物欲和普通人的需求中得到滿足,就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裡說的,是「一條新路」。
成為「第一人」的這個人,那年四十八歲。這個在中國科學院的一潭死水般的院子裡扔進一塊石頭的人,肯定是個見異思遷的天才。
陳春先開創的歷史,始於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天,他創辦了一個別出心裁的組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很難說它是一間企業,因為它在當時既無工商註冊,也無法人代表,甚至連他的上級也被蒙在鼓裡。紀世瀛說它是「偷偷成立的」,這並非故作神秘。因為當時他們如果報告上級,可以肯定不會獲得批准。創業的動議最初只在三人之間商討,性質類似於密謀。其中最富戲劇性的情節,是整件事情完全在中關村八十八號樓醞釀而成。這座建築因為住著眾多成就非凡的科學家而在當日中國享有盛名,其中包括陳景潤、楊樂和張廣厚。紀世瀛一家人住在一層最東頭的房間,門牌「一○三」。那是一個以「振興中華」號令全國的年代。記者們頻繁出入,把這群科學家弄到報紙、電臺、電視臺上去張揚,當作為國奉獻的榜樣。他們居然沒有發現,這樓房裡正在進行一項對抗國家體制的計畫。
密謀者的隊伍漸漸擴大,到一九八○年秋天已有十人。為首者陳春先是物理所一室主任、中國科學院裡最年輕的研究員,還是中國有機半導體和原子能受控熱核聚變融合(@台灣通稱「熱核融合」@)研究領域的領先人物。此外還有紀世瀛,自詡為「嚴濟慈的關門弟子」,如果這話有些誇張,那麼「第一批參加原子彈設計的大學生中的一個」,以及「中國科學院裡最年輕的工程師」,則是真的。那年他三十八歲,喜歡張揚,花樣百出,誇誇其談,而且還將隨著年齡的增長更加偏執和疾惡如仇。有崔文棟,他是物理所高壓電氣技師;有曹永仙,力學研究所工程師;有陳首燊,電工研究所研究員;吳德順,電子研究所工程師;羅承沐,清華大學講師;劉春城,物理研究所技師;潘英,物理所會計;還有汪詩金,他是北京等離子體協會秘書長,也是這支隊伍中唯一不屬於中國科學院的人。
這天晚上,十個人聚在物理所,宣告成立「服務部」。因為是個週末,院子裡空無一人,沒有張燈結彩,沒有鮮花,沒有賀詞,沒有鞭炮齊鳴,甚至連個公司的牌子也沒有。他們經過辦公樓,再繞到核聚變實驗樓的東北角上。這裡有個小屋子,木板結構,鐵門,原本是個堆放廢舊實驗物資的庫房,現在經過一番打掃,就成了「服務部」的第一個辦公地點。
根據學者們後來的考證,這是中關村第一個民營科技企業。當時的一切都像是美國矽谷學生創業故事的翻版:幾個文化人,舉債五百元,還有一間舊倉庫。倉庫的窗戶掛著一塊蔚藍色的塑膠布,權作窗簾。從外面看去分外顯眼,所以被他們叫做「藍色小屋」。多年以後,服務部早已不復存在,陳春先已不在人世,藍色小屋也在中關村的大規模拆建中夷為平地,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只有紀世瀛仍舊對它一往情深。就在小屋將被拆除的那一刻,他跑去為它留下照片。他還清楚記得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沒想到它會成為歷史」,他逢人就說。遇到喜歡聽他說話的人,他就繪聲繪色地描述這段「歷史」。
所謂「中關村第一個民營科技企業」,其實也是中國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當日中國的科技企業數以千計,不是「國家的」,就是「集體的」,還沒有哪一家是屬於私人的。多年以後中關村聲譽鵲起,每年一度在白頤路舉行盛大「慶典」,成為慣例。在那些情緒激昂、如痴如狂的日子裡,我們在這裡看到人流如織,熙熙攘攘,他們是來自全國的官員、學生、工程師、經銷商、消費者和媒體記者。大街小巷彩旗招展、巨大的條幅橫跨在馬路上方,上面的寫的是,「中關村——伴您進入資訊時代」。因此中關村不僅被描繪成一個電腦樂園,而且還是一個把整個國家引向新世界的開拓者。陳春先的別出心裁是中國歷史合乎邏輯的延伸,這一點暗示對中關村不是沒有影響的。甚至「中關村」這個名稱本身,也是借助於這種邏輯才超越了地理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