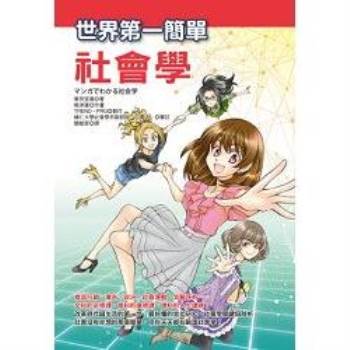1.3 風俗習慣與民德
■ 屬於個人與社會的風俗習慣
風俗習慣(folkways,又稱習俗、民俗)一詞出自活躍於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社會學家孫末楠(W. G. Sumner,又作孫莫楠)。孫末楠解釋:「風俗習慣是為了努力滿足內心欲求而產生的個人習慣(habbit)、社會習慣(custom)。」(Sumner 1906/1959:p.vi)藉由遵從風俗習慣以獲得利益、消除不便,我們即可生活得更輕鬆。這是人們共有且固著化、定型化的行為模式,亦即存於日常生活的種種約束。
以承載眾多乘客的大眾交通工具為例,在車廂內閱讀報章雜誌、用手機,甚至是耳機流洩出來的樂聲都會影響到他人,當然在車廂內化妝散發出來的化妝品與香水味也會造成他人的困擾。為了盡量減低於尖峰時段通勤的痛苦與不開心,人們摸索出可約束行為的個人習慣,甚至是社會習慣。在車廂內化妝或喧嘩,雖然尚無法律加以約束,但確實違反了風俗習慣。
■ 有嚴格懲處辦法的民德
違反民德(mores,又稱為律習、民規)是毫無轉圜餘地的,民德是最重要的風俗習慣,是某個共同體認為正確的事,一般人相信民德受破壞會剝奪人們的幸福,損害共同體的利益,而破壞之人當然必須接受懲罰(sanction),也就是制裁。孫末楠對民德的定義是:由構成「真實」與「正確」的要素發展而來的「福利的教義」(doctrines of welfare,意指絕對正確而不可違背、損害的教條,若違背之,將有損共同體的利益);是一種在哲學與倫理上具有普遍性的風俗習慣(意指在哲學與倫理上,人們都應遵守這些風俗習慣)。(Sumner 1906/1959:P.35)
偷拍是指未獲得被拍攝者的同意,逕自拍攝的行為,有時會伴隨暴力、脅迫,甚至會被拍成影片。多數偷拍行為將女性視為性幻想對象,具有貶抑意味,例如偷拍裙底風光、臉部與身姿等,這種行為只為滿足單方性欲,是違反社會期望的行為。如果偷窺、偷拍他人容貌與身體的行為不受到約束,人們將無法安心地上街與生活。偷窺與偷拍這種侵犯私領域與性領域的行為,不只錯誤、鬼祟,更會破壞個人的幸福與公共福祉。
現代日本法律已明定,偷窺、偷拍是違法行為。除了國家介入的刑事處罰,做出此行為的犯人在公民社會也會因為侵犯民德而受到嚴厲制裁。在共同體中,破壞重要規則的人會失去人們的信任,進一步失去工作、受排斥、被輕蔑,有時甚至會遭受眾人的私刑(lynching)。嚴厲的制裁間接反映了民德的重要性,及遵守的必要。傳統社會的村落共同體所訂定的規則大多屬於民德,例如日本江戶時代的「村八分」即是對破壞村落規矩、秩序者,所施予的消極制裁,斷絕侵犯民德者與他人的往來,並禁止與他人交易。■ 風俗習慣使人們的行為定型化,屬於一種規範
在大眾交通工具上喧嘩、化妝、偷拍都違反了規範。規範(norm)即是規定、約束人們行為的尺度。風俗習慣是一種規範,會使人們的行為定型化。在大眾交通工具上小心地不干擾到他人、排隊結帳、欣然捐款、參與義賣活動、尊敬長者,都是風俗習慣,上述例子只是整體風俗習慣的一小部分。世界充滿了「無意識的、自然發生的、不完備的」風俗習慣(Sumner,1906/1959:p.19),它們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且為數眾多。無論是個人習慣、社會整體的習慣,或是固定化、定型化的行為,只要大家都遵守各式各樣的風俗習慣,就會為群體帶來共同利益,可使整個社會的成員都生活得更便利。
■ 風俗習慣的不合理與傳統
風俗習慣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能提高生活的便利性,有助於社會成員經營舒適的共同生活,但是風俗習慣包括了自古以來的習慣,一定有不符合現代的、不合理的習慣。那些不合理、徒留形式的風俗習慣,即是趕不上時代變化的舊習(convention)。過年包紅包、中元節與歲末的送禮習慣皆屬於此類。日本以前的「紅包」(日文為「年玉」)寫作「年賜」、「歲魂」,是藉由發送食品、物品來慶祝新年的「歲神信仰」儀式,但現代的紅包已失去原本的意義,演變成發送現金的方式,原本的信仰色彩變得薄弱,對孩子與年輕人來說,只剩下開心拿零用錢的表面形式,祝福意味淡薄。
風俗習慣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會充分發揮使行為固著化、定型化的作用,因此,即使父母與長者手頭不方便,也不容易廢除紅包的習俗。對大人來說,取消紅包或許比較合理,曾有節目報導,許多父母會把孩子收到的紅包存起來,當作教育基金或結婚基金,甚至有人會轉包給其他孩子,由此可知,即使風俗習慣原有的意義已改變,仍被視為傳統,被人們所遵守。■ 民德居於風俗習慣的最上層
違反風俗習慣只會引來人們異樣的眼光,即使受懲罰,也都很輕微,例如在大眾交通工具上化妝。另外,發紅包很吝嗇的大人總是會給孩子「小氣鬼」的印象,但應該不會因此遭受極大的譴責。
相對於此,侵犯民德則是無法補償、不可原諒的。除了前文所述的偷拍,性侵、放火、強盜、殺人等都是嚴重侵犯民德的例子。民德以不能殺人、不能傷害他人、不能偷盜等禁令來表示,因為「民德的大部分行為是由被視為不可行的禁忌所形成的」(Sumner 1906/1959:p.30),相較於易隨時間和空間變化的風俗習慣,民德可超越語言、宗教與文化的差異,大多通用於不同的時空背景。除非是戰爭與社會動盪不安的時代,否則獎勵強姦、放火、偷盜、殺人的社會是不被認可的。另外,由於侵犯民德會為社會全體成員帶來嚴重的傷害,所以國家大多以法律(law)的形式要求社會成員遵守民德,並以司法的制裁、刑罰(punishment)來懲罰違反者。
有些民德雖然法律不追究,但仍被重視,例如學生考試作弊,會被處以退學、停學、取消學分的懲罰。另外,日本雖然未對外遇與不倫戀處以刑罰,但當事人仍可能因此受到社會譴責,而使人生走下坡。
民德作為個人與社會的習慣,雖隸屬於風俗習慣,但位於風俗習慣的最上層,具有特殊型態。因為遵守民德有利於人們的幸福與社會全體的福祉,因此人們堅信它的「正確性」,且為了確保民德被遵守會制定嚴苛的制裁。
■ 風俗習慣與民德衍生為法律與道德
美國社會學家孫末楠曾經論及,人們共同生活,會自然形成風俗習慣,以及發展自風俗習慣,且被人們認為極為正確的民德。風俗習慣、民德、法律與道德在現實中是相互重疊的,但在社會學則有所區分。最初的風俗習慣與民德是被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結構化、文字化、認可的產物制度與法律;而個別的風俗習慣與民德則在宗教信仰的拉扯下成為抽象化、一般化的產物道德與倫理。「制度與法律生於民德」(Sumner 1905/1959:p.53)、「處世哲學、生活準則、正確性、各種權利、道德皆為風俗習慣的產物」(Sumner 1905/1959:p.29)。風俗習慣與民德具有易於掌握的具體形式,是理解何謂「規範」的出發點。
■ 屬於個人與社會的風俗習慣
風俗習慣(folkways,又稱習俗、民俗)一詞出自活躍於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社會學家孫末楠(W. G. Sumner,又作孫莫楠)。孫末楠解釋:「風俗習慣是為了努力滿足內心欲求而產生的個人習慣(habbit)、社會習慣(custom)。」(Sumner 1906/1959:p.vi)藉由遵從風俗習慣以獲得利益、消除不便,我們即可生活得更輕鬆。這是人們共有且固著化、定型化的行為模式,亦即存於日常生活的種種約束。
以承載眾多乘客的大眾交通工具為例,在車廂內閱讀報章雜誌、用手機,甚至是耳機流洩出來的樂聲都會影響到他人,當然在車廂內化妝散發出來的化妝品與香水味也會造成他人的困擾。為了盡量減低於尖峰時段通勤的痛苦與不開心,人們摸索出可約束行為的個人習慣,甚至是社會習慣。在車廂內化妝或喧嘩,雖然尚無法律加以約束,但確實違反了風俗習慣。
■ 有嚴格懲處辦法的民德
違反民德(mores,又稱為律習、民規)是毫無轉圜餘地的,民德是最重要的風俗習慣,是某個共同體認為正確的事,一般人相信民德受破壞會剝奪人們的幸福,損害共同體的利益,而破壞之人當然必須接受懲罰(sanction),也就是制裁。孫末楠對民德的定義是:由構成「真實」與「正確」的要素發展而來的「福利的教義」(doctrines of welfare,意指絕對正確而不可違背、損害的教條,若違背之,將有損共同體的利益);是一種在哲學與倫理上具有普遍性的風俗習慣(意指在哲學與倫理上,人們都應遵守這些風俗習慣)。(Sumner 1906/1959:P.35)
偷拍是指未獲得被拍攝者的同意,逕自拍攝的行為,有時會伴隨暴力、脅迫,甚至會被拍成影片。多數偷拍行為將女性視為性幻想對象,具有貶抑意味,例如偷拍裙底風光、臉部與身姿等,這種行為只為滿足單方性欲,是違反社會期望的行為。如果偷窺、偷拍他人容貌與身體的行為不受到約束,人們將無法安心地上街與生活。偷窺與偷拍這種侵犯私領域與性領域的行為,不只錯誤、鬼祟,更會破壞個人的幸福與公共福祉。
現代日本法律已明定,偷窺、偷拍是違法行為。除了國家介入的刑事處罰,做出此行為的犯人在公民社會也會因為侵犯民德而受到嚴厲制裁。在共同體中,破壞重要規則的人會失去人們的信任,進一步失去工作、受排斥、被輕蔑,有時甚至會遭受眾人的私刑(lynching)。嚴厲的制裁間接反映了民德的重要性,及遵守的必要。傳統社會的村落共同體所訂定的規則大多屬於民德,例如日本江戶時代的「村八分」即是對破壞村落規矩、秩序者,所施予的消極制裁,斷絕侵犯民德者與他人的往來,並禁止與他人交易。■ 風俗習慣使人們的行為定型化,屬於一種規範
在大眾交通工具上喧嘩、化妝、偷拍都違反了規範。規範(norm)即是規定、約束人們行為的尺度。風俗習慣是一種規範,會使人們的行為定型化。在大眾交通工具上小心地不干擾到他人、排隊結帳、欣然捐款、參與義賣活動、尊敬長者,都是風俗習慣,上述例子只是整體風俗習慣的一小部分。世界充滿了「無意識的、自然發生的、不完備的」風俗習慣(Sumner,1906/1959:p.19),它們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且為數眾多。無論是個人習慣、社會整體的習慣,或是固定化、定型化的行為,只要大家都遵守各式各樣的風俗習慣,就會為群體帶來共同利益,可使整個社會的成員都生活得更便利。
■ 風俗習慣的不合理與傳統
風俗習慣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能提高生活的便利性,有助於社會成員經營舒適的共同生活,但是風俗習慣包括了自古以來的習慣,一定有不符合現代的、不合理的習慣。那些不合理、徒留形式的風俗習慣,即是趕不上時代變化的舊習(convention)。過年包紅包、中元節與歲末的送禮習慣皆屬於此類。日本以前的「紅包」(日文為「年玉」)寫作「年賜」、「歲魂」,是藉由發送食品、物品來慶祝新年的「歲神信仰」儀式,但現代的紅包已失去原本的意義,演變成發送現金的方式,原本的信仰色彩變得薄弱,對孩子與年輕人來說,只剩下開心拿零用錢的表面形式,祝福意味淡薄。
風俗習慣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會充分發揮使行為固著化、定型化的作用,因此,即使父母與長者手頭不方便,也不容易廢除紅包的習俗。對大人來說,取消紅包或許比較合理,曾有節目報導,許多父母會把孩子收到的紅包存起來,當作教育基金或結婚基金,甚至有人會轉包給其他孩子,由此可知,即使風俗習慣原有的意義已改變,仍被視為傳統,被人們所遵守。■ 民德居於風俗習慣的最上層
違反風俗習慣只會引來人們異樣的眼光,即使受懲罰,也都很輕微,例如在大眾交通工具上化妝。另外,發紅包很吝嗇的大人總是會給孩子「小氣鬼」的印象,但應該不會因此遭受極大的譴責。
相對於此,侵犯民德則是無法補償、不可原諒的。除了前文所述的偷拍,性侵、放火、強盜、殺人等都是嚴重侵犯民德的例子。民德以不能殺人、不能傷害他人、不能偷盜等禁令來表示,因為「民德的大部分行為是由被視為不可行的禁忌所形成的」(Sumner 1906/1959:p.30),相較於易隨時間和空間變化的風俗習慣,民德可超越語言、宗教與文化的差異,大多通用於不同的時空背景。除非是戰爭與社會動盪不安的時代,否則獎勵強姦、放火、偷盜、殺人的社會是不被認可的。另外,由於侵犯民德會為社會全體成員帶來嚴重的傷害,所以國家大多以法律(law)的形式要求社會成員遵守民德,並以司法的制裁、刑罰(punishment)來懲罰違反者。
有些民德雖然法律不追究,但仍被重視,例如學生考試作弊,會被處以退學、停學、取消學分的懲罰。另外,日本雖然未對外遇與不倫戀處以刑罰,但當事人仍可能因此受到社會譴責,而使人生走下坡。
民德作為個人與社會的習慣,雖隸屬於風俗習慣,但位於風俗習慣的最上層,具有特殊型態。因為遵守民德有利於人們的幸福與社會全體的福祉,因此人們堅信它的「正確性」,且為了確保民德被遵守會制定嚴苛的制裁。
■ 風俗習慣與民德衍生為法律與道德
美國社會學家孫末楠曾經論及,人們共同生活,會自然形成風俗習慣,以及發展自風俗習慣,且被人們認為極為正確的民德。風俗習慣、民德、法律與道德在現實中是相互重疊的,但在社會學則有所區分。最初的風俗習慣與民德是被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結構化、文字化、認可的產物制度與法律;而個別的風俗習慣與民德則在宗教信仰的拉扯下成為抽象化、一般化的產物道德與倫理。「制度與法律生於民德」(Sumner 1905/1959:p.53)、「處世哲學、生活準則、正確性、各種權利、道德皆為風俗習慣的產物」(Sumner 1905/1959:p.29)。風俗習慣與民德具有易於掌握的具體形式,是理解何謂「規範」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