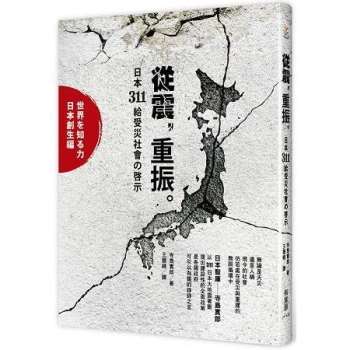收看電視連戲劇《仁醫》之後─人人都是「南方仁」
經歷了好幾代,祖先們沿續了生命,拜此所賜,我現在才會在這裡─這樣一寫,或許有很多人會聯想到2011年6月時才播映完畢,日本TBS電視的高收視連戲劇《仁醫》吧。以下引用該劇的作品介紹,讓沒有收看過的人也能了解一下。
一部壯麗的歷史劇,一位現代的腦外科醫師─南方仁(大澤隆夫飾演),因為某個事件的緣故而穿梭時空到了江戶時代,在沒有令人滿意的醫療器具的環境下,拯救了幕末時代許多人的性命,透過他的醫術,加深了和幕末英雄坂本龍馬(內野聖陽飾演)等人的交流,同時和無論於公於私都給與他許多協助的橘咲(綾瀨遙飾演),以及曾經是吉原花魁的野風(中谷美紀飾演),一起身陷於幕末的動亂之中。
這部電視劇裡,將南方仁原本的未婚妻─友永未來─以及花魁野風,描述成極為相像的兩個人。角色的設定上,暗示了野風是友永未來幾代之前的祖先。再加上南方仁面對著即將被贖身的花魁,發現了她有罹患乳癌的徵兆時,想到如果為她進行乳房摘除手術,導致贖身一事破局的話,他的未婚妻將可能無法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因而對手術感到遲疑。結果雖然因為下定決心進行手術,導致贖身一事破局,但是不久之後,野風和一位法國人之間有了孩子……。這真是荒誕無稽的故事。我似乎也可以聽到有人批評說:「如果這麼害怕因為自己的介入而改變了歷史,乾脆一開始就到深山裡頭躲起來生活不就好了。」說起來的確是異想天開,但是其實也讓我重新想起了─因為有生命的連鎖,所以方才有現在的自己。原本的原著漫畫(村上紀香原作)之中,沒有友永未來這一號人物出現,將野風設定為可能是未婚妻的直系祖先這一點,據說是連戲劇改編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原著裡的南方仁,或許可以說只是單純地離開非常熟悉的日常環境,投身至另一個世界的一個人。而那個時代是幕府時代末期的江戶,包括坂本龍馬在內,還有勝海舟、西鄉隆盛、佐久間象山……,這些有如耀眼繁星般,為幕末維新增色的人物,為著開闢「新的世界」而奮鬥。南方仁就被丟入這其中。我個人很喜歡這段描寫幕末維新傑出人物們的方式。因為我覺得有將他們共通的美德很好地描寫出來。所謂的美德就是,無論是佐幕派,抑或是薩長派、勤皇派,立場雖然互異,卻沒有一個人是為了私利私欲或保全自己而利用外國的勢力。倘若每個派別只為自己或自家的利益著想而勾結外國勢力的話,日本會變得如何呢?恐怕日本會像清朝一樣,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主要戰場,而日本人將會被迫面對莫大的苦難吧。
結果日本雖然依賴英國及法國甚多,但是卻能免於成為列強的戰場,憑藉的全是他們心中懷有高潔的志向。
在這裡,我看到了新渡戶稻造(1862∼1933)著作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根源所在,有著自立自重的精神。對於依賴他人而厚顏無恥地活下去,抑或是欺騙他人、只求自己能苟活的想法,都能夠打從心底拒絕的態度,就存在於武士道。我認為這種生活的「態度」,或者是「靈魂的核心」,正確實存在於幕末維新的人們心中,所以即使面臨了來自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危機,面對了前所未有的國難,同時還伴隨著內戰狀態,依舊能保有內部的團結,建立了近代的日本。
幕末維新的傑出人物們,不!即便是當時沒沒無聞的平凡百姓們,雖然沒有穿梭時空,但是仔細想想,他們全都是被丟置在以往的常識或生活方式均不適用的世界裡。無論知名抑或是沒沒無名,對於被迫身處於其中的世界,只有採取真摯面對的態度,方能夠認真地活著,認真地死去吧。
幕末維新的人們雖然不自由,但是他們的生活態度堅定而明確,對於心無所依的現代日本人來說,幕末維新的人們應該顯得更為光彩奪目吧。
原著漫畫第一冊裡,在南方仁穿越時空到了幕末維新的時代時,曾經有以下的自問自答。
在御茶水的峽谷間,穿梭飛舞著無數的螢火蟲,彷彿像是被病魔擊倒而遺憾逝去者的靈魂……數萬的魂魄問我:你是誰,你是為了什麼而來到這裡……而後在最後一冊裡,知曉天命。
和這個時代的所有人們,一樣地生、一樣地死─在死之前,拼命掙扎地活下去……這就是我現在的心願。
我們全都是「南方仁」。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我們的存在,就像是被放逐到這個世界裡。只不過我們和南方仁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並不是從隔絕的世界被丟置在這裡。我們是經由連綿不斷的生命連鎖,而生活在2011年的日本。龍馬的聲音,你聽到了嗎?
在電視劇《仁醫》的最後一集裡,回到現代社會的南方仁,腦子裡傳來了坂本龍馬的聲音。
─就算再也見不到、聽不到,無論何時,我們永遠在仁醫師的身邊!
對於龍馬所說的話,我是這麼解讀的。(幕末的志士們,佐幕派、勤皇派、攘夷派、開國派,彼此相互殺伐。但是一切全都是希望這個國家「能夠成為我下輩子還要再來投胎的國家」。希望後代的日本人千萬別忘了這一點。因為縱使物質上的世界一再地改變,無形的靈魂世界仍然緊緊相繫。)前,拼命掙扎地活下去……這就是我現在的心願。我們全都是「南方仁」。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我們的存在,就像是被放逐到這個世界裡。只不過我們和南方仁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並不是從隔絕的世界被丟置在這裡。我們是經由連綿不斷的生命連鎖,而生活在2011年的日本。「能夠成為我下輩子還要再來投胎的國家」─這句訊息透過了整部電視劇,像是連續低音(thoroughbass)一樣地鳴響迴盪在我的內心深處。
為了將這個國家往前推進一步,為了讓這個國家的人民能過得更幸福,他們祈願,他們為了將來的生,而選擇了現在的死。未赴戰場的人們應該也是同樣的想法,而在自己身處的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
這樣的時代結束後,經過65年,我們是否真的建立了他們所期盼「再投胎一次」的國家呢?我們的生存,是否有置身於過去的目光中而活在當下的自覺呢?或者對於未來將誕生的世代,我們的生存方式是否能讓我們抬頭挺胸自信地說:「我們就是想讓日本成為這樣的國家,所以竭盡全力地活著」呢?我非常沒有把握。我可以坦白說,在我們的生活態度中,如果沒有與過去的目光相視而望的自覺,將無法產生洞悉未來的觀察力。
思考「311以後的日本」,不需要輕率的絕望和希望。不是為著毫無根據的悲觀和樂觀一喜一憂,而是該有條有理地深入思考。這時候最能成為助力的,我發現就是在歷史的脈絡之中去思考。傾聽先人的聲音,自然而然地我們就應該能夠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新渡戶稻造在接近結語的部分,曾經這麼說過。
有人預言,封建日本的道德體系將如其城廓一樣地土崩瓦解而歸於塵土,惟新的道德將像不死鳥般地奮起,引導新日本前進。而此預言已由過去半個世紀所發生的事情而得經確認。如此的預言實現是值得期望的,且應發生的,然而千萬別忘了,不死鳥僅只會在其自身的灰燼中奮起,牠不是候鳥,而且牠也不會借用其他鳥兒的翅膀飛翔。因為「不死鳥僅只會在其自身的灰燼中」復活重生。
村上春樹所提倡的方向
6月9日,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加泰羅尼亞(Cataluña)國際獎頒獎儀式」的場合裡,作家村上春樹發表了得獎記念演說。
附帶一提,「加泰羅尼亞國際獎」是加泰羅尼亞州政府自1989年創設的獎項,針對文化、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領域,每年頒獎給一位被評選為熱情性、創作性活動的人。村上春樹這次在56個國家,196位候選人之中脫穎而出。
一般人都知道,得獎人的演說主軸,通常是環繞在得獎之研究或作品的小故事上。但是村上春樹則不是如此,他一開始就先從311大地震談起。
演說的前半部分是強烈大地震方面的事。在談完活在日本這座地震列島上的宿命,日本人的內心裡也因此已經培養出了「無常」的精神特性和美學意識之後,他很清楚地提出了以下的斷言。因為這次大地震的關係,幾乎讓所有的日本人都受到強烈的打擊。連平常應該對地震習以為常的我們,直到現在都對於災情規模之大而感到心有餘悸。我們有著無力感,甚至對國家的未來都感到不安。
但是最後,我們一定會重新組織我們的精神,重新站起來走向復興之路。對此,我並沒有太擔心。我們不會永遠因為打擊而癱倒在地。我們會重新建立毀壞的家園,修補寸斷的道路。然而村上春樹真正想說的,並不是這些事。對於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問題,向全世界發言,這才是他的主要目的。
如同各位所知,我們日本人是歷史上唯一經歷過原子彈轟炸經驗的人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廣島與長崎這兩座城市,遭到美軍轟炸機投下原子彈,超過二十萬的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而存活下來的人之中,許多人因為曝露在輻射之下,後來即飽受後遺症折磨,經歷一段時間之後死亡。原子彈具有多大的破壞性,輻射對於這個世界、對於人體會留下多麼深的傷痛,我們已經從那些人的犧牲中學到了。
這次福島核能發電廠的事故,是我們日本人在歷史上經歷到的第二次重大核災。然而這次並不是被別人投擲炸彈,而是我們日本人自己親手準備,自己親手鑄下的大錯,自己污染了自己的國土,自己破壞了自己的生活。
村上春樹並且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接著他導出了以下的答案。
答案很簡單。答案就是「效率」,是「efficiency」。我們日本人對於核能,應該持續地呼喊「No!」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們應該要認真地面對村上春樹的訊息。能源是超過作家直覺的政策科學議題,我認為應該要將之積極地納入視野、認清事實,建立起當下應為正確恰當之判斷的日本能源策略。
打造公民參與型的復興構想
無論是新產業基礎的創生,抑或是首都機能的分散,或者是思考日本創生的計畫,採取公民參與型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復興的構想中,如果沒有讓公民有親身參與的興奮期待感,無法描繪出與創造未來有關的主體感動,創造新日本的運動就無法成立。「喔,對!反正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與我無關」─倘若復興的構想只讓公民冷眼旁觀而已,結果只會造就一項膚淺的構想。我認為創造新日本的運動裡,必須要有吸引有心參與者的計畫。舉例來說,1929年的大恐慌之後,美國推出及發展羅斯福新政作為國家計畫,其中即以經濟復興隊的形式,讓年輕人紛紛參與其中。我希望復興運動也能帶有那股熱忱。年輕世代的參與,比任何人都來得重要。舉例而言,像是在東北災區各縣,各組成以數百人為單位的「復興計畫推動隊」之類的組織,在全日本及亞洲公開招募人選,在一年到三年的期間裡,在策略性的目標計畫裡,每年提供二百至三百萬日圓的報酬請他們工作,這項構想如何呢?
像是投入農業生產法人的具體復興計畫,或者是副首都機能分散計畫等等,不是義務性質的志工活動,而是在「收取報酬、擔負責任地工作」的架構之下,讓年輕的能量參與,而且以培養未來能夠支援現場的人才體系來說,我認為有它的意義存在。
現今的日本因為長期處於就業冰河期,到處都是為就業所苦的年輕人。有些部分是因為不景氣,所以求才的人數減少,使得就業的機會受到限制;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些年輕人迷惘,有人想要把人生投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卻找不到想挑戰的工作。對於這些年輕人,應該要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在自己希望的地方工作,像是東北地方的農業生產法人也好,漁業與IT之間的同步也好,副首都的設計也行。我希望他們能擦擦額頭上的汗水,絞盡腦汁,四處奔走,與人接觸、討論、爭執,全力投入工作中。倘若復興計畫能夠塑造出這樣的機會,復興計畫就不會變得索然無味。從某個層面來說,或許這個過程正代表了日本創生。
以那須市作為副首都的構想為例,如果年輕人能前仆後繼地投入參與就好了。單只靠上了年紀的行政官員或專家閉門構思,往往容易被批評是「與災民無關、背離現實的討論」。建構出能讓人感受到,這是由眾人一起建構未來的復興與創生活動,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一環。
一直到這裡,我提到的都是年輕人的參與;其實還有另一項很重要的,那就是年長者的參與。這個年代的屆齡退休人士,不但一點兒也不顯得老態,而且和年輕世代相較之下,因為他們在職時代曾經經歷過經濟高度成長的年代,因此手頭上也寬裕很多。讓年長者參與的方案之一,便是讓他們以承銷人的角色,把錢花在復興債券上。據說個人金融資產有一千四百兆日圓,而其中的絕大部分就是由年長者持有。
復興財源方面的討論,內容不外乎增稅或者是發行國債。在財政困難的當頭,總是希望能避開這兩種選項,但是復興的財源一般認為至少超過二十兆日圓,這又該以何種形式籌措才好呢?這個部分需要發揮最大的智慧。即使是採取復興債券的方式,一想到關東大地震之後,因為國債擴大發行而引發了金融恐慌,總是讓人無法輕易地選擇它。因此我想提出的方案,便是盡可能減少後代子孫負擔的無利息國債。
或許有人會覺得─「有人會蠢到購買完全沒有利息的國債嗎?」但是我不這麼認為。舉例來說,提出激勵方案,只要購買復興債券即提供遺產稅減免,這個方法如何呢?對於多多少少希望能多留一點資產給兒孫的老年人來說,他們應該會非常關注吧。而且這筆資金是作為東日本復興、日本創生的事業資金所用。雖然他們不能揮汗參與計畫,但是卻依然能感覺到自己是計畫中的一分子。這並不像「全國一心」之類的說法,它和強制所有的人做同一件事的一體感不同,它沒有危險的氛圍,只有一種和聲般的一體感。「為了日本的創生和未來產業、未來技術,我希望能貢獻一己心力」─這份訊息應該也傳到了擔心日本未來的年長者心中。不需要發行戰爭債券的日本,可以說是幸福的國家。鄰近的韓國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曾經推動了「請把櫃子裡的錢奉獻出來」的國民運動。對日本的年長者提出呼籲,籌措大約十兆日圓的金額,作為投資未來的財源,僅提供遺產稅減免的優點,讓年長者承購無利息國債,我相信不是不可能的事。
本章前前後後所討論的事,主要是針對復興事業,以比較有彈性的想法,提出社會工程學式的方案。工程學是從宏觀的角度,組合個別的事業,以謀求解決問題的方案,我認為現今的日本,需要的正是Socialengineering,也就是社會工程學。我希望我們能具有社會工程學的解決方式,面對眼前存在的苦難,憑藉著有所根據的希望來面對它。
經歷了好幾代,祖先們沿續了生命,拜此所賜,我現在才會在這裡─這樣一寫,或許有很多人會聯想到2011年6月時才播映完畢,日本TBS電視的高收視連戲劇《仁醫》吧。以下引用該劇的作品介紹,讓沒有收看過的人也能了解一下。
一部壯麗的歷史劇,一位現代的腦外科醫師─南方仁(大澤隆夫飾演),因為某個事件的緣故而穿梭時空到了江戶時代,在沒有令人滿意的醫療器具的環境下,拯救了幕末時代許多人的性命,透過他的醫術,加深了和幕末英雄坂本龍馬(內野聖陽飾演)等人的交流,同時和無論於公於私都給與他許多協助的橘咲(綾瀨遙飾演),以及曾經是吉原花魁的野風(中谷美紀飾演),一起身陷於幕末的動亂之中。
這部電視劇裡,將南方仁原本的未婚妻─友永未來─以及花魁野風,描述成極為相像的兩個人。角色的設定上,暗示了野風是友永未來幾代之前的祖先。再加上南方仁面對著即將被贖身的花魁,發現了她有罹患乳癌的徵兆時,想到如果為她進行乳房摘除手術,導致贖身一事破局的話,他的未婚妻將可能無法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因而對手術感到遲疑。結果雖然因為下定決心進行手術,導致贖身一事破局,但是不久之後,野風和一位法國人之間有了孩子……。這真是荒誕無稽的故事。我似乎也可以聽到有人批評說:「如果這麼害怕因為自己的介入而改變了歷史,乾脆一開始就到深山裡頭躲起來生活不就好了。」說起來的確是異想天開,但是其實也讓我重新想起了─因為有生命的連鎖,所以方才有現在的自己。原本的原著漫畫(村上紀香原作)之中,沒有友永未來這一號人物出現,將野風設定為可能是未婚妻的直系祖先這一點,據說是連戲劇改編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原著裡的南方仁,或許可以說只是單純地離開非常熟悉的日常環境,投身至另一個世界的一個人。而那個時代是幕府時代末期的江戶,包括坂本龍馬在內,還有勝海舟、西鄉隆盛、佐久間象山……,這些有如耀眼繁星般,為幕末維新增色的人物,為著開闢「新的世界」而奮鬥。南方仁就被丟入這其中。我個人很喜歡這段描寫幕末維新傑出人物們的方式。因為我覺得有將他們共通的美德很好地描寫出來。所謂的美德就是,無論是佐幕派,抑或是薩長派、勤皇派,立場雖然互異,卻沒有一個人是為了私利私欲或保全自己而利用外國的勢力。倘若每個派別只為自己或自家的利益著想而勾結外國勢力的話,日本會變得如何呢?恐怕日本會像清朝一樣,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主要戰場,而日本人將會被迫面對莫大的苦難吧。
結果日本雖然依賴英國及法國甚多,但是卻能免於成為列強的戰場,憑藉的全是他們心中懷有高潔的志向。
在這裡,我看到了新渡戶稻造(1862∼1933)著作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根源所在,有著自立自重的精神。對於依賴他人而厚顏無恥地活下去,抑或是欺騙他人、只求自己能苟活的想法,都能夠打從心底拒絕的態度,就存在於武士道。我認為這種生活的「態度」,或者是「靈魂的核心」,正確實存在於幕末維新的人們心中,所以即使面臨了來自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危機,面對了前所未有的國難,同時還伴隨著內戰狀態,依舊能保有內部的團結,建立了近代的日本。
幕末維新的傑出人物們,不!即便是當時沒沒無聞的平凡百姓們,雖然沒有穿梭時空,但是仔細想想,他們全都是被丟置在以往的常識或生活方式均不適用的世界裡。無論知名抑或是沒沒無名,對於被迫身處於其中的世界,只有採取真摯面對的態度,方能夠認真地活著,認真地死去吧。
幕末維新的人們雖然不自由,但是他們的生活態度堅定而明確,對於心無所依的現代日本人來說,幕末維新的人們應該顯得更為光彩奪目吧。
原著漫畫第一冊裡,在南方仁穿越時空到了幕末維新的時代時,曾經有以下的自問自答。
在御茶水的峽谷間,穿梭飛舞著無數的螢火蟲,彷彿像是被病魔擊倒而遺憾逝去者的靈魂……數萬的魂魄問我:你是誰,你是為了什麼而來到這裡……而後在最後一冊裡,知曉天命。
和這個時代的所有人們,一樣地生、一樣地死─在死之前,拼命掙扎地活下去……這就是我現在的心願。
我們全都是「南方仁」。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我們的存在,就像是被放逐到這個世界裡。只不過我們和南方仁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並不是從隔絕的世界被丟置在這裡。我們是經由連綿不斷的生命連鎖,而生活在2011年的日本。龍馬的聲音,你聽到了嗎?
在電視劇《仁醫》的最後一集裡,回到現代社會的南方仁,腦子裡傳來了坂本龍馬的聲音。
─就算再也見不到、聽不到,無論何時,我們永遠在仁醫師的身邊!
對於龍馬所說的話,我是這麼解讀的。(幕末的志士們,佐幕派、勤皇派、攘夷派、開國派,彼此相互殺伐。但是一切全都是希望這個國家「能夠成為我下輩子還要再來投胎的國家」。希望後代的日本人千萬別忘了這一點。因為縱使物質上的世界一再地改變,無形的靈魂世界仍然緊緊相繫。)前,拼命掙扎地活下去……這就是我現在的心願。我們全都是「南方仁」。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我們的存在,就像是被放逐到這個世界裡。只不過我們和南方仁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並不是從隔絕的世界被丟置在這裡。我們是經由連綿不斷的生命連鎖,而生活在2011年的日本。「能夠成為我下輩子還要再來投胎的國家」─這句訊息透過了整部電視劇,像是連續低音(thoroughbass)一樣地鳴響迴盪在我的內心深處。
為了將這個國家往前推進一步,為了讓這個國家的人民能過得更幸福,他們祈願,他們為了將來的生,而選擇了現在的死。未赴戰場的人們應該也是同樣的想法,而在自己身處的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
這樣的時代結束後,經過65年,我們是否真的建立了他們所期盼「再投胎一次」的國家呢?我們的生存,是否有置身於過去的目光中而活在當下的自覺呢?或者對於未來將誕生的世代,我們的生存方式是否能讓我們抬頭挺胸自信地說:「我們就是想讓日本成為這樣的國家,所以竭盡全力地活著」呢?我非常沒有把握。我可以坦白說,在我們的生活態度中,如果沒有與過去的目光相視而望的自覺,將無法產生洞悉未來的觀察力。
思考「311以後的日本」,不需要輕率的絕望和希望。不是為著毫無根據的悲觀和樂觀一喜一憂,而是該有條有理地深入思考。這時候最能成為助力的,我發現就是在歷史的脈絡之中去思考。傾聽先人的聲音,自然而然地我們就應該能夠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新渡戶稻造在接近結語的部分,曾經這麼說過。
有人預言,封建日本的道德體系將如其城廓一樣地土崩瓦解而歸於塵土,惟新的道德將像不死鳥般地奮起,引導新日本前進。而此預言已由過去半個世紀所發生的事情而得經確認。如此的預言實現是值得期望的,且應發生的,然而千萬別忘了,不死鳥僅只會在其自身的灰燼中奮起,牠不是候鳥,而且牠也不會借用其他鳥兒的翅膀飛翔。因為「不死鳥僅只會在其自身的灰燼中」復活重生。
村上春樹所提倡的方向
6月9日,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加泰羅尼亞(Cataluña)國際獎頒獎儀式」的場合裡,作家村上春樹發表了得獎記念演說。
附帶一提,「加泰羅尼亞國際獎」是加泰羅尼亞州政府自1989年創設的獎項,針對文化、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領域,每年頒獎給一位被評選為熱情性、創作性活動的人。村上春樹這次在56個國家,196位候選人之中脫穎而出。
一般人都知道,得獎人的演說主軸,通常是環繞在得獎之研究或作品的小故事上。但是村上春樹則不是如此,他一開始就先從311大地震談起。
演說的前半部分是強烈大地震方面的事。在談完活在日本這座地震列島上的宿命,日本人的內心裡也因此已經培養出了「無常」的精神特性和美學意識之後,他很清楚地提出了以下的斷言。因為這次大地震的關係,幾乎讓所有的日本人都受到強烈的打擊。連平常應該對地震習以為常的我們,直到現在都對於災情規模之大而感到心有餘悸。我們有著無力感,甚至對國家的未來都感到不安。
但是最後,我們一定會重新組織我們的精神,重新站起來走向復興之路。對此,我並沒有太擔心。我們不會永遠因為打擊而癱倒在地。我們會重新建立毀壞的家園,修補寸斷的道路。然而村上春樹真正想說的,並不是這些事。對於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問題,向全世界發言,這才是他的主要目的。
如同各位所知,我們日本人是歷史上唯一經歷過原子彈轟炸經驗的人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廣島與長崎這兩座城市,遭到美軍轟炸機投下原子彈,超過二十萬的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而存活下來的人之中,許多人因為曝露在輻射之下,後來即飽受後遺症折磨,經歷一段時間之後死亡。原子彈具有多大的破壞性,輻射對於這個世界、對於人體會留下多麼深的傷痛,我們已經從那些人的犧牲中學到了。
這次福島核能發電廠的事故,是我們日本人在歷史上經歷到的第二次重大核災。然而這次並不是被別人投擲炸彈,而是我們日本人自己親手準備,自己親手鑄下的大錯,自己污染了自己的國土,自己破壞了自己的生活。
村上春樹並且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接著他導出了以下的答案。
答案很簡單。答案就是「效率」,是「efficiency」。我們日本人對於核能,應該持續地呼喊「No!」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們應該要認真地面對村上春樹的訊息。能源是超過作家直覺的政策科學議題,我認為應該要將之積極地納入視野、認清事實,建立起當下應為正確恰當之判斷的日本能源策略。
打造公民參與型的復興構想
無論是新產業基礎的創生,抑或是首都機能的分散,或者是思考日本創生的計畫,採取公民參與型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復興的構想中,如果沒有讓公民有親身參與的興奮期待感,無法描繪出與創造未來有關的主體感動,創造新日本的運動就無法成立。「喔,對!反正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與我無關」─倘若復興的構想只讓公民冷眼旁觀而已,結果只會造就一項膚淺的構想。我認為創造新日本的運動裡,必須要有吸引有心參與者的計畫。舉例來說,1929年的大恐慌之後,美國推出及發展羅斯福新政作為國家計畫,其中即以經濟復興隊的形式,讓年輕人紛紛參與其中。我希望復興運動也能帶有那股熱忱。年輕世代的參與,比任何人都來得重要。舉例而言,像是在東北災區各縣,各組成以數百人為單位的「復興計畫推動隊」之類的組織,在全日本及亞洲公開招募人選,在一年到三年的期間裡,在策略性的目標計畫裡,每年提供二百至三百萬日圓的報酬請他們工作,這項構想如何呢?
像是投入農業生產法人的具體復興計畫,或者是副首都機能分散計畫等等,不是義務性質的志工活動,而是在「收取報酬、擔負責任地工作」的架構之下,讓年輕的能量參與,而且以培養未來能夠支援現場的人才體系來說,我認為有它的意義存在。
現今的日本因為長期處於就業冰河期,到處都是為就業所苦的年輕人。有些部分是因為不景氣,所以求才的人數減少,使得就業的機會受到限制;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些年輕人迷惘,有人想要把人生投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卻找不到想挑戰的工作。對於這些年輕人,應該要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在自己希望的地方工作,像是東北地方的農業生產法人也好,漁業與IT之間的同步也好,副首都的設計也行。我希望他們能擦擦額頭上的汗水,絞盡腦汁,四處奔走,與人接觸、討論、爭執,全力投入工作中。倘若復興計畫能夠塑造出這樣的機會,復興計畫就不會變得索然無味。從某個層面來說,或許這個過程正代表了日本創生。
以那須市作為副首都的構想為例,如果年輕人能前仆後繼地投入參與就好了。單只靠上了年紀的行政官員或專家閉門構思,往往容易被批評是「與災民無關、背離現實的討論」。建構出能讓人感受到,這是由眾人一起建構未來的復興與創生活動,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一環。
一直到這裡,我提到的都是年輕人的參與;其實還有另一項很重要的,那就是年長者的參與。這個年代的屆齡退休人士,不但一點兒也不顯得老態,而且和年輕世代相較之下,因為他們在職時代曾經經歷過經濟高度成長的年代,因此手頭上也寬裕很多。讓年長者參與的方案之一,便是讓他們以承銷人的角色,把錢花在復興債券上。據說個人金融資產有一千四百兆日圓,而其中的絕大部分就是由年長者持有。
復興財源方面的討論,內容不外乎增稅或者是發行國債。在財政困難的當頭,總是希望能避開這兩種選項,但是復興的財源一般認為至少超過二十兆日圓,這又該以何種形式籌措才好呢?這個部分需要發揮最大的智慧。即使是採取復興債券的方式,一想到關東大地震之後,因為國債擴大發行而引發了金融恐慌,總是讓人無法輕易地選擇它。因此我想提出的方案,便是盡可能減少後代子孫負擔的無利息國債。
或許有人會覺得─「有人會蠢到購買完全沒有利息的國債嗎?」但是我不這麼認為。舉例來說,提出激勵方案,只要購買復興債券即提供遺產稅減免,這個方法如何呢?對於多多少少希望能多留一點資產給兒孫的老年人來說,他們應該會非常關注吧。而且這筆資金是作為東日本復興、日本創生的事業資金所用。雖然他們不能揮汗參與計畫,但是卻依然能感覺到自己是計畫中的一分子。這並不像「全國一心」之類的說法,它和強制所有的人做同一件事的一體感不同,它沒有危險的氛圍,只有一種和聲般的一體感。「為了日本的創生和未來產業、未來技術,我希望能貢獻一己心力」─這份訊息應該也傳到了擔心日本未來的年長者心中。不需要發行戰爭債券的日本,可以說是幸福的國家。鄰近的韓國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曾經推動了「請把櫃子裡的錢奉獻出來」的國民運動。對日本的年長者提出呼籲,籌措大約十兆日圓的金額,作為投資未來的財源,僅提供遺產稅減免的優點,讓年長者承購無利息國債,我相信不是不可能的事。
本章前前後後所討論的事,主要是針對復興事業,以比較有彈性的想法,提出社會工程學式的方案。工程學是從宏觀的角度,組合個別的事業,以謀求解決問題的方案,我認為現今的日本,需要的正是Socialengineering,也就是社會工程學。我希望我們能具有社會工程學的解決方式,面對眼前存在的苦難,憑藉著有所根據的希望來面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