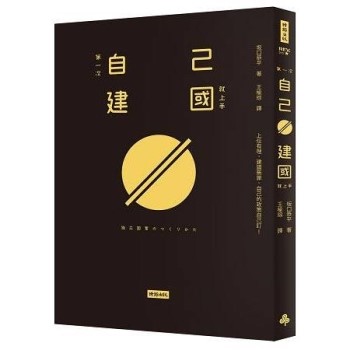第一章 生活中早已有無限的層面(節錄)
1街友的新層面生活
房子只能算是寢室
我在隅田川附近散步時,看到一些用藍色塑膠布搭成的房子。大約十二年前,二○○○年時,我還是早稻田建築系大四的學生。當時我不想找工作,也沒有打算成立設計公司,對自己的未來一片茫然,不過我每天都會到處觀察,就像是在尋找些什麼一樣。
當時在我眼中,那些人只不過是遊民而已,不過,我卻有些在意他們的生活情形。我在大學裡學習建築知識,打量他們的房子後,我疑惑:這也能算是建築物嗎?這些人的房子看起來很小,小到似乎一點發展性也沒有,我反而還覺得他們很需要別人的救濟。
但有一次,我卻發現一間很特別的房子。雖然看起來不過是由藍布搭成的房子,但屋頂上卻裝著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東西。仔細一看,才發現那是太陽能發電板。我對這個從來沒見過的高科技房屋感到很驚奇。
走進屋裡一看,還能發現裡頭有一張榻榻米,是一間小房子呢。而且裡頭使用的也全是電器產品喔!房子的規格,正面寬度剛好是九十公分,看得出是一間經過精心設計的房子。
事實上,我認為這間房子是所有我看過的建築物中,最貼近我的想法的房子。不但在都市中自然生息,而且以東京的自然素材為原料,不花費半毛錢(廢物回收利用),親手打造出剛好合住的房屋。這一點和為了勉強配合生活,只好花錢付房貸、房租的現代房子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大家都稱這種人是「無家可歸的遊民」,然而這又確實是他的家。
和他聊過以後,我更加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道地的「家」。同時,我覺得我自己還比較像是借宿在別人的房子裡的遊民。
不過,他家很小,狹窄到讓人覺得這不適合人類居住,裡頭的空間就只有一塊榻榻米長的四十公分大小。我問他,住在這麼狹窄的房子裡,不會覺得很麻煩嗎?結果他說:「這你就錯了。這個房子只能算是我的寢室而已。」
當時我聽了,只覺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所以他便開始為我解釋。
晴天時,他會在隔壁的隅田公園看書,或是參考撿來的國中音樂課本來彈吉他。此外,公園廁所和自來水也都隨便他使用,而且他一個禮拜會去附近的澡堂洗一次澡。想吃飯就去超市幫忙打掃,就能順便拿到人家給的肉和青菜。所以,對他來說,一個寢室大小的房子就夠用了。
聽完後,我感到茅塞頓開。後來,我在演說中一直提及的許多觀念,就是在這時開始萌芽的。
對他來說,公園就像是起居室、廁所、供水處;圖書館則是書房,超市就像冰箱,至於那個房子就是寢室了。
我把這種生活方式稱為「一個屋簷下的都市」。對他而言,他的居住空間不只有那個房屋,每天生活的整個都市空間都算是他的大房子。同樣的事物,只要改變觀點,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意義。而他使用的房屋、生活方式、看待都市的著眼點,其中都存在著無數的層面(Layer)。
他看待事物的層面和普通人所見的層面不同,不但沒有人發現到他的這種生活觀點,而且也沒人跟他搶著利用資源,同時沒有人會反對他的行為,而且他還能確實地實踐前所未有的空間使用概念。我發現這和最近常常提倡的「分享」有些不同,而他能將這種空間使用概念完全融入生活裡,這簡直就是「另類層面的生活空間」。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也曾表示,借用既有的他物來達成目的,即是「拼裝」的概念。我有預感,這種全新的房屋使用態度,能幫我找到重要的研究線索。
單純的觀點
我們怎麼會覺得人類要生活(不管是用水、用火、吃飯)就非得要有錢呢?而且我們不但不思考這樣是否合理,還像笨蛋一樣乖乖的花錢求生存。結果這種不良的生活方式,反而讓自己愈活愈不安心。
我在看到生活起居一切免費的生活方式時,心中思考著:「如果街坊鄰居們團結起來,讓回收利用的生活圈形成共識,不就能輕易地維持這種不用花錢的生活嗎?」同時我也很好奇,這樣做有這麼困難嗎?
為了維持有錢可花的生活,更加努力地保住工作,在佐佐木先生的眼中,這種勉強自己工作的人才是「笨蛋」,因為這種人「沒有動腦思考」。
通常有人發表這類意見時,就會被批評:「你這種沒在工作的人,才不了解上班不能亂請假」、「辭掉工作只會讓生活變得更難過」,或是「不然你覺得怎麼做才能讓社會進步?那我們的經濟發展又要如何?」,又或是「那種露宿生活能夠成立,還不是因為多數人正常生活,使社會得以正常運作的關係」等等。
但等到這些正常工作的人終於覺醒時,奴隸制度幾乎成了社會運作的普遍現象,人們仍舊不敢罷工。話雖如此,大家依然不覺得這種表面正常、實則奇怪的生活充滿了弔詭的邏輯,所以也不會想到其他層面的生活方式。這就是目前大眾對生活感到麻木的現狀。
我認為社會陷入了一種狀況,就像是每個人都還清貸款後,會造成銀行倒閉一樣,我把這種現象稱為「負債思維」。指的是工作的動機是為了解決負債的這種思考模式。
那種古怪的邏輯,就像是你去申請三十五年的長期貸款,然後就以為自己會在負債壓力下專心工作。你工作的企業和銀行,在賺錢的當下,不但能順利營運,而且你還會歡呼:「萬歲!咱們的經濟得到發展囉。」但當我表達這樣的看法時,總會有人告訴我事情不像我講的這麼單純。但我再反問,那麼其中又有什麼複雜的體制運作時,卻從來沒有人可以給我一個解釋。我看,其實大家也不知道自己所認為的複雜到底有多複雜。
我倒認為,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就該好好想清楚再提出答案,這是很簡單的道理。與其老是把事情想得太複雜,不如先學會讓自己習慣用單純的觀點看待事物,否則我們將難以應付各種複雜的社會現象。
思考產生新空間
在我發現和一般人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的街友生活圈後,經過實地考察,我把這個發現稱之為「層面」。
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人類一直都試著在這唯一的地球上開疆闢土,而這也是造成各種戰爭、對立的原因。日本這個國家的人們習慣透過獲得金錢,來增加自己名下的土地。各種增加自己所有物的行為,就成了活絡社會經濟和生活的基礎。然而,街友們的觀點卻完全不同。
我身處的建築界也是如此。大家都在自己擁有的土地上建造一棟又一棟的建築物,以為用牆壁圍起來才是拓增生活空間的方法。但事實上,真是如此嗎?當然,我個人是持相反的意見。因為不管在自己的領土上建造多少個牆壁互相堆疊的建築,空間事實上還是不會增加,我反倒認為那是在減少生活空間。
而街友們對空間的看法就不是如此了。由於他們大多無法以金錢買地,因此不得不放棄擁有土地的可能。不過,為此他們自己製造出了新層面空間的概念。有別於日本大眾習以為常的「封閉化」社會,他們可以製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層面。
當然,街友們不是魔術師,無法真的憑空變出空間,但他們可以善用思考。建築物無法爭取到空間,但透過思考就能營造出絕佳的生活空間。
新層面思維能將創意轉換為空間,告訴我這點的就是鈴木先生房屋的玄關。他只要把門關上,將藍色帆布闔上,將熱水加入容器中,就能變成用來泡澡的塑膠浴缸。如果把門打開,在門的內側掛上菜刀,就會生出做菜用的流理台。隨著站立之處的不同,原本只是作為玄關的空間就能變化出各種用途。
換句話說,隨著使用動機的不同,可以切換到各種不同的層面,讓生活空間因此變多。這和「如何用牆壁圍住一個空間」的概念完全相反,因為這根本不需要使用到牆壁,更何況人類本身就有不斷創造出肉眼看不見的使用空間的能力。
我所說的這種層面,並不是什麼嶄新的技術,而是人類自古以來就擁有的能力。
2為房屋裝上車輪──移動式住家
移動式住家
我對現存會自動向居住者徵收房租的居住環境,以及總會和基礎建設產生連結的社會體制進行了思考,然後開始想找一個異於這種環境的「場所」,來重啟大眾對於「家」的看法。到目前為止,我的工作只是調查街友的生態,不過這次我要向前跨出一步了,為的就是讓社會的視野變得更廣大。
「為何人類要生存就一定要付房租?」這是我對居住所提出的質疑。然而,大家聽了這個問題,都覺得花錢生存是毋庸置疑的事。每個人都認為付房租、用錢買房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明明就有許多街友在河邊,不用花錢買地就能蓋出免費的房屋。這根本就是明擺著的事實,但我們依然對於花錢付房租的生活模式深信不疑,這個現象其實最值得質疑。
我不反對付錢取得居住環境,但目前的居住體制已經威脅到我們的生存權。換句話說,我覺得這種制度已經違法了。讓所有人都有地方住,不正是我們的國家該負的責任嗎?
即使如此,現在才來抱怨也無濟於事。想要生存,我們只能以具體的行動來解決問題。
因此,我們首先就要改變原本那種自動繳納房租的觀念,並且試著效法鈴木先生。鈴木先生的家沒有牢牢固定在土地上,因此在法律上不能算是「住家」,但在感情上,鈴木先生當然把它當成「家」。而我打算就此觀點做個延伸,進而建造出新型態的房屋。
鈴木先生的家是一間「不是房屋的房屋」。簡單地說,那是間沒有固定在土地上,會移動的房屋。只要看一下日本的《建築基準法》,就會發現鈴木先生的家不能算是「房屋」,所以除了沒有執照也能蓋的優點外,也不需要繳稅,是一棟不被法律框架束縛的自由房屋。
因此,我為自己的房子裝了四個手拉車車輪。光是這樣做,就可以讓移動式住家在法律上不被視為建築物,而是被視為車子。而且施工費只要三萬日圓,還不必繳固定資產稅。這個房屋有三疊榻榻米(約一點五坪)大,可以用太陽能發電板幫iPad和iPhone充電。這麼一來,靠私人用電源使用電器的住宅就簡單地建造好了。
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放置移動式住家的「場所」。在前文中,我們從鈴木先生的故事裡了解到,日本所有土地都已經被分類了。在日本,想建造住宅,就要把房屋蓋在住宅用地上,因此得想辦法用大量的錢取得建地。而我要做的,就是將可建造房屋的場所擴大解讀。
移動式住家在法律上是「車子」,所以不管是農地也好、停車場也罷,只要是能停車的地方,就可以安放移動式住家。尤其東京又有很多停車場,所以接著我要找的是一個願意讓我放房屋的地主。我在問到第三個地主後,對方終於爽快地允諾了。「我只是在停車場放一個很像房屋的『車子』而已,根本沒有違法。」只要地主能認同這點就沒問題了。
不過,他還是問了我一個問題:「你不會住在裡面吧?」
我立刻回答:「對啊,我不會住進去」。
我其實是打算要住進去的,只是不這麼說可能就租不到車位了。但說謊畢竟是不好的行為,心裡多少會有罪惡感。
但是,我又想到,「居住」的定義又是什麼?
我想從法律觀點來解答這個問題,但結果我又發現了讓我吃驚的事。
我們的國家竟然沒有法律規定什麼才算是「居住」。
在裡面接自來水就算嗎?在裡面睡覺就算嗎?在裡面吃飯就算嗎?
事實上,我們根本就沒有規定怎樣才算「居住」。在法律上,擁有「房屋」就要繳稅給國家,然而法律中又沒有任何關於「居住」的規定。簡單地說,國民在居住這方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發揮。
由此可見,日本這個國家或許比印象中的還要棒。因為這是一個擁有居住自由的國家,所以我愛怎麼住就可以怎麼住。
第二章 私人與公共之間(節錄)
2 逐漸醞釀出的公共空間
神奇的庭院
我曾在《ecocolo》雜誌上寫專欄,其中有關於東京庭院的調查。
雖說主題是東京的庭院,不過畢竟東京土地太小,真正家中有庭院的人其實不多。不過,也是有一些人會花費心思打造出理想中的庭院,這些庭院就是我在專欄上的訪問對象,而且我也將之命名為「4D GARDEN」。
而在這之中,有一個特別吸引我的庭院。
請看左邊的照片。這是一個家住中野區,沒有足夠的空間能作為庭院的人所打造出的庭院景觀。原本我以為那只是花圃,不過仔細看卻會發現汽車的引擎蓋。
我想要停車場,也想要有庭院,而這個庭院景觀就是這個想法下的成果了。
那麼,車子又要怎麼辦?那整個就成了花圃了說……。而且車子外觀又很乾淨,看起來平時也有保養。於是,我問了一下這個庭院的主人,但他卻說:「明天早上你再過來看看吧。」我聽從他的話,隔天早上再過來。
結果就看到了這個景象。
庭院主人告訴我,每天早上他都會小心地把盆栽拿下來,然後開車送兒子到距離他們家五百公尺的中野車站。其實他根本不需要特地開車出去,但他表示,車子要常常用,不然很容易壞掉。而且他每次送兒子到車站後,回家又要把盆栽放回車上。這雖然是很費工夫的事,但他卻會微笑著進行這個工作。尤其是整個布置不花他半毛錢,這點最厲害。換句話說,那些盆栽都不是用買的。
問他如何收集到這些植物,才知道原來這些都是從路邊摘來的。他在路邊看到喜歡的植物,就會馬上摘下來,放在小盆栽裡種著,然後一直讓它們不斷生長。他的庭院就是透過這樣的作業逐步地完成。
我又問他,那些小盆栽現在放在哪兒呢?他一邊說「就在那啊」,一邊指向對面的公寓。我馬上看到公寓牆角放了一整排盆栽,看起來就跟花店沒兩樣。而且它們就像棒球的二軍球員,等長大後就能擺到車上的那個大聯盟裡了。
我對他說:「你除了有一棟房屋,還有一棟公寓嗎?你真行啊。」
他回答:「其實那棟公寓不是我的喔。」
聽了他的解釋才知道,原來那棟公寓的房東看到他的庭園造景技術,覺得很棒,所以跟他說好:「公寓這邊可以隨你布置,這樣還能讓你稍微有地方管理這附近的空間。」我看他根本就是園藝界的傑出人才了。
自己動手做公立公園
看著這個庭院,我思考了許多關於「私人擁有」的觀念。那位庭院的主人原本只是想布置自己的庭院,結果他的領域居然還延伸到對面的公寓。如果他放的是廚餘或一些怪東西,那大概也輪不到他幫人家管理公寓景觀。植物繁衍的力量可以豐富人的內心,甚至還能超越土地擁有的觀念,讓人與人之間更加親近。
如果再仔細看這些盆栽,還會發現每一個都有標上植物名的牌子。由於他的盆栽實在太多,所以我沒辦法把所有植物的種類記下來。我心裡很好奇,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因此我問了庭院主人。他回道:「因為很多路人停在這邊觀賞,他們都一定會問我植物的名字。」原來名牌是特地標給路人看的。
他接著又說:「這附近雖然有公立的公園,不過地面上有很多小石子,樹木也只有幾棵而已,待在那裡實在無法讓人感到自在。我覺得公園最好能像我家一樣,綠意盎然,這樣大家也會比較高興。」
聽了他這麼說,害我差點哭出來。本來我以為這裡只是他個人的庭院,但他其實是當作公立公園在管理,而且這個公立公園還是他親手創立的。他不是用「因為擁有所以快樂」的觀念在布置庭院,而是明顯把自己的土地當作公共空間,而且那還是園藝師親手打造出的公共空間。
我把因為這種方法而生的公共空間,取名為「Private Public(私人型公共)」。
將「自身」作為起點
對於現今的公共設施,我一直有許多疑慮。尤其常在我們一不留神時,就莫名地多出很多公共設施,不管是新圖書館、劇場、還是鎮民集會中心等等,都是這樣。當然,我不是要否定這些設施的功能,但原本還有很多舊的公共設施可用,就算沒有新的也不會讓人感到不便。
還有,雖然那些設施的建體都很大,但卻不允許大家在裡面躺著休息。這些設施既然有這種使用規定,那還不如有廣大草皮的公園會更好。此外,那些設施還規定晚上不得入內、不得在裡面吃便當等等,不禁讓人覺得那根本不是為了市民而建的。
以露宿生活為範本
雖然我說這是新政府,但我不打算一肩扛下該政府的所有行政工作。我主要是想讓我的政府死守國民的生存權,雖然這句話半帶著開玩笑的意味,但目前的政府真的沒人做這個工作。
我這個新政府的施政方向很單純,那就是「盡全力讓自殺人數降到零」。
在我的新政府中,生活得痛苦到想死就算是違憲行為,也因此我才想趕快動起來,因為那些會成為街友的人就已經違憲了。
所以我想重新詮釋「街友」的意義,以及零圓房屋的生活型態。他們實現了不花錢就能生存的世界,用自己的技術將所有垃圾化為「貨幣」。我認為這已經算是全新的經濟型態。
但讓我困擾的就是,大家都會說:「我才不想過那種乞丐生活」、「我不要像那樣弄個巢穴住進去」、「我才不想撿廚餘吃」。所以我還是要再三聲明,我沒要求大家一定要過那樣的生活。我是希望大家能在都市裡,運用自己的創意,從零開始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生活層面。想要有理想的生活,就要靠自己來。
初次外交並開始組閣
庇護所成立一段時間後,熊本縣長的直屬幕僚小野泰輔先生來到Zero Center找我。這除了是新政府的首次外交活動之外,他也對移動式住家表示興趣。於是我告訴他,我這麼做就是想要改變大家居住和勞動的觀念。因此,我開始展開了和熊本縣政府的外交活動。
《蒙特婁公約》中有一個「何為國家?」的條目,而我看了其中的內容後,也想效法該條目中對於國家的定義。
該條目認為國家必要的條件為:
一、人民
二、政府
三、領土
四、外交能力
一、二項我已經擁有了,第三項如前文所述,就是銀座的那個無主土地。至於第四項,則是和熊本縣進行外交。
由於我是新政府的內閣行政院長,因此也必須組閣。
我先打了電話給人文、宗教學者中澤新一先生。我在二○一○年時認識他,當時我們兩人很合得來。
而且他還告訴過我:「你就繼續保持小孩子般的心態,向大眾提出單純的質疑吧」。
也因為這件往事,所以我自顧自地跟中澤先生說,我要任命他為教育部長,而他也很爽快的答應了我的要求。
後來,我還邀請告訴我輻射恐怖之處的鐮仲仁美導演,請她擔任勞動部長。還有建築師藤村龍至先生擔任交通部長,行政院長則是長期和我在網路上合作節目的音樂人磯部涼先生。此外還有其他朋友,都成了我的內閣成員。
此外,要是有人可以緩和現場氣氛,我會叫他「緩和氣氛部長」;很會按摩的就叫「按摩部長」;能輕易要到他人電話號碼的,就叫「電話部長」。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能,而將自己的能力發揚光大,就是他們的使命。
換句話說,你只要成為新政府的國民,就有機會成為某某部長。而且,我除了擔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長之外,也能擔任你的新政府中的某某部長。我這個人不是為了想統治國家而成立新政府的,我只是想效法那位在自家門前、靠自己布置出公園的園藝師,想要以身體力行作為起點,號召大家一同打造新政府罷了。
我甚至想過,要在報紙上刊登全版廣告,告訴所有人我開創了新政府。二○一二年四月的現在,我的推特有一萬兩千名網友關注,由於全版廣告要價數百萬到一千萬日圓,所以網友們一人捐一千日圓就能輕易幫我完成這個夢想。
「你想當什麼部長呢?我們的新政府急需你的才能,請立刻撥打以下電話,和新政府內閣行政院長坂口恭平討論吧!Tel. 090-8106-4666」
1街友的新層面生活
房子只能算是寢室
我在隅田川附近散步時,看到一些用藍色塑膠布搭成的房子。大約十二年前,二○○○年時,我還是早稻田建築系大四的學生。當時我不想找工作,也沒有打算成立設計公司,對自己的未來一片茫然,不過我每天都會到處觀察,就像是在尋找些什麼一樣。
當時在我眼中,那些人只不過是遊民而已,不過,我卻有些在意他們的生活情形。我在大學裡學習建築知識,打量他們的房子後,我疑惑:這也能算是建築物嗎?這些人的房子看起來很小,小到似乎一點發展性也沒有,我反而還覺得他們很需要別人的救濟。
但有一次,我卻發現一間很特別的房子。雖然看起來不過是由藍布搭成的房子,但屋頂上卻裝著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東西。仔細一看,才發現那是太陽能發電板。我對這個從來沒見過的高科技房屋感到很驚奇。
走進屋裡一看,還能發現裡頭有一張榻榻米,是一間小房子呢。而且裡頭使用的也全是電器產品喔!房子的規格,正面寬度剛好是九十公分,看得出是一間經過精心設計的房子。
事實上,我認為這間房子是所有我看過的建築物中,最貼近我的想法的房子。不但在都市中自然生息,而且以東京的自然素材為原料,不花費半毛錢(廢物回收利用),親手打造出剛好合住的房屋。這一點和為了勉強配合生活,只好花錢付房貸、房租的現代房子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大家都稱這種人是「無家可歸的遊民」,然而這又確實是他的家。
和他聊過以後,我更加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道地的「家」。同時,我覺得我自己還比較像是借宿在別人的房子裡的遊民。
不過,他家很小,狹窄到讓人覺得這不適合人類居住,裡頭的空間就只有一塊榻榻米長的四十公分大小。我問他,住在這麼狹窄的房子裡,不會覺得很麻煩嗎?結果他說:「這你就錯了。這個房子只能算是我的寢室而已。」
當時我聽了,只覺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所以他便開始為我解釋。
晴天時,他會在隔壁的隅田公園看書,或是參考撿來的國中音樂課本來彈吉他。此外,公園廁所和自來水也都隨便他使用,而且他一個禮拜會去附近的澡堂洗一次澡。想吃飯就去超市幫忙打掃,就能順便拿到人家給的肉和青菜。所以,對他來說,一個寢室大小的房子就夠用了。
聽完後,我感到茅塞頓開。後來,我在演說中一直提及的許多觀念,就是在這時開始萌芽的。
對他來說,公園就像是起居室、廁所、供水處;圖書館則是書房,超市就像冰箱,至於那個房子就是寢室了。
我把這種生活方式稱為「一個屋簷下的都市」。對他而言,他的居住空間不只有那個房屋,每天生活的整個都市空間都算是他的大房子。同樣的事物,只要改變觀點,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意義。而他使用的房屋、生活方式、看待都市的著眼點,其中都存在著無數的層面(Layer)。
他看待事物的層面和普通人所見的層面不同,不但沒有人發現到他的這種生活觀點,而且也沒人跟他搶著利用資源,同時沒有人會反對他的行為,而且他還能確實地實踐前所未有的空間使用概念。我發現這和最近常常提倡的「分享」有些不同,而他能將這種空間使用概念完全融入生活裡,這簡直就是「另類層面的生活空間」。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也曾表示,借用既有的他物來達成目的,即是「拼裝」的概念。我有預感,這種全新的房屋使用態度,能幫我找到重要的研究線索。
單純的觀點
我們怎麼會覺得人類要生活(不管是用水、用火、吃飯)就非得要有錢呢?而且我們不但不思考這樣是否合理,還像笨蛋一樣乖乖的花錢求生存。結果這種不良的生活方式,反而讓自己愈活愈不安心。
我在看到生活起居一切免費的生活方式時,心中思考著:「如果街坊鄰居們團結起來,讓回收利用的生活圈形成共識,不就能輕易地維持這種不用花錢的生活嗎?」同時我也很好奇,這樣做有這麼困難嗎?
為了維持有錢可花的生活,更加努力地保住工作,在佐佐木先生的眼中,這種勉強自己工作的人才是「笨蛋」,因為這種人「沒有動腦思考」。
通常有人發表這類意見時,就會被批評:「你這種沒在工作的人,才不了解上班不能亂請假」、「辭掉工作只會讓生活變得更難過」,或是「不然你覺得怎麼做才能讓社會進步?那我們的經濟發展又要如何?」,又或是「那種露宿生活能夠成立,還不是因為多數人正常生活,使社會得以正常運作的關係」等等。
但等到這些正常工作的人終於覺醒時,奴隸制度幾乎成了社會運作的普遍現象,人們仍舊不敢罷工。話雖如此,大家依然不覺得這種表面正常、實則奇怪的生活充滿了弔詭的邏輯,所以也不會想到其他層面的生活方式。這就是目前大眾對生活感到麻木的現狀。
我認為社會陷入了一種狀況,就像是每個人都還清貸款後,會造成銀行倒閉一樣,我把這種現象稱為「負債思維」。指的是工作的動機是為了解決負債的這種思考模式。
那種古怪的邏輯,就像是你去申請三十五年的長期貸款,然後就以為自己會在負債壓力下專心工作。你工作的企業和銀行,在賺錢的當下,不但能順利營運,而且你還會歡呼:「萬歲!咱們的經濟得到發展囉。」但當我表達這樣的看法時,總會有人告訴我事情不像我講的這麼單純。但我再反問,那麼其中又有什麼複雜的體制運作時,卻從來沒有人可以給我一個解釋。我看,其實大家也不知道自己所認為的複雜到底有多複雜。
我倒認為,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就該好好想清楚再提出答案,這是很簡單的道理。與其老是把事情想得太複雜,不如先學會讓自己習慣用單純的觀點看待事物,否則我們將難以應付各種複雜的社會現象。
思考產生新空間
在我發現和一般人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的街友生活圈後,經過實地考察,我把這個發現稱之為「層面」。
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人類一直都試著在這唯一的地球上開疆闢土,而這也是造成各種戰爭、對立的原因。日本這個國家的人們習慣透過獲得金錢,來增加自己名下的土地。各種增加自己所有物的行為,就成了活絡社會經濟和生活的基礎。然而,街友們的觀點卻完全不同。
我身處的建築界也是如此。大家都在自己擁有的土地上建造一棟又一棟的建築物,以為用牆壁圍起來才是拓增生活空間的方法。但事實上,真是如此嗎?當然,我個人是持相反的意見。因為不管在自己的領土上建造多少個牆壁互相堆疊的建築,空間事實上還是不會增加,我反倒認為那是在減少生活空間。
而街友們對空間的看法就不是如此了。由於他們大多無法以金錢買地,因此不得不放棄擁有土地的可能。不過,為此他們自己製造出了新層面空間的概念。有別於日本大眾習以為常的「封閉化」社會,他們可以製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層面。
當然,街友們不是魔術師,無法真的憑空變出空間,但他們可以善用思考。建築物無法爭取到空間,但透過思考就能營造出絕佳的生活空間。
新層面思維能將創意轉換為空間,告訴我這點的就是鈴木先生房屋的玄關。他只要把門關上,將藍色帆布闔上,將熱水加入容器中,就能變成用來泡澡的塑膠浴缸。如果把門打開,在門的內側掛上菜刀,就會生出做菜用的流理台。隨著站立之處的不同,原本只是作為玄關的空間就能變化出各種用途。
換句話說,隨著使用動機的不同,可以切換到各種不同的層面,讓生活空間因此變多。這和「如何用牆壁圍住一個空間」的概念完全相反,因為這根本不需要使用到牆壁,更何況人類本身就有不斷創造出肉眼看不見的使用空間的能力。
我所說的這種層面,並不是什麼嶄新的技術,而是人類自古以來就擁有的能力。
2為房屋裝上車輪──移動式住家
移動式住家
我對現存會自動向居住者徵收房租的居住環境,以及總會和基礎建設產生連結的社會體制進行了思考,然後開始想找一個異於這種環境的「場所」,來重啟大眾對於「家」的看法。到目前為止,我的工作只是調查街友的生態,不過這次我要向前跨出一步了,為的就是讓社會的視野變得更廣大。
「為何人類要生存就一定要付房租?」這是我對居住所提出的質疑。然而,大家聽了這個問題,都覺得花錢生存是毋庸置疑的事。每個人都認為付房租、用錢買房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明明就有許多街友在河邊,不用花錢買地就能蓋出免費的房屋。這根本就是明擺著的事實,但我們依然對於花錢付房租的生活模式深信不疑,這個現象其實最值得質疑。
我不反對付錢取得居住環境,但目前的居住體制已經威脅到我們的生存權。換句話說,我覺得這種制度已經違法了。讓所有人都有地方住,不正是我們的國家該負的責任嗎?
即使如此,現在才來抱怨也無濟於事。想要生存,我們只能以具體的行動來解決問題。
因此,我們首先就要改變原本那種自動繳納房租的觀念,並且試著效法鈴木先生。鈴木先生的家沒有牢牢固定在土地上,因此在法律上不能算是「住家」,但在感情上,鈴木先生當然把它當成「家」。而我打算就此觀點做個延伸,進而建造出新型態的房屋。
鈴木先生的家是一間「不是房屋的房屋」。簡單地說,那是間沒有固定在土地上,會移動的房屋。只要看一下日本的《建築基準法》,就會發現鈴木先生的家不能算是「房屋」,所以除了沒有執照也能蓋的優點外,也不需要繳稅,是一棟不被法律框架束縛的自由房屋。
因此,我為自己的房子裝了四個手拉車車輪。光是這樣做,就可以讓移動式住家在法律上不被視為建築物,而是被視為車子。而且施工費只要三萬日圓,還不必繳固定資產稅。這個房屋有三疊榻榻米(約一點五坪)大,可以用太陽能發電板幫iPad和iPhone充電。這麼一來,靠私人用電源使用電器的住宅就簡單地建造好了。
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放置移動式住家的「場所」。在前文中,我們從鈴木先生的故事裡了解到,日本所有土地都已經被分類了。在日本,想建造住宅,就要把房屋蓋在住宅用地上,因此得想辦法用大量的錢取得建地。而我要做的,就是將可建造房屋的場所擴大解讀。
移動式住家在法律上是「車子」,所以不管是農地也好、停車場也罷,只要是能停車的地方,就可以安放移動式住家。尤其東京又有很多停車場,所以接著我要找的是一個願意讓我放房屋的地主。我在問到第三個地主後,對方終於爽快地允諾了。「我只是在停車場放一個很像房屋的『車子』而已,根本沒有違法。」只要地主能認同這點就沒問題了。
不過,他還是問了我一個問題:「你不會住在裡面吧?」
我立刻回答:「對啊,我不會住進去」。
我其實是打算要住進去的,只是不這麼說可能就租不到車位了。但說謊畢竟是不好的行為,心裡多少會有罪惡感。
但是,我又想到,「居住」的定義又是什麼?
我想從法律觀點來解答這個問題,但結果我又發現了讓我吃驚的事。
我們的國家竟然沒有法律規定什麼才算是「居住」。
在裡面接自來水就算嗎?在裡面睡覺就算嗎?在裡面吃飯就算嗎?
事實上,我們根本就沒有規定怎樣才算「居住」。在法律上,擁有「房屋」就要繳稅給國家,然而法律中又沒有任何關於「居住」的規定。簡單地說,國民在居住這方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發揮。
由此可見,日本這個國家或許比印象中的還要棒。因為這是一個擁有居住自由的國家,所以我愛怎麼住就可以怎麼住。
第二章 私人與公共之間(節錄)
2 逐漸醞釀出的公共空間
神奇的庭院
我曾在《ecocolo》雜誌上寫專欄,其中有關於東京庭院的調查。
雖說主題是東京的庭院,不過畢竟東京土地太小,真正家中有庭院的人其實不多。不過,也是有一些人會花費心思打造出理想中的庭院,這些庭院就是我在專欄上的訪問對象,而且我也將之命名為「4D GARDEN」。
而在這之中,有一個特別吸引我的庭院。
請看左邊的照片。這是一個家住中野區,沒有足夠的空間能作為庭院的人所打造出的庭院景觀。原本我以為那只是花圃,不過仔細看卻會發現汽車的引擎蓋。
我想要停車場,也想要有庭院,而這個庭院景觀就是這個想法下的成果了。
那麼,車子又要怎麼辦?那整個就成了花圃了說……。而且車子外觀又很乾淨,看起來平時也有保養。於是,我問了一下這個庭院的主人,但他卻說:「明天早上你再過來看看吧。」我聽從他的話,隔天早上再過來。
結果就看到了這個景象。
庭院主人告訴我,每天早上他都會小心地把盆栽拿下來,然後開車送兒子到距離他們家五百公尺的中野車站。其實他根本不需要特地開車出去,但他表示,車子要常常用,不然很容易壞掉。而且他每次送兒子到車站後,回家又要把盆栽放回車上。這雖然是很費工夫的事,但他卻會微笑著進行這個工作。尤其是整個布置不花他半毛錢,這點最厲害。換句話說,那些盆栽都不是用買的。
問他如何收集到這些植物,才知道原來這些都是從路邊摘來的。他在路邊看到喜歡的植物,就會馬上摘下來,放在小盆栽裡種著,然後一直讓它們不斷生長。他的庭院就是透過這樣的作業逐步地完成。
我又問他,那些小盆栽現在放在哪兒呢?他一邊說「就在那啊」,一邊指向對面的公寓。我馬上看到公寓牆角放了一整排盆栽,看起來就跟花店沒兩樣。而且它們就像棒球的二軍球員,等長大後就能擺到車上的那個大聯盟裡了。
我對他說:「你除了有一棟房屋,還有一棟公寓嗎?你真行啊。」
他回答:「其實那棟公寓不是我的喔。」
聽了他的解釋才知道,原來那棟公寓的房東看到他的庭園造景技術,覺得很棒,所以跟他說好:「公寓這邊可以隨你布置,這樣還能讓你稍微有地方管理這附近的空間。」我看他根本就是園藝界的傑出人才了。
自己動手做公立公園
看著這個庭院,我思考了許多關於「私人擁有」的觀念。那位庭院的主人原本只是想布置自己的庭院,結果他的領域居然還延伸到對面的公寓。如果他放的是廚餘或一些怪東西,那大概也輪不到他幫人家管理公寓景觀。植物繁衍的力量可以豐富人的內心,甚至還能超越土地擁有的觀念,讓人與人之間更加親近。
如果再仔細看這些盆栽,還會發現每一個都有標上植物名的牌子。由於他的盆栽實在太多,所以我沒辦法把所有植物的種類記下來。我心裡很好奇,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因此我問了庭院主人。他回道:「因為很多路人停在這邊觀賞,他們都一定會問我植物的名字。」原來名牌是特地標給路人看的。
他接著又說:「這附近雖然有公立的公園,不過地面上有很多小石子,樹木也只有幾棵而已,待在那裡實在無法讓人感到自在。我覺得公園最好能像我家一樣,綠意盎然,這樣大家也會比較高興。」
聽了他這麼說,害我差點哭出來。本來我以為這裡只是他個人的庭院,但他其實是當作公立公園在管理,而且這個公立公園還是他親手創立的。他不是用「因為擁有所以快樂」的觀念在布置庭院,而是明顯把自己的土地當作公共空間,而且那還是園藝師親手打造出的公共空間。
我把因為這種方法而生的公共空間,取名為「Private Public(私人型公共)」。
將「自身」作為起點
對於現今的公共設施,我一直有許多疑慮。尤其常在我們一不留神時,就莫名地多出很多公共設施,不管是新圖書館、劇場、還是鎮民集會中心等等,都是這樣。當然,我不是要否定這些設施的功能,但原本還有很多舊的公共設施可用,就算沒有新的也不會讓人感到不便。
還有,雖然那些設施的建體都很大,但卻不允許大家在裡面躺著休息。這些設施既然有這種使用規定,那還不如有廣大草皮的公園會更好。此外,那些設施還規定晚上不得入內、不得在裡面吃便當等等,不禁讓人覺得那根本不是為了市民而建的。
以露宿生活為範本
雖然我說這是新政府,但我不打算一肩扛下該政府的所有行政工作。我主要是想讓我的政府死守國民的生存權,雖然這句話半帶著開玩笑的意味,但目前的政府真的沒人做這個工作。
我這個新政府的施政方向很單純,那就是「盡全力讓自殺人數降到零」。
在我的新政府中,生活得痛苦到想死就算是違憲行為,也因此我才想趕快動起來,因為那些會成為街友的人就已經違憲了。
所以我想重新詮釋「街友」的意義,以及零圓房屋的生活型態。他們實現了不花錢就能生存的世界,用自己的技術將所有垃圾化為「貨幣」。我認為這已經算是全新的經濟型態。
但讓我困擾的就是,大家都會說:「我才不想過那種乞丐生活」、「我不要像那樣弄個巢穴住進去」、「我才不想撿廚餘吃」。所以我還是要再三聲明,我沒要求大家一定要過那樣的生活。我是希望大家能在都市裡,運用自己的創意,從零開始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生活層面。想要有理想的生活,就要靠自己來。
初次外交並開始組閣
庇護所成立一段時間後,熊本縣長的直屬幕僚小野泰輔先生來到Zero Center找我。這除了是新政府的首次外交活動之外,他也對移動式住家表示興趣。於是我告訴他,我這麼做就是想要改變大家居住和勞動的觀念。因此,我開始展開了和熊本縣政府的外交活動。
《蒙特婁公約》中有一個「何為國家?」的條目,而我看了其中的內容後,也想效法該條目中對於國家的定義。
該條目認為國家必要的條件為:
一、人民
二、政府
三、領土
四、外交能力
一、二項我已經擁有了,第三項如前文所述,就是銀座的那個無主土地。至於第四項,則是和熊本縣進行外交。
由於我是新政府的內閣行政院長,因此也必須組閣。
我先打了電話給人文、宗教學者中澤新一先生。我在二○一○年時認識他,當時我們兩人很合得來。
而且他還告訴過我:「你就繼續保持小孩子般的心態,向大眾提出單純的質疑吧」。
也因為這件往事,所以我自顧自地跟中澤先生說,我要任命他為教育部長,而他也很爽快的答應了我的要求。
後來,我還邀請告訴我輻射恐怖之處的鐮仲仁美導演,請她擔任勞動部長。還有建築師藤村龍至先生擔任交通部長,行政院長則是長期和我在網路上合作節目的音樂人磯部涼先生。此外還有其他朋友,都成了我的內閣成員。
此外,要是有人可以緩和現場氣氛,我會叫他「緩和氣氛部長」;很會按摩的就叫「按摩部長」;能輕易要到他人電話號碼的,就叫「電話部長」。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能,而將自己的能力發揚光大,就是他們的使命。
換句話說,你只要成為新政府的國民,就有機會成為某某部長。而且,我除了擔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長之外,也能擔任你的新政府中的某某部長。我這個人不是為了想統治國家而成立新政府的,我只是想效法那位在自家門前、靠自己布置出公園的園藝師,想要以身體力行作為起點,號召大家一同打造新政府罷了。
我甚至想過,要在報紙上刊登全版廣告,告訴所有人我開創了新政府。二○一二年四月的現在,我的推特有一萬兩千名網友關注,由於全版廣告要價數百萬到一千萬日圓,所以網友們一人捐一千日圓就能輕易幫我完成這個夢想。
「你想當什麼部長呢?我們的新政府急需你的才能,請立刻撥打以下電話,和新政府內閣行政院長坂口恭平討論吧!Tel. 090-8106-4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