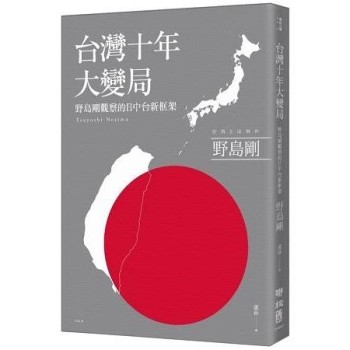序章 轉換期的台灣
靈活多變的台灣政治
每次想要重讀過去自己所寫有關台灣的文章時,多少需要一點勇氣,有時還會感覺有點鬱卒。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以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身分,獲得壓倒性勝利當選的那一晚,這樣的思緒就層層包圍著我。
儘管這一夜的台北仍然籠罩在寒冬裡,但街頭卻充滿著熾熱的氛圍。的確,雖然大家在事前都已認定民進黨必定會重新奪回執政權,但有點超乎想像的是,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竟然以三百萬票的差距擊敗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而且在立委選舉方面,民進黨也輕鬆獲得單獨過半席次,可說是壓倒性的勝利。這讓我不禁想起八年前,國民黨擊敗民進黨,重回執政地位的那個夜晚。那晚的台北也是一樣熾熱。當時我清楚地有種感覺,那就是國民黨新的「一黨獨大時代」已然到來。相較之下,醜聞纏身外加施政失當,遭受強烈批判的民進黨,則是顯得完全乏善可陳。不只如此,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其光芒四射的程度,簡直就像今天的蔡英文。2016年的台灣選舉,彷彿和2008年是同樣的一齣劇本,只是演出的主角換了一個人。國民黨從頭到尾都陷在無止盡的內部鬥爭中,完全沒有打出整體作戰的感覺,敗北自是理所當然。至於民進黨則是極力呼喚中間選民,他們一方面成功吸引了追求「安定與自立」這個漂亮品牌的人們,另一方面則確切鞏固了既有的、擁有強烈「台灣意識」的支持層,從而第二度贏得執政權。只不過是八年前,那時的國民黨團結一致,民進黨卻分崩離析。勝負,或許往往就是這麼一回事。
每八年就能目睹一次如此鮮活演出的台灣政治「逆轉劇」,對專家而言可說是件非常幸運的事。不過,在此同時回想起自己八年前寫的東西,不免感到有些尷尬—「民進黨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大概都無法恢復元氣了」,選舉之後,台灣人不斷這麼議論著,也出現了許多抱持這種觀點的文章。然而,這回民進黨不只贏得了總統大選,還達成了陳水扁執政八年間從來不曾掌握的立法院過半優勢,輕而易舉實現了長久以來夢想的「完全執政」。
台灣政治的變化確實相當激烈。就像黑白棋遊戲一樣,一、兩手的失誤就可能導致徹底翻盤。台灣,總是跳脫我們的預測,讓我們看得頭暈目眩;但是,儘管如此,這種巨大流動所帶來的爽快感,也正是台灣政治的魅力所在。正因如此,我們也不能就此斷言,認為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不過,國民黨若是不壯士斷腕、全黨從根本進行徹底的改革—譬如將「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字去掉—想要再站起來恐怕很困難。
想要寫一本書來描述這樣變化劇烈的台灣,這樣的報導文學作品,它的壽命一定不會很長。過去,我曾經寫過關於台北故宮與蔣介石、台灣的自行車產業、台灣電影等主題明確的書籍,但是對於書寫台灣政治,我總是有意識地敬而遠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我在內心深處對於「保存期限」有種畏懼感吧!或許,對自己寫出來的書不該有過多的奢望,但我至少還是希望能讓人讀上個五年、十年。
更進一步說,「台灣」這個主題本身就是難以處理的題材。就像「台灣」與「中華民國」很難畫上等號一樣,隨著觀察者和談論者在立場與尺度上的不同,對於台灣的看法也大相逕庭。因此,不管怎麼寫都要面對被轟得滿頭包的窘況。所以我想,若要對台灣進行總論性的描述,以我的能力大概力有未逮。
只是,儘管內容或許並不充分,但我還是想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這十年間觀察台灣的變化留下一份「報告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認為2016年的台灣,在很多意義上其實都面臨了重要的關鍵轉折點。
台灣本身,便是亞洲的縮影
作為單獨討論的個體,台灣絕對稱不上是「大」。伴隨著葡萄牙人那聲聞名的驚歎—伊拉.福爾摩莎(美麗之島)—台灣從16世紀開始登上世界史。這是一座形狀總會讓人聯想到蕃薯、擁有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群山,被稱為「高山國」的島嶼;它的面積約為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不過是九州程度的大小而已。
台灣的人口規模和日本近畿地方相當,約有兩千三百萬人左右,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期間出現了高度經濟成長,因而被列入「亞洲四小龍」之一。從GDP(國內生產毛額)來看,它的經濟規模大約和比利時相等。
但是,在台灣島上,還充滿著這些數字所難以計數的趣味。
直到五百年前為止,台灣都還是今日稱為「原住民」的南島語族聚居地;不過,自十六世紀以降,包括福建、客家裔的南方系漢民族,以及從中國各地匯聚而來的外省人等等,新族群陸陸續續、重重疊疊地渡海來台。正如日本台灣政治研究先驅若林正丈所指出,台灣的民族構成混合了「海洋亞洲」與「大陸亞洲」,成為一種極富多樣性的形式。再加上日本統治五十年,留下了許多對日本文化造詣甚深且通日本語言的人,凡此種種,皆讓台灣成了亞洲世界的一幅縮影。
另一方面,和台灣有著最深切利害關係的三個國家—中國、美國和日本,不用說,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三個國家。這三個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屢屢圍繞著台灣議題產生衝突。美中關係與日中關係,也常被台灣人視為最敏感的議題。筆者過去主跑外務省線新聞,就中國議題進行取材時,曾經有某位負責中國外交的中國學派官員(譯注:指日本外務省等處理對華關係的政府部門中,一批比較了解中國,或在中國任職經歷較長的官員(China school)。)對我說:「日中關係(的核心)就是歷史與台灣,你只要牢牢記住這點就行了。」他的話在我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台灣的重要性,與這座島嶼所背負的歷史重擔有極深的關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份屈辱後來演變成導火線,引爆了辛亥革命,最終推翻了滿清。此後,經歷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隨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也包括在內)中戰敗,再次回到中國的手中;可是,不到幾年時間,台灣卻變成了國民黨輸掉國共內戰之後的反攻據點,同時也成為共產黨「未完成的國家統一」當中最後一塊拼圖。實質阻礙這種統一的,是因冷戰導致的美國介入。
換言之,甲午戰爭、中國革命、中日戰爭、國共內戰、東西方冷戰,這些深刻改變東亞世界的近現代史大事件,全都與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不只如此,國共內戰與東西方冷戰的框架,直到如今依然束縛著台灣。
台灣本身也產生了某種重大的變化,那就是「台灣認同極大化」。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國;抱持這種想法的人數,已經超過人口的六成。這麼一來,尋求「讓台灣成為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自然而然水漲船高。只不過,考慮到中國強力的「一個中國」束縛,以及和中國經濟相關的利益,發表獨立宣言、建立獨立國家,這條路便顯得很不現實。另一方面,迄今為止一直抱持著不同認同觀的台灣與中國,真的會一直恆久待在「一個中國」這樣的框架下嗎?這次的總統大選,已經將這個問題送到我們鼻尖前了。
2014年春天,由學生和市民占領立法院、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太陽花運動」,其主體正是來自具有強烈台灣認同,對中國不抱持祖國幻夢的「天然獨」(與生俱來的台灣獨立派)年輕人。毫無疑問,他們的動向將會成為今後台灣政治的焦點。比起上述這些,我更想指出的是:對我們日本人而言,此刻,我們正面臨一段對台灣「認識的轉換期」。「認識的轉換期」這個詞彙或許有點難以理解,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應該如何與台灣往來?又應該如何理解台灣?關於這些,我們都來到了必須回到原點、重新思考的時候了。
只要是和台灣有關的日本人,最近大概都會突然產生這樣的感覺吧:迄今為止只被看成「中國之一部分」的台灣,是否其實不能僅以此衡量、理解的重要存在呢?日本和台灣之間存在著特別的關係嗎?日本人該如何理解台灣的親日性?為何在東日本大震災時,台灣人會主動提供鉅額的援助捐款?這麼多問題現在一下子塞進日本人的腦袋裡,會弄得腦袋暈頭轉向,我想也是無可厚非的情況吧!於是,讓我們回到問題意識上:對於台灣和日本、台灣和中國,以及台灣本身,我們應當如何思索,又該怎樣去面對?身為長年以台灣為主題來撰寫書籍的人之一,筆者想在這裡試著向包含自己在內的讀者提出這個問題。這正是本書最主要的執筆動機,同時也是追尋的目標。
第一章 當不了「台灣人總統」的馬英九
馬英九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漂亮地獲得了壓倒性勝利。不只在原本地盤的北部,他在南部也獲得了相當高的票數。馬英九的時代來臨了;這個時期的馬英九,要說他「背後有光環」,一點也不為過。就在馬英九當選的第二天,我有幸獲得機會,成為第一個面對面採訪馬英九的外國媒體人。只是,和中國或俄羅斯不同,台灣的政治家幾乎沒有什麼神祕性可言,因此就算是面晤,只要內容沒什麼新聞性,就不會獲得很大的版面可刊登。不過,我身為記者,還是敏銳地抓住了馬英九所講的一句話,那是我問出一個稀鬆平常的問題:「您希望成為怎樣的總統」時,他所做的回答。當時,馬英九是這樣講的:「我要成為全民總統。」
「全民總統」這個詞彙,用日語並不是很好翻譯。和「君臨所有民眾之上的領導者」有著微妙的不同,它的感覺大概可以說是一種「超越性的領導者」吧?我從這句話中清楚感受到馬英九想要超越國民黨與民進黨、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區別,成為受所有台灣人尊敬、愛戴的領導者的那種決心。
只是,如今回想起來,馬英九的挫敗,或許從那時候起就已經埋下了伏筆。畢竟,不管怎麼說,在台灣—不,甚至放眼全世界—只要是有選舉制度、實施自由政治的國家,要出現全體民眾都認同的領導者,根本是連做夢都辦不到的事。
支持率急速滑落
馬英九作為「全民總統」的時期,只不過維持了一年多一點而已。2009年8月8日,發生了後來稱為「八八水災」的災難。大量雨水伴隨颱風降下,使得台灣各地不斷發生土石流,高雄的小林村甚至因此全滅,死者不計其數。
這時候,馬英九遭到了嚴厲的批判,批判的焦點在於他根本沒有拿出領導者應有的表現;相對於災害規模日益擴大,馬英九政權的反應則是顯得異常遲鈍。事實上,在台灣,總統只負責外交、國防、國家安全、兩岸關係等事務,至於其他問題則是交給相當於首相的行政院長,以及其下的內閣去處理。所以,關於總統該如何應對風災水災,台灣的法律根本沒有任何規定。
可是,台灣是個過度媒體化的社會,不管總統的權限在制度上為何,作為一種演出,總統在國家面臨危機時,都必須站到最前線才行。忘了這種最基本的台灣政治ABC的馬英九,一下子就因為八八水災而瞬間失去了自己貴重的資產—支持率。「無能總統」、「無能政府」的怨懟之聲充滿了社會,馬英九的支持率從原本的百分之七十馬上遽降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此後更是有減無增。現在想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就在政府召開八八水災記者會時,我舉起手,向馬英九提了這個問題:「現在社會上都批評您是『無能總統』,您對此有何感覺?」儘管知道聽起來會很刺耳,但我還是大膽地提出了這個質疑。毫無疑問,馬英九當然感到相當不悅;只見他苦著一張臉,幾乎是下意識地說了一些岔開話題的言語,然後便結束了這場記者會。
說馬英九是無能總統,當然是有點言過其實;只不過,在民眾的罵聲中,從「全民總統」跌落到「無能總統」,這樣的轉變也未免太戲劇性了。此後,在我感覺起來,馬英九背後的「光環」似乎就漸漸褪色了。
九合一選舉,歷史性的大敗
九月政爭、太陽花運動、訪問北京失敗……這一連串事件的總帳,就是2014年11月九合一地方首長選舉的敗北。在台灣的媒體上,「變天」兩個字躍然而出。儘管這個辭彙有著「世界發生令人驚訝變化」的意味,但對國民黨在此次大選中那種雪崩式的慘敗,恐怕光憑這兩個字還不足以形容之。
在記者會上,只見馬英九帶著滿臉苦澀表情,竭盡全力地回答說:「人民的聲音,我聽到了。」對過去從來不曾在選舉中落敗的馬英九而言,這次的挫敗,應該比自己的敗北還要更加刻骨銘心吧!這是對過去馬英九路線的否定,也就等於對他自己的否定,同時,這也意味著馬英九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完全失去了主導權。馬英九不得不將黨主席的寶座讓給新北市長朱立倫,他最忠實的心腹、人稱「馬英九政權CEO」的行政院長江宜樺,也辭去了職務;事實上,馬英九時代已經宣告結束了。
這是一場前所未見的大慘敗。在22個縣市首長中,民進黨所占的席次從選前的6席,一下子大幅躍升到13席。不只如此,占全台灣人口七成的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六大直轄市,國民黨原本占有4席,這次卻除了新北市險勝以外,其他五市全都輸掉了。特別是一向被視為國民黨的地盤、也是事實上首都的台北,更是自1994年黨內分裂、敗在民進黨的陳水扁手下以來首次失守。
尤有甚者,在台北市擊敗國民黨的人,乃是最初被看做是泡沫候選人、人稱「政治素人」的無黨籍候選人—外科醫生柯文哲。而當初被認為會輕鬆勝選、國民黨元老(前副總統連戰)的兒子連勝文,則是以25萬票的極大差距敗北。
針對國民黨大敗的原因,黨內直指「頭號戰犯馬英九」的聲浪四起。這果然是熟知九月政爭、太陽花運動等一連串事件來龍去脈的人,必定會導出的結論。
在這之後又過了一年。直到2015年兩岸高峰會(馬習會)為止,馬英九幾乎是徹底沉潛。這場馬習會本身,對台灣絕對不是壞事,輿論對會談本身,也並不抱持否定的態度。儘管有人對馬英九在政權末期還進行兩岸高峰會這件事做出批判,但真正更大的問題是,馬英九身為總統,卻到最後還在向中國尋求握手,好為自己任期八年的末尾妝點光彩。
靈活多變的台灣政治
每次想要重讀過去自己所寫有關台灣的文章時,多少需要一點勇氣,有時還會感覺有點鬱卒。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以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身分,獲得壓倒性勝利當選的那一晚,這樣的思緒就層層包圍著我。
儘管這一夜的台北仍然籠罩在寒冬裡,但街頭卻充滿著熾熱的氛圍。的確,雖然大家在事前都已認定民進黨必定會重新奪回執政權,但有點超乎想像的是,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竟然以三百萬票的差距擊敗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而且在立委選舉方面,民進黨也輕鬆獲得單獨過半席次,可說是壓倒性的勝利。這讓我不禁想起八年前,國民黨擊敗民進黨,重回執政地位的那個夜晚。那晚的台北也是一樣熾熱。當時我清楚地有種感覺,那就是國民黨新的「一黨獨大時代」已然到來。相較之下,醜聞纏身外加施政失當,遭受強烈批判的民進黨,則是顯得完全乏善可陳。不只如此,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其光芒四射的程度,簡直就像今天的蔡英文。2016年的台灣選舉,彷彿和2008年是同樣的一齣劇本,只是演出的主角換了一個人。國民黨從頭到尾都陷在無止盡的內部鬥爭中,完全沒有打出整體作戰的感覺,敗北自是理所當然。至於民進黨則是極力呼喚中間選民,他們一方面成功吸引了追求「安定與自立」這個漂亮品牌的人們,另一方面則確切鞏固了既有的、擁有強烈「台灣意識」的支持層,從而第二度贏得執政權。只不過是八年前,那時的國民黨團結一致,民進黨卻分崩離析。勝負,或許往往就是這麼一回事。
每八年就能目睹一次如此鮮活演出的台灣政治「逆轉劇」,對專家而言可說是件非常幸運的事。不過,在此同時回想起自己八年前寫的東西,不免感到有些尷尬—「民進黨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大概都無法恢復元氣了」,選舉之後,台灣人不斷這麼議論著,也出現了許多抱持這種觀點的文章。然而,這回民進黨不只贏得了總統大選,還達成了陳水扁執政八年間從來不曾掌握的立法院過半優勢,輕而易舉實現了長久以來夢想的「完全執政」。
台灣政治的變化確實相當激烈。就像黑白棋遊戲一樣,一、兩手的失誤就可能導致徹底翻盤。台灣,總是跳脫我們的預測,讓我們看得頭暈目眩;但是,儘管如此,這種巨大流動所帶來的爽快感,也正是台灣政治的魅力所在。正因如此,我們也不能就此斷言,認為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不過,國民黨若是不壯士斷腕、全黨從根本進行徹底的改革—譬如將「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字去掉—想要再站起來恐怕很困難。
想要寫一本書來描述這樣變化劇烈的台灣,這樣的報導文學作品,它的壽命一定不會很長。過去,我曾經寫過關於台北故宮與蔣介石、台灣的自行車產業、台灣電影等主題明確的書籍,但是對於書寫台灣政治,我總是有意識地敬而遠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我在內心深處對於「保存期限」有種畏懼感吧!或許,對自己寫出來的書不該有過多的奢望,但我至少還是希望能讓人讀上個五年、十年。
更進一步說,「台灣」這個主題本身就是難以處理的題材。就像「台灣」與「中華民國」很難畫上等號一樣,隨著觀察者和談論者在立場與尺度上的不同,對於台灣的看法也大相逕庭。因此,不管怎麼寫都要面對被轟得滿頭包的窘況。所以我想,若要對台灣進行總論性的描述,以我的能力大概力有未逮。
只是,儘管內容或許並不充分,但我還是想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這十年間觀察台灣的變化留下一份「報告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認為2016年的台灣,在很多意義上其實都面臨了重要的關鍵轉折點。
台灣本身,便是亞洲的縮影
作為單獨討論的個體,台灣絕對稱不上是「大」。伴隨著葡萄牙人那聲聞名的驚歎—伊拉.福爾摩莎(美麗之島)—台灣從16世紀開始登上世界史。這是一座形狀總會讓人聯想到蕃薯、擁有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群山,被稱為「高山國」的島嶼;它的面積約為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不過是九州程度的大小而已。
台灣的人口規模和日本近畿地方相當,約有兩千三百萬人左右,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期間出現了高度經濟成長,因而被列入「亞洲四小龍」之一。從GDP(國內生產毛額)來看,它的經濟規模大約和比利時相等。
但是,在台灣島上,還充滿著這些數字所難以計數的趣味。
直到五百年前為止,台灣都還是今日稱為「原住民」的南島語族聚居地;不過,自十六世紀以降,包括福建、客家裔的南方系漢民族,以及從中國各地匯聚而來的外省人等等,新族群陸陸續續、重重疊疊地渡海來台。正如日本台灣政治研究先驅若林正丈所指出,台灣的民族構成混合了「海洋亞洲」與「大陸亞洲」,成為一種極富多樣性的形式。再加上日本統治五十年,留下了許多對日本文化造詣甚深且通日本語言的人,凡此種種,皆讓台灣成了亞洲世界的一幅縮影。
另一方面,和台灣有著最深切利害關係的三個國家—中國、美國和日本,不用說,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三個國家。這三個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屢屢圍繞著台灣議題產生衝突。美中關係與日中關係,也常被台灣人視為最敏感的議題。筆者過去主跑外務省線新聞,就中國議題進行取材時,曾經有某位負責中國外交的中國學派官員(譯注:指日本外務省等處理對華關係的政府部門中,一批比較了解中國,或在中國任職經歷較長的官員(China school)。)對我說:「日中關係(的核心)就是歷史與台灣,你只要牢牢記住這點就行了。」他的話在我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台灣的重要性,與這座島嶼所背負的歷史重擔有極深的關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份屈辱後來演變成導火線,引爆了辛亥革命,最終推翻了滿清。此後,經歷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隨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也包括在內)中戰敗,再次回到中國的手中;可是,不到幾年時間,台灣卻變成了國民黨輸掉國共內戰之後的反攻據點,同時也成為共產黨「未完成的國家統一」當中最後一塊拼圖。實質阻礙這種統一的,是因冷戰導致的美國介入。
換言之,甲午戰爭、中國革命、中日戰爭、國共內戰、東西方冷戰,這些深刻改變東亞世界的近現代史大事件,全都與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不只如此,國共內戰與東西方冷戰的框架,直到如今依然束縛著台灣。
台灣本身也產生了某種重大的變化,那就是「台灣認同極大化」。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國;抱持這種想法的人數,已經超過人口的六成。這麼一來,尋求「讓台灣成為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自然而然水漲船高。只不過,考慮到中國強力的「一個中國」束縛,以及和中國經濟相關的利益,發表獨立宣言、建立獨立國家,這條路便顯得很不現實。另一方面,迄今為止一直抱持著不同認同觀的台灣與中國,真的會一直恆久待在「一個中國」這樣的框架下嗎?這次的總統大選,已經將這個問題送到我們鼻尖前了。
2014年春天,由學生和市民占領立法院、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太陽花運動」,其主體正是來自具有強烈台灣認同,對中國不抱持祖國幻夢的「天然獨」(與生俱來的台灣獨立派)年輕人。毫無疑問,他們的動向將會成為今後台灣政治的焦點。比起上述這些,我更想指出的是:對我們日本人而言,此刻,我們正面臨一段對台灣「認識的轉換期」。「認識的轉換期」這個詞彙或許有點難以理解,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應該如何與台灣往來?又應該如何理解台灣?關於這些,我們都來到了必須回到原點、重新思考的時候了。
只要是和台灣有關的日本人,最近大概都會突然產生這樣的感覺吧:迄今為止只被看成「中國之一部分」的台灣,是否其實不能僅以此衡量、理解的重要存在呢?日本和台灣之間存在著特別的關係嗎?日本人該如何理解台灣的親日性?為何在東日本大震災時,台灣人會主動提供鉅額的援助捐款?這麼多問題現在一下子塞進日本人的腦袋裡,會弄得腦袋暈頭轉向,我想也是無可厚非的情況吧!於是,讓我們回到問題意識上:對於台灣和日本、台灣和中國,以及台灣本身,我們應當如何思索,又該怎樣去面對?身為長年以台灣為主題來撰寫書籍的人之一,筆者想在這裡試著向包含自己在內的讀者提出這個問題。這正是本書最主要的執筆動機,同時也是追尋的目標。
第一章 當不了「台灣人總統」的馬英九
馬英九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漂亮地獲得了壓倒性勝利。不只在原本地盤的北部,他在南部也獲得了相當高的票數。馬英九的時代來臨了;這個時期的馬英九,要說他「背後有光環」,一點也不為過。就在馬英九當選的第二天,我有幸獲得機會,成為第一個面對面採訪馬英九的外國媒體人。只是,和中國或俄羅斯不同,台灣的政治家幾乎沒有什麼神祕性可言,因此就算是面晤,只要內容沒什麼新聞性,就不會獲得很大的版面可刊登。不過,我身為記者,還是敏銳地抓住了馬英九所講的一句話,那是我問出一個稀鬆平常的問題:「您希望成為怎樣的總統」時,他所做的回答。當時,馬英九是這樣講的:「我要成為全民總統。」
「全民總統」這個詞彙,用日語並不是很好翻譯。和「君臨所有民眾之上的領導者」有著微妙的不同,它的感覺大概可以說是一種「超越性的領導者」吧?我從這句話中清楚感受到馬英九想要超越國民黨與民進黨、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區別,成為受所有台灣人尊敬、愛戴的領導者的那種決心。
只是,如今回想起來,馬英九的挫敗,或許從那時候起就已經埋下了伏筆。畢竟,不管怎麼說,在台灣—不,甚至放眼全世界—只要是有選舉制度、實施自由政治的國家,要出現全體民眾都認同的領導者,根本是連做夢都辦不到的事。
支持率急速滑落
馬英九作為「全民總統」的時期,只不過維持了一年多一點而已。2009年8月8日,發生了後來稱為「八八水災」的災難。大量雨水伴隨颱風降下,使得台灣各地不斷發生土石流,高雄的小林村甚至因此全滅,死者不計其數。
這時候,馬英九遭到了嚴厲的批判,批判的焦點在於他根本沒有拿出領導者應有的表現;相對於災害規模日益擴大,馬英九政權的反應則是顯得異常遲鈍。事實上,在台灣,總統只負責外交、國防、國家安全、兩岸關係等事務,至於其他問題則是交給相當於首相的行政院長,以及其下的內閣去處理。所以,關於總統該如何應對風災水災,台灣的法律根本沒有任何規定。
可是,台灣是個過度媒體化的社會,不管總統的權限在制度上為何,作為一種演出,總統在國家面臨危機時,都必須站到最前線才行。忘了這種最基本的台灣政治ABC的馬英九,一下子就因為八八水災而瞬間失去了自己貴重的資產—支持率。「無能總統」、「無能政府」的怨懟之聲充滿了社會,馬英九的支持率從原本的百分之七十馬上遽降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此後更是有減無增。現在想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就在政府召開八八水災記者會時,我舉起手,向馬英九提了這個問題:「現在社會上都批評您是『無能總統』,您對此有何感覺?」儘管知道聽起來會很刺耳,但我還是大膽地提出了這個質疑。毫無疑問,馬英九當然感到相當不悅;只見他苦著一張臉,幾乎是下意識地說了一些岔開話題的言語,然後便結束了這場記者會。
說馬英九是無能總統,當然是有點言過其實;只不過,在民眾的罵聲中,從「全民總統」跌落到「無能總統」,這樣的轉變也未免太戲劇性了。此後,在我感覺起來,馬英九背後的「光環」似乎就漸漸褪色了。
九合一選舉,歷史性的大敗
九月政爭、太陽花運動、訪問北京失敗……這一連串事件的總帳,就是2014年11月九合一地方首長選舉的敗北。在台灣的媒體上,「變天」兩個字躍然而出。儘管這個辭彙有著「世界發生令人驚訝變化」的意味,但對國民黨在此次大選中那種雪崩式的慘敗,恐怕光憑這兩個字還不足以形容之。
在記者會上,只見馬英九帶著滿臉苦澀表情,竭盡全力地回答說:「人民的聲音,我聽到了。」對過去從來不曾在選舉中落敗的馬英九而言,這次的挫敗,應該比自己的敗北還要更加刻骨銘心吧!這是對過去馬英九路線的否定,也就等於對他自己的否定,同時,這也意味著馬英九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完全失去了主導權。馬英九不得不將黨主席的寶座讓給新北市長朱立倫,他最忠實的心腹、人稱「馬英九政權CEO」的行政院長江宜樺,也辭去了職務;事實上,馬英九時代已經宣告結束了。
這是一場前所未見的大慘敗。在22個縣市首長中,民進黨所占的席次從選前的6席,一下子大幅躍升到13席。不只如此,占全台灣人口七成的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六大直轄市,國民黨原本占有4席,這次卻除了新北市險勝以外,其他五市全都輸掉了。特別是一向被視為國民黨的地盤、也是事實上首都的台北,更是自1994年黨內分裂、敗在民進黨的陳水扁手下以來首次失守。
尤有甚者,在台北市擊敗國民黨的人,乃是最初被看做是泡沫候選人、人稱「政治素人」的無黨籍候選人—外科醫生柯文哲。而當初被認為會輕鬆勝選、國民黨元老(前副總統連戰)的兒子連勝文,則是以25萬票的極大差距敗北。
針對國民黨大敗的原因,黨內直指「頭號戰犯馬英九」的聲浪四起。這果然是熟知九月政爭、太陽花運動等一連串事件來龍去脈的人,必定會導出的結論。
在這之後又過了一年。直到2015年兩岸高峰會(馬習會)為止,馬英九幾乎是徹底沉潛。這場馬習會本身,對台灣絕對不是壞事,輿論對會談本身,也並不抱持否定的態度。儘管有人對馬英九在政權末期還進行兩岸高峰會這件事做出批判,但真正更大的問題是,馬英九身為總統,卻到最後還在向中國尋求握手,好為自己任期八年的末尾妝點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