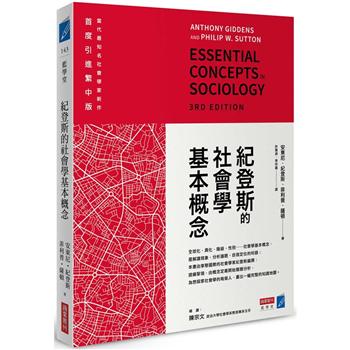【摘錄1】主題一 社會學之思
02全球化(Globalization)
現行的定義
藉由各種過程使分散各地的人彼此之間更密切、更直接地交流,從而建立了單一的命運共同體或全球社會。
概念的起源
全球人類社會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期把「人性」(humanity)視為整體的討論。全球化也可以從十九世紀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擴張趨勢,以及涂爾幹關於分工地理分散的想法中提煉出來。但是就現代意義而言,「全球化」第一次編入字典是在一九六一年,直到一九八○年代初經濟學才經常使用這個字(Kilminster 1998: 93)。
社會學討論全球化理論的重要先驅是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1974, 1980, 1989)。華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行超越國家層次,是由相對富裕的國家組成核心,最貧窮的社會形成邊陲,兩者之間夾著半邊陲。然而,當代爭論是源於一九七○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發展與權力導致全球化加速,涉及民族國家的衰弱、超國家貿易區塊以及區域性經濟政治實體(例如歐盟)的興起,旅費更便宜導致更普遍的國外觀光與移民,還有網際網路出現促進更快速的全球通訊。到了一九九○年代,全球化概念已經進入社會學主流,影響了這門學科的各個專業領域。
意義與詮釋
雖然大多數的社會學家都可以接受我們提出的現行定義,但對於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以及它帶來的是正面或負面的發展,仍然存在許多分歧。全球化提醒我們注意變遷的過程,或者是邁向全世界互賴的社會趨勢。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必然導向一個單一的全球社會。全球化有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面向(Waters 2001)。
對於某些人來說,全球化主要是經濟活動,涉及金融交易、貿易、全球生產和消費、全球分工和全球金融體系(Martell 2017)。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人口遷移的增加,改變遷徙和定居的型態,創造了一種更具流動性的人類存在形式。對於其他人而言,文化全球化更為重要。例如,羅伯森(Robertson 1995)提出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融合全球和在地元素),用以掌握地方社群集體主動修改全球過程以符合本地文化。這導致世界各地文化產品的多向流動。那些對政治全球化印象深刻的人把重點放在日益增強的區域和國際治理機制,例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s)和歐盟(European Union)。這些機構把民族國家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匯集到共同的決策論壇中,規範新興的全球社會體系。
全球化已經被理論化成為幾個相互連結的過程。貿易及市場交換通常以全球範圍進行。國際政治合作日益增長,例如活躍的「國際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或使用多國維和部隊等概念,展現了超越國界的政治和軍事合作。最新的資訊技術發展和更有系統(更便宜)的運輸也意味著社會和文化活動也全球範圍內開展。另外,人類活動的全球化變得愈來愈密集。也就是說,更多全球貿易、更多國際政治、更頻繁的全球運輸、更常態的文化交流。以全球為範圍的活動數量日益增加。許多社會學家意識到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因為數位化、資訊技術的進步以及商品運輸、服務和人員的改善,導致全球化加速。快速的全球化產生深遠的影響,二○二○年新冠狀病毒在全球迅速傳播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一地做出的經濟和政治決定,可能會對其他遙遠的社會和民族國家產生巨大影響,因此,那些長期以來身處核心的要角,似乎已經失去了一些權力與控制。
批評之處
全球化理論專家認為全球化的過程徹底改變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其他人則認為這種說法過於誇大。批評者(也被稱為「懷疑論者」)認為,儘管現今民族國家之間的聯繫與貿易已多於過去,但這些國家並未建立一個統一的全球經濟體系(Hirst et al, 2009)。取而代之的是,歐盟、亞太地區和北美的內部有一股區域貿易強化的趨勢。由於這三個區域經濟體彼此相對獨立運作,因此懷疑論者認為任何全世界、全球經濟體系的概念仍屬空想。
全球化削弱民族國家作用的想法也受到挑戰。各國政府繼續扮演關鍵角色,因為他們在貿易協定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中規範和協調經濟活動。國家主權的匯聚(pooling)並不等於喪失主權。儘管全球互賴增強,但各國政府依然保有很多權力,並且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情況下,採取更加積極、外向的立場。全球化不是更緊密整合的單向過程,而是帶來各種結果的影像、資訊和影響的雙向流動。
延伸相關
由於全球化形成社會學基本概念的背景,因此它出現在近期針對不同主題範圍龐大的研究之中,包括跨國恐怖主義、社會運動、衝突與戰爭、移民研究、環境社會學、多元文化主義等更多研究議題。隨著研究的推展,全球化五花八門的非意圖性結果也得到挖掘。舉例來說,雷納德(Renard, 1999)針對「公平貿易」產品浮現與成長的研究發現,儘管全球化過程由大型跨國公司主導,但經濟全球化也創造了更少的落差或利基,小規模的生產者得以憑藉公平與團結等共享的價值觀跨入那些利基市場。
現在,全球化的概念已被普遍接受為社會學主流的一部份,並且幾乎在每一個專業研究領域成為研究的背景。羅多梅托夫(Roudometof 2020)認為,全球化已經更普遍地成為當代社會科學與公共論述中的關鍵字彙,包含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混合性(hybridity)、全球在地化、跨國主義和跨文化主義。整體而言,這個綜合的概念使社會學家能夠更牢牢掌握超越單一民族國家層次所發生的社會和經濟重大變遷。羅多梅托夫認為這是全球化概念最重要的功能,而不是為了對全球化理論及其正負面結果達成一致看法而做的各種嘗試。
針對全球化的評判南轅北轍,但馬泰爾(Martell 2017)的評價又回到了人們熟悉的不平等這個主題。他認為儘管許多社會學家將全球化視為部分或主要是一種文化現象,但我們必須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學和物質利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馬泰爾對新興跨國政治領域的世界主義理論(cosmopolitan theories)存有疑慮,他認為此說過度樂觀。即使全球化為真也並不平均,它複製既有的不平等與不公平的權力機會。例如,全球自由流動意味著「移動需求最低的人——有錢的精英——是最能自由流動的人;而最需要移動的人——窮人以及核心富豪以外的人——卻受到最大限制」(Martell 2017: 251)。儘管文化變遷很重要,但對於馬泰爾而言,資本主義經濟學仍然是形塑現代世界的重要驅力。
【摘錄2】主題五 不平等的生活機會
35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
現行定義
是指人或社會群體在社會階層體系中向上或向下的流動。在已開發的現代社會中,社會流動是指在社會階級體系中的移動。
概念的起源
社會流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後,當時社會學家試圖評估社會不平等(通常是階級),是否會隨著社會日益富裕而減少。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從工業化之前低度不平等,經濟起飛持續的經濟成長導致了不平等的增加,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流動性增加,不平等將趨於平緩並進入逆轉。在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國的研究發現許多垂直流動,儘管實際的流動相當少或僅是小範圍的流動。大範圍的移動,例如工人階級到中上層階級,仍然非常罕見。向下流動的情況就更罕見,因為白領階層和專業工作增加的速度比藍領工作更快,使得藍領工人的兒子能夠進入白領階層工作。
利普賽特和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 1959)分析九個國家的資料做了一項重要研究,分別是英國、法國、西德、瑞典、瑞士、日本、丹麥、義大利和美國。他們研究聚焦於男性從藍領工作流動到白領工作,並有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發現。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比歐洲社會更開放,因為美國的垂直流動率為30%,歐洲則介於27%到31%之間。作者的結論指出所有的工業化社會都經歷類似的白領工作擴張,促進了向上的流動。現在的社會流動研究越來越重視性別和族群的面向,試圖評估整體社會流動是增加還是減少。
意義與詮釋
社會流動是指個人和群體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流動。垂直流動是指在社會經濟尺度的上升或下降。因此,收入、資本或地位提高的人被稱為向上流動,而經濟或地位惡化的人則是向下流動。在現代社會中,由於人們搬遷到新的地區尋找工作,也有很多地理上的流動,這被稱為橫向流動。這兩者往往密切相關,因為個人可能獲得晉升,需要轉移到同一個集團在其他地方的分公司,甚至是國外分公司。
社會學家研究社會流動的兩個主要面向。一是代內流動,著眼於個人一生中在社會量表上的上升或下降程度。再來是代際流動,探討小孩與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相比,在社會量表上向上或向下移動以及移動的程度。爭論的重點往往是階級體系相對固定或流動,以及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熟,社會流動是否變得更加容易。如果向上的社會流動程度仍然很低,那麼我們可以推測,階級依然牢牢掌控人們的生活機會,但如果今天的社會流動比以前更多,那我們可以說階級的控制正在減少,社會越來越以功績導向,而且不平等的情況更少。
英國社會流動程度在戰後獲得廣泛的研究,有豐富的經驗證據和研究報告。格拉斯(Glass 1954)分析一九五〇年代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的代際流動,他的結論指出英國不是一個特別開放的社會,儘管有許多小範圍的流動。向上流動比向下流動更普遍,但那些處於底層的人往往動彈不得。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份〈牛津流動性研究〉(The Oxford Mobility Study),即《現代英國的社會流動性和階級結構》(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1980] 1987),試圖找出自格拉斯的研究以來,英國社會流動形態發生多大的變化。研究發現男性整體流動的程度比先前要高,階級體系中大範圍的流動更多。但是,職業體系並沒有變得更加平等:截至一九八〇年代,藍領男性獲得專業與管理工作的機會增加是因為職業結構的變化,而不是因為機會增加或不平等減少。戈德索普與傑克森(Goldthorpe and Jackson 2007)使用更多新資料得出結論,沒有證據表明代際流動在絕對意義上下滑,但有一些跡象表明大範圍的流動下降。他們還發現男性向下和向上流動之間出現了較不受人歡迎的平衡,這代表不大可能恢復向上流動的上升率。
批判之處
針對社會流動研究的一個重要批評是它一直以來幾乎只關注職業男性。這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也許可以理解,因為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是男主外女主內,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正式職場,這種說法已站不住腳了。事實上,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婦女是靠著自己的收入成為一家之主。最近一些研究表明,現代女性比前幾代人有更多的機會,尤以中產階級的婦女受益最多。如果社會流動研究要告訴我社會是否開放的真實變化,也就需要考慮到女性的經驗。
有一些長期以來對整個社會流動性研究傳統的批評者認為,英國和其他已開發社會是功績導向,因為報酬是給那些「表現」與成就最好的人。因此,能力和努力是職業成功的關鍵因素,而不是階級背景(Saunders 1996)。桑德斯使用〈國家兒童發展研究〉(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的實證資料表明,無論是經歷社會優勢或弱勢的英國兒童,只要他們聰明、勤奮努力就能取得成功。英國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但它基本上也是一個公正的社會,報酬是給那些為此努力付出並因此應得的人。有些人認為個人才能是決定階級地位的因素之一,但「階級出身」仍然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影響因素,這意味著來自弱勢背景的小孩必須比其他人表現出更多的優點,才能獲得類似的階級位置。
延伸相關
對於社會學者來說,要想建立跨階級的職業和流動趨勢,社會流動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現在,許多人認為全球化和經濟市場的去管制正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和階級不平等的「僵化」(hardening),導致社會流動的機會更少。然而,重要的是記住,我們的活動從來不是完全由階級劃分所決定,許多人確實經歷過社會流動。
阿克斯(Ackers 2019)最近的研究探討男性技術工人的社會流動,討論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所經歷的個人緊張與不安。這份質化研究涵蓋二十八位男工的生活史,發現這些成功的代際流動案例中,有一種「雙重緊張」(dual tension)在發揮作用。第一個緊張來源是他們從傳統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轉向到更接近中產階級的生活形式。第二個緊張來源是家庭給他們的壓力,改善他們從父母輩繼承的工人地位。本質上,這些人經歷集體歸屬和個人成就之間的階級錯置和緊張關係,他們採取一種在生活中「過得去」(getting on)的觀點來應對。然而,他們也希望自己向上流動後的職業能為父母接受,彷彿他們仍然「保有」自己的家庭背景。這項研究與其他研究相反,他們認為社會流動向上顯然是一件「好事」,但這項研究卻點出個人向上流動還有自我意識轉變所牽扯的問題。
社會轉型或革命如何影響社會流動的前景?赫茲等人(Hertz et al. 2009)以後社會主義國家保加利亞為例探討這個問題。這項研究記錄保加利亞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一年期間代際間社會流動的急劇下降,這段時間發生劇烈的變化、經濟蕭條和公共支出(特別是教育)的大量刪減。特別是,這段期間父母教育程度較低的小孩,平均教育程度是絕對下降,代際間的社會流動也隨之下滑。赫茲等人認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的大幅削減和學校數量減少、失業率攀升,以及政治風向轉變遠離過去的平等主義立場。我們可能不會太驚訝前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會造成很多混亂,但可以想像的是二〇〇八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可能會使得要扭轉該文所指出的趨勢將變得更加困難。
【摘錄3】主題十 政治社會學
60污名Stigma
現行定義
被認定帶著有辱人格或社會不認可的身體或社會特徵,並且引來咒罵、社會疏遠或歧視。
概念起源
社會學研究污名和污名化過程,主要在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的符號互動主義的傳統中進行。有些早期的研究,如高夫曼(Goffman [1963]1990),把污名化過程如何產生歧視進行理論化,同時也研究被污名化的人如何回應。對高夫曼而言,污名的類型不同會有一些重要的差異,這會影響人們管理自我身分和保護自我意識的程度。污名觀點的另一個來源是障礙者運動。亨特(Paul Hunt)的《污名:障礙的體驗》(Stigma: The Experience of Disability 1966)是早期對障礙者個人模式的重要挑戰。亨特認為與其說障礙者的問題是由自己的損傷所引起,不如說是障礙者和健全者之間的互動導致障礙者的污名化。最近,這一概念被成功地用於探討罹患愛滋病毒/愛滋病患者和其他與健康相關的情況。
意義和詮釋
高夫曼的研究是關於污名產生最成功也最有系統的說明。他的研究充分說明社會認同和體現之間的密切聯繫,因為他表明一旦一個人身體的某些部分被其他人歸類為污名的來源問題就來了。例如,他說明障礙者是如何因為外顯的身體缺陷而遭到污名化。然而,並非所有的污名來源都是身體,因為污名也會看一個人的經歷、人格「缺陷」或個人關係。
污名有多種形式。身體上的污名,例如明顯的損傷,往往很難或不太可能隱藏起來不被他人看見,高夫曼認為這可能使身分的管理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稱為「明顯遭貶抑的」(discredited)的污名——在互動中必須被認知。傳記性污名,例如前科,可能比較容易隱瞞不為人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稱為「讓人遭貶抑的」(discrediting)污名——如果被更多人知道的話會導致污名化。管理這種類型的污名可能比較容易一些,但仍需持續加以控制。人格上的污名,例如與吸毒者來往可能是一種使人遭到貶抑的污名,但如果這個人被看到和一群壞朋友在一起,他就可能變成明顯遭貶抑的污名。值得注意的是,高夫曼並不是建議人應該隱藏污名;他只是想弄清楚在現實世界中污名化過程是如何運作,以及人們是如何使用策略來避免被污名化。
高夫曼認為,污名是一種貶抑的社會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一個人失去被其他人完全接受的社會資格。污名化往往出現在醫療脈絡下,因為人們生病,他們的身分也會發生改變—有時是暫時的,但在其他時候,例如慢性病的情況下,則是永久揮之不去。高夫曼認為污名化過程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控制。污名化群體是整個社會控制他們行為的一種方式。在某些情況下,污名永遠不會拿不掉,當事人也永遠不會被社會完全接受。早期對於許多愛滋病患者是如此,而且在一些國家現在還是。
同性戀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長期以來一直被污名化,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對男同性戀者與女同性戀的仇恨被描述為恐同症(homophobia)。這可能是言語傷人和辱駡,但也可能採取公然的暴力。二〇一六年,有一名槍手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Orlando)的一家夜店開槍射擊同性戀,造成四十九人死亡、五十三人受傷,這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之一。長期以來,虐待同性戀的主要場景之一是學校,諸如「呸」(poof,指男同性戀)、「娘娘腔」(sissy)、「怪人」(queer)等許多詞彙,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操場上的常聽到的話。由於童年是社會自我形成的關鍵,學校中對同性戀的霸凌被看成是社會複製「異性戀」的關鍵面向。內特爾頓(Nettleton)(2021)指出,由於愛滋病最初是在美國的男同性戀者之間發現,所以最初稱為GRID(Gay 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男同性戀有關的免疫缺陷),這是暗示男同性戀「快車道般」(fast-lane)刺激的生活方式導致這種疾病,媒體經常說成「同性戀瘟疫」(gay plague)。雖然這是錯的,但從流行病學角度將男同性戀者解釋為「高風險群體」的一部分,往往會強化這些群體與「異性戀普通人」之間的分歧。
批判之處
關於污名研究的問題之一就是相對缺乏對政治和結構議題的關注(Tyler and Slater 2018)。例如,誰生產污名,其目的為何?污名是否與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有關,一旦污名化上身,是否有可能抵抗?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中污名功能的研究試著對污名化的過程做出更全面的描述,人們對於這些問題的興趣越來越大。
以個人層次為例,人們可以直接拒絕一個污名化的標籤,儘管從個別來看他們不大可能成功。然而,集體的抵抗對於挑戰污名深具意義。身障者運動和男女同性戀運動往往透過抗議和直接行動,挑戰主流社會對「明顯遭貶抑的污名」和「讓人遭貶抑的污名」的詮釋。高能見度的象徵性抗議和正面挑戰歧視性語言和標籤化,施壓推動改變和新的平權立法,而且有助於改變社會的態度。污名化過程也許比早期理論所認定的範圍更容易改變。
延伸相關
污名的概念仍然很實用。例如,對自殘行為的研究表明,那些傷害自己的人清楚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被污名化,所以選擇自殘是身體在公共場合中最容易隱藏的部分,以避免自己從「讓人遭貶抑的污名」變成「明顯遭貶抑的污名」。同樣地,針對厭食症等飲食失調的研究表明,人們會竭盡所能隱藏自己的行為,以便管理他們的自我呈現,進而管理他們的身分,而不是將控制權交給其他人,並在此過程中承受強加上來的社會污名。
陳潔儀(Kit Yee Chan)和同事(Chan et al. 2009)對於泰國性濫交的標籤和愛滋病的研究中清楚看到污名概念持續發揮作用。這項研究採用了混合方法,探討曼谷的護理師對值勤必須承受意外暴露於愛滋病毒風險的看法。作者發現護理師對愛滋病毒的恐懼主要源自於她們和那些感染者的連結所造成的社會排斥,而不是感染在醫學上的後果。儘管護理師很清楚在工作中實際感染病毒的概率非常低,但她們仍然會恐懼,支持這份恐懼的是她們腦中感染愛滋病毒帶來的社會後果。這種社會恐懼會因她們近距離觀察到病人身上的污名而強化。
02全球化(Globalization)
現行的定義
藉由各種過程使分散各地的人彼此之間更密切、更直接地交流,從而建立了單一的命運共同體或全球社會。
概念的起源
全球人類社會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期把「人性」(humanity)視為整體的討論。全球化也可以從十九世紀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擴張趨勢,以及涂爾幹關於分工地理分散的想法中提煉出來。但是就現代意義而言,「全球化」第一次編入字典是在一九六一年,直到一九八○年代初經濟學才經常使用這個字(Kilminster 1998: 93)。
社會學討論全球化理論的重要先驅是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1974, 1980, 1989)。華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行超越國家層次,是由相對富裕的國家組成核心,最貧窮的社會形成邊陲,兩者之間夾著半邊陲。然而,當代爭論是源於一九七○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發展與權力導致全球化加速,涉及民族國家的衰弱、超國家貿易區塊以及區域性經濟政治實體(例如歐盟)的興起,旅費更便宜導致更普遍的國外觀光與移民,還有網際網路出現促進更快速的全球通訊。到了一九九○年代,全球化概念已經進入社會學主流,影響了這門學科的各個專業領域。
意義與詮釋
雖然大多數的社會學家都可以接受我們提出的現行定義,但對於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以及它帶來的是正面或負面的發展,仍然存在許多分歧。全球化提醒我們注意變遷的過程,或者是邁向全世界互賴的社會趨勢。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必然導向一個單一的全球社會。全球化有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面向(Waters 2001)。
對於某些人來說,全球化主要是經濟活動,涉及金融交易、貿易、全球生產和消費、全球分工和全球金融體系(Martell 2017)。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人口遷移的增加,改變遷徙和定居的型態,創造了一種更具流動性的人類存在形式。對於其他人而言,文化全球化更為重要。例如,羅伯森(Robertson 1995)提出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融合全球和在地元素),用以掌握地方社群集體主動修改全球過程以符合本地文化。這導致世界各地文化產品的多向流動。那些對政治全球化印象深刻的人把重點放在日益增強的區域和國際治理機制,例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s)和歐盟(European Union)。這些機構把民族國家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匯集到共同的決策論壇中,規範新興的全球社會體系。
全球化已經被理論化成為幾個相互連結的過程。貿易及市場交換通常以全球範圍進行。國際政治合作日益增長,例如活躍的「國際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或使用多國維和部隊等概念,展現了超越國界的政治和軍事合作。最新的資訊技術發展和更有系統(更便宜)的運輸也意味著社會和文化活動也全球範圍內開展。另外,人類活動的全球化變得愈來愈密集。也就是說,更多全球貿易、更多國際政治、更頻繁的全球運輸、更常態的文化交流。以全球為範圍的活動數量日益增加。許多社會學家意識到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因為數位化、資訊技術的進步以及商品運輸、服務和人員的改善,導致全球化加速。快速的全球化產生深遠的影響,二○二○年新冠狀病毒在全球迅速傳播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一地做出的經濟和政治決定,可能會對其他遙遠的社會和民族國家產生巨大影響,因此,那些長期以來身處核心的要角,似乎已經失去了一些權力與控制。
批評之處
全球化理論專家認為全球化的過程徹底改變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其他人則認為這種說法過於誇大。批評者(也被稱為「懷疑論者」)認為,儘管現今民族國家之間的聯繫與貿易已多於過去,但這些國家並未建立一個統一的全球經濟體系(Hirst et al, 2009)。取而代之的是,歐盟、亞太地區和北美的內部有一股區域貿易強化的趨勢。由於這三個區域經濟體彼此相對獨立運作,因此懷疑論者認為任何全世界、全球經濟體系的概念仍屬空想。
全球化削弱民族國家作用的想法也受到挑戰。各國政府繼續扮演關鍵角色,因為他們在貿易協定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中規範和協調經濟活動。國家主權的匯聚(pooling)並不等於喪失主權。儘管全球互賴增強,但各國政府依然保有很多權力,並且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情況下,採取更加積極、外向的立場。全球化不是更緊密整合的單向過程,而是帶來各種結果的影像、資訊和影響的雙向流動。
延伸相關
由於全球化形成社會學基本概念的背景,因此它出現在近期針對不同主題範圍龐大的研究之中,包括跨國恐怖主義、社會運動、衝突與戰爭、移民研究、環境社會學、多元文化主義等更多研究議題。隨著研究的推展,全球化五花八門的非意圖性結果也得到挖掘。舉例來說,雷納德(Renard, 1999)針對「公平貿易」產品浮現與成長的研究發現,儘管全球化過程由大型跨國公司主導,但經濟全球化也創造了更少的落差或利基,小規模的生產者得以憑藉公平與團結等共享的價值觀跨入那些利基市場。
現在,全球化的概念已被普遍接受為社會學主流的一部份,並且幾乎在每一個專業研究領域成為研究的背景。羅多梅托夫(Roudometof 2020)認為,全球化已經更普遍地成為當代社會科學與公共論述中的關鍵字彙,包含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混合性(hybridity)、全球在地化、跨國主義和跨文化主義。整體而言,這個綜合的概念使社會學家能夠更牢牢掌握超越單一民族國家層次所發生的社會和經濟重大變遷。羅多梅托夫認為這是全球化概念最重要的功能,而不是為了對全球化理論及其正負面結果達成一致看法而做的各種嘗試。
針對全球化的評判南轅北轍,但馬泰爾(Martell 2017)的評價又回到了人們熟悉的不平等這個主題。他認為儘管許多社會學家將全球化視為部分或主要是一種文化現象,但我們必須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學和物質利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馬泰爾對新興跨國政治領域的世界主義理論(cosmopolitan theories)存有疑慮,他認為此說過度樂觀。即使全球化為真也並不平均,它複製既有的不平等與不公平的權力機會。例如,全球自由流動意味著「移動需求最低的人——有錢的精英——是最能自由流動的人;而最需要移動的人——窮人以及核心富豪以外的人——卻受到最大限制」(Martell 2017: 251)。儘管文化變遷很重要,但對於馬泰爾而言,資本主義經濟學仍然是形塑現代世界的重要驅力。
【摘錄2】主題五 不平等的生活機會
35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
現行定義
是指人或社會群體在社會階層體系中向上或向下的流動。在已開發的現代社會中,社會流動是指在社會階級體系中的移動。
概念的起源
社會流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後,當時社會學家試圖評估社會不平等(通常是階級),是否會隨著社會日益富裕而減少。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從工業化之前低度不平等,經濟起飛持續的經濟成長導致了不平等的增加,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流動性增加,不平等將趨於平緩並進入逆轉。在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國的研究發現許多垂直流動,儘管實際的流動相當少或僅是小範圍的流動。大範圍的移動,例如工人階級到中上層階級,仍然非常罕見。向下流動的情況就更罕見,因為白領階層和專業工作增加的速度比藍領工作更快,使得藍領工人的兒子能夠進入白領階層工作。
利普賽特和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 1959)分析九個國家的資料做了一項重要研究,分別是英國、法國、西德、瑞典、瑞士、日本、丹麥、義大利和美國。他們研究聚焦於男性從藍領工作流動到白領工作,並有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發現。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比歐洲社會更開放,因為美國的垂直流動率為30%,歐洲則介於27%到31%之間。作者的結論指出所有的工業化社會都經歷類似的白領工作擴張,促進了向上的流動。現在的社會流動研究越來越重視性別和族群的面向,試圖評估整體社會流動是增加還是減少。
意義與詮釋
社會流動是指個人和群體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流動。垂直流動是指在社會經濟尺度的上升或下降。因此,收入、資本或地位提高的人被稱為向上流動,而經濟或地位惡化的人則是向下流動。在現代社會中,由於人們搬遷到新的地區尋找工作,也有很多地理上的流動,這被稱為橫向流動。這兩者往往密切相關,因為個人可能獲得晉升,需要轉移到同一個集團在其他地方的分公司,甚至是國外分公司。
社會學家研究社會流動的兩個主要面向。一是代內流動,著眼於個人一生中在社會量表上的上升或下降程度。再來是代際流動,探討小孩與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相比,在社會量表上向上或向下移動以及移動的程度。爭論的重點往往是階級體系相對固定或流動,以及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熟,社會流動是否變得更加容易。如果向上的社會流動程度仍然很低,那麼我們可以推測,階級依然牢牢掌控人們的生活機會,但如果今天的社會流動比以前更多,那我們可以說階級的控制正在減少,社會越來越以功績導向,而且不平等的情況更少。
英國社會流動程度在戰後獲得廣泛的研究,有豐富的經驗證據和研究報告。格拉斯(Glass 1954)分析一九五〇年代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的代際流動,他的結論指出英國不是一個特別開放的社會,儘管有許多小範圍的流動。向上流動比向下流動更普遍,但那些處於底層的人往往動彈不得。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份〈牛津流動性研究〉(The Oxford Mobility Study),即《現代英國的社會流動性和階級結構》(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1980] 1987),試圖找出自格拉斯的研究以來,英國社會流動形態發生多大的變化。研究發現男性整體流動的程度比先前要高,階級體系中大範圍的流動更多。但是,職業體系並沒有變得更加平等:截至一九八〇年代,藍領男性獲得專業與管理工作的機會增加是因為職業結構的變化,而不是因為機會增加或不平等減少。戈德索普與傑克森(Goldthorpe and Jackson 2007)使用更多新資料得出結論,沒有證據表明代際流動在絕對意義上下滑,但有一些跡象表明大範圍的流動下降。他們還發現男性向下和向上流動之間出現了較不受人歡迎的平衡,這代表不大可能恢復向上流動的上升率。
批判之處
針對社會流動研究的一個重要批評是它一直以來幾乎只關注職業男性。這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也許可以理解,因為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是男主外女主內,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正式職場,這種說法已站不住腳了。事實上,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婦女是靠著自己的收入成為一家之主。最近一些研究表明,現代女性比前幾代人有更多的機會,尤以中產階級的婦女受益最多。如果社會流動研究要告訴我社會是否開放的真實變化,也就需要考慮到女性的經驗。
有一些長期以來對整個社會流動性研究傳統的批評者認為,英國和其他已開發社會是功績導向,因為報酬是給那些「表現」與成就最好的人。因此,能力和努力是職業成功的關鍵因素,而不是階級背景(Saunders 1996)。桑德斯使用〈國家兒童發展研究〉(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的實證資料表明,無論是經歷社會優勢或弱勢的英國兒童,只要他們聰明、勤奮努力就能取得成功。英國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但它基本上也是一個公正的社會,報酬是給那些為此努力付出並因此應得的人。有些人認為個人才能是決定階級地位的因素之一,但「階級出身」仍然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影響因素,這意味著來自弱勢背景的小孩必須比其他人表現出更多的優點,才能獲得類似的階級位置。
延伸相關
對於社會學者來說,要想建立跨階級的職業和流動趨勢,社會流動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現在,許多人認為全球化和經濟市場的去管制正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和階級不平等的「僵化」(hardening),導致社會流動的機會更少。然而,重要的是記住,我們的活動從來不是完全由階級劃分所決定,許多人確實經歷過社會流動。
阿克斯(Ackers 2019)最近的研究探討男性技術工人的社會流動,討論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所經歷的個人緊張與不安。這份質化研究涵蓋二十八位男工的生活史,發現這些成功的代際流動案例中,有一種「雙重緊張」(dual tension)在發揮作用。第一個緊張來源是他們從傳統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轉向到更接近中產階級的生活形式。第二個緊張來源是家庭給他們的壓力,改善他們從父母輩繼承的工人地位。本質上,這些人經歷集體歸屬和個人成就之間的階級錯置和緊張關係,他們採取一種在生活中「過得去」(getting on)的觀點來應對。然而,他們也希望自己向上流動後的職業能為父母接受,彷彿他們仍然「保有」自己的家庭背景。這項研究與其他研究相反,他們認為社會流動向上顯然是一件「好事」,但這項研究卻點出個人向上流動還有自我意識轉變所牽扯的問題。
社會轉型或革命如何影響社會流動的前景?赫茲等人(Hertz et al. 2009)以後社會主義國家保加利亞為例探討這個問題。這項研究記錄保加利亞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一年期間代際間社會流動的急劇下降,這段時間發生劇烈的變化、經濟蕭條和公共支出(特別是教育)的大量刪減。特別是,這段期間父母教育程度較低的小孩,平均教育程度是絕對下降,代際間的社會流動也隨之下滑。赫茲等人認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的大幅削減和學校數量減少、失業率攀升,以及政治風向轉變遠離過去的平等主義立場。我們可能不會太驚訝前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會造成很多混亂,但可以想像的是二〇〇八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可能會使得要扭轉該文所指出的趨勢將變得更加困難。
【摘錄3】主題十 政治社會學
60污名Stigma
現行定義
被認定帶著有辱人格或社會不認可的身體或社會特徵,並且引來咒罵、社會疏遠或歧視。
概念起源
社會學研究污名和污名化過程,主要在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的符號互動主義的傳統中進行。有些早期的研究,如高夫曼(Goffman [1963]1990),把污名化過程如何產生歧視進行理論化,同時也研究被污名化的人如何回應。對高夫曼而言,污名的類型不同會有一些重要的差異,這會影響人們管理自我身分和保護自我意識的程度。污名觀點的另一個來源是障礙者運動。亨特(Paul Hunt)的《污名:障礙的體驗》(Stigma: The Experience of Disability 1966)是早期對障礙者個人模式的重要挑戰。亨特認為與其說障礙者的問題是由自己的損傷所引起,不如說是障礙者和健全者之間的互動導致障礙者的污名化。最近,這一概念被成功地用於探討罹患愛滋病毒/愛滋病患者和其他與健康相關的情況。
意義和詮釋
高夫曼的研究是關於污名產生最成功也最有系統的說明。他的研究充分說明社會認同和體現之間的密切聯繫,因為他表明一旦一個人身體的某些部分被其他人歸類為污名的來源問題就來了。例如,他說明障礙者是如何因為外顯的身體缺陷而遭到污名化。然而,並非所有的污名來源都是身體,因為污名也會看一個人的經歷、人格「缺陷」或個人關係。
污名有多種形式。身體上的污名,例如明顯的損傷,往往很難或不太可能隱藏起來不被他人看見,高夫曼認為這可能使身分的管理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稱為「明顯遭貶抑的」(discredited)的污名——在互動中必須被認知。傳記性污名,例如前科,可能比較容易隱瞞不為人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稱為「讓人遭貶抑的」(discrediting)污名——如果被更多人知道的話會導致污名化。管理這種類型的污名可能比較容易一些,但仍需持續加以控制。人格上的污名,例如與吸毒者來往可能是一種使人遭到貶抑的污名,但如果這個人被看到和一群壞朋友在一起,他就可能變成明顯遭貶抑的污名。值得注意的是,高夫曼並不是建議人應該隱藏污名;他只是想弄清楚在現實世界中污名化過程是如何運作,以及人們是如何使用策略來避免被污名化。
高夫曼認為,污名是一種貶抑的社會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一個人失去被其他人完全接受的社會資格。污名化往往出現在醫療脈絡下,因為人們生病,他們的身分也會發生改變—有時是暫時的,但在其他時候,例如慢性病的情況下,則是永久揮之不去。高夫曼認為污名化過程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控制。污名化群體是整個社會控制他們行為的一種方式。在某些情況下,污名永遠不會拿不掉,當事人也永遠不會被社會完全接受。早期對於許多愛滋病患者是如此,而且在一些國家現在還是。
同性戀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長期以來一直被污名化,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對男同性戀者與女同性戀的仇恨被描述為恐同症(homophobia)。這可能是言語傷人和辱駡,但也可能採取公然的暴力。二〇一六年,有一名槍手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Orlando)的一家夜店開槍射擊同性戀,造成四十九人死亡、五十三人受傷,這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之一。長期以來,虐待同性戀的主要場景之一是學校,諸如「呸」(poof,指男同性戀)、「娘娘腔」(sissy)、「怪人」(queer)等許多詞彙,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操場上的常聽到的話。由於童年是社會自我形成的關鍵,學校中對同性戀的霸凌被看成是社會複製「異性戀」的關鍵面向。內特爾頓(Nettleton)(2021)指出,由於愛滋病最初是在美國的男同性戀者之間發現,所以最初稱為GRID(Gay 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男同性戀有關的免疫缺陷),這是暗示男同性戀「快車道般」(fast-lane)刺激的生活方式導致這種疾病,媒體經常說成「同性戀瘟疫」(gay plague)。雖然這是錯的,但從流行病學角度將男同性戀者解釋為「高風險群體」的一部分,往往會強化這些群體與「異性戀普通人」之間的分歧。
批判之處
關於污名研究的問題之一就是相對缺乏對政治和結構議題的關注(Tyler and Slater 2018)。例如,誰生產污名,其目的為何?污名是否與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有關,一旦污名化上身,是否有可能抵抗?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中污名功能的研究試著對污名化的過程做出更全面的描述,人們對於這些問題的興趣越來越大。
以個人層次為例,人們可以直接拒絕一個污名化的標籤,儘管從個別來看他們不大可能成功。然而,集體的抵抗對於挑戰污名深具意義。身障者運動和男女同性戀運動往往透過抗議和直接行動,挑戰主流社會對「明顯遭貶抑的污名」和「讓人遭貶抑的污名」的詮釋。高能見度的象徵性抗議和正面挑戰歧視性語言和標籤化,施壓推動改變和新的平權立法,而且有助於改變社會的態度。污名化過程也許比早期理論所認定的範圍更容易改變。
延伸相關
污名的概念仍然很實用。例如,對自殘行為的研究表明,那些傷害自己的人清楚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被污名化,所以選擇自殘是身體在公共場合中最容易隱藏的部分,以避免自己從「讓人遭貶抑的污名」變成「明顯遭貶抑的污名」。同樣地,針對厭食症等飲食失調的研究表明,人們會竭盡所能隱藏自己的行為,以便管理他們的自我呈現,進而管理他們的身分,而不是將控制權交給其他人,並在此過程中承受強加上來的社會污名。
陳潔儀(Kit Yee Chan)和同事(Chan et al. 2009)對於泰國性濫交的標籤和愛滋病的研究中清楚看到污名概念持續發揮作用。這項研究採用了混合方法,探討曼谷的護理師對值勤必須承受意外暴露於愛滋病毒風險的看法。作者發現護理師對愛滋病毒的恐懼主要源自於她們和那些感染者的連結所造成的社會排斥,而不是感染在醫學上的後果。儘管護理師很清楚在工作中實際感染病毒的概率非常低,但她們仍然會恐懼,支持這份恐懼的是她們腦中感染愛滋病毒帶來的社會後果。這種社會恐懼會因她們近距離觀察到病人身上的污名而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