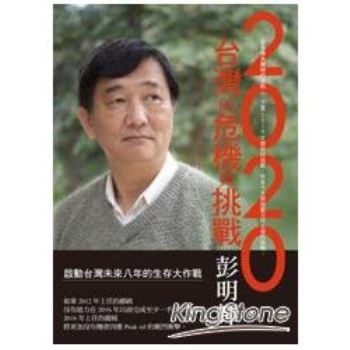【2020台灣的嚴峻挑戰】
台灣將會在2020年遭遇到極為嚴峻的挑戰,如果我們的現行政策或思維模式不變,將會在糧食上無以自足,經濟上經歷數十年的持續衰退與大蕭條,不但實質所得有可能會在2035年降低到僅剩今天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而且會有飆漲的失業率和貧窮人口數,以致於經濟、社會與政治都濱於崩解的邊緣。
把台灣推往這絕境的力量主要有四個:(1)少子化的危機將會使得人均所得持續下降並埋下失業潮的危機──2025年起每兩個上班的人要扶養一個老人或小孩(扶養比約50%),2055年時每一個上班的人要撫養0.9個老人和小孩,經濟負擔將愈來愈吃重;2060年時老年人口將是幼年人口的四倍,幼教機構將大幅消失,老人照護產業需求遽增,國內產業需要在50年內天翻地覆地大風吹,來不及調整的企業將倒閉或經營困難。(2)全球石油產能很可能會在2015年之前跨越最高點而開始下降,這現象被英語世界稱為「peak oil」;而牛津大學預測2023年時全球石油供給量將僅及需求的一半,使油價上看每桶200~500美元,導致越洋貿易萎縮而全球GDP持續下降數十年,也使得大陸和亞洲成為台灣主要貿易伙伴。(3)油價高漲,使得穀物提煉生質燃料有利可圖,歐美出口的糧食將銳減,而亞洲在肥料與糧食生產上都無法自給自足,使得糧食自給率僅32%的台灣面臨缺糧的危機。(4)既有產業政策仰賴「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高工時與低毛利」的「血汗工廠」競爭模式,未來在油、電、糧與工資四漲且代工產業萎縮的情況下,許多企業將倒閉,而引起失業潮。(5)加入WTO後被迫金融自由化,加上兩岸競爭,使得財團有本錢恐嚇政府,要求政府降低稅收,進行各種補助,而導致政府負債急遽擴大,而沒有能力在失業潮中對難以為生的人伸出援手。
如果我們想要擺脫上述窘境,就必須在未來十年內完成以下變革:(1)改變糧食生產方式,逐漸擺脫對石油、化肥與農藥的倚賴,發展出適合亞熱帶模式的高產能農、魚、牧整合的生產系統;(2)發展綠能產業與公共運輸,減少私人車輛,以降低對能源的需求;(3)徹底改變台灣的產業結構,減少對代工產業的倚賴,協助中小企業技術升級,往「低污染、低耗能、低耗水、高毛利與合理工時」的方向發展;(4)以亞洲為市場,強化金融、商業資訊服務、軟體、文化創意產業與品牌等產業賺取外匯的能力,同時減少經濟與貿易上對大陸的過度倚賴;(5)停止劫貧濟富的稅制與產業補貼,提高資本利得稅與富人稅,以便降低國債與隱藏性債務,並且讓政府有足夠的稅收強化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的職能,以便在GDP下降與失業率上升的過程中扶助弱勢,避免造成嚴重的社會失序與流血衝突。
由於沒有看到未來潛在的危機,政府施政一向只顧富人的需要而任由窮苦的人流浪街頭,甚至過勞死、燒炭自殺。但是,茉莉革命告訴我們一個教訓:如果一個社會不能讓最弱勢的20%人口活下去,他們將會被迫以極端的手段爭生存權,那時候富人不但無法安居樂業,經濟也會在動盪不安中無法持續運轉。
這一切並非杞人憂天,也非恫嚇之言。少子化的危機已經變成無法逆轉的事實,而全球能源供不應求的日子也即將來臨!(待續)從無稽之談到無法逃避的事實
很多人誤以為要到石油枯竭才會有石油危機,其實只要石油產能開始下跌,供不應求的危機就已經開始並逐漸惡化,使得油價與失業率持續飆漲。很多人老早就知道,遲早有一天地球上的石油會供不應求;但是很少人會想到:它有可能會在四年內發生。
經濟學家一直主張:不需要擔心能源與礦產耗竭的問題,那些都是無稽之談──在能源與礦產耗竭之前,市場機制會使得逐漸稀有的能源與物資價格上漲,因而帶動資金進入可以產出科技革命的相關產業,從而引發破壞性的創造,產出節能的商品、替代性能源、替代性材料,以及商品的回收再利用。因此,一切問題都會在市場機制和科技創新的力量下自動地被解決,無須杞人憂天。
經濟學家的樂觀態度隱藏著兩個他們沒有自覺到的假設:市場萬能以及科學萬能。但這兩個假設並非永遠會實現!
有人問過我:綠色革命曾經化解了人類的糧食危機,為什麼我沒想到科學將會化解能源與糧食的危機?問題不是「會不會」,而是「來不來得及」。綠色革命「及時」挽救了人類的危機,這是歷史上罕見的例外,而非常態。科學的進展速度無法預測,也不一定正比於資金的投入──我們等待氫融合的乾淨電能已經60年了,歐陸最權威的專家卻說我們至少還需要再等40年;中國歷代的皇帝投入無數的資源想要研發長生不老的藥,結果卻往往短命而死。
許多石油專家都預測peak oil(石油跨越最高產能)很可能會在2020年之前發生,而且大部分的預測都落在2010年到2014年之間。接著,天然氣會在10年後跟著跨越產能極限,使得運輸工具的燃料開始供不應求。假如2023年時全球原油供給量只剩需求量的一半,今天的石油用戶之中將有一半的人會因為負擔不起高油價而退出消費市場,其中很可能包括糧食與肥料的運洋貿易,以及利潤低微的越洋產業代工。
儘管經濟學家一再保證新興能源最後會取代石化能源,很不幸地,這些替代能源的發展速度卻太慢,很可能來不及填補 peak oil 所造成的能源缺口。
纖維素酒精將是石油的最佳替代品,但是成本太高而發展速度太慢,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將2011年纖維酒精的法定產量削減為原來的1%~3%。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第一優先用途是替代石化燃料的火力發電,發電量有餘時才可以用來製造氫氣,作為替代性燃料;然而風力發電能量規模有限,而太陽能發電成本太高。審慎的估計認為2050年時太陽能將只佔全美發電總量的69%與總能量的35%,並且在2100年才達到全美總能量需求的92%。因此,從成本因素考量,在2100年之前很難期待用風能與太陽能生產氫氣來填補 peak oil 之後的燃料缺口。
經濟學家一向期待市場機制會自動調節供需,在油價上漲的過程吸引大量資金投入新能源的開發,而促成技術的突破,最後解決能源危機。懷著這種期待的人應該要認真想一想凱因斯的名言:「在長遠的未來,我們都死了。」──問題不是科技發展與市場機制「會不會」自行解決問題,而是「來不來得及」。
石油被稱為當代社會的血液,不僅維繫著各種農業與工業的生產,也維繫著全球的運輸與貿易,以及冷暖氣與家庭用電所建構起來的舒適環境──高價的石油與石油的減產意味著許多人將必須減少生活上的舒適或者放棄它。此外,油價每上漲10%,全球平均GDP將下降0.55%,而GDP的持續下降則會造成失業率和貧窮人口數的飆升,以及政府稅收的短缺,而亞洲等仰賴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更可能會因而失控。
不幸的是,這本書所蒐集到的文獻與證據顯示:市場將無法在危機發生前搶救地球,而必須要靠所有人和政府從制度、生活習慣與觀念上進行徹底的改變,來因應這個變局──而且動作要快,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應變了。(待續)不是遲來的警告,而是持續40年的警告
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就已經委由麻省理工學院所組成的專家團隊發表了《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這本書,他們用電腦模擬做出一個預測:如果全球經濟發展模式不變,全球經濟將會因為有限能源與物資的耗竭而遭遇到經濟持續衰退,全球人均工業產值與糧食產量將會在21世紀中葉之前跨越最高峰,並迅速地歷經大蕭條而衰退到1950年代左右的水準。
在目前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市場機制中,經濟負成長無可避免地意味著經濟與社會的大災難。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充分就業是靠GDP的持續成長來維持,而GDP的成長則來自於消費的擴充。一旦可用的能源或物資減少而使消費無法擴充,GDP的成長就會趨緩;即便只是生產效率的提升速度超過GDP的成長速度,失業率都會開始上升。一旦GDP進入持續的負成長,失業率、貧窮人口數和政府債務就會失控地飆漲,以致於整個經濟系統崩潰。
為了避免這個悲劇的發生,《成長的極限》建議控制出生率與人口數,保護農地並控制環境污染,同時將經濟成長從工業部門轉向服務部門,以便在發生失控的經濟負成長之前將全球經濟引導進入一個較少消耗而可永續的穩定狀態(sustainable steady state)。
然而,羅馬俱樂部與麻省理工學院團隊的建議很快地被管理學界和經濟學者斥為謬誤,而置之不理。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Robert M. Solow批評《成長的極限》引用的原始數據錯誤,並把他在1972年度的Richard T. Ely 講座用來駁斥這本書的預測。許多經濟學者也相繼加入批評的行列。然而2008年和2009年的兩份研究報告卻發現:儘管《成長的極限》引用的數據有些錯誤,但是過去30年來全球的實際發展過程卻跟該書的預測高度吻合。此外,《成長的極限》的原作者在2005年將所有數據更新後,再度檢驗他們的模擬結果,發現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已經比地球所能承載的極限超出20%;如果人類繼續目前的發展模式,全球每人可分配到的糧食將在2030年左右開始急速下降,全球海洋魚類的繁殖系統將在2048年崩潰,2050年之前將有70億以上的人口水資源匱乏,而人均工業產值也將在2040年左右開始下降。
由於氣候暖化的效應已經一一浮現,包括全球各地冰河退縮,南北極冰層變薄,冰山融化,地球確實已經不堪負荷,而極端化氣候更造成歐美各國天怒民怨的各種天災,未曾有一年中斷。因此,國際減碳公約的協商雖然困難重重,但是通過新一波減碳公約的壓力卻也愈來愈大。
美國的經濟學家一再保證市場機制和技術革新會解決一切問題,而且只有通過全球財富的不斷擴張才有機會解決貧窮的問題,而放任的市場機制則是財富累積速度最快的管道。但是新的經濟學研究卻顯示:市場與科技的創新不會自動解決有限資源的問題──技術革新的結果雖然可以使能源與物資的利用更經濟,但是也會使各種產品的價格變得更低廉而刺激更多的消費,最後的總結果是「科技愈進步,所消耗的總資源也愈多」。此外,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放任的市場機制不但無法解決貧窮的問題,還使貧富差距劇烈擴張,失業率上升,而溫室效應所引起的災難一天比一天嚴重。由於經濟發展的果實集中於少數人而災難卻降臨於絕大多數人,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人已經覺悟:經濟愈發展,生活品質愈差。因此,愈來愈多學者主張要另闢蹊徑,以便達成可永續的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通往可永續發展的手段包括:將企業的環境成本內部化,把對能源的補貼改為對就業與環境的補貼,減少營利導向的市場經濟並擴張政府部門的教育與醫療服務以提供非營利導向的就業機會,減少工時以促進普遍就業,以及對跨國公司、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進行管控,使它們的經營目標符合社會與環境正義。甚至有愈來愈多的著名的經濟學家加入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生態經濟學」(ecological economics),主張經濟發展必須被控制在生態系統可以支持的規模之內,而經濟規模超過國內生態系統負擔極限的國家則應該要通過逆成長(degrowth)來降低經濟規模,以便進入一個可永續的「穩態經濟」(steady-state economy)。
不管是訴求較溫和的可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或者訴求較激烈的逆成長(degrowth),都要求政府在財富重分配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擴大政府的服務範圍,把更多的資本交給政府以便讓資本利得可以更公平地分配給所有的人,甚至是以經濟弱勢為先地進行分配;此外,政府必須更有效地監管市場經濟的運作,以避免不公平的競爭與壟斷;而媒體的效能也必須更加發達,以便讓政府的作為徹底透明化,藉此強化政府效能、避免官商勾結與貪污、舞弊。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巨大改革。
然而,過去十數年來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方向卻剛好跟這些大方向背道而馳:因為厭惡國民黨長期的貪腐政權,2000年綠營政府在國人的期待中上任,卻利用八年時間賤賣國產,在產業政策上與稅賦政策上承繼前朝的劫貧濟富,使得GDP的成長歸於富人,而受薪階級的實質所得卻持續下降。2008年政權更易,但是劫貧濟富的政策不變,媒體甘願繼續作當權者的佞臣,以八卦、虛假、扭曲的報導與評論煽動視聽、製造對立、湮滅事實。
除非我們能夠在 peak oil 降臨之前徹底改變這一切的惡習,台灣將危如累卵。即使 peak oil 不發生,一旦少子化的問題一天天嚴重下去而導致台灣人均所得逐年下降,台灣還是有機會發生社會的動亂,乃至於像茉莉革命那樣的流血事件。(待續)結語
政府偏厚園區產業而罔顧中小企業,「劫貧濟富」的政策不僅表現在租稅減免,大學與工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受惠者也是園區產業。因此,肥者愈肥而瘦者愈瘦。園區產業早就自立有餘還可以回饋社會,卻繼續享受政府的重複補貼;中小企業亟需政府挹注資源來升級,卻被政府漠視而無力升級、轉型。然後,為了怕這些中小企業倒閉而引起高失業率,政府就縱容他們壓低工作條件(超時上班不加薪、無薪假、沒有福利制度的派遣員工)。在連鎖效應下,給了其他企業一起壓低工資與工作條件的機會;最後政府還被企業主勒索,降低稅賦,然後反過來叫生活艱困的受薪階級負擔73%的所得稅。
歷經長期劫貧濟富的產業與賦稅制度,過去十年來台灣所得最低的20%一直處於負儲蓄。如果政府繼續既往的劫貧濟富政策,等願意燒炭自殺或過勞死的人都死光了之後,剩下的人不會暴動嗎?
很多人誤以為茉莉革命是為了反抗獨裁,而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所以不會有茉莉革命。這是典型的胡亂歸因,跟「腐肉生蛆」一樣地不明究理。
只要日子過得好,誰在乎是民主或獨裁?蔣經國也是獨裁,但當時有多少人巴望他長命百歲?阿根廷前總統裴隆(Juan Domingo Peron,1895-1974)在近乎獨裁的9年執政期間徹底搞垮了阿根廷的經濟,但是他任內胡亂調漲工資來討好選民,所以被迫流亡海外期間照樣深得民心,繼任的總統都是他的人。
獨裁不是問題,民不聊生才是問題。茉莉革命的地區都是長期以來糧價飆漲而工資不漲,以致於最低所得的廣大群眾無以維生,才會導致革命。但是,當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都已充滿貪腐、無能與劫貧濟富的作為,而媒體卻又慣於傳播不公不義的論述時,即使革命也解決不了積累數十年的陳疾。
2011年初埃及的茉莉革命推翻了獨裁的穆巴拉克,死傷無數;但糧食生產與產業、經濟結構的崩廢已經無人能治,官商勾結與貧富懸殊的社會機制也已經病入膏肓。革命群眾與接掌政權的軍方政府歷經十數次的抗爭、衝突與鎮壓,死傷無數,終於在2011年底再度爆發「二度革命」,造成數千人的死傷。
埃及歷經兩次革命也解決不了問題,如果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未來,今天起我們就必需開始全面性地進行變革!而且,這些轉變必須在2020以前完成,才能將未來的衝擊與傷亡降到最低。這是極為嚴峻的挑戰──不是2020才開始的挑戰,而是現在開始都已經太晚的挑戰。譬如,如果在peak oil 之後維持一個有效的交通系統,就要建立一套以電力驅動的公共運輸系統來取代80%的私人運輸;為了要建立這一套運輸系統,將必需要徵收土地來搭建軌道,從擬計畫、編預算、立法院通過相關法令與預算、到土地整備、招標、施工等,至少要花10~20年才能完成。
如果2012年上任的總統沒有能力在2016年以前完成二分之一以上的政治、經濟、交通、能源與產業結構變革,2016年上任的總統將更加沒有機會完成這個挑戰。這本書後繼所有的篇幅將會進一步提供所有的證據,讓讀者相信以上論述證據確鑿,絕非空穴來風。(待續)【跨世代的志業與共業】
三、四年級的這一代跟著上一代度過台灣戰爭前後最窮困的年代,省吃儉用地輸出血汗、輸入污染而創造出「台灣奇蹟」。到了該含飴弄孫的晚年,卻發現下一代的未來更暗淡,許多年輕人失業、超時加班到過勞死、不敢結婚育子。這樣的晚景,絕對不是我們兩代茹苦含辛的目的!
不管 peak oil 什麼時候會降臨,或者會不會降臨,政府的首要任務都應該是救窮,因為只要所得最低的20%生活無憂,其他人的日子也就都無須過慮。但是台灣的政府卻畏於承擔社會福利與財富重分配的責任,而形同「有權無責」。
2011年台灣的人均GDP為35,227美元,位居全球第20名,高於英國的34,920美元、法國的34,077美元、芬蘭的34,585美元和日本的33,805美元,而略低於德國的36,033美元和丹麥的36,450美元。以人均實質購買力算,2010年台灣約82,000美元,位居全球第18、19名之間,甚至高於荷蘭的68,000美元和瑞典的35,500美元。但是,台灣的貧富差距遠高於北歐國家而接近西歐國家,而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嚴重匱乏,政府部門服務範圍與品質屈居全球各國排名之末而接近第三世界國家。
乍看之下,台灣像是先進國家的人均產值,搭配著落後國家的政府效能和服務品質。實際上,亮麗的人均產值是靠著超時加班與過勞死硬撐出來的;此外,「人均產值 35,227美元」所創造的財富高度集中到最富有的10%人手中,其他90%的人大部份是看得到而吃不到的!難怪台灣的人均產值接近丹麥、瑞典和芬蘭,失業率只有5.2%,國人還是處於嚴重的不安之中,看不到未來!
而這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兩個關鍵性的源頭:從政治、經濟、產業到學術,我們都一直盲從美國的軌範,而沒有看見台灣跟美國之間對比懸殊的差異,也不曾意識到台灣必須要有適合自己的社會發展目標;其次,藍綠兩黨都在產業與財經政策上偏袒富人,劫貧濟富,而完全沒有擔負起政府在保障勞動條件、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上最起碼的責任,任令窮苦的人被剝削而陷入卡債、過勞死與燒炭自殺。
面對這樣不公不義的社會,我們可以花一、兩個世代的心力來改變它,以便留給後代子孫更好的社會;或者讓它沿著過去的軌跡繼續惡化下去。一個社會是好是壞,由她所有成員的行為來集聚而成──我們必須要決定為下一代的幸福而一起建立起一個更好的社會,或者留給下一代一個不適合人居住的社會。
如果願意為了子孫的幸福而棄而不捨地繼續為台灣付出,那麼這份志業必須始於一個務實可行的遠景──它必須符合台灣的先天條件,而且它必須值得我們一起為它而共同努力!(待續)2020 台灣的社會發展願景
過去在兩蔣的反共思想洗腦、美國新聞處的宣傳與大量留美學人的倡導下,台灣把發生在美國的一切都視為「先進的、正確的」,同時把一切跟美國不相同的都視為「落伍的、錯誤的」。當我們說「歐美先進國家」時,從來都不知道一個簡單的事實:歐陸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產業與社會發展目標截然不同於美國,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看不起美國,甚至連英國都還有許多知識分子不認同美國、看不起美國!我們更少去思索一個更簡單而根本的問題:台灣人口少、國內市場小,天然資源遠不如美國豐富,我們是應該學習國情跟我們更相似的歐陸國家?還是應該模仿國情跟我們迥異的美國?
其實,到過歐洲和美國旅遊的人都有機會發現:不管是生活步調的優閒、建築景觀與藝術文化的表現、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或者財富分配的公平性,歐陸國家都遠比美國更值得我們羨慕!
即使不去談大家較熟悉與羨慕的北歐,荷蘭也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人認真了解與學習的國家。她的人口約1,678萬人,人口密度只小於全球九個主權國家,因此土地與資源匱乏的壓力接近台灣。但是,荷蘭人均國民所得40,765美元,接近美國而遠高於德、英、法和加拿大;而反應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卻僅有0.31,遠低於美國的0.41和英國的0.36,在西歐國家中僅遜於德國的0.28。此外,荷蘭的稅收佔GDP的39%,而政府支出佔GDP的51.4%,但她的失業率卻只有4.3%,遠低於英、美、德、法等先進國家,甚至還低於台灣的5.2%!這個成就使得荷蘭被稱為福利國家中的「荷蘭奇蹟」。
自從美國政治學者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以《拆散福利國家: 雷根、柴契爾和緊縮政治學》一書來為雷根與柴契爾的無情手腕喝采後,許多英語世界的學者相率跟進而預言福利國家遲早會破產,台灣也就跟著一面倒地認定「同情弱勢會拖垮國家財政,禍留子孫」! 但是荷蘭與丹麥卻都相繼打破這個斷言。
荷蘭和德國都是「組合主義福利國家」(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的典型,他們都有強而有力的全國性工會與地方性工會,足以代表全國勞工跟全國資方代表進行理性而互利的制度性協商,以便因應時局而商討出最適合彼此主觀意願和當下外在客觀形勢的勞動條件,以及生產單位的經營、管理與人事制度。政黨有時候參與協商,有時候直接把勞資雙方的協議落實為政策或立法。在這個高度協商、合作的制度與文化裡,勞、資團體代表雖然有不同的立場與關切,但是都可以跳脫私人利益、個人恩怨以及勞資雙方的相互猜忌或彼此傾軋,在利益共享與共體時艱的高度社會共識下,較客觀地尋找勞方與資方的最佳折衝與利益整合,從而脫離福利國家「永久性緊縮」(permanent austerity)的魔咒。譬如,面對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張危機,他們採取的是延長退休年齡、減輕保費負擔,以及勞動條件彈性化等措施,而不是沒有配套地降低工資、以國家力量壓迫勞工團體、國營事業私有化等粗暴的舉動。
荷蘭也曾經歷過福利國家的夢靨: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期間,荷蘭的經濟成長明顯減緩且失業率漸漸升高,但社會福利支出卻仍持續成長;至1980年代仍未好轉,超過25%的勞動力都處於失業或待業的狀態,以致於社會救濟福利支出消耗了GDP 的26.7%。這種「無需工作就可享受社會福利」(welfare without work)的制度注定會吃垮國家,因而一度被稱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但是在歷經1980年代一系列的勞資協商與立法後,勞工接受薪資凍結與工作契約彈性化的資方訴求,以增進業者的國際競爭力;而資方則用減少工時來促進就業,並改善部份工時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來回應勞方的訴求;政府則對勞工給予部份社會福利保障以救濟其損失,並對僱用長期失業者的雇主給予租稅獎勵。在勞、資與政黨三方合作下,荷蘭經濟重新成長、失業率逐年下降,國家支付社會福利安全體系經費的能力也持續上升,而被稱譽為為「荷蘭奇蹟」。
其他歐陸傳統福利國家無法順利脫離福利國家困境,而荷蘭卻能,關鍵因素在於荷蘭能夠跳脫其他國家的僵滯制度與勞資對抗,針對新的世界形勢,在勞、資與政黨三方面成功地建立新的共識,調整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的結構與理念,使它具有適應新局勢的彈性。
這樣一種社會共識的建構過程和財富與義務的分配模式,遠比美國或英國任令資方踐踏勞方的方式更人性化,也更值得台灣去追求!何況,作為一個人口僅2,300萬人的蕞爾小國,並有著熱情而體卹窮苦者的傳統,台灣遠比人口眾多而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更有本錢發展荷蘭式的「組合主義社會福利」!(待續)一份跨世代的志業
一個「可永續的福利國家」雖然是很難達成的目標,卻是我們能留給後代的最佳禮物。假如我們不去追求「可永續的台灣福利社會」,我實在再也想不出來有什麼可以用來標示「社會發展」或「進步」的了。
台灣的主流經濟論述一再強調「市場比較有效率」,卻看不見一個最簡單的事實:以今天台灣與全球自動化程度之普遍,以及全球物資供應的充分程度,我們的生產效率已經高到「能消耗的量遠低於充分就業所能產出的量」,因此只好選擇大家一起減少工時(在產能不變的條件下促進就業),或者讓一部份競爭力較弱的人失業而製造社會的不安。其實「生產效率」本身已經是個問題的製造者,而不該再被盲目地追求──如果我們沒有能力通過協調與溝通來一起降低工時,就必需一起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而彼此傾軋,使得有工作的人都要超時加班(因而就業機會更少、競爭更激烈),而沒有時間過正常的人的生活(男性與女性各在最適婚與最適合育子的年齡結婚生子)。
何況,放任式的市場機制根本就不是刺激景氣與促進就業的有效解方:英美國債分別為GDP的79.5%和69.4%,而失業率分別為7.9%與9.6%;但是荷蘭和丹麥國債分別為GDP的64.4%與46.9%,而失業率分別為4.3%和7.2%,表現遠比英美兩國亮麗;其他北歐福利國家的國債都少於GDP的49%,而失業率則在3.6%和8.4%之間,總體表現優於美國;即使是德國和法國,國債分別為GDP的81.5%和85.5%,而失業率分別為6.8%與9.3%,表現也不遜於英美兩國。
但是,如果我們提議要全國一起降低工時,台灣的主流經濟論述又會再強調「國際競爭」。其實,如果資方願意通過協商同步降低資本利得,而勞方(含管理階層)也願意通過協商同步降低工時與工資,則台灣的產品在價格上就照樣會具有國際競爭力。由於高所得國家的貧富感受主要是來自於國內不同職業、階層相對收入的變化,而非絕對收入的變化,因此在前述資本利得與薪資一起調降的過程中大家的相對貧富感沒有變,但卻既可以促進就業,又可以增加休閒時間,大大地改善全國每一個人實際上的生活品質。
其實,對於像台灣這樣一個人均所得超過三萬美元的國家而言,生活的品質與幸福感主要地是來自於工作時間、休閒時間與家庭時間的合理化分配,工作權的保障,以及通過社會集體保險來一起控管未來的風險(社會安全體系與社會福利體系的建立與改良),而非人均所得的增減。因此,真正值得所有台灣人努力的目標,應該是對「可永續的台灣福利社會」達成普遍的社會共識與適合台灣國情的制度性設計,以便留給子孫一個人人安心、有人味而又有品質的生活;否則,如果每一個人都繼續只顧自己而不願意去凝聚社會共識,最後一定是所有的人都沒有安全感,所有的人都過勞死而不得休息!這將會是一個我們最不想留給子孫的共業!
但是,社會共識與制度性設計絕對無法抄襲自國外,而必須根據台灣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特殊性,以及其天然資源與國際相對競爭優勢來設計。因此,如何釐清「可永續的福利國家」所涉及的問題面向,要經由怎樣的溝通過程才能達成普遍而有效的共識,以及如何將這些共識具體化為可實踐的制度,都考驗著全國學術界、政黨、民間團體,以及願意參與公共事務的選民共同的智慧。
與其去追逐荒誕無聊的「世界一流大學」,不如將資源與心力用來探索、追求、營建一個「可永續的福利國家」!
建立一個福利國家所需要的創意和過程的艱困,絕對遠遠超過建立一個用錢堆砌出來的「一流大學」:如果欠缺有效的勞資協商機制,福利國家很容易會發展出勞資的對抗,而把該用來生產或休閒的心力與時間浪費在罷工和抗爭上;此外,如果沒有夠透明的媒體監督與夠普及的公眾參予,福利國家的國家資源很容易會被浪費在官商勾結與劫貧濟富的各種勾當裡。因此,在建立福利國家的共識與制度之前,我們必須先要讓媒體健全地發展,並且發展出全民普遍參予的公民社會,從而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出資方與勞方各自的組織與全國性代表,作為未來與政黨進行全國性協商時的有效機構。
對於解嚴時間有限而政黨輪替極端不順利的台灣而言,連公眾參與都推動困難,更難在這個階段奢談「公民社會」的理想。如果我們再看看歷來政府的顢頇、無能與劫貧濟富,以及低能的媒體和自甘被媒體愚弄的群眾,「公民社會」與「永續福利國」的期待將會顯得更加天真。
但是,這是唯一值得我們努力的路,因為放任式的市場機制絕對不會是有效的解方。(待續)社會進步的力量
堅持主張讓自由市場管理社會一切運作的人經常威脅我們:我們授予政府的資源幾乎都會被用來進行無效率的浪費與舞弊,遠不如讓市場管理它自己(以及我們所有的人)。
從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開始,粗通政治或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官商勾結的誘因無所不在。解決貪腐的典型辦法有兩種:縮小政府經費與權責,或者擴大媒體與公民監督的機制。
縮小政府經費與權責其實於事無補,因為官商勾結的主要管道在於無法縮編的政府權力,而非政府經費。美國與台灣的高速公路網路之所以發達,主要不是因為這樣比較節能或方便,而是因為每個高速公路出口都是炒作房地產的好議題;台灣各個地方政府爭相要求設立大學與科學園區,主要的不是為了促進在地的產業發展與教育,而是可以炒作園區外和大學周圍的房地產。但是,我們真的要把教育、產業政策與交通全部交給市場去管理嗎?
另一個選項是強化媒體監督與公民參與,這是建立福利國家的先決條件,也是建立福利國家之前的社會基礎工程。如果媒體監督與公民參與的機制夠健全,我們可以用公有民營的方式提昇國營事業的績效,也可以用績效獎金乃至於紅利提升公務員的效率。即使最後政府效率仍舊低於私人企業,我們還是得要記得:私人企業的績效提升主要是在增加大老板與大股東的資產,對於其他90%的受薪者而言,可能是弊多於利!
對於資源貧乏的國家而言,本來就應該盡量共享資源,一起承擔風險,才能讓所有的人在合理的貧富差距下安居樂業。但是,要安居樂業,我們就必須要先學會公共參與和公共管理。
民主本來就是一個「棒打老虎,雞吃蟲」的制衡遊戲,只有通過透明的媒體訊息,選民才有辦法知道哪個政黨或候選人比較符合自己的期待,並且在選舉的時刻裡以選票對政黨或候選人進行獎懲,從而促進政治的良性競爭與良性循環。然而台灣的主流媒體已經嚴重地被庸俗化與政黨化,電視成為藍營與綠營操弄群眾、製造對立的工具,連報紙也充滿置入性行銷,使得民眾經常分不清楚事實是什麼,更遑論在選舉的關鍵時刻裡以選票促進政治的良性競爭。
面對被癱瘓的媒體和長期被愚弄的80%以上選民,「強化媒體監督與公民參與」幾乎是不可能的社會改造工程。面對這艱難的挑戰,我們可以做的第一步是什麼?我過去在演講中一再被問到類似的問題,而我總是回答:「設法瞭解台灣真實的處境、挑戰、危機與轉機,也設法從國外的案例裡了解台灣可以有多少種真實的選擇,然後把妳知道與相信的事實告訴身邊的人」。這回答讓很多人不滿意,總期待著有更好、更速成的答案。但是,我在十幾年的社會改革運動過程中一再受挫而自省,也一再去翻閱過去歐洲社會改革運動的相關典籍來瞭解社會進步(與挫折)的真實過程與各種力量。最後我所能相信的力量只有一種:覺醒的人有幾個,社會就有多少進步的力量。
「進步的力量」永遠是從社會上的少數(甚至極少數)人開始,他們所能倚靠的是認知、覺醒,與散播他們的認知和覺醒。表面上這樣做好像成效難彰,緩不濟急,但它們確實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婦女運動與環境運動就是典型的案例。
西歐與北歐國家的社會進步也是始於個人卑微的行動──1848年的原始共產黨員人數稀少,甚至還遠比今天劍橋、牛津、哈佛的博士更稀有;他們能力傑出,犧牲的熱情罕有人能及,人格與道德特質出眾,而且往往有貴族的身份;但是他們做什麼事來改變社會?他們到礦場去當礦工,利用休息時間教礦工寫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感受到自己不再是沒有名姓的「群眾」(the mass),而是「約翰兄弟」、「瑪莉姐妹」,是跟他們的地主一樣地有靈魂,有尊嚴、有獨立人格的人。
如果他們願意從這麼卑微的事做起,我們是否也願意從最踏實而看似卑微的事做起?社會改革運動基本上是一種價值觀的戰爭,也是一種對於「更好的社會」的務實追求與摸索。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種更好而現實上又可行的社會遠景,就有機會說服別人為這樣的社會而一起努力。
一個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對於「如何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都多多少少有一點認知,這些認知的總和加起來就是社會進步的程度。一個社會裡這些認知的總和量愈大,愈有機會提出較好的社會發展遠景,以及就此遠景達成共識。
這些認知也使得她的成員有機會脫離媒體的愚弄與置入性行銷,以及政黨的搬弄是非與煽動群眾,並且使得愈來愈多的人有能力監督政黨與政府,甚至對政黨與政府施壓,使他們朝著集體意志所要求的方向前進。
因此,要改變台灣看起來是很難,但具體能做的事卻很清楚:先增加你的認知,再把你的認知擴散出去!
結語
為了減緩peak oil 的衝擊,未來十年我們必需完成一系列的變革,包含糧食自給率的提升與生產方式的變革、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發展、綠能產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稅賦制度的公平化與合理化、隱藏性國債的處理以及政府資本的累積、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以及最高工時的規範、立法與落實。只有同時把這些問題一起作完整的配套解決,才有機會將少子化與peak oil的衝擊降到最低。
然而,為了要讓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能有效地運作,我們必須要建立良好的社會共識與勞、資、政黨協商機制和互信基礎。
其實,要認真做好這些事,十年根本就不夠!但是,我們距離peak oil 的降臨也許甚至連十年都不到。
如果你跟我一樣地相信這是台灣必須要面對的現實,讓我們一起來把這個聲音傳出去,直到2012年上任的總統和內閣願意面對事實,開始積極謀思對策,並嘗試著建立社會的共識為止!
台灣將會在2020年遭遇到極為嚴峻的挑戰,如果我們的現行政策或思維模式不變,將會在糧食上無以自足,經濟上經歷數十年的持續衰退與大蕭條,不但實質所得有可能會在2035年降低到僅剩今天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而且會有飆漲的失業率和貧窮人口數,以致於經濟、社會與政治都濱於崩解的邊緣。
把台灣推往這絕境的力量主要有四個:(1)少子化的危機將會使得人均所得持續下降並埋下失業潮的危機──2025年起每兩個上班的人要扶養一個老人或小孩(扶養比約50%),2055年時每一個上班的人要撫養0.9個老人和小孩,經濟負擔將愈來愈吃重;2060年時老年人口將是幼年人口的四倍,幼教機構將大幅消失,老人照護產業需求遽增,國內產業需要在50年內天翻地覆地大風吹,來不及調整的企業將倒閉或經營困難。(2)全球石油產能很可能會在2015年之前跨越最高點而開始下降,這現象被英語世界稱為「peak oil」;而牛津大學預測2023年時全球石油供給量將僅及需求的一半,使油價上看每桶200~500美元,導致越洋貿易萎縮而全球GDP持續下降數十年,也使得大陸和亞洲成為台灣主要貿易伙伴。(3)油價高漲,使得穀物提煉生質燃料有利可圖,歐美出口的糧食將銳減,而亞洲在肥料與糧食生產上都無法自給自足,使得糧食自給率僅32%的台灣面臨缺糧的危機。(4)既有產業政策仰賴「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高工時與低毛利」的「血汗工廠」競爭模式,未來在油、電、糧與工資四漲且代工產業萎縮的情況下,許多企業將倒閉,而引起失業潮。(5)加入WTO後被迫金融自由化,加上兩岸競爭,使得財團有本錢恐嚇政府,要求政府降低稅收,進行各種補助,而導致政府負債急遽擴大,而沒有能力在失業潮中對難以為生的人伸出援手。
如果我們想要擺脫上述窘境,就必須在未來十年內完成以下變革:(1)改變糧食生產方式,逐漸擺脫對石油、化肥與農藥的倚賴,發展出適合亞熱帶模式的高產能農、魚、牧整合的生產系統;(2)發展綠能產業與公共運輸,減少私人車輛,以降低對能源的需求;(3)徹底改變台灣的產業結構,減少對代工產業的倚賴,協助中小企業技術升級,往「低污染、低耗能、低耗水、高毛利與合理工時」的方向發展;(4)以亞洲為市場,強化金融、商業資訊服務、軟體、文化創意產業與品牌等產業賺取外匯的能力,同時減少經濟與貿易上對大陸的過度倚賴;(5)停止劫貧濟富的稅制與產業補貼,提高資本利得稅與富人稅,以便降低國債與隱藏性債務,並且讓政府有足夠的稅收強化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的職能,以便在GDP下降與失業率上升的過程中扶助弱勢,避免造成嚴重的社會失序與流血衝突。
由於沒有看到未來潛在的危機,政府施政一向只顧富人的需要而任由窮苦的人流浪街頭,甚至過勞死、燒炭自殺。但是,茉莉革命告訴我們一個教訓:如果一個社會不能讓最弱勢的20%人口活下去,他們將會被迫以極端的手段爭生存權,那時候富人不但無法安居樂業,經濟也會在動盪不安中無法持續運轉。
這一切並非杞人憂天,也非恫嚇之言。少子化的危機已經變成無法逆轉的事實,而全球能源供不應求的日子也即將來臨!(待續)從無稽之談到無法逃避的事實
很多人誤以為要到石油枯竭才會有石油危機,其實只要石油產能開始下跌,供不應求的危機就已經開始並逐漸惡化,使得油價與失業率持續飆漲。很多人老早就知道,遲早有一天地球上的石油會供不應求;但是很少人會想到:它有可能會在四年內發生。
經濟學家一直主張:不需要擔心能源與礦產耗竭的問題,那些都是無稽之談──在能源與礦產耗竭之前,市場機制會使得逐漸稀有的能源與物資價格上漲,因而帶動資金進入可以產出科技革命的相關產業,從而引發破壞性的創造,產出節能的商品、替代性能源、替代性材料,以及商品的回收再利用。因此,一切問題都會在市場機制和科技創新的力量下自動地被解決,無須杞人憂天。
經濟學家的樂觀態度隱藏著兩個他們沒有自覺到的假設:市場萬能以及科學萬能。但這兩個假設並非永遠會實現!
有人問過我:綠色革命曾經化解了人類的糧食危機,為什麼我沒想到科學將會化解能源與糧食的危機?問題不是「會不會」,而是「來不來得及」。綠色革命「及時」挽救了人類的危機,這是歷史上罕見的例外,而非常態。科學的進展速度無法預測,也不一定正比於資金的投入──我們等待氫融合的乾淨電能已經60年了,歐陸最權威的專家卻說我們至少還需要再等40年;中國歷代的皇帝投入無數的資源想要研發長生不老的藥,結果卻往往短命而死。
許多石油專家都預測peak oil(石油跨越最高產能)很可能會在2020年之前發生,而且大部分的預測都落在2010年到2014年之間。接著,天然氣會在10年後跟著跨越產能極限,使得運輸工具的燃料開始供不應求。假如2023年時全球原油供給量只剩需求量的一半,今天的石油用戶之中將有一半的人會因為負擔不起高油價而退出消費市場,其中很可能包括糧食與肥料的運洋貿易,以及利潤低微的越洋產業代工。
儘管經濟學家一再保證新興能源最後會取代石化能源,很不幸地,這些替代能源的發展速度卻太慢,很可能來不及填補 peak oil 所造成的能源缺口。
纖維素酒精將是石油的最佳替代品,但是成本太高而發展速度太慢,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將2011年纖維酒精的法定產量削減為原來的1%~3%。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第一優先用途是替代石化燃料的火力發電,發電量有餘時才可以用來製造氫氣,作為替代性燃料;然而風力發電能量規模有限,而太陽能發電成本太高。審慎的估計認為2050年時太陽能將只佔全美發電總量的69%與總能量的35%,並且在2100年才達到全美總能量需求的92%。因此,從成本因素考量,在2100年之前很難期待用風能與太陽能生產氫氣來填補 peak oil 之後的燃料缺口。
經濟學家一向期待市場機制會自動調節供需,在油價上漲的過程吸引大量資金投入新能源的開發,而促成技術的突破,最後解決能源危機。懷著這種期待的人應該要認真想一想凱因斯的名言:「在長遠的未來,我們都死了。」──問題不是科技發展與市場機制「會不會」自行解決問題,而是「來不來得及」。
石油被稱為當代社會的血液,不僅維繫著各種農業與工業的生產,也維繫著全球的運輸與貿易,以及冷暖氣與家庭用電所建構起來的舒適環境──高價的石油與石油的減產意味著許多人將必須減少生活上的舒適或者放棄它。此外,油價每上漲10%,全球平均GDP將下降0.55%,而GDP的持續下降則會造成失業率和貧窮人口數的飆升,以及政府稅收的短缺,而亞洲等仰賴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更可能會因而失控。
不幸的是,這本書所蒐集到的文獻與證據顯示:市場將無法在危機發生前搶救地球,而必須要靠所有人和政府從制度、生活習慣與觀念上進行徹底的改變,來因應這個變局──而且動作要快,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應變了。(待續)不是遲來的警告,而是持續40年的警告
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就已經委由麻省理工學院所組成的專家團隊發表了《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這本書,他們用電腦模擬做出一個預測:如果全球經濟發展模式不變,全球經濟將會因為有限能源與物資的耗竭而遭遇到經濟持續衰退,全球人均工業產值與糧食產量將會在21世紀中葉之前跨越最高峰,並迅速地歷經大蕭條而衰退到1950年代左右的水準。
在目前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市場機制中,經濟負成長無可避免地意味著經濟與社會的大災難。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充分就業是靠GDP的持續成長來維持,而GDP的成長則來自於消費的擴充。一旦可用的能源或物資減少而使消費無法擴充,GDP的成長就會趨緩;即便只是生產效率的提升速度超過GDP的成長速度,失業率都會開始上升。一旦GDP進入持續的負成長,失業率、貧窮人口數和政府債務就會失控地飆漲,以致於整個經濟系統崩潰。
為了避免這個悲劇的發生,《成長的極限》建議控制出生率與人口數,保護農地並控制環境污染,同時將經濟成長從工業部門轉向服務部門,以便在發生失控的經濟負成長之前將全球經濟引導進入一個較少消耗而可永續的穩定狀態(sustainable steady state)。
然而,羅馬俱樂部與麻省理工學院團隊的建議很快地被管理學界和經濟學者斥為謬誤,而置之不理。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Robert M. Solow批評《成長的極限》引用的原始數據錯誤,並把他在1972年度的Richard T. Ely 講座用來駁斥這本書的預測。許多經濟學者也相繼加入批評的行列。然而2008年和2009年的兩份研究報告卻發現:儘管《成長的極限》引用的數據有些錯誤,但是過去30年來全球的實際發展過程卻跟該書的預測高度吻合。此外,《成長的極限》的原作者在2005年將所有數據更新後,再度檢驗他們的模擬結果,發現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已經比地球所能承載的極限超出20%;如果人類繼續目前的發展模式,全球每人可分配到的糧食將在2030年左右開始急速下降,全球海洋魚類的繁殖系統將在2048年崩潰,2050年之前將有70億以上的人口水資源匱乏,而人均工業產值也將在2040年左右開始下降。
由於氣候暖化的效應已經一一浮現,包括全球各地冰河退縮,南北極冰層變薄,冰山融化,地球確實已經不堪負荷,而極端化氣候更造成歐美各國天怒民怨的各種天災,未曾有一年中斷。因此,國際減碳公約的協商雖然困難重重,但是通過新一波減碳公約的壓力卻也愈來愈大。
美國的經濟學家一再保證市場機制和技術革新會解決一切問題,而且只有通過全球財富的不斷擴張才有機會解決貧窮的問題,而放任的市場機制則是財富累積速度最快的管道。但是新的經濟學研究卻顯示:市場與科技的創新不會自動解決有限資源的問題──技術革新的結果雖然可以使能源與物資的利用更經濟,但是也會使各種產品的價格變得更低廉而刺激更多的消費,最後的總結果是「科技愈進步,所消耗的總資源也愈多」。此外,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放任的市場機制不但無法解決貧窮的問題,還使貧富差距劇烈擴張,失業率上升,而溫室效應所引起的災難一天比一天嚴重。由於經濟發展的果實集中於少數人而災難卻降臨於絕大多數人,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人已經覺悟:經濟愈發展,生活品質愈差。因此,愈來愈多學者主張要另闢蹊徑,以便達成可永續的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通往可永續發展的手段包括:將企業的環境成本內部化,把對能源的補貼改為對就業與環境的補貼,減少營利導向的市場經濟並擴張政府部門的教育與醫療服務以提供非營利導向的就業機會,減少工時以促進普遍就業,以及對跨國公司、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進行管控,使它們的經營目標符合社會與環境正義。甚至有愈來愈多的著名的經濟學家加入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生態經濟學」(ecological economics),主張經濟發展必須被控制在生態系統可以支持的規模之內,而經濟規模超過國內生態系統負擔極限的國家則應該要通過逆成長(degrowth)來降低經濟規模,以便進入一個可永續的「穩態經濟」(steady-state economy)。
不管是訴求較溫和的可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或者訴求較激烈的逆成長(degrowth),都要求政府在財富重分配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擴大政府的服務範圍,把更多的資本交給政府以便讓資本利得可以更公平地分配給所有的人,甚至是以經濟弱勢為先地進行分配;此外,政府必須更有效地監管市場經濟的運作,以避免不公平的競爭與壟斷;而媒體的效能也必須更加發達,以便讓政府的作為徹底透明化,藉此強化政府效能、避免官商勾結與貪污、舞弊。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巨大改革。
然而,過去十數年來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方向卻剛好跟這些大方向背道而馳:因為厭惡國民黨長期的貪腐政權,2000年綠營政府在國人的期待中上任,卻利用八年時間賤賣國產,在產業政策上與稅賦政策上承繼前朝的劫貧濟富,使得GDP的成長歸於富人,而受薪階級的實質所得卻持續下降。2008年政權更易,但是劫貧濟富的政策不變,媒體甘願繼續作當權者的佞臣,以八卦、虛假、扭曲的報導與評論煽動視聽、製造對立、湮滅事實。
除非我們能夠在 peak oil 降臨之前徹底改變這一切的惡習,台灣將危如累卵。即使 peak oil 不發生,一旦少子化的問題一天天嚴重下去而導致台灣人均所得逐年下降,台灣還是有機會發生社會的動亂,乃至於像茉莉革命那樣的流血事件。(待續)結語
政府偏厚園區產業而罔顧中小企業,「劫貧濟富」的政策不僅表現在租稅減免,大學與工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受惠者也是園區產業。因此,肥者愈肥而瘦者愈瘦。園區產業早就自立有餘還可以回饋社會,卻繼續享受政府的重複補貼;中小企業亟需政府挹注資源來升級,卻被政府漠視而無力升級、轉型。然後,為了怕這些中小企業倒閉而引起高失業率,政府就縱容他們壓低工作條件(超時上班不加薪、無薪假、沒有福利制度的派遣員工)。在連鎖效應下,給了其他企業一起壓低工資與工作條件的機會;最後政府還被企業主勒索,降低稅賦,然後反過來叫生活艱困的受薪階級負擔73%的所得稅。
歷經長期劫貧濟富的產業與賦稅制度,過去十年來台灣所得最低的20%一直處於負儲蓄。如果政府繼續既往的劫貧濟富政策,等願意燒炭自殺或過勞死的人都死光了之後,剩下的人不會暴動嗎?
很多人誤以為茉莉革命是為了反抗獨裁,而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所以不會有茉莉革命。這是典型的胡亂歸因,跟「腐肉生蛆」一樣地不明究理。
只要日子過得好,誰在乎是民主或獨裁?蔣經國也是獨裁,但當時有多少人巴望他長命百歲?阿根廷前總統裴隆(Juan Domingo Peron,1895-1974)在近乎獨裁的9年執政期間徹底搞垮了阿根廷的經濟,但是他任內胡亂調漲工資來討好選民,所以被迫流亡海外期間照樣深得民心,繼任的總統都是他的人。
獨裁不是問題,民不聊生才是問題。茉莉革命的地區都是長期以來糧價飆漲而工資不漲,以致於最低所得的廣大群眾無以維生,才會導致革命。但是,當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都已充滿貪腐、無能與劫貧濟富的作為,而媒體卻又慣於傳播不公不義的論述時,即使革命也解決不了積累數十年的陳疾。
2011年初埃及的茉莉革命推翻了獨裁的穆巴拉克,死傷無數;但糧食生產與產業、經濟結構的崩廢已經無人能治,官商勾結與貧富懸殊的社會機制也已經病入膏肓。革命群眾與接掌政權的軍方政府歷經十數次的抗爭、衝突與鎮壓,死傷無數,終於在2011年底再度爆發「二度革命」,造成數千人的死傷。
埃及歷經兩次革命也解決不了問題,如果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未來,今天起我們就必需開始全面性地進行變革!而且,這些轉變必須在2020以前完成,才能將未來的衝擊與傷亡降到最低。這是極為嚴峻的挑戰──不是2020才開始的挑戰,而是現在開始都已經太晚的挑戰。譬如,如果在peak oil 之後維持一個有效的交通系統,就要建立一套以電力驅動的公共運輸系統來取代80%的私人運輸;為了要建立這一套運輸系統,將必需要徵收土地來搭建軌道,從擬計畫、編預算、立法院通過相關法令與預算、到土地整備、招標、施工等,至少要花10~20年才能完成。
如果2012年上任的總統沒有能力在2016年以前完成二分之一以上的政治、經濟、交通、能源與產業結構變革,2016年上任的總統將更加沒有機會完成這個挑戰。這本書後繼所有的篇幅將會進一步提供所有的證據,讓讀者相信以上論述證據確鑿,絕非空穴來風。(待續)【跨世代的志業與共業】
三、四年級的這一代跟著上一代度過台灣戰爭前後最窮困的年代,省吃儉用地輸出血汗、輸入污染而創造出「台灣奇蹟」。到了該含飴弄孫的晚年,卻發現下一代的未來更暗淡,許多年輕人失業、超時加班到過勞死、不敢結婚育子。這樣的晚景,絕對不是我們兩代茹苦含辛的目的!
不管 peak oil 什麼時候會降臨,或者會不會降臨,政府的首要任務都應該是救窮,因為只要所得最低的20%生活無憂,其他人的日子也就都無須過慮。但是台灣的政府卻畏於承擔社會福利與財富重分配的責任,而形同「有權無責」。
2011年台灣的人均GDP為35,227美元,位居全球第20名,高於英國的34,920美元、法國的34,077美元、芬蘭的34,585美元和日本的33,805美元,而略低於德國的36,033美元和丹麥的36,450美元。以人均實質購買力算,2010年台灣約82,000美元,位居全球第18、19名之間,甚至高於荷蘭的68,000美元和瑞典的35,500美元。但是,台灣的貧富差距遠高於北歐國家而接近西歐國家,而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嚴重匱乏,政府部門服務範圍與品質屈居全球各國排名之末而接近第三世界國家。
乍看之下,台灣像是先進國家的人均產值,搭配著落後國家的政府效能和服務品質。實際上,亮麗的人均產值是靠著超時加班與過勞死硬撐出來的;此外,「人均產值 35,227美元」所創造的財富高度集中到最富有的10%人手中,其他90%的人大部份是看得到而吃不到的!難怪台灣的人均產值接近丹麥、瑞典和芬蘭,失業率只有5.2%,國人還是處於嚴重的不安之中,看不到未來!
而這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兩個關鍵性的源頭:從政治、經濟、產業到學術,我們都一直盲從美國的軌範,而沒有看見台灣跟美國之間對比懸殊的差異,也不曾意識到台灣必須要有適合自己的社會發展目標;其次,藍綠兩黨都在產業與財經政策上偏袒富人,劫貧濟富,而完全沒有擔負起政府在保障勞動條件、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上最起碼的責任,任令窮苦的人被剝削而陷入卡債、過勞死與燒炭自殺。
面對這樣不公不義的社會,我們可以花一、兩個世代的心力來改變它,以便留給後代子孫更好的社會;或者讓它沿著過去的軌跡繼續惡化下去。一個社會是好是壞,由她所有成員的行為來集聚而成──我們必須要決定為下一代的幸福而一起建立起一個更好的社會,或者留給下一代一個不適合人居住的社會。
如果願意為了子孫的幸福而棄而不捨地繼續為台灣付出,那麼這份志業必須始於一個務實可行的遠景──它必須符合台灣的先天條件,而且它必須值得我們一起為它而共同努力!(待續)2020 台灣的社會發展願景
過去在兩蔣的反共思想洗腦、美國新聞處的宣傳與大量留美學人的倡導下,台灣把發生在美國的一切都視為「先進的、正確的」,同時把一切跟美國不相同的都視為「落伍的、錯誤的」。當我們說「歐美先進國家」時,從來都不知道一個簡單的事實:歐陸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產業與社會發展目標截然不同於美國,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看不起美國,甚至連英國都還有許多知識分子不認同美國、看不起美國!我們更少去思索一個更簡單而根本的問題:台灣人口少、國內市場小,天然資源遠不如美國豐富,我們是應該學習國情跟我們更相似的歐陸國家?還是應該模仿國情跟我們迥異的美國?
其實,到過歐洲和美國旅遊的人都有機會發現:不管是生活步調的優閒、建築景觀與藝術文化的表現、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或者財富分配的公平性,歐陸國家都遠比美國更值得我們羨慕!
即使不去談大家較熟悉與羨慕的北歐,荷蘭也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人認真了解與學習的國家。她的人口約1,678萬人,人口密度只小於全球九個主權國家,因此土地與資源匱乏的壓力接近台灣。但是,荷蘭人均國民所得40,765美元,接近美國而遠高於德、英、法和加拿大;而反應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卻僅有0.31,遠低於美國的0.41和英國的0.36,在西歐國家中僅遜於德國的0.28。此外,荷蘭的稅收佔GDP的39%,而政府支出佔GDP的51.4%,但她的失業率卻只有4.3%,遠低於英、美、德、法等先進國家,甚至還低於台灣的5.2%!這個成就使得荷蘭被稱為福利國家中的「荷蘭奇蹟」。
自從美國政治學者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以《拆散福利國家: 雷根、柴契爾和緊縮政治學》一書來為雷根與柴契爾的無情手腕喝采後,許多英語世界的學者相率跟進而預言福利國家遲早會破產,台灣也就跟著一面倒地認定「同情弱勢會拖垮國家財政,禍留子孫」! 但是荷蘭與丹麥卻都相繼打破這個斷言。
荷蘭和德國都是「組合主義福利國家」(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的典型,他們都有強而有力的全國性工會與地方性工會,足以代表全國勞工跟全國資方代表進行理性而互利的制度性協商,以便因應時局而商討出最適合彼此主觀意願和當下外在客觀形勢的勞動條件,以及生產單位的經營、管理與人事制度。政黨有時候參與協商,有時候直接把勞資雙方的協議落實為政策或立法。在這個高度協商、合作的制度與文化裡,勞、資團體代表雖然有不同的立場與關切,但是都可以跳脫私人利益、個人恩怨以及勞資雙方的相互猜忌或彼此傾軋,在利益共享與共體時艱的高度社會共識下,較客觀地尋找勞方與資方的最佳折衝與利益整合,從而脫離福利國家「永久性緊縮」(permanent austerity)的魔咒。譬如,面對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張危機,他們採取的是延長退休年齡、減輕保費負擔,以及勞動條件彈性化等措施,而不是沒有配套地降低工資、以國家力量壓迫勞工團體、國營事業私有化等粗暴的舉動。
荷蘭也曾經歷過福利國家的夢靨: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期間,荷蘭的經濟成長明顯減緩且失業率漸漸升高,但社會福利支出卻仍持續成長;至1980年代仍未好轉,超過25%的勞動力都處於失業或待業的狀態,以致於社會救濟福利支出消耗了GDP 的26.7%。這種「無需工作就可享受社會福利」(welfare without work)的制度注定會吃垮國家,因而一度被稱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但是在歷經1980年代一系列的勞資協商與立法後,勞工接受薪資凍結與工作契約彈性化的資方訴求,以增進業者的國際競爭力;而資方則用減少工時來促進就業,並改善部份工時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來回應勞方的訴求;政府則對勞工給予部份社會福利保障以救濟其損失,並對僱用長期失業者的雇主給予租稅獎勵。在勞、資與政黨三方合作下,荷蘭經濟重新成長、失業率逐年下降,國家支付社會福利安全體系經費的能力也持續上升,而被稱譽為為「荷蘭奇蹟」。
其他歐陸傳統福利國家無法順利脫離福利國家困境,而荷蘭卻能,關鍵因素在於荷蘭能夠跳脫其他國家的僵滯制度與勞資對抗,針對新的世界形勢,在勞、資與政黨三方面成功地建立新的共識,調整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的結構與理念,使它具有適應新局勢的彈性。
這樣一種社會共識的建構過程和財富與義務的分配模式,遠比美國或英國任令資方踐踏勞方的方式更人性化,也更值得台灣去追求!何況,作為一個人口僅2,300萬人的蕞爾小國,並有著熱情而體卹窮苦者的傳統,台灣遠比人口眾多而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更有本錢發展荷蘭式的「組合主義社會福利」!(待續)一份跨世代的志業
一個「可永續的福利國家」雖然是很難達成的目標,卻是我們能留給後代的最佳禮物。假如我們不去追求「可永續的台灣福利社會」,我實在再也想不出來有什麼可以用來標示「社會發展」或「進步」的了。
台灣的主流經濟論述一再強調「市場比較有效率」,卻看不見一個最簡單的事實:以今天台灣與全球自動化程度之普遍,以及全球物資供應的充分程度,我們的生產效率已經高到「能消耗的量遠低於充分就業所能產出的量」,因此只好選擇大家一起減少工時(在產能不變的條件下促進就業),或者讓一部份競爭力較弱的人失業而製造社會的不安。其實「生產效率」本身已經是個問題的製造者,而不該再被盲目地追求──如果我們沒有能力通過協調與溝通來一起降低工時,就必需一起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而彼此傾軋,使得有工作的人都要超時加班(因而就業機會更少、競爭更激烈),而沒有時間過正常的人的生活(男性與女性各在最適婚與最適合育子的年齡結婚生子)。
何況,放任式的市場機制根本就不是刺激景氣與促進就業的有效解方:英美國債分別為GDP的79.5%和69.4%,而失業率分別為7.9%與9.6%;但是荷蘭和丹麥國債分別為GDP的64.4%與46.9%,而失業率分別為4.3%和7.2%,表現遠比英美兩國亮麗;其他北歐福利國家的國債都少於GDP的49%,而失業率則在3.6%和8.4%之間,總體表現優於美國;即使是德國和法國,國債分別為GDP的81.5%和85.5%,而失業率分別為6.8%與9.3%,表現也不遜於英美兩國。
但是,如果我們提議要全國一起降低工時,台灣的主流經濟論述又會再強調「國際競爭」。其實,如果資方願意通過協商同步降低資本利得,而勞方(含管理階層)也願意通過協商同步降低工時與工資,則台灣的產品在價格上就照樣會具有國際競爭力。由於高所得國家的貧富感受主要是來自於國內不同職業、階層相對收入的變化,而非絕對收入的變化,因此在前述資本利得與薪資一起調降的過程中大家的相對貧富感沒有變,但卻既可以促進就業,又可以增加休閒時間,大大地改善全國每一個人實際上的生活品質。
其實,對於像台灣這樣一個人均所得超過三萬美元的國家而言,生活的品質與幸福感主要地是來自於工作時間、休閒時間與家庭時間的合理化分配,工作權的保障,以及通過社會集體保險來一起控管未來的風險(社會安全體系與社會福利體系的建立與改良),而非人均所得的增減。因此,真正值得所有台灣人努力的目標,應該是對「可永續的台灣福利社會」達成普遍的社會共識與適合台灣國情的制度性設計,以便留給子孫一個人人安心、有人味而又有品質的生活;否則,如果每一個人都繼續只顧自己而不願意去凝聚社會共識,最後一定是所有的人都沒有安全感,所有的人都過勞死而不得休息!這將會是一個我們最不想留給子孫的共業!
但是,社會共識與制度性設計絕對無法抄襲自國外,而必須根據台灣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特殊性,以及其天然資源與國際相對競爭優勢來設計。因此,如何釐清「可永續的福利國家」所涉及的問題面向,要經由怎樣的溝通過程才能達成普遍而有效的共識,以及如何將這些共識具體化為可實踐的制度,都考驗著全國學術界、政黨、民間團體,以及願意參與公共事務的選民共同的智慧。
與其去追逐荒誕無聊的「世界一流大學」,不如將資源與心力用來探索、追求、營建一個「可永續的福利國家」!
建立一個福利國家所需要的創意和過程的艱困,絕對遠遠超過建立一個用錢堆砌出來的「一流大學」:如果欠缺有效的勞資協商機制,福利國家很容易會發展出勞資的對抗,而把該用來生產或休閒的心力與時間浪費在罷工和抗爭上;此外,如果沒有夠透明的媒體監督與夠普及的公眾參予,福利國家的國家資源很容易會被浪費在官商勾結與劫貧濟富的各種勾當裡。因此,在建立福利國家的共識與制度之前,我們必須先要讓媒體健全地發展,並且發展出全民普遍參予的公民社會,從而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出資方與勞方各自的組織與全國性代表,作為未來與政黨進行全國性協商時的有效機構。
對於解嚴時間有限而政黨輪替極端不順利的台灣而言,連公眾參與都推動困難,更難在這個階段奢談「公民社會」的理想。如果我們再看看歷來政府的顢頇、無能與劫貧濟富,以及低能的媒體和自甘被媒體愚弄的群眾,「公民社會」與「永續福利國」的期待將會顯得更加天真。
但是,這是唯一值得我們努力的路,因為放任式的市場機制絕對不會是有效的解方。(待續)社會進步的力量
堅持主張讓自由市場管理社會一切運作的人經常威脅我們:我們授予政府的資源幾乎都會被用來進行無效率的浪費與舞弊,遠不如讓市場管理它自己(以及我們所有的人)。
從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開始,粗通政治或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官商勾結的誘因無所不在。解決貪腐的典型辦法有兩種:縮小政府經費與權責,或者擴大媒體與公民監督的機制。
縮小政府經費與權責其實於事無補,因為官商勾結的主要管道在於無法縮編的政府權力,而非政府經費。美國與台灣的高速公路網路之所以發達,主要不是因為這樣比較節能或方便,而是因為每個高速公路出口都是炒作房地產的好議題;台灣各個地方政府爭相要求設立大學與科學園區,主要的不是為了促進在地的產業發展與教育,而是可以炒作園區外和大學周圍的房地產。但是,我們真的要把教育、產業政策與交通全部交給市場去管理嗎?
另一個選項是強化媒體監督與公民參與,這是建立福利國家的先決條件,也是建立福利國家之前的社會基礎工程。如果媒體監督與公民參與的機制夠健全,我們可以用公有民營的方式提昇國營事業的績效,也可以用績效獎金乃至於紅利提升公務員的效率。即使最後政府效率仍舊低於私人企業,我們還是得要記得:私人企業的績效提升主要是在增加大老板與大股東的資產,對於其他90%的受薪者而言,可能是弊多於利!
對於資源貧乏的國家而言,本來就應該盡量共享資源,一起承擔風險,才能讓所有的人在合理的貧富差距下安居樂業。但是,要安居樂業,我們就必須要先學會公共參與和公共管理。
民主本來就是一個「棒打老虎,雞吃蟲」的制衡遊戲,只有通過透明的媒體訊息,選民才有辦法知道哪個政黨或候選人比較符合自己的期待,並且在選舉的時刻裡以選票對政黨或候選人進行獎懲,從而促進政治的良性競爭與良性循環。然而台灣的主流媒體已經嚴重地被庸俗化與政黨化,電視成為藍營與綠營操弄群眾、製造對立的工具,連報紙也充滿置入性行銷,使得民眾經常分不清楚事實是什麼,更遑論在選舉的關鍵時刻裡以選票促進政治的良性競爭。
面對被癱瘓的媒體和長期被愚弄的80%以上選民,「強化媒體監督與公民參與」幾乎是不可能的社會改造工程。面對這艱難的挑戰,我們可以做的第一步是什麼?我過去在演講中一再被問到類似的問題,而我總是回答:「設法瞭解台灣真實的處境、挑戰、危機與轉機,也設法從國外的案例裡了解台灣可以有多少種真實的選擇,然後把妳知道與相信的事實告訴身邊的人」。這回答讓很多人不滿意,總期待著有更好、更速成的答案。但是,我在十幾年的社會改革運動過程中一再受挫而自省,也一再去翻閱過去歐洲社會改革運動的相關典籍來瞭解社會進步(與挫折)的真實過程與各種力量。最後我所能相信的力量只有一種:覺醒的人有幾個,社會就有多少進步的力量。
「進步的力量」永遠是從社會上的少數(甚至極少數)人開始,他們所能倚靠的是認知、覺醒,與散播他們的認知和覺醒。表面上這樣做好像成效難彰,緩不濟急,但它們確實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婦女運動與環境運動就是典型的案例。
西歐與北歐國家的社會進步也是始於個人卑微的行動──1848年的原始共產黨員人數稀少,甚至還遠比今天劍橋、牛津、哈佛的博士更稀有;他們能力傑出,犧牲的熱情罕有人能及,人格與道德特質出眾,而且往往有貴族的身份;但是他們做什麼事來改變社會?他們到礦場去當礦工,利用休息時間教礦工寫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感受到自己不再是沒有名姓的「群眾」(the mass),而是「約翰兄弟」、「瑪莉姐妹」,是跟他們的地主一樣地有靈魂,有尊嚴、有獨立人格的人。
如果他們願意從這麼卑微的事做起,我們是否也願意從最踏實而看似卑微的事做起?社會改革運動基本上是一種價值觀的戰爭,也是一種對於「更好的社會」的務實追求與摸索。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種更好而現實上又可行的社會遠景,就有機會說服別人為這樣的社會而一起努力。
一個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對於「如何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都多多少少有一點認知,這些認知的總和加起來就是社會進步的程度。一個社會裡這些認知的總和量愈大,愈有機會提出較好的社會發展遠景,以及就此遠景達成共識。
這些認知也使得她的成員有機會脫離媒體的愚弄與置入性行銷,以及政黨的搬弄是非與煽動群眾,並且使得愈來愈多的人有能力監督政黨與政府,甚至對政黨與政府施壓,使他們朝著集體意志所要求的方向前進。
因此,要改變台灣看起來是很難,但具體能做的事卻很清楚:先增加你的認知,再把你的認知擴散出去!
結語
為了減緩peak oil 的衝擊,未來十年我們必需完成一系列的變革,包含糧食自給率的提升與生產方式的變革、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發展、綠能產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稅賦制度的公平化與合理化、隱藏性國債的處理以及政府資本的累積、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以及最高工時的規範、立法與落實。只有同時把這些問題一起作完整的配套解決,才有機會將少子化與peak oil的衝擊降到最低。
然而,為了要讓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能有效地運作,我們必須要建立良好的社會共識與勞、資、政黨協商機制和互信基礎。
其實,要認真做好這些事,十年根本就不夠!但是,我們距離peak oil 的降臨也許甚至連十年都不到。
如果你跟我一樣地相信這是台灣必須要面對的現實,讓我們一起來把這個聲音傳出去,直到2012年上任的總統和內閣願意面對事實,開始積極謀思對策,並嘗試著建立社會的共識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