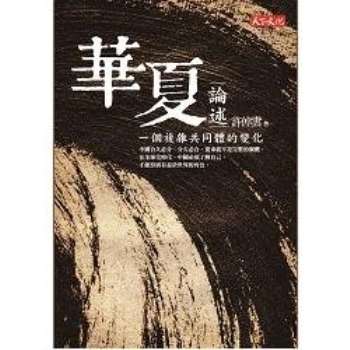自序提出的問題:「究竟我們是什麼人?」這個問題確實有待思量。我們自己對於自己是誰,常
常視所當然。用今天社會學、人類學的名詞來說,這是一個「認同」和「歸屬」的問題。歸屬的圈子並不一定是國界,因為國界經常會變動;也並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為族群本身究竟是按照基因,還是生物學的判斷?每一代都可能有外來的血統進入這一個群體,究竟該按照哪一種傳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語言、文化學上的理念?或者,根據文化本身的定義,按照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價值觀念等等做為定義?但上面這幾個定義,從語言到價值觀念各項,又是經常在變動。人群與人群之間會互相學習,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和信仰,交談的工具(語言與文字),一代與一代之間未必一樣,何況是長期的演變,更會累積轉變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體系。
成核:共同體的誕生
上述的大問題,並不是三言兩語可解決。這本書的誕生,就是為了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一些關於我們自己何所歸屬的發展過程。從系統學觀念看,每一個複雜系統,都有內部各種變數之間不斷互動,以及互動之後得到的總體相。然而,時間永遠在前進,沒有任何總體相可以長久不變。任何複雜系統,也都在不斷地擴大或縮小其涵蓋範圍,某一個時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成為界內;同樣,本來在界內的部分可以忽然排除在界外。中國古代的名學有「飛鳥無影」、「輪不輾地」等觀念,意指飛鳥和車輪都是具象的觀念,然而他們留下的痕跡,卻不可能是定格的。因此,在本書提出關於我們自己所屬的系統,我寧可從過程方面著眼,討論其變化,而不從「定格」著眼,咬定某一個時期的體相,做為歸屬所在。
任何複雜系統,無論是宇宙、花朵、世界,或者是沙粒,其中都包含不同部分,其間又不斷因為各自力量強弱而發生對抗、分合等函數關係。在一個大的人群體系之中,如前所述,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權力、社會力量和經濟制度等四個方面,做為考察的基本變數。中國歷史觀念的「朝代」,毋寧代表的是政治權威,可是任何政治權威都無法獨立運作。政權必須倚仗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三個方向的維繫,才能具體將這一個政權統治之下的人群,結合為一個共同體。
共同體的出現,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須要有一個可以結合的核心,才能擴大為一個重量足以降落成為雨滴的大水滴。大而言之,我們所屬的太陽系,也必須有一個太陽做為核心,這一連串行星才能構成一個星系。因此,在上述變動的過程之中,我們必須要從「成核」開始。
大概一萬年前,東亞地區出現新石器時代,人類群體開始有比較固定的居住點,這個共同體出現若干文化圈,形成中國複雜系統的「顆粒」或「粒子」。考古學先以各個新石器時代的地區文化,以及文獻傳留的傳說互相印證,以界定這些「粒子」。然後,才討論到由此分合,演化出的一些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過程,在傳說部分,呈現為擬親屬的文化群傳承譜系。再談到,如何在今天的黃河流域中游出現一個核心,以夏—商—周的連續融合,將四周圍地方文化吸納於內。接下來的春秋戰國時期,兩階段的演化,將這一核心推展到黃、淮、江、漢,形成中國文化共同體堅實的「核心」,堪稱為其本部。
秦漢時代,終於組成一個龐大的共同體網絡,以「天下」格局及其開放性,不斷吸收與消化外來影響。這一共同體,從此長期屹立於東亞。在共同體之內,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四環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調節的功效。東漢以後,大批外族進入中國,同時中國主流族群轉移於南方,這一調整經過上百年,吸收了南、北兩方面的新成分,開啟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時代。在這一時期,亞洲中部和西部出現強大的游牧文化圈,及由此孕育而出的伊斯蘭文化。東亞主流的中國複雜體系,面對來自西、北兩方壓力,收縮到這一共同體的本部,宋代中國雖然仍舊以「天下」自居,其實已經縮小為列國體制中的一個國家。
遼、金、元與最後的滿清時代,幾度出現的征服王朝,對中國人的心態具有嚴重影響。自從秦漢時代以來,中國基本上是「編戶齊民」的社會,沒有永久階級。征服王朝的主奴區別,則改變了統治權力的性質,集權專制的皇權,抹殺了儒家人本思想對皇權的約束,也淡化了社會與文化精英的影響力。明代雖是中國人的朝代,但夾在蒙古和滿清之間,其皇權的專制集權,卻與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權並無二致。因此,中國經歷了四、五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相當程度喪失了過去政治、社會、文化三環互相制衡的結構。
常視所當然。用今天社會學、人類學的名詞來說,這是一個「認同」和「歸屬」的問題。歸屬的圈子並不一定是國界,因為國界經常會變動;也並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為族群本身究竟是按照基因,還是生物學的判斷?每一代都可能有外來的血統進入這一個群體,究竟該按照哪一種傳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語言、文化學上的理念?或者,根據文化本身的定義,按照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價值觀念等等做為定義?但上面這幾個定義,從語言到價值觀念各項,又是經常在變動。人群與人群之間會互相學習,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和信仰,交談的工具(語言與文字),一代與一代之間未必一樣,何況是長期的演變,更會累積轉變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體系。
成核:共同體的誕生
上述的大問題,並不是三言兩語可解決。這本書的誕生,就是為了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一些關於我們自己何所歸屬的發展過程。從系統學觀念看,每一個複雜系統,都有內部各種變數之間不斷互動,以及互動之後得到的總體相。然而,時間永遠在前進,沒有任何總體相可以長久不變。任何複雜系統,也都在不斷地擴大或縮小其涵蓋範圍,某一個時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成為界內;同樣,本來在界內的部分可以忽然排除在界外。中國古代的名學有「飛鳥無影」、「輪不輾地」等觀念,意指飛鳥和車輪都是具象的觀念,然而他們留下的痕跡,卻不可能是定格的。因此,在本書提出關於我們自己所屬的系統,我寧可從過程方面著眼,討論其變化,而不從「定格」著眼,咬定某一個時期的體相,做為歸屬所在。
任何複雜系統,無論是宇宙、花朵、世界,或者是沙粒,其中都包含不同部分,其間又不斷因為各自力量強弱而發生對抗、分合等函數關係。在一個大的人群體系之中,如前所述,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權力、社會力量和經濟制度等四個方面,做為考察的基本變數。中國歷史觀念的「朝代」,毋寧代表的是政治權威,可是任何政治權威都無法獨立運作。政權必須倚仗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三個方向的維繫,才能具體將這一個政權統治之下的人群,結合為一個共同體。
共同體的出現,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須要有一個可以結合的核心,才能擴大為一個重量足以降落成為雨滴的大水滴。大而言之,我們所屬的太陽系,也必須有一個太陽做為核心,這一連串行星才能構成一個星系。因此,在上述變動的過程之中,我們必須要從「成核」開始。
大概一萬年前,東亞地區出現新石器時代,人類群體開始有比較固定的居住點,這個共同體出現若干文化圈,形成中國複雜系統的「顆粒」或「粒子」。考古學先以各個新石器時代的地區文化,以及文獻傳留的傳說互相印證,以界定這些「粒子」。然後,才討論到由此分合,演化出的一些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過程,在傳說部分,呈現為擬親屬的文化群傳承譜系。再談到,如何在今天的黃河流域中游出現一個核心,以夏—商—周的連續融合,將四周圍地方文化吸納於內。接下來的春秋戰國時期,兩階段的演化,將這一核心推展到黃、淮、江、漢,形成中國文化共同體堅實的「核心」,堪稱為其本部。
秦漢時代,終於組成一個龐大的共同體網絡,以「天下」格局及其開放性,不斷吸收與消化外來影響。這一共同體,從此長期屹立於東亞。在共同體之內,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四環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調節的功效。東漢以後,大批外族進入中國,同時中國主流族群轉移於南方,這一調整經過上百年,吸收了南、北兩方面的新成分,開啟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時代。在這一時期,亞洲中部和西部出現強大的游牧文化圈,及由此孕育而出的伊斯蘭文化。東亞主流的中國複雜體系,面對來自西、北兩方壓力,收縮到這一共同體的本部,宋代中國雖然仍舊以「天下」自居,其實已經縮小為列國體制中的一個國家。
遼、金、元與最後的滿清時代,幾度出現的征服王朝,對中國人的心態具有嚴重影響。自從秦漢時代以來,中國基本上是「編戶齊民」的社會,沒有永久階級。征服王朝的主奴區別,則改變了統治權力的性質,集權專制的皇權,抹殺了儒家人本思想對皇權的約束,也淡化了社會與文化精英的影響力。明代雖是中國人的朝代,但夾在蒙古和滿清之間,其皇權的專制集權,卻與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權並無二致。因此,中國經歷了四、五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相當程度喪失了過去政治、社會、文化三環互相制衡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