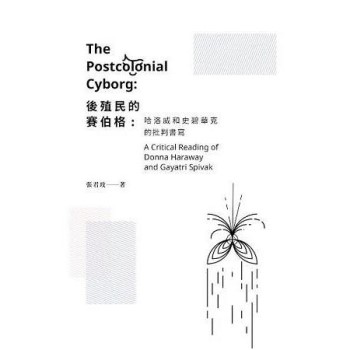第三章 哈洛威:跨界的抵抗辯證
來了,來了
來了一個詞,來了
穿過黑夜而來,
想照亮,想照亮。
(策蘭,「密接和應」,孟明譯 2011: 255)
一、轉換隱喻:對呈現邏輯的批判
圖像是展演的意象,可以棲居其中。無論是言說或影像,圖像都可以是關於可爭議世界的凝縮地圖。所有的語言,包括數學語言,都是圖像的,也就是喻說所做成的,由很多突起所構成,致使我們偏離字面的理解。我強調圖像,是為了彰顯所有物質─記號的過程都無可避免具有喻說的性質,尤其在科技科學中。─哈洛威(Haraway 1997a: 11)
本書第二章討論了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批判意象與意向,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呈現與權力議題。關於怎樣的呈現(或替現、代表)才算是真正讓「從屬者」、「弱勢」、「邊緣」或「自然」得以被看見、被聽見,從來就不是抱著良善的意圖就足夠的,甚至也不是靜態客觀的認知所能確保。在肯定被壓迫者的能動力的同時,必然會影響我們正視她們所身受的壓迫或剝削嗎?其中的緊張拉鋸,是無可避免的嗎?抑或這是某種發言位置的效應?也可能是特定批判方法所造成的作用?因為,很顯然,受壓迫或被剝削,並不一定表示就沒有能動力可言,儘管行動的空間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壓縮。同樣的,在那些優勢的生存處境中,也常有能動力乏善可陳或受到高度限縮的個體與群體。此外,能動力的展現並無法確保不會形成與體制之間的共謀關係,進而有利於維持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更重要的是,能動力,或行動力,從來就不是「有」或「無」的存有論問題,甚至也不是如何知道誰有能動力的知識論問題,而是特定個體「如何可能」展現出能動力的政治問題,以及在怎樣的條件底下或情境之中,這樣的能動力展現可以被認為是「有效」(可以發揮某種程度與層面的影響力)的倫理問題。然而,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來說,我們必須留心不要落入某種領域論的陷阱,誤認存有、知識、政治、倫理等不同分析層次的問題乃是在實質上各自不相干的。實際上正好相反,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曖昧且界線交錯的。但在某個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也必須在分析上加以區分,方能思考行動與介入的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在商榷或重構政治、倫理的相關問題時,我們也必然重新構造知識和存有的問題。第三章 哈洛威:跨界的抵抗辯證
來了,來了
來了一個詞,來了
穿過黑夜而來,
想照亮,想照亮。
(策蘭,「密接和應」,孟明譯 2011: 255)
一、轉換隱喻:對呈現邏輯的批判
圖像是展演的意象,可以棲居其中。無論是言說或影像,圖像都可以是關於可爭議世界的凝縮地圖。所有的語言,包括數學語言,都是圖像的,也就是喻說所做成的,由很多突起所構成,致使我們偏離字面的理解。我強調圖像,是為了彰顯所有物質─記號的過程都無可避免具有喻說的性質,尤其在科技科學中。─哈洛威(Haraway 1997a: 11)
本書第二章討論了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批判意象與意向,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呈現與權力議題。關於怎樣的呈現(或替現、代表)才算是真正讓「從屬者」、「弱勢」、「邊緣」或「自然」得以被看見、被聽見,從來就不是抱著良善的意圖就足夠的,甚至也不是靜態客觀的認知所能確保。在肯定被壓迫者的能動力的同時,必然會影響我們正視她們所身受的壓迫或剝削嗎?其中的緊張拉鋸,是無可避免的嗎?抑或這是某種發言位置的效應?也可能是特定批判方法所造成的作用?因為,很顯然,受壓迫或被剝削,並不一定表示就沒有能動力可言,儘管行動的空間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壓縮。同樣的,在那些優勢的生存處境中,也常有能動力乏善可陳或受到高度限縮的個體與群體。此外,能動力的展現並無法確保不會形成與體制之間的共謀關係,進而有利於維持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更重要的是,能動力,或行動力,從來就不是「有」或「無」的存有論問題,甚至也不是如何知道誰有能動力的知識論問題,而是特定個體「如何可能」展現出能動力的政治問題,以及在怎樣的條件底下或情境之中,這樣的能動力展現可以被認為是「有效」(可以發揮某種程度與層面的影響力)的倫理問題。然而,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來說,我們必須留心不要落入某種領域論的陷阱,誤認存有、知識、政治、倫理等不同分析層次的問題乃是在實質上各自不相干的。實際上正好相反,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曖昧且界線交錯的。但在某個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也必須在分析上加以區分,方能思考行動與介入的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在商榷或重構政治、倫理的相關問題時,我們也必然重新構造知識和存有的問題。
在史碧華克備受爭議的「從屬者不能發言」的陳述,以及哈洛威關於「實驗室動物參與勞動」的說法中,我們所看到的是,能動力,包括行動和發言,所具有的社會或政治效力並不是沒有條件的。簡言之,行動的物質條件乃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如何可能做出這些條件,很可能是一種最根本的社會改造實踐。換言之,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想像中的「忠實呈現」或「如實代表」,而是展演與行動。
在這些思考中,我們必須盡量避免單純的選邊站,或僅止於浪漫化任何明顯的「弱勢」立場。在本書接下去的討論中,透過從批判意象/意向到批判方法論的探討,我想凸顯的是,我們身為文化解釋與批判者所運用的隱喻不僅是我們藉以思考的概念,也不僅是建立在我們對於社會現實的特定觀察與取用,甚至也不僅是具有研究或探討的引導力。我們的隱喻是一個種子,包裹著世界的圖像,以及我們的未來。種子需要適當的時機、土壤、氣候與其他條件,才能夠發芽成長轉化。這個生態學的比喻,對我來說是當代思想的豐饒所在,是連結我們思考和生活的有機橋樑。哈洛威的賽伯格、怪物、同伴物種,史碧華克的從屬者、土著報導人、行星性,都像是這樣的種子,提供了我們特定的世界圖像與問題意識。這些種子並不是固定或靜態的,在思考未來的方向與可能時,我們有必要去追蹤這些批判意象或隱喻角色的軌跡,才能更深刻瞭解其中的潛力與偏誤。
基本上,這兩位女性主義理論家都充份認知到隱喻的重要性。哈洛威求學階段的主修是生物學。她一直在關心科學做了什麼,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隱喻,其實是一個做思考的過程,有時候像美麗的萬花筒,有時候則像恐怖的俄羅斯輪盤。她在70年代研究胚胎學的論述建構時,就已經開始投入日後持續對科學的文化批判,或更精確地來說,對科學文化的批判,把科技科學當成一種知識敘事生產的過程來加以剖析。到最後,她真正挑戰的,乃是科技和文化之間的僵化界線,指出其中流動的權力操弄。她在博士論文《水晶、纖維,以及場域。二十世紀發展生物學的有機比喻》( Crystals, Fabrics, and Fields: Metaphors of Organicism in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Embryo])中指出,「隱喻具有一種預測性的價值」,足以引導生物學家的研究往哪裡走去,因此也對「典範」具有指導方向的作用。「一個具有解釋力的隱喻乃是一個典範的生命精神」(a metaphor with explanatory power is the vital spirit of a paradigm)(Haraway 1976: 9)。她討論了二十世紀初主要的胚胎學理論,藉此探討文化裡的隱喻與相關期待,包括像是〔血液〕循環的視覺圖象,如何影響了當時的生物學研究計劃。那時候,她已經開始思考有機的界線如何維持,以及有機和機器之間如何區分。1984年出版的《泰迪熊父權體制》(Teddy Bear Patriarchy: Taxidermy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w York City, 1908-36)討論了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透視圖設計人卡爾.艾克里(Carl Akeley)如何運用槍枝、攝影機、剝製標本術等相互交纏的科技,從而建構出一種特定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並用肉眼觀察的立即視覺圖象去建立資料的科學權威。哈洛威指出,在科技科學的實踐與論述中,隱喻和敘事佔有核心的運作地位。換言之,它們在論述中發揮了非常具體的作用,主動引導了論述的進行,而不僅是被運用。
在史碧華克備受爭議的「從屬者不能發言」的陳述,以及哈洛威關於「實驗室動物參與勞動」的說法中,我們所看到的是,能動力,包括行動和發言,所具有的社會或政治效力並不是沒有條件的。簡言之,行動的物質條件乃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如何可能做出這些條件,很可能是一種最根本的社會改造實踐。換言之,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想像中的「忠實呈現」或「如實代表」,而是展演與行動。
在這些思考中,我們必須盡量避免單純的選邊站,或僅止於浪漫化任何明顯的「弱勢」立場。在本書接下去的討論中,透過從批判意象/意向到批判方法論的探討,我想凸顯的是,我們身為文化解釋與批判者所運用的隱喻不僅是我們藉以思考的概念,也不僅是建立在我們對於社會現實的特定觀察與取用,甚至也不僅是具有研究或探討的引導力。我們的隱喻是一個種子,包裹著世界的圖像,以及我們的未來。種子需要適當的時機、土壤、氣候與其他條件,才能夠發芽成長轉化。這個生態學的比喻,對我來說是當代思想的豐饒所在,是連結我們思考和生活的有機橋樑。哈洛威的賽伯格、怪物、同伴物種,史碧華克的從屬者、土著報導人、行星性,都像是這樣的種子,提供了我們特定的世界圖像與問題意識。這些種子並不是固定或靜態的,在思考未來的方向與可能時,我們有必要去追蹤這些批判意象或隱喻角色的軌跡,才能更深刻瞭解其中的潛力與偏誤。基本上,這兩位女性主義理論家都充份認知到隱喻的重要性。哈洛威求學階段的主修是生物學。她一直在關心科學做了什麼,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隱喻,其實是一個做思考的過程,有時候像美麗的萬花筒,有時候則像恐怖的俄羅斯輪盤。她在70年代研究胚胎學的論述建構時,就已經開始投入日後持續對科學的文化批判,或更精確地來說,對科學文化的批判,把科技科學當成一種知識敘事生產的過程來加以剖析。到最後,她真正挑戰的,乃是科技和文化之間的僵化界線,指出其中流動的權力操弄。她在博士論文《水晶、纖維,以及場域。二十世紀發展生物學的有機比喻》( Crystals, Fabrics, and Fields: Metaphors of Organicism in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Embryo])中指出,「隱喻具有一種預測性的價值」,足以引導生物學家的研究往哪裡走去,因此也對「典範」具有指導方向的作用。「一個具有解釋力的隱喻乃是一個典範的生命精神」(a metaphor with explanatory power is the vital spirit of a paradigm)(Haraway 1976: 9)。她討論了二十世紀初主要的胚胎學理論,藉此探討文化裡的隱喻與相關期待,包括像是〔血液〕循環的視覺圖象,如何影響了當時的生物學研究計劃。那時候,她已經開始思考有機的界線如何維持,以及有機和機器之間如何區分。1984年出版的《泰迪熊父權體制》(Teddy Bear Patriarchy: Taxidermy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w York City, 1908-36)討論了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透視圖設計人卡爾.艾克里(Carl Akeley)如何運用槍枝、攝影機、剝製標本術等相互交纏的科技,從而建構出一種特定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並用肉眼觀察的立即視覺圖象去建立資料的科學權威。哈洛威指出,在科技科學的實踐與論述中,隱喻和敘事佔有核心的運作地位。換言之,它們在論述中發揮了非常具體的作用,主動引導了論述的進行,而不僅是被運用。
文學比較出身的史碧華克則特別強調很多人文學科或文化批判論述中的關鍵概念其實都是一種隱喻,或「一個文本裡的概念隱喻」。比如馬克思理論中的「價值」(Spivak 1988: 171),和女性主義裡的「女人」、「性別」等。所有的概念隱喻同時都是一種化約,相當程度簡約了原本必然是多重決定的現象,片面強調單一的因果面向。此外,這些概念隱喻往往也是一種「詞語誤用」(catachresis)或是舊名新用(paleonymy)。任何一個既定的「名」必然有特定用法的歷史,承載了許多的意象與涵義。所謂的「舊名新用」,並非單純指涉舊有命名的延用,而是一種刻意的「詞語誤用」,同時也是一種「舊名新用的邏輯」(logic of paleonymy),一種策略的必然性。也就是說,在號稱「新的」的論述策略中,往往必須保存或借用「舊的」名稱(Derrida 1982: 307-330)。在這些分析中,史碧華克標舉出書寫的策略性,就像哈洛威所強調的存活權力,亦即活下去的力量。
對我來說,在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相關思考中,最核心的概念隱喻可能就是土地,土地不僅是真實的孕育,也是觀念的聯繫,情感的牽絆。而「土地」作為一個隱喻,其實正是信念之所以能夠生根發芽的社會與物質基礎。這也是我在本書最後一章將回返的主題。
本章要探討哈洛威的社會批判理論,同時也是她對於生命與生存的看法。對哈洛威來說,生存始終是凡俗的、入世的、此生的。在她的學術實踐中,經歷了幾次很關鍵隱喻轉換,每一次轉換都代表了一種批判當時社會歷史處境的意象與視角。隱喻,是一種批判社會的方法,也是一種如何共同生活的方法。在1985年的〈賽伯格宣言〉中她的口號是「為了凡俗生存的賽伯格!」(Cyborgsforearthly survival!),到了2004年的《同伴物種宣言》(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她的口號變成「快快跑;用力咬!」(Run fast;bite hard!),然後,在2008年的《當物種相遇》(When Species Meet)以後,她告訴我們「不要逃避麻煩!」(Stay with the trouble)。無論是不帶純淨幻夢的、充滿褻瀆與歡慶、但也堅持負起重構界線責任的賽伯格凡俗生存,或是身心相繫、彼此建構、共同演化的同伴物種的跑跳咬,或是勇敢承擔多重主體混雜相處、矛盾衝突、痛苦受難的糾結關係,都是關於如何面對「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難題。
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倫理學問題,除了顯然有政治面向之外,必然同時涉及了存有論和知識論的提問。這樣的宣稱看似簡單,尤其在大家逐漸熟悉這類交織性的詞彙之後,其實非常的複雜,並且充滿了難解的內在矛盾。但是,有矛盾並不等同於不真實或錯誤。相反的,面對與處理內在矛盾很可能正是最關鍵的任務。我們存在著、消失著,認識著、迷惑著,活著、死著,愛著、吃著,彼此。簡單來說,我們互相依賴,又彼此切割。
在當前充滿剝削、宰制、支配的全球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生命處境中,批判社會與共同生活必然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哈洛威對於「剝削」與「壓迫」有不一樣的反省。在碎裂的處境中,她傾向於強調受剝削者和被壓迫者本身的行動力,甚至因此會被批判忽略了對壓迫者的譴責,以及對優勢者行動的檢驗。她的出發點之一是對於代言政治的質疑,但更重要的是傳統「呈現」或「代表」在概念與操作上的批判。在此,我將稱之為對於「呈現邏輯」(logic of representation)的批判。哈洛威主張,我們必須留心呈現的可能陷阱,並練習更曲折的看見。
基本上,哈洛威的隱喻可以分為兩種類型,而此二者在運作上的交織也凸顯了知識和存在的密不可分。第一類是關於批判的意象,可以作為批判領航員的獨特存在物,怪物、賽伯格、同伴物種。第二種是關於批判的方法論,關於科學如何可能,以及更廣義來說,如何認識世界的途徑,衍射、內爆、花繩。意象,同時也是意向,並藉此連結了方法,從而進入世界,並和世界一起演化。換言之,批判的意象和方法並非二分,必須互相支援。哈洛威的隱喻都有一個共同點,界線的開放、混雜、拆解、重組。在談界線的問題時,開放、混雜、拆解、重組是四個必須同時並重的向度,若只有前三項,而少了持續進行的重組,也就等於放棄了最重要的基本責任:重新打造界限,也就是重新去釐清關係(relations, relationships)。而關係,正是哈洛威所說的「最小分析單位」(Haraway 2003: 24),稍後更改為「最小的可能分析模式」(the smallest patterns for analysis),因為她認為「單位」一詞會產生實體化的誤導,尤其是她始終極力在概念上排斥的自生系統論(autopoiesis)或其他有機形式的想像(Haraway 2008: 26, 313n. 31)。儘管我們可以商榷,這和她在談論同伴物種時所強調的物種特定能力(species-specific capacity)與成就(Haraway 2003: 53)之間是否造成某種抵觸。其實,哈洛威對「有機」概念的排斥是有其特定歷史意義的,主要因應美國從1950年代開始在社會學與生物學界同時崛起的結構功能論(Haraway 1991)。在當時,有機整體論所連結的政治傾向往往是保守與拒絕徹底改革的。然而,這樣的知識情況已逐漸改變。事實上,有機的界線開放乃是生物學近年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此我要強調的是,「有機」概念的開放與封界,如此持續不斷地辯證運動,正是哈洛威理論中的張力。這份張力不會總是均衡的,但在某些關鍵議題上,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衡,比如當她的論述觸角更深入到活生生的具體動物生活時,往往忽略了有界線的生命。如何對待動物,關乎批判理論的未來。本書上一章觸及了這個議題,本章將更充分討論哈洛威的理論面貌與動向,以期藉此更深刻領會其中的兩難處境與倫理要務。
文學比較出身的史碧華克則特別強調很多人文學科或文化批判論述中的關鍵概念其實都是一種隱喻,或「一個文本裡的概念隱喻」。比如馬克思理論中的「價值」(Spivak 1988: 171),和女性主義裡的「女人」、「性別」等。所有的概念隱喻同時都是一種化約,相當程度簡約了原本必然是多重決定的現象,片面強調單一的因果面向。此外,這些概念隱喻往往也是一種「詞語誤用」(catachresis)或是舊名新用(paleonymy)。任何一個既定的「名」必然有特定用法的歷史,承載了許多的意象與涵義。所謂的「舊名新用」,並非單純指涉舊有命名的延用,而是一種刻意的「詞語誤用」,同時也是一種「舊名新用的邏輯」(logic of paleonymy),一種策略的必然性。也就是說,在號稱「新的」的論述策略中,往往必須保存或借用「舊的」名稱(Derrida 1982: 307-330)。在這些分析中,史碧華克標舉出書寫的策略性,就像哈洛威所強調的存活權力,亦即活下去的力量。
對我來說,在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相關思考中,最核心的概念隱喻可能就是土地,土地不僅是真實的孕育,也是觀念的聯繫,情感的牽絆。而「土地」作為一個隱喻,其實正是信念之所以能夠生根發芽的社會與物質基礎。這也是我在本書最後一章將回返的主題。
本章要探討哈洛威的社會批判理論,同時也是她對於生命與生存的看法。對哈洛威來說,生存始終是凡俗的、入世的、此生的。在她的學術實踐中,經歷了幾次很關鍵隱喻轉換,每一次轉換都代表了一種批判當時社會歷史處境的意象與視角。隱喻,是一種批判社會的方法,也是一種如何共同生活的方法。在1985年的〈賽伯格宣言〉中她的口號是「為了凡俗生存的賽伯格!」(Cyborgsforearthly survival!),到了2004年的《同伴物種宣言》(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她的口號變成「快快跑;用力咬!」(Run fast;bite hard!),然後,在2008年的《當物種相遇》(When Species Meet)以後,她告訴我們「不要逃避麻煩!」(Stay with the trouble)。無論是不帶純淨幻夢的、充滿褻瀆與歡慶、但也堅持負起重構界線責任的賽伯格凡俗生存,或是身心相繫、彼此建構、共同演化的同伴物種的跑跳咬,或是勇敢承擔多重主體混雜相處、矛盾衝突、痛苦受難的糾結關係,都是關於如何面對「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難題。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倫理學問題,除了顯然有政治面向之外,必然同時涉及了存有論和知識論的提問。這樣的宣稱看似簡單,尤其在大家逐漸熟悉這類交織性的詞彙之後,其實非常的複雜,並且充滿了難解的內在矛盾。但是,有矛盾並不等同於不真實或錯誤。相反的,面對與處理內在矛盾很可能正是最關鍵的任務。我們存在著、消失著,認識著、迷惑著,活著、死著,愛著、吃著,彼此。簡單來說,我們互相依賴,又彼此切割。
在當前充滿剝削、宰制、支配的全球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生命處境中,批判社會與共同生活必然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哈洛威對於「剝削」與「壓迫」有不一樣的反省。在碎裂的處境中,她傾向於強調受剝削者和被壓迫者本身的行動力,甚至因此會被批判忽略了對壓迫者的譴責,以及對優勢者行動的檢驗。她的出發點之一是對於代言政治的質疑,但更重要的是傳統「呈現」或「代表」在概念與操作上的批判。在此,我將稱之為對於「呈現邏輯」(logic of representation)的批判。哈洛威主張,我們必須留心呈現的可能陷阱,並練習更曲折的看見。
上一章探討了第一類關於批判意象的隱喻。基本上,那都在引領批判的意向時指出一個重要事實:過往的呈現邏輯已經不足以因應當代複雜的政治倫理佈局,我們必須在此之外提出更有效的發聲模式,以利社會改革的發生。當代政治倫理佈局最大的特性在於外在與內在界線的日趨模糊,但權力的支配與壓迫並未因此稍減,而以更細緻的方式深入日常生活的理路。發言位置的物質條件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在界線混雜的處境中,物質條件的釐清也變得更困難。史碧華克會用共謀來形容這樣的狀況,儘管這不必然是悲觀的,而可能召喚出更具反思性更加負起說明責任的行動能力。面對這個歷史處境,哈洛威的因應方式則是更強調「共享」。從「同伴物種」的隱喻轉向上,我們已經看到這點。無論在行動力、勞動、苦難、責任,乃至於知識建構和政治倫理的可能性上,哈洛威都主張以關係為最小的分析模式與理解脈絡。換言之,不僅必須跨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知識論界線,也要體認到存在及其界線的浮現,乃是發生在複雜的關係與元素過程中。
這樣的知識立場,當然並不容易理解。畢竟我們大多已經習慣了啓蒙以降的知識論姿態,以一個相對來說固定位置的認識主體去掌握世界。哈洛威並沒有徹底揚棄這點,她最大的貢獻是要去釐清「位置」的物質性與複雜性,尤其在當代的科學科技政權中,或是她所說的「支配的訊息學」,以及種種重要學科界線的內爆,包括科學家用以形塑世界觀的生物學和化學,以及生物學和資訊學等等。
在1989年出版的《靈長類視線: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The Primate Vision: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導論一開始,哈洛威引用了南非博物學家尤金.馬雷(Eugene Marais)的話指出,「因為所有事物都必須以一個愛的行動為開端。」(For thus all things must begin with an act of love.)(Haraway 1989: 1)愛、權力和科學,交織在文化對於自然的建構過程中。哈洛威後來針對1996年知名的「索卡惡作劇」(Sokal hoax)指出,索可對於「社會建構論」的批判其實是基於誤解,他認為所謂的建構論者不相信現實的存在,這並不是真的。哈洛威再度引用馬雷,強調對科學的愛是知識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因素,而這適用於「科學家及其研究對象之間,還有研究科學的人及其主題之間的關係」(Haraway 1997c: 124)。她並沒有直接回應索卡等科學家對於建構論或解構的抨擊,她直言這其中有很多的情緒,報復、憤恨與惡意,在多年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s)裡,有很多說法都像是惡作劇,很難讓人當真,雖然這樣的戰爭是很真實的(Haraway 1997c: 123)。哈洛威以自己同時身為生物學家和科學史研究者的雙重經驗出發,去回應這些所謂的科學戰爭。
她指出,無論是科學,或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探討,都是持續「製造意義」的實作,這樣的實作同時必然是歷史的,涉及到許多有著特定社會、文化、物質處境的行動者,包括人與非人的行動者,諸如「機器、有機體、人、土地、制度、金錢、分子,以及很多其他類型的事物」(Haraway 1997c: 124)。她強調,在科學知識中一直都有很多的故事,若是硬要把這些故事除去,那將是一種「知識論的避孕或科學的自虐」(epistemological contraception or scientific self-abuse)(Haraway 1997c: 126)。不僅故事重要,故事的故事更重要。換言之,故事如何被生產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社會存有論與知識論問題。就像哈洛威在〈同伴物種宣言〉中所說的,她要說的是「關於故事的故事」(Haraway 2003: 21),科學和文學在喻說中不斷流通運輸的正是故事。比如,metaplasm這個詞,在修辭學上是「詞形變化」,指的是一個字透過發音、音節和字母的增減或換位而產生改變;在生物學上則是「後生質」或「後成質」,指的是細胞裡面不屬於原生質(protoplasm)的、沒有生命的物質,因此也有譯成「副漿」。哈洛威很喜歡這類字詞的意象與隱喻,跨越學科分界,也跨越意義的限域,貌似錯誤,猶如新生。「後生質」代表「錯誤」,也就是一個轉折,而英文喻說(trope)的原意,一個關乎肉身的差異(Haraway 2003: 20-21)。
換言之,科學作為有系統的知識(此為科學一詞的原意),並不是僅止於忠實地呈現事實,而是一個不斷在進行敘事的過程,不斷透過隱喻在說故事。但這並不表示沒有「現實」存在。而只是說現實的顯露不可能是沒有中介的。另一個很重要的點是政治倫理的參與。哈洛威提到自己的教學經驗,在反越戰的年代中,他們在對非本科系學生傳授生物學相關的知識時,乃是抱著一種公民教育的使命感。這並不是說科學才是啓蒙的唯一道路,反而必須指出,科學的實作本身早已透露出知識、技術、符號、政治、物質等層面都是連結交錯的。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正是如此製造得出。
生物學是一個政治論述,我們在其中必須致力於實作的每一個層次,包括技術上的、記號上的、道德上的、經濟上的、制度上的實作。除此之外,生物學也帶來了強烈的歡樂,包括知識的、情緒的、社會的和肉體上的歡樂。任何像這樣的東西,都不應該被輕易放棄,也不應該片面加以譴責或讚頌。(Haraway 1997c: 127)
基本上,哈洛威的隱喻可以分為兩種類型,而此二者在運作上的交織也凸顯了知識和存在的密不可分。第一類是關於批判的意象,可以作為批判領航員的獨特存在物,怪物、賽伯格、同伴物種。第二種是關於批判的方法論,關於科學如何可能,以及更廣義來說,如何認識世界的途徑,衍射、內爆、花繩。意象,同時也是意向,並藉此連結了方法,從而進入世界,並和世界一起演化。換言之,批判的意象和方法並非二分,必須互相支援。哈洛威的隱喻都有一個共同點,界線的開放、混雜、拆解、重組。在談界線的問題時,開放、混雜、拆解、重組是四個必須同時並重的向度,若只有前三項,而少了持續進行的重組,也就等於放棄了最重要的基本責任:重新打造界限,也就是重新去釐清關係(relations, relationships)。而關係,正是哈洛威所說的「最小分析單位」(Haraway 2003: 24),稍後更改為「最小的可能分析模式」(the smallest patterns for analysis),因為她認為「單位」一詞會產生實體化的誤導,尤其是她始終極力在概念上排斥的自生系統論(autopoiesis)或其他有機形式的想像(Haraway 2008: 26, 313n. 31)。儘管我們可以商榷,這和她在談論同伴物種時所強調的物種特定能力(species-specific capacity)與成就(Haraway 2003: 53)之間是否造成某種抵觸。其實,哈洛威對「有機」概念的排斥是有其特定歷史意義的,主要因應美國從1950年代開始在社會學與生物學界同時崛起的結構功能論(Haraway 1991)。在當時,有機整體論所連結的政治傾向往往是保守與拒絕徹底改革的。然而,這樣的知識情況已逐漸改變。事實上,有機的界線開放乃是生物學近年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此我要強調的是,「有機」概念的開放與封界,如此持續不斷地辯證運動,正是哈洛威理論中的張力。這份張力不會總是均衡的,但在某些關鍵議題上,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衡,比如當她的論述觸角更深入到活生生的具體動物生活時,往往忽略了有界線的生命。如何對待動物,關乎批判理論的未來。本書上一章觸及了這個議題,本章將更充分討論哈洛威的理論面貌與動向,以期藉此更深刻領會其中的兩難處境與倫理要務。上一章探討了第一類關於批判意象的隱喻。基本上,那都在引領批判的意向時指出一個重要事實:過往的呈現邏輯已經不足以因應當代複雜的政治倫理佈局,我們必須在此之外提出更有效的發聲模式,以利社會改革的發生。當代政治倫理佈局最大的特性在於外在與內在界線的日趨模糊,但權力的支配與壓迫並未因此稍減,而以更細緻的方式深入日常生活的理路。發言位置的物質條件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在界線混雜的處境中,物質條件的釐清也變得更困難。史碧華克會用共謀來形容這樣的狀況,儘管這不必然是悲觀的,而可能召喚出更具反思性更加負起說明責任的行動能力。面對這個歷史處境,哈洛威的因應方式則是更強調「共享」。從「同伴物種」的隱喻轉向上,我們已經看到這點。無論在行動力、勞動、苦難、責任,乃至於知識建構和政治倫理的可能性上,哈洛威都主張以關係為最小的分析模式與理解脈絡。換言之,不僅必須跨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知識論界線,也要體認到存在及其界線的浮現,乃是發生在複雜的關係與元素過程中。
這樣的知識立場,當然並不容易理解。畢竟我們大多已經習慣了啓蒙以降的知識論姿態,以一個相對來說固定位置的認識主體去掌握世界。哈洛威並沒有徹底揚棄這點,她最大的貢獻是要去釐清「位置」的物質性與複雜性,尤其在當代的科學科技政權中,或是她所說的「支配的訊息學」,以及種種重要學科界線的內爆,包括科學家用以形塑世界觀的生物學和化學,以及生物學和資訊學等等。在1989年出版的《靈長類視線: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The Primate Vision: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導論一開始,哈洛威引用了南非博物學家尤金.馬雷(Eugene Marais)的話指出,「因為所有事物都必須以一個愛的行動為開端。」(For thus all things must begin with an act of love.)(Haraway 1989: 1)愛、權力和科學,交織在文化對於自然的建構過程中。哈洛威後來針對1996年知名的「索卡惡作劇」(Sokal hoax)指出,索可對於「社會建構論」的批判其實是基於誤解,他認為所謂的建構論者不相信現實的存在,這並不是真的。哈洛威再度引用馬雷,強調對科學的愛是知識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因素,而這適用於「科學家及其研究對象之間,還有研究科學的人及其主題之間的關係」(Haraway 1997c: 124)。她並沒有直接回應索卡等科學家對於建構論或解構的抨擊,她直言這其中有很多的情緒,報復、憤恨與惡意,在多年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s)裡,有很多說法都像是惡作劇,很難讓人當真,雖然這樣的戰爭是很真實的(Haraway 1997c: 123)。哈洛威以自己同時身為生物學家和科學史研究者的雙重經驗出發,去回應這些所謂的科學戰爭。她指出,無論是科學,或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探討,都是持續「製造意義」的實作,這樣的實作同時必然是歷史的,涉及到許多有著特定社會、文化、物質處境的行動者,包括人與非人的行動者,諸如「機器、有機體、人、土地、制度、金錢、分子,以及很多其他類型的事物」(Haraway 1997c: 124)。她強調,在科學知識中一直都有很多的故事,若是硬要把這些故事除去,那將是一種「知識論的避孕或科學的自虐」(epistemological contraception or scientific self-abuse)(Haraway 1997c: 126)。不僅故事重要,故事的故事更重要。換言之,故事如何被生產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社會存有論與知識論問題。就像哈洛威在〈同伴物種宣言〉中所說的,她要說的是「關於故事的故事」(Haraway 2003: 21),科學和文學在喻說中不斷流通運輸的正是故事。比如,metaplasm這個詞,在修辭學上是「詞形變化」,指的是一個字透過發音、音節和字母的增減或換位而產生改變;在生物學上則是「後生質」或「後成質」,指的是細胞裡面不屬於原生質(protoplasm)的、沒有生命的物質,因此也有譯成「副漿」。哈洛威很喜歡這類字詞的意象與隱喻,跨越學科分界,也跨越意義的限域,貌似錯誤,猶如新生。「後生質」代表「錯誤」,也就是一個轉折,而英文喻說(trope)的原意,一個關乎肉身的差異(Haraway 2003: 20-21)。換言之,科學作為有系統的知識(此為科學一詞的原意),並不是僅止於忠實地呈現事實,而是一個不斷在進行敘事的過程,不斷透過隱喻在說故事。但這並不表示沒有「現實」存在。而只是說現實的顯露不可能是沒有中介的。另一個很重要的點是政治倫理的參與。哈洛威提到自己的教學經驗,在反越戰的年代中,他們在對非本科系學生傳授生物學相關的知識時,乃是抱著一種公民教育的使命感。這並不是說科學才是啓蒙的唯一道路,反而必須指出,科學的實作本身早已透露出知識、技術、符號、政治、物質等層面都是連結交錯的。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正是如此製造得出。
生物學是一個政治論述,我們在其中必須致力於實作的每一個層次,包括技術上的、記號上的、道德上的、經濟上的、制度上的實作。除此之外,生物學也帶來了強烈的歡樂,包括知識的、情緒的、社會的和肉體上的歡樂。任何像這樣的東西,都不應該被輕易放棄,也不應該片面加以譴責或讚頌。(Haraway 1997c: 127)
來了,來了
來了一個詞,來了
穿過黑夜而來,
想照亮,想照亮。
(策蘭,「密接和應」,孟明譯 2011: 255)
一、轉換隱喻:對呈現邏輯的批判
圖像是展演的意象,可以棲居其中。無論是言說或影像,圖像都可以是關於可爭議世界的凝縮地圖。所有的語言,包括數學語言,都是圖像的,也就是喻說所做成的,由很多突起所構成,致使我們偏離字面的理解。我強調圖像,是為了彰顯所有物質─記號的過程都無可避免具有喻說的性質,尤其在科技科學中。─哈洛威(Haraway 1997a: 11)
本書第二章討論了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批判意象與意向,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呈現與權力議題。關於怎樣的呈現(或替現、代表)才算是真正讓「從屬者」、「弱勢」、「邊緣」或「自然」得以被看見、被聽見,從來就不是抱著良善的意圖就足夠的,甚至也不是靜態客觀的認知所能確保。在肯定被壓迫者的能動力的同時,必然會影響我們正視她們所身受的壓迫或剝削嗎?其中的緊張拉鋸,是無可避免的嗎?抑或這是某種發言位置的效應?也可能是特定批判方法所造成的作用?因為,很顯然,受壓迫或被剝削,並不一定表示就沒有能動力可言,儘管行動的空間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壓縮。同樣的,在那些優勢的生存處境中,也常有能動力乏善可陳或受到高度限縮的個體與群體。此外,能動力的展現並無法確保不會形成與體制之間的共謀關係,進而有利於維持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更重要的是,能動力,或行動力,從來就不是「有」或「無」的存有論問題,甚至也不是如何知道誰有能動力的知識論問題,而是特定個體「如何可能」展現出能動力的政治問題,以及在怎樣的條件底下或情境之中,這樣的能動力展現可以被認為是「有效」(可以發揮某種程度與層面的影響力)的倫理問題。然而,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來說,我們必須留心不要落入某種領域論的陷阱,誤認存有、知識、政治、倫理等不同分析層次的問題乃是在實質上各自不相干的。實際上正好相反,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曖昧且界線交錯的。但在某個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也必須在分析上加以區分,方能思考行動與介入的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在商榷或重構政治、倫理的相關問題時,我們也必然重新構造知識和存有的問題。第三章 哈洛威:跨界的抵抗辯證
來了,來了
來了一個詞,來了
穿過黑夜而來,
想照亮,想照亮。
(策蘭,「密接和應」,孟明譯 2011: 255)
一、轉換隱喻:對呈現邏輯的批判
圖像是展演的意象,可以棲居其中。無論是言說或影像,圖像都可以是關於可爭議世界的凝縮地圖。所有的語言,包括數學語言,都是圖像的,也就是喻說所做成的,由很多突起所構成,致使我們偏離字面的理解。我強調圖像,是為了彰顯所有物質─記號的過程都無可避免具有喻說的性質,尤其在科技科學中。─哈洛威(Haraway 1997a: 11)
本書第二章討論了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批判意象與意向,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呈現與權力議題。關於怎樣的呈現(或替現、代表)才算是真正讓「從屬者」、「弱勢」、「邊緣」或「自然」得以被看見、被聽見,從來就不是抱著良善的意圖就足夠的,甚至也不是靜態客觀的認知所能確保。在肯定被壓迫者的能動力的同時,必然會影響我們正視她們所身受的壓迫或剝削嗎?其中的緊張拉鋸,是無可避免的嗎?抑或這是某種發言位置的效應?也可能是特定批判方法所造成的作用?因為,很顯然,受壓迫或被剝削,並不一定表示就沒有能動力可言,儘管行動的空間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壓縮。同樣的,在那些優勢的生存處境中,也常有能動力乏善可陳或受到高度限縮的個體與群體。此外,能動力的展現並無法確保不會形成與體制之間的共謀關係,進而有利於維持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更重要的是,能動力,或行動力,從來就不是「有」或「無」的存有論問題,甚至也不是如何知道誰有能動力的知識論問題,而是特定個體「如何可能」展現出能動力的政治問題,以及在怎樣的條件底下或情境之中,這樣的能動力展現可以被認為是「有效」(可以發揮某種程度與層面的影響力)的倫理問題。然而,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來說,我們必須留心不要落入某種領域論的陷阱,誤認存有、知識、政治、倫理等不同分析層次的問題乃是在實質上各自不相干的。實際上正好相反,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曖昧且界線交錯的。但在某個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也必須在分析上加以區分,方能思考行動與介入的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在商榷或重構政治、倫理的相關問題時,我們也必然重新構造知識和存有的問題。
在史碧華克備受爭議的「從屬者不能發言」的陳述,以及哈洛威關於「實驗室動物參與勞動」的說法中,我們所看到的是,能動力,包括行動和發言,所具有的社會或政治效力並不是沒有條件的。簡言之,行動的物質條件乃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如何可能做出這些條件,很可能是一種最根本的社會改造實踐。換言之,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想像中的「忠實呈現」或「如實代表」,而是展演與行動。
在這些思考中,我們必須盡量避免單純的選邊站,或僅止於浪漫化任何明顯的「弱勢」立場。在本書接下去的討論中,透過從批判意象/意向到批判方法論的探討,我想凸顯的是,我們身為文化解釋與批判者所運用的隱喻不僅是我們藉以思考的概念,也不僅是建立在我們對於社會現實的特定觀察與取用,甚至也不僅是具有研究或探討的引導力。我們的隱喻是一個種子,包裹著世界的圖像,以及我們的未來。種子需要適當的時機、土壤、氣候與其他條件,才能夠發芽成長轉化。這個生態學的比喻,對我來說是當代思想的豐饒所在,是連結我們思考和生活的有機橋樑。哈洛威的賽伯格、怪物、同伴物種,史碧華克的從屬者、土著報導人、行星性,都像是這樣的種子,提供了我們特定的世界圖像與問題意識。這些種子並不是固定或靜態的,在思考未來的方向與可能時,我們有必要去追蹤這些批判意象或隱喻角色的軌跡,才能更深刻瞭解其中的潛力與偏誤。
基本上,這兩位女性主義理論家都充份認知到隱喻的重要性。哈洛威求學階段的主修是生物學。她一直在關心科學做了什麼,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隱喻,其實是一個做思考的過程,有時候像美麗的萬花筒,有時候則像恐怖的俄羅斯輪盤。她在70年代研究胚胎學的論述建構時,就已經開始投入日後持續對科學的文化批判,或更精確地來說,對科學文化的批判,把科技科學當成一種知識敘事生產的過程來加以剖析。到最後,她真正挑戰的,乃是科技和文化之間的僵化界線,指出其中流動的權力操弄。她在博士論文《水晶、纖維,以及場域。二十世紀發展生物學的有機比喻》( Crystals, Fabrics, and Fields: Metaphors of Organicism in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Embryo])中指出,「隱喻具有一種預測性的價值」,足以引導生物學家的研究往哪裡走去,因此也對「典範」具有指導方向的作用。「一個具有解釋力的隱喻乃是一個典範的生命精神」(a metaphor with explanatory power is the vital spirit of a paradigm)(Haraway 1976: 9)。她討論了二十世紀初主要的胚胎學理論,藉此探討文化裡的隱喻與相關期待,包括像是〔血液〕循環的視覺圖象,如何影響了當時的生物學研究計劃。那時候,她已經開始思考有機的界線如何維持,以及有機和機器之間如何區分。1984年出版的《泰迪熊父權體制》(Teddy Bear Patriarchy: Taxidermy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w York City, 1908-36)討論了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透視圖設計人卡爾.艾克里(Carl Akeley)如何運用槍枝、攝影機、剝製標本術等相互交纏的科技,從而建構出一種特定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並用肉眼觀察的立即視覺圖象去建立資料的科學權威。哈洛威指出,在科技科學的實踐與論述中,隱喻和敘事佔有核心的運作地位。換言之,它們在論述中發揮了非常具體的作用,主動引導了論述的進行,而不僅是被運用。
在史碧華克備受爭議的「從屬者不能發言」的陳述,以及哈洛威關於「實驗室動物參與勞動」的說法中,我們所看到的是,能動力,包括行動和發言,所具有的社會或政治效力並不是沒有條件的。簡言之,行動的物質條件乃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如何可能做出這些條件,很可能是一種最根本的社會改造實踐。換言之,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想像中的「忠實呈現」或「如實代表」,而是展演與行動。
在這些思考中,我們必須盡量避免單純的選邊站,或僅止於浪漫化任何明顯的「弱勢」立場。在本書接下去的討論中,透過從批判意象/意向到批判方法論的探討,我想凸顯的是,我們身為文化解釋與批判者所運用的隱喻不僅是我們藉以思考的概念,也不僅是建立在我們對於社會現實的特定觀察與取用,甚至也不僅是具有研究或探討的引導力。我們的隱喻是一個種子,包裹著世界的圖像,以及我們的未來。種子需要適當的時機、土壤、氣候與其他條件,才能夠發芽成長轉化。這個生態學的比喻,對我來說是當代思想的豐饒所在,是連結我們思考和生活的有機橋樑。哈洛威的賽伯格、怪物、同伴物種,史碧華克的從屬者、土著報導人、行星性,都像是這樣的種子,提供了我們特定的世界圖像與問題意識。這些種子並不是固定或靜態的,在思考未來的方向與可能時,我們有必要去追蹤這些批判意象或隱喻角色的軌跡,才能更深刻瞭解其中的潛力與偏誤。基本上,這兩位女性主義理論家都充份認知到隱喻的重要性。哈洛威求學階段的主修是生物學。她一直在關心科學做了什麼,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隱喻,其實是一個做思考的過程,有時候像美麗的萬花筒,有時候則像恐怖的俄羅斯輪盤。她在70年代研究胚胎學的論述建構時,就已經開始投入日後持續對科學的文化批判,或更精確地來說,對科學文化的批判,把科技科學當成一種知識敘事生產的過程來加以剖析。到最後,她真正挑戰的,乃是科技和文化之間的僵化界線,指出其中流動的權力操弄。她在博士論文《水晶、纖維,以及場域。二十世紀發展生物學的有機比喻》( Crystals, Fabrics, and Fields: Metaphors of Organicism in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Embryo])中指出,「隱喻具有一種預測性的價值」,足以引導生物學家的研究往哪裡走去,因此也對「典範」具有指導方向的作用。「一個具有解釋力的隱喻乃是一個典範的生命精神」(a metaphor with explanatory power is the vital spirit of a paradigm)(Haraway 1976: 9)。她討論了二十世紀初主要的胚胎學理論,藉此探討文化裡的隱喻與相關期待,包括像是〔血液〕循環的視覺圖象,如何影響了當時的生物學研究計劃。那時候,她已經開始思考有機的界線如何維持,以及有機和機器之間如何區分。1984年出版的《泰迪熊父權體制》(Teddy Bear Patriarchy: Taxidermy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w York City, 1908-36)討論了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透視圖設計人卡爾.艾克里(Carl Akeley)如何運用槍枝、攝影機、剝製標本術等相互交纏的科技,從而建構出一種特定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並用肉眼觀察的立即視覺圖象去建立資料的科學權威。哈洛威指出,在科技科學的實踐與論述中,隱喻和敘事佔有核心的運作地位。換言之,它們在論述中發揮了非常具體的作用,主動引導了論述的進行,而不僅是被運用。
文學比較出身的史碧華克則特別強調很多人文學科或文化批判論述中的關鍵概念其實都是一種隱喻,或「一個文本裡的概念隱喻」。比如馬克思理論中的「價值」(Spivak 1988: 171),和女性主義裡的「女人」、「性別」等。所有的概念隱喻同時都是一種化約,相當程度簡約了原本必然是多重決定的現象,片面強調單一的因果面向。此外,這些概念隱喻往往也是一種「詞語誤用」(catachresis)或是舊名新用(paleonymy)。任何一個既定的「名」必然有特定用法的歷史,承載了許多的意象與涵義。所謂的「舊名新用」,並非單純指涉舊有命名的延用,而是一種刻意的「詞語誤用」,同時也是一種「舊名新用的邏輯」(logic of paleonymy),一種策略的必然性。也就是說,在號稱「新的」的論述策略中,往往必須保存或借用「舊的」名稱(Derrida 1982: 307-330)。在這些分析中,史碧華克標舉出書寫的策略性,就像哈洛威所強調的存活權力,亦即活下去的力量。
對我來說,在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相關思考中,最核心的概念隱喻可能就是土地,土地不僅是真實的孕育,也是觀念的聯繫,情感的牽絆。而「土地」作為一個隱喻,其實正是信念之所以能夠生根發芽的社會與物質基礎。這也是我在本書最後一章將回返的主題。
本章要探討哈洛威的社會批判理論,同時也是她對於生命與生存的看法。對哈洛威來說,生存始終是凡俗的、入世的、此生的。在她的學術實踐中,經歷了幾次很關鍵隱喻轉換,每一次轉換都代表了一種批判當時社會歷史處境的意象與視角。隱喻,是一種批判社會的方法,也是一種如何共同生活的方法。在1985年的〈賽伯格宣言〉中她的口號是「為了凡俗生存的賽伯格!」(Cyborgsforearthly survival!),到了2004年的《同伴物種宣言》(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她的口號變成「快快跑;用力咬!」(Run fast;bite hard!),然後,在2008年的《當物種相遇》(When Species Meet)以後,她告訴我們「不要逃避麻煩!」(Stay with the trouble)。無論是不帶純淨幻夢的、充滿褻瀆與歡慶、但也堅持負起重構界線責任的賽伯格凡俗生存,或是身心相繫、彼此建構、共同演化的同伴物種的跑跳咬,或是勇敢承擔多重主體混雜相處、矛盾衝突、痛苦受難的糾結關係,都是關於如何面對「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難題。
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倫理學問題,除了顯然有政治面向之外,必然同時涉及了存有論和知識論的提問。這樣的宣稱看似簡單,尤其在大家逐漸熟悉這類交織性的詞彙之後,其實非常的複雜,並且充滿了難解的內在矛盾。但是,有矛盾並不等同於不真實或錯誤。相反的,面對與處理內在矛盾很可能正是最關鍵的任務。我們存在著、消失著,認識著、迷惑著,活著、死著,愛著、吃著,彼此。簡單來說,我們互相依賴,又彼此切割。
在當前充滿剝削、宰制、支配的全球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生命處境中,批判社會與共同生活必然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哈洛威對於「剝削」與「壓迫」有不一樣的反省。在碎裂的處境中,她傾向於強調受剝削者和被壓迫者本身的行動力,甚至因此會被批判忽略了對壓迫者的譴責,以及對優勢者行動的檢驗。她的出發點之一是對於代言政治的質疑,但更重要的是傳統「呈現」或「代表」在概念與操作上的批判。在此,我將稱之為對於「呈現邏輯」(logic of representation)的批判。哈洛威主張,我們必須留心呈現的可能陷阱,並練習更曲折的看見。
基本上,哈洛威的隱喻可以分為兩種類型,而此二者在運作上的交織也凸顯了知識和存在的密不可分。第一類是關於批判的意象,可以作為批判領航員的獨特存在物,怪物、賽伯格、同伴物種。第二種是關於批判的方法論,關於科學如何可能,以及更廣義來說,如何認識世界的途徑,衍射、內爆、花繩。意象,同時也是意向,並藉此連結了方法,從而進入世界,並和世界一起演化。換言之,批判的意象和方法並非二分,必須互相支援。哈洛威的隱喻都有一個共同點,界線的開放、混雜、拆解、重組。在談界線的問題時,開放、混雜、拆解、重組是四個必須同時並重的向度,若只有前三項,而少了持續進行的重組,也就等於放棄了最重要的基本責任:重新打造界限,也就是重新去釐清關係(relations, relationships)。而關係,正是哈洛威所說的「最小分析單位」(Haraway 2003: 24),稍後更改為「最小的可能分析模式」(the smallest patterns for analysis),因為她認為「單位」一詞會產生實體化的誤導,尤其是她始終極力在概念上排斥的自生系統論(autopoiesis)或其他有機形式的想像(Haraway 2008: 26, 313n. 31)。儘管我們可以商榷,這和她在談論同伴物種時所強調的物種特定能力(species-specific capacity)與成就(Haraway 2003: 53)之間是否造成某種抵觸。其實,哈洛威對「有機」概念的排斥是有其特定歷史意義的,主要因應美國從1950年代開始在社會學與生物學界同時崛起的結構功能論(Haraway 1991)。在當時,有機整體論所連結的政治傾向往往是保守與拒絕徹底改革的。然而,這樣的知識情況已逐漸改變。事實上,有機的界線開放乃是生物學近年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此我要強調的是,「有機」概念的開放與封界,如此持續不斷地辯證運動,正是哈洛威理論中的張力。這份張力不會總是均衡的,但在某些關鍵議題上,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衡,比如當她的論述觸角更深入到活生生的具體動物生活時,往往忽略了有界線的生命。如何對待動物,關乎批判理論的未來。本書上一章觸及了這個議題,本章將更充分討論哈洛威的理論面貌與動向,以期藉此更深刻領會其中的兩難處境與倫理要務。
文學比較出身的史碧華克則特別強調很多人文學科或文化批判論述中的關鍵概念其實都是一種隱喻,或「一個文本裡的概念隱喻」。比如馬克思理論中的「價值」(Spivak 1988: 171),和女性主義裡的「女人」、「性別」等。所有的概念隱喻同時都是一種化約,相當程度簡約了原本必然是多重決定的現象,片面強調單一的因果面向。此外,這些概念隱喻往往也是一種「詞語誤用」(catachresis)或是舊名新用(paleonymy)。任何一個既定的「名」必然有特定用法的歷史,承載了許多的意象與涵義。所謂的「舊名新用」,並非單純指涉舊有命名的延用,而是一種刻意的「詞語誤用」,同時也是一種「舊名新用的邏輯」(logic of paleonymy),一種策略的必然性。也就是說,在號稱「新的」的論述策略中,往往必須保存或借用「舊的」名稱(Derrida 1982: 307-330)。在這些分析中,史碧華克標舉出書寫的策略性,就像哈洛威所強調的存活權力,亦即活下去的力量。
對我來說,在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相關思考中,最核心的概念隱喻可能就是土地,土地不僅是真實的孕育,也是觀念的聯繫,情感的牽絆。而「土地」作為一個隱喻,其實正是信念之所以能夠生根發芽的社會與物質基礎。這也是我在本書最後一章將回返的主題。
本章要探討哈洛威的社會批判理論,同時也是她對於生命與生存的看法。對哈洛威來說,生存始終是凡俗的、入世的、此生的。在她的學術實踐中,經歷了幾次很關鍵隱喻轉換,每一次轉換都代表了一種批判當時社會歷史處境的意象與視角。隱喻,是一種批判社會的方法,也是一種如何共同生活的方法。在1985年的〈賽伯格宣言〉中她的口號是「為了凡俗生存的賽伯格!」(Cyborgsforearthly survival!),到了2004年的《同伴物種宣言》(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她的口號變成「快快跑;用力咬!」(Run fast;bite hard!),然後,在2008年的《當物種相遇》(When Species Meet)以後,她告訴我們「不要逃避麻煩!」(Stay with the trouble)。無論是不帶純淨幻夢的、充滿褻瀆與歡慶、但也堅持負起重構界線責任的賽伯格凡俗生存,或是身心相繫、彼此建構、共同演化的同伴物種的跑跳咬,或是勇敢承擔多重主體混雜相處、矛盾衝突、痛苦受難的糾結關係,都是關於如何面對「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難題。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倫理學問題,除了顯然有政治面向之外,必然同時涉及了存有論和知識論的提問。這樣的宣稱看似簡單,尤其在大家逐漸熟悉這類交織性的詞彙之後,其實非常的複雜,並且充滿了難解的內在矛盾。但是,有矛盾並不等同於不真實或錯誤。相反的,面對與處理內在矛盾很可能正是最關鍵的任務。我們存在著、消失著,認識著、迷惑著,活著、死著,愛著、吃著,彼此。簡單來說,我們互相依賴,又彼此切割。
在當前充滿剝削、宰制、支配的全球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生命處境中,批判社會與共同生活必然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哈洛威對於「剝削」與「壓迫」有不一樣的反省。在碎裂的處境中,她傾向於強調受剝削者和被壓迫者本身的行動力,甚至因此會被批判忽略了對壓迫者的譴責,以及對優勢者行動的檢驗。她的出發點之一是對於代言政治的質疑,但更重要的是傳統「呈現」或「代表」在概念與操作上的批判。在此,我將稱之為對於「呈現邏輯」(logic of representation)的批判。哈洛威主張,我們必須留心呈現的可能陷阱,並練習更曲折的看見。
上一章探討了第一類關於批判意象的隱喻。基本上,那都在引領批判的意向時指出一個重要事實:過往的呈現邏輯已經不足以因應當代複雜的政治倫理佈局,我們必須在此之外提出更有效的發聲模式,以利社會改革的發生。當代政治倫理佈局最大的特性在於外在與內在界線的日趨模糊,但權力的支配與壓迫並未因此稍減,而以更細緻的方式深入日常生活的理路。發言位置的物質條件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在界線混雜的處境中,物質條件的釐清也變得更困難。史碧華克會用共謀來形容這樣的狀況,儘管這不必然是悲觀的,而可能召喚出更具反思性更加負起說明責任的行動能力。面對這個歷史處境,哈洛威的因應方式則是更強調「共享」。從「同伴物種」的隱喻轉向上,我們已經看到這點。無論在行動力、勞動、苦難、責任,乃至於知識建構和政治倫理的可能性上,哈洛威都主張以關係為最小的分析模式與理解脈絡。換言之,不僅必須跨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知識論界線,也要體認到存在及其界線的浮現,乃是發生在複雜的關係與元素過程中。
這樣的知識立場,當然並不容易理解。畢竟我們大多已經習慣了啓蒙以降的知識論姿態,以一個相對來說固定位置的認識主體去掌握世界。哈洛威並沒有徹底揚棄這點,她最大的貢獻是要去釐清「位置」的物質性與複雜性,尤其在當代的科學科技政權中,或是她所說的「支配的訊息學」,以及種種重要學科界線的內爆,包括科學家用以形塑世界觀的生物學和化學,以及生物學和資訊學等等。
在1989年出版的《靈長類視線: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The Primate Vision: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導論一開始,哈洛威引用了南非博物學家尤金.馬雷(Eugene Marais)的話指出,「因為所有事物都必須以一個愛的行動為開端。」(For thus all things must begin with an act of love.)(Haraway 1989: 1)愛、權力和科學,交織在文化對於自然的建構過程中。哈洛威後來針對1996年知名的「索卡惡作劇」(Sokal hoax)指出,索可對於「社會建構論」的批判其實是基於誤解,他認為所謂的建構論者不相信現實的存在,這並不是真的。哈洛威再度引用馬雷,強調對科學的愛是知識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因素,而這適用於「科學家及其研究對象之間,還有研究科學的人及其主題之間的關係」(Haraway 1997c: 124)。她並沒有直接回應索卡等科學家對於建構論或解構的抨擊,她直言這其中有很多的情緒,報復、憤恨與惡意,在多年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s)裡,有很多說法都像是惡作劇,很難讓人當真,雖然這樣的戰爭是很真實的(Haraway 1997c: 123)。哈洛威以自己同時身為生物學家和科學史研究者的雙重經驗出發,去回應這些所謂的科學戰爭。
她指出,無論是科學,或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探討,都是持續「製造意義」的實作,這樣的實作同時必然是歷史的,涉及到許多有著特定社會、文化、物質處境的行動者,包括人與非人的行動者,諸如「機器、有機體、人、土地、制度、金錢、分子,以及很多其他類型的事物」(Haraway 1997c: 124)。她強調,在科學知識中一直都有很多的故事,若是硬要把這些故事除去,那將是一種「知識論的避孕或科學的自虐」(epistemological contraception or scientific self-abuse)(Haraway 1997c: 126)。不僅故事重要,故事的故事更重要。換言之,故事如何被生產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社會存有論與知識論問題。就像哈洛威在〈同伴物種宣言〉中所說的,她要說的是「關於故事的故事」(Haraway 2003: 21),科學和文學在喻說中不斷流通運輸的正是故事。比如,metaplasm這個詞,在修辭學上是「詞形變化」,指的是一個字透過發音、音節和字母的增減或換位而產生改變;在生物學上則是「後生質」或「後成質」,指的是細胞裡面不屬於原生質(protoplasm)的、沒有生命的物質,因此也有譯成「副漿」。哈洛威很喜歡這類字詞的意象與隱喻,跨越學科分界,也跨越意義的限域,貌似錯誤,猶如新生。「後生質」代表「錯誤」,也就是一個轉折,而英文喻說(trope)的原意,一個關乎肉身的差異(Haraway 2003: 20-21)。
換言之,科學作為有系統的知識(此為科學一詞的原意),並不是僅止於忠實地呈現事實,而是一個不斷在進行敘事的過程,不斷透過隱喻在說故事。但這並不表示沒有「現實」存在。而只是說現實的顯露不可能是沒有中介的。另一個很重要的點是政治倫理的參與。哈洛威提到自己的教學經驗,在反越戰的年代中,他們在對非本科系學生傳授生物學相關的知識時,乃是抱著一種公民教育的使命感。這並不是說科學才是啓蒙的唯一道路,反而必須指出,科學的實作本身早已透露出知識、技術、符號、政治、物質等層面都是連結交錯的。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正是如此製造得出。
生物學是一個政治論述,我們在其中必須致力於實作的每一個層次,包括技術上的、記號上的、道德上的、經濟上的、制度上的實作。除此之外,生物學也帶來了強烈的歡樂,包括知識的、情緒的、社會的和肉體上的歡樂。任何像這樣的東西,都不應該被輕易放棄,也不應該片面加以譴責或讚頌。(Haraway 1997c: 127)
基本上,哈洛威的隱喻可以分為兩種類型,而此二者在運作上的交織也凸顯了知識和存在的密不可分。第一類是關於批判的意象,可以作為批判領航員的獨特存在物,怪物、賽伯格、同伴物種。第二種是關於批判的方法論,關於科學如何可能,以及更廣義來說,如何認識世界的途徑,衍射、內爆、花繩。意象,同時也是意向,並藉此連結了方法,從而進入世界,並和世界一起演化。換言之,批判的意象和方法並非二分,必須互相支援。哈洛威的隱喻都有一個共同點,界線的開放、混雜、拆解、重組。在談界線的問題時,開放、混雜、拆解、重組是四個必須同時並重的向度,若只有前三項,而少了持續進行的重組,也就等於放棄了最重要的基本責任:重新打造界限,也就是重新去釐清關係(relations, relationships)。而關係,正是哈洛威所說的「最小分析單位」(Haraway 2003: 24),稍後更改為「最小的可能分析模式」(the smallest patterns for analysis),因為她認為「單位」一詞會產生實體化的誤導,尤其是她始終極力在概念上排斥的自生系統論(autopoiesis)或其他有機形式的想像(Haraway 2008: 26, 313n. 31)。儘管我們可以商榷,這和她在談論同伴物種時所強調的物種特定能力(species-specific capacity)與成就(Haraway 2003: 53)之間是否造成某種抵觸。其實,哈洛威對「有機」概念的排斥是有其特定歷史意義的,主要因應美國從1950年代開始在社會學與生物學界同時崛起的結構功能論(Haraway 1991)。在當時,有機整體論所連結的政治傾向往往是保守與拒絕徹底改革的。然而,這樣的知識情況已逐漸改變。事實上,有機的界線開放乃是生物學近年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此我要強調的是,「有機」概念的開放與封界,如此持續不斷地辯證運動,正是哈洛威理論中的張力。這份張力不會總是均衡的,但在某些關鍵議題上,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衡,比如當她的論述觸角更深入到活生生的具體動物生活時,往往忽略了有界線的生命。如何對待動物,關乎批判理論的未來。本書上一章觸及了這個議題,本章將更充分討論哈洛威的理論面貌與動向,以期藉此更深刻領會其中的兩難處境與倫理要務。上一章探討了第一類關於批判意象的隱喻。基本上,那都在引領批判的意向時指出一個重要事實:過往的呈現邏輯已經不足以因應當代複雜的政治倫理佈局,我們必須在此之外提出更有效的發聲模式,以利社會改革的發生。當代政治倫理佈局最大的特性在於外在與內在界線的日趨模糊,但權力的支配與壓迫並未因此稍減,而以更細緻的方式深入日常生活的理路。發言位置的物質條件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在界線混雜的處境中,物質條件的釐清也變得更困難。史碧華克會用共謀來形容這樣的狀況,儘管這不必然是悲觀的,而可能召喚出更具反思性更加負起說明責任的行動能力。面對這個歷史處境,哈洛威的因應方式則是更強調「共享」。從「同伴物種」的隱喻轉向上,我們已經看到這點。無論在行動力、勞動、苦難、責任,乃至於知識建構和政治倫理的可能性上,哈洛威都主張以關係為最小的分析模式與理解脈絡。換言之,不僅必須跨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知識論界線,也要體認到存在及其界線的浮現,乃是發生在複雜的關係與元素過程中。
這樣的知識立場,當然並不容易理解。畢竟我們大多已經習慣了啓蒙以降的知識論姿態,以一個相對來說固定位置的認識主體去掌握世界。哈洛威並沒有徹底揚棄這點,她最大的貢獻是要去釐清「位置」的物質性與複雜性,尤其在當代的科學科技政權中,或是她所說的「支配的訊息學」,以及種種重要學科界線的內爆,包括科學家用以形塑世界觀的生物學和化學,以及生物學和資訊學等等。在1989年出版的《靈長類視線: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The Primate Vision: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導論一開始,哈洛威引用了南非博物學家尤金.馬雷(Eugene Marais)的話指出,「因為所有事物都必須以一個愛的行動為開端。」(For thus all things must begin with an act of love.)(Haraway 1989: 1)愛、權力和科學,交織在文化對於自然的建構過程中。哈洛威後來針對1996年知名的「索卡惡作劇」(Sokal hoax)指出,索可對於「社會建構論」的批判其實是基於誤解,他認為所謂的建構論者不相信現實的存在,這並不是真的。哈洛威再度引用馬雷,強調對科學的愛是知識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因素,而這適用於「科學家及其研究對象之間,還有研究科學的人及其主題之間的關係」(Haraway 1997c: 124)。她並沒有直接回應索卡等科學家對於建構論或解構的抨擊,她直言這其中有很多的情緒,報復、憤恨與惡意,在多年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s)裡,有很多說法都像是惡作劇,很難讓人當真,雖然這樣的戰爭是很真實的(Haraway 1997c: 123)。哈洛威以自己同時身為生物學家和科學史研究者的雙重經驗出發,去回應這些所謂的科學戰爭。她指出,無論是科學,或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探討,都是持續「製造意義」的實作,這樣的實作同時必然是歷史的,涉及到許多有著特定社會、文化、物質處境的行動者,包括人與非人的行動者,諸如「機器、有機體、人、土地、制度、金錢、分子,以及很多其他類型的事物」(Haraway 1997c: 124)。她強調,在科學知識中一直都有很多的故事,若是硬要把這些故事除去,那將是一種「知識論的避孕或科學的自虐」(epistemological contraception or scientific self-abuse)(Haraway 1997c: 126)。不僅故事重要,故事的故事更重要。換言之,故事如何被生產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社會存有論與知識論問題。就像哈洛威在〈同伴物種宣言〉中所說的,她要說的是「關於故事的故事」(Haraway 2003: 21),科學和文學在喻說中不斷流通運輸的正是故事。比如,metaplasm這個詞,在修辭學上是「詞形變化」,指的是一個字透過發音、音節和字母的增減或換位而產生改變;在生物學上則是「後生質」或「後成質」,指的是細胞裡面不屬於原生質(protoplasm)的、沒有生命的物質,因此也有譯成「副漿」。哈洛威很喜歡這類字詞的意象與隱喻,跨越學科分界,也跨越意義的限域,貌似錯誤,猶如新生。「後生質」代表「錯誤」,也就是一個轉折,而英文喻說(trope)的原意,一個關乎肉身的差異(Haraway 2003: 20-21)。換言之,科學作為有系統的知識(此為科學一詞的原意),並不是僅止於忠實地呈現事實,而是一個不斷在進行敘事的過程,不斷透過隱喻在說故事。但這並不表示沒有「現實」存在。而只是說現實的顯露不可能是沒有中介的。另一個很重要的點是政治倫理的參與。哈洛威提到自己的教學經驗,在反越戰的年代中,他們在對非本科系學生傳授生物學相關的知識時,乃是抱著一種公民教育的使命感。這並不是說科學才是啓蒙的唯一道路,反而必須指出,科學的實作本身早已透露出知識、技術、符號、政治、物質等層面都是連結交錯的。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正是如此製造得出。
生物學是一個政治論述,我們在其中必須致力於實作的每一個層次,包括技術上的、記號上的、道德上的、經濟上的、制度上的實作。除此之外,生物學也帶來了強烈的歡樂,包括知識的、情緒的、社會的和肉體上的歡樂。任何像這樣的東西,都不應該被輕易放棄,也不應該片面加以譴責或讚頌。(Haraway 1997c: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