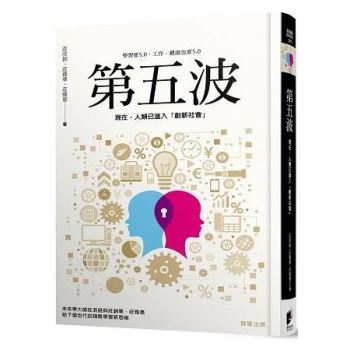第壹章 創新社會
時間移民
曾在台灣是金飯碗的金融業,最近有80萬員工面臨不轉型就淘汰;長期被視為鐵飯碗的師範畢業生,現在有四萬多名流浪教師;一直被視為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大學,開始接二連三的關閉,連被認為是鋼飯碗的大學教授都飯碗快不保;無人駕駛汽車的研發,將導致駕駛的工作機會減少。如同電腦排版取代了打字排版公司;教育部的博士資料有八千多位薪水22K;高學歷高失業率;啃老族越來越多,教育部青年署成立啃老族處理委員會;政府持續提出退休基金面臨未來的破產。
教授未來學多年,經常被媒體訪問上述問題。我的回答是:「會發生的事,必然會發生」。從未來學的角度看,這些問題有的早在幾十年前就種下的「因」,今日只是承擔其「果」。比如,退休基金破產,就是當初制度設計錯誤的「因」,造成將來必定破產的「果」。這在退休5.0的章節有詳細說明。啃老族主要則是家庭教育種下錯誤的「因」,所造成的結果,這在教養5.0的章節有系統性的說明。有的是隨著科技的發達,自然會形成。比如,三輪車被計程車取代;會計報表計算被電腦程式取代;銀行的存取款服務被ATM取代。
那何謂「未來學」?在課堂上,有學生問此一問題。這個名詞需要解釋一下。這是真實的故事,上我未來學的學生儀佩,有一次在課堂上說,儀佩的母親看到成績單說有一名課被指出曠課,要她注意。她跟她媽說,沒關係,偶爾兩堂缺課請假就是了。回家一看,成績單上那曠課的名稱就叫「未來學」。儀佩的母親誤以為是儀佩沒有來上課。
在我的課堂上,提出問題、交流意見、激盪腦力是常有的事。未來學是一門新興的學門,許多人誤解未來學是算命或預測術,其實未來學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下,已逐漸成熟成為一門學問。第一個提出未來學名詞的學者是吉爾費蘭(S.C.Gilfillan),他在其論文中說「未來學家(Mellontologist)是推論未來整體文明的人士,就如同考古學家能將史前文化合理的分析出來一般」。爾後,艾文.托弗勒(Alvin Toffler,1928),出版了《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第三波》(The Third Wave),引發了全球對未來學的重視。
在《未來的衝擊》一書中,托氏提出的未來「震撼」是指,個人在太短的時間內,接受了太多的外界變化,因適應不良而產生誤導與壓力。托弗勒強調,社會變遷的速度不會因人類的不適應,而緩慢下來,相反的,變遷的速度將越來越快。托弗勒預測的沒錯,現在社會變遷的速度,是他寫書時代的五倍以上。也因為「未來學」越來越受到重視,全球不少國家都成立了「未來學協會」,國內學校如淡江大學及佛光大學都設有「未來學研究所」。
由於社會變遷的速度急遽增加,且變遷的方式又與以往大不相同,致使在許多方面,連古老的格言「鑑往知來」、「以不變應萬變」已逐漸不能適用了。變遷的加快可從農業革命形成農業社會數千年,到工業革命形成工業社會不到兩百年,就快速引發一波波的科技文明浪潮。教育方式在這快速變遷的社會,同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各種新的教育改革理念如雨後春筍孕育而生,如學習革命、EQ重於IQ、新學力觀等。艾文。托佛勒指出:送小孩上第二波的學校,強調考試與背誦既有知識與標準答案,需要反覆練習。 這些教育方式是為工業社會時代的社會需要所設計。 在現在的知識社會中,已經不符時代需求。 為了面對新趨勢,美國已開設「新科技高中」,提供不給標準答案的教育,培養思考、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由於變遷的多樣性及快速,需要瞭解變遷的原因,才能「知變應變」。
梅德夫人(Mead,1901)對未來變遷有深入的研究,她提出的「後形文化」、「共形文化」及「先形文化」等觀念,清楚的分析了未來變遷的文化現象。「後形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乃指年輕人向年長的人學習的文化型態;「共形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則為同輩互相學習的文化型態;「先形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與後形文化相反,是年老的向年輕的學習的文化型態。
學生又曾在此向我提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分呢?」
我則回答:「哲學家培根講課時一再強調,學習任何知識,不能只看表面,要看知識的內涵,看能不能找出『Form』,也就是規則,萃取分析出知識內部的規則。」
「後形文化」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因為農業社會幾乎沒有變遷,下一代是上一代的翻版。活得越久,懂得越多。因此就會出現「我吃過的鹽,你吃過的米多」、「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多」的俗諺,這都是「後形文化」的產物。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後,社會開始變遷,但變遷速度不快,大約一個世代才有明顯的改變,所以,出現了「代溝」的名詞。在工業社會就是「共形文化」,是指各自的世代相互學習。到了第三波資訊社會後,變遷日益快速,下一代懂得新科技已超過上一代。締造了人類有史以來的特殊現象「世代超越」。
在解釋過後又曾有所領悟:「我學到第一個Form了,社會變遷的速度決定了哪種型態的文化。這個Form也告訴我們,在後形文化中,過去支配現在,在先行文化中則是未來支配現在。」
在這裡介紹第二個Form,「時間移民」,與「空間移民」的觀念。
這時學生儀佩問:「何謂時間移民?」
我反問儀佩:「如果要移民到阿拉伯,要不要準備?」
儀佩:「當然要啊!要學阿拉伯國家的語言,了解阿拉伯文化,學會在阿拉伯生存的謀生能力。」
我便回答:「沒錯,然而,為什麼要準備這些?因為阿拉伯跟我們是不同的社會。要移民到不同的社會,當然要準備。想想,阿拉伯為什麼跟我們是不同的社會,是因為空間不同造成不同的社會。」
此時庭安回應:「我知道了,因為空間不同會造成不同的社會,同樣的,因為時間不同,同樣的空間也會變成新的社會。如,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或是從「後形文化」進入「先形文化」。這就是『時間移民』。」
我回應庭安:「You got it。因為空間不同造成不同的社會,我們要移民過去,我們有警覺,要準備,否則很容易被淘汰。因為時間不同造成的新社會,當然也要有時間移民的準備。第二個Form是,社會持續變遷,時間移民是現在進行式,隨時要新社會的變化,以進行移民的準備。」
2000年我獲得宏碁創立的文教基金會的多專業獎,因為那時候我有六個專業。有朋友問我為何獲得此獎,
我回答:「因為工業社會一個專長就夠,資訊社會要兩個,知識社會則需要多專長。我在工業社會就看出來移民到未來的知識社會要多專長,所以,我及早學習多專長,所以,獲得該獎項。」
同樣的,看出未來社會需要多語言,所以,學習了多種語言,學習語言的方法將在語言5.0章中討論。
再以指導研究生為例。我指導的博士生拿到博士學位的有幾十位,其中一位於2014年就擔任國立大學校長。有不少現在於各大學擔任教務長或總務長及資訊中心主任等。比如,真理大學總務長周鈺和教授及北教大資訊中心主任林仁智教授。
1988年回國後,我擔任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主任時就鼓勵碩士生研讀博士。然而,2006年後,碩士生找我寫推薦信要讀博士時,我就建議它們到業界工作,等工作穩定發展,有興趣或需要再讀博士。
碩士生問我:「為什麼鼓勵學長讀博士,卻不贊成我讀博士。」
我則回答:「因為,社會變遷了。博士已經快過多了。一個社會不需要那麼多的教師,培養過多的教師,就會製造流浪教師。一個社會不需要那麼多的博士,培養過多的博士,就會製造流浪博士。你們再花五到六年讀博士,等你們畢業,很多機會都不見了。而且,因為少子化,大學教師的職缺也會大幅減少。」
許多學生聽我的建議,現在,在IT產業都有不錯的職務。近幾年,大學畢業生,找我寫推薦信,要申請碩士班。我的回應是,除非這個研究所,有特殊的專長。否則,先到業界工作,看自己的興趣及未來生涯的需要,再回來讀在職的碩士班。不要因為讀書而耽擱了工作機會及工作年資。在工業社會,花七到十年讀碩士到讀博士拿到學位,那種生涯規劃是OK的,因為博士少博士缺多。然而,當隨著時間從工業社會移民到了知識社會,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第二個Form「時間移民」要好好運用,不要被舊社會觀念束縛,要為新的社會而準備。下面另一個Form可以讓你更清楚,如何為移民未來而準備。
第三個Form,「萃往析來,鑑來知往」。在這快速變遷的社會,已無法光靠過去來探討未來了,甚至應培養未來觀,即「未來導向」才能解決現在的問題。「歷史導向」就是「鑑往知來」也就是農業社會的「後形文化」。由於下一代是上一代的翻版,所以,從以往的經驗就可以推動未來,形成「鑑往知來」。然而,進入資訊社會後,變遷加劇,農業社會的人看不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人看不到資訊社會。也因此,要先能分析出可能新社會的風貌,才能正確的為未來的社會而準備。所以,學習未來學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如何萃取分析出可能的未來社會。就如同托佛勒在四十多年前就分析出資訊社會形成,彼得.杜拉克在三十多年前就分析出知識社會形成。亦即「萃往析來」,從既有的資料分析出可能的未來。然後,以這個分析出來的未來社會當做「殷鑑」,以能正確準備走向未來,也就是「鑑來知往」,其意涵就是「未來導向」。簡而言之,第三個Form就是我們要學習分析判斷未來社會,然後,好好準備移民未來。教育部有八千多個博士的薪資收入資料,平均是兩萬兩千元,原因就是停留在工業社會的思維,以為讀到博士就會有高薪收入。不知道已經由時間移民到「高學歷高失業率」的新社會。
由於研究未來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獲得許多國家的政府重視。任何政府均要對施行的政策進行規劃,基本上規劃是為「未來」而設計,從這個觀點看,沒有未來觀的政策規劃是相當危險的。政治上有一句名言:「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這些設有未來研究單位的政府一定深知在這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沒有前瞻性及未來研究作決策之依據,極易產生錯誤的決策」。為增進規劃政策的品質,瑞典政府的內閣中就設有「未來部」,該部對未來的研究結果提供給各部會作決定政策之重要參考。此外,美國、法國、南韓甚至印度都在政府決策單位,設有未來研究機構。美國甚至在其小學及中學都開有未來學之課程。相信將來教育部門對未來學的重視會如同電腦一樣。屆時認知未來學(Future Literacy)可能就如同認知電腦(Computer Literacy)一樣成為教育中的必修課程。
時間移民
曾在台灣是金飯碗的金融業,最近有80萬員工面臨不轉型就淘汰;長期被視為鐵飯碗的師範畢業生,現在有四萬多名流浪教師;一直被視為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大學,開始接二連三的關閉,連被認為是鋼飯碗的大學教授都飯碗快不保;無人駕駛汽車的研發,將導致駕駛的工作機會減少。如同電腦排版取代了打字排版公司;教育部的博士資料有八千多位薪水22K;高學歷高失業率;啃老族越來越多,教育部青年署成立啃老族處理委員會;政府持續提出退休基金面臨未來的破產。
教授未來學多年,經常被媒體訪問上述問題。我的回答是:「會發生的事,必然會發生」。從未來學的角度看,這些問題有的早在幾十年前就種下的「因」,今日只是承擔其「果」。比如,退休基金破產,就是當初制度設計錯誤的「因」,造成將來必定破產的「果」。這在退休5.0的章節有詳細說明。啃老族主要則是家庭教育種下錯誤的「因」,所造成的結果,這在教養5.0的章節有系統性的說明。有的是隨著科技的發達,自然會形成。比如,三輪車被計程車取代;會計報表計算被電腦程式取代;銀行的存取款服務被ATM取代。
那何謂「未來學」?在課堂上,有學生問此一問題。這個名詞需要解釋一下。這是真實的故事,上我未來學的學生儀佩,有一次在課堂上說,儀佩的母親看到成績單說有一名課被指出曠課,要她注意。她跟她媽說,沒關係,偶爾兩堂缺課請假就是了。回家一看,成績單上那曠課的名稱就叫「未來學」。儀佩的母親誤以為是儀佩沒有來上課。
在我的課堂上,提出問題、交流意見、激盪腦力是常有的事。未來學是一門新興的學門,許多人誤解未來學是算命或預測術,其實未來學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下,已逐漸成熟成為一門學問。第一個提出未來學名詞的學者是吉爾費蘭(S.C.Gilfillan),他在其論文中說「未來學家(Mellontologist)是推論未來整體文明的人士,就如同考古學家能將史前文化合理的分析出來一般」。爾後,艾文.托弗勒(Alvin Toffler,1928),出版了《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第三波》(The Third Wave),引發了全球對未來學的重視。
在《未來的衝擊》一書中,托氏提出的未來「震撼」是指,個人在太短的時間內,接受了太多的外界變化,因適應不良而產生誤導與壓力。托弗勒強調,社會變遷的速度不會因人類的不適應,而緩慢下來,相反的,變遷的速度將越來越快。托弗勒預測的沒錯,現在社會變遷的速度,是他寫書時代的五倍以上。也因為「未來學」越來越受到重視,全球不少國家都成立了「未來學協會」,國內學校如淡江大學及佛光大學都設有「未來學研究所」。
由於社會變遷的速度急遽增加,且變遷的方式又與以往大不相同,致使在許多方面,連古老的格言「鑑往知來」、「以不變應萬變」已逐漸不能適用了。變遷的加快可從農業革命形成農業社會數千年,到工業革命形成工業社會不到兩百年,就快速引發一波波的科技文明浪潮。教育方式在這快速變遷的社會,同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各種新的教育改革理念如雨後春筍孕育而生,如學習革命、EQ重於IQ、新學力觀等。艾文。托佛勒指出:送小孩上第二波的學校,強調考試與背誦既有知識與標準答案,需要反覆練習。 這些教育方式是為工業社會時代的社會需要所設計。 在現在的知識社會中,已經不符時代需求。 為了面對新趨勢,美國已開設「新科技高中」,提供不給標準答案的教育,培養思考、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由於變遷的多樣性及快速,需要瞭解變遷的原因,才能「知變應變」。
梅德夫人(Mead,1901)對未來變遷有深入的研究,她提出的「後形文化」、「共形文化」及「先形文化」等觀念,清楚的分析了未來變遷的文化現象。「後形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乃指年輕人向年長的人學習的文化型態;「共形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則為同輩互相學習的文化型態;「先形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與後形文化相反,是年老的向年輕的學習的文化型態。
學生又曾在此向我提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分呢?」
我則回答:「哲學家培根講課時一再強調,學習任何知識,不能只看表面,要看知識的內涵,看能不能找出『Form』,也就是規則,萃取分析出知識內部的規則。」
「後形文化」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因為農業社會幾乎沒有變遷,下一代是上一代的翻版。活得越久,懂得越多。因此就會出現「我吃過的鹽,你吃過的米多」、「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多」的俗諺,這都是「後形文化」的產物。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後,社會開始變遷,但變遷速度不快,大約一個世代才有明顯的改變,所以,出現了「代溝」的名詞。在工業社會就是「共形文化」,是指各自的世代相互學習。到了第三波資訊社會後,變遷日益快速,下一代懂得新科技已超過上一代。締造了人類有史以來的特殊現象「世代超越」。
在解釋過後又曾有所領悟:「我學到第一個Form了,社會變遷的速度決定了哪種型態的文化。這個Form也告訴我們,在後形文化中,過去支配現在,在先行文化中則是未來支配現在。」
在這裡介紹第二個Form,「時間移民」,與「空間移民」的觀念。
這時學生儀佩問:「何謂時間移民?」
我反問儀佩:「如果要移民到阿拉伯,要不要準備?」
儀佩:「當然要啊!要學阿拉伯國家的語言,了解阿拉伯文化,學會在阿拉伯生存的謀生能力。」
我便回答:「沒錯,然而,為什麼要準備這些?因為阿拉伯跟我們是不同的社會。要移民到不同的社會,當然要準備。想想,阿拉伯為什麼跟我們是不同的社會,是因為空間不同造成不同的社會。」
此時庭安回應:「我知道了,因為空間不同會造成不同的社會,同樣的,因為時間不同,同樣的空間也會變成新的社會。如,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或是從「後形文化」進入「先形文化」。這就是『時間移民』。」
我回應庭安:「You got it。因為空間不同造成不同的社會,我們要移民過去,我們有警覺,要準備,否則很容易被淘汰。因為時間不同造成的新社會,當然也要有時間移民的準備。第二個Form是,社會持續變遷,時間移民是現在進行式,隨時要新社會的變化,以進行移民的準備。」
2000年我獲得宏碁創立的文教基金會的多專業獎,因為那時候我有六個專業。有朋友問我為何獲得此獎,
我回答:「因為工業社會一個專長就夠,資訊社會要兩個,知識社會則需要多專長。我在工業社會就看出來移民到未來的知識社會要多專長,所以,我及早學習多專長,所以,獲得該獎項。」
同樣的,看出未來社會需要多語言,所以,學習了多種語言,學習語言的方法將在語言5.0章中討論。
再以指導研究生為例。我指導的博士生拿到博士學位的有幾十位,其中一位於2014年就擔任國立大學校長。有不少現在於各大學擔任教務長或總務長及資訊中心主任等。比如,真理大學總務長周鈺和教授及北教大資訊中心主任林仁智教授。
1988年回國後,我擔任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主任時就鼓勵碩士生研讀博士。然而,2006年後,碩士生找我寫推薦信要讀博士時,我就建議它們到業界工作,等工作穩定發展,有興趣或需要再讀博士。
碩士生問我:「為什麼鼓勵學長讀博士,卻不贊成我讀博士。」
我則回答:「因為,社會變遷了。博士已經快過多了。一個社會不需要那麼多的教師,培養過多的教師,就會製造流浪教師。一個社會不需要那麼多的博士,培養過多的博士,就會製造流浪博士。你們再花五到六年讀博士,等你們畢業,很多機會都不見了。而且,因為少子化,大學教師的職缺也會大幅減少。」
許多學生聽我的建議,現在,在IT產業都有不錯的職務。近幾年,大學畢業生,找我寫推薦信,要申請碩士班。我的回應是,除非這個研究所,有特殊的專長。否則,先到業界工作,看自己的興趣及未來生涯的需要,再回來讀在職的碩士班。不要因為讀書而耽擱了工作機會及工作年資。在工業社會,花七到十年讀碩士到讀博士拿到學位,那種生涯規劃是OK的,因為博士少博士缺多。然而,當隨著時間從工業社會移民到了知識社會,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第二個Form「時間移民」要好好運用,不要被舊社會觀念束縛,要為新的社會而準備。下面另一個Form可以讓你更清楚,如何為移民未來而準備。
第三個Form,「萃往析來,鑑來知往」。在這快速變遷的社會,已無法光靠過去來探討未來了,甚至應培養未來觀,即「未來導向」才能解決現在的問題。「歷史導向」就是「鑑往知來」也就是農業社會的「後形文化」。由於下一代是上一代的翻版,所以,從以往的經驗就可以推動未來,形成「鑑往知來」。然而,進入資訊社會後,變遷加劇,農業社會的人看不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人看不到資訊社會。也因此,要先能分析出可能新社會的風貌,才能正確的為未來的社會而準備。所以,學習未來學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如何萃取分析出可能的未來社會。就如同托佛勒在四十多年前就分析出資訊社會形成,彼得.杜拉克在三十多年前就分析出知識社會形成。亦即「萃往析來」,從既有的資料分析出可能的未來。然後,以這個分析出來的未來社會當做「殷鑑」,以能正確準備走向未來,也就是「鑑來知往」,其意涵就是「未來導向」。簡而言之,第三個Form就是我們要學習分析判斷未來社會,然後,好好準備移民未來。教育部有八千多個博士的薪資收入資料,平均是兩萬兩千元,原因就是停留在工業社會的思維,以為讀到博士就會有高薪收入。不知道已經由時間移民到「高學歷高失業率」的新社會。
由於研究未來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獲得許多國家的政府重視。任何政府均要對施行的政策進行規劃,基本上規劃是為「未來」而設計,從這個觀點看,沒有未來觀的政策規劃是相當危險的。政治上有一句名言:「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這些設有未來研究單位的政府一定深知在這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沒有前瞻性及未來研究作決策之依據,極易產生錯誤的決策」。為增進規劃政策的品質,瑞典政府的內閣中就設有「未來部」,該部對未來的研究結果提供給各部會作決定政策之重要參考。此外,美國、法國、南韓甚至印度都在政府決策單位,設有未來研究機構。美國甚至在其小學及中學都開有未來學之課程。相信將來教育部門對未來學的重視會如同電腦一樣。屆時認知未來學(Future Literacy)可能就如同認知電腦(Computer Literacy)一樣成為教育中的必修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