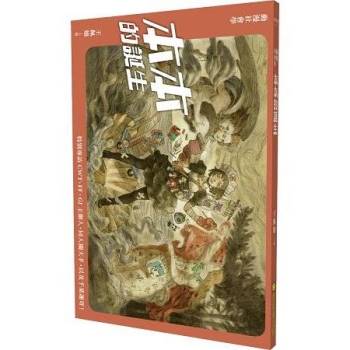〈這就是愛──從迷與二次創作談起〉
李衣雲
現今,世界各地的動漫同人展蓬勃發展,日本的Comiket、美國的Comic-con入場人數動輒數十萬,台灣的CWT、FF每場也都有數萬人,寒暑假時更是上看十萬人,很難想像1975年第一場Comiket的入場人數只有600人,而台灣在90年代的同人展更是雖小卻不擁擠。
在這些會場上,除了排隊排得殺氣十足的大手攤位之外,總是會看到還有許許多多小攤位,沒有宣傳、不會招攬,攤位販售人默默地畫著自己的圖、或沉浸在社入時搶到的本子裡,堅守陣地,並不因乏人問津而提早退場。
會場外,扮成各種角色的COSER們,擺著角色著名的姿勢。問他們:「39度的氣溫,把自己封死在紙盒里不熱嗎?」──這位扮的是鋼彈,實在太像了,完全看不出是紙作的;「寒流來襲,露出絕對領域不冷嗎?」──其實太多角色符合這項描述了,不過這位是月光仙子──答案當然是會熱和會冷。
走在會場附近(包括方圓三公里內的車站),類似以下的對話有如電波般不時竄入耳中:
「因為要寫本趕印,報告交不出來,被當了。」
「為了作這幾套科學小飛俠,我們五天五夜沒睡。」
「為了要出角,每天不能吃三餐以外的任何東西,保持身材。」
「繪師畫的根本不是能穿得上身體的樣式呀!為了一條腰帶,花了我N小時在研究和服。」
「前面排的那個人竟然還邊翻本邊考慮要不要買,結果最後一本被旁邊那排的人買走了!沒有事先作功課就來戰場,太可惡了!」
(以下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現象的製造者往往「其詞若有憾/怨焉,實則喜也」。然而,對這樣的狀況竟甘之如飴,絕不是因為他們是被虐狂,而是因為──愛。
同人誌這個名詞,原本指的是一群同好合資自費出版自己的作品。日本在明治時期的文學界,印刷術不像今日這麼普及又便宜,要找出版社出書很困難,要獨力出一本書也很難,所以同人誌這樣的產物就順勢而生。除了原創作品外,慢慢地也出現了自費出版的文學評論、漫畫評論,以及閱讀原作後衍生出來的二次創作 同人誌。隨著印刷費的下降,個人誌成了同人圈的主流。
所謂「誌」,指的是紙本,但在網路普及之後,要分享自己的作品不一定要花錢出版成冊,更不一定是用文字或圖畫表現,還可以剪接影音、製作遊戲或角色的配件、Q版公仔,甚至將角色概念化作出代表色手環、飾品等,COSPLAY更是完整複製出角色的實像。從20世紀末以來,同人的概念已經脫離了「同人誌」的平面範疇,迷們的心血結晶,我將之通稱為同人作品。
要作出一個同人作品,花費的金錢與心力絕對不小,因為這個作品其實代表了迷們自我的表現。對消費者來說,選擇這個角色/商品而不是那個角色/商品的原因,從來都不只是客觀的,還包括了主體經驗的投注與詮釋,也就是P. 布爾迪厄所說的「品味」。品味的形成與我們在社會中所處的社會地位、生活經驗、價值觀、自我等息息相關。也因此,當我們在消費一樣文化商品時,也是在實踐自己的品味,而他人也把我們所展現出來的品味,當作理解我們的一個指標。
那麼,當一群人共同去想像、感受一個文本、一個角色、一個文化商品時,這些人彼此間容易產生親近感,甚至進一步形成同好團體。任何的團體的形成,成員間必然要有某種關連的存在,或許是利益、或許是感情、價值觀,讓成員們意識到原來「我們是一樣的」,也相信對方對自己具有同樣的想法,如此一來,一個團體才能夠穩定下來。尤其是當這個團體是以某種情感或價值為基礎時,彼此間更容易產生同情或同理心。舉例來說,在路上看到一個人跌倒了,你會去扶起他,這或許出於「我們都是人」的想法,但如果摔跌的是自己的同學、朋友、戀人、或是家人,你可能就不只是扶起他,還會對他的受傷感到心疼。這就是共同體的基礎。以二次創作來說,原作或角色對讀者提供了一種共同的價值或情感的對象,使得迷們能夠形成一個「我群」,並將「我們」與不是同好的「他們」區分開來。
這樣的「我群」對著迷有什麼幫助呢?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對所有經驗過同人圈的人來說,在連載休刊、出刊太慢、對劇情不滿(足)、喜愛的角色出場太少等等時候,迷們滿腔無處可去的熱情要到哪裡找著落?同人作品是最佳選項之一。有了同人作品,原作連載的兩個時間點之間,有了讓愛繼續的橋樑,不然,以《全職獵人》不定期長時間休刊的狀態,龐大讀者怎麼維繫對它的情感?要是實際生活裡的戀人,在這種狀態下,大概早因「感情不在」宣告分手了吧。
更進一步來說,當「我群」從創作與閱讀的互動,進入到會互相交談、討論劇情甚至實際的生活後,「我群」的凝聚力更滲入迷們的生活,即使對作品的愛有消退的跡像,往往也會努力挽留這份愛,因為它代表了屬於「我群」的標誌。
所以說,一個人挖坑大多比較淺,一群人一起挖坑,就會是要爬出來很難,要拖人下去很容易的深度了。
當然,這種熱情的延長也還是有時限的,畢竟沒有了原作,以原作為基底的二次創作無法存在,所以,一部作品完結後,以原作為共同價值的迷群與二創也會逐漸消散,2000年代在日本同人界紅極一時的《鋼之鍊金術師》,如今已是往事不可追,那些曾經敗家來的戰利品,也就成為迷們架上曾經愛過的紀念。
既然我們對於文化商品的消費,投射了自己的欲望與認同,某種程度上,這個文化商品就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無機物,而已被「人類化」,成為我們理想自我的投射。
比如說,從物質的概念來看,說到底公仔不過就是塊塑膠,一塊塑膠掉在地上,不過就是沾點灰而已,稀罕嗎?但如果這塊塑膠長得跟《進擊的巨人》的兵長一樣…竟然讓利威爾吃灰?!!趕快撿起來給他拍拍,順便跟他說一下今日沒有好好照顧他的歉意。旁邊沒看過《進擊》的路人經過,大約覺得這個自言自語的傢伙有病需要被遠離,但萬一同樣是兵長迷,雖然不必然會走上前搭訕,但也一定會覺得還好兵長又被好好抱起來了。再或者在巧克力展示櫃前看見蝙蝠俠人偶在宣傳,立刻停下來拍照,臉上帶著詭異的微笑,臨走前不忘買一盒巧克力。至於旁邊那個綠巨人…什麼?旁邊有這個物體存在嗎?
這就是人類化或擬主體化。對迷們來說,自己喜愛的文化商品絕對不是一個冰冷的無機物,若非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分身與表徵,誰願意在已經不算輕的包包上加諸如此多的吊飾?塑膠也是有重量的!
人在生命中不斷追求著意義,文化就是人們界定意義的展現與源頭—無論是所論的高級文化或大眾文化。因此,公仔也好,原作也好,二創也好,這些都是我們對自己存在意義的一種表現。
2014年日本出了一系列的動漫角色面膜,面膜設計成貼在臉上會呈現角色的臉,從《進擊的巨人》裡的巨人、《北斗神拳》的拳四郎,到多啦A夢和鋼鐵人皆陣列在前。為什麼選擇多啦A夢而不是鋼鐵人?因為對迷們來說,必須是這個角色才有意義。面膜初始的目的,是為了要讓臉部皮膚緊緻保溼,只是要用面膜的人,應該不會選擇印著拳四郎或巨人包裝的面膜,萬一用了以後膚質變得跟他們一樣呢?!但是迷們不在意。他們選擇這個而不是那個包裝的面膜,是因為唯有這部而非那部作品乃至角色對他們才有意義,重要的不在實用,而在投射了自身意義的符號價值。
於是,當我們喜愛的文化商品被別人嫌棄時,會讓我們產生整個人格都被否定了的感覺,而我們也會努力地將自己的愛推薦給別人,因為他人對這些文化商品的認可,就等於認同了我們的品味與自我。這也是動漫在台灣的1990年代前,受到政治乃至主流社會的壓制,依然能夠草根地活下來的原因之一。
迷們像這樣積極地推坑、二創,來滿足自己的不滿足,源起於對文化作品的愛。為什麼說是愛?因為愛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理性計算,甚至具備了獻身性。
在現代社會裡,作什麼事情多半都會落在貨幣交換的計算裡。但是,當一個人三天三夜不睡就為了出本趕同人展,不只沒稿費,還要交參展報名費,更不要說當天擺攤是無薪的,更有可能擺了一天攤只賣出幾本,如果拿這些時間去麥當勞打工,荷包大約也有數千元進帳,但應該不會有迷們說:「早知道就拿這時間去打工了。」(如果說了,應該會被「我群」以「破壞愛的神聖性」之名逐出群體。)就算萬一因此沒去上課沒交報告被老師當了,怪罪的對象也不會是那個愛的對象。
這就是超越了理性計算的愛的力量。
迷的獻身性在二次元的作品與角色上更能突顯出來。因為基本上,真人的偶像會結婚、會解散、會改變或不長進,即使迷知道他/她永遠不可能回應,但對方既是真實存在的人,迷們仍然會抱持著一絲期待與幻想,會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得到回報。但二次元不同,角色們既真又幻,是迷們碰觸不到的存在,沒有期待,也就不會計算彼此的付出是否等量。當然,這裡說的獻身絕不是指偶像迷們荷包出的血會比較少,也不是指付出的愛比較少,事實上,在日本,傑尼斯與寶塚迷裡有著明顯的階級排序,要能見到偶像,還得服從迷團體中的年功序列,箇中甘苦,只有熱愛中的迷們才知道吧。
李衣雲
現今,世界各地的動漫同人展蓬勃發展,日本的Comiket、美國的Comic-con入場人數動輒數十萬,台灣的CWT、FF每場也都有數萬人,寒暑假時更是上看十萬人,很難想像1975年第一場Comiket的入場人數只有600人,而台灣在90年代的同人展更是雖小卻不擁擠。
在這些會場上,除了排隊排得殺氣十足的大手攤位之外,總是會看到還有許許多多小攤位,沒有宣傳、不會招攬,攤位販售人默默地畫著自己的圖、或沉浸在社入時搶到的本子裡,堅守陣地,並不因乏人問津而提早退場。
會場外,扮成各種角色的COSER們,擺著角色著名的姿勢。問他們:「39度的氣溫,把自己封死在紙盒里不熱嗎?」──這位扮的是鋼彈,實在太像了,完全看不出是紙作的;「寒流來襲,露出絕對領域不冷嗎?」──其實太多角色符合這項描述了,不過這位是月光仙子──答案當然是會熱和會冷。
走在會場附近(包括方圓三公里內的車站),類似以下的對話有如電波般不時竄入耳中:
「因為要寫本趕印,報告交不出來,被當了。」
「為了作這幾套科學小飛俠,我們五天五夜沒睡。」
「為了要出角,每天不能吃三餐以外的任何東西,保持身材。」
「繪師畫的根本不是能穿得上身體的樣式呀!為了一條腰帶,花了我N小時在研究和服。」
「前面排的那個人竟然還邊翻本邊考慮要不要買,結果最後一本被旁邊那排的人買走了!沒有事先作功課就來戰場,太可惡了!」
(以下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現象的製造者往往「其詞若有憾/怨焉,實則喜也」。然而,對這樣的狀況竟甘之如飴,絕不是因為他們是被虐狂,而是因為──愛。
同人誌這個名詞,原本指的是一群同好合資自費出版自己的作品。日本在明治時期的文學界,印刷術不像今日這麼普及又便宜,要找出版社出書很困難,要獨力出一本書也很難,所以同人誌這樣的產物就順勢而生。除了原創作品外,慢慢地也出現了自費出版的文學評論、漫畫評論,以及閱讀原作後衍生出來的二次創作 同人誌。隨著印刷費的下降,個人誌成了同人圈的主流。
所謂「誌」,指的是紙本,但在網路普及之後,要分享自己的作品不一定要花錢出版成冊,更不一定是用文字或圖畫表現,還可以剪接影音、製作遊戲或角色的配件、Q版公仔,甚至將角色概念化作出代表色手環、飾品等,COSPLAY更是完整複製出角色的實像。從20世紀末以來,同人的概念已經脫離了「同人誌」的平面範疇,迷們的心血結晶,我將之通稱為同人作品。
要作出一個同人作品,花費的金錢與心力絕對不小,因為這個作品其實代表了迷們自我的表現。對消費者來說,選擇這個角色/商品而不是那個角色/商品的原因,從來都不只是客觀的,還包括了主體經驗的投注與詮釋,也就是P. 布爾迪厄所說的「品味」。品味的形成與我們在社會中所處的社會地位、生活經驗、價值觀、自我等息息相關。也因此,當我們在消費一樣文化商品時,也是在實踐自己的品味,而他人也把我們所展現出來的品味,當作理解我們的一個指標。
那麼,當一群人共同去想像、感受一個文本、一個角色、一個文化商品時,這些人彼此間容易產生親近感,甚至進一步形成同好團體。任何的團體的形成,成員間必然要有某種關連的存在,或許是利益、或許是感情、價值觀,讓成員們意識到原來「我們是一樣的」,也相信對方對自己具有同樣的想法,如此一來,一個團體才能夠穩定下來。尤其是當這個團體是以某種情感或價值為基礎時,彼此間更容易產生同情或同理心。舉例來說,在路上看到一個人跌倒了,你會去扶起他,這或許出於「我們都是人」的想法,但如果摔跌的是自己的同學、朋友、戀人、或是家人,你可能就不只是扶起他,還會對他的受傷感到心疼。這就是共同體的基礎。以二次創作來說,原作或角色對讀者提供了一種共同的價值或情感的對象,使得迷們能夠形成一個「我群」,並將「我們」與不是同好的「他們」區分開來。
這樣的「我群」對著迷有什麼幫助呢?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對所有經驗過同人圈的人來說,在連載休刊、出刊太慢、對劇情不滿(足)、喜愛的角色出場太少等等時候,迷們滿腔無處可去的熱情要到哪裡找著落?同人作品是最佳選項之一。有了同人作品,原作連載的兩個時間點之間,有了讓愛繼續的橋樑,不然,以《全職獵人》不定期長時間休刊的狀態,龐大讀者怎麼維繫對它的情感?要是實際生活裡的戀人,在這種狀態下,大概早因「感情不在」宣告分手了吧。
更進一步來說,當「我群」從創作與閱讀的互動,進入到會互相交談、討論劇情甚至實際的生活後,「我群」的凝聚力更滲入迷們的生活,即使對作品的愛有消退的跡像,往往也會努力挽留這份愛,因為它代表了屬於「我群」的標誌。
所以說,一個人挖坑大多比較淺,一群人一起挖坑,就會是要爬出來很難,要拖人下去很容易的深度了。
當然,這種熱情的延長也還是有時限的,畢竟沒有了原作,以原作為基底的二次創作無法存在,所以,一部作品完結後,以原作為共同價值的迷群與二創也會逐漸消散,2000年代在日本同人界紅極一時的《鋼之鍊金術師》,如今已是往事不可追,那些曾經敗家來的戰利品,也就成為迷們架上曾經愛過的紀念。
既然我們對於文化商品的消費,投射了自己的欲望與認同,某種程度上,這個文化商品就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無機物,而已被「人類化」,成為我們理想自我的投射。
比如說,從物質的概念來看,說到底公仔不過就是塊塑膠,一塊塑膠掉在地上,不過就是沾點灰而已,稀罕嗎?但如果這塊塑膠長得跟《進擊的巨人》的兵長一樣…竟然讓利威爾吃灰?!!趕快撿起來給他拍拍,順便跟他說一下今日沒有好好照顧他的歉意。旁邊沒看過《進擊》的路人經過,大約覺得這個自言自語的傢伙有病需要被遠離,但萬一同樣是兵長迷,雖然不必然會走上前搭訕,但也一定會覺得還好兵長又被好好抱起來了。再或者在巧克力展示櫃前看見蝙蝠俠人偶在宣傳,立刻停下來拍照,臉上帶著詭異的微笑,臨走前不忘買一盒巧克力。至於旁邊那個綠巨人…什麼?旁邊有這個物體存在嗎?
這就是人類化或擬主體化。對迷們來說,自己喜愛的文化商品絕對不是一個冰冷的無機物,若非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分身與表徵,誰願意在已經不算輕的包包上加諸如此多的吊飾?塑膠也是有重量的!
人在生命中不斷追求著意義,文化就是人們界定意義的展現與源頭—無論是所論的高級文化或大眾文化。因此,公仔也好,原作也好,二創也好,這些都是我們對自己存在意義的一種表現。
2014年日本出了一系列的動漫角色面膜,面膜設計成貼在臉上會呈現角色的臉,從《進擊的巨人》裡的巨人、《北斗神拳》的拳四郎,到多啦A夢和鋼鐵人皆陣列在前。為什麼選擇多啦A夢而不是鋼鐵人?因為對迷們來說,必須是這個角色才有意義。面膜初始的目的,是為了要讓臉部皮膚緊緻保溼,只是要用面膜的人,應該不會選擇印著拳四郎或巨人包裝的面膜,萬一用了以後膚質變得跟他們一樣呢?!但是迷們不在意。他們選擇這個而不是那個包裝的面膜,是因為唯有這部而非那部作品乃至角色對他們才有意義,重要的不在實用,而在投射了自身意義的符號價值。
於是,當我們喜愛的文化商品被別人嫌棄時,會讓我們產生整個人格都被否定了的感覺,而我們也會努力地將自己的愛推薦給別人,因為他人對這些文化商品的認可,就等於認同了我們的品味與自我。這也是動漫在台灣的1990年代前,受到政治乃至主流社會的壓制,依然能夠草根地活下來的原因之一。
迷們像這樣積極地推坑、二創,來滿足自己的不滿足,源起於對文化作品的愛。為什麼說是愛?因為愛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理性計算,甚至具備了獻身性。
在現代社會裡,作什麼事情多半都會落在貨幣交換的計算裡。但是,當一個人三天三夜不睡就為了出本趕同人展,不只沒稿費,還要交參展報名費,更不要說當天擺攤是無薪的,更有可能擺了一天攤只賣出幾本,如果拿這些時間去麥當勞打工,荷包大約也有數千元進帳,但應該不會有迷們說:「早知道就拿這時間去打工了。」(如果說了,應該會被「我群」以「破壞愛的神聖性」之名逐出群體。)就算萬一因此沒去上課沒交報告被老師當了,怪罪的對象也不會是那個愛的對象。
這就是超越了理性計算的愛的力量。
迷的獻身性在二次元的作品與角色上更能突顯出來。因為基本上,真人的偶像會結婚、會解散、會改變或不長進,即使迷知道他/她永遠不可能回應,但對方既是真實存在的人,迷們仍然會抱持著一絲期待與幻想,會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得到回報。但二次元不同,角色們既真又幻,是迷們碰觸不到的存在,沒有期待,也就不會計算彼此的付出是否等量。當然,這裡說的獻身絕不是指偶像迷們荷包出的血會比較少,也不是指付出的愛比較少,事實上,在日本,傑尼斯與寶塚迷裡有著明顯的階級排序,要能見到偶像,還得服從迷團體中的年功序列,箇中甘苦,只有熱愛中的迷們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