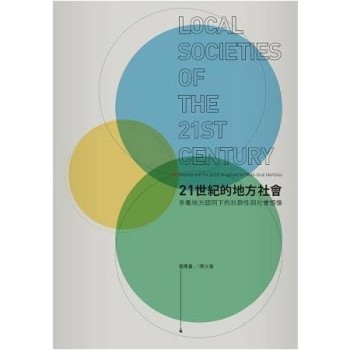一、序曲:當代東埔社是否仍是個地方社會?
新自由主義化對於地方社會是否造成影響?若有,其影響係以何種方式進行?造成怎樣的後果?讓筆者以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的東埔社之個案研究來具體回答。自日治時期以來,在特定地理空間範圍中發展出文化傳統的東埔社與整個陳有蘭溪流域,在1999年921災後重建後,納入大臺中地區的消費市場。當時新修建的快速道路,將東埔社到臺中間的通車時間,由原先的三、四小時縮短為兩小時,從而使當時由國際資金在該地區投資設立的十個大賣場,迅速吸收了整個大臺中地區的消費者。這造成了東埔社布農人開始每個星期驅車前往臺中大賣場,購足一星期所需日用品及食物的生活習慣。此一消費型態與生活圈的形成,導致二戰之後做為陳有蘭溪流域對外的交通及商業中心的水里,生意一落千丈,快速蕭條。到了2000年,資本額介於前述國際資金與水里原有商店之間的國內興農超商,正式進駐水里設點,部分東埔社及陳有蘭溪流域的布農人,重新前往水里採購食品及日用品,不再獨厚臺中的大賣場。興農超商的成功讓法商家樂福察覺到大臺中的腹地仍有巨大商機,同年便進軍南投市設分店。此舉再次改變東埔社布農人從事消費活動的空間範圍。至少,截至2012年,大部分擁有私家轎車的東埔社布農家庭,多半選擇前往南投市的家樂福大賣場採買日常生活所需。由上可見,隨著新資本的不斷投入,整個大臺中消費性區域體系內部因而產生了一連串細緻的再結構過程與重組,導致東埔社居民的消費行為更加異質化,同時帶來了不同的地方感。
事實上,做為新自由主義化動力的新資本前仆後繼進入地方社會,以商場建築、機構、交通網絡等形式具體現身並發揮作用,持續影響地方社會人們的生活與各項活動。除消費之外,當地醫療體系同樣因著新資本的投入而產生變化。在921災後重建改善區域交通網絡後,東埔社居民生病時,不再像過去那樣前往水里或埔里就醫,而是直接驅車到臺中榮總、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等教學醫院掛號,重症患者更是如此。事實上,當時從東埔社開車到埔里所需的時間,竟然比前往臺中更費時,這使得上述新的就醫習慣,成了難以挽回的趨勢。猶有進之,此一就醫習慣更使得水里原有的私人診所因病人紛紛流失而難以維持。這些私人診所只得另起爐灶,遷往和社及信義等這些未有醫療院所進駐的山區偏鄉,就近吸收非重症的與常見疾病的患者。此時,落入醫療真空狀態的水里,吸引了資金較上述私人診所更為雄厚的埔里基督長老教醫院及彰化基督長老教醫院,於2004年分別在水里及南投建立分院(東埔社布農人稱之為「水基」及「南基」)。此後,東埔社及陳有蘭溪流域的居民的就醫習慣隨之改變:若遇到感冒這類常見疾病,就近前往和社的私人診所看病;但若罹患稍微嚴重的疾病,就前往水基及南基,而不再像過去一樣前往較遠的臺中榮總或埔里基督教醫院看病。隨著東埔社人就醫地點的日益多元,當地人也開始有了與過去不同的地方感。這種因新資本不斷投入而產生不斷再結構的過程,同樣發生在交通、教育、觀光等其他層面,進而影響人們的具體活動。
其中,由於921災後重建導致交通運輸系統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快速道路及2007年高鐵全線通車,使得東埔社布農人習於以自用小客車代步,導致原本行駛水里到臺中路段的國光客運及員林客運,因無法承受虧損而必須停掉這些偏遠路線。其中,國光客運改變營運策略,轉而利用快速道路及高速道路去經營往返臺北與南投及南投到南部(嘉義、臺南、高雄)這類全新的路線,而員林客運繼續經營南投與彰化、員林、雲林等地的縣級路線。如此一來,大臺中的偏遠地區完全失去公共交通的服務。在此情形下,資本額低於國光客運及員林客運的總達客運,開始以21人座小型巴士有效地經營這些被放棄的偏遠路線,使交通運輸網路重又進行了再結構過程。此外,高鐵的通車促使統聯得以開拓南投市到新烏日的路線,方便南投居民銜接高鐵。同樣,原本早已乏人問津的集集線鐵道,因為新自由主義化帶來鐵道沿線觀光產業的快速發展,鐵路局便將該線延伸至臺中,使東埔村的溫泉觀光區及新中橫直接納入大臺中地區的休閒旅遊與觀光景點,讓整個大臺中地區因而更容易與新烏日的高鐵站接軌。這些相互銜接的交通要道形成了一條快捷、平價的路線,成為東埔社居民前往北臺灣或南臺灣時的最佳選擇。
由前述,我們看到消費物資、醫療、交通甚至觀光等產業,因不同額度的新資本陸續進入地方社會不斷進行再結構的過程,導致大臺中地區區域內部的不斷重整。最明顯的就是原本做為南投縣政治行政中心的南投市,因為上述各種產業在921災後重建之後陸續匯聚至此,躍身成為大臺中地區僅次臺中市的新都會及金融中心,取代了中興新村、草屯、水里這些戰後新興市鎮。在區域不斷再結構過程的同時,東埔社布農人更在聚落層次之上,發展出各種範圍不同卻又不完全重疊的新興區域活動範疇。
例如,921災後重建帶來交通及溝通工具的快速發展,使得原本僅在聚落內舉行的生命儀禮,因跨聚落親屬之間的聯繫與彼此關係之維繫,已從單一聚落擴大到陳有蘭溪流域的八個聚落,這點在婚禮的實踐最為突顯。原本在東埔社,婚禮時主人家只需宰殺三頭豬,分送給聚落成員與女方父系親屬及其聚落成員共享。在當代,為了讓整個陳有蘭溪流域的親屬都能分得豬肉,婚禮主人家革新了舊日的共享規範,將宰殺豬隻的數目增加至十八頭以上。一方面,這種將陳有蘭溪流域的親屬納入生命儀禮之交換與共享範圍內的實踐,幾乎同時表現在其他的親屬儀式活動上。例如,小孩成長禮(Magalav或Manqaul)中分豬肉回贈母親娘家的儀式、或者婚出女兒一起殺豬回報娘家的新儀式、或者婚出女兒在母親節時必須返回娘家同祝等活動,皆以陳有蘭溪流域為主要的地域範疇,有別於過去以聚落為生命儀禮主要進行的單位。甚至,聚落內日益增加的異族通婚,讓親屬關係不僅超越陳有蘭溪流域,更跨越國家領土的範圍。簡言之,本世紀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使得那些與親屬相關的社會活動,超越了既有的聚落單位,轉而以陳有蘭溪流域的區域體系為主要的地域範疇。另一方面,某些儀式或社會活動在本世紀也產生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小孩成長禮的分豬肉。當出嫁女兒在小孩順利成長時要回報娘家的祝福時,必須宰豬,並將豬肉分贈給娘家聚落的父系氏族成員。而這些接受婚出女兒贈與之豬肉的氏族成員,往往會集資殺豬,回送給所有婚出到陳有蘭溪流域的女子。當這些婚出的女子收到來自父系氏族餽贈的豬肉後,會再次集資殺豬,回請娘家的父系氏族成員。由於這些新增的豬肉分贈與回贈,均是雙方自願出資進行的交換,並非傳統儀式上的義務與權利。因此,沒有出資的人就無法分得豬肉。而前述額外兩次的分贈豬肉回報交換,強化了親屬間的緊密聯繫。如此,當他們日後若遭遇困難時,尚有親屬可以做為其最後的依賴。然而,這種將沒有出資的親屬排除在日後尋求協助的人群範疇之外的新形實踐,說明了經濟的邏輯如何滲透到親屬的邏輯之中。
同樣,整個中部布農人(包括信義鄉及仁愛鄉)的基督長老教會中各項宗教活動的進行,原本就是以各地方教會為主要運作單位。1987年,開始了每個月由各聚落輪流舉行的禁食禱告活動,而中部布農中會於1994年正式成立,進一步加強推動超越聚落的全區性(整個中部)布農人的集體活動,但實際日常運作時,仍以地方教會為主。由於921災後重建促成了交通及溝通系統的快速發展,中部布農中會負責籌劃與主導的活動日漸頻繁,甚至有逐漸取代地方教會的宗教活動之態勢。此時,參與中會活動的成員,已不限於信義鄉陳有蘭溪流域的布農人,更包含了仁愛鄉、南投市與臺中市的布農人教會。換言之,在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中,主導基督長老教會的宗教活動之進行的主要活動單位,逐漸由地方教會轉向中部布農中會。然而這並不意味地方教會的活動與作用消失殆盡,事實上,地方教會的宗教活動採取了新的形式,而得繼續存在並發揮作用。各地方教會為了挽救教會日漸沒落的危機,試圖引入甚至創造新的宗教活動,以滿足教友的不同需求。除了以靈恩化的儀式活動取代過往常使用的靜態讀聖經經文之外,地方教會更留心教友所面臨的特定問題,發展出許多新形宗教活動。例如,中部地方基督長老教會當中的羅娜、東埔社、人倫、迪巴恩、卡度等五處的教會,共同推動連結禱告。這是因一再目睹當代許多教友面臨了家庭成員之間無法和睦相處,甚至造成成員離去與家庭的破碎,地方教會決心推動集體的靈恩禱告活動,希望提升個人的宗教信仰與心靈,解決家庭成員間的紛擾。再如,羅娜基督長老教會在921災後重建時,籌畫了「為臺灣行走」的活動,信徒環島拜訪全臺各地的基督長老教會,以表達他們對其他地方教會的關懷。這項一年一度的宗教活動,吸引了「希望走出去」陳有蘭溪流域的基督長老教徒,並持續至今。甚至,羅娜教會在2005年成立了「為以色列祈禱」活動,每星期二晚上在該教會舉行,更吸引了該區域內一些希望向外開拓視野的南島民族及漢人信徒前來參與。儘管能定期參與這項活動的信徒仍然有限,但這足以說明各地方教會為了回應並解決信徒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煩惱與憂心之事,發展、創造出各類新的活動,以滿足信徒各種心理需求。更重要地,前來參與這類新的宗教活動的信徒,往往不限於該地地方教會成員,甚至有不同族群及不同教派的信徒參與。
事實上,地方政治事務的進行與政治群體的組成,也有類似跨地參與、合作或結盟,而這使得參與者的身分更加異質。原先,東埔社僅是地方行政體系中的一個鄰,即使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東埔社的行政位階依然照舊。但在921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東埔社的重建工程竟然被外部企業認養,而當地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更被外來的專業規劃團隊所壟斷。再加上,(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毫不掩飾地挾外資進入地方社會,透過資源分配,將當地人納入自己的政治後援群體。來自企業、社造專業技師與中央層級的民意代表的資源與資金陸續下放、投入當地之後,讓東埔社成了各種外部勢力交會、競逐的權力場域。此外,不同的外來政治力量,往往在原住民聚落培植了各自的「政治團隊」,這些看似四散各處的「團隊」實則相互串連,形成消長互見的政治勢力。換言之,依附外部力量的政治派系的出現,一方面加深地方社會內部的分化與衝突,嚴重影響地方政治的有效運作;另一方面,各派系又與其他聚落的同派系成員彼此串連、合作,形成(企圖)能影響區域政治運作的政治團體,其成員分布範圍不僅橫跨花蓮、臺東,甚至遠達高雄地區。對照之下,原本以東埔社為主要運作單位的地方政治,卻因跨聚落的地方派系為了確保各自利益,不惜彼此傾軋、爭權奪利,無視東埔社布農人面臨的生活問題。此一政治失能導致當地年輕布農人轉而對政治冷漠,而地方社會的政治生活因沒有年輕人願意投入,不僅失去活力,更與當地居民的真正關懷嚴重脫節。
儘管如此,原東埔社做為地方社會活動的最主要單位,仍可在日常生活中窺見其存在。例如,居民最主要的經濟生產活動與生產所仰賴的土地,依然以東埔社為主要的範圍。的確,自本世紀以來,受惠於921災後重建帶來的交通便利,不少人可開車前往鄉公所所在的信義、陳有蘭溪流域對外交通及商業中心的水里、乃至於聚集了各種原住民公私輔助機構所在的埔里等地通勤上班;此外,許多承攬林班地砍草及高山嚮導的工作,更分散到全島林班地及各大山脈。然而,對此地大部分布農人而言,東埔社才是他們日常各項生產活動的主要所在。同樣,儘管他們會前往南投採購日常用品、進行外地旅遊甚至出國旅行消費,但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仍然以家所在的東埔社為主要實踐場所。
由上,我們可以發現,進入本世紀後,在新資本的不斷投入區域造成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斷再結構的新自由主義化趨勢下,東埔社這個地方社會中各個社會生活層面的進行,多半已超越既有的東埔社範圍,而且每個層面的範圍又不相一致。如果我們繼續堅持,所謂的地方社會是關乎「以特定土地或地理空間範圍為基礎、成員彼此間有權利義務關係、且必須遵循特定的行為規範」等面向,那麼,「當代的東埔社是否仍是一個符合社會科學界普遍接受的地方社會?」這個問題,將變得更加棘手。或許,正如當地布農人所說的,做為地方社會的東埔社早已沒落了。但若我們能夠跳脫出社會科學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有如有機體的這個概念加諸於我們認識論上的框限,反而能清明且如實地看見當代地方社會的新面貌。至少,若我們從個人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東埔社,便能清楚看到其呈現出多重地方認同的新現象與新趨勢。例如,一名東埔社布農人,可以是東埔社基督長老教會的成員,同時也是中部布農中會的會員,甚至對一個同時參與數個不同教派活動的布農人而言,其宗教認同更是多重且複雜。再者,這名布農人除了做為東埔村第一鄰的居民,同時也可能是某位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為首的跨地域政治派系成員(或是不屬任何派系的政治冷漠者)。此外,他或她會有不少親屬成員居住在陳有蘭溪流域範圍內,其親屬關係更可能因為跨國婚姻而超越了國家領土的範圍。這意味著依親屬關係而來的群體認同更為彈性,同時也更加複雜。就此,新資本不斷進入地方社會不僅直接影響了布農人經濟活動的各個層面,導致其活動範疇的不斷再結構,進而形成各種依附關係,而這些更回過頭來塑造出不同的經濟活動群體以及不同地方感。前述新現象與新趨勢,或隱或顯地呈現在本論文集各篇論文中。
新自由主義化對於地方社會是否造成影響?若有,其影響係以何種方式進行?造成怎樣的後果?讓筆者以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的東埔社之個案研究來具體回答。自日治時期以來,在特定地理空間範圍中發展出文化傳統的東埔社與整個陳有蘭溪流域,在1999年921災後重建後,納入大臺中地區的消費市場。當時新修建的快速道路,將東埔社到臺中間的通車時間,由原先的三、四小時縮短為兩小時,從而使當時由國際資金在該地區投資設立的十個大賣場,迅速吸收了整個大臺中地區的消費者。這造成了東埔社布農人開始每個星期驅車前往臺中大賣場,購足一星期所需日用品及食物的生活習慣。此一消費型態與生活圈的形成,導致二戰之後做為陳有蘭溪流域對外的交通及商業中心的水里,生意一落千丈,快速蕭條。到了2000年,資本額介於前述國際資金與水里原有商店之間的國內興農超商,正式進駐水里設點,部分東埔社及陳有蘭溪流域的布農人,重新前往水里採購食品及日用品,不再獨厚臺中的大賣場。興農超商的成功讓法商家樂福察覺到大臺中的腹地仍有巨大商機,同年便進軍南投市設分店。此舉再次改變東埔社布農人從事消費活動的空間範圍。至少,截至2012年,大部分擁有私家轎車的東埔社布農家庭,多半選擇前往南投市的家樂福大賣場採買日常生活所需。由上可見,隨著新資本的不斷投入,整個大臺中消費性區域體系內部因而產生了一連串細緻的再結構過程與重組,導致東埔社居民的消費行為更加異質化,同時帶來了不同的地方感。
事實上,做為新自由主義化動力的新資本前仆後繼進入地方社會,以商場建築、機構、交通網絡等形式具體現身並發揮作用,持續影響地方社會人們的生活與各項活動。除消費之外,當地醫療體系同樣因著新資本的投入而產生變化。在921災後重建改善區域交通網絡後,東埔社居民生病時,不再像過去那樣前往水里或埔里就醫,而是直接驅車到臺中榮總、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等教學醫院掛號,重症患者更是如此。事實上,當時從東埔社開車到埔里所需的時間,竟然比前往臺中更費時,這使得上述新的就醫習慣,成了難以挽回的趨勢。猶有進之,此一就醫習慣更使得水里原有的私人診所因病人紛紛流失而難以維持。這些私人診所只得另起爐灶,遷往和社及信義等這些未有醫療院所進駐的山區偏鄉,就近吸收非重症的與常見疾病的患者。此時,落入醫療真空狀態的水里,吸引了資金較上述私人診所更為雄厚的埔里基督長老教醫院及彰化基督長老教醫院,於2004年分別在水里及南投建立分院(東埔社布農人稱之為「水基」及「南基」)。此後,東埔社及陳有蘭溪流域的居民的就醫習慣隨之改變:若遇到感冒這類常見疾病,就近前往和社的私人診所看病;但若罹患稍微嚴重的疾病,就前往水基及南基,而不再像過去一樣前往較遠的臺中榮總或埔里基督教醫院看病。隨著東埔社人就醫地點的日益多元,當地人也開始有了與過去不同的地方感。這種因新資本不斷投入而產生不斷再結構的過程,同樣發生在交通、教育、觀光等其他層面,進而影響人們的具體活動。
其中,由於921災後重建導致交通運輸系統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快速道路及2007年高鐵全線通車,使得東埔社布農人習於以自用小客車代步,導致原本行駛水里到臺中路段的國光客運及員林客運,因無法承受虧損而必須停掉這些偏遠路線。其中,國光客運改變營運策略,轉而利用快速道路及高速道路去經營往返臺北與南投及南投到南部(嘉義、臺南、高雄)這類全新的路線,而員林客運繼續經營南投與彰化、員林、雲林等地的縣級路線。如此一來,大臺中的偏遠地區完全失去公共交通的服務。在此情形下,資本額低於國光客運及員林客運的總達客運,開始以21人座小型巴士有效地經營這些被放棄的偏遠路線,使交通運輸網路重又進行了再結構過程。此外,高鐵的通車促使統聯得以開拓南投市到新烏日的路線,方便南投居民銜接高鐵。同樣,原本早已乏人問津的集集線鐵道,因為新自由主義化帶來鐵道沿線觀光產業的快速發展,鐵路局便將該線延伸至臺中,使東埔村的溫泉觀光區及新中橫直接納入大臺中地區的休閒旅遊與觀光景點,讓整個大臺中地區因而更容易與新烏日的高鐵站接軌。這些相互銜接的交通要道形成了一條快捷、平價的路線,成為東埔社居民前往北臺灣或南臺灣時的最佳選擇。
由前述,我們看到消費物資、醫療、交通甚至觀光等產業,因不同額度的新資本陸續進入地方社會不斷進行再結構的過程,導致大臺中地區區域內部的不斷重整。最明顯的就是原本做為南投縣政治行政中心的南投市,因為上述各種產業在921災後重建之後陸續匯聚至此,躍身成為大臺中地區僅次臺中市的新都會及金融中心,取代了中興新村、草屯、水里這些戰後新興市鎮。在區域不斷再結構過程的同時,東埔社布農人更在聚落層次之上,發展出各種範圍不同卻又不完全重疊的新興區域活動範疇。
例如,921災後重建帶來交通及溝通工具的快速發展,使得原本僅在聚落內舉行的生命儀禮,因跨聚落親屬之間的聯繫與彼此關係之維繫,已從單一聚落擴大到陳有蘭溪流域的八個聚落,這點在婚禮的實踐最為突顯。原本在東埔社,婚禮時主人家只需宰殺三頭豬,分送給聚落成員與女方父系親屬及其聚落成員共享。在當代,為了讓整個陳有蘭溪流域的親屬都能分得豬肉,婚禮主人家革新了舊日的共享規範,將宰殺豬隻的數目增加至十八頭以上。一方面,這種將陳有蘭溪流域的親屬納入生命儀禮之交換與共享範圍內的實踐,幾乎同時表現在其他的親屬儀式活動上。例如,小孩成長禮(Magalav或Manqaul)中分豬肉回贈母親娘家的儀式、或者婚出女兒一起殺豬回報娘家的新儀式、或者婚出女兒在母親節時必須返回娘家同祝等活動,皆以陳有蘭溪流域為主要的地域範疇,有別於過去以聚落為生命儀禮主要進行的單位。甚至,聚落內日益增加的異族通婚,讓親屬關係不僅超越陳有蘭溪流域,更跨越國家領土的範圍。簡言之,本世紀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使得那些與親屬相關的社會活動,超越了既有的聚落單位,轉而以陳有蘭溪流域的區域體系為主要的地域範疇。另一方面,某些儀式或社會活動在本世紀也產生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小孩成長禮的分豬肉。當出嫁女兒在小孩順利成長時要回報娘家的祝福時,必須宰豬,並將豬肉分贈給娘家聚落的父系氏族成員。而這些接受婚出女兒贈與之豬肉的氏族成員,往往會集資殺豬,回送給所有婚出到陳有蘭溪流域的女子。當這些婚出的女子收到來自父系氏族餽贈的豬肉後,會再次集資殺豬,回請娘家的父系氏族成員。由於這些新增的豬肉分贈與回贈,均是雙方自願出資進行的交換,並非傳統儀式上的義務與權利。因此,沒有出資的人就無法分得豬肉。而前述額外兩次的分贈豬肉回報交換,強化了親屬間的緊密聯繫。如此,當他們日後若遭遇困難時,尚有親屬可以做為其最後的依賴。然而,這種將沒有出資的親屬排除在日後尋求協助的人群範疇之外的新形實踐,說明了經濟的邏輯如何滲透到親屬的邏輯之中。
同樣,整個中部布農人(包括信義鄉及仁愛鄉)的基督長老教會中各項宗教活動的進行,原本就是以各地方教會為主要運作單位。1987年,開始了每個月由各聚落輪流舉行的禁食禱告活動,而中部布農中會於1994年正式成立,進一步加強推動超越聚落的全區性(整個中部)布農人的集體活動,但實際日常運作時,仍以地方教會為主。由於921災後重建促成了交通及溝通系統的快速發展,中部布農中會負責籌劃與主導的活動日漸頻繁,甚至有逐漸取代地方教會的宗教活動之態勢。此時,參與中會活動的成員,已不限於信義鄉陳有蘭溪流域的布農人,更包含了仁愛鄉、南投市與臺中市的布農人教會。換言之,在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中,主導基督長老教會的宗教活動之進行的主要活動單位,逐漸由地方教會轉向中部布農中會。然而這並不意味地方教會的活動與作用消失殆盡,事實上,地方教會的宗教活動採取了新的形式,而得繼續存在並發揮作用。各地方教會為了挽救教會日漸沒落的危機,試圖引入甚至創造新的宗教活動,以滿足教友的不同需求。除了以靈恩化的儀式活動取代過往常使用的靜態讀聖經經文之外,地方教會更留心教友所面臨的特定問題,發展出許多新形宗教活動。例如,中部地方基督長老教會當中的羅娜、東埔社、人倫、迪巴恩、卡度等五處的教會,共同推動連結禱告。這是因一再目睹當代許多教友面臨了家庭成員之間無法和睦相處,甚至造成成員離去與家庭的破碎,地方教會決心推動集體的靈恩禱告活動,希望提升個人的宗教信仰與心靈,解決家庭成員間的紛擾。再如,羅娜基督長老教會在921災後重建時,籌畫了「為臺灣行走」的活動,信徒環島拜訪全臺各地的基督長老教會,以表達他們對其他地方教會的關懷。這項一年一度的宗教活動,吸引了「希望走出去」陳有蘭溪流域的基督長老教徒,並持續至今。甚至,羅娜教會在2005年成立了「為以色列祈禱」活動,每星期二晚上在該教會舉行,更吸引了該區域內一些希望向外開拓視野的南島民族及漢人信徒前來參與。儘管能定期參與這項活動的信徒仍然有限,但這足以說明各地方教會為了回應並解決信徒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煩惱與憂心之事,發展、創造出各類新的活動,以滿足信徒各種心理需求。更重要地,前來參與這類新的宗教活動的信徒,往往不限於該地地方教會成員,甚至有不同族群及不同教派的信徒參與。
事實上,地方政治事務的進行與政治群體的組成,也有類似跨地參與、合作或結盟,而這使得參與者的身分更加異質。原先,東埔社僅是地方行政體系中的一個鄰,即使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東埔社的行政位階依然照舊。但在921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東埔社的重建工程竟然被外部企業認養,而當地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更被外來的專業規劃團隊所壟斷。再加上,(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毫不掩飾地挾外資進入地方社會,透過資源分配,將當地人納入自己的政治後援群體。來自企業、社造專業技師與中央層級的民意代表的資源與資金陸續下放、投入當地之後,讓東埔社成了各種外部勢力交會、競逐的權力場域。此外,不同的外來政治力量,往往在原住民聚落培植了各自的「政治團隊」,這些看似四散各處的「團隊」實則相互串連,形成消長互見的政治勢力。換言之,依附外部力量的政治派系的出現,一方面加深地方社會內部的分化與衝突,嚴重影響地方政治的有效運作;另一方面,各派系又與其他聚落的同派系成員彼此串連、合作,形成(企圖)能影響區域政治運作的政治團體,其成員分布範圍不僅橫跨花蓮、臺東,甚至遠達高雄地區。對照之下,原本以東埔社為主要運作單位的地方政治,卻因跨聚落的地方派系為了確保各自利益,不惜彼此傾軋、爭權奪利,無視東埔社布農人面臨的生活問題。此一政治失能導致當地年輕布農人轉而對政治冷漠,而地方社會的政治生活因沒有年輕人願意投入,不僅失去活力,更與當地居民的真正關懷嚴重脫節。
儘管如此,原東埔社做為地方社會活動的最主要單位,仍可在日常生活中窺見其存在。例如,居民最主要的經濟生產活動與生產所仰賴的土地,依然以東埔社為主要的範圍。的確,自本世紀以來,受惠於921災後重建帶來的交通便利,不少人可開車前往鄉公所所在的信義、陳有蘭溪流域對外交通及商業中心的水里、乃至於聚集了各種原住民公私輔助機構所在的埔里等地通勤上班;此外,許多承攬林班地砍草及高山嚮導的工作,更分散到全島林班地及各大山脈。然而,對此地大部分布農人而言,東埔社才是他們日常各項生產活動的主要所在。同樣,儘管他們會前往南投採購日常用品、進行外地旅遊甚至出國旅行消費,但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仍然以家所在的東埔社為主要實踐場所。
由上,我們可以發現,進入本世紀後,在新資本的不斷投入區域造成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斷再結構的新自由主義化趨勢下,東埔社這個地方社會中各個社會生活層面的進行,多半已超越既有的東埔社範圍,而且每個層面的範圍又不相一致。如果我們繼續堅持,所謂的地方社會是關乎「以特定土地或地理空間範圍為基礎、成員彼此間有權利義務關係、且必須遵循特定的行為規範」等面向,那麼,「當代的東埔社是否仍是一個符合社會科學界普遍接受的地方社會?」這個問題,將變得更加棘手。或許,正如當地布農人所說的,做為地方社會的東埔社早已沒落了。但若我們能夠跳脫出社會科學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有如有機體的這個概念加諸於我們認識論上的框限,反而能清明且如實地看見當代地方社會的新面貌。至少,若我們從個人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東埔社,便能清楚看到其呈現出多重地方認同的新現象與新趨勢。例如,一名東埔社布農人,可以是東埔社基督長老教會的成員,同時也是中部布農中會的會員,甚至對一個同時參與數個不同教派活動的布農人而言,其宗教認同更是多重且複雜。再者,這名布農人除了做為東埔村第一鄰的居民,同時也可能是某位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為首的跨地域政治派系成員(或是不屬任何派系的政治冷漠者)。此外,他或她會有不少親屬成員居住在陳有蘭溪流域範圍內,其親屬關係更可能因為跨國婚姻而超越了國家領土的範圍。這意味著依親屬關係而來的群體認同更為彈性,同時也更加複雜。就此,新資本不斷進入地方社會不僅直接影響了布農人經濟活動的各個層面,導致其活動範疇的不斷再結構,進而形成各種依附關係,而這些更回過頭來塑造出不同的經濟活動群體以及不同地方感。前述新現象與新趨勢,或隱或顯地呈現在本論文集各篇論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