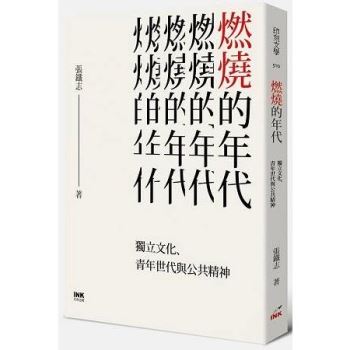輯一 台灣
小確幸的時代意義
「如果沒有這種小確幸,我認為人生只不過像乾巴巴的沙漠而已。」村上春樹在小說裡這麼說。
「小確幸」確實是理解我們這個時代與青年世代的關鍵字(註),它既是商品行銷的流行口號,也是台灣發展停滯不前的代罪羔羊。然而,太多對「小確幸」的批評都是對其根源與意義的不理解。
一種主流論述(特別是來自財經界)喜歡把小確幸是和大志向對比,他們認為台灣年輕人太小確幸,只向內看,只想開咖啡店、蹲在社區、做小東西;真正志氣的青年,應該要走出去,不論是去中國、去澳洲、還是去西方。
這一來是不了解小確幸之所以是小確幸的理由,二來不了解小確幸翻轉的時代意義,甚至不知道小確幸可能比去上海打工的人更國際化!
首先,很少人注意到兩種小確幸的區分,一種是消費意義,一種是作為工作。兩者有某些相同的背景,但也有很不同的意義。
有一些人指出過,小確幸出現的社會脈絡很大部分是來自台灣經濟的崩壞與世代不正義。尤其,年輕人薪資停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加上物價與房價上漲,貧窮化的年輕世代只能透過簡單的消費來感受那「微小而確定的幸福」,不論是美食或旅遊。小確幸因此成為一種生活風格的追求。
這意味者,小確幸的現象是大人們造成的惡果,是他們的父輩世代沒有讓台灣經濟轉型、是他們讓貧富不均日益惡化,所以被擠壓的「魯蛇」世代只能選擇那些微小幸福。
上一個世代沒能推動台灣經濟前進也影響小確幸作為一種工作選擇態度:與其去選擇低薪工作乃至大量的非典型工作,很多年輕人更寧願選擇微型創業,以及返鄉創業。
另一方面,除了經濟環境不如以往的「推力」,這個小確幸世代其實代表台灣社會的前進:他們比父輩們更具有更多元的價值,他們不以競爭力、賺大錢為最高價值,而是寧願選擇更能實踐自我的工作。同時,不論是開獨立小店(以反對壟斷連鎖)、追求環境友善、本土農業,他們其實是這個新時代價值的創造者。或者更精確地說,他們是過去二十年的革命的後代:因為戰後台灣的發展模式就是威權政治加上經濟成長主義,但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衝擊了過去單一的主流價值,讓環境保護、社區改造、多元平權、民主參與等改變台灣社會,年輕世代可以說出生就承接了這些價值,並且讓這些價值開花結果。
更進一步來看,在台灣開店的小確幸世代是內向、去外國打工才是大志向,其實是一種錯誤的對立:除了著名的麵包師,台灣的咖啡師也拿下世界冠軍,台南的霜淇淋店在日本拿到比賽大獎,這證明他們的國際水準。此外,台灣的許多農業工作者、社區工作者也有深厚國際視野,有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他們是真正國際視野、在地實踐。也有許多民宿或生活小店的經營者是走過地球許多地方,然後回到故鄉,開啟了他的夢想。可以說,他們許多人是在追求「職人精神」:把一杯咖啡做好,把水果種好,把一種工藝做到更精緻。
這些與其他國家相比並不特殊,台灣熟悉的日本有更多青年選擇這樣的工作,歐美更是。因為,這些「先進」國家具有更多元的價值,而不像發展中國家只以拼經濟作為最高價值。認為去國外打工更有志向,實在是一種過時的想法。
所以去批評年輕人不往外走是沒有意義的批評:因為有能力、願意往外走的人,自然會出去,而願意留在台灣或者返鄉從事更草根工作的人,當然也是一種美好的實踐,且也是真真切切地改變台灣。
當然,這並不是說現在的年輕世代一切就很好,內向封閉就是對的。台灣社會當然視野狹窄、缺乏國際觀,但有這問題的人可能不只是在一個在台灣工作的年輕人,也可能是一名去中國工作的創業家,因為問題在於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媒體提供多少思想的養分,廣闊的視野。這是台灣整個社會的共業。
結論是:小確幸世代是台灣過去發展路徑依賴的產物,上一代的企業人士沒有讓台灣經濟向上提升,卻批評年輕世代的小確幸心態,是很荒謬的。另一方面,小確幸世代也是此前社會改革者的後代,因此讓他們有多元的價值。但他們當然有其局限性,只是這個局限性的根源不在於他們,掌握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媒體的老人們。
註,以聯合報系來說,在二○○六年出現第一則以小確幸為關鍵字的報導,到二○一○年還只有三則,後來就被倍數成長。見邱子珉,《從「小確幸」現象看台灣八○後世代的失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所碩士論文,二○一六。
這座城市沒有噪音
台北地下文化的基地與十五年來一直是獨立音樂搖籃的Live House「地下社會」,在二○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午夜被迫關門了。這一天,正好是台灣解嚴二十五週年。
回到那個冰冷黑暗的戒嚴體制下,我們只有一個「純淨」的社會,只有單一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忠黨愛國加經濟發展),而沒有任何異質與異議的可能:在七○年代初期,長髮男子還會被抓進警局中剪頭髮。
也是從七○年代,新的力量,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開始掙脫戒嚴體制的霸權價值:文藝青年們開始打破道德法西斯逐步建立起青年反文化;鄉土/本土意識開始對抗陳舊的大中國意識;民主運動開始對黨國體制的控制提出挑戰;各種社會矛盾也不斷爆發,挑戰以經濟成長為唯一價值的發展策略。
腐朽的單一價值秩序逐漸崩解,國民黨終於被迫在一九八七年解嚴。解嚴更進一步解放了人們被桎梏多年的想像力與實踐可能,更多思想、文化與社會的小革命開始在街頭、在書店、在地下室、在人們的腦中湧現。音樂也是—正好在解嚴後,「新台語歌」和地下音樂開始衝擊八○年代保守的流行音樂。
進入九○年代初期,各種另類的文化與思潮在島嶼的邊緣爆發,到了九○年代中期幾乎成就一個高潮—以音樂來說,出現了春天吶喊音樂祭以及野台開唱的前身,而女巫店、地下社會和更多的live house出現,一個新的地下文化場景於焉浮現。
只是,隨著形式民主的確立(九六年首次總統直選),以及九○年代全球化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八○年代到九○年代中期的社會反抗與躁動逐漸平息,部分異議之聲與主流和平共存,只剩少數人繼續持續游擊。
從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來看,戒嚴體制下的政治威權加經濟發展的保守價值雖然不斷被挑戰,但是保守主義的核心並沒有被徹底顛覆。民主化二十多年,人民雖然獲得自由,卻沒有成為真正的主人,而是讓資本成為社會的主人,讓金權政治主導了我們的政治。
解嚴二十五年,經歷這麼多場社會運動和政黨輪替,我們赫然發現發展主義的幽靈回來了,而保守主義的幽靈卻始終在此—政治戒嚴解除了,道德戒嚴卻開始了。現在的人們比二十五年前的人更懂得追求「美好生活」,但這個美好生活的想像背後是中產階級的道德觀,是地產霸權作為物質基礎。這是威權統治的當代變種,富有的秩序守護者要剷除那些礙眼的異質,要在城市中消滅那些破敗的房子蓋起嶄新的大樓(在許多例子中建商會先蓋起叫做「台北好好看」的假公園),在城市的河岸拆毀破舊的都市原住民部落,要把吸菸者、遊民、偶爾在公園喝酒談天的文藝青年驅逐出公園,要拒絕癌童中途之家進入他們高貴的社區。
於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乾淨無菌、沒有人渣失敗者流浪漢邊緣人搖滾青年與頹廢詩人,最好也沒有窮人的城市;在那裡,將沒有黑暗的地下社會,只有光亮潔白的地上美麗新世界。
走了一個地下社會,不只代表這個城市失去了多樣的豐富靈魂,或者這個政府對於音樂產業的根源是多麼漠視,而是當這座城市沒有了地下噪音,這個民主之殼也將失去異議。
輯二 香港
《十年》之前—現在還來得及
二○一四年,台灣和香港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公民運動。
一年後,台灣的金曲獎把「年度最佳歌曲」頒給了獨立樂隊滅火器為太陽花運動所寫的歌曲〈島嶼天光〉。這既是一個文化的也是一個政治的歷史時刻:金曲獎這個台灣流行音樂最重要獎項把年度最佳歌曲頒給一個獨立樂隊,並且是一首誕生於社會抗爭的歌曲。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出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的劇烈變遷。
在香港雨傘運動後一年多後,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給了一部本地獨立製片、一部非常政治的電影《十年》。這不僅是香港年度文化事件,也會是這個時代的重要記憶。
然而,後太陽花的台灣,氣氛是昂揚的,年輕人覺得被empowered:他們讓柯文哲當選市長,讓國民黨倒台和小英上台,他們覺得他們可以改變些什麼。
香港卻是相反:後雨傘的氣氛是低迷的、是挫敗的,只有主張自決甚至獨立的本土思潮,以及勇武抗爭越來越受到年輕人支持,似乎越來越少人相信透過體制可以改變香港。
《十年》這部影片的成本約五十萬港元,由五部短片分別想像十年後的香港:政府為了推動國安法而暗殺議員以製造混亂;普通話和簡體字成為香港主流,不懂普通話的的士司機難以生存;本地農業受到擠壓、書籍被查禁,而香港少年如紅衛兵般去鬥爭還有本土意識的上一代;一對戀人以製作標本的方式保衛城市「被消失」的事物;最激烈的一部片在二十三條已立法的香港,有人為了港獨理念而絕食,甚至自焚。
上片初期只有個別影院播放,但口碑越來越好,一個月後《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批評《十年》這部片「宣揚絕望」,「帶給香港社會的害處很可能大過好處」,並說該片票房只有三百多萬,影響的只是香港小眾。此話一出,小眾很快成為大眾,兩個月後,《十年》票房累積至六百萬港元,連續三周躋身香港十大賣座電影,並繼續由公民團體組織在香港各大社區放映,反應熱烈。
然後,這部片拿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
不少人質疑這部片藝術性不夠,以及頒獎的動機是政治性的。當然,一部電影的藝術性是見仁見智的,許多商業片拿到最佳影片也都是可被爭議;而最佳影片到底是什麼判準,每個人心中的尺也都不同—一種看法便是,一旦某部片反映某個時代人心的渴望與焦慮到了成為現象的地步,乃是年度影片的重要精神。
無論如何,當《十年》不只是屬於一種反抗的姿態,而被香港最主流的電影獎項所接受,確實代表香港人心轉變之激烈。這已經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
看看從去年十二月《十年》上映到這個春天(二○一六)的香港發生了什麼事:銅鑼灣書店老闆被消失、警察和民眾嚴重流血衝突的旺角騷動、「以本土主義為綱,勇武抗爭為實,堅守港中區隔」的參選人在新界東補選中15%得票率,學民思潮宣布停止。
這是一個極為焦慮與惶惶然的香港,絕望的年輕人只能越來越激進化,或者用另一種文化方式去表達他們的困頓與不滿:如去年香港政治諷刺網路節目「毛記電視」頒獎典禮造成熱潮,人們是在城市不同角落聚集起來一起看;《十年》也在四月一日於三十個以上社區同步舉行放映會和映後導演的線上對談。可以說,這些香港青年世代的集體觀影是對具有濃厚本土情懷的文化想像的肯認、是對當下的拒絕,更是對另一種未來的渴望。
這是當下香港最迫切的命題,但香港主流電影工業卻無能反思,商業電影中偶爾出現的政治暗喻就能讓許多人興奮地覺得那反映出現實。然而,香港電影工業的主流是合拍片,而中港合作的影片怎可能去討論最敏感的中港矛盾或者北京的政治黑手呢?這是當下香港電影文化的最大弔詭。
《十年》或許有不少瑕疵,或許許多人不同意其觀點,但這部影片代表的是香港這一代青年在主流電影界迴避思考自身的命運時,願意去質問他們的未來,並提醒人們,這個島嶼將走向人們不想見到的未來—如果這個城市的人不嘗試奪回他們的未來十年。
「現在還來得及」—這是電影最終的字幕。
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
香港當然不是文化沙漠,但是來自地產霸權和不友善的公共政策所形成的沙塵暴確實強大,因此文化創意工作者的日常生存和演出空間非常有限。
然而過去數年,在觀塘與牛頭角一帶的工廠大廈中,散布著許多文化小綠洲,有許多文化創意工作者在此蟄居或游擊,不論是設計店鋪、個人工作室、藝廊、小咖啡店等等,他們在這些困頓的環境中,奮力演繹自己的生命力與創造力,成為另一種香港美麗的風景。
在最近這兩週,有一連串的活動在這些工廈中進行,包括烹飪教室、工藝工作坊、藝術欣賞、獨立書店講座、電影放映等等,其中一場是在一間Live House的音樂表演,演出者是知名香港歌手何韻詩和幾個獨立樂隊。
這是歌手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出的一站,那些音樂以外的活動是由她的團隊和另一個單位「牛遊」合作舉辦的。
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出,並不僅僅是音樂表演,而是一個實驗,一場文化和社區運動:因為她希望在每一站都有和社區連結的不同方式。
這一站的名稱是:「有種香港叫做『工廈生命力』」。
過去三年,歌手何韻詩經歷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二○一二年底,她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並且參與組成同志平權團體「大愛同盟」,成為公眾意見領袖;二○一四年,她開始寫專欄,並走到雨傘運動前線,成為華語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個參與公民抗命而被拘捕的明星歌手。
此刻的香港是低迷而憂鬱的,人們對何韻詩的未來也有許多猜測。在雨傘運動後,她選擇在音樂上重新出發,並以獨立歌手身分出發。
「今天,我正式從主流歌手成為獨立歌手,這個遲來的春天,滿是可能性。朋友們,不用替我擔心,我生命力頑強,像長在崖上的花,每每在最嚴峻的處境,才最能盛放。
面對前方的未知,我無限期待,同時也無畏無懼。」
這是她的獨立宣言。
過去何韻詩是主流音樂工業的知名歌手、是梅豔芳的徒弟,但阿詩一直很重視自己在音樂創作上的自主性,不想成為唱片公司打造的偶像歌手。她跟我說:「我的個性本來就是對於規則、對於大家慣性在用的方法很不以為然。因為你可能很穩定地賺,但是不會有成長。我是一個一直在追求成長的人。」
因此,何韻詩與主流音樂產業的斷裂是一場遲來的分手。這不只是因為政治壓力,而是香港的主流音樂工業早已衰落,失去想像與創新的能力。她認為主流樂壇太過「離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知道在不同社會角落茁壯的生命力。
這兩年間,她開始認識更多優秀的獨立文化工作者,她也相信這是未來她可以扮演好的角色:扮演主流和獨立音樂之間的橋梁,透過她的音樂去傳遞理念。
「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唱會就是要「將有心有力的香港人,重新連接起來,重新描繪一個被遺忘了的香港。」她在文章中如此描述。
「這個計畫,根本不只是一個個人巡演,而應該是一個集體社區實驗。『十八』,起點為香港十八區,但亦可以解讀為十八般武藝,18ways of life。香港本應是個擁有無限可能的地方,集合中西方的最長處,只是不知從何時被規限了,個性被沖淡了。現時香港,可謂身處最狹窄的年代,做任何事好似都只有一個方法:抗爭如是,唱歌如是,拍戲如是,甚至表達自己也如是。」
簡言之,這個巡迴是要透過她的音樂,一方面是連結起各種獨立的、草根的文化工作者,另方面使大家重新去認識香港不同的社區,重新想像不同的香港。
這正是現在的香港需要的。香港正處於一個重新尋找自我認同的時刻,正經歷一場巨大的社會與價值轉型,人人都在思考香港的出路:「後中環價值」的香港精神是什麼呢?與中國的關係該何去何從?
何韻詩在許多時刻選擇了一條更挑戰的險路:她的公開出櫃、她的公民抗命、她從主流到獨立的音樂生涯—她的勇氣也是香港社會該具有的,一如這個演唱會的另一個標題「Re-imagine Hong Kong」:十八種香港,無限種可能。
小確幸的時代意義
「如果沒有這種小確幸,我認為人生只不過像乾巴巴的沙漠而已。」村上春樹在小說裡這麼說。
「小確幸」確實是理解我們這個時代與青年世代的關鍵字(註),它既是商品行銷的流行口號,也是台灣發展停滯不前的代罪羔羊。然而,太多對「小確幸」的批評都是對其根源與意義的不理解。
一種主流論述(特別是來自財經界)喜歡把小確幸是和大志向對比,他們認為台灣年輕人太小確幸,只向內看,只想開咖啡店、蹲在社區、做小東西;真正志氣的青年,應該要走出去,不論是去中國、去澳洲、還是去西方。
這一來是不了解小確幸之所以是小確幸的理由,二來不了解小確幸翻轉的時代意義,甚至不知道小確幸可能比去上海打工的人更國際化!
首先,很少人注意到兩種小確幸的區分,一種是消費意義,一種是作為工作。兩者有某些相同的背景,但也有很不同的意義。
有一些人指出過,小確幸出現的社會脈絡很大部分是來自台灣經濟的崩壞與世代不正義。尤其,年輕人薪資停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加上物價與房價上漲,貧窮化的年輕世代只能透過簡單的消費來感受那「微小而確定的幸福」,不論是美食或旅遊。小確幸因此成為一種生活風格的追求。
這意味者,小確幸的現象是大人們造成的惡果,是他們的父輩世代沒有讓台灣經濟轉型、是他們讓貧富不均日益惡化,所以被擠壓的「魯蛇」世代只能選擇那些微小幸福。
上一個世代沒能推動台灣經濟前進也影響小確幸作為一種工作選擇態度:與其去選擇低薪工作乃至大量的非典型工作,很多年輕人更寧願選擇微型創業,以及返鄉創業。
另一方面,除了經濟環境不如以往的「推力」,這個小確幸世代其實代表台灣社會的前進:他們比父輩們更具有更多元的價值,他們不以競爭力、賺大錢為最高價值,而是寧願選擇更能實踐自我的工作。同時,不論是開獨立小店(以反對壟斷連鎖)、追求環境友善、本土農業,他們其實是這個新時代價值的創造者。或者更精確地說,他們是過去二十年的革命的後代:因為戰後台灣的發展模式就是威權政治加上經濟成長主義,但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衝擊了過去單一的主流價值,讓環境保護、社區改造、多元平權、民主參與等改變台灣社會,年輕世代可以說出生就承接了這些價值,並且讓這些價值開花結果。
更進一步來看,在台灣開店的小確幸世代是內向、去外國打工才是大志向,其實是一種錯誤的對立:除了著名的麵包師,台灣的咖啡師也拿下世界冠軍,台南的霜淇淋店在日本拿到比賽大獎,這證明他們的國際水準。此外,台灣的許多農業工作者、社區工作者也有深厚國際視野,有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他們是真正國際視野、在地實踐。也有許多民宿或生活小店的經營者是走過地球許多地方,然後回到故鄉,開啟了他的夢想。可以說,他們許多人是在追求「職人精神」:把一杯咖啡做好,把水果種好,把一種工藝做到更精緻。
這些與其他國家相比並不特殊,台灣熟悉的日本有更多青年選擇這樣的工作,歐美更是。因為,這些「先進」國家具有更多元的價值,而不像發展中國家只以拼經濟作為最高價值。認為去國外打工更有志向,實在是一種過時的想法。
所以去批評年輕人不往外走是沒有意義的批評:因為有能力、願意往外走的人,自然會出去,而願意留在台灣或者返鄉從事更草根工作的人,當然也是一種美好的實踐,且也是真真切切地改變台灣。
當然,這並不是說現在的年輕世代一切就很好,內向封閉就是對的。台灣社會當然視野狹窄、缺乏國際觀,但有這問題的人可能不只是在一個在台灣工作的年輕人,也可能是一名去中國工作的創業家,因為問題在於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媒體提供多少思想的養分,廣闊的視野。這是台灣整個社會的共業。
結論是:小確幸世代是台灣過去發展路徑依賴的產物,上一代的企業人士沒有讓台灣經濟向上提升,卻批評年輕世代的小確幸心態,是很荒謬的。另一方面,小確幸世代也是此前社會改革者的後代,因此讓他們有多元的價值。但他們當然有其局限性,只是這個局限性的根源不在於他們,掌握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媒體的老人們。
註,以聯合報系來說,在二○○六年出現第一則以小確幸為關鍵字的報導,到二○一○年還只有三則,後來就被倍數成長。見邱子珉,《從「小確幸」現象看台灣八○後世代的失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所碩士論文,二○一六。
這座城市沒有噪音
台北地下文化的基地與十五年來一直是獨立音樂搖籃的Live House「地下社會」,在二○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午夜被迫關門了。這一天,正好是台灣解嚴二十五週年。
回到那個冰冷黑暗的戒嚴體制下,我們只有一個「純淨」的社會,只有單一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忠黨愛國加經濟發展),而沒有任何異質與異議的可能:在七○年代初期,長髮男子還會被抓進警局中剪頭髮。
也是從七○年代,新的力量,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開始掙脫戒嚴體制的霸權價值:文藝青年們開始打破道德法西斯逐步建立起青年反文化;鄉土/本土意識開始對抗陳舊的大中國意識;民主運動開始對黨國體制的控制提出挑戰;各種社會矛盾也不斷爆發,挑戰以經濟成長為唯一價值的發展策略。
腐朽的單一價值秩序逐漸崩解,國民黨終於被迫在一九八七年解嚴。解嚴更進一步解放了人們被桎梏多年的想像力與實踐可能,更多思想、文化與社會的小革命開始在街頭、在書店、在地下室、在人們的腦中湧現。音樂也是—正好在解嚴後,「新台語歌」和地下音樂開始衝擊八○年代保守的流行音樂。
進入九○年代初期,各種另類的文化與思潮在島嶼的邊緣爆發,到了九○年代中期幾乎成就一個高潮—以音樂來說,出現了春天吶喊音樂祭以及野台開唱的前身,而女巫店、地下社會和更多的live house出現,一個新的地下文化場景於焉浮現。
只是,隨著形式民主的確立(九六年首次總統直選),以及九○年代全球化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八○年代到九○年代中期的社會反抗與躁動逐漸平息,部分異議之聲與主流和平共存,只剩少數人繼續持續游擊。
從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來看,戒嚴體制下的政治威權加經濟發展的保守價值雖然不斷被挑戰,但是保守主義的核心並沒有被徹底顛覆。民主化二十多年,人民雖然獲得自由,卻沒有成為真正的主人,而是讓資本成為社會的主人,讓金權政治主導了我們的政治。
解嚴二十五年,經歷這麼多場社會運動和政黨輪替,我們赫然發現發展主義的幽靈回來了,而保守主義的幽靈卻始終在此—政治戒嚴解除了,道德戒嚴卻開始了。現在的人們比二十五年前的人更懂得追求「美好生活」,但這個美好生活的想像背後是中產階級的道德觀,是地產霸權作為物質基礎。這是威權統治的當代變種,富有的秩序守護者要剷除那些礙眼的異質,要在城市中消滅那些破敗的房子蓋起嶄新的大樓(在許多例子中建商會先蓋起叫做「台北好好看」的假公園),在城市的河岸拆毀破舊的都市原住民部落,要把吸菸者、遊民、偶爾在公園喝酒談天的文藝青年驅逐出公園,要拒絕癌童中途之家進入他們高貴的社區。
於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乾淨無菌、沒有人渣失敗者流浪漢邊緣人搖滾青年與頹廢詩人,最好也沒有窮人的城市;在那裡,將沒有黑暗的地下社會,只有光亮潔白的地上美麗新世界。
走了一個地下社會,不只代表這個城市失去了多樣的豐富靈魂,或者這個政府對於音樂產業的根源是多麼漠視,而是當這座城市沒有了地下噪音,這個民主之殼也將失去異議。
輯二 香港
《十年》之前—現在還來得及
二○一四年,台灣和香港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公民運動。
一年後,台灣的金曲獎把「年度最佳歌曲」頒給了獨立樂隊滅火器為太陽花運動所寫的歌曲〈島嶼天光〉。這既是一個文化的也是一個政治的歷史時刻:金曲獎這個台灣流行音樂最重要獎項把年度最佳歌曲頒給一個獨立樂隊,並且是一首誕生於社會抗爭的歌曲。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出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的劇烈變遷。
在香港雨傘運動後一年多後,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給了一部本地獨立製片、一部非常政治的電影《十年》。這不僅是香港年度文化事件,也會是這個時代的重要記憶。
然而,後太陽花的台灣,氣氛是昂揚的,年輕人覺得被empowered:他們讓柯文哲當選市長,讓國民黨倒台和小英上台,他們覺得他們可以改變些什麼。
香港卻是相反:後雨傘的氣氛是低迷的、是挫敗的,只有主張自決甚至獨立的本土思潮,以及勇武抗爭越來越受到年輕人支持,似乎越來越少人相信透過體制可以改變香港。
《十年》這部影片的成本約五十萬港元,由五部短片分別想像十年後的香港:政府為了推動國安法而暗殺議員以製造混亂;普通話和簡體字成為香港主流,不懂普通話的的士司機難以生存;本地農業受到擠壓、書籍被查禁,而香港少年如紅衛兵般去鬥爭還有本土意識的上一代;一對戀人以製作標本的方式保衛城市「被消失」的事物;最激烈的一部片在二十三條已立法的香港,有人為了港獨理念而絕食,甚至自焚。
上片初期只有個別影院播放,但口碑越來越好,一個月後《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批評《十年》這部片「宣揚絕望」,「帶給香港社會的害處很可能大過好處」,並說該片票房只有三百多萬,影響的只是香港小眾。此話一出,小眾很快成為大眾,兩個月後,《十年》票房累積至六百萬港元,連續三周躋身香港十大賣座電影,並繼續由公民團體組織在香港各大社區放映,反應熱烈。
然後,這部片拿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
不少人質疑這部片藝術性不夠,以及頒獎的動機是政治性的。當然,一部電影的藝術性是見仁見智的,許多商業片拿到最佳影片也都是可被爭議;而最佳影片到底是什麼判準,每個人心中的尺也都不同—一種看法便是,一旦某部片反映某個時代人心的渴望與焦慮到了成為現象的地步,乃是年度影片的重要精神。
無論如何,當《十年》不只是屬於一種反抗的姿態,而被香港最主流的電影獎項所接受,確實代表香港人心轉變之激烈。這已經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
看看從去年十二月《十年》上映到這個春天(二○一六)的香港發生了什麼事:銅鑼灣書店老闆被消失、警察和民眾嚴重流血衝突的旺角騷動、「以本土主義為綱,勇武抗爭為實,堅守港中區隔」的參選人在新界東補選中15%得票率,學民思潮宣布停止。
這是一個極為焦慮與惶惶然的香港,絕望的年輕人只能越來越激進化,或者用另一種文化方式去表達他們的困頓與不滿:如去年香港政治諷刺網路節目「毛記電視」頒獎典禮造成熱潮,人們是在城市不同角落聚集起來一起看;《十年》也在四月一日於三十個以上社區同步舉行放映會和映後導演的線上對談。可以說,這些香港青年世代的集體觀影是對具有濃厚本土情懷的文化想像的肯認、是對當下的拒絕,更是對另一種未來的渴望。
這是當下香港最迫切的命題,但香港主流電影工業卻無能反思,商業電影中偶爾出現的政治暗喻就能讓許多人興奮地覺得那反映出現實。然而,香港電影工業的主流是合拍片,而中港合作的影片怎可能去討論最敏感的中港矛盾或者北京的政治黑手呢?這是當下香港電影文化的最大弔詭。
《十年》或許有不少瑕疵,或許許多人不同意其觀點,但這部影片代表的是香港這一代青年在主流電影界迴避思考自身的命運時,願意去質問他們的未來,並提醒人們,這個島嶼將走向人們不想見到的未來—如果這個城市的人不嘗試奪回他們的未來十年。
「現在還來得及」—這是電影最終的字幕。
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
香港當然不是文化沙漠,但是來自地產霸權和不友善的公共政策所形成的沙塵暴確實強大,因此文化創意工作者的日常生存和演出空間非常有限。
然而過去數年,在觀塘與牛頭角一帶的工廠大廈中,散布著許多文化小綠洲,有許多文化創意工作者在此蟄居或游擊,不論是設計店鋪、個人工作室、藝廊、小咖啡店等等,他們在這些困頓的環境中,奮力演繹自己的生命力與創造力,成為另一種香港美麗的風景。
在最近這兩週,有一連串的活動在這些工廈中進行,包括烹飪教室、工藝工作坊、藝術欣賞、獨立書店講座、電影放映等等,其中一場是在一間Live House的音樂表演,演出者是知名香港歌手何韻詩和幾個獨立樂隊。
這是歌手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出的一站,那些音樂以外的活動是由她的團隊和另一個單位「牛遊」合作舉辦的。
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出,並不僅僅是音樂表演,而是一個實驗,一場文化和社區運動:因為她希望在每一站都有和社區連結的不同方式。
這一站的名稱是:「有種香港叫做『工廈生命力』」。
過去三年,歌手何韻詩經歷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二○一二年底,她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並且參與組成同志平權團體「大愛同盟」,成為公眾意見領袖;二○一四年,她開始寫專欄,並走到雨傘運動前線,成為華語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個參與公民抗命而被拘捕的明星歌手。
此刻的香港是低迷而憂鬱的,人們對何韻詩的未來也有許多猜測。在雨傘運動後,她選擇在音樂上重新出發,並以獨立歌手身分出發。
「今天,我正式從主流歌手成為獨立歌手,這個遲來的春天,滿是可能性。朋友們,不用替我擔心,我生命力頑強,像長在崖上的花,每每在最嚴峻的處境,才最能盛放。
面對前方的未知,我無限期待,同時也無畏無懼。」
這是她的獨立宣言。
過去何韻詩是主流音樂工業的知名歌手、是梅豔芳的徒弟,但阿詩一直很重視自己在音樂創作上的自主性,不想成為唱片公司打造的偶像歌手。她跟我說:「我的個性本來就是對於規則、對於大家慣性在用的方法很不以為然。因為你可能很穩定地賺,但是不會有成長。我是一個一直在追求成長的人。」
因此,何韻詩與主流音樂產業的斷裂是一場遲來的分手。這不只是因為政治壓力,而是香港的主流音樂工業早已衰落,失去想像與創新的能力。她認為主流樂壇太過「離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知道在不同社會角落茁壯的生命力。
這兩年間,她開始認識更多優秀的獨立文化工作者,她也相信這是未來她可以扮演好的角色:扮演主流和獨立音樂之間的橋梁,透過她的音樂去傳遞理念。
「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唱會就是要「將有心有力的香港人,重新連接起來,重新描繪一個被遺忘了的香港。」她在文章中如此描述。
「這個計畫,根本不只是一個個人巡演,而應該是一個集體社區實驗。『十八』,起點為香港十八區,但亦可以解讀為十八般武藝,18ways of life。香港本應是個擁有無限可能的地方,集合中西方的最長處,只是不知從何時被規限了,個性被沖淡了。現時香港,可謂身處最狹窄的年代,做任何事好似都只有一個方法:抗爭如是,唱歌如是,拍戲如是,甚至表達自己也如是。」
簡言之,這個巡迴是要透過她的音樂,一方面是連結起各種獨立的、草根的文化工作者,另方面使大家重新去認識香港不同的社區,重新想像不同的香港。
這正是現在的香港需要的。香港正處於一個重新尋找自我認同的時刻,正經歷一場巨大的社會與價值轉型,人人都在思考香港的出路:「後中環價值」的香港精神是什麼呢?與中國的關係該何去何從?
何韻詩在許多時刻選擇了一條更挑戰的險路:她的公開出櫃、她的公民抗命、她從主流到獨立的音樂生涯—她的勇氣也是香港社會該具有的,一如這個演唱會的另一個標題「Re-imagine Hong Kong」:十八種香港,無限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