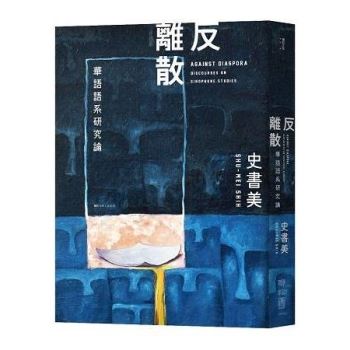第一章 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
本章就「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定義提供一個概略性的、綱領性的視角,這一視角將後殖民研究、種族研究、跨國族研究以及區域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融會起來。華語語系研究是對處於中國和中國性(Chineseness)邊緣的各種華語(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體的研究。這裡「中國和中國性邊緣」不僅僅理解為具體的,同時也要理解為概略的。它包括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地緣政治之外的華語群體,他們遍及世界各地,是持續幾個世紀以來移民和海外拓居這一歷史過程的結果;同時,它也包括中國域內的那些非漢族群體,由於漢族文化居於主導地位,面對強勢漢語時,它們或吸收融合,或進行抗拒,形成了諸多不同的回應。由此,華語語系研究整體上就是比較的、跨國族的,但它又處處與時空的具體性緊密相關,即依存於其不同研究對象而變動不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並不專門聚焦於文學,而是借助對「離散中國人」(the Chinese diaspora)這一概念的分析和批評,提出華語語系研究的粗略輪廓。在我看來,「離散中國人」這種提法是不恰當的。
一、「離散中國人」
數百年來,那些從中國遷徙出去、在全球範圍內散居各處的人們,對他們的研究作為中國研究、東南亞研究、美國華裔研究的一個子域而存在,同時,在美國的歐洲研究、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中也有零星關注。此一子域,其邊界圈定在那些從中國移居任一他鄉的人們,故被稱為「離散中國人研究」。「離散中國人」被理解為中華民族在世界範圍內的播散,作為一個普遍化範疇,它以一個統一的民族、文化、語言、發源地或祖國為基礎。新疆的維吾爾人、西藏及其周邊地區的藏人、內蒙古的蒙古人,如果他們移民海外,通常並不被認作離散中國人的一分子,而移居海外的滿人則模棱兩可。涵蓋與否的標準似乎取決於這些民族的漢化程度,因為慣常被完全棄置不顧的事實是,離散中國人主要是指漢族人的海外流散。「中國人」,換而言之,本來是一個國家屬性標誌,卻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的、語言的標誌被傳遞,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漢族中心的標籤。而事實上,在中國由官方認定的民族就有五十六個,各民族所操持的語言更是多種多樣。
通常被認定和理解的「漢語」不過是國家推行的標準語,即漢族之語,亦被稱為普通話;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很大程度上被限定為漢人;而「中國文化」指的也是漢文化。簡而言之,「中國人」這一術語作為一個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範疇,常常被限定於指稱漢族,而將所有其他民族、語言和文化排除在外。將域外的中國性簡化為漢族這一單一民族屬性,其實也只是類似訴求之翻轉(inverse)而已。歷史上,眾多民族對於形成今天的「中國」有著重要的貢獻,例如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滿族的重要遺產──他們擴充的疆域,被之後的中華民國以及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因此,這種將中國人視為漢人的民族簡化主義,與把美國人誤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並沒有什麽不同。在上述兩種情況中,都有一種貌似不同卻類似的民族中心主義在作祟。
中國海內外的各種因素究竟如何共同促成了一統的「中國人」觀念?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我們或許要追溯到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的種族主義觀念體系,他們根據膚色來認定中國人,從而忽視了中國內部的豐富性和差異性。這就是中國人成為「黃種人」且被化簡為單一民族的開始,而事實上,在不斷變化的中國地緣政治的邊界內,歷史上一直存在眾多明顯存在差異的族群。中國人一統性的外在促成力量,與中國內部一統的訴求悖論地不謀而合,尤其是在一九一一年滿族統治終結之後,中國急切盼望著出現一個統一的中國和中國人群體,以凸顯自身在文化和政治上獨立於西方的自主性。唯有在這種語境中,我們才能夠理解在十九世紀末,由西方傳教士提出的「中國人的國民性」話題,何以同時在海內外的西方人和漢人中流行起來;我們也才能夠理解,這一觀念何以在當日中國對於占據主流的漢人一如既往地散發著魅力,如有關中國人的素質問題的討論。
一方面,對於西方列強而言,它為一九四九年之前殖民中國找到理由,也使得十九世紀末到現在在這些列強國家內部實施對華人移民和華人少數群體的差別管理變得合情合理;不管出於哪個目的,「黃禍」(the Yellow Peril)這一說法的用處都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和漢人而言,種族意義上的「中國人」至少出於三個不同的意圖:以統一的民族抵制二十世紀早期的帝國主義和半殖民主義;踐行自省(self-examination),這是一種將自我(self)這一西方概念內在化的努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除了給部分少數民族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之外,還要把少數民族的國家訴求和愛國奉獻精神調適到中國這一國族身分上。
以上對「中國人」和「中國性」術語問題簡要而寬泛的探討充分表明:這些術語被激活,乃是由於與中國外部其他人的接觸,以及與內部其他族群的碰撞。這些術語的意義並非只是在最一般層面上使用,同時也在最具排他性的層面上發揮著作用,它們兼含普遍和特殊於一體。更確切地說,強勢個體把自己仿冒成普遍性,這與外部因素施加給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性的粗糙的普遍化串通一氣。這種外部因素來自西方,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自亞洲其他國家,如日本和韓國,它們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抑制且抵抗著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影響。日本和韓國明確地開展「去漢化」運動,定義自己國家的語言,以反抗中國文化的霸權,例如,在它們各自的語言中,消除日文漢字和朝鮮漢字的重要性。
人們從中國移居世界各地,在暫住國逗留,有時候也進行殖民開拓,例如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新加坡)。雖然離散中國人研究試圖通過對他們本土化傾向的強調,去拓寬中國人和中國性的問題,但「中國性」在這一領域依然占有主導地位。因此,審視「離散中國人」這個一統性的範疇在當下顯得十分重要。
這不僅是因為它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之間存在共謀關系──民族主義者習慣用「海外中國人」,而「海外中國人」這一提法假定這些人渴望回到作為祖國的中國,而且他們的最終目的也是服務中國──同時也由於它不知不覺地與西方和非西方(如美國和馬來西亞)國家對「中國性」的種族主義建構聯系在一起,且起著強化作用──在這些國家,「中國性」永遠被看做是外國的(所謂「離散的」),而不具備真正本土的資格。在東南亞、非洲、南美洲的後殖民民族國家裡,如果從歷史上說操持各種華語的人已經進入本土居民的行列,這並沒有什麽牽強之處。畢竟有些人早在六世紀就來到東南亞,比那裡民族國家的存在還要早得多,理所當然地足以經得起與國籍捆綁在一起的身分標籤。問題在於,誰在阻止他們成為一個泰國人、菲律賓人、馬來西亞人、印度尼西亞人,或是新加坡人,和其他的國民一樣被認為僅僅是多語言和多文化的居民,只不過恰好有一個來自中國的祖先而已。情況相類,誰在阻止那些在美國的中國移民(他們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來到美國)成為「華裔美國人」(在這個複合詞中強調後者「美國人」)?我們可以細想五花八門的種族排斥的行為,諸如美國的《排華法案》,越南政府對當地中國人的驅逐,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反中國人的種族暴亂,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以及爪哇的荷蘭人對中國人的屠殺,菲律賓針對中國小孩的綁架,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案例。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國人」這一具體化的範疇,作為一個種族和民族的標籤,是如何成全了諸如排外、替罪羊和迫害的各種企圖。當意大利人、猶太人和愛爾蘭人的移民逐漸成為「白人」,融入美國白人社會的主流之中,而作為華裔美國人的黃種「中國人」卻依舊還在為爭取認同而飽嘗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