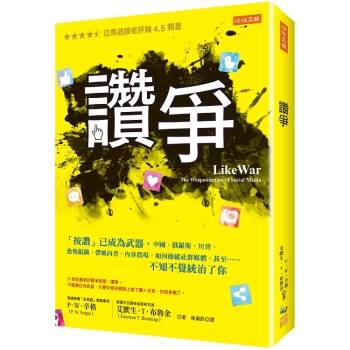1998年,中國正式展開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這項數位工程最突出的部分,是它的關鍵字過濾系統。應該加入禁用詞清單的用字或片語,它都有效的予以停用了。隨著中國網路使用者從早期靜態的網站,躍入2000年代初期的部落格平臺,再進入2009年開始的大量「微網誌」(microblogging,微博)社群媒體服務,這個關鍵字過濾系統也齊步前進。如今,每個擁有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的人肩上,都好像有一名若隱若現的政府審查員,不僅網頁的搜尋結果找不到禁用的答案,帶著禁用詞的訊息也無法送達預定的接收對象。因為禁用詞的清單即時更新,世界其他地區的網路所出現的事件,根本不會在中國發生。
舉例來說,2016年,名為「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的大批資料被洩露在網路上,並迅速轟動到病毒式蔓延。這批曾經是機密資訊的文件,容量為2.6 TB(terabytes,兆位元組),是全球精英人士用來藏錢的離岸銀行帳戶資訊──這是「網際網路完全透明化」發揮作用的有力實證。在這批洩露的公文中有紀錄顯示,8名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家人(包括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姐夫)透過離岸的空殼公司,轉移數千萬美元到中國境外。
這項資訊的每一個細節,任何線上網民都可以取得──除非你住在中國。當消息一傳出,中國中央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就發送一則緊急的「刪帖通知」。該命令表示:「查刪已轉載的巴拿馬檔相關報導。相關內容一律不再跟進,任何網站一旦發現傳播境外媒體攻擊中國的內容,將從重處理。」隨後,所有中國網民都無法取得巴拿馬文件和當中的資訊。曾有一度,巴拿馬這個國家在中國的網路搜尋結果中暫時消失,直到審查員調整禁令,貼文的刪除條件才只有當中包含「巴拿馬」與領導人名字,或者像是「離岸」之類的關聯詞。
這種過濾實在無所不在,讓中國大量衍生出一批稀奇古怪的雙關語,試圖繞過篩檢。多年來,中國的網路用戶稱呼「審查制度」為「和諧」──一個參考胡錦濤「和諧社會」的影射用字。針對審查屏蔽了一個用詞,他們可能就會說成:「和諧」它。等到審查員察覺到了,「和諧」這個用詞就被封禁了。然而,「和諧」的讀音和「河蟹」很像,於是一個字詞遭屏蔽的時候,意會到的中國網路用戶就開始稱它「被河蟹了」。此外,當社群媒體更重於視覺呈現時,審查封鎖的範圍也擴展到影像。2017年,可愛的小熊維尼消失在中國的網路上──審查員發覺「小熊維尼」是在影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因為他走路的姿勢神似維尼。
透過這種過濾、「清理整治網路」的政策,歷史本身(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人民對歷史的知識與體認)也會遭到更改。鎖定過去任何無法與政權的「和諧」歷史統一的內容,數十億網路舊貼文從現實世界中被抹除。諸如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這類重大事件,由於封禁將近三百個「危險」文字與片語,全數盡遭清除。中國相當於維基百科的百度百科,搜尋「1989」時曾經只會出現兩個回答:介於「1988」與「1990」的數字,以及「電腦病毒名稱」。其結果是集體的失憶──一整個世代對過去的關鍵時刻全然無知,而且如果他們真的意識到了,也無法搜尋到更多資訊。
就我們已經見到的,很多國家會箝制網路的討論,但在中國有一個關鍵的差異處:情況有時候和認知的犯罪不相干。其他國家會聚焦在禁止討論人權或呼籲民主化,但中國不是如此,它的審查制度會試圖壓制任何得到過多草根力量支持的訊息,不管它們無關政治──或甚至褒揚政府當局。舉例來說,一名環保人士發起禁用塑膠袋的群眾活動,即使這名活動發起人剛開始還得到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但這個看似正面的新聞就遭到嚴厲審查。在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只有北京中央政府才理當有權力用這種規模,鼓舞與動員群眾。
自中國網際網路第一天開始,政府當局已經規定網站與社群媒體服務供應商,得要承擔法律責任,負責壓制任何託管在他們網路上的「顛覆性」內容。然而,到頭來,最重的負擔落在個別的中國人民身上。雖然在2000年代初期,中國出現獨立的部落客社群,但到了2013年,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當權,情勢跟著突然逆轉。這一年,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個人散播的「網路謠言」,如果點擊瀏覽的網路用戶數達5,000名,或轉載分享超過5,000次,會面臨誹謗指控(並可能判處3年監禁)。大約在同一時間,中國最受歡迎的網路名人被「邀請」參加一場在北京開的強制會議;他們都收到印上中國網路安全局徽標的手冊,還有一場投影片簡介報告等著他們。報告中顯示,一名部落客從撰寫政治內容,轉換成探討更「合宜的」主題──例如飯店評論與時尚──之後,他變得多麼快樂。這項訊息表達得很清楚:加入我們,否則後果自負。
隨後不久,與網際網路相關的羈押步調急劇加快。由於習近平掌權,數萬名中國人民被指控「網路犯罪」,其定罪的範圍從駭客到政府當局不喜歡的任何數位內容。比方說,2017年,中國監管機構裁定,微信討論群組的創建人不僅要為自身的言論負責,也要為每位群組成員的言論擔責。
在中國,僅僅只是壓制公眾意見是不夠的,國家還必須積極塑造公眾意見。2004年開始,中國省級部門已經動員大批官僚和大學生,發表關於政府的正面、積極報導。正如一份外洩的政府公文指出,這些評論員的目標是「積極宣傳,促進團結穩定」。總之,他們的工作就是擔任啦啦隊長,展現出中國時刻保持正面積極的意象,而且他們做這件事時,看起來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
批評者很快就為這些評論員封上「五毛黨」的稱號,因為傳聞他們每發一則貼文,可換得人民幣五毛錢(最後,中國完全禁止社群媒體使用「五毛」這個用詞)。一則早期徵聘五毛黨的啟事中承諾:「年終根據發帖量、跟帖量等情況進行綜合測評,並列入全市宣傳工作表彰獎勵範疇。」到了2008年,五毛黨的成員已經壯大到約28萬人。今天,它的成員多達200萬人,一年至少會產出5億則社群媒體貼文。這種大規模、有組織的網路宣傳模式,已經發展得相當成功與普及,以至於再也不需要支付酬勞給許多成員。此外,在中國,從公關公司到中學等其他各式各樣的組織,也模仿了五毛黨的模式。
中國所有的防火牆、監視、關鍵字審查、拘捕,以及群眾外包的宣傳者,目的全是要讓14億人民的意識,與國家的意識融為一體。雖然有些人可能視其為「歐威爾風格」(Orwellian,按:指現代專制政權藉由嚴厲執行政治宣傳、監視、故意提供虛假資料、否認事實和操縱過去的政策來控制社會),但其實與它有更多共通之處的,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毛澤東所說的「群眾路線」。當毛澤東在1950年代與蘇聯決裂時,他曾批評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與蘇維埃版的共產主義太在意「個人主義」;相對的,毛澤東反而展望一個政治循環的願景,當中的群眾意志會透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折射而出,然後塑造成政策,只有歸還給人民才能進一步改善。經由這個過程,各種意見才會灌輸成所有中國人民共有的單一見解。不過現實已證明,群眾路線更難以達成;甚至因為1960年代到1970年代肅清百萬人的文化大革命,這種思維被指責為罪魁禍首,一直到毛澤東在1976年過世之後才停止履行。
藉由中國網際網路帶來的可能性,這種群眾路線的哲學捲土重來。習近平讚揚了這些新科技,因為它們實現了毛澤東「『凝聚』輿論成為一項有力共識」的願景。
為了達成這項目標,眼前暗藏更強勢的控管計畫。在新疆難駕馭的少數回族地區,已強迫居民的智慧型手機安裝「淨網衛士」的應用程式。這支應用程式不僅讓他們的訊息被追蹤或封鎖,還搭載遠端遙控功能,讓政府當局直接進入居民的手機和居家網路。為了確保人民一定會安裝這些「電子手銬」,公安會在街上設置巡迴的檢查站,查看人民的手機是否安裝這支程式。
不過,群眾路線最雄心勃勃的落實做法,是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這套體系於2015年展開序幕,在它的願景公文中,提到這套體系要如何營造一個「向上向善、誠信互助的社會風尚」──對國家忠誠不二的一項特徵。為了達成這項目標,所有中國人民都要接受許多評分,反映出他們「從商場交易到社會行為等所有生活面向的……可信任度」。
它與傳統的金融信用分數非常類似,每位人民的「社會信用」計算方法,是彙整龐大的個人資訊,並估算一個可信任度分數,分數的衡量標準基本上是依據一個人對社會的有用性。這項做法可能行得通,是因為中國人民幾乎普遍依賴微信之類的行動服務,社群網路、聊天、消費者評論、匯款,以及叫計程車或食物外送等日常事務,全部靠一支應用程式包辦。在這個過程中,使用者洩露出的訊息量相當可觀,且和自己密切相關,包括對話、朋友、閱讀清單、旅行、消費習慣等等,這些資料片斷可以形成籠統的品行評判基礎。一名程式設計師表示,購買太多電玩遊戲,或許會間接代表閒散怠惰,減低個人的分數;另一方面,經常購買尿布,可能就暗指父母的身分,這是具社會價值的有力指標。當然,一個人的政治傾向也在評分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個人在網路上對中國的凝聚力表現越「正面積極」,分數就越高;相反的,若一個人在網路發表的異議聲音「破壞社會信賴」,分數就會拉低。
這套體系的規畫公文也提到:「新體系會獎勵失信行為的舉報人。」換句話說,如果你舉報他人的不良行為,分數就會提高。你的分數也會取決於朋友與家人的分數,如果他們不夠正面積極,你會因為他們的負面消極而受到懲罰,由此鼓勵每個人去塑造自身社交網路裡的成員行為。
賦予可信任度分數力量的,是為它奠定基礎的獎賞與風險,兩者都很實際,且感受得到。這套預計在2020年全面部署於中國的評分體系,已經用在求職申請評估和發送小獎勵上,例如:得分不錯的人,可以在咖啡店免費為手機充電。不過,如果你的分數太低,就會失去使用任何東西的權利,從通宵火車的保留床位到福利津貼都是。這項分數甚至被匯集到中國最大的線上婚介服務中,就這樣,在中國政府眼中的價值,也會形塑人民的浪漫愛情與生育的觀點。
舉例來說,2016年,名為「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的大批資料被洩露在網路上,並迅速轟動到病毒式蔓延。這批曾經是機密資訊的文件,容量為2.6 TB(terabytes,兆位元組),是全球精英人士用來藏錢的離岸銀行帳戶資訊──這是「網際網路完全透明化」發揮作用的有力實證。在這批洩露的公文中有紀錄顯示,8名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家人(包括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姐夫)透過離岸的空殼公司,轉移數千萬美元到中國境外。
這項資訊的每一個細節,任何線上網民都可以取得──除非你住在中國。當消息一傳出,中國中央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就發送一則緊急的「刪帖通知」。該命令表示:「查刪已轉載的巴拿馬檔相關報導。相關內容一律不再跟進,任何網站一旦發現傳播境外媒體攻擊中國的內容,將從重處理。」隨後,所有中國網民都無法取得巴拿馬文件和當中的資訊。曾有一度,巴拿馬這個國家在中國的網路搜尋結果中暫時消失,直到審查員調整禁令,貼文的刪除條件才只有當中包含「巴拿馬」與領導人名字,或者像是「離岸」之類的關聯詞。
這種過濾實在無所不在,讓中國大量衍生出一批稀奇古怪的雙關語,試圖繞過篩檢。多年來,中國的網路用戶稱呼「審查制度」為「和諧」──一個參考胡錦濤「和諧社會」的影射用字。針對審查屏蔽了一個用詞,他們可能就會說成:「和諧」它。等到審查員察覺到了,「和諧」這個用詞就被封禁了。然而,「和諧」的讀音和「河蟹」很像,於是一個字詞遭屏蔽的時候,意會到的中國網路用戶就開始稱它「被河蟹了」。此外,當社群媒體更重於視覺呈現時,審查封鎖的範圍也擴展到影像。2017年,可愛的小熊維尼消失在中國的網路上──審查員發覺「小熊維尼」是在影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因為他走路的姿勢神似維尼。
透過這種過濾、「清理整治網路」的政策,歷史本身(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人民對歷史的知識與體認)也會遭到更改。鎖定過去任何無法與政權的「和諧」歷史統一的內容,數十億網路舊貼文從現實世界中被抹除。諸如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這類重大事件,由於封禁將近三百個「危險」文字與片語,全數盡遭清除。中國相當於維基百科的百度百科,搜尋「1989」時曾經只會出現兩個回答:介於「1988」與「1990」的數字,以及「電腦病毒名稱」。其結果是集體的失憶──一整個世代對過去的關鍵時刻全然無知,而且如果他們真的意識到了,也無法搜尋到更多資訊。
就我們已經見到的,很多國家會箝制網路的討論,但在中國有一個關鍵的差異處:情況有時候和認知的犯罪不相干。其他國家會聚焦在禁止討論人權或呼籲民主化,但中國不是如此,它的審查制度會試圖壓制任何得到過多草根力量支持的訊息,不管它們無關政治──或甚至褒揚政府當局。舉例來說,一名環保人士發起禁用塑膠袋的群眾活動,即使這名活動發起人剛開始還得到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但這個看似正面的新聞就遭到嚴厲審查。在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只有北京中央政府才理當有權力用這種規模,鼓舞與動員群眾。
自中國網際網路第一天開始,政府當局已經規定網站與社群媒體服務供應商,得要承擔法律責任,負責壓制任何託管在他們網路上的「顛覆性」內容。然而,到頭來,最重的負擔落在個別的中國人民身上。雖然在2000年代初期,中國出現獨立的部落客社群,但到了2013年,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當權,情勢跟著突然逆轉。這一年,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個人散播的「網路謠言」,如果點擊瀏覽的網路用戶數達5,000名,或轉載分享超過5,000次,會面臨誹謗指控(並可能判處3年監禁)。大約在同一時間,中國最受歡迎的網路名人被「邀請」參加一場在北京開的強制會議;他們都收到印上中國網路安全局徽標的手冊,還有一場投影片簡介報告等著他們。報告中顯示,一名部落客從撰寫政治內容,轉換成探討更「合宜的」主題──例如飯店評論與時尚──之後,他變得多麼快樂。這項訊息表達得很清楚:加入我們,否則後果自負。
隨後不久,與網際網路相關的羈押步調急劇加快。由於習近平掌權,數萬名中國人民被指控「網路犯罪」,其定罪的範圍從駭客到政府當局不喜歡的任何數位內容。比方說,2017年,中國監管機構裁定,微信討論群組的創建人不僅要為自身的言論負責,也要為每位群組成員的言論擔責。
在中國,僅僅只是壓制公眾意見是不夠的,國家還必須積極塑造公眾意見。2004年開始,中國省級部門已經動員大批官僚和大學生,發表關於政府的正面、積極報導。正如一份外洩的政府公文指出,這些評論員的目標是「積極宣傳,促進團結穩定」。總之,他們的工作就是擔任啦啦隊長,展現出中國時刻保持正面積極的意象,而且他們做這件事時,看起來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
批評者很快就為這些評論員封上「五毛黨」的稱號,因為傳聞他們每發一則貼文,可換得人民幣五毛錢(最後,中國完全禁止社群媒體使用「五毛」這個用詞)。一則早期徵聘五毛黨的啟事中承諾:「年終根據發帖量、跟帖量等情況進行綜合測評,並列入全市宣傳工作表彰獎勵範疇。」到了2008年,五毛黨的成員已經壯大到約28萬人。今天,它的成員多達200萬人,一年至少會產出5億則社群媒體貼文。這種大規模、有組織的網路宣傳模式,已經發展得相當成功與普及,以至於再也不需要支付酬勞給許多成員。此外,在中國,從公關公司到中學等其他各式各樣的組織,也模仿了五毛黨的模式。
中國所有的防火牆、監視、關鍵字審查、拘捕,以及群眾外包的宣傳者,目的全是要讓14億人民的意識,與國家的意識融為一體。雖然有些人可能視其為「歐威爾風格」(Orwellian,按:指現代專制政權藉由嚴厲執行政治宣傳、監視、故意提供虛假資料、否認事實和操縱過去的政策來控制社會),但其實與它有更多共通之處的,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毛澤東所說的「群眾路線」。當毛澤東在1950年代與蘇聯決裂時,他曾批評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與蘇維埃版的共產主義太在意「個人主義」;相對的,毛澤東反而展望一個政治循環的願景,當中的群眾意志會透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折射而出,然後塑造成政策,只有歸還給人民才能進一步改善。經由這個過程,各種意見才會灌輸成所有中國人民共有的單一見解。不過現實已證明,群眾路線更難以達成;甚至因為1960年代到1970年代肅清百萬人的文化大革命,這種思維被指責為罪魁禍首,一直到毛澤東在1976年過世之後才停止履行。
藉由中國網際網路帶來的可能性,這種群眾路線的哲學捲土重來。習近平讚揚了這些新科技,因為它們實現了毛澤東「『凝聚』輿論成為一項有力共識」的願景。
為了達成這項目標,眼前暗藏更強勢的控管計畫。在新疆難駕馭的少數回族地區,已強迫居民的智慧型手機安裝「淨網衛士」的應用程式。這支應用程式不僅讓他們的訊息被追蹤或封鎖,還搭載遠端遙控功能,讓政府當局直接進入居民的手機和居家網路。為了確保人民一定會安裝這些「電子手銬」,公安會在街上設置巡迴的檢查站,查看人民的手機是否安裝這支程式。
不過,群眾路線最雄心勃勃的落實做法,是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這套體系於2015年展開序幕,在它的願景公文中,提到這套體系要如何營造一個「向上向善、誠信互助的社會風尚」──對國家忠誠不二的一項特徵。為了達成這項目標,所有中國人民都要接受許多評分,反映出他們「從商場交易到社會行為等所有生活面向的……可信任度」。
它與傳統的金融信用分數非常類似,每位人民的「社會信用」計算方法,是彙整龐大的個人資訊,並估算一個可信任度分數,分數的衡量標準基本上是依據一個人對社會的有用性。這項做法可能行得通,是因為中國人民幾乎普遍依賴微信之類的行動服務,社群網路、聊天、消費者評論、匯款,以及叫計程車或食物外送等日常事務,全部靠一支應用程式包辦。在這個過程中,使用者洩露出的訊息量相當可觀,且和自己密切相關,包括對話、朋友、閱讀清單、旅行、消費習慣等等,這些資料片斷可以形成籠統的品行評判基礎。一名程式設計師表示,購買太多電玩遊戲,或許會間接代表閒散怠惰,減低個人的分數;另一方面,經常購買尿布,可能就暗指父母的身分,這是具社會價值的有力指標。當然,一個人的政治傾向也在評分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個人在網路上對中國的凝聚力表現越「正面積極」,分數就越高;相反的,若一個人在網路發表的異議聲音「破壞社會信賴」,分數就會拉低。
這套體系的規畫公文也提到:「新體系會獎勵失信行為的舉報人。」換句話說,如果你舉報他人的不良行為,分數就會提高。你的分數也會取決於朋友與家人的分數,如果他們不夠正面積極,你會因為他們的負面消極而受到懲罰,由此鼓勵每個人去塑造自身社交網路裡的成員行為。
賦予可信任度分數力量的,是為它奠定基礎的獎賞與風險,兩者都很實際,且感受得到。這套預計在2020年全面部署於中國的評分體系,已經用在求職申請評估和發送小獎勵上,例如:得分不錯的人,可以在咖啡店免費為手機充電。不過,如果你的分數太低,就會失去使用任何東西的權利,從通宵火車的保留床位到福利津貼都是。這項分數甚至被匯集到中國最大的線上婚介服務中,就這樣,在中國政府眼中的價值,也會形塑人民的浪漫愛情與生育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