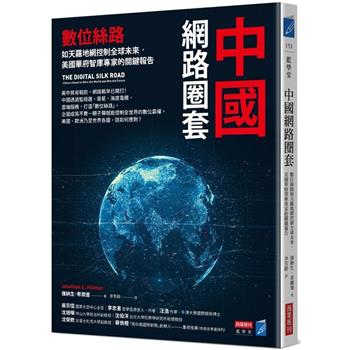【摘錄1】_戰場全貌與局勢
中國透過一個又一個的計畫,增強了自己在全球網路中的地位。我追蹤中國的全球基礎建設行動長達五年,集成有關中國計畫的最大開放源碼資料庫之一,確實且仔細地研究它們。我跋山涉水,包括走上通往中國與巴基斯坦邊界的一條新闢道路;爬上中國建造的、從衣索比亞到吉布地共和國(Djibouti)的鐵路;進入中國位於希臘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港口。這些只不過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幾個旗艦計畫而已。
但別像我剛開始那樣,被這些表面的陸上工程給欺騙了。中國可不是僅僅在建造新的運輸網絡,它最宏大的野心從地下、海底,一直延伸至空中的電波頻道。前述三項建設工程全都有比較看不到的數位層面,中國的光纖電纜橫跨中國與巴基斯坦和衣索比亞與吉布地邊界,中國的海底電纜準備連結巴基斯坦和吉布地,還包括延伸至歐洲的分支。在比雷埃夫斯,華為公司安裝了路由器與轉換器,翻修此港口的網路,為來到此港口的遊輪及其他訪查客提供免費Wi-Fi。中國把數位和傳統的基礎建設包裝在一起,而世界迫切需要兩者。
就連在蒙大拿州的鄉村地區,都可以見到中國的銷售宣傳。我造訪美國最偏僻的城鎮之一蒙大拿州格拉斯哥鎮(Glasgow)時,原本預期當地居民會因使用華為的通訊器材設備傳輸而感到憂心。但我發現,在格拉斯哥鎮,馬斯洛的數位需求層次是不同的,比起外國器材設備的現身,失去連結的風險反倒令居民感覺更迫切、更糟糕。不論在美國的鄉村地區,或者是亞洲的開發中國家,多數用戶沒那麼關心外國的情報刺探活動,他們更關心的是可以不必繳大筆的電信費。需要研究與修改產業政策才能提供別的平價選擇,若不提供這樣的選擇,美國官員打的近乎是一場不可能勝出的戰役。
光是憂懼,不足以抵擋中國的數位絲路。中國在國內使用監控技術來鎮壓人民,但很多外國領導人非但沒有被這事實驚駭,反而心生興趣,他們看到了機會——取得這不僅可用於強化自身統治權,還能在他們的城市減少犯罪與刺激成長的工具(參見第四章)。根據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席娜‧切斯納‧格雷勝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的研究指出,現在有超過八十個國家使用中國的監控技術,而這些國家遍及澳洲和南極洲除外的每個大陸。跟其他連網器材一樣,從智慧型家電到健身手環,這些系統通常側重成本勝過資安性能,這也致使它們易於發生錯誤和遭到攻擊。
這個結構反映了中國利益的網際網路新版圖正在形成。中國的電信業三巨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通信——擴張進入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僅僅十年,中國從仰賴外國公司的海底電纜,轉變成控制舉世第四大這類系統的供應商,且鋪設了足以環繞、當權的電纜。本書第五章將進一步探討中國的這些行動,這是不對稱戰略的一部分:北京當局想傳輸、儲存及探勘更多的全球資料,同時希望保持中國自身的網路不被外界觸及。
中國軍方領導人說,太空是「新的制高點」。完成於二○二○年的北斗衛星網路,不僅能引導中國的飛彈、戰鬥機與海軍軍艦,還可以引導車輛、拖拉機、手機。中國替懷抱太空雄心的國家,提供入門的套裝方案,佐以中國發射、甚至掌控的衛星,直到夥伴能夠起飛。太空衛星競賽已經移向地球低軌衛星(參見第六章),希望為全球提供寬頻,馬斯克的SpaceX、亞馬遜與其他幾家公司都推出龐大的衛星群,中國當然也有自己的計畫。
若中國能夠整合自己在無線網路、連網器材、網際網路骨幹及衛星這四大領域的活動,收穫將巨額增加。當一項服務或產品的價值,隨著使用者增加而提高時,就會發生網路效應,誠如創造了電信帝國的前AT&T總裁西奧多‧魏爾(Theodore Vail)在一九○八年時解釋的:「一具電話,若未連結至另一端,它甚至連玩具或科學器材都稱不上,就是世上最沒用的東西之一。它的價值有賴於和另一具電話連結,以及這種連結數量的增加。」網路效應不是什麼新概念,但它們的重要性更甚以往。
在資訊價值空前的時代,中國透過數位絲路,正在把自己變成全球資訊網路的中心。誠如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主席湯姆‧惠勒(Tom Wheeler),在著作《從古騰堡到谷歌》(From Gutenberg to Google)中所言:「十九和二十世紀的資本資產是由網路促進的工業生產,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資產是源自於網路創造出的資訊。」矽谷投資人詹姆斯‧庫里爾(James Currier)估計,自一九九四年以來,科技公司創造價值中的七○%是得力於網路效應,最強大且可捍衛的網路效應來自實體結點與連結,因為它們需要龐大的前置投資。
中國正在投資這些項目,把尖端系統拼湊起來。中國的工程師在二○一七年舉辦世上第一場量子加密(quantum-encrypted)視訊會議,需要使用一顆造價一億美元的特製衛星、地面光纖網路,以及先進的演算法。雖然,這系統還不完善,仍然是朝建造超級安全網路邁進了一大步。製造量子加密系統的麥吉丘科技公司(MagiQ Technologies)的首席科學家卡雷布‧克里斯汀生(Caleb Christensen),告訴《連線》(Wired)雜誌記者陳蘇菲(Sophia Chen,音譯):「他們展示了一個完整的基礎設施,把所有環節連結起來,沒人這麼做過。」
中國聚焦於新興市場,這可以大大增強其網路效應。根據預測,直到二○五○年,全球人口成長將有過半數發生在非洲,而非洲有七○%的4G網路是華為所建設的。由中國鋪設、連結巴基斯坦和吉布地的海底電纜,將成為亞洲與非洲之間最短的網際網路連結,而這兩個洲是近年間國際頻寬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中國甚至已經使自己成為奈及利亞和白俄羅斯之間的中心結點,這兩個國家有中國發射的衛星,並且在中國的促進下,簽定相互提供支援服務的合約。中國在發展下一代通訊技術的同時,也企圖預先取得下一代的市場。
這種左右開弓的做法可以使中國具有建立下一波通訊技術標準的地位,且進一步擴大其網路效應。當某種標準被廣為接受時——例如,通用序列匯流排(USB),一種纜線標準——器材就能夠跨國及跨廠連結或相容。若能建立起全球標準的話,你的產品就變得更通用。中國官員了解這點,他們很早就說過:三流國家製造東西;二流國家設計東西;一流國家建立標準。他們大舉投資既有的標準組織,並提議創立「一帶一路標準論壇」——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平行架構。
若中國成為全球首要的網路營運者,就可以意外地收割商業及戰略的果實;它可以重塑全球的資料、財金和通訊流,以反映利益。在隔絕美國的制裁與情報刺探之下,它可以無敵地掌握與了解市場動向、外國競爭者的商議內容,以及陷入其網路中無數個人的生活。
【摘錄2】_「歷史已經停止了」
在中國西北部的新疆省,政府強迫超過一百萬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及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進入拘禁營。雖然,維吾爾族已被迫害了數十年,但在二○○九年發生近兩百人死亡和數千人受傷的烏魯木齊示威暴動事件後,中國政府開始採取更極端的手段。當記者揭露拘禁營時,中國官方先是否認,後來聲稱參加者是出於自願。
但是,外洩的中共內部計畫文件,顯示了駭人細節。美國官員稱其為:「當今世上最大規模的監禁少數民族。」而新聞工作者貝書穎(Bethany Allen-Ebrahimian)為「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報導這些文件時,如此描述風格:「(它)結合了標準的中國官腔與歐威爾式的雙言巧語。」跟《一九八四》中大洋國負責逮捕、折磨異議人士的「友愛部」(Ministry of Love)一樣,中國把監禁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拘禁營稱為「再教育營」,將遭監禁者名為「學員」。
根據倖存者描述,拘禁營裡的生活非常殘暴。每天的活動就是為了剝除遭監禁者的個人特性,把他們轉化成臣服於中國政府的哀求者。遭監禁者被迫做出懺悔,被政府宣傳影片洗腦,上國語及中國共產黨思想課。先前被拘禁者告訴《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進餐時,他們的唯一選擇非常不人道。他們可以喊:「習近平萬歲!」然後獲得一個包子或一碗飯;或者,他們可以保持沉默,然後飽嘗電牛棒上身的劇痛。「權力就在於把人們的思想粉碎,再把它們拼湊成你選擇的新樣子。」《一九八四》中的反派人物歐布萊恩說。
新疆拘禁營倚賴持續監視與重罰,被洩露的中國政府官方文件中,要求獄方必須確保:「全面影像監視宿舍與教室,完全無死角、無盲點。」遭監禁者就算只是最細微的違規,也可能導致他(她)被拘禁的期間延長,「你進入拘禁營時是一千分,無法再得分,但若你打呵欠或微笑,就會扣分。」一位倖存者解釋35:「一旦低於五百分,你就得被多拘禁一年。」這是一種旨在傷害、只往下扣分的制度,你無法靠提高分數而獲釋,只能靠著減少扣分來走出拘禁營。
就算走出中國的勞動營也沒有自由。遭監禁者返回社區後,仍然被鋪天蓋地的監視器及公安所監控。在使用惡意軟體監視維吾爾族的手機多年後,中國政府的方法與手段更是變本加厲,它規定維吾爾族必須安裝用於監視自身所在地、電話及簡訊的應用程式,還必須呈報「健康檢查」——包括抽血及DNA樣本,以貢獻給中國不斷擴增的生物特徵資料庫。
中國採取數位鎮壓和低科技監控手段雙管齊下,嚴禁那些維吾爾族穆斯林留鬍子和戴面紗,除了「少數民族特徵偵測」,中國的監控設備製造商還在其下的人臉分析中提供「鬍鬚偵測」。剝除維吾爾族的身分認同後,中國政府還不罷手,在每天的「反恐」安全訓練中,讓他們跟一個無形、虛構的敵人戰鬥。這「敵人」看起來就像他們以往的自身,但被誇張地扭曲成一個陰暗的人物。
致力於消滅維吾爾族身分的同時,中國當局也拆毀維吾爾族文化信仰中心的實體場所。喀什市是歷史悠久的貿易站,有許多維吾爾族的聖地,該市最古老的建築在二○○九年被摧毀,而中國當局聲稱這是為了地震安全考量。偏執的中國當局還把有幾百年歷史、維吾爾族做禮拜的艾提朵爾清真寺(Id Kah Mosque)轉變成旅遊景點,一個向世界展示與宣傳中國尊重穆斯林宗教自由的樣板。喀什市到處都有檢查站監視個人行動,把監視資料輸入詳細記錄他們家庭、教育及以往活動的資料庫裡。
新疆的綠洲城市和田市,幾世紀以來都是繁榮貿易樞紐,也是維吾爾族朝聖者的聚集地。現在,進入此市集必須做臉部掃描,並出示身分證。和田市廣場上有座維吾爾族農民暨政治人物庫爾班‧土魯木(Kurban Tulum)和毛澤東握手的雕像。離這雕像不到一千六百多公尺處,有一座具千年歷史的維吾爾族蘇爾坦公墓,在二○一九年被中國政府挖掘後夷平。中國官方聲稱這是為了發展,並且表示:「為全市市民提供一個廣闊優美的環境。」被夷平之地,有部分成了停車場。
在《一九八四》中,主角溫斯頓問道:「你發現了沒有,從昨天的過往,實際上全都被消除了?……每一個紀錄都被摧毀或竄改,每一本書都被改寫,每一幅畫都被重畫,每座雕像、每條街、每棟建築都被改名,每個日期都被改動,每天、每分鐘都在進行這種過程。歷史已經停止了,除了無盡的現在,別無其他存在,在這無盡的現在中,黨永遠是正確的。」
中國共產黨想藉由改寫過去來控制未來。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指出,根據衛星影像顯示,自二○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的政策行動已經造成新疆省三分之二的清真寺被摧毀或損壞。那些未被摧毀的清真寺則被裝滿了監視器。海康威視承包的一項工程,是在新疆某個縣、近千座清真寺門口安裝監視器。根據羅雷特的研究指出,光是二○一六年與二○一七年間,海康威視和大華科技就獲得了中國政府超過十億美元的新疆監視器裝設承包合約。
自二○一○年在深圳證交所掛牌上市後,海康威視就一直持續加強它和中國政府的關係與合作。在二○一五年四月舉行的中共中電海康集團有限公司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海康威視董事長致詞時強調,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該公司的事業發展目標整合起來的重要性。幾週後,習近平來到海康威視總部,視察產品及研發中心,告訴該公司員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指日可待。」那年年底,中國政府就為海康威視提供了三十億美元的信用額度。
中國的監控業巨人也受惠於美國的科技與投資。海康威視從輝達公司(Nvidia)購買可編程晶片,用於訓練其人工智慧演算法;該公司也聲稱和英特爾(Intel)、索尼(Sony)、威騰電子(Western Digital)合作。威騰電子在二○一九年初的貿易展廣告中,還宣傳它跟海康威視有合作關係。希捷科技(Seagate)在二○○五年與海康威視共同發布,推出稱為第一款專門針對監控設備開發的硬碟機。當希捷在二○一七年宣布推出第一款為人工智慧監控系統開發的硬碟機時,該公司還引述海康威視、大華科技及宇視科技這三家公司代表的話,「作為策略夥伴,希捷的先進技術將幫助大華科技在人工智慧領域達到新高水平。」大華科技國內銷售業務中心的總監說。
【摘錄3】_「難忘的恥辱」
中國是太空領域的遲到者,但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證明當軍事及商業利益開始結合時,它能夠快速行動。命名自「北斗七星」的北斗系統計畫,正式啟動於一九九四年,接下來二十五年,中國工程師分三階段來應付建造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挑戰,外國的威脅促使他們加緊腳步向前。
中國聰明地把北斗計畫,裝扮成純粹良善的公共財,以及它重返創新前鋒的例子。中國甚至在二○一九年六月時,於奧地利維也納國際中心,舉辦了一場中國導航展。這場主題為「從指南針到北斗」(From the Compass to BeiDou)的展覽,選在聯合國年度衛星研討會的幾個月前舉行,彰顯中國對導航與計時系統的貢獻。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副主任馬加慶,在開幕式中致詞時說:「我們想展示導航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以增進人們的了解。」
但是,跟美國的GPS系統一樣,中國的北斗系統的發展,有其軍事根源。中國在一九七○年發射其第一顆人造衛星——以毛澤東主義革命頌歌〈東方紅〉為命名的「東方紅一號」,其重量遠大於蘇聯、美國、法國及日本這四個國家分別發射的第一顆衛星的重量總和。它只有基本功能,設計主要是為了收集遙測數據、傳回地球。但是,這顆衛星振奮了中國的雄心,在其二十八天的短暫壽命中,循環廣播〈東方紅〉樂曲。
中國投資於太空及其他戰略性技術,在一九八六年三月獲得動能。當時,中國四位知名的戰略武器科學家,聯名寫了一封建議書給鄧小平。他們在建議書中強調,科技發展事關國際國力競爭,並且警告,若中國繼續漠不關心,將會落後。鄧小平只花了兩天就決定,他在建議書的複製本上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請找專家和有關負責同志,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做決斷,不可拖延。」
一九九○年代,兩事件凸顯了美國在太空領域的力量及中國的弱點。第一個事件是波灣戰爭,這讓GPS在戰場上做出驚人展示,中國軍官觀看美國使用其太空能力來瞄準、收集情報和戰場通訊。「這次戰爭的實踐表明,電子戰已成為現代聯合戰役首要的作戰方式,」中國軍事期刊後來寫道:「太空戰場的正式亮相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更顯中國的弱點。此危機始於一九九五年,在美國國會的協助下,台灣總統李登輝不理會中國的壓力,前往康乃爾大學演講。隨著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日期逼近(現任總統李登輝為候選人之一),中國宣布進行大規模軍演,並朝東海發射三枚飛彈,距離一個台灣軍事基地僅約十六公里。
第一枚飛彈命中目標,第二及第三枚飛彈射偏。多年後,一名已退役的中國解放軍上校把這失敗歸因於美國關閉GPS訊號所導致,「這對解放軍來說是莫大的恥辱……難忘的恥辱,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下定決心,要開發自己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及定位系統的原因,無論花多少錢,」他在二○○九年告訴《南華早報》:「北斗對我們是必要,我們從慘痛教訓中學到這點。」
為了改進衛星能力,中國當時已經尋求美國公司,包括羅拉太空與通訊(Loral Space & Communications)及休斯電子(Hughe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幫助解決近期一連串發射失敗的問題。根據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九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這些美國公司的協助與建議,改善了中國的長征火箭。美國政府後來對這些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外洩重大關鍵技術的美國公司處以罰款,國會也縮減對中國出口衛星的限制,但已經太遲,中國已經取得衛星的關鍵技術,包括設計及導引系統的改進。
中國在二○○○年發射了第一顆北斗衛星,就在此時,中國軍方開始論述,太空是在所有其他領域發動戰爭的重要環節。當然啦,中國仍繼續堅稱北斗衛星計畫與中國的其他太空活動都是以和平為目的。二○○三年九月,中國加入歐盟的伽利略定位系統(Galileo Positioning System)計畫,二○○三年十月,中國外交部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方願意按照平等互利原則積極參與伽利略系統的開發和未來的應用。」
參與伽利略系統計畫,為中國提供了改進北斗系統的捷徑。中國和歐盟合作簽署的十二紙合約,迄今都未公開。中國負責製造與測試有關於訊號干擾、衛星定位、地面接收等功能的技術。中國科學家透過參與,取得了和歐洲科學家共事的更好通路。這也讓中國得以購買原子鐘,進行逆向工程,這是導航系統中關鍵至要的元件。另一方面,中國對伽利略系統計畫投資的二億二千八百萬美元,實際上是花在中國公司身上,這些中國公司保有硬體及智慧財產的所有權。
中國在二○○七年完成北斗計畫的第一階段,成功發射了第四顆衛星。一個衛星導航系統要啟用,起碼需要四顆衛星。這系統主要覆蓋中國領土,性能上大致是實驗性質,但中國已經做出了大躍進。它現在已有基本要素,展示了能夠正確地結合它們,並把最終成品送到太空。
中國從此開始奔向覆蓋全球的目標,到了二○一二年年底,北斗系統已有十六顆衛星在軌道上,開放商業使用,服務中國及鄰近的亞太地區國家。二○一八年,中國增加了十八顆北斗衛星,達成全球覆蓋。這一年,中國完成成功發射任務的次數位居全球國家之冠,這是中國太空計畫史上頭一次寫下的紀錄。「從今往後,無論你走到哪裡,北斗都會一直陪著你。」北斗計畫發言人冉承其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說。
推動完成北斗系統時,中國結合了太空及網路能力,著眼於贏得未來的戰爭。二○一五年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戰略支援部隊:負責把太空、網路及電子作戰能力整合成軍事行動的新組織。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有了單一組織,負責中國軍事規畫者所謂的「信息支援」(資訊支援)及「信息優勢」(資訊優勢)。這可以使人民解放軍在衝突中運作,同時也能夠癱瘓敵人的系統。翌年,中國發布《二○一六年中國航天活動白皮書》,宣布意圖在二○二一年前完成「穩定可靠的航天基礎設施」。
中國的北斗系統,甚至在一些層面上表現優於GPS。在亞太地區,它比GPS更準確,但全球來說,它的準確性稍遜於GPS。它的衛星占用較少的軌道平面,維修因此較容易,這受惠於它從更早建立的衛星導航系統中所學習而得的知識。北斗系統也讓使用者可以傳送簡訊,它的較大足跡提高其可得性,根據《日經新聞》(Nikkei Asia)報導,在一百六十五個首都城市,北斗衛星提供的覆蓋面積比GPS更廣。
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得的北斗系統服務還要更強大,它提供十公分的定位精度,而且使用時毫不浪費時間。二○二○年八月,人民解放軍在監視台灣海峽活動的東部戰區,為其地面部隊部署了裝備北斗功能的火箭系統,次月,中國在台灣海峽的海空聯合軍演時,可能也已經測試了使用北斗系統的軍武的能力。人民解放軍沒忘記二十五年前的恥辱。
中國透過一個又一個的計畫,增強了自己在全球網路中的地位。我追蹤中國的全球基礎建設行動長達五年,集成有關中國計畫的最大開放源碼資料庫之一,確實且仔細地研究它們。我跋山涉水,包括走上通往中國與巴基斯坦邊界的一條新闢道路;爬上中國建造的、從衣索比亞到吉布地共和國(Djibouti)的鐵路;進入中國位於希臘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港口。這些只不過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幾個旗艦計畫而已。
但別像我剛開始那樣,被這些表面的陸上工程給欺騙了。中國可不是僅僅在建造新的運輸網絡,它最宏大的野心從地下、海底,一直延伸至空中的電波頻道。前述三項建設工程全都有比較看不到的數位層面,中國的光纖電纜橫跨中國與巴基斯坦和衣索比亞與吉布地邊界,中國的海底電纜準備連結巴基斯坦和吉布地,還包括延伸至歐洲的分支。在比雷埃夫斯,華為公司安裝了路由器與轉換器,翻修此港口的網路,為來到此港口的遊輪及其他訪查客提供免費Wi-Fi。中國把數位和傳統的基礎建設包裝在一起,而世界迫切需要兩者。
就連在蒙大拿州的鄉村地區,都可以見到中國的銷售宣傳。我造訪美國最偏僻的城鎮之一蒙大拿州格拉斯哥鎮(Glasgow)時,原本預期當地居民會因使用華為的通訊器材設備傳輸而感到憂心。但我發現,在格拉斯哥鎮,馬斯洛的數位需求層次是不同的,比起外國器材設備的現身,失去連結的風險反倒令居民感覺更迫切、更糟糕。不論在美國的鄉村地區,或者是亞洲的開發中國家,多數用戶沒那麼關心外國的情報刺探活動,他們更關心的是可以不必繳大筆的電信費。需要研究與修改產業政策才能提供別的平價選擇,若不提供這樣的選擇,美國官員打的近乎是一場不可能勝出的戰役。
光是憂懼,不足以抵擋中國的數位絲路。中國在國內使用監控技術來鎮壓人民,但很多外國領導人非但沒有被這事實驚駭,反而心生興趣,他們看到了機會——取得這不僅可用於強化自身統治權,還能在他們的城市減少犯罪與刺激成長的工具(參見第四章)。根據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席娜‧切斯納‧格雷勝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的研究指出,現在有超過八十個國家使用中國的監控技術,而這些國家遍及澳洲和南極洲除外的每個大陸。跟其他連網器材一樣,從智慧型家電到健身手環,這些系統通常側重成本勝過資安性能,這也致使它們易於發生錯誤和遭到攻擊。
這個結構反映了中國利益的網際網路新版圖正在形成。中國的電信業三巨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通信——擴張進入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僅僅十年,中國從仰賴外國公司的海底電纜,轉變成控制舉世第四大這類系統的供應商,且鋪設了足以環繞、當權的電纜。本書第五章將進一步探討中國的這些行動,這是不對稱戰略的一部分:北京當局想傳輸、儲存及探勘更多的全球資料,同時希望保持中國自身的網路不被外界觸及。
中國軍方領導人說,太空是「新的制高點」。完成於二○二○年的北斗衛星網路,不僅能引導中國的飛彈、戰鬥機與海軍軍艦,還可以引導車輛、拖拉機、手機。中國替懷抱太空雄心的國家,提供入門的套裝方案,佐以中國發射、甚至掌控的衛星,直到夥伴能夠起飛。太空衛星競賽已經移向地球低軌衛星(參見第六章),希望為全球提供寬頻,馬斯克的SpaceX、亞馬遜與其他幾家公司都推出龐大的衛星群,中國當然也有自己的計畫。
若中國能夠整合自己在無線網路、連網器材、網際網路骨幹及衛星這四大領域的活動,收穫將巨額增加。當一項服務或產品的價值,隨著使用者增加而提高時,就會發生網路效應,誠如創造了電信帝國的前AT&T總裁西奧多‧魏爾(Theodore Vail)在一九○八年時解釋的:「一具電話,若未連結至另一端,它甚至連玩具或科學器材都稱不上,就是世上最沒用的東西之一。它的價值有賴於和另一具電話連結,以及這種連結數量的增加。」網路效應不是什麼新概念,但它們的重要性更甚以往。
在資訊價值空前的時代,中國透過數位絲路,正在把自己變成全球資訊網路的中心。誠如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主席湯姆‧惠勒(Tom Wheeler),在著作《從古騰堡到谷歌》(From Gutenberg to Google)中所言:「十九和二十世紀的資本資產是由網路促進的工業生產,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資產是源自於網路創造出的資訊。」矽谷投資人詹姆斯‧庫里爾(James Currier)估計,自一九九四年以來,科技公司創造價值中的七○%是得力於網路效應,最強大且可捍衛的網路效應來自實體結點與連結,因為它們需要龐大的前置投資。
中國正在投資這些項目,把尖端系統拼湊起來。中國的工程師在二○一七年舉辦世上第一場量子加密(quantum-encrypted)視訊會議,需要使用一顆造價一億美元的特製衛星、地面光纖網路,以及先進的演算法。雖然,這系統還不完善,仍然是朝建造超級安全網路邁進了一大步。製造量子加密系統的麥吉丘科技公司(MagiQ Technologies)的首席科學家卡雷布‧克里斯汀生(Caleb Christensen),告訴《連線》(Wired)雜誌記者陳蘇菲(Sophia Chen,音譯):「他們展示了一個完整的基礎設施,把所有環節連結起來,沒人這麼做過。」
中國聚焦於新興市場,這可以大大增強其網路效應。根據預測,直到二○五○年,全球人口成長將有過半數發生在非洲,而非洲有七○%的4G網路是華為所建設的。由中國鋪設、連結巴基斯坦和吉布地的海底電纜,將成為亞洲與非洲之間最短的網際網路連結,而這兩個洲是近年間國際頻寬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中國甚至已經使自己成為奈及利亞和白俄羅斯之間的中心結點,這兩個國家有中國發射的衛星,並且在中國的促進下,簽定相互提供支援服務的合約。中國在發展下一代通訊技術的同時,也企圖預先取得下一代的市場。
這種左右開弓的做法可以使中國具有建立下一波通訊技術標準的地位,且進一步擴大其網路效應。當某種標準被廣為接受時——例如,通用序列匯流排(USB),一種纜線標準——器材就能夠跨國及跨廠連結或相容。若能建立起全球標準的話,你的產品就變得更通用。中國官員了解這點,他們很早就說過:三流國家製造東西;二流國家設計東西;一流國家建立標準。他們大舉投資既有的標準組織,並提議創立「一帶一路標準論壇」——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平行架構。
若中國成為全球首要的網路營運者,就可以意外地收割商業及戰略的果實;它可以重塑全球的資料、財金和通訊流,以反映利益。在隔絕美國的制裁與情報刺探之下,它可以無敵地掌握與了解市場動向、外國競爭者的商議內容,以及陷入其網路中無數個人的生活。
【摘錄2】_「歷史已經停止了」
在中國西北部的新疆省,政府強迫超過一百萬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及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進入拘禁營。雖然,維吾爾族已被迫害了數十年,但在二○○九年發生近兩百人死亡和數千人受傷的烏魯木齊示威暴動事件後,中國政府開始採取更極端的手段。當記者揭露拘禁營時,中國官方先是否認,後來聲稱參加者是出於自願。
但是,外洩的中共內部計畫文件,顯示了駭人細節。美國官員稱其為:「當今世上最大規模的監禁少數民族。」而新聞工作者貝書穎(Bethany Allen-Ebrahimian)為「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報導這些文件時,如此描述風格:「(它)結合了標準的中國官腔與歐威爾式的雙言巧語。」跟《一九八四》中大洋國負責逮捕、折磨異議人士的「友愛部」(Ministry of Love)一樣,中國把監禁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拘禁營稱為「再教育營」,將遭監禁者名為「學員」。
根據倖存者描述,拘禁營裡的生活非常殘暴。每天的活動就是為了剝除遭監禁者的個人特性,把他們轉化成臣服於中國政府的哀求者。遭監禁者被迫做出懺悔,被政府宣傳影片洗腦,上國語及中國共產黨思想課。先前被拘禁者告訴《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進餐時,他們的唯一選擇非常不人道。他們可以喊:「習近平萬歲!」然後獲得一個包子或一碗飯;或者,他們可以保持沉默,然後飽嘗電牛棒上身的劇痛。「權力就在於把人們的思想粉碎,再把它們拼湊成你選擇的新樣子。」《一九八四》中的反派人物歐布萊恩說。
新疆拘禁營倚賴持續監視與重罰,被洩露的中國政府官方文件中,要求獄方必須確保:「全面影像監視宿舍與教室,完全無死角、無盲點。」遭監禁者就算只是最細微的違規,也可能導致他(她)被拘禁的期間延長,「你進入拘禁營時是一千分,無法再得分,但若你打呵欠或微笑,就會扣分。」一位倖存者解釋35:「一旦低於五百分,你就得被多拘禁一年。」這是一種旨在傷害、只往下扣分的制度,你無法靠提高分數而獲釋,只能靠著減少扣分來走出拘禁營。
就算走出中國的勞動營也沒有自由。遭監禁者返回社區後,仍然被鋪天蓋地的監視器及公安所監控。在使用惡意軟體監視維吾爾族的手機多年後,中國政府的方法與手段更是變本加厲,它規定維吾爾族必須安裝用於監視自身所在地、電話及簡訊的應用程式,還必須呈報「健康檢查」——包括抽血及DNA樣本,以貢獻給中國不斷擴增的生物特徵資料庫。
中國採取數位鎮壓和低科技監控手段雙管齊下,嚴禁那些維吾爾族穆斯林留鬍子和戴面紗,除了「少數民族特徵偵測」,中國的監控設備製造商還在其下的人臉分析中提供「鬍鬚偵測」。剝除維吾爾族的身分認同後,中國政府還不罷手,在每天的「反恐」安全訓練中,讓他們跟一個無形、虛構的敵人戰鬥。這「敵人」看起來就像他們以往的自身,但被誇張地扭曲成一個陰暗的人物。
致力於消滅維吾爾族身分的同時,中國當局也拆毀維吾爾族文化信仰中心的實體場所。喀什市是歷史悠久的貿易站,有許多維吾爾族的聖地,該市最古老的建築在二○○九年被摧毀,而中國當局聲稱這是為了地震安全考量。偏執的中國當局還把有幾百年歷史、維吾爾族做禮拜的艾提朵爾清真寺(Id Kah Mosque)轉變成旅遊景點,一個向世界展示與宣傳中國尊重穆斯林宗教自由的樣板。喀什市到處都有檢查站監視個人行動,把監視資料輸入詳細記錄他們家庭、教育及以往活動的資料庫裡。
新疆的綠洲城市和田市,幾世紀以來都是繁榮貿易樞紐,也是維吾爾族朝聖者的聚集地。現在,進入此市集必須做臉部掃描,並出示身分證。和田市廣場上有座維吾爾族農民暨政治人物庫爾班‧土魯木(Kurban Tulum)和毛澤東握手的雕像。離這雕像不到一千六百多公尺處,有一座具千年歷史的維吾爾族蘇爾坦公墓,在二○一九年被中國政府挖掘後夷平。中國官方聲稱這是為了發展,並且表示:「為全市市民提供一個廣闊優美的環境。」被夷平之地,有部分成了停車場。
在《一九八四》中,主角溫斯頓問道:「你發現了沒有,從昨天的過往,實際上全都被消除了?……每一個紀錄都被摧毀或竄改,每一本書都被改寫,每一幅畫都被重畫,每座雕像、每條街、每棟建築都被改名,每個日期都被改動,每天、每分鐘都在進行這種過程。歷史已經停止了,除了無盡的現在,別無其他存在,在這無盡的現在中,黨永遠是正確的。」
中國共產黨想藉由改寫過去來控制未來。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指出,根據衛星影像顯示,自二○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的政策行動已經造成新疆省三分之二的清真寺被摧毀或損壞。那些未被摧毀的清真寺則被裝滿了監視器。海康威視承包的一項工程,是在新疆某個縣、近千座清真寺門口安裝監視器。根據羅雷特的研究指出,光是二○一六年與二○一七年間,海康威視和大華科技就獲得了中國政府超過十億美元的新疆監視器裝設承包合約。
自二○一○年在深圳證交所掛牌上市後,海康威視就一直持續加強它和中國政府的關係與合作。在二○一五年四月舉行的中共中電海康集團有限公司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海康威視董事長致詞時強調,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該公司的事業發展目標整合起來的重要性。幾週後,習近平來到海康威視總部,視察產品及研發中心,告訴該公司員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指日可待。」那年年底,中國政府就為海康威視提供了三十億美元的信用額度。
中國的監控業巨人也受惠於美國的科技與投資。海康威視從輝達公司(Nvidia)購買可編程晶片,用於訓練其人工智慧演算法;該公司也聲稱和英特爾(Intel)、索尼(Sony)、威騰電子(Western Digital)合作。威騰電子在二○一九年初的貿易展廣告中,還宣傳它跟海康威視有合作關係。希捷科技(Seagate)在二○○五年與海康威視共同發布,推出稱為第一款專門針對監控設備開發的硬碟機。當希捷在二○一七年宣布推出第一款為人工智慧監控系統開發的硬碟機時,該公司還引述海康威視、大華科技及宇視科技這三家公司代表的話,「作為策略夥伴,希捷的先進技術將幫助大華科技在人工智慧領域達到新高水平。」大華科技國內銷售業務中心的總監說。
【摘錄3】_「難忘的恥辱」
中國是太空領域的遲到者,但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證明當軍事及商業利益開始結合時,它能夠快速行動。命名自「北斗七星」的北斗系統計畫,正式啟動於一九九四年,接下來二十五年,中國工程師分三階段來應付建造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挑戰,外國的威脅促使他們加緊腳步向前。
中國聰明地把北斗計畫,裝扮成純粹良善的公共財,以及它重返創新前鋒的例子。中國甚至在二○一九年六月時,於奧地利維也納國際中心,舉辦了一場中國導航展。這場主題為「從指南針到北斗」(From the Compass to BeiDou)的展覽,選在聯合國年度衛星研討會的幾個月前舉行,彰顯中國對導航與計時系統的貢獻。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副主任馬加慶,在開幕式中致詞時說:「我們想展示導航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以增進人們的了解。」
但是,跟美國的GPS系統一樣,中國的北斗系統的發展,有其軍事根源。中國在一九七○年發射其第一顆人造衛星——以毛澤東主義革命頌歌〈東方紅〉為命名的「東方紅一號」,其重量遠大於蘇聯、美國、法國及日本這四個國家分別發射的第一顆衛星的重量總和。它只有基本功能,設計主要是為了收集遙測數據、傳回地球。但是,這顆衛星振奮了中國的雄心,在其二十八天的短暫壽命中,循環廣播〈東方紅〉樂曲。
中國投資於太空及其他戰略性技術,在一九八六年三月獲得動能。當時,中國四位知名的戰略武器科學家,聯名寫了一封建議書給鄧小平。他們在建議書中強調,科技發展事關國際國力競爭,並且警告,若中國繼續漠不關心,將會落後。鄧小平只花了兩天就決定,他在建議書的複製本上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請找專家和有關負責同志,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做決斷,不可拖延。」
一九九○年代,兩事件凸顯了美國在太空領域的力量及中國的弱點。第一個事件是波灣戰爭,這讓GPS在戰場上做出驚人展示,中國軍官觀看美國使用其太空能力來瞄準、收集情報和戰場通訊。「這次戰爭的實踐表明,電子戰已成為現代聯合戰役首要的作戰方式,」中國軍事期刊後來寫道:「太空戰場的正式亮相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更顯中國的弱點。此危機始於一九九五年,在美國國會的協助下,台灣總統李登輝不理會中國的壓力,前往康乃爾大學演講。隨著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日期逼近(現任總統李登輝為候選人之一),中國宣布進行大規模軍演,並朝東海發射三枚飛彈,距離一個台灣軍事基地僅約十六公里。
第一枚飛彈命中目標,第二及第三枚飛彈射偏。多年後,一名已退役的中國解放軍上校把這失敗歸因於美國關閉GPS訊號所導致,「這對解放軍來說是莫大的恥辱……難忘的恥辱,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下定決心,要開發自己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及定位系統的原因,無論花多少錢,」他在二○○九年告訴《南華早報》:「北斗對我們是必要,我們從慘痛教訓中學到這點。」
為了改進衛星能力,中國當時已經尋求美國公司,包括羅拉太空與通訊(Loral Space & Communications)及休斯電子(Hughe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幫助解決近期一連串發射失敗的問題。根據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九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這些美國公司的協助與建議,改善了中國的長征火箭。美國政府後來對這些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外洩重大關鍵技術的美國公司處以罰款,國會也縮減對中國出口衛星的限制,但已經太遲,中國已經取得衛星的關鍵技術,包括設計及導引系統的改進。
中國在二○○○年發射了第一顆北斗衛星,就在此時,中國軍方開始論述,太空是在所有其他領域發動戰爭的重要環節。當然啦,中國仍繼續堅稱北斗衛星計畫與中國的其他太空活動都是以和平為目的。二○○三年九月,中國加入歐盟的伽利略定位系統(Galileo Positioning System)計畫,二○○三年十月,中國外交部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方願意按照平等互利原則積極參與伽利略系統的開發和未來的應用。」
參與伽利略系統計畫,為中國提供了改進北斗系統的捷徑。中國和歐盟合作簽署的十二紙合約,迄今都未公開。中國負責製造與測試有關於訊號干擾、衛星定位、地面接收等功能的技術。中國科學家透過參與,取得了和歐洲科學家共事的更好通路。這也讓中國得以購買原子鐘,進行逆向工程,這是導航系統中關鍵至要的元件。另一方面,中國對伽利略系統計畫投資的二億二千八百萬美元,實際上是花在中國公司身上,這些中國公司保有硬體及智慧財產的所有權。
中國在二○○七年完成北斗計畫的第一階段,成功發射了第四顆衛星。一個衛星導航系統要啟用,起碼需要四顆衛星。這系統主要覆蓋中國領土,性能上大致是實驗性質,但中國已經做出了大躍進。它現在已有基本要素,展示了能夠正確地結合它們,並把最終成品送到太空。
中國從此開始奔向覆蓋全球的目標,到了二○一二年年底,北斗系統已有十六顆衛星在軌道上,開放商業使用,服務中國及鄰近的亞太地區國家。二○一八年,中國增加了十八顆北斗衛星,達成全球覆蓋。這一年,中國完成成功發射任務的次數位居全球國家之冠,這是中國太空計畫史上頭一次寫下的紀錄。「從今往後,無論你走到哪裡,北斗都會一直陪著你。」北斗計畫發言人冉承其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說。
推動完成北斗系統時,中國結合了太空及網路能力,著眼於贏得未來的戰爭。二○一五年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戰略支援部隊:負責把太空、網路及電子作戰能力整合成軍事行動的新組織。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有了單一組織,負責中國軍事規畫者所謂的「信息支援」(資訊支援)及「信息優勢」(資訊優勢)。這可以使人民解放軍在衝突中運作,同時也能夠癱瘓敵人的系統。翌年,中國發布《二○一六年中國航天活動白皮書》,宣布意圖在二○二一年前完成「穩定可靠的航天基礎設施」。
中國的北斗系統,甚至在一些層面上表現優於GPS。在亞太地區,它比GPS更準確,但全球來說,它的準確性稍遜於GPS。它的衛星占用較少的軌道平面,維修因此較容易,這受惠於它從更早建立的衛星導航系統中所學習而得的知識。北斗系統也讓使用者可以傳送簡訊,它的較大足跡提高其可得性,根據《日經新聞》(Nikkei Asia)報導,在一百六十五個首都城市,北斗衛星提供的覆蓋面積比GPS更廣。
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得的北斗系統服務還要更強大,它提供十公分的定位精度,而且使用時毫不浪費時間。二○二○年八月,人民解放軍在監視台灣海峽活動的東部戰區,為其地面部隊部署了裝備北斗功能的火箭系統,次月,中國在台灣海峽的海空聯合軍演時,可能也已經測試了使用北斗系統的軍武的能力。人民解放軍沒忘記二十五年前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