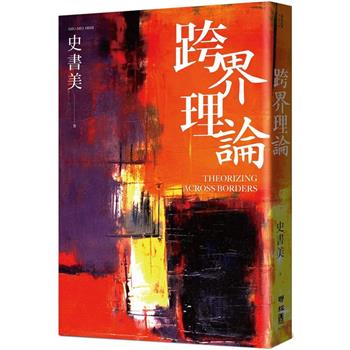近來,文學研究界在處理全球化問題時,大致上企圖找出當代文學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糾纏關係。這樣的研究企圖,是要為一種嶄新的文學「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命名——在此的「結構」一詞,強調各地各種的文學整合併入一個世界體系(world system);而「感知」一詞,顯示文學生產過程利用新的形式、新的風格、新的文類來呈現新的情感(affects)。文學的全球化其實早有前身——那就是「 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的觀念。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首先在一八二七年提倡了「世界文學」,後來「世界文學」的觀念又被人拾起。「世界文學」一詞具有歐洲本位主義的血統(Eurocentric origins),所以當下許多學者在重談「世界文學」舊調時,都至少在口頭上為「世界文學」漂白撇清;只可惜,她/他們卻很少進而分析歐洲本位主義(Eurocentrism)所講究的尊卑次序(hierarchies)以及不平等狀態(asymmetries)。薩依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一書中特別評析了歌德——《東方主義》甚至是很多年前的舊書了——但是當今學者對於歐洲本位主義的批判卻不見得進步了多少,反而欲振乏力。彷彿學者在遇見歐洲本位主義時,只需要表示「我並沒有忽視歐洲本位主義喔」,就已經盡了道義,而不需要進一步做些什麼——彷彿學者對於歐洲本位主義根本無可奈何。在看待文學的全球化議題時,許多學者並沒有直接鑽研問題,而只是向問題點頭示意而已;這種「反正我也看見歐洲本位主義了」的「認可」(recognition)動作,只是迴避問題的方便手段;學者在亮出這種虛張聲勢的警示手勢之後,好像就可以推開研究倫理的路障,安然踏上全球化的文學研究之路,向全球文學大步邁進。
學術界一方面已經對後殖民批評失去興趣,另一方面又擔心玩不出新花招,所以就不斷尋求新的理論、新的典範、新的點子。但是,學術界這種喜新厭舊的心情並無法滌除一個惱人的事實:歐洲本位主義——或西方本位主義——仍然存在。歐洲本位主義的存在形式有新也有舊。如果有人仍然堅持繼續剖析歐洲本位主義,這樣的人免不了被人嫌棄、被人說是在炒冷飯、被人說玩不出新把戲。可是,此時經濟的、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越來越興旺,這樣的現象誘發出「全球文學」(global literature)的新觀念;既然以前歌德提出來的「世界文學」需要被檢討,那麼「全球文學」也該被研究。在此,不能不提「認可的機制」——這種機制將某一些文學列入世界文學的行列,但這種選擇性的,甚至專斷的認可機制,卻同時忽視了另一些文學,如某些在地文學、漂泊離散文學、弱勢族群文學、小國的文學等等。認同機制大致上貼合了、加入了幾種尊卑次序,如國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語言優勢等的尊卑次序。我在此所指的機制(technology),是借自於德.羅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的觀念;而德.羅瑞提斯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改寫傅柯(Michel Foucault)筆下的機制。我將機制置於兩種場域之中:一是跨國的場域,場域中奔騰的權力政治是跨文化的;另一場域是國族的場域,場域中的權力政治是各種族之間的、各文化之間的。我所指的機制,包括了繁多的論述,各種機關的運作,學院生產,大眾媒體,以及其他可以創造觀念、仲裁觀念的「再現」(representation)形式。所以,「認可的機制」指的是論述意識/論述潛意識之中的運作機關,以及這些運作機關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理解/誤解。認可的機制,將「西方」視為認可的主體,而將西方之外的世界視為認可的客體,將客體封存於「再現」之中。
這裡,我的焦點放在兩種認可的機制上:一種是學術論述,另一種是文學市場。這兩種機制和其他的認可機制並非無關,但我認為這兩種機制特別值得注意:它們看起來似乎很複雜,卻驚人地始終如一。我發現在這兩種認可的機制中,有五種既獨立又相關的特徵。我首先要分析的兩種特色——「體制的復活」(the return of the systematic)與「寓言的時差」(the time lag of allegory)——雖然具有明顯的問題,卻不容忽視。非西方的文學以及弱勢族群的文學,幾乎只在區域研究和族裔研究的領域之內才會被重視,而能夠在區域研究、族裔研究之外受到注意的文本則少之又少。在極少的例子之中,即可發現上述「體制的復活」、「寓言的時差」兩種特色。大部分理論家仍然在生產歐洲本位主義的、以不變應萬變的理論,而將「乍看遙遠」(seemingly distant)的領域置之不理。其實,「乍看遙遠」的領域並不遙遠,反而造就了歐洲本位的、放諸四海皆準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價值。如果將西方之外的國度、將弱勢族群置之不理,就陷入莎拉.阿梅(Sara Ahmed)所指的「距離妄想」(fantasy of distance)。我就談一件顯而易見卻常被人忽視的事吧:有什麼動作比「認可」更早發生?有什麼比「認可的政治」更暴烈?答案是:全然忽視,以及假裝無知。忽視「他者」(the other (s)),對「他者」無知,並非天真無邪的;忽視和無知,是新殖民時期知識生產過程的基礎,是全球性知識分工體系的根。緘默,未必是被動的,而也可能是強而有力的;強而有力的緘默,遮掩了忽視和無知,拒絕認可五花八門的他者。而拒絕認可他者的手段,就只是簡單的否認動作而已。這個否認他者的動作,直到至今還沒有被充分分析。這個否認他者的動作,仍然跨騎「西方/非西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強勢族群/弱勢族群」等等分界,維持、製造尊卑次序的知識。早在西方本位主義的「再現」政治、認可政治進場操作之前,沉默和無知就已經在這些分界上頭作祟。在製造知識的場域,眾人都向中心看,而研究非西方文學、弱勢族群文學的學者處於這個場域的邊緣。這樣的邊緣學者,也處於尊卑次序的低處。這種比較邊緣的學者經常要和學科比較主流的學者抗爭。學科比較主流的學者——出於「好」意——經常用低於自己學科水平的標準,去看待比較邊緣的研究對象。這種大方的學者抱持雙重標準:在面對非西方、弱勢族群文本時,就忍不住採用比較鬆散的評估標準;而在面對經典文本時,又改用原本信奉的高標準。這種大方,其實是假平等。
這一章並且要指出,主體建制過程(subjectivization)的機制有很多種,而黑格爾主義的認可觀念只是其中一種機制而已。許多人認為,黑格爾的認可觀念充分主宰了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辯證過程,但我反對這種偏袒黑格爾的觀點。許多討論認可的學者接受黑格爾的「主人/奴僕」的辯證觀,進而將這種辯證觀用來詮釋自我/他者的關係。在黑格爾辯證模式中,主體性被簡化了,只須處理主體/客體之間的二元對立,只須處理二元對立的「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可是,客體的主體性(且讓我採用乍聽矛盾的說法)並不是全然由主體/客體的關係來決定。就算「臣服」(subjection)這個動作對於主體性具有重大的意義,客體對於單個主人的臣服動作並不該全然決定客體的主體性——客體的主體性,應該還有別的決定因素。如果將相互主體性視為一個場域,那麼場域裡的關係錯綜複雜,沒有人只對應單個主體或單個客體,而該同時對應許多主體、許多客體。非西方並不該僅僅只是西方的鏡中倒影;非西方的成形過程中,還有許多西方之外的其他因素加入攪和。
同理,弱勢族群如果要立足,並不是只靠強勢族群的認可(或強勢族群的不認可);弱勢族群和許多主體、許多客體有關,更和其他弱勢族群相呼應。認可,並不能涵包一切。有些人一直巴望被認可,結果這些人就被認可的機制給套牢了,陷入「壓迫之病」(pathology of oppression)裡頭。這些企求被認可的人,可能反而廢盡武功,只淪為認可機制的水中倒影。換句話說,主體/客體的相互關係固然操作了認可機制,但是這種兩方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不至於決定一切——畢竟,場域中的玩家絕對不只「兩」方。對話式的相互主體性,向來都不是只發生在「兩」方之間而已。雖然西方多多少少決定了非西方看待自我的方式,而強勢族群決定了弱勢族群看待自己的方式,但是這種來自西方、來自強勢族群的力量,並非強大到決定一切的程度。在西方之外,在強勢族群之外,總有別的空間可以容納不一樣的相互辨認關係(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不一樣的身分認同(identity),甚至不一樣的「去認同」(disidentification)。
在此,我認為學術論述和文學市場的認可機制特徵,至少有以下五種:「體制的復活」、「寓言的時差」、「全球多元文化主義」(global multiculturalism)、「鶴立雞群的土產」(the exceptional particular),與「後差異的倫理」(postdifference ethics)。當然,認可機制的特徵並不是只有這五種而已。希望我選出的這五種特徵可以或多或少曝顯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現象的世界文學之多重斷層線。
學術界一方面已經對後殖民批評失去興趣,另一方面又擔心玩不出新花招,所以就不斷尋求新的理論、新的典範、新的點子。但是,學術界這種喜新厭舊的心情並無法滌除一個惱人的事實:歐洲本位主義——或西方本位主義——仍然存在。歐洲本位主義的存在形式有新也有舊。如果有人仍然堅持繼續剖析歐洲本位主義,這樣的人免不了被人嫌棄、被人說是在炒冷飯、被人說玩不出新把戲。可是,此時經濟的、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越來越興旺,這樣的現象誘發出「全球文學」(global literature)的新觀念;既然以前歌德提出來的「世界文學」需要被檢討,那麼「全球文學」也該被研究。在此,不能不提「認可的機制」——這種機制將某一些文學列入世界文學的行列,但這種選擇性的,甚至專斷的認可機制,卻同時忽視了另一些文學,如某些在地文學、漂泊離散文學、弱勢族群文學、小國的文學等等。認同機制大致上貼合了、加入了幾種尊卑次序,如國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語言優勢等的尊卑次序。我在此所指的機制(technology),是借自於德.羅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的觀念;而德.羅瑞提斯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改寫傅柯(Michel Foucault)筆下的機制。我將機制置於兩種場域之中:一是跨國的場域,場域中奔騰的權力政治是跨文化的;另一場域是國族的場域,場域中的權力政治是各種族之間的、各文化之間的。我所指的機制,包括了繁多的論述,各種機關的運作,學院生產,大眾媒體,以及其他可以創造觀念、仲裁觀念的「再現」(representation)形式。所以,「認可的機制」指的是論述意識/論述潛意識之中的運作機關,以及這些運作機關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理解/誤解。認可的機制,將「西方」視為認可的主體,而將西方之外的世界視為認可的客體,將客體封存於「再現」之中。
這裡,我的焦點放在兩種認可的機制上:一種是學術論述,另一種是文學市場。這兩種機制和其他的認可機制並非無關,但我認為這兩種機制特別值得注意:它們看起來似乎很複雜,卻驚人地始終如一。我發現在這兩種認可的機制中,有五種既獨立又相關的特徵。我首先要分析的兩種特色——「體制的復活」(the return of the systematic)與「寓言的時差」(the time lag of allegory)——雖然具有明顯的問題,卻不容忽視。非西方的文學以及弱勢族群的文學,幾乎只在區域研究和族裔研究的領域之內才會被重視,而能夠在區域研究、族裔研究之外受到注意的文本則少之又少。在極少的例子之中,即可發現上述「體制的復活」、「寓言的時差」兩種特色。大部分理論家仍然在生產歐洲本位主義的、以不變應萬變的理論,而將「乍看遙遠」(seemingly distant)的領域置之不理。其實,「乍看遙遠」的領域並不遙遠,反而造就了歐洲本位的、放諸四海皆準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價值。如果將西方之外的國度、將弱勢族群置之不理,就陷入莎拉.阿梅(Sara Ahmed)所指的「距離妄想」(fantasy of distance)。我就談一件顯而易見卻常被人忽視的事吧:有什麼動作比「認可」更早發生?有什麼比「認可的政治」更暴烈?答案是:全然忽視,以及假裝無知。忽視「他者」(the other (s)),對「他者」無知,並非天真無邪的;忽視和無知,是新殖民時期知識生產過程的基礎,是全球性知識分工體系的根。緘默,未必是被動的,而也可能是強而有力的;強而有力的緘默,遮掩了忽視和無知,拒絕認可五花八門的他者。而拒絕認可他者的手段,就只是簡單的否認動作而已。這個否認他者的動作,直到至今還沒有被充分分析。這個否認他者的動作,仍然跨騎「西方/非西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強勢族群/弱勢族群」等等分界,維持、製造尊卑次序的知識。早在西方本位主義的「再現」政治、認可政治進場操作之前,沉默和無知就已經在這些分界上頭作祟。在製造知識的場域,眾人都向中心看,而研究非西方文學、弱勢族群文學的學者處於這個場域的邊緣。這樣的邊緣學者,也處於尊卑次序的低處。這種比較邊緣的學者經常要和學科比較主流的學者抗爭。學科比較主流的學者——出於「好」意——經常用低於自己學科水平的標準,去看待比較邊緣的研究對象。這種大方的學者抱持雙重標準:在面對非西方、弱勢族群文本時,就忍不住採用比較鬆散的評估標準;而在面對經典文本時,又改用原本信奉的高標準。這種大方,其實是假平等。
這一章並且要指出,主體建制過程(subjectivization)的機制有很多種,而黑格爾主義的認可觀念只是其中一種機制而已。許多人認為,黑格爾的認可觀念充分主宰了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辯證過程,但我反對這種偏袒黑格爾的觀點。許多討論認可的學者接受黑格爾的「主人/奴僕」的辯證觀,進而將這種辯證觀用來詮釋自我/他者的關係。在黑格爾辯證模式中,主體性被簡化了,只須處理主體/客體之間的二元對立,只須處理二元對立的「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可是,客體的主體性(且讓我採用乍聽矛盾的說法)並不是全然由主體/客體的關係來決定。就算「臣服」(subjection)這個動作對於主體性具有重大的意義,客體對於單個主人的臣服動作並不該全然決定客體的主體性——客體的主體性,應該還有別的決定因素。如果將相互主體性視為一個場域,那麼場域裡的關係錯綜複雜,沒有人只對應單個主體或單個客體,而該同時對應許多主體、許多客體。非西方並不該僅僅只是西方的鏡中倒影;非西方的成形過程中,還有許多西方之外的其他因素加入攪和。
同理,弱勢族群如果要立足,並不是只靠強勢族群的認可(或強勢族群的不認可);弱勢族群和許多主體、許多客體有關,更和其他弱勢族群相呼應。認可,並不能涵包一切。有些人一直巴望被認可,結果這些人就被認可的機制給套牢了,陷入「壓迫之病」(pathology of oppression)裡頭。這些企求被認可的人,可能反而廢盡武功,只淪為認可機制的水中倒影。換句話說,主體/客體的相互關係固然操作了認可機制,但是這種兩方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不至於決定一切——畢竟,場域中的玩家絕對不只「兩」方。對話式的相互主體性,向來都不是只發生在「兩」方之間而已。雖然西方多多少少決定了非西方看待自我的方式,而強勢族群決定了弱勢族群看待自己的方式,但是這種來自西方、來自強勢族群的力量,並非強大到決定一切的程度。在西方之外,在強勢族群之外,總有別的空間可以容納不一樣的相互辨認關係(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不一樣的身分認同(identity),甚至不一樣的「去認同」(disidentification)。
在此,我認為學術論述和文學市場的認可機制特徵,至少有以下五種:「體制的復活」、「寓言的時差」、「全球多元文化主義」(global multiculturalism)、「鶴立雞群的土產」(the exceptional particular),與「後差異的倫理」(postdifference ethics)。當然,認可機制的特徵並不是只有這五種而已。希望我選出的這五種特徵可以或多或少曝顯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現象的世界文學之多重斷層線。